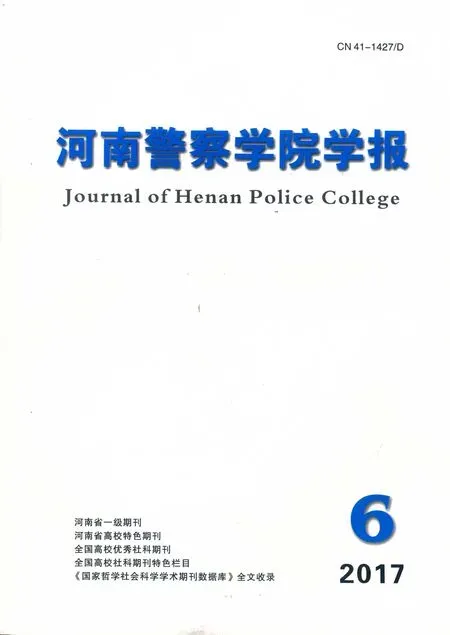论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
张红晓
(河南警察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论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
张红晓
(河南警察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家庭暴力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儿童健康成长,易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公安机关应积极干预家庭暴力。但是因为家暴案件自身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反复性,目前公安机关的干预行为存在执法力度不够、制裁措施不力,易入心理误区,调查取证难度大等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应全面界定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完善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归属、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紧密结合社区力量。
家庭暴力; 举证责任; 警察干预
长期以来,家庭之内的暴力和家庭之外的暴力因为一门之隔而被区别对待。家庭之外的暴力会被谴责,国际公权力会及时介入,受害者会得到保护,施暴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家庭之内的暴力常常会被轻描淡写,国家公权力会尽量回避介入,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施暴者也往往会逃避惩罚。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家暴治理首次以专门法的方式被纳入官方立法中。更重要的是,该法全文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公安机关介入家暴案件的必要性。依据该法规定,在家庭暴力发生后,警察是干预家庭暴力最早的公权力形式,公安机关在处置家暴工作中承担着预防、出警、取证、调解、处罚等多重职责。该法实施一年多来,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具体的时间、方式、程序、限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研究并着力解决这些困境对于推进规范反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权的行使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必要性
(一)家庭暴力的危害严重
家庭暴力使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严重者直接威胁生命,受害方因为恐惧、孤立无援会长期屈从于施暴方的意愿。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对心理上的伤害往往更残酷,可能终生无法治愈和康复。
对家庭来讲,家暴影响夫妻感情,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25%的家庭因此解体,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1]。处在持续长期家庭暴力状态中的儿童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性格会偏向消极、孤僻、残忍、冷漠,易致人格扭曲,大大增加了他们长大后成为施暴者或受暴者的可能性。
对社会来讲,一方面家暴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不同程度会导致治安案件甚至是残忍血腥的刑事案件。“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使许多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作出的选择往往是沉默和忍耐,在忍无可忍时会自残、自杀,或者以暴制暴等。2010年发生的四川李彦因家暴杀夫案,就是在遭受严重家暴之后没有获得有效帮助而以暴制暴的典型案例。受害者通过杀死施暴者来终止这种暴力循环,让自己摆脱暴力控制,最后自己也付出了被判决死刑的代价;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大大增加社会成本,包括对受害者身体伤害的治疗、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辅导、暴力对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所付出的代价等等[2]。
(二)家庭暴力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反复性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施暴者存在着通过暴力伤害达到目的的主观故意,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私人环境中,行为隐蔽,暴力的发生常常不为人所知。受害者处于危险环境中的时间较长,暴力发生时受害者常处于无防备状态。家庭暴力的发展有螺旋式重复的特点,施暴者在施暴后不断自我谴责、悔恨、发誓悔改,受害者满怀希望、原谅、接纳,之后施暴者继续施暴……在暴力—和解—再次暴力—再次和解周而复始的循环重复中,双方的误会、矛盾和仇恨一次次积累、释放、爆发,暴力周期间隔缩短,暴力程度逐渐升级。无数案例显示,家庭暴力通常不会自动终止,除非有外部公共力量介入进行强制性干预。
2009年因家暴死亡的北京姑娘董珊珊案件就是个惨痛的例子。董珊珊结婚十个月,无数次遭遇丈夫王光宇的残酷殴打,期间她及家人曾八次报警控诉丈夫的暴力行为,也曾提起过离婚诉讼,但是所有努力都逃不过死亡,直到她在医院病危,其丈夫才被刑拘,这却是他第一次因家暴面对警察[3]。如果董珊珊在第一次报警时警察就能介入进行强制性干预,而不是消极地怠慢和姑息,事件不至于到这样无可挽回的结果。
(三)公安机关是干预家庭暴力的最早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举报者会选择打110报警,警察自然而然成为干预家庭暴力的首个外部力量,也成为对家暴案件情况最熟悉的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最原始和完整。警察在老百姓眼中代表着政府,会对施暴者有一定的威慑力,使家暴干预积极而富有成效。
即时强制权是警察权的特有权利,危险正在发生时,警察可以动用强制力及时消除。施暴者和受害者处于水火不容的强对抗关系,非常容易对某一方的身体、精神、生命造成伤害,这样显然需要强制性力量平息对抗,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警察的即时强制权成为制止这种暴力的必要权力。
二、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现状分析
(一)警察干预家暴的态度存在偏差
目前虽然很多警察认识到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但是警察职责范围限于公共领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对很多执法者来讲,限于家庭内部的家暴行为属于私事,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公共领域的安全而不及于家庭。受“床头打架床尾和”“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影响,对于家暴类报警,民警容易和普通家庭纠纷混淆,出警不及时不积极,出警后也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处理目标定位仅仅满足于暂时阻止事态升级。这样只会导致施暴者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受害者也会失去对警察的信任[4]。
还有些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时,不能正确定位警察角色。在了解到受害方本身存在过错,比如出轨、不孝、不良习惯等情况下,就会认为施暴者的暴力行为是情有可原的,就会不自觉把情绪带到处置现场,在语言、方式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受害方更为孤立无援。警察这样做其实是混淆了自身角色,更多情况下把自己看成一个“情况处理者”而非执法者。警察是规则的执行者,是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是非的判断者,受害方的任何错误都不是施暴者进行家庭暴力的理由。警察根据受害方意愿并依法处理案件后,可以告知施暴方正确的处理方式:先是充分沟通,无效后可以分居、起诉离婚等,但施暴是最不应该的方式。
(二)执法力度不够,制裁措施不力
我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执法环境使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问题时采取非常谨小慎微的态度,在需要采取强制手段、处罚措施时畏手畏脚,从而放纵了施暴者。
在暴力程度轻微未达犯罪程度的情况下,民警常用治安调解来作为干预手段,绝大多数家暴案件会在民警主持下进行调解。这种调解的约束力度通常较弱,因为第一,调解以“和谐”为精神内涵,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主要方式,以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为初衷,所以调解更适合于普通家庭纠纷,对于家庭暴力这样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来说过于温和。第二,警察在调解过程中的身份也发生变化,由管理者执法者的身份转化为居中调和的第三方身份,调解的权威性极大减弱,对施暴者的威慑作用不够;第三,按照惯常的调解方法,民警会希望双方都作一定程度的让步,以便达成协议。受害方也会被要求反思自身错误,只好被动妥协,承认错误,双方口头或书面达成协议下次不会再犯;第四,在“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调解形势下,施暴方会产生投机心理,降低了他们违法的预期成本,认识不到自己暴力行为的危害性,会形成受害方也有错就该打的错误认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地应付警察调解,实质上纵容了下一次家暴的发生,情况只会愈来愈糟,进入周而复始的暴力循环。
《反家暴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告诫制度是一项新制度,旨在通过正式的书面形式对施暴人进行批评诫勉,防止家暴进一步升级。这项制度也成为多数警察乐于采取的处置方式,但是实践中发现,告诫制度和调解一样效力十分有限,在施暴方和受害方一次次的心理博弈下,所有的宽容都成为激发下一次家暴的种子,调解达成的协议和告诫书的内容也都成了一纸空文。
(三)家庭暴力案件的不告不理
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禁止家庭暴力,但是这些规定很零散且极为原则性,操作起来很困难;反家庭暴力法发布实施后,在预防、认定、救助、处罚、程序方面有了较为明晰的规定,但是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只有发生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时,家暴案件才会作为公诉案件处理。受传统的处理方法影响,警察在面对情节不够严重的家暴案件时,都会将其视为自诉案件,告知受害者自己到法院去起诉。
这种不告不理的做法使受害方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家暴案件中受害方基本都处于极弱势的状态,可能为了维系家庭关系、子女成长等原因,也有可能是受到施暴者的威胁、强制等原因不愿或不敢提出请求。虽然《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都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完全代替当事人,仍要遵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受害方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老人、儿童,这一困境就尤为突出,施暴者往往是法定监护人的角色,是要由其代为诉讼的,谁会把自己送到审判席呢?
(四)调查取证难度大
因为家暴行为具有隐蔽性,暴力多发生在私人场合且发生在具有亲属身份和亲属关系的成员之间,公安机关出警时暴力往往已经结束,很难取到直接有效的证据。受害人长期被控制,处于恐惧、软弱、被动的状态下,其举证能力会有所减弱或丧失,除了伤情鉴定外,很难提供更充足的证据。在警察干预后,受害人态度又容易反复,立场不坚定,证据程度弱。举报者或目击者通常只能提供较为间接的证据,证明力较弱,无法形成证据链条。
另外,如果是夫妻一方遭遇家庭暴力,必然会涉及极其隐私的个人问题,此时的家庭状态通常是不堪入目、一地鸡毛,取证时当事人会选择不配合;如果是老人或孩子遭遇家庭暴力,会由于行为能力、语言表达等问题而由成年人代为描述和表达,其中真相会被淡化或抹杀,依然无法获得有效证据。
三、我国公安机关有效干预家庭暴力的对策探讨
(一)全面界定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
美国最初也是采取“清官不断家务事”的放任模式和温和手段来处理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的数量、规模未得到任何控制,反而愈演愈烈。事实最终证明:法律不仅使受害人懂得了在面对暴力时如何自救,更为警察提供了坚实的行动依据。在公安机关第一次介入家暴事件时,态度应非常明确,让施暴者明白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让其反思及时接受教训,而不是急于让受害方退步来缓和关系。警察在运用调解时应保持高度谨慎,切勿高估调解的作用。民警应坚持以受害者为中心,要像对待其他犯罪行为一样来对待家庭暴力,要及时对施暴者采取必要措施,杜绝“和稀泥”“劝和不劝离”“尽快平息事态”等心理。
加拿大《家庭暴力法》规定:妇女受到暴力威胁时,可随时向警察求救,即使未获当事人允许,警察也可以破门而入,并带走施暴者,限定施暴者一段时间内不得回家,直到警方认为结束暴力威胁为止[5]68-74。我国相关法律未赋予警察这么大的权利,但是《反家庭暴力法》也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规定.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应对施暴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知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相应的后果;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对于夫妻间暴力行为可基于受害方的意愿考虑是否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受害方为老人和儿童的,应及时给予处罚,防范和制止事态扩大;如果涉嫌犯罪行为,应及时采取带离现场、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震慑施暴者。
(二)完善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归属
加拿大《家庭暴力法》《紧急状态保护令》规定:情节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将被提起刑事控诉。审判过程中,受害人仅作为证人参加审判,无提供证据义务[5]68-74。但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属于民法领域,在无特殊规定的情形下,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具体到家暴案件,如前文所述,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举证能力不对等,受害者的举证能力明显减弱或丧失,而目击者或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往往是受害方亲属,因存在利益关系而证明力较弱,这样的举证方式对受害者来说是显失公平的。
为更好保护受害方的权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家暴案件证据体系:1.从受害人角度,可降低证明强度,报警回执、伤害照片、医院治疗证明、悔过书、子女证言等经查证属实后均可作为证据;2.采取隐蔽方式获取证人证言,到合适的地点取证,保护证人身份不被暴露,免除证人的后顾之忧;3.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分配部分举证责任给施暴者,让其提供未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如果施暴者能够提供这些证据,可推定其实施家庭暴力。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举证难的问题,还可以使施暴者因为要承担举证责任而产生畏惧,一定程度上延迟或放弃暴力行为;4.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人身保护令、伤情鉴定等都可以作为法院审判时的证据,美国警察在出警处理家暴案件后都要作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受害人有权要求获取一份该报告的复印件。
(三)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的操作:1.受案出警。公安机关在受理家暴案件的报案后,应立即赶赴现场;2.现场处理、取证。到达现场后,警察应立即中止暴力,隔离当事人,缓和形势。之后简单询问、拍照,大致评估伤情和财物损毁状况,询问目击者、亲属、邻居;3.调解、出具告诫书。调解应谨慎进行,要考虑受害方意愿和施暴方暴力程度,对于受害方不同意调解的、施暴方暴力后果较重的、非初次暴力行为的,均不宜进行治安调解。警察进行调解时,建议同时出具告诫书,对施暴者会有一定的约束作用;4.采取强制措施。很多情况下,调解或劝说并不能制止施暴者的暴力行为,或者不能使施暴者认识到暴力行为的危害性,所以视暴力程度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能够有效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继续。但是因为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仍要考虑被害者的意愿,如果没有被害者的支持,警察采取的强制措施会很难得到认同,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进行后续法律程序;5.协助申请、执行人身保护令。《反家庭暴力法》第四章详细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确无能力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公安机关有义务协助代为申请,同时公安机关有义务协助法院执行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中的内容如果没有具体的执行,就等同于一纸空文,但是具体怎么执行,警察的角色定位,权力的边界等等并没有细化的操作措施,实践中警察对此也处于困惑状态;6.建立家暴处理后的评估、回访制度。科学判断施暴者的危险等级和犯罪风险,借鉴外警24小时回访行动和重复到场制度,确认受害者是否处于危险中,避免家暴的反复和升级[6]。尤其是实施告诫制度的家庭,一次告诫不可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多次回访介入家暴家庭,多次对施暴者进行矫治疏导,才有可能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想效果。
关于以上处置流程,《反家庭暴力法》中都有涉及,但缺乏具体操作程序,对于警察的出警、调解、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包括后期的评估和回访等工作内容没有严格要求和具体标准。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初作尝试,出台了一些家暴案件处理程序的工作规范,但是适用范围很窄。公安部应制作全国性的统一的“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手册”,提供具体工作规程和操作规范,形成程序化、标准化的工作制度。
(四)结合社区力量解决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
预防和制止家暴是需要社会各方联手进行的复杂工程。伴随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居民完成了“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化,社区成了家庭问题的聚集地,很多需要社会干预的问题已转移至社区承担。作为群众基础机构的社区在处理家暴方面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社区应与公安、妇联、司法等加强协作共同开展预防、宣传、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回访监督工作,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多机构合作来干预家暴的发生。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处置家暴案件时,都会采取利用社区与警务机构合作的方法,会吸纳社工人员加入一起研讨、分析个案,警方也会采纳有效建议。
社区便于营造支持家暴受害者,谴责、惩罚家暴施暴者的氛围,比如组织家暴主体的宣传活动,提供家暴方面的法律咨询,吸纳男性参与反家暴工作等。社区民警对社区群众的情况比较熟悉,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比较多,在家暴案件发生报警后,社区民警迅速到达现场,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家暴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把受害者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预防暴力升级。社区民警可依托社区设置临时庇护所,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可开设反家暴培训班,引导居民自觉反对家庭暴力,教育施暴者自省。
前文提到的董珊珊案件中,董珊珊死亡后,其丈夫王光宇被判刑六年,2014年年初服刑四年的王光宇被释放后,结识一个23岁的小姑娘,并与之结婚。可悲的是,王光宇与她的相处模式跟死去的董珊珊一模一样,数次实施虐待伤害,女孩一提离婚,王光宇就扬言要杀她全家[7]。虽然后续事情没有任何跟踪报道,这一消息还是让我们倍感痛心,董珊珊在死亡后已经成了家暴受害者的符号了,而施暴者还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再次结婚重复家暴,这样有过家暴犯罪的人怎么会没有案底?这也反映出家暴案件中评估、回访制度的重要性。英国《克莱尔法案》规定女性对配偶或伴侣是否曾有过家庭暴力行为有知情权,并有权通过警方查询。如果查询申请审查合格且申请者伴侣确有严重暴力史,则警方将在确保合法的前提下,向申请者公开其伴侣暴力前科及相关信息,警方还会派出经过特训的警员及顾问,给予这些潜在的暴力受害者适当帮助[8]。为防止家暴的持续和升级,社区在配合公安机关进行家暴案件的评估回访中有着重要作用。
民警应对社区内的家暴案件建立档案,一方面档案可以成为证明家暴长期性存在的证据,另一方面可以成为受害人起诉时的证据支撑,并且有助于信息的查询。所以完善家暴案件的档案材料,对于保护受害者权利、限制并震慑施暴者有着重要作用。
[1]王琛莹.家庭暴力调查[N].中国青年报,2015-3-25.
[2]欧阳艳文.警察应不应该干预家庭暴力[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1(2):91-92.
[3]茉莉.26岁帝都女董珊珊,婚后10个月家暴致死,终审判决[ED/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907843/ 2012-03-04.
[4]赵敏.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调查和思考[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2):49-54.
[5]高扬.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困境与可行性对策[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7(1):68-74.
[6]周飞.浅谈公安机关介入家暴预防机制的建立[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4):23-25.
[7]李天琪.反家暴立法元年[ED/OL]. 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5-03-25/content-1114726.html.2015-03-25.
[8]英国明年实施克莱尔法案[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3-12-03/content_10720493.html。2013-12-03 06:34:00.
(责任编辑:岳凯敏)
OntheCurrentSituationandCountermeasuresofPolice′sInterventioninDomesticViolence
ZHANG Hong-xiao
(Henan Police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Familyviolence undermines family harmony, influences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causes serious violent incidents.Police should actively intervene in family violence.However, because the case of domestic violence itself has a strong concealment and repeti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ineffective sanctions, easily into misconceptions and difficult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of police.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tervention in domestic violence, improve at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domestic violence proof, form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closely integrate community forces.
familyviolence;burden of proof; police intervention
2017-09-20
河南警察学院2016年度调研课题“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研究”(HNJY-2016-08)的阶段性成果。
张红晓(1973— ),女,河南巩义人,河南警察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刑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治安学。
D631
A
1008-2433(2017)06-01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