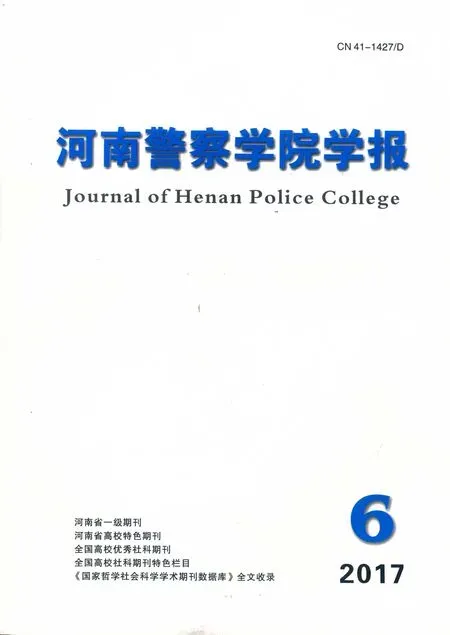刑法微罪扩张的正当性评判与司法适用分析
张平寿,张 凯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2.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矫正教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刑法微罪扩张的正当性评判与司法适用分析
张平寿1,张 凯2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2.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矫正教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微罪立法扩张造成的刑事处罚泛化,压缩了行政处罚的空间,不利于我国现行二元处罚机制的实施,其片面强调刑法威慑而易掩饰行政监管等治理手段的缺位,且刑罚给犯罪人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与微罪本身法益侵害的轻微性极不相适应。实践中应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强化刑法但书规定对微罪入罪的限制功能,确立微罪起诉例外原则,将微罪处置纳入考评机制以引导司法打击向严重刑事犯罪转向,从而缓和微罪扩张导致的对公民自由过于妨碍的紧张态势。
微罪扩张;正当性;司法适用
根据罪行轻重对犯罪进行分类在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多有体现,如法国刑法规定了重罪、轻罪和违警罪,德国刑法将犯罪区分为重罪与轻罪,美国《模范刑法典》将犯罪划定为重罪、轻罪、微罪和违警罪[1]。我国刑法未对重罪、轻罪等进行界定,理论与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刑法》第七条、第八条管辖规定和第七十二条缓刑规定等来看,法定刑为三年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轻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则为重罪,关于“微罪”概念则并无专门限定,通常作为轻微犯罪的代称,实际与“轻罪”概念在同等含义上使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从宽发落多数轻微罪案、突显打击少数严重罪案,主张解构轻刑罪案、推出微罪概念,并将“微罪”定义为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2]。笔者对该微罪概念的内涵表示赞同。将“微罪”脱离于“轻罪”范围而单独界定,不仅有助于强化轻重有别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亦可因微罪、轻罪、重罪之犯罪分层体系的形成,促使立法者更加注重轻微不法行为入刑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考察,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并引领普通公众对轻重有别的犯罪形成不同的内心体验和恰当的处罚预判,进而有利于刑法的实施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然而,考察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变迁,微罪刑事立法虽能一定程度上达到弱化我国刑法失衡的重刑结构之功用,但其持续扩张态势所导致的刑事处罚扩张与泛化,亦使其适用陷入合理性危机。
一、微罪刑事立法及司法处罚的扩张
微罪意指处拘役或其以下之刑的犯罪,其实际可包括二类:其一是刑法明文规定最高刑为拘役的犯罪,笔者称之为法定的微罪,此类犯罪因其法益侵害性总体较轻,立法者对其设定了较轻法定刑,如危险驾驶罪;其二是刑法虽规定最高刑可判处拘役以上刑罚,但根据具体案情却应判处拘役或拘役以下刑罚的犯罪,笔者称之为事实的微罪,此类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行为人具体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如盗窃罪,既可是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也可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亦可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刑罚的微罪。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风险社会法益保护前置化的需求,近些年我国刑法的修正已不再满足于主要围绕罪状与法定刑而展开,而是不断着力于犯罪圈的扩大和刑罚权的强化,微罪在刑法中的设置亦呈加速扩张趋势。一方面,通过大量增设法定的微罪,将部分行政不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圈,彰显刑罚的威慑效应。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开创性地增设了刑法中唯一仅处拘役及罚金刑的危险驾驶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继续以此为效仿,增设了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窃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其刑罚均为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既有犯罪的罪状,扩大其处罚范围,从而形成大量事实的微罪或拓展法定微罪的范围。如《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增设为盗窃罪的要件要素,从而使得上述情形下即使未能窃得任何财物的轻微盗窃行为亦当被作为犯罪处理;删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条文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罪要素,使得该罪由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造成司法实践中即使生产、销售数量极少的假药亦可能受到刑事追究。《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而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等行为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将买卖居民身份证和伪造、变造、买卖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行为予以犯罪化即成立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导致此类犯罪处罚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刑法修正案(九)》还增设了较多量刑幅度仅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的犯罪,如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等,使得大量轻微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而进入刑事处罚圈。
危险驾驶、使用虚假、盗窃身份证件、代替考试等行为的入罪化以及盗窃、生产、销售假药等犯罪之构罪范围的扩大,迎合了当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下通过刑法手段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的社会需求,满足了普通公众基于犯罪案件持续高发而强化刑法打击、维护社会稳定的心理期待。刑事微罪立法扩张在司法上的直接回应是相关犯罪案件的急剧增长。如2012 年全国法院危险驾驶罪案件增加 5.3 万件,同比上升4.38倍;2010年盗窃罪案件本已同比下降4.66%,《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2012年盗窃罪案件因入罪标准放宽而增加3.2 万件,同比上升16.67%;盗窃、危险驾驶案件已分别居各类刑事案件的第一位、第四位[3]。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达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2012年1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4]。此后,这种立法扩张所带来的犯罪上升态势仍在持续。全国法院2014年新收盗窃罪案件21.6万件,同比上升3.8%[5],2015年新收盗窃罪案件224907件,同比上升4%[6];全国法院2014年新收危险驾驶罪案件11.1万件,比2013年上升22.5%[5],2015年危险驾驶案件量较之2014年又上升48.9%,2016年1月至9月此类案件量较之2015年同期同比上升23.8%[7]。显然,伴随微罪立法及其犯罪圈的不断扩大,一般公众面临刑事追诉的概率和风险正在显著上升,特别是危险驾驶、使用虚假身份证件、代替考试、买卖身份证、驾驶证等与公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相关微罪的设立,造成往昔对普遍人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刑事犯罪,如今正变得日益迫近。
二、正当性反思:微罪扩张的价值与效应评判
对于微罪之立法和司法处罚的扩张,理论界存在不同立场。赞同者认为,我国传统刑法立法具有过于注重实害结果的结果本位之偏颇性,片面强调对犯罪的事后惩罚而忽视事前预防,不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安全,应引入危险控制原则,通过刑法提前介入,扩大犯罪圈,加大刑法保护力度[8];对于醉酒驾驶等严重威胁重大法益的危险行为,不能单靠行政制裁手段,更不能等到出现严重危害后果刑法才介入,而应是危险刚出现时刑法即介入,以避免侵害发生和警示国民,实现刑法的预防功能[9];刑法降低入罪标准把一些原本未达刑事处分标准的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是必要的,对于弥补原有刑法规定不足、严密刑事法网具有重要意义[10]。反对者则主张,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犯罪化的同时,应对可以通过行政措施调整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保证刑法在安全与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尽可能避免对公民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11];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彻底打破了“违法”和“犯罪”的分水岭,将原本属于“违法”的行为人为强行提升为“犯罪”而遭受刑事制裁[12];代替考试罪中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过于抽象,存在入罪泛化危险,且该罪的规定并没有必要,属于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界限的模糊,应通过严格考试纪律和实施行政处罚进行遏制[13]。
上述观点或立足于公共安全维护和社会秩序控制而极力推崇刑法微罪的扩张,或基于刑法谦抑、公民自由保障和个人权利张扬而严格限缩刑法处罚的范围。然而,刑法机能的发挥具有双重性,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始终是刑法实施所兼具的机能体现,公民自由与秩序安全亦是刑法立法不可废一的价值追求。故而,若简单地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否认其社会保护机能,或是相反,均有违刑法的自身机能属性,进而不可能在刑法微罪扩张的争辩之间寻求到支持或反对的正当性基础。笔者以为,尽管由于我国刑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使得犯罪圈的设定要较西方国家远为狭窄,社会治安及犯罪案件持续高发亦使公众的秩序安全需求日益高涨,严密刑事法网进行犯罪化以及扩充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手段功能似乎已成势之所迫、理之当然;但在刑事微罪的扩张上,除了需进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机能偏重选择外,我国现行处罚体系、行政规制可能性、入罪评价效应等更应是我们在进行立法设置时需不断加以权衡考虑的因素,理应做到谨慎与克制。
(一)微罪扩张以行为定性为主导,不利于我国二元处罚体制的实施
当前我国对不法侵害的规制体现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衔接的二元处罚体制,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对于法律关系的调控,只有在行政法难以达到规制效果时才予以介入。故对于轻微不法行为一般均以行政处罚进行制裁,只有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进入刑事领域并对其动用刑法手段。为此,不同于德日等国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立法模式,我国刑法对于犯罪的设置采取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即犯罪成立必须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明确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法行为排除于犯罪范围之外。故我国犯罪立法模式的要求决定了犯罪成立要件的设定必须考虑到为行政处罚留下必要的空间,并尽可能地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设置明确的界限,防止因界限的模糊而导致刑事处罚的泛化。
然而,我国刑事微罪的立法设置显然并未围绕二元处罚体制的有效实施而进行。代替考试罪中,只要实施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之行为即可构罪,刑法条文并无关于情节、损害后果等方面之量的要求,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此类违法行为的行政规制完全可能出现虚置化,大量本应予以行政处罚即可的代替考试行为因司法机关从严打击的需要而被犯罪化处理;即使存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对于入罪的限制,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仍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的界限模糊而难显分明,实践中以行政规制可能性为先的二元处罚体系也就必然难以形成。同样的情形也体现于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销售假药等以行为定性化、非量化为特征的入罪立法设置。司法实践中,进入居民封闭式院落盗窃一个价值极低的花盆、未窃到任何财物的扒窃、销售一粒假伟哥等被作为犯罪追究的案例屡见不鲜。显然在侦控机关追究犯罪本能的驱使下,《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已难以发挥其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作用进而对构罪形成阻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行政处罚的萎缩和刑事处罚的扩张,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衔接的二元处罚必然转向为以刑事处罚为重心的一元化处罚。危险驾驶罪设置之前,醉酒驾驶仅属交通行政违法处罚范畴,《刑法修正案(八)》将其入罪并未有任何情节、危害后果等量的要求,其实质亦是对行政处罚空间的剥夺和压制,有违二元处罚有效衔接的机制原理。
(二)微罪扩张片面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易掩盖行政监管等治理手段的缺位
我国刑法近年来微罪的扩张主要以法定犯或行政犯为主,即没有违反伦理道德、只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为犯罪的行为,如危险驾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窃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假药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等。此类微罪设立的主要背景即是相关领域违法犯罪现象日益突显,立法者寄望于通过犯罪化的刑罚惩治来达到有效防范和控制犯罪的效果。如危险驾驶入罪即是因为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等行为呈高发多发态势,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案、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致多人死亡案、杭州胡斌飙车案等危险驾驶恶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应强烈;代替考试罪等的设立即是因为当前教育考试领域作弊现象滋生蔓延,各种“助考”违法犯罪活动多发,并呈现高度的团伙化和产业化。
尽管刑罚通过对罪刑关系实在性的宣示以及对犯罪人权利的剥夺等手段,具有对社会的一般威慑和个别威慑功能,从而有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但希冀主要借助刑罚的威慑效应去减少乃至防范犯罪发生无疑是虚幻的。前述全国2011至2015年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刑罚的确定性比严厉性更有效[14];不让真正的犯罪找到任何安身之地,这是防范犯罪的极有效的措施[15]。行政犯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上升和严重化,往往与行政监管的缺位存在紧密联系。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达13864人,同比上升6.1%,其中行政执法人员6067人,2015年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13040人。引发全国震动的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共有山东等17个省(区、市)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的相关责任人被依法依纪问责,有关方面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暴露出疫苗质量监管和使用管理不到位、对非法经营行为发现和查处不及时、监管和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16]。因而,将轻微不法特别是行政犯领域内的违法行为动辄予以犯罪化处理,将会导致行政执法环节存在的监管不力、乱作为等问题易被忽略,从而使得通过有效行政治理缓解或解决违法现象上升的合理路径,如代替考试的防范通过严格身份审查、健全发现机制,危险驾驶的治理通过加大警力投入、规范执法考核等,因为立法犯罪化的处理而转向刑事威吓,使强化监督体系、深化法制宣传、健全社会自治等防控违法行为的有效方式受到忽视,形成社会治理手段的刑法依赖,这与刑法谦抑性、经济性及保障法等原则属性明显背道而驰。
(三)相较于微罪法益侵害的轻微性,微罪处罚对犯罪人产生的负面效果过于沉重
微罪立法多是源于社会保护需要而使刑法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结果,犯罪一般体现为对法益的威胁而非实害,如危险驾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等,尽管被予以犯罪处理,但仍呈现出行政不法所普遍具有的行为性质及侵害后果轻微之特性。虽然刑法对于微罪刑事责任承担配置的是拘役、管制或罚金等较轻刑罚,实践中亦存在因情节轻微而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似乎在处罚上并无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嫌。然而我国自古至今素有耻刑、耻讼的文化传统,公众对诉讼普遍存在抵触和厌恶情绪,对于成为被告或科以刑罚更是视其为大辱而唯恐避之不及,因而犯罪人的标签一旦标示,不仅会造成行为人自我否定和背负沉重的屈辱感,更意味着日后与自身社会交往圈的渐行渐远及与主流社会的日益隔离,社会也因此而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从我国刑事追诉机制的模型来看,受“严打”刑事政策以及长期以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思维定势的影响,犯罪的刑事追诉一直以圆柱形体现,即侦查与审查起诉环节对犯罪的过滤作用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犯罪在审前并未被过滤掉从而最终被定罪量刑,这与西方国家的漏斗形追诉模型迥异。在日本,警察对其负责侦查的案件可以根据检察官指示实施微罪处分,即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不移送检察机关,2007年有38.2%的成人轻微普通犯罪案件被给予微罪处分[17]。德国起诉法定主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正日益弱化,越来越多刑事案件被以不起诉等方式分流,1981年仅有约19%的案件起诉至法院,到1997年则仅有12%的案件被起诉[18]。而我国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2001年至2010年均保持在2%到3%[19],2013年、2014年、2015年不起诉率分别为3.73%、3.61%、3.52%,*数据系根据2014年、2015年、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整理得出。因此包括微罪在内的绝大多数案件难逃被定罪判刑的命运。由于我国轻罪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并未建立,公民一旦被定罪量刑,除未成年人外,犯罪的标签效应将伴随终身,如被开除公职,丧失担任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资格,不得从事教育、医疗、法律等行业,在工作与生活上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更使子女、父母等亲友遭受非议和就学、就业等方面的不当牵连,带来精神上的极度痛苦。醉酒驾驶、代替考试、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等行为的入罪化,不但与民众一贯视之为轻微行政不法的常理常情不符,更因刑罚负面效应和犯罪标签的无限放大使得此类犯罪的实际惩罚程度远高于其自身罪行的程度,从而在比例上明显不相适应。显然,我国当前刑事处罚的制度设置并未给微罪惩处提供充分的正当性依据和合理空间。定罪科刑的严重负面效果决定了刑罚处罚的对象理当是具有相当程度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多数轻微不法,即使入罪,也应进行适当的审前分流而以非刑罚方法处置为要。
三、现实路径之析:微罪立法扩张的司法适用弥补
尽管我国刑法对犯罪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使得犯罪圈的范围实际远大于德日等西方国家,且伴随社会的进一步信息化、科技化和工业化,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涌现,民众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求持续强化,由此导致刑法保护的触角进一步延伸,犯罪化可能成为今后刑法修订的主要趋势。然而在微罪的扩张上,犯罪化不应成为主流,而应始终保持谨慎与克制,立法、司法者应以刑法作为部门法保障法的价值取向为引领,充分利用我国现行二元处罚体系,强化行政规制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刑法过于介入公民日常行为,保证刑法自由保障机能的实现。法律终究不是嘲笑的对象,“没有不讲理的法,只有不讲理的人”。在当前我国立法已经对刑事微罪设置了构成要件及罚则的情况下,一味指责与批评无疑并非解决之道。笔者以为,在刑法微罪条文的实施中,应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和弹性功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理利用既有规定内容和制度设计,以审前分流为导向实现司法处置的限缩,进而缓和微罪扩张所导致的对公民自由过于妨碍的紧张态势。
(一)强化刑法但书规定对微罪入罪的限制功能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作为法定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犯罪概念定量因素和二元处罚体系的立法反映。尽管理论界对于但书的功能定位、但书可否作为出罪的直接根据等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为司法者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法行为排除于犯罪处罚圈之外提供了有效保障,实践中直接援引但书规定实现除罪化的判决也时有存在。我国刑法上的法定微罪多由行政不法演化而来,其危害性实际介于违法与犯罪两可之间,依据但书对其除罪化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从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来看,分则的适用理当受到总则的制约,第十三条但书属于总则规定,危险驾驶、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窃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等均属分则规定,后者的入罪与否当然需要考虑行为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司法机关强化但书对微罪成立的限制,有利于为行政处罚的实施预留更加广泛的空间,使得我国二元处罚体制的实施更加均衡,避免因刑事程序上的追诉惯性导致行政处罚因被刑事程序无限压挤而难以得到适用,进而助益于行政规制功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充分运用,降低公民面临国家刑事追究和刑罚权惩处的风险。有观点认为,在司法领域扩张但书规定的出罪功能,将立法机关出罪权赋予司法机关,必将对司法裁量权的界限和犯罪构成标准唯一性地位带来冲击与拷问[20]。笔者以为,此种忧虑实无必要。近代以来,针对司法权恣意的批判主要围绕罪刑擅断、滥用刑罚而使民众随时面临不可预知的刑罚展开,防范司法权不当延伸刑事触角、加重刑罚严苛程度从而造成国民自由难以保障成为规范司法权运行的主线,罪刑法定原则正是基于此背景而产生,意在禁绝司法恣意,限缩国家刑罚权适用和保障人权,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刑法明确性和处罚适正性原则等无不以此为旨归。显然刑事司法权的主要症结仍在于其可能的无限扩张造成入罪及处罚范围的扩大,而非因出罪所导致的刑罚权在国民面前的限制和退让,后者在价值取向上无疑并不违背人权保障的立场;况且,出罪权并非立法机关的专享,法有限而情无穷,法律的适用必然包含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抽象的法律条文不可能明示每个具体案件罪与非罪的详细评判,将司法裁量得出的出罪结论视为对立法权的不当侵犯显然并不妥当;至于论者关于但书扩大适用会对犯罪构成标准唯一性造成冲击的疑问亦不存在,但书的适用并非建立于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基础之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判断虽是案件事实综合衡量的结果,但同时也代表着构成要件的非充足性,二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关系。
(二)充分拓展微罪不起诉范围,确立起诉例外原则
与德日等国较高的刑事案件不起诉率及漏斗形的审前分流程序设置相比,我国侦查机关并无微罪处分权限,且通常基于法定追诉职能驱动及犯罪打击数考核等因素,在办案中极易形成有罪思维模式,缺乏立案后再主动撤销案件的积极性,导致案件侦结后绝大多数均被移送检察机关,而审查起诉环节仅有3%左右的案件被检察机关不起诉,导致微罪的定罪判刑率极高,不仅给被告人带来与其轻微罪行程度不相适应的严重刑罚负面后果,更因其对有限司法资源的大量占用而影响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成效。实际上,相比于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等危险犯或行为犯,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轻伤)罪等实害犯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显然要高于前者,但实践中根据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后者往往被予以不起诉处理,从而产生轻罪判刑而重罪不诉的法律适用不均衡情形,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因而,无论是基于刑罚权限缩、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严重刑事犯罪打击的需要,充分发挥审前过滤功能,降低我国当前极高的刑事案件起诉率已尤为必要,而微罪不起诉无疑是实现该目的的可行突破口和有效路径。笔者以为,在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律框架下,应大力拓展微罪不起诉范围,确立微罪起诉例外原则。具体而言,对于微罪的处理,在通常情形下应以不起诉为原则、以起诉为例外,在司法实践中对各具体微罪可明确必须予以起诉的例外情形,凡未出现此类情形的若无特殊理由均应作不起诉处理。如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可规定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一定数值以上的,无驾驶资格而驾驶的,抗拒检查或逃跑的,曾有酒后驾驶违法犯罪前科的,或造成交通事故等情形,均应提起公诉,无上述情形的则一般由检察机关作酌定不起诉处理。同时,简化微罪不起诉的操作程序,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微罪,无须报检察长审批或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由员额检察官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以推动微罪案件的快速办理和节约司法资源。
(三)设置微罪案件处理考评机制,引导司法打击合理转向
由于侦查、公诉机关追诉犯罪的共同职能属性,以及审前分流体系的严重缺失,我国刑事诉讼进程呈现出圆柱形的结构模型,包括微罪在内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侦、诉、审环节表现为单向流水式作业,层层过滤功能极不明显,造成轻重犯罪处理同质化,刑事打击重心不突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不到位,进而微罪刑事处罚范围必然过宽。法律的效力在于实施,其实施成效往往与司法者素质、民众法意识水平、刑事政策等因素存在莫大关联,而盛行于司法机关内部的考核评价体系更实际发挥着引领刑事办案的导向作用。近年来,虽然轻微犯罪案件处理的宽缓化、非刑罚化一直为实务部门所接受和倡导,但司法机关对于微罪案件的追究却越发呈现泛化趋势,微罪案件在刑事犯罪打击中的地位已日益凸显,似乎已成为打击的重点所在。如危险驾驶罪,自酒驾入刑至2013年10月,苏州检察机关共受理4754件危险驾驶案,已成为仅次于盗窃的第二大刑事犯罪[21];2015年浙江检察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案件共23973件,仅次于盗窃案件的26270件,该年盗窃、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分别占总数的25.9%和16.6%[22];如前文所提,近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危险驾驶案件正呈逐年大幅攀升之势。上述情形或可说明,一方面,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有违宽严相济政策和理念,导致微罪打击成为重点;另一方面,危险驾驶案件犯罪化及刑事打击的成效并不理想,犯罪数不仅没有明显下降,反而越打越多。其原因除了有司法人员理念存在偏差、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等因素外,其实亦与司法部门内部考核机制具有重要关联。长期以来,各类刑事犯罪打击数一直是公安机关内部以及上级对下级进行业务考评的重要内容,然而考核对于数量较为偏重而忽视质量上的要求,导致办案单位在“两抢一盗”、毒品等严重刑事犯罪打击数量上难以取得突破时,往往将目标转向危险驾驶案件的查处。因为此类犯罪查处简便,只需民警在道路上“守株待兔”,醉酒驾驶者自会“送货上门”,且事实和证据简单、取证难度低,只需较少的侦查投入即可实现案件的快速侦破,从而成为公安机关完成考核任务数的极佳选择。检察机关又往往囿于不起诉程序复杂以及不起诉率考评等因素,通常对危险驾驶案件亦是一诉了之。笔者以为,为扭转上述对微罪打击失之过广的局面,有必要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微罪案件处理考评机制。公安机关应在刑事犯罪打击数的基础上,将法定微罪案件比例、相对不起诉案件比例、判处拘役及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等指标纳入考核内容,检察机关应将法定微罪起诉率、判处拘役及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等指标作为考核依据,从而切实降低微罪案件查处率、起诉率,引导司法机关将打击的重心转向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妨害社会秩序等犯罪,有效防止在微罪打击范围上的不当扩大。
四、结语
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刑罚应该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与维护法秩序任务时的最后手段[23]。在警察微罪处分权阙如、不起诉裁量权狭窄、前科消灭制度未能有效建立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微罪的刑事立法扩张,无疑是对刑罚威慑效应的片面理解,实际是以犯罪化、刑罚化以及刑罚量的轻重取代了刑罚确定性之威慑内容,体现了将刑法作为社会压制工具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刑法工具主义和泛刑法化思维的结果。尽管如此,法律一经生效即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如何在既有法律框架内秉持公正与道义,合理运用司法裁量的权限与手段,消解立法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于司法者来说是一门艺术。微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扩张已是现实,其后果是司法对于微罪案件处罚的大幅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二元处罚机制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弱化。对此,坚持司法能动主义,以微罪刑事处理效果为导向,面对立法扩张变被动司法为积极应对,从而充分维护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和实现其人权保障机能,不失为当前微罪立法扩张背景下司法者可以选择的现实可行的弥补路径。
[1]郑丽萍.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J].中国法学,2013,(2):128-138.
[2]储槐植.解构轻刑罪案,推出“微罪”概念[N].检察日报,2011-10-13.
[3]佟季,严戈.2012年全国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分析报告[J].人民司法·应用,2013(7):56-58.
[4]许剑锋,王逸吟.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为何多发[N].光明日报,2012-08-08.
[5]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守护国家法治生态——2014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分析[N].人民法院报,2015-05-07.
[6]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5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N].人民法院报,2016-03-18.
[7]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危险驾驶罪[EB/OL].(2016-12-22).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3631.html.2017年3月6日访问.
[8]利子平.风险社会中传统刑法立法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论坛,2011(4):26-32.
[9]柳忠卫.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3):51-54.
[10]刘志伟.《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问题[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2):17-26.
[11]孙万怀.违法相对性理论的崩溃——对刑法前置化立法倾向的一种批评[J].政治与法律,2016(3):10-21.
[12]于志刚.刑法修正何时休[J].法学,2011(4):9-13.
[13]庄乾龙.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的扩张与克制[J].东方法学,2016(3):106-118.
[14][意]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87.
[15][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2.
[16]李丹丹.山东疫苗案:357名公职人员撤职降级[N].新京报,2016-04-14.
[17]辛素,秦文超.日本微罪处分制度及其借鉴意义[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2):89-92.
[18]黎莎.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起诉率问题研究[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8(2):90-98.
[19]詹建红,李纪亮.困境与出路:我国刑事程序分流的制度化[J].当代法学,2011(6):71-79.
[20]李翔.论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司法化之非[J].东方法学,2016(2):2-11.
[21]陆季惠.苏州检方发布危险驾驶案审理报告,成第二高发刑事犯罪[N].姑苏晚报,2014-01-03.
[22]黄小星.案多人少!怎么看怎么干怎么变[N].钱江晚报,2016-03-14.
[23]林山田.刑罚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28.
(责任编辑:付传军)
OntheJustifiabilityandJudicialApplicationofExpansionofPettyMisdemeanorinCriminalLaw
ZHANG Ping-shou1, ZHANG Kai2
(1.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2.Central Institut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 Baoding 071000,China)
The generalization of criminal punishment caused by expansion of petty misdemeanor in criminal law compresses the spac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nd makes against implementation of current binary punish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The expansion of petty misdemeanor emphasizes the deterrence of criminal law one-sidedly and can be easy to conceal the absence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and the severe negative effect of penalty of petty misdemeanor is very incompatible with the slightness of the crime.In practic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judicial active role, intensify the function of the proviso in criminal law to restrict establishment of crime,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prosecuting petty misdemeanor exceptionally, and bring the treatment of petty misdemeanor into evalu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lead the judicial crackdown to serious criminal offences, thus easing the tension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petty misdemeanor to civil liberties.
petty misdemeanor expansion; justifiability; judicial application
2017-10-12
张平寿(1979— ),男,安徽芜湖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省宁波市象山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 凯(1979— ),男,吉林图们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矫正教育系副教授,社区矫正教研室主任。
D926.3
A
1008-2433(2017)06-00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