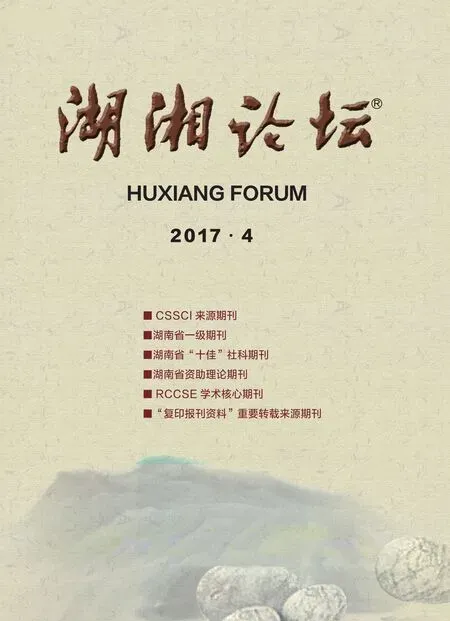汉初文献对于《庄子》要义之征引、诠释要论
王攸欣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30074)
汉初文献对于《庄子》要义之征引、诠释要论
王攸欣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30074)
汉初才士贾谊对于《庄子》甚为熟悉,《鵩鸟赋》征用、化用庄子要义、典故甚多。儒生韩婴着《韩诗外传》,视庄子为儒家对立者的诸子之一进行批评,但也较多地暗引、改易《庄子》寓言。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很可能是《庄子》文献的整理者,为《庄子》内篇定题,且对《庄子》要义作出了相当深刻而影响后世的诠释。
《鵩鸟赋》;《韩诗外传》;《淮南子》;《庄子》;要义
《庄子》在战国末年传播已颇广泛,东至齐,西达秦,北括韩魏,南及楚地,可以说遍传列国,却不太可能运用于诸侯混战攻守之策。秦以法治国,愚黔首,恃武力,吞并六国,敌视儒学六艺及诸子之说,禁固焚烧。《庄子》之思想属于最为反对“法教”的“私学”“百家语”,自在禁锢焚烧之列,这对于《庄子》在秦朝和汉初的传播肯定有重大的阻碍。汉兴,解除禁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庄子》之流通理所当然。
可以说,汉初近七十年,以先秦道家为主,融合诸子的黄老之学盛行,《庄子》在黄老之学中,虽未占主导地位,但其自然无为的基本价值取向,因循万物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却不失为重要内容。这足以隐约见出《庄子》在汉初流传的文化语境。事实上,汉初学者文人,于《庄子》颇有领会和征引。
贾谊《鵩鸟赋》之征引、化用
洛阳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汉文帝召为博士。贾谊本是儒生,又兼善律令。汉文帝甚为欣赏,破格奖拔,为老旧大臣嫉恨,贬谪为长沙王吴差太傅①当时长沙王为吴差,见《资治通鉴》第462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贾谊贬谪长沙之故居遗址尚存。。贾谊自伤悼,作《鵩鸟赋》,以鵩鸟的语气表达对于世事、人生的悲叹和忧伤,开首即用《庄子》文意:“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全篇征引《庄子》典故、文句甚多,仅末尾一节230余字,据《昭明文选》李善注,明引《庄子》达16处,意味着这一节多数句子均化用《庄子》思想: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怳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①《文选·鵩鸟赋》第607-6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一句,李善注“《庄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乃出乎《真人真知·大宗师》篇,今传本原文“子黎”为“子来”,相关段落是对于人固执于特定的存在形态的着意消解。又如李善注“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一句:“《庄子》:‘老聃曰:其居也,渊而静,其唯人心乎’。……《庄子》曰:‘汎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前一句是《在宥》篇老子对于崔瞿“慎无撄人心”的告诫:“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中间有所省略。后一句则出自《列御寇》,强调消除主体的欲望,甚至消除主体意识,才能不与外物相忤,逍遥于人世。上段引文中,尚有个别地方,李善注虽没有指明源自《庄子》,但按他的注,似认为出乎《庄子》。如“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他注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合其德”的说法都来自《庄子》。
从《鵩鸟赋》来看,贾谊对《庄子》要义的一个方面,有相当深入的领悟,那就是如何去超越人生苦难而达到解脱的境界。他以庄子所推崇的至人、真人、大人与贪夫、愚士、众人对照,认为至人们能够认识到人只是“万化而未始有极”中的一种存在形态,不必执着于这样一种形态,也不必执着于特定主体的名、利、权、生,因为一切存在物,都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只有虚己任命,消除主体意识,消除一切欲望,才能恬漠超然,无累无忧。他是接受了庄子从世间一切的存在者都处于变化之中这个角度,来述说人生应该超脱的理由的。实际上,这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超越自我——的多种阐述方式之一。当然,接受了庄子的思想,不见得能够真正超越自我,无所执着,彻底解脱。当贾谊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刘楫太傅,梁怀王意外堕马而死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这意味着他对于责任、情感的超乎常人的执着。对庄子要义的领会和行之于实际人生是两回事,仅从纯粹理解的角度来说,贾谊不失为汉初《庄子》思想的出色解读者。以贾谊杰出的才华,对《庄子》要义的其他方面,也自会有相当精深的领悟,只是现存文赋中未能充分显示。
韩婴《韩诗外传》②《韩诗外卷》《四库全书》本,下同,不另注。之明贬、暗引与改易
燕人韩婴,长于说《诗》,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成为燕赵地区解诗的权威。他说《诗》大都是以一个故事或寓言,说明一句诗的意义,主要是借此陈述一些儒家的道德训诫,也偶有表达自然无为、安命养性、超越名利、逍遥彷徨等之近于庄子观念者。不过,大都断章取义,或即先秦赋《诗》言志之遗风,亦见汉初解经之特征。从《韩诗外传·卷四》对于先秦十子的概括与评价来看,韩婴对庄子是持贬斥态度的。他继承《荀子·非十二子》的儒家立场,于诸子百家多有针砭,只是对于荀子着力批评的对象有所增删,《荀子》所否定者,包括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惠施、邓析、慎到、田骈、子思、孟子十二子,而《韩诗外传》去掉了它嚣、陈仲、史鰌、子思、孟子,增加了范雎、田文、庄周,为十子,这或许既说明汉初庄子的影响更趋广泛,却还没有达到黄老之权威的程度,足以昭示当时儒生之大致取向。
不过,《韩诗外传》篇幅不大,征引《庄子》处却颇多,粗略统计,不下30处,只是一方面,几乎从不明标源于《庄子》,且似刻意隐其渊源,尤其是引关于庄子本人的寓言,均替换为其他人,如北郭先生、戴晋生等;另一方面对引述文字的理解也每每独出己意,别具一格,既以文本为根据,又似有意偏离文本的原旨,表达自己的认识。有学者把他的征引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增益《庄子》中故事的情节内容,如引《寓言》中曾子两次为官,因父母存亡而心境大异的故事;二是对于《庄子》中不同寓言作出重新组合,表达新的寓意,如泽雉、戴晋人见魏王、庄子见魏王三则寓言糅合为戴晋生见梁王寓言;三是完全改变《庄子》中寓言的主旨,如引《人间世》螳臂当车寓言[1]。当然,也应指出,对于有些句子的解释,《韩诗外传》比后代注疏者更近于《庄子》本意。
《韩诗外传·卷五》对于《诗经·大雅·文王》一诗末章中“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一句的解说,采用《庄子·天道》篇一则流传甚广的寓言,轮扁对桓公,以为圣人之书乃古人之糟粕,即表达庄子关于语言文字无法传达微妙的经验的论旨,但韩婴刻意改变寓言中人物,把(齐)桓公易为楚成王,轮扁之对也略作调整(原文略),初看上去,对“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阐释较为勉强,细体之,尚称吻合,而且可以说是汉初解诗的通行方式。另一则寓言解说《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卒章之“彼美淑姬,可与晤言”,竟然改写《秋水》《列御寇》中楚王聘庄子的寓言,把全部人物都替换了,原为表达爱情的诗句,在这里通过对于北郭先生之夫人的价值观念的陈述,既表现了妇人的贤良智慧,又表现了夫妇相爱之情。妇人形象是《庄子》原文根本没有的,而实质的内容却是宣扬了庄子的不为名利殉身,不愿放弃逍遥无为、自由自在生活状态的价值取向——而这是和儒家的锐意进取相悖的。
《韩诗外传·卷九》戴晋生见梁王寓言,不知是解说哪句诗,未作说明,或系文字散佚所致(原文略)。其中,泽雉寓言来自《因其固然·养生主》篇,戴晋人见魏王寓言来自《则阳》篇,庄子弊衣见魏王寓言来自《山木》篇。“泽雉”一则寓言,《因其固然·养生主》原文仅21字,亦颇有异解。前面10字乃“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后代注疏者多认为是写泽雉之“饮啄自在,放旷逍遥”。如郭象注:“夫俯仰乎天地之间,逍遥乎自得之场,固养生之妙处也。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又如成玄英疏:“夫泽中之雉,任于野性,饮啄自在,放旷逍遥,岂欲入樊笼而求服养!譬养生之人,萧然嘉遁,唯适情于林籁,岂企羡于荣华!”也就是表现泽雉自由的状态。因为和后文“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构成强烈的对比,有利于表达庄子对于自由状态的肯定,所以被普遍接受为权威解释。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写泽雉的警觉谨慎,如明学者陶望龄《解庄》:“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饮,防患周慎,岂祈畜樊中哉!”[2]。而韩婴认为泽雉“五步一噣,终日乃饱”,意味着在他的理解中,这是写泽雉饮啄之难,即寻食艰难的状态。仔细体会,《韩诗外传》更得庄子本意。后来也有注庄者赞同这种解释,如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解说为:“泽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饮,言其饮啄之难也”[3]。其实,这种解释既和“不蕲畜乎樊中”,构成转折对照关系,又由这种转折对照关系一起表达了自由的状态,所谓“彼乐其志也”,与后文“神虽王,不善也”构成另一重对照关系,因为樊中之雉“彼不得其志也”。当然,对“神虽王,不善也”与前文的关系,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戴晋人见魏王寓言的蜗角之争的寓意被忽略,而庄子见魏王的傲视王侯的寓意尚有所保留,却是以戴晋生对于梁王不能真正好士的嘲讽而加以表达。这种糅合改变不失其精彩之处,对于《庄子》的传播而言,当然是有得有失,或许弊大于利了。
《韩诗外传》对于《庄子》螳臂当车寓言的征引和反其意而用之,大概最能够充分地显示作为儒生的韩婴和道家创始者之一庄子的价值观念之异。《庄子》之《唯道集虚·人间世》《天地》两次述及螳臂当车寓言,均指螳螂不自知其才力,敢于阻挡车辙,因此人必须以此为戒。而《韩诗外传·卷八》齐庄公遇螳螂寓言之视螳螂则不然,作者虚设了齐庄公出猎,对于螳螂之勇敢精神赞许有加,并认为齐庄公堪称贤主,以此来解释《商颂·长发》中“汤降不迟”一句:
齐庄公出猎,有螳蜋举足将抟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螳蜋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以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诗曰:“汤降不迟。”①此螳螂寓言,在《淮南子·人间训》中有相近的叙述,《淮南子》或系采自《韩诗外传》,或两者另有共同渊源。本文所引《韩诗外传》均据四库全书本。
“汤降不迟”本是歌颂殷商先王成汤降生正当其时,这里就以齐庄公之尊重勇士精神,使天下勇士归之,加以说明。齐庄公吕购为齐桓公之祖父,在位64年,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所以韩婴称说如此,可谓以半真实半虚构的历史说诗矣。
《淮南子》编纂者对《庄子》的整理和文献保存
《淮南子》编纂者刘安及其门客,很可能是郭象33篇《庄子注》之前流行的《庄子》52篇本的整理者,笔者在他文已有较详细论述[4]。此处再增补陈述理由一条:《庄子》内篇篇名应为《淮南子》编纂者所定,《淮南子》中《齐俗训》《人间训》颇显《庄子》内篇《齐物论》《人间世》命意渊源,且内容也具有一定的关联,尤其《齐俗训》与《齐物论》思想关系密切,详后。《应帝王》可能和《道应训》篇名有关联,而《应帝王》不宜概括《庄子》该篇正文内容,却足以概括《道应训》正文。
淮南王及其门客对《庄子》文本甚为熟悉,已经散佚的《庄子略要》篇应该是对于《庄子》要义的概括和阐述,如《文选》李善注三次引述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并引“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①《文选》第1250页,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句,李善注。,涉及到庄子思想的主导价值取向,即看重个体自由,推崇自然,轻视世俗功利,贬斥矫饰。可惜仅存此句,无法概览全貌。《淮南子》引述《庄子》相当广泛,从现存《庄子》33篇本看,引述遍及其中32篇,只有杂篇中的《说剑》篇未经引述,有些文句、字词比郭象本更接近《庄子》原文,而且《淮南子》还保留有现存《庄子》已散佚的文句。其中,有的散佚文句是更准确理解《庄子》阐释史的重要文本根据,前人有所发现,却尚没有充分阐发其意义。这里以一例证之。
《淮南子·俶真训》有一段,以《庄子》之圣人与真人恬漠无事、虚寂无为之道批评儒墨仁义之术:
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下缩排直引均出此,不另注。
《俶真训》全篇大体以《庄子》文本为根据,谈《庄子》之至人、真人、圣人等的寂寞无为之道,不少文字直接来自《庄子》,并且逐句进行训释。如开篇即对《道通为一·齐物论》中“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一节作出详细、明确的阐发,对原文的引述与今存《庄子》略有出入,不易断定何者更近于《庄子》原本。上引“圣人有所于达”一段,毫无疑问符合《庄子》的核心观念,不少语词、句子可以肯定来源于《庄子》,如圣人、许由、滑心、恬漠、无事、真人、与造化者为人等,但从今存版本中找不到整段的直接来源。惟最后一句“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精神训》有:“化物者未尝化也”。《列子·天瑞》有“故生物者不生,而化物者不化”,张湛注曰:“《庄子》亦有此言”。后紧接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③《列子·天瑞》第16-17页,世德堂刊本,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影印版。此句佚文及向秀注,既显示了郭象《庄子注》中被学界认为体现其创造性的“独化说”最直接而明确的《庄子》文本根据,尽管在通行本《庄子》中,也有相近的观念;也显示了此一说法,郭象之前已成共识,且因为原文意义很明确,不会产生太多岐解。
《淮南子》对《庄子》要旨的阐释
《淮南子》包括《要略》共21篇,绝大部分篇目都引述也阐述了《庄子》观念,而且从条目上看,《淮南子》对《庄子》内篇的引述尤多,且最重要。《淮南子》21篇中,有《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齐俗训》《道应训》等诸多篇目以《庄子》为重要甚至主要的思想和素材来源。其自序性的《要略》中,叙《俶真训》则曰“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明显以《庄子》学说为根据;叙《道应训》则明确说“考验乎老庄之术”。所以《淮南子》编纂者实为精通《庄子》的学者,在具体的阐释中,颇见其卓识。
据笔者判断,《庄子》内篇篇名为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定,且定名于《淮南子》成书之后[4]。对于《庄子》最为核心的篇目《齐物论》,虽然命名不当,《淮南子》在《齐俗训》《俶真训》等篇可以说作出了相当深刻而准确的诠释,却被后人选择性地运用,大部分继承,有时也改变了《齐物论》文本的要旨,如《庄子》诠释史上最具权威性的郭象《庄子注》。《齐物论》的要旨,在不少《庄子》注疏者看来,就是昭示万物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同主体存在与是非判断的相对性,在这两个方面,《淮南子·齐俗训》都作出了较充分的论述,尤其在后一论题上,《齐俗训》作出了《道通为一·齐物论》诠释史上最为出色的解释,非后学所及。
《道通为一·齐物论》阐述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万物的存在具有相对性,而且万物各有其性,各有所宜,所以超越每一具体事物,从道的立场上观照,则物无贵贱。这一思想,在《秋水》中以北海若之口作出较充分的理论阐释。《齐俗训》则以一系列具体的事物来说明论证“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有一些例证即取自《道通为一·齐物论》。如其中一段:
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柱不可以摘齿,筐[莛]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
“万物一齐”一语,既直接来源于《秋水》篇,又很可能是《道通为一·齐物论》定名为《齐物论》的缘由之一。
“齐物论”之命名,既可能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对于“齐物”的诠释,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庄子》诠释史上几乎笼罩百代的郭象解题,视“物”为人,着眼于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特定立场上,肯定自己的主张、判断,否定他人的判断,美己恶人,所以在是非的评判上,往往相异,但在自我肯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硫》,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下引郭象注,成玄英疏,均出此,不另注。。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和阐释,尽管与《道通为一·齐物论》本身的核心思想颇有出入。而这一解题并非如历来多数论者所认为的出自郭象独创,而是很可能渊源于《淮南子·齐俗训》: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这就把一般人往往以个人的利益立场来判断是非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总结出来了,而且同时指出,这样一种评判绝不是公允的,而是拘于一隅。《淮南子》很好地领会了《庄子》的旨意,认为这样一种立场是应该超越的,真正的是非应该是站在宇宙的立场,道的立场上来看。所以《淮南子》一方面看到了是非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又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要着意超越个体的相对性,达到对于宇宙的整体直观。而这恰恰是后来的相当多诠释者误解了《庄子》的地方。庄子也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而是一个力图超越相对性,达到绝对的追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编纂者比有些后人对《道通为一·齐物论》的理解要准确得多,也高明得多。
“化”的观念是庄子哲学独特而重要的观念,《庄子》内篇“化”字出现20多次。庄子之“化”,既指每一个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只是“万化而未始有极”中的一种存在形态;又凸显在个体的不同形态、不同类别的存在者之间都呈现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更意指每一作为主体的个体,面对世界这样一种无所不在的“化”的状态,应该有自觉的意识,不固执于任何既成的形态和规则,“与时俱化”,方能“应物而不穷”,即不断调适主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达到和谐。而这种“与时俱化”的领悟,即是对于道的体会。《淮南子》编纂者接受了庄子“化”的几个层面的观念,不仅《俶真训》有:“一范人之形而犹喜,若人者,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其为乐也,可胜计邪!”“是故至道无为,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而且《齐俗训》还探讨了“道”“法”与“化”的关系:“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此句中“所以为法者”,即指“道”,“道”是与化推移的。这样一种道、法关系,也是法家源于道家的线索。事实上,《庄子·天运》所说“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就囊括了《齐俗训》这一论断中所包含的“法”。
《淮南子》作为汉初黄老道家的著作,目标在于治邦安民,真正的根源和目标都是功利性的,但编纂者却有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要实现社会安定,却需要宣扬超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化解争竞之心,所以《庄子》全书主导的价值倾向也可以说是其要义之一即论证超越性自由的价值——无为、逍遥即超功利性追求——成为《淮南子》着意阐释、发扬的重心之一。当然,在对无为本身的解释上,又加入了实际政治操作的策略性考量。“无为”是《淮南子》使用频次最高的概念之一,全书达50余次,“逍遥(消摇)”全书出现共7次,全部意指闲旷、自在。与此相关的圣人、至人、真人等词更是频繁出现,虽然圣人一词并不是所有用法都与《庄子》一致。《庄子》之无为,即顺物自然,命物之化,无所作为,不去追求功利性目标。而《淮南子》的无为,牟钟鉴总结出其不仅继承了《吕氏春秋》的几个方面:(1)治国依法不任意;(2)君主驭臣以术;(3)尊重自然规律;(4)随顺民性习俗;(5)不为物先,以柔克刚;(6)等待客观条件成熟而行事,不操之过急。[5]190-191而且还增加了“无为”的四个意涵:(1)不以私害公;(2)不以欲枉正;(3)遵照事理与实际条件而为;(4)事成而不炫耀自大。[5]193牟氏的总结是言之成理的。这里想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对“无为”的阐释,也是郭象注《庄子》,所阐释的“无为”观念的渊源,同样不是郭象本人的创造。可见《淮南子》在《庄子》诠释史上,借助于郭象《庄子注》,也发生了相当大影响,只是这一点尚未得到前人充分重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对“因其固然”“唯道集虚”等等重要观念,《淮南子》对《庄子》也有所引述、发挥,本文因篇幅所限,不遑多论了。
[1] 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1-425.
[2]崔大华.庄子歧解[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120.
[3]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53.
[4]王攸欣.庄子文献论要[J].长江学术,2017(1):64-74.
[5]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
责任编辑:曹桂芝
H1
A
1004-3160(2017)04-0165-06
2017-03-16
王攸欣,男,湖南湘乡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