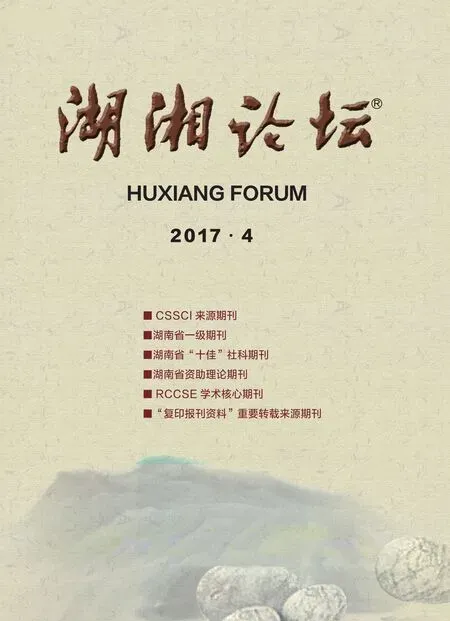错置与重构:传统官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探析
黄建跃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错置与重构:传统官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探析
黄建跃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立足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传统官德文化包涵诸多为政美德和道德规范,能为当代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此同时,传统官德文化存在“德治越位”“德政错位”“德格畸位”“德福异位”四重错置,它们是传统德治理念无法在政治实践中充分释放积极效应的根本原因。只有完成价值重构、体制重构、角色重构和激励重构,才能架设传统官德文化对接现代行政道德建设的通道,找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正确路径。
行政道德建设;官德文化;思想错置;当代重构
传统官德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是当代行政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源和思想。因此,如何客观评价传统官德文化的内在价值与时代意义,继承发扬其中的积极因子;如何准确定位其中的思想缺陷,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以补偏救弊;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传统官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便成为了我们重视与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官德文化的定义及其积极价值
广义来看,传统官德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传统官德理念赖以形成的理论框架(如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内圣外王”的治道规划、“修己安人”的实践门径等等),又包括为政主体必须恪守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如“天下为公”“礼义廉耻”“仁民爱物”“清、慎、勤”等),还包括儒家德治理念进入政治实践的制度安排和操作办法。由此可见,传统官德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涵括德治框架、德治目标、德治规范与德治操作的整全性概念。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官德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价值。
首先,传统官德文化“以德治国”与“以德配位”的理念契合人类政治实践的一般要求。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表明,德治是达成善治的重要保障。孔子宣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道“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主张将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提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强调即便建构了良好的治理体系,仍然需要重视行政主体的道德修养。荀子虽是“隆礼重法”的主张者,但对于行政主体的道德要求始终心有戚戚,故而反复强调修身。总而言之,儒家都要求在现实政治中倾注道德关切,藉此追求良好的、崇德向善的政治效果。[1]笔者认为,传统德治理念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仅能为中国自身的政治文明所证成,亦能为西方政治实践所证实。众所周知,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之后,对于道德之于行政是否必要的问题进行过长期的讨论。许多政治理论学派预设了国家的价值中立,以及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认为行政活动主要强调科学和效率,无需对行政人员寄予道德期待。如官僚责任派就认为,着意去为政府官员套上束手束脚的道德枷锁实在是多此一举。[2]直到行政伦理学学科诞生,西方国家才把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理念变成实践,将行政科学与行政伦理看作达成善治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行政伦理规范及行政伦理制度于是粲然大备。综上可知,善治离不开道德是立基于古今中外人类政治实践而形成的规律性认识,传统中国对于德治的崇尚及为政主体道德品行的强调,源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必须继承和发扬。
其次,当代中国的行政道德建设若要达成理想效果,必须遵循立足传统官德文化进行推陈出新的路径。应当看到,“现代”与“传统”绝非两个断裂的实体,现代行政道德建设并不意味着必须颠覆传统官德价值,相反必须走“让新生命吹进古文明”的道德文化复兴路径。深入分析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演进历程不难发现,那些试图排除或摈弃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全盘引进和接纳西方价值标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非但没有成功实现现代化,也没有形成良好的行政伦理生态。恰恰是一些善于“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的国家”[3]才成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之途,培育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行政道德。行政道德建设的不同路径选择导致的不同结果无疑昭示出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道德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即现代社会的新道德文化并没有完全脱离旧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4]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所蕴含的真理,自觉将当代行政道德的建设植根于传统官德思想这片营养丰富的文化沃土当中,结合具体实践探寻当代中国行政道德建设的途径,自主创建行政道德建设和公务员道德培养的模式。
再次,传统官德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配套体制仍然可以作为当前行政道德建设的文化滋养与操作借鉴。就核心价值的内容而言,传统官德文化“以民为本”的仁政理念、“仁民爱物”的为政情怀、“清正廉洁”的为政要求、“秉公理政”的为政操守、“勤勉尽职”的官箴规诫等等,与当代行政伦理“信念坚定、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依法办事”的主要内容实有内在相通之处,完全可以作为当代行政道德培养的一种文化滋养。就德治理念进入政治实践的操作方法而言,传统中国具有合家庭、学校、官方为一体的行政道德教化机制,人才选任过程中的道德甄别制度,行政主体道德监管方面的评价与考核机制,等等,这些体制机制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完善,早已凝成了别具特色的行政道德制度文化。其中有的对于当代行政道德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有的则能为当代行政道德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最后,传统官德文化正己修身方面的思想资源能为当前行政主体的道德修养提供有益启示。就正己修身的内容体系而言,传统官德文化要求为政主体坚定道德信念、澄明道德理性、醇化道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这些内容与当代道德生成理论桴鼓相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如坚定道德信念方面,传统官德文化基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为政》)的政治经验,高扬“内圣外王”之道,激励行政主体崇德重德、鼓勇赴义。澄明道德理性方面,传统官德文化主张为政主体践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要求通过不断学习,“光明”“光大”自身的良知德性,进而教化民众,达到臻于至善的境界。醇化道德情感方面,传统官德文化主张为政者恪守“忠恕之道”,在工作和生活中经由“以情絜情”“将心比心”的共情原则,做到检点身心意念,保持道德热忱。锤炼道德意志方面,传统官德文化倡导“君子慎其独也”的“慎独之道”,要求行政主体即使在无人监督、独自活动的情况下,依然要按照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除此之外,传统官德文化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修德方法,如“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修养路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成德次第,“能近取譬”的“为仁之方”,以及“三省吾身”的道德自省、“功过格”“日课”的自我道德审查、训诫铭文(如汤盘铭、碗铭、座右铭)的自我道德提醒,等等。这些修德方法,能够切实发挥敦促为政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传统官德文化当中的修德内容和修德方法,不仅能够为当代行政主体的品行砥砺提供方法论启示,而且还能为之注入从严律德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传统官德文化的四重错置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官德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充分释放其所具有的积极效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立足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德治理念,以及这些德治理念进入政治实践的过程存在着理论缺陷。笔者暂且将这些缺陷归纳为四重思想错置。它们是“德治越位”“德政错位”“德格畸位”和“德福异位”。
所谓“德治越位”主要是指传统德治文化夸大了道德的治理效能。善治离不开道德尽管是古今中外政治实践的通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凭道德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儒家高估了道德的治理功效,抬高道德的治理地位,不断开拓道德的治理地盘,极端情况下甚至认为仅仅依靠统治者良好的个人道德,便能自发生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态,由此落入德治越位的理论窠臼。
应当承认,孔子、孟子并没有否定道德以外的其他治理方式的必要性。《论语·子路》篇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将“名”“言”“事”“礼乐”“刑罚”这些治理之具相提并论,表明他对“正名”之外的“刑罚”有所注目。孟子主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声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显然是在强调德治与法治不可偏废。当然,孟子高扬“崇王贱霸”的思想旗帜,对德治别具青眼的意识彰彰甚明。如果儒家有关道德与礼法关系的论述到此为止,似乎还只能用德治优位来定义。德治越位与德治优位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寄予德治的期望,大大超过了道德实际能够承载的治理功效,势必会引申出不断强化道德治理并试图以之取代其他治理方式的倾向。《论语》中的“风草之喻”正是这种理论逻辑的渊薮。为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季康子主张任刑用法,孔子则强调由统治者率先垂范以导民向善,其理论根据在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徐复观先生指出,“子欲善而民善矣”是为“反对刑制而提出的”,目的是“极力防止统治者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去统治人民”,因而具有积极的价值。[5]181可见孔子的主张不仅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且还具有改良原有治理模式的进步意义。然而值得追究的是,“子欲善而民善矣”的理论根据能否成立?也就是说,即便“君子之德”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小人之德”,能够产生导民、教民和化民的效果,但这种影响效果是否真如“草上行风”一般,又是否具备“风行草偃”的必然性?对此,孔子始终未予证明,“风行草偃”顶多只能算是他的德治信心和为政信念。关键在于,随着这种信心和信念的不断强化,道德的治理地盘不断拓展,甚至挤掉了其他治理工具的空间。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等议论,都是过分夸大道德治理效果得出的。至此可明,夸大道德的治理功用,主张用道德感化主导政治的理念肇端于孔子,并在后世德治理论中持久存续,不断强化。孟子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即一显例。孟子要求君主居仁由义,端正自身从而推行仁政的主张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是不是君主讲究仁义道德、端正自身,便会人人都讲究仁义道德、都端正自身呢?或者说,“正君”能否成为“国定”的充分必要条件?孟子对此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德治越位的理论缺陷,使儒家走向了重“治道”轻“政道”、重“内圣”轻“外王”的歧路。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始终无法突破“圣君贤相”格局的理论根源,也是儒家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安立于现实世界的主要原因。
“德政错位”是指德治理念进入传统政治的过程中,出现了礼治实践扭曲德治理念的情况。我们知道,礼治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为礼治的功能性目标在于区分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级,通过明尊卑、别贵贱实现有序治理。《左传·桓公二年》中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差”,《左传·昭公七年》中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都是礼治等级性的显证。儒家的德治主张针对的是礼坏乐崩的现实场景,援“仁”入“礼”是为了恢复并维持礼治。故而其以德治维护礼治的意图十分明显: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儒家的治理话语当中有“德治”和“礼治”两套治理体系、两套治理逻辑。德治预设人性相近、德性平等。无论是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还是《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都对人人崇德、人人修德、人人行德进行了清晰界定,带有鲜明的以德为治(rule of ethics)特征。而礼治恰恰强调政治的不平等。德治与礼治之间的区隔决定了二者实际上无法相容自洽。具体地说,儒家仅靠德治这种“批判的武器”无力扭转礼治的不平等基础,其处理办法要么是以托古形式虚设以德为治的乌托邦,要么通过理论加工将德治之魂灌注于礼治之体,其结果,则是以礼治的等级形式为“型范”,把德治的平等形式扭曲成了德治的等级形式。试看下面的引文: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孟子·离娄上》)
儒家“天下有道”的治理规划,继承了大夫不能制定政教刑法、朝章国典和庶民不得议政这类礼治等级规则;德治却要求无论“天子”“大臣”还是“庶人”,都应沿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拾级而上。二者之间的张力清晰显明。孟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小德役大德”,即根据礼治规定的政治等级构造出道德等级,借此将德的大小与位的高低关联起来。问题在于,伦理道德的等级性一旦奠立,德性平等的基础便顷刻瓦解。德治理论中的人人向德负责变成了政治实践中的“低位”向“高位”负责,以德为治(rule of ethics)异变成以德促治(Rule by ethics),造成理想之“德治”与现实之“政制”的错位。这样一种理论妥协,导致的负面后果至少有如下两端:一是道德观念的阐述、伦理规范的制定、道德标准的设置与解释、道德教化与道德是非的评价权力,都由优势地位者垄断;二是伴随道德等级性出现了道德奴役性。[6]如此,儒家“天下有道”的治理规划便只有道德理论的入口,找不到现实政治的出口,道德理想之于现实政治的超越性以及对于优势地位者的强制约束无从彰显,公正的道德评判、合理的道德监督当然都会因此大打折扣。
“德格畸位”主要指对行政人格的德性预设、道德要求与目标追求脱离实际,出现了畸形的定位与设计。原始儒家虽然建构了希贤法圣的道德理想,却并不认为为政主体都能达到圣人境界,故而孔子、孟子对为政主体设立的道德准则大多符合实际,亲切可行。《论语》云“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孟子道“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孟子·梁惠王下》),没有提出为政者必须“优入圣境”的要求。然而,由于道德理论的更新远远落后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原有的道德理论、道德要求和制度安排变得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此处仅将为政清廉的道德要求与传统俸禄制度结合起来略作分析。笔者认为,儒家的诸多道德理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等等,存在爵级体制的制度前提。在此制度安排之下,君子(有土者)和士具备践履廉洁为政的物质保障。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之际以“世袭”和“采邑”为内容的爵级体制仍然存在,由于“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有禄者必有土”,为政者的爵级特权非常优厚。此亦可见于《孟子》中的相关记载。《滕文公下》载齐国世卿陈戴“食禄万钟”,作为文学之士的孟子也获得了“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厚遇,可见当时出仕者完全不用替“恒产”操心。问题在于,随着封建制向郡县制的变革,发生了“爵—食体制”向“爵—秩体制”的重大转变[7],出仕所获物质保障不再优厚如昨。而后世行政道德理论不仅没有根据这种变革进行必要的调整,反而极力把为政者塑造成纯粹的道德主体,甚至恨不得把他们预设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如此,道德要求和制度保障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简而言之,西周“爵—食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种德性预设、道德标准变得凌空蹈虚,不再切合实际。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薄薪制基础上的廉洁从政要求不断失败,即是明证。以清初为例,官员薪资俸禄竟然低到了无法维持生计的程度。1669年御史赵璟奏告康熙皇帝,直陈知县的生存境况是“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指出薄俸制导致了“禁贪而愈贪”[8]的恶果。由此可见,“无恒产而有恒心”的道德信条自有其前提,如果缺乏这种前提,完全忽视道德背后的利益基础,一味要求为政者具备纯粹的行政德性、追求高尚的行政人格,终究只能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畸形道德预设。
“德福异位”是传统官德理论的第四重错置。我们知道,“德”是超越性的,主要属于应然世界;“治”是世俗的,主要属于实然世界。儒家意欲用“德”统领“治”最终成就“天下有道”,就必须让超越的“德”通过世俗的“治”得以呈现。若非如此,德治合理性便难以确证,为政主体的道德信心和行德意愿也很难激起。正因如此,儒家描绘了一幅“内圣外王”的理想图景。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这种对接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的允诺强度明显不够,因此招来了冉求“非不悦子之道也,力不足也”(《论语·卫灵公》)的推却。孟子提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认为是否推行仁政决定着天下、国家的存亡兴废。问题在于,不仅“圣”(德)与“王”(治)之间的联系不能被现实证实,而且常常被证伪,就连孟子自己也承认“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孟子·尽心下》)。至于儒家的其他典籍,愈加决绝地作出了德福统一的允诺。《礼记·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等等,莫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勉励为政主体崇德、修德和行德。而由于“德治越位”和“德政错位”的存在,上述德福统一的允诺缺乏坚强制度保障。例如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许以“三仁”,却一个“去之”,一个“为之奴”,一个“谏而死”。就连孔子本人,也未因“大德”而得“大位”。由此观之,儒家德福统一的允诺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最终只能是无果之花。既然在政治实践中不能达成因“德”获“福”,甚至反而会因“德”致“祸”,为政主体的行德意愿必然大大削弱,行德无力感也必然生发滋长。
三、传统官德文化的当代重构
若欲儒家优秀道德文化有益于当代行政道德建设并充分发挥积极效应,就必须经由系统性重构,找到传统官德文化对接当代行政道德建设的通道。所谓系统性重构,包括价值重构、体制重构、角色重构和激励重构四个方面。
价值重构即合理定位道德的治理功用,科学评价道德的治理价值。传统官德文化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夸大道德的治理功用,始终未能划清道德之于政治的边际界限。正是因为在权衡道德治理价值时出现了德治越位,才导致了传统治理理论中科学性与效率性内容的缺失。这种缺失在学理上表现为德治理论当中的政治学始终未能突破伦理学的母胎,发育成为一门独立科学,造成了“政治学失位”和“政治学错位”的后果。[9]现实表现则是轻视治理框架的进化与完善,忽视治理效果的追求与达成,此即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治道”完善而“政道”悬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和现代政治的系统性、复杂性、大众化、协商式等时代特色,伦理型政治亟需进行根本调整。促成伦理型政治向治理型政治的转向,是解决德治越位的必要环节。也就是说,在道德进入现代治理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德治僭越的负面效果。这就要求消化、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和西方法理政治的优长,建构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科学合理的治理框架,用以承载和落实儒家的德治理想,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前文论及,为了将德治理念灌注到现实政治当中,儒家用礼治的等级秩序扭曲了德治的平等要求,使得德治体系虽然在理论上自成一统(即“道统”),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却只能依附于礼治。正因如此,孟子思想中“德”“爵”两个并驾齐驱的“达尊”被捆绑到了一起,并最终让“爵尊”吞噬了“德尊”,德治的启动和推行于是缺乏了外在的和独立的制度保障,而是内化于为政主体一身,道德治理因此等同于权力治理,最终沦落为个人化的人治。儒家聚讼纷纭的“道”(公理)“势”(强权)之争,正是导源于此。虽然荀子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但这种理念仅仅只是停留在为政主体个体选择的层次,没有成为完善政治制度的理论助援,故而无法实现德治序列之于礼治序列的超越。至于西汉以后不断强化的“君为臣纲”这类伦理纲常,则进一步窒息了德治发挥积极效应的可能性。分析至此可知,若要德治理念真正落实,就必须彻底破除儒家的道德等级性,使政治制度安排充分表达德治的平等理念。徐复观先生曾道:“德治思想实通于民主政治,也要在彻底的民主政治中才能实现。”[5]195此诚卓见。有识如此,当代行政道德建设必须奠基于权利平等和德性平等的理论基石之上,着力完成纲常道德向民主道德的转型。
角色重构主要针对“德格畸位”的畸形预设而言。对于行政主体进行恰当的德性预设,制定合适的道德规范,确立可行的成德目标,是完成角色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的来说,传统官德文化产生“德格畸位”的原因,在于其以性善论为基础、以纯粹道德主体为标准、以圣人理想为最终目标确证的行政人格,超越性有余而现实性不足。由于道德设准远远超过现实行政主体能够企及的高度,导致道德规范成为了不切实际的空洞条文,同时还导致了实际行政生活中普遍性的道德失范或伪善横行。为了克服上述种种弊病,当代行政道德的行政人格确证有必要揖别“圣人道德”的理想预设,综合考虑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恪守超越性、现实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推动圣人道德向角色道德转向。应当指出,圣人道德向角色道德转向绝不是弱化或者说放弃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是把行政道德建设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正如学者所言:官员作为完全的社会存在而言,是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处于多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中,充当多重社会角色的主体,而非单一纯正的道德主体。[10]
激励重构主要指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手段,促成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与行为结果达成基本一致,进而增进行政主体的道德信心和行德意愿,促使其自觉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动。展开来说,道德激励包括负向激励和正向激励。负向激励除了建构不敢失德的法律制约机制之外,还应该让学术界、社会群体、公民个人顺畅进行道德监督,建构不能失德的立体监督机制,使“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具有外在制度和社会舆论的支撑。正向激励则是要通过优化考评机制、晋升机制和奖惩机制,使为政主体的道德行为能够转化为物质或精神上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德允诺得以实现。比如,新加坡为了敦促公务员恪守诚信之德设计出的“诚信公积金制度”,便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举措。
[1]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J].伦理学研究,2012(4):27.
[2]马国泉.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9.
[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34.
[4]万俊人.现代道德仍需传统滋养[J].传承,2012(3):58.
[5]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6]刘忠世.析传统道德理念的等级性[J].齐鲁学刊,2001(6):53.
[7]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1-55.
[8]刘凤云.从清代京官的资历、能力和俸禄看官场中的潜规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48.
[9]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2.
[10]李建华,李建国.公忠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1.
责任编辑:曹桂芝
D9
A
1004-3160(2017)04-0149-06
2017-03-19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3AZD032),课题负责人黎红雷教授。
黄建跃,男,湖南长沙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哲学、中国管理哲学。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