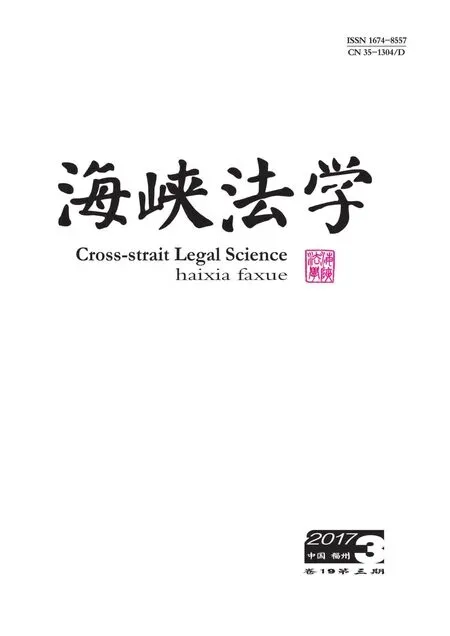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环境法上的状态责任为核心
吴志光
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环境法上的状态责任为核心
吴志光
按行政罚上之状态责任若未达特别牺牲之程度,自未逾财产权社会义务所应忍受之范围。而状态责任系指人民依法规之规定,对某种状态之维持,因基于“与物之联结关系”而具有义务(尤其是所有人、占有人),因违背此种义务,故须受到行政罚。就各类涉及污染防冶、危害预防之法规而言,当行为责任之追究不足以达成立法目的时,状态责任确实在现代干涉行政法(尤其是环境法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惟关于其概念之厘清,就学理与实务见解而言,则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财产权社会义务;状态责任;行为责任
一、前言
环境污染问题早已不是区域性之问题,更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生态均衡,故事先预防及事后处理环境污染成为当下环境法上的核心议题。若难以防范于未然,则亡羊补牢即相形重要。而最主要的亡羊补牢手段,即是透过行政罚的方式,制裁其制造环境污染之行为,环境污染排除之可能性,亦系透过行政罚的方式,促使其履行环境污染排除之义务。
按行政罚之对象原则上应以行为人为重心(即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在例外情形方处罚非行为人,此即所谓“行为责任”(Verhaltenshaftung)与“状态责任”(Zustandsverantwortung)之区别。按状态责任则指人民依法规之规定,对某种状态之维持,因基于“与物之联结关系”而具有义务(尤其是所有人、占有人),因违背此种义务,故须受到行政罚。就各类涉及污染防冶、危害预防之法规而言,当行为责任之追究不足以达成立法目的时,状态责任确实在现代干涉行政法(尤其是环境法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相较于行为责任之界定,状态责任有其特别之处,甚至亦具有宪法上之重要意义,即状态责任人虽非行为责任人,其责任的基础及界限何在。有鉴于状态责任已成为台湾地区环境法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拟由其宪法基础为出发,探讨其在台湾地区环境法制中应有之内涵及相关议题。
二、财产权社会义务的宪法基础
按就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性质,台湾地区大法官在“宪法”解释中,即曾多次提及财产权具有社会义务(或责任),而非如论者所言,只能委诸于公共利益之要求。①例如“司法院”释字第291号解释即指出,“民法”关于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之规定,乃为促使原权利人善尽积极利用其财产之“社会责任”,并尊重长期占有之既成秩序,以增进公共利益而设。此项依法律规定而取得之财产权,应为“宪法”所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司法院”释字第400号解释以“特别牺牲”作为划定财产权社会责任界限的理论基础,其称“‘宪法’第十五条关于人民财产权应予保障之规定,旨在确保个人依财产之存续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之权能,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惟个人行使财产权仍应依法受社会责任及环境生态责任之限制,其因此类责任使财产之利用有所限制,而形成个人利益之特别牺牲,社会公众并因而受益者,应享有相当补偿之权利”。而“司法院”释字第564号解释亦称:“人民之财产权应予保障,‘宪法’第15条设有明文。惟基于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对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国家并非不得以法律为合理之限制,此项限制究至何种程度始逾人民财产权所应忍受之范围,应就行为之目的与限制手段及其所造成之结果予以衡量,如手段对于目的而言尚属适当,且限制对土地之利用至为轻微,则属人民享受财产权同时所应负担之社会义务,“国家”以法律所为之合理限制即与‘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之本旨不相抵触。”“司法院”释字第577号解释则提及:“又于烟品容器上应为上述之一定标示,纵属对烟品业者财产权有所限制,但该项标示因攸关国民健康,乃烟品财产权所具有之社会义务,且所受限制尚属轻微,未逾越社会义务所应忍受之范围,与‘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之规定,并无违背。”
综上所言,由于财产权有社会义务性,立法者可以确定财产权人为了那些的公共利益(轻、中、高)所须课予之社会义务,而对人民财产权分别为比例性的拘束或剥夺。惟“司法院”释字第400号解释特别将环境生态责任独立与社会义务外,其更可作为环境法上状态责任的宪法基础。且对于重大污染中状态责任(乃至于整治责任)之课予,自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土地资源系人民生存条件所不可或缺,并具有易破坏性及不易回复性等特质,自应以永续使用为维护保育目标,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既享有土地使用之利益,即应负担社会义务,承担适时排除对土地危害之责任,而不应存有对其土地遭受破坏之可能性可予袖手旁观之误解。且基于行政机关人力物力之局限性、土地之有限性、生活环境之易破坏性与难以回复性,乃有必要课予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维持土地秩序之状态责任,尤其于行为人不明时,“状态责任”之课予更属维护土地环境不可避免之手段。②此种状态责任若未达特别牺牲之程度,自未逾财产权社会义务所应忍受之范围。
三、状态责任之立法意旨及其概念之厘清
按行政罚之处罚对象,原则上应以行为人为重心,在例外情形方处罚非行为人,此即所谓“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之区别。其中行为责任依自己或他人之行为,又可分为自己责任与代位责任,③而私法人、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私法组织之代表权人,依“行政罚法”第15条之规定观之,则兼有自己责任与代位责任。④至于状态责任则指人民依法规之规定,对某种状态之维持,因基于“与物之联结关系”而具有义务(尤其是所有人、占有人),因违背此种义务,故须受到行政罚 。故所谓“状态责任”,系以具备排除危害可能性为重要考量,而物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对物的状态原则上应系最为明了而能排除危害者。⑤申言之,现代社会发展多元,危害、干扰公共秩序、环境之类型亦种类繁多,行政机关为尽其所能排除危害、预防危害以达成维护公共秩序的行政任务,在理论上,不应有漏洞存在,故除可动用公权力机关本身之力量外,有时亦得要求人民负担之。故状态责任,系基于对物之支配力,就物之状态所产生之危害,负有防止或排除危害(或称‘排除危险状态或回复安全状态’)之自己责任,其理论依据在于财产权之社会义务,⑥只要人民所增加之负担,并未逾越合理限度,亦为法所许 。⑦惟此等义务本身并无“人的行为”要素存在。易言之,当物之支配权人改变时,继受者自应因承受成为状态责任义务人。⑧
综言之,而立法者之所以课予特定人行政法上义务,究其缘由,不外基于两大类因素:该等特定人之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与容忍等表现形态)所生之“行为责任”,或该等特定人对于物之支配实力,是以物之状态为中心的“状态责任”。前者着眼于人对自己行为之后果的承担可能性与必要性;后者则着眼于特定人对其所具实力支配可能之物之状态的操控可能性与必要性。⑨状态责任的立法意旨已如上述,惟关于其概念之厘清,就学理与实务见解而言,则尚可有以下之补充说明:
(一)状态责任与行为责任之追究顺位
在行政罚之立法中,以处罚违章行为人较为常见,然于部分行政法规,则常见就“状态”课予特定人维护之义务,故当状态责任人非同时为行为人时,其所负的即为纯属状态责任。且对于行为责任人与状态责任人竞合时,原则上应由行政机关就其查获违法之事实,为适当、合理之裁量,并非容许行政机关得恣意选择处罚之对象,择一处罚,或两者皆予处罚。且基于行政罚系处罚行为人为原则,处罚行为人以外之人为例外,如须对行为人以外之人科处行政罚,自应具备充分、合理及适当之理由,且行政机关如对行为人处罚,已足达成行政目的时,即不得对所有权人处罚。对此,“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1月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即指出“建筑法”第91条第1项第1款之规定,究应对建筑物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处罚,应就其查获建筑物违规使用之实际情况,于符合“建筑法”之立法目的为必要裁量,并非容许建筑主管机关恣意选择处罚之对象,择一处罚,或两者皆予处罚。又行政罚系以处罚行为人为原则,处罚行为人以外之人则属例外。建筑主管机关如对行为人处罚,已足达成行政目的时,即不得对建筑物所有权人处罚。于本题情形,擅自变更使用者为行为人,如建筑主管机关已对行为人处罚,并已足达成行政目的时,即不得对所有权人处罚。简言之,行政罚依法律及自治条例规定,虽得同时处罚行为人与所有权人,但若行为人无从调查探知时,处罚所有权人之前提要件为所有权人对该违法行为或状态有过失时,方得例外成为受罚对象,如此方能符合行政罚处罚实际违法行为人之本旨,且亦能突显出行为责任应优先于状态责任之法理。
一般而言,同属状态责任,应由直接管领力者(近者),优先于无直接管领力者(远者)而受处罚,若置直接应负责任之人免受处分,而处分次要责任之人,即非适法,向为实务上之一贯见解。⑩实务上常见有直接管领力者抗辩其为次要责任人,或与行为责任混为一谈:诸如土地之所有人,将土地借用他人使用,该他人又允许第三人掩埋废弃物时,土地之所有人即不得主张其为次要责任之人。按借用人违反约定或依物之性质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或未经贷与人同意,允许第三人使用者,贷与人得终止契约,“民法”第472条第2款定有明文。故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仍有管理之责,于所有土地遭倾倒废弃物时,自应负担排除危害之状态责任。11又事业产出之废弃物纵使确为“委托清除”行为或“委托处理”行为,但尚无使事业以委托之契约关系,免除其应负行政法上义务之理。故仅为委托办理废弃物盛装打包及存放之劳务工作而非法律规定之“从事委托清除行为”或“从事委托处理行为”者,则系争有害污泥之包装贮存作业,其物之状态事实上仍为状态责任人所“产出”而“持有”并“所有”,且于其实力可支配范围内,纵因其委托他人于工作时发生瑕疵者,状态责任人尚可请求该他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约履行,甚而请求瑕疵之担保,此为两造契约之权利义务。是以,状态责任人对于有害事业废弃物,在未清除离开厂区之前,依“废弃物清理法”等相关法令规定,即负有管理及监督系争有害性污泥 有关“贮存”事宜之责任,状态责任人若主张应优先处罚委托之他人,显将“状态责任”与“行为责任”混为一谈。12
再者,前已论之,当行为责任人与状态责任人竞合时,原则上应由行政机关就其查获违法之事实,为适当、合理之裁量,并非容许行政机关得恣意选择处罚之对象,择一处罚,或两者皆予处罚。且基于行政罚系处罚行为人为原则,处罚行为人以外之人为例外,如须对行为人以外之人科处行政罚,自应具备充分、合理及适当之理由,且行政机关如对行为人处罚,已足达成行政目的时,即不得对所有权人处罚。如此方能符合行政罚处罚实际违法行为人之本旨,且亦能突显出行为责任应优先于状态责任之法理。实务上即曾出现行政裁量错误,未顾及原则上行为责任应优先于状态责任之法理,例如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第1项之规定,都市计划范围内土地或建筑物之使用,或从事建造、采取土石、变更地形,违反本法或内政部、直辖市、县(市)(局)政府依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者,当地地方政府或乡、镇、县辖市公所得处其土地或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复原状。其受裁处之对象包括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以非仅以处罚行为人为限,此即所谓“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之竞合,故“都市计划法”第79条对于裁处对象之规定,实即授权行政机关得依个案情形,就裁处对象为选择之裁量。故行政机关对于查获营业场所经营赌博性电动玩具,而依违反“都市计划法”第79条规定,裁处罚锾,并勒令停止使用,若同时对建筑物使用人(即行为责任人)及所有人(即状态责任人)为之时,即应考量行为责任应优先于状态责任之法理。实务上即因此认为若“未考量于存有租赁关系之建物,建物所有权人就出租建物,并无实际管理使用权限,故其监督范围有事实上之局限性,所有权人自无可能于使用人从事违法行为时,即可立即得知而予制止,纵认所有权人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负有维护建物合法使用之状态责任,该责任亦应建立于合理且符合法规目的之基础上。……裁罚标准,虽可维持法律适用之一致性,然仅以查获次数、台数,作为是否处罚所有权人之依据,已难认可区别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本质,且该标准就可对违章行为人裁处之情形下,何以仍认无法达成行政目的,而须一律并予处罚建物所有权人一节,亦无裁量理由可参,已有恣意处分之违法。……”“内政部”2002年11月21日台内营字第0910081556号函着有释示:“……二、为免旨揭规定执行产生疑义并减少类似争讼,请贵府参酌本部八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台八八内营字第八八七三八六九号有关‘建筑法’第九十条规定之执行方式略以:‘……为达直接处罚吓阻行为效果,第一次违规处罚对象为其使用人并副知所有权人,其后经勒令停止使用不停止使用之连续处罚,得认定所有权人为共犯,并罚之。’办理。未予考量‘行政罚法’第14条第1项共同违章行为人之成立要件,不论建物所有权人与使用人有无共同违章之意思联络,遽然以共同违章行为人论处,混淆行政罚共犯与行为责任、状态责任之区别,属违法之裁量,……自得不予适用”。13
(二)状态责任并非结果责任,仍以具备责任条件为前提
所谓状态责任系以具备排除危害可能性为重要考量,而物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对物的状态原则上应系最为明了把握而能排除危害者,而此等义务本身并无“人的行为”要素存在。然状态责任之追究仍应以构成故意、过失为前提,而非有此身份者即当然有此责任之“结果责任”,故“状态责任”及“行为责任”毋宁是一种“状态义务”或“行为义务”,14其重点在于“排除危险、回复安全”之义务。15例如“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不依该法第11条第1款至第7款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者,处新台币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罚锾。经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连续处罚。故行为人是否具有违章之故意或过失,其所应审究者,乃对于“不依第11条第1 款至第7 款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之作为义务违反有无认识,及是否有违章之意欲,或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至于废弃物是否是遭人违法倾倒之事实有无认识,则非所论。16/span>
惟不乏学者认为状态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17申言之,状态责任人因既然有权自由享受使用其所有物,对于其所有物产生对公众之危害,亦有义务加以排除。且基于裁量之简易性、有效性,在认定时首认其有防止危害之可能。危害之发生不以本人有故意或过失为前提,18亦非因行为与危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而承担责任,而是对发生危害之物具有事实上之管领力而负责,因此,危害之发生纵然是自然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亦须负责。19然回归“行政罚法”第7条之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其立法理由亦称“现代国家基于‘有责任始有处罚’之原则,对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处罚,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有可非难性及可归责性为前提,如行为人主观上并非出于故意或过失情形,应无可非难性及可归责性,故第一项明定不予处罚”。故状态责任欲解释为一种结果责任,自有违“行政罚法”第7条之规定。20而实务上似不乏裁判受此影响,称“此行政法上义务并非因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对危害发生间有因果关系而承担责任,而系因为对发生危害之物具有事实管领力而需负责,除系因不可抗力或无期待之可能原因外,苟有违反之状态即应负责”,似将状态责任解释为一种近乎无过失责任,而忽略对责任条件之要求。21惟实务上亦不乏裁判22虽受到前述学理之影响,认为状态责任性质上系一种“结果责任”,但亦同时强调“状态责任”的责任条件,而有以下不同于上述学理内容之论述:“状态责任指人民对于物之性质或状态,原则上最能把握,具有防止危害发生之可能,且依法规之规范目的,亦课予人民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却疏于防止,则对此义务之违反,即须受到行政秩序罚之处罚,核其性质,该项责任乃是一种‘结果责任’”;23或虽援引前述学理所强调状态责任性质上是一种“结果责任”,但仍指明“原告应对其‘过失行为’负有状态责任,可为行政罚义务之人,自为明确”。24换言之,实务上对“结果责任”的理解应未脱离“行政罚法”第7条之立法精神,而非将之定位为“无过失责任”。
惟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基于个别立法中状态责任之特殊性,特别规定(但并非因此采无过失责任)状态责任人之责任要件,甚或援引“民法”之责任概念取代源自于“刑法”之行政罚责任概念,实不乏其例。诸如“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第1项前段即规定,不依规定清除、处理之废弃物,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执行机关得命事业、受托清除处理废弃物者、中介非法清除处理废弃物者、“容许或因重大过失”致废弃物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处理;2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2条第1项第3款规定,未经公告为整治场址之控制场址污染土地关系人“未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致其土地公告为控制场址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锾。而所谓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之认定要件、注意事项、管理措施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依同法第31条第4项规定,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一方面,其突显了状态责任并非不作为之行为责任,即依“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第1项前段认定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是否有“容许或因重大过失”而具状态责任要件适格者,其认定时点,应为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时,而非遭查获时。且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应负责者并非不作为之行为责任,而系“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所规定之状态责任,故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系该规定状态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状态事实,不应再进而解释成同法第52条及第53条第2款贮存废弃物之不作为行为责任;26惟另一方面,上述责任条件之改变,是否亦因此架空了状态责任的立法意旨,故不乏论者批评上述立法体例其实已紊乱了整个行政制裁体系。27
再者,私法规定之表现一般法理者,如与公法之性质具共通性者,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而公法上之连带债务如何成立,并无明文,但民法成立连带债务之规定所表现之一般法理,应与公法具有共通性,故行政机关若欲课予当事人必须与其他事业负起清除事业废弃物之连带责任,必须有相关法律之明文或经债务人明示,始可成立。28
(三)状态责任人不得因另有行为责任人而主张免责
此类情形,多半系因已难以对行为责任人究责,以及状态责任人所负之危害排除责任本系独立之行政法上之义务(例如“废弃物清理法”第11条及第50条),与行为责任之是否究责无涉,自不生行为责任人与状态责任人责任竞合之情形。29
惟就重大污染及急迫之危害防止而言,主管机关基于快速且有效率的危害防止措施,自得裁量选择状态责任人之责任优先于行为责任人,盖前者对于危害来源的特定物具有法律上或事实上作用的支配可能性,较能早日达成危害排除之目的。30特别是在重大污染所形成的整治责任,需要整治的土地不属于行为责任人所有,且行为责任人无财政上给付能力时,基于立法目的考量快速且有效的危害排除,由状态责任人负担自较能解决问题。31惟对重大污染所形成之状态责任(乃至于升级为所谓的“整治责任”,参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要求是否应有其一定之界限,已系“宪法”议题。纵令立法重点在于追究行为责任人,惟其中涉及公法上义务继受是否溯及既往,以及责任承担之界限等重要问题,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安顺厂案即为台湾地区之着例。32其因此衍生“司法院”释字第714号解释,其中公法上义务继受是否溯及既往的问题,该号解释认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将所列规定适用于该法施行前已发生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污染行为人,使其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后之污染状况负整治义务等。其意旨仅在揭示前述整治义务以仍继续存在之污染状况为规范客体,不因污染之行为发生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前或施行后而有所不同;反之,施行前终了之污染行为,如于施行后已无污染状况,系争规定则无适用之余地,是尚难谓牴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惟“司法院”释字第714号解释并未论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是否应完整建立状态责任之体系,以及行为责任义务继受的要件,恐徒留日后之争议。33
盖状态责任人既然有权自由享受使用其所有物,对于其所有物产生对公众之危害,亦有义务加以排除。故当物之支配权人改变时,继受者自应因承受成为状态责任义务人。换言之,状态责任系一种对物责任,状态责任所致之义务,乃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义务,通常是排除危险,回复物之安全状态的义务,此等义务本身并无“人的行为”要素存在。故当物之支配权人改变时——所有权人改变或具有事实管领能力者改变,基于危险状态所形成之状态责任义务人自然随之改变,严格而言,并不涉及一般所谓权利义务的继受问题。典型之例,如买受负有违建之建筑物者,自应因承受该违建物所有权而成为状态责任义务人,其因此所负之受罚或违建拆除义务并不因该违章建筑非其所建而得以免除其责,理由正在于其所负之责任为状态责任,而非行为责任。34
惟对重大污染所形成之状态责任(乃至于升级为所谓的“整治责任”)要求是否应有其一定之界限,已系“宪法”议题。其中涉及公法上义务继受是否溯及既往,以及责任承担之界限等重要问题,尤其是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求取调和与均衡,此时恐无法无限制地课予在义务继受时之状态责任。35否则实务上即会采取以下看法:“盖‘废弃物清理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土地或建筑物与公共卫生有关之一般废弃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系无法追究‘行为责任’时,基于防止污染之公益需求,才不得不课以所有人或实际管领控制之占有人之状态责任。是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于所管理土地遭人弃置废弃物,自应负担排除危害之责任。所谓‘状态责任’者,实系以具备排除危害可能性为重要考量,而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对物的状态一般应系最为明了把握而能排除危害者。准此而论,课予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维持土地秩序之状态责任,要属维护土地环境不可避免之手段,只要符合前开法律规定之要件者,不问其土地面积大小,位在何处,均不得以其现实上无法完全尽到监督责任而主张免除其清除处理之责”。36
四、结语
按行政罚上之状态责任若未达特别牺牲之程度,自未逾财产权社会义务所应忍受之范围。惟就环境保护的效益而言,一方面尽管“课予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维持土地秩序之状态责任,要属维护土地环境不可避免之手段,只要法律规定之要件者,不问其土地面积大小,位在何处,均不得以其现实上无法完全尽到监督责任而主张免除其清除处理之责”,惟行政罚上之状态责任的实际执行成效其实是有待评估,另一方面状态责任只是环境保护事后究责的手段之一。环境行政法真正需要建构的还是预先维护的手段,但在此种制度未能有效建构前,状态责任的亡羊补牢还是在环境行政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苏 婷)
①参见林昱梅:《土地所有人之土壤污染整治责任及其界限——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1 BvR 242/91;315/99)评释》,载《黄宗乐教授六秩祝贺公法学篇(二)》,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72页。
②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度判字第941号判决。
③参见“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0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5条之4。
④参见李惠宗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3页以下。
⑤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度简字第662号判决。
⑥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9年度诉字第114号判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度简字第662号判决。
⑦参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10年度简字第270号判决。
⑧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8年度简字第731号判决。
⑨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15年度判字第157号判决。
⑩参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9年度诉字第548号判决、2010年度诉字第117号判决。
11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度诉字第3000号判决。
12参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9年度简字第165号判决。
13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9年度诉字第667号判决。
14参见洪家殷:《行政罚之状态责任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六年诉字第一二八八号判决简评》,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04期,第330页。
15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09年度判字第452号判决。
16参见“行政院环保署”96年1月31日环署废字第0960004566号解释函、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8年度简字第667号判决。
17参见李惠宗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6页。
18参见蔡宗珍:《论秩序行政下之状态责任》,载《第三届行政法实务与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页。
19参见黄启祯:《干涉行政法上责任人之探讨》,载《当代公法新论(中)》,第301页以下。
20参见洪家殷:《行政罚之状态责任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六年诉字第一二八八号判决简评》,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04期,第330页。
21参见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010年度简字第66号判决。
22就关键字搜寻,其清一色均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之裁判。
23参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度诉字第1011号判决。
24参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8年度诉字第167号判决。
25故依“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认定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是否有“容许或因重大过失”而具状态责任要件适格者,其认定时点,应为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时,而非遭查获时。且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应负责者并非不作为之行为责任,而系“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所规定之状态责任,故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系该规定状态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状态事实。此为多数之实务见解(例如“最高行政法院”2016年度判字第537号判决、2015年度判字第号663号判决)。惟亦有实务见解认为“废弃物清理法”第71条第1项规定,系课容许或因重大过失致废弃物遭非法弃置于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处理之责任,虽行为人以不作为之方式违反该规定,惟基本上仍属行为责任,而非状态责任,纵有因故无法对于行为人予以追究,而转为对于土地所有人追究状态责任之可能,惟仍应以追究行为责任人为优先顺位,无法追究时始转为追究状态责任人,而非可迳对状态责任人予以究责(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16年度判字第128号判决)。惟依此见解混淆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的本质,应不可采。
26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度判字第537号判决。
27参见李介民:《干涉行政法上整治责任之继受及界限——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为范围——兼评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诉字第九四一号判决》,载《警学丛刊》2007年第3期,第79页以下。
28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度判字第203号判决。
29实务上对此之认定似颇为严格,特别是在重大污染之情形,例如纵令状态责任人主张其已设“围篱多处,防止他人任意入内倾倒废弃物,已尽废弃物清理法上之防护义务,且主动提供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之行为人为何者之具体事证”,法院亦往往认定“衡诸一般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土地侵害者与土地权利者常非同一人,是若法律仅欲处罚实际侵害行为者,殊无必要另外规范土地所有权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亦为处罚对象,足证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纵非实际行为者,亦有可能因其管理之土地范围遭受破坏而受归责……纵令原告主张倾倒废弃物者另有他人为真实,仍无碍其依法应负清除废弃物之责任,亦不因原告有无设置围篱防范,而认已尽依法清除废弃物之责任。是原告主张,均非可采”。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度简字第662号判决。
30参见李介民:《干涉行政法上整治责任之继受及界限——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为范围——兼评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诉字第九四一号判决》,载《警学丛刊》2007年第3期,第82页。
31同上,第83页。
32参见“最高行政法院”2007年度判字第1954号判决。
33参见李建良:《污染行为、整治义务与责任继受的法律关联与宪法思辨——释字第714号解释》,载《台湾法学杂志》2013年第238期,第72页以下。
34参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8年度简字第731号判决、2007年度诉字第2460号判决。
35参见周元浙:《国家承担水土保持义务之责任》,载《军法专刊》2009年第6期,第9页。
36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9年度诉字第114号判决。
D927.582.1;D927.582.683
A
1674-8557(2017)03-0022-08
2017-08-31
吴志光(1966-),男,台湾新北人,台湾辅仁大学学士后法律学系教授,辅仁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兼学士后法律学系系主任,德国汉堡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