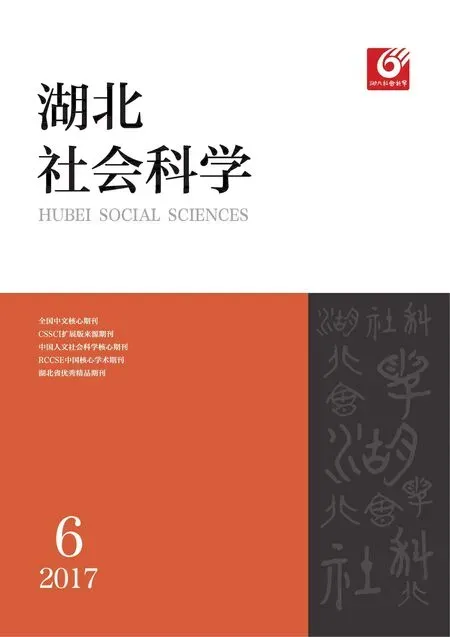遮蔽与祛蔽:劳动的教育意蕴
——基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价值澄明
徐海娇,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遮蔽与祛蔽:劳动的教育意蕴
——基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价值澄明
徐海娇,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如何理解劳动的概念,是探讨劳动教育的首要问题,然而受制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劳动概念时常遭到曲解和误读。“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门的一把钥匙。回到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三重向度阐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揭示马克思劳动概念在教育场域中求真、至善、臻美的意蕴,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深化与创新新时期下的劳动教育。
马克思;劳动概念;扭曲:澄明:教育意蕴
2015年8月3日,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意见》的出台一方面折射出党和政府对于劳动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劳动在教育场域中被弱化、软化及淡化的窘境。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一项内容被予以肯定,并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和内容上均有所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曾以不同形式开展过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在培养学生劳动知识、技能、热爱劳动情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回顾新中国近七十年劳动教育历史轨迹,可以看到由于对“劳动”概念存在种种误读,劳动在一定时期内曾被“妖魔化”为惩罚的手段,扭曲为改造学生思想的工具,窄化为培养学生技能的训练,遮蔽了劳动的本真教育意蕴。
劳动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培养人的劳动能力也是各级各类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新时期,重提劳动教育,是否意味着让学生重新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呢?“劳动”是劳动教育的本体论范畴,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是由劳动的内涵这一本体论问题所决定的。因此,如何理解劳动的概念,成为研究劳动教育的首要问题。基于马克思劳动概念,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三重阐释劳动概念的内涵,揭示其在教育场域中求真、至善、臻美的意蕴,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影响劳动教育的实施及效果,而且关涉劳动教育在“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
一、遮蔽之象:教育场域中“劳动概念”的扭曲
在全面考察了全球的教育发展动向,为决策者
(一)僵化为惩罚限制的规训手段。
从词源学上来看,在古汉语当中,“劳”作为会意字,其小篆字形上面是“焱”,表灯火通明的意义;中间是“冖”,表示房屋,下面是“力”,表示用力。本义是使受辛苦,如“是犹推舟于陆地,劳而无功”(《庄子》)。“动”即“动,作也”(《说文解字》),表示“活动”、“行动”、“移动”,如“终将岁勤动”(《孟子》)。在欧洲,劳动一词在词源上也与痛苦或者厌烦有着历史性联系。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雷蒙·威廉斯在其1976年出版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从词源学上梳理了“劳动(labour)”词义的演绎与发展:“其中的两个例子就是:‘开始工作(laboure)……不辞劳苦(toure)与‘劳动’(labour)和悲痛(soru)(这两个例子都出现在13世纪)。这两个意涵——工作与辛苦(痛苦)——与labour的词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p256)
劳动具有劳累、辛苦的意涵,教育场域内“劳动”的概念在一定时期内被断章取义地肢解为“劳动之烦”,将劳动等同于限制学生自由、规训学生行为的教化手段。“劳动”被误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学生犯了错误,教师将“劳动”做成一种惩罚的手段。例如,让犯错误的儿童打扫厕所、做值日、捡垃圾……这种将打扫卫生、脏的、苦的、累的都让犯错的儿童来做的惩罚方式,通过让其身体受苦,以其对痛苦的恐惧和规避防止被禁止行为的重复发生,从而达到规训其行为的目的。然而这种将劳动污名化为惩罚的手段,扭曲为外在强加于学生的奴役工具,这种异化加深了儿童与劳动之间的隔阂,使得劳动无法走进儿童的心灵世界。将劳动僵化为惩罚规训的手段,“劳动之烦”的惩罚训诫之意遮蔽了劳动的教育意蕴,在儿童的内心留下惧怕与厌恶的阴影,对劳动产生排斥心理。劳动被畸形化地误读为可耻的、丢人的、消极的行为,长以此往,这种观念必然有损儿童心灵的正常生长秩序,致使其扭曲地发展,也必将使劳动教育日趋边缘化、污名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之义。
(二)窄化为政治思想的改造工具。
中国自古就有“劳动心者治人,劳动力者治于人”这一关于劳动与精神关系问题的探讨,这一问题也一直受到西方哲学的广泛关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马克思、汉娜·阿伦特等都曾论述过。马克思是这一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劳动向现实劳动的回归,特别是马克思“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3](p538)这一口号更是一度被我国奉为圭臬,将劳动被视为根除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等剥削阶级思想的改造利器。
“体力劳动是改造思想的利器”这一思想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文革”时期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课”,“四人帮”一伙打着所谓“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教育革命”的旗号,讲什么“劳动越多越好”,“知识越多越反动”,通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体力劳动来“反资反修”,肆意破坏教育事业,以劳动代替教学。历史到现在给人们留下了浓厚的阴影,有种谈虎色变的后遗症。尽管拨乱反正后,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劳动作为塑造学生政治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教育的手段一直延续至今。不同于“文革”时期以劳动取代教学的极端现象,此时各级各类学校将劳动作为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劳动教育被狭隘化为德育内容之一,只见劳动教育与德育的重要关系,忽视其与智育、体育、美育等的关系,忽视其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本真价值意蕴。
(三)弱化为生产技能的训练方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础性贡献就在于其揭示了劳动价值问题,认为价值来源于生产劳动,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主导下,人类社会对于劳动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劳动被抬上创造物质财富的神殿。劳动创造物质财富这一观念对我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文革”后随着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向教育提出了培养拥有现代知识与技术的人才规格,劳动在教育场域内被等同于培养潜在劳动力,并以劳动技术教育的形式被列为整体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把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一方面,组织学生到校办厂(场)或校外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去农村、田间劳动。这一时期,劳动概念的“经济之维”日渐凸显,浓重的功利化色彩遮掩了本真的育人功能。一些学校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纷纷建立校办工厂、农场或实验园地,组织学生进行劳动实践,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与育人初衷背道而驰,在追求利润和收益的驱动下,学生被视为创造利润的潜在劳动力,向其灌输校办工厂、农场所需的基本劳动技能。劳动在这一时期被弱化为生产技能的培训,以往教育形式中不可或缺的、以实现人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独立存在的劳动教育,在此等同于生产技能的培训,明显弱化了劳动的本真教育意蕴。
二、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向度
受自考茨基以来特别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以及特殊时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制约,我们对劳动概念产生种种误读,将劳动概念局限于工具理性范畴,加之囿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下的劳动,因而往往只谈劳动作为人生存的物质基础的价值,视而不见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旨趣。回到马克思本身,劳动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从哲学层面,从人的生命活动、人的存在方式来加以把握和理解的深刻概念。恰如卢卡奇所说,“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哲学概念。”[4](p137-138)“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起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前提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个层面上阐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一)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作为一种“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5](p105)从这一角度不难理解,作为“肉体的主体”有其物质生活的需要,要想生存,必须满足自身吃喝拉撒睡等一切现实的需求。为了维持生命,人必须进行劳动,通过使用一切自然力来占有、改造自然物,使自身的劳动固定、物化在某个对象当中,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恰如马克思所言:“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5](p56)人类只有通过劳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撇开了特定的社会形式,认为劳动是不以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的条件,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口腹之欲、安身立命之所等现实的物质生活所需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换言之,劳动是人类生活得以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在一般的情况下,自然物不能自发地满足人的需要,而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成为人生存的物质条件。劳动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如若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不去改造自然物,就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人就没有衣食之源,就没有生存条件,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个社会摆脱自然力量的统治”的开始,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建造适用于人的生存的对象世界,劳动使人类从自然界中跃升出来,是人类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劳动的第一重向度,即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劳动的过程之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了预定的变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既满足了人的生命活动需求,又创造了人本身,使人获得了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的存在。
(二)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劳动。
从人与自然的向度出发,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劳动作为人类独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进行的,劳动本身就产生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如若不能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孤立的个人是不能改造自然物的和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是自生的,既不是外在于也不是强加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内生于人的劳动之中,并非是凌驾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先验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任何劳动“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6](p24)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一方面,人的劳动实践离不开社会,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以实现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并非是孤立的人与抽象的自然物之间的简单结合,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可以说,社会关系不是自生的,而是形成于人的现实的劳动实践之中,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脱离个人的社会或脱离社会的个人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虚构幻想之中;另一方面,劳动增强了人的社会性,劳动的开展大大丰富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7](p270)现实的人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而非在与世隔绝、纯粹自然状态下进行,劳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如同费希特指出的,“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8](p18)
(三)人与自身关系层面上的劳动。
古典经济学家将劳动囿于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马克思的突破在于揭示创造物质财富并不是劳动的终极目的,劳动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去“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从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高度出发深刻揭示了人在劳动中创造和发展人自身。马克思富有洞察力地发现,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己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9](p177)劳动这种“自由自居的活动”,不仅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建立了人化的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活动中建立了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人自身。
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5](p58)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出发来考察劳动,认为人在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体的同时,也是人展示、实现或创造自我的过程,是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如果没有了对象,人就会失去自己的类生活,如果没有对象性的活动,人就无法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可见,劳动的过程就是人自我张扬、自我实现的过程。就好比人们为了更清楚地认清自己的面貌,需要借助镜子一样,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这面认清自己的镜子。“生产……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10](p37)基于此,马克思创造性地认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不仅是获得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和确证人自身,通过劳动使自己的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等得到提升。人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也在劳动中不断地发展和充实自己。
三、澄明之境: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教育意蕴
近年来,“信息化”、“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谷歌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以4 1战胜韩国围棋职业九段李世石,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人工智能(AI)的威力,人工智能终结劳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劳动的基础性作用在“后工业化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态势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功能成为争论的聚焦点。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重提劳动教育,是否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劳动概念在教育场域中还有没有解释力和批判力?对于这些问题,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劳动概念三重向度,回到教育场域,才能澄清问题,揭示马克思劳动概念被遮蔽的教育意蕴。
(一)求真——认知之真。
“真”的尺度,侧重反映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是对事物存在的变化规律的认同,体现着合规律性的认识世界目标。人的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11](p23)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人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体的同时,离不开对于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与认同,也把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可见,劳动并不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地施加于自然物,人要想通过劳动实现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变,就必须遵循作为外在必然性强加给人的客体对象的尺度。换言之,人必须按照客体对象的必然规律改变世界,才能支配客体对象,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得自由,离开“真”的尺度,一切劳动都是徒劳与枉然的。
正如列宁所说:“人在自己的实践中面向着客体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12](p200),教育场域中的“劳动”,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活动,合规律性是人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对客体进行改造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而这一前提的获得,就是人自身必须能够求真。教育场域中的劳动,从来都不是背离“真”的尺度的“用脑不用手”的低下活动,不能断章取义地用“脑力劳动”和“体力活动”来人为划分割裂劳动教人求真的意蕴。教育场域中的劳动本真地蕴含着“求真”的尺度,在劳动中教人探求真知,探求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认知之真,对于“真”的遵循,是学生改造客观事物的劳动实践的前提基础。戴维·珀金斯教授作为“零点项目”的创始人在《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中提出通过开放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去发现,从而实现真正的学习。[13](p71)教育场域中的劳动,在对客体的否定性改造的过程中恰好为学生提供了具有生命力的开放性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培养智力方面的好奇心和对世界奥秘的探索心。可见,“求真”是劳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劳动的过程中激发受学生探求真理的热情和能力,并且尊重认知之真,在合规律性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二)至善——伦理之善。
“善”的尺度,侧重反映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是对整体关系观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和谐关系的认同,体现着合目的性改造世界的目标。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劳动,现实中的人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人要想在社会关系之中生存和发展,必须要遵循周围个体、群体、社会所普遍公认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按照他人、群体、社会的共同利益去进行。劳动使个体在为自己创造生活的同时,客观上也为他人创造了生活,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互为状态。可见,作为交往性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离不开对于“善”的追求。
社会交往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从事劳动是人们之间社会联系与交往不可或缺的纽带。黑格尔指出:“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具有特殊目的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幸福的同时满足自己”。[14](p197)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使得学生由独立的个体存在转变为走向公共的关系性存在。劳动作为一种教化的形式,为学生个体由个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提供了媒介。教育场域中的劳动,不是单个个体的活动,而是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交往活动,在交往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个性的同时,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教育场域中的劳动不同于其他领域中的劳动以追求财富和价值为终极旨归,劳动教育以引领学生成长为旨趣,通过学生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交流以及相互理解,在劳动的过程中塑造儿童的品性,引导学生平等地进行交往,融入公共生活,获得公共理性的浸染。
(三)臻美——成人之美。
“美”的尺度,侧重反映人与世界的情感关系,体现着合感受性的超越。人作为类存在物,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要遵循着“真”与“善”的尺度,而且也要遵循“美”的尺度。背弃了“美”的尺度,人就不能在实践活动中真正达到主客体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就难以创造和重塑人的外部与自身的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p58)正是通过劳动,人在不断创造和确立的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确证人自身以及人类的全部历史。因此,人通过劳动而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人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基础,而且还表现为人通过劳动而使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得以全部展示,使自身的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鉴赏能力等得到提升。
对于教育,康德认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称之为人”,“教育或许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每一代都向着人性的完满实现更进一步;因为在教育背后,存在着关于人类存在之完满性的伟大秘密。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来越好地得到发展,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来的、更加幸福的人类的前景”。[15](p5-6)劳动在教育场域中,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在学生个体在把自身的目的、智力、知识、技能以及体力投射到劳动对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本质力量积淀、凝聚到对象中,不仅实现了对外在对象的占有,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学生个体自身天性的发展。可以说,劳动教育,学生个体通过劳动实现目标和理想的过程中,也是其自我实现的过程,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不仅收获自身创造的劳动产品,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内心的充实和满足。教育场域的劳动,使得人生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并赋予人的生活世界以主体性、生成性、超越性的特点。教育的终极指向就是力求超越现实,所以人总是处于一种相对的“有限性”和不完满的生存境况之中,处于对整体性、完整性价值理想与生存意义的“美”的追求之中。
结语
可以说,教育场域中的“劳动”本真地蕴含着“真”、“善”、“美”,是教人求真、教人至善、教人臻美的有机统一整体,既不能将扭曲为惩罚规训的手段,也不能将其孤立为政治改造的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培训方式。新时期,我们澄明场域中“劳动”的“真”、“善”、“美”的价值意蕴,重提劳动教育,并不代表试图以劳动能替代一切教化的路径,劳动只是教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因而,劳动教育只有与其他各类教育的路径相结合,才能发挥它自身的教化之意。正如马卡连柯所讲,“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只有把劳动作为总的体系的一部分时,劳动才可能成为教育的手段。”[16](p13-14)因而,合理的劳动教育不是抹杀其他各类教育的积极性,而是与其他教化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实现劳动教育“真”、“善”、“美”的本真意蕴。
[1][伊朗]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马胜利,高毅,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美]戴维·珀金斯.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M].杨彦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1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5][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6]吴式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张 豫
G40
A
1003-8477(2017)06-0013-06
徐海娇(1989—),女,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柳海民(1953—),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基于科学计量学的教育知识管理及其综合效益研究”(20120043110015)。进行教育体系的革新提供合理意见以及指明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时,S·拉塞克和G·维迪努在《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中指出:“如果有一个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焦点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肯定是在教育实践中确立并建立普通教育过程同劳动世界之间的连接,而目前的状态则似乎表明,教育和劳动这两个世界仍然互相漠不关心。”[1](p162)劳动与教育的疏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不同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劳动概念时常遭到曲解和误读,形式化、扭曲化、单一化的视角遮蔽了劳动的本真意蕴,使得“污名化”的劳动教育蒙上了价值之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