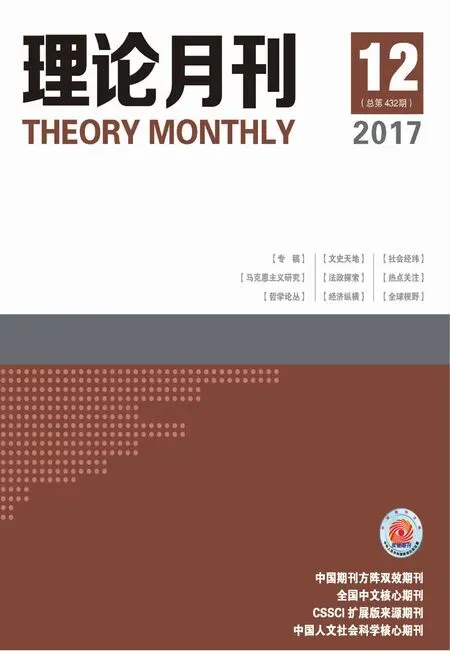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存在论题
□吴三喜,张文琦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存在论题
□吴三喜1,张文琦2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在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中有一种从纯粹概念出发进行推导的本体论证明,康德对此提出了一种批判,其核心主张即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这就是所谓康德的存在论题。康德的存在论题意在区分存在和实在,将实在归为质的范畴,而将存在纳入模态范畴。模态范畴中的存有—非有表达的是与认识能力中的知性的经验运用之能力的关系,而知性的经验运用之能力的前提是对客体的知觉先行于客体的概念。海德格尔对康德存在论题的现象学解释集中在对知觉概念的分析上,他首先描述出知觉的三重结构,即行知觉、被知觉性以及被知觉者,进而将康德那里的被知觉性与认识主体之关系还原为存在与此在之关系,这一还原是通过对先验自我的存在论—生存论改造而获得的。
存在;实在;被知觉性;先验自我;此在
纵观康德著述可以发现,在康德哲学中“存在”问题很少获得专题化的论述,这与康德对形而上学与先验哲学之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先验哲学是一切传统形而上学之不再可能的前提,同时也是一切未来形而上学之可能的起点,在没有先行厘清先验哲学工作之前,任何越界的形而上学谈论都是没有根基的。然而即便如此,康德也没有完全把存在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等同起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一方面在“先验分析论”部分将“存有—非有”归入模态范畴之中,另一方面又在“先验辨证论”部分展开了对“存在”和“实在”的区分工作。这两部分的论述共同组成了海德格尔所谓康德的存在论题的核心内容。然而,令海德格尔不满的是,与中世纪哲学(尤其是托马斯哲学)相比,康德的存在论题过于看重存在与认识能力的关系,从而使得存在问题最终来说成为一种对象性问题。海德格尔对康德存在论题的解构,正在于破除这样一种对象性还原,力图使存在问题彻底出离近代表象主义认识论模式。
1 康德的存在论题
海德格尔所说的康德的存在论题,指的是康德在反驳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时所提出来的一个核心主张,即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这一主张早在1763年的论文《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中就被表达出来了:“存在根本不是某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者规定性”[1]78。 其更为成熟的表达则是在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之中:“‘存在’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2]476。在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中,本体论证明是完全不依赖经验的、单独从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的一种证明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左右的安瑟尔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一个借助三段论格式来完成的推论:大前提:上帝依其概念乃是最完满的存在者;小前提:最完满的存在者概念必然包含存在;结论:上帝存在。上帝就其概念规定而言,必然是最完满的存在者,既然是最完满的存在者,那么存在就必然属于这样的存在者,否则它就不是最完满的了,因而可以推出上帝存在。在这个证明中,概念或概念规定指的是本质,也即康德用“实在”(reales)一词所指的东西,而存在实际指的就是实存,上帝存在指的就是上帝实存。
针对这一证明,康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反驳,这个反驳的核心就是如下一种主张: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存在论题中的“实在”(reales),在康德那里取一种特别的用法,这种用法不能等同于实在论意义上的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实在的乃是那属于事物的。当康德谈论omnitudo realitatis,实在性之大全时,他所指的并非真正现成者的大全,恰恰相反是可能的实事规定性之大全,实事内涵、本质性、可能物之大全……实在性是可能物一般的何所内涵,无论其是否现实(即我们现代意义的‘实在’)。实在性概念同义于柏拉图的idea概念,后者是当我问ti esti,这存在者是什么之时对一存在者被把握到的东西”[3]40。可见,在康德的论题中,实在指的乃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事物的“何所内涵”(Wasgehalt)。我们切不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康德这里所说的实在,他对实在的用法延续的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在存在论题中,除了实在概念需要辨析之外,存在这一概念也需要加以界定。康德在此使用的“Sein”,指的是上帝的实存、实有,是实在论意义上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主张用“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或“现成性”(Vorhandenheit)来代替存在论题中的存在一词[3]32。
康德为什么会反对说存在(实存、实有、现成存在)不是实在(概念、本质、何所内涵)的谓词呢?在康德的范畴表中,实在性概念属于质的范畴,而存在、实存或实有则属于模态范畴[2]71-72。所谓质的范畴,指的是在由它主导的判断中,谓词对主词或者加以肯定和赞同,或者是加以否定,实在性指的是谓词对主词加以肯定的判断之形式。与质的范畴不同,模态范畴指的是判断主体对判断中的东西所持有的态度,存在—实存—实有作为模态范畴指的是在其中判断主体对判断对象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判断之形式。由此可见,实在性概念关涉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是事物自身按其概念来说应有的所有内涵,它不关涉判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实在性不需要超出事物的本质内涵;存在—实存关涉的不是事物与自身的关系,而是事物与主体的关系,当这样作出一个实存判断时,就必须超出事物自身的本质规定而将一种关系补充添加到事物身上。一百个可能的塔勒和一百个现实的塔勒就其实在性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实在性指的是本质规定,本质规定是不依对象的可能性或现实性而不同的。由此来看,“A实存”(比如上帝实存)和“A是B”(比如上帝是无限完满的)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判断:A是B这种陈述关涉的只是A的实在性,是对A的本质内涵的规定;A实存这种陈述不是对A的本质内涵的规定,而是对一种关系的设定,这种关系指的是事物的概念内容和概念对象之间的关系,“实有陈述的综合所关涉的并非物及其关系的实在规定,而是那在实有陈述中所设定的,并且补充设定到单纯表象、概念上去的东西,是‘现实的物和我自身的关涉’。被设定的关系是完整的概念内容、概念完全的实在性和概念的对象的关系。在实有陈述的综合中自在自为、直截了当地设定了在概念中被意指的事物。述谓性综合在事态之内活动。实有综合关涉整体事态与其对象的关系……在实有设定中我们必须越出概念之外。那被综合地附加设定在概念上的,正是概念对其对象亦即现实者的关系”[3]49。
与述谓陈述相比,实有陈述涉及的是对事物的“绝对肯定”:“在一个实存着的东西中比在一个单纯可能的东西中没有设定任何更多的东西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说的是该事物的谓词);然而,借助某种实存着的东西要比借助一个单纯可能的东西设定了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也涉及对事物自身的绝对肯定”[1]82。如此看来,在康德的规定中,实存指的就是对一个事物的绝对肯定[1]80。正如海德格尔所表明的,实有陈述并非像述谓陈述那样止留于事物的实在规定之内,而是将事物的所有实在规定一起加以绝对地设定了。所谓绝对地设定或肯定,指的是将如下一种关联置入眼帘:概念的对象与概念内涵之间的关联。这种将一种关联置入眼帘的功能其实就是康德在论述模态范畴时强调的主体对客体所持有的态度,也即与“认识能力”的关系:“模态的诸范畴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们丝毫也不增加它们作为谓词附加于其上的那个作为客体规定的概念,而只是表达出对认识能力的关系”[2]197。根据康德的表述,模态范畴中的存有—非有(即实存—非实存)表达的是与认识能力中的知性的经验运用之能力的关系,而知性的经验运用之能力的前提是对客体的知觉先行于客体的概念。康德指出,如若没有对某物的知觉而只有对其的概念思维,那么这只能意味着此物的可能性,而非意味着此物的现实性,也即实存—实有,对某物的知觉才是某物实存的唯一担保[2]201。如此一来,康德存在论题的关隘就转渡为知觉问题:实有—实存作为模态范畴表明的是认识主体对概念内涵的一种绝对肯定—设定,这种绝对肯定之能够成立必须借助先行的知觉,因为只有知觉才能为概念提供材料,它是实存的唯一担保。
2 知觉的结构
既然康德存在论题的关键被表明为知觉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恰切地理解知觉呢?康德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知觉这一概念的呢?在谈及先天感性形式时康德说道,一切现象之形式均在一切现实之知觉之前被给予我们了;并将这些在现实知觉之前就具备了的、可以被先天认识的东西称为纯直观[2]31/42。在康德那里,知觉与感性、感觉均有不同。感性指的是以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而获得表象的那种能力,康德将其称为一种接受能力;而感觉指的则是对象对接受能力产生刺激时在表象能力上所造成的一种结果[2]25。感性指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刻画特征是其被动的接受性,而感觉不是在能力上来使用的,而是感性能力的一种结果。在康德那里,知觉多与“现实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它与作为能力的感性能力接近,但是与感性能力不同,康德并没有突出知觉也是一种被动接受性能力。除此之外,知觉还可以在一种结果的意义上来使用,这时它就与作为结果的感觉类似,但是与感觉不同的是,康德并没有突出知觉作为一种结果是一种单纯的接受性结果。海德格尔将前一种意义上的知觉即作为一种能力的知觉称为“行知觉”(Wahrnehmen),突出知觉能力的行使;将后一种结果意义上的知觉称为“被知觉者”,突出知觉的结果意义。这里的被知觉者,指的不是物自身,而是在知觉中被知觉着的东西。当康德说实存就是知觉时,这里知觉是哪种意义上的知觉呢?是行知觉还是被知觉者?海德格尔认为都不是。他进而提出了知觉的第三种意义,即“被知觉性”(Wahrgenommenheit)[3]58。 康德所说的实存与知觉的等同,指的就是这种作为被知觉性的知觉,说某一物实存—存在,其实就是说此物的被知觉性和被发现性。这样一来,知觉就其自身而言就具备了一个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是由行知觉、被知觉者和被知觉性共同组建的,这样组建起来的知觉概念就获得了如下一种完整的意义:“知觉着把自己指向被知觉者,以至于把被知觉者领会为在其被知觉性本身之中的被知觉者”[3]70。
在由三重维度组建的知觉的结构中,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行知觉的“把自己指向”之特性。简单地说,知觉“把自己指向”某物说的就是对某一对象的知觉,知觉行为具有与某物相关之特征,以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将行为的这种“把自己指向”某物之结构称为意向性:“就它们是对某物的意识而言,它们被说成是‘意向地关涉于’这个东西”[4]50。通过指向之结构,知觉行为将自身表明为一种意向性行为。在意向性中,有一个由“意向”和“所意向”构成的二元结构。意向性中的朝向某物而为就是意向行为的意向或 “意指”,而被意向或被意指的东西就是“所意向”。按照自然态度的观点,意向性的意向—所意向结构,指的无非就是主体—知觉—客体这一结构,现成的心理主体通过知觉行为活动于某一客体,知觉行为在两个现成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也是现成性的:“知觉关系就是两个现成者之间的一种现成关系”[3]73。 由此以来,所谓意向关系,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由某一现成主体肇始的、指向某一现成客体的一种现成关系。正如海德格尔表明的,这样的理解方式必然蕴含着如下一种可能,即主体无需意向性便可存在,意向性只是当主体指向客体时才产生的一种现成关系。自然态度对意向性的误解,错失了主体本身就是意向性的这一关键规定。意向性的结构代表着行为之实施者的主体的本质构成:“意向性作为行为自身的结构就是自身施为着的主体之结构。意向性作为这一关系之关系特性存在于自身施为着的主体之存在方式之中”[3]75。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又容易造成另一种误解。既然意向性是一种主体之规定,主体的一切意向活动作为属于主观领域的体验行为均是内在性的,这样其面临的困境就是内在性如何超越自身以便真正切中外部世界。对意向关系的这种误解非常普遍,甚至连尼古拉·哈特曼这样的亲现象学哲学家都对此产生了疑惑。海德格尔指出,对意向性和意向关系的这种误解,导源于某种特定的认识论态度,理论态度的居先性压倒了现象自身的表达。就现象自身来看,实情毋宁是麦克道威尔描述过的如下一种情况:“人们能够思维比如春天开始了,而且春天开始了这同一个事项能够是实际情况”[5]50。 也即是说,意向性中的所意向不是什么感觉或表象,而就是被意向者本身。在意向活动中,我们并非局限在主观性领域之内,而是直接指向事物本身。当我说我的书本放在教室的桌子上时,我并非是在谈论书本的表象,而是就在谈论我的那些书本本身。由此可见,从这种得到正切理解的意向性出发,我们根本就没有遭遇上面提到的那个困境,即主观性领域内的体验如何超越自身的内在性去抵达外在性。意向性不像哈特曼等人设想的那样是内在性的,它本身就是超越性的[3]78。 与传统的自我、主体概念相比,意向性应该获得更加本源的地位,这样,从主体来理解意向性的道路就应该被翻转成从意向性来理解主体。鉴于意向性指的就是与物的直接关联、即物而在,因而传统的封闭的自我概念就无法再成立。但是正如布伦塔诺区分的,意向性是适合于心理现象而非物理现象的属性,也即意向性是与主体等概念所言说的东西更加接近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就在主体、自我等概念之外提出了另一个概念——Dasein来表达这种意向性。
在海德格尔解释过的康德的存在论题中,实存—存在被表明与知觉等同,而我们已经指出,实存既不是知觉结构中的行知觉,也不是其中的被知觉者,与其接近的可能是被知觉性。从形式上看,被知觉性看似属于被知觉者,也即属于意向行为中的所意向。然而,意向行为的所意向奠定在意向的指向意义之中,由意向的指向意义给出的所意向是包含意蕴的东西,比如知觉到一个作为工具的锤头,但是不管这种意蕴如何,在其中都发现不了所谓的被知觉性,如此一来被知觉性就有可能不是被知觉者身上的某类东西。当否定了被知觉性属于被知觉者之后,我们便倾向于将被知觉性归属给行知觉,也即意向。从正确理解的意向性出发,被知觉性属于意向并不是说它就属于主观领域,尤其不能够说其属于主体的认识能力。但是在康德的存在论题中,存在却正是通过知觉的担保被还原为了与认识能力相一致的被知觉性。也即是说,存在乃是现实的被认识状态,潜在的存在就是潜在的可被认识性,必然的存在则是必然的可被认识性[2]197[6]546。 这样,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主体性哲学家,在他那里存在问题被置换成了对象性问题,而对象性问题说到底要依赖于对主体之认识能力的一种先行分析,这种分析就是先验哲学的要旨。
3 先验自我的成形和消失
海德格尔并不反对康德对存在与知觉之关系的强调,他反对的是康德将作为被知觉性的存在与被认识性相等同、进而又将被认识性与主体的认识能力相等同的做法。与被知觉者相比,被知觉性更加靠近行知觉,这一点是海德格尔和康德共同享有的观点。行知觉可以发现、敞开、揭示存在者,由此被知觉性指的就是主体(此在)的这种“显敞性让照面”,而存在者的被发现性也就依赖于这种“让照面”的能力:“行知觉中的存在者之被知觉性,也就是其特殊的显敞,就是被发现性一般的一个样态”[3]86。 但是,主体或此在的这种让照面之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是一种认识性的、将存在者置放入与主体的照面之中的表象能力吗?海德格尔否定了这一回答,在他看来,行使让照面之能力的主体不首先是认识性的主体,而是生存着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用他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术语来说就是这样的主体不是“认识之我”(erkennenden Ich)[7]74或“理论之我”(theoretischen Ich)[7]208,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之我”(historische Ich)[7]85。 从认识之我到历史之我的过渡,并不是先验哲学的一种自然化,而是先验哲学在保持其先验方向的同时作出的一次改造和推进。
先验哲学作为一个哲学谱系非常复杂,即便那些被公认为是先验哲学的哲学家,他们对先验哲学的理解也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塞巴斯坦·盖德耐尔(Sebastian Gardner)曾从系统性的角度概括出先验哲学的五个基本要素:其一,追求一种超出经验探寻之外的哲学反思,并同时据此批评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上的幼稚性;其二,追求一种终极性证明来反对怀疑论的挑战;其三,认同“哥白尼革命”的内在意涵:知识的基础来源于认知主体的功能,也即康德所谓的“可能性条件”,但绝不能把这些功能和条件视为一种心理学事实;其四,这些先验的可能性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规范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先验逻辑;其五,先验哲学追求一种卓越的突出的先验论证模式[8]2。在这五个要素中,前四个要素基本上可以归入同一个结构。盖德耐尔将第一个要素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先验哲学所要求的这种形而上学既保留了古希腊意义又带有近代认识论意义:形而上学等同于一种哲学反思,这种反思超出经验性思维,这种超出对应着形而上学之中的 “meta”和物理学之中的“之后”,超出、meta、之后既可以是存在论上的也可以是认识论上的,不过在这里盖德耐尔似乎更加接近超出的认识论含义,而这一点正好是康德对先验哲学的首要规定。康德说,“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一个体系就将叫作先验—哲学”[2]19。这一点与第三点是结合在一起的,先验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反思模式它关注的是我们关于对象所具有的先天概念和先天认识方式,这些先天概念和认识就是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些可能性条件组成的规范性系统就是先验逻辑,阐明先验逻辑乃是先验哲学的核心任务。对先验逻辑进行阐明和论证,就是先验论证,所以说先验论证承担着先验哲学之是否可能的责任。先验哲学的核心是先验地阐明先验逻辑,而先验逻辑指的是认识主体具有的关于对象的先天认识能力,康德将这种认识能力称为可能性条件。可能性条件被表明为先验哲学的核心,可以这样说,对可能性条件的不同解释构成了先验哲学多样化的最终根源。海德格尔也是如此,他对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进行了存在论改造,这样就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等同成了一种存在论,并突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这种存在哲学的内在关联。
在康德那里,可能性条件有很多含义,它可以指经验的可能性条件,也用来指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有时还可以用来指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2]151。从文本的正面论述来看,康德更加倾向于将可能性条件等同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与他对先验哲学的定义是接近的。先验哲学不以存在者为定向,而是以我们具有的、先天的关于存在者的认识方式为定向,先验哲学的对象是先天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正是这些对诸事物的先天认识方式,构成了一切知识的真正基础,也即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康德用可能性条件首先指的就是这种先天认识能力。我们所具有的这种先天认识能力分为感性能力中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能力中的概念。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只是表象的杂多,这种杂多之间的联结或综合是无法通过单纯的直观能力被给予的,它只能通过知性的概念能力来获得。直观中的杂多能够联结为一,乃是出自知性的作为,知性就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2]91。所谓统觉的统一性,指的是先验自我对于一切表象的伴随和行统一,一切表象都是我的表象,在表象杂多中我能够意识到同一个自己。先验自我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不仅能够先天必然地将直观中的杂多统一为 “我”的表象,它同时还能够将这些表象视为客体的表象。按照康德的规定,客体乃是在其概念中结合直观杂多的东西,这种结合得以可能的根源同样在于统觉的综合统一,统觉的综合统一将直观杂多综合为诸表象,并将其视为是我的表象,与此同时它还将诸表象视为是关于“它”的表象,即与一个对象发生关系,这样这些表象就获得了客观有效性从而成为知识。由此,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就被显示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先验自我或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被表明是最根本的东西,最关键的可能性条件,其他一切可能性条件比如先天感性条件都有赖于统觉的综合统一。就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而言,单纯的直观没有办法做成知识,在直观之中被给予的只是杂多,它必须借助知性的“判断的逻辑机能”被纳入统觉之下被统觉加以综合统一;对于我们人而言,单纯的知性也没有办法做成知识,因为知识和认识在于确定表象与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样,直观和范畴的结合才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而这种结合根本说来要依赖于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它是知性之一切运用的最高原理。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不仅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在这种统一中不仅给出了表象的统一,而且还给出了表象与客体、对象的关系。对象是经验中的对象,经验的条件就是对象的条件,既然统觉统一是经验的可能性条件,那么它也就是对象的可能性条件。所谓对象的条件,指的就是使对象的对象性得以可能的东西。我们上面指出过,对象的对象性等于被知觉性,而被知觉性就是存在,所以当先验哲学将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视为对象的对象性条件时,意思是说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乃是对象之存在的条件,对象的存在之根被移植在了先验自我那里。
我们说海德格尔继承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指的是他在形式上仍然追问可能性条件,即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条件,海德格尔以自己的语言完全肯定了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真正意义:“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势必要依循存在论的真理来调整方向”[9]13。之所以说他改造了康德哲学,指的是这种可能性条件的内涵已经由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改造成了此在的在世存在、先验逻辑改造成了以时间化为其本质规定的时间性。海德格尔既承认康德将存在与主体拉拢在一起的做法,同时又不满于康德的做法过于急切,以至于使存在完全消融于主体之中。在他看来,一方面必须挽救存在论出离实在论的诱惑,存在必须借助主体因素才能显现;另一方面必须挽救存在论于观念论的泥潭,存在对于主体因素的借助不能被还原为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依赖,而康德无疑没能避免后一种诱惑,只不过他的观念论披上了一层先验论的外衣。海德格尔在1927年左右的马堡阶段发展出一种以此在生存论分析为内容的“基础存在论”,既是对先验哲学的继承,也是对先验哲学的推进,它被标榜为既不是以存在者为定向的实在论,也成功出离了以传统主体概念为定向的观念论。
然而,此在概念对先验自我的转换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先验哲学的观念论倾向,这一问题并不像海德格尔自夸的那样得到了成功地解决。当《存在与时间》开始在法国传播的时候,法国哲学家首先将这一问题抛向了海德格尔,并与其后来的“转向”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持续其一生,主题纷繁复杂。我们这里处理的这一存在论题,在内容上讲属于海德格尔哲学的上升期,但在思想意义上讲,它关涉了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进程和转向。在其晚年,即1961年,海德格尔再次谈论起康德的存在论题,但是我们会发现,晚年的谈论与早年相比,非常谨慎地加入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让在场”—Anwesenlassen、“给予”—Es gibt),这些东西属于转向之后的阶段,并隐蔽地参与着对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批评和辩护。
[1]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Ⅱ(1757-177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HEIDEGGER.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GA56/57[M].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1987.
[8]SEBASTIAN GARDNER.The Transcendental Turn[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9]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2.006
B516
A
]1004-0544(2017)12-0036-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X03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TJZX16-003)。
吴三喜(1988-),男,河北清河人,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文琦(1988-),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推所《世界汉学》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