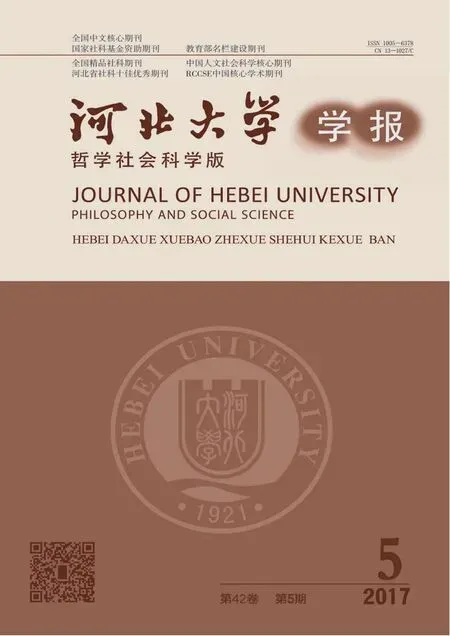打倒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
——张申府的儒学观
程志华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哲学研究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张申府的儒学观
程志华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面对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批儒和尊孔思潮,张申府认为,对于这两股思潮应当“重新估价”,即应该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即区分儒教糟粕与孔子精神。在他看来,对作为儒教糟粕的“孔家店”应该打倒,而对作为孔子精神的“孔夫子”应该继承。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仅仅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针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总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张申府;孔家店;孔夫子;儒学观
20世纪初叶,相对于儒学而言,国内学界出现了两股对照鲜明的思潮。一是激进主义,主张以外来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一是保守主义,以“国粹”来看待儒家文化,故主张维护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面对这样两股思潮,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扬弃”地提出另一种主张:一方面,承认传统儒学的确存在糟粕,而且主张必须清除这些糟粕。另一方面,亦肯定儒学有许多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并主张继承并弘扬这些精神遗产。很显然,这样一种主张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在继承儒学精神遗产的同时,还需要“哲学地”发展儒学,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之源。这样一种思想主张,体现出张申府的儒学观。
一
20世纪初叶,在多种历史机缘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以至形成了激进主义思潮。概括地看,这股思潮认为儒学存在三个方面的缼欠:其一,儒学服务于君主专制,为封建专制的“傀儡”。梁启超说:“孔学则严差等,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1]其二,儒学违背人性,形成对人的“道德压迫”。胡适说:“理学家们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2]其三,儒学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社会进步。梁启超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3]基于这样几个方面,激进主义学者认为儒学应当被批判,孔子应当被打倒。对于这样一种主张,胡适曾以“打倒孔家店”来概说。他在《吴虞文录·序》中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4]在此,“打倒孔家店”虽是胡适在介绍吴虞时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却准确概括了当时学界的批儒思潮。质言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打倒孔家店”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在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的同时,作为对批儒思潮的“反弹”,学界亦出现了一股以“尊孔”为特征的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虽具体体现于“保皇党”“国粹派”和“保教派”之不同阵营,但其核心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确千疮百孔,几于病入膏肓,但根源并不在于儒学和孔子。相反,“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5]6。之所以如此,在于孔子的“为人之道”并未在中国社会真正实行。柳诒徵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5]9具体来讲,这股思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表示或粉饰太平”;其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在全世界的盛行;其三,在复古潮流下对“思想重心”的追寻;其四,借尊孔以恢复民族自信等[6]143-144。关于这样几个方面,章太炎曾概而言之说:“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7]对于上述两种思潮,张申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激进主义思潮,张申府认为,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已有批判过于盲目、浅显。他说:“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这些年来,在思想上中国诚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问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封建思想的依然弥漫,也是不能掩盖的情实。”[6]191“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6]190总之,“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6]190。关于保守主义思潮,依着张申府的理解,“尊孔”思潮只停留于“外在”的尊孔,故无助于“解放”孔子“圆融而切实的教义”。他说:“近来对于孔子的信仰实在已失坠了。若想恢复之,而不从培养大师阐发其教义上着手,乃突然地因仍故常举行宗教的仪式,便令别无害处,也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说得上什么恢复信心,挽救国运?”[6]145对此,张申府解释说:“吾的意思,并不只简单地说,孔子是不该尊的,不值得尊的。但吾深信,在现在情形之下,如果尊之不得其法……那便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6]144质言之,“尊孔”是应该的,但“尊孔”的方法一定要恰当。他说:“要想解决现在中国的根本经济问题,也只能用前进的方法,不能用倒退的方法。不幸,现在尊孔的种种起因,竟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6]144
由此来看,张申府对于上述两种对立思潮均持有异议。进而,他认为,要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讲,需要对上述两股思潮进行“重新估价”。他说:“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6]192在张申府,“重新估价”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相对于20世纪初叶“启蒙运动”来讲可称为“新启蒙运动”。他说:“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6]191之所以谓之“新启蒙运动”,缘于此运动的基础是“理性”,而上述两股思潮的基础并非如此。他说:“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除了加紧努力于五四所对付的对外问题外,不但在宣传上,而且在实践上,推动这个新启蒙运动,应是今日一桩最当务之急。而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6]193那么,何为“理性”呢?消极地讲,它是指“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积极地讲,它是指宣传和实践“切实”“客观”“唯物”的“科学法”。他说:
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6]191-192
基于“理性”,张申府认为,这种“新启蒙运动”乃是在“继承”前提下的“扬弃”。他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6]191那么,何谓“扬弃”呢?他说:“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6]304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对儒学和孔子所产生的“误解”,辨明孔子思想中的是与非;才能“阐发”孔子的“真精神”,真正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6]192为了实现“扬弃”的目标,面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张申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他说:
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6]190
二
从张申府的口号来看,“打倒孔家店”是其中一义。他说:“在抗战时期我又常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6]632-633在张申府,所谓“孔家店”有其限定的含义,其所指乃“孔门儒教”。具体来讲,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指被作为宗教看待的儒教;其二,指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因此,所谓“打倒孔家店”,一是指把孔子从“圣坛”上请下来,去除其身上的“神圣光环”;此意指反对以孔子为“万能”。二是指把儒学置于学术思想的“百花园”,去除其所享有的“独尊”地位;此意指反对以儒学为“全对”。他说:“若以他(指孔子——引者)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6]145就此来讲,他说:“今日对于孔子再不必有一点迷信了,也再不可有一点迷信了……孔子及其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逃的时代限制。”[6]633那么,为何张申府要主张“打倒孔家店”呢?基于“理性”,他认为,“孔家店”应被“打倒”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孔家店”限制学术自由。在张申府看来,无论是学术进步,还是文明发展,均依赖于“自由的空气”。质言之,“思想自由”乃学术繁荣的前提,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正是前引他所谓“第一要自主”之所指。对此,他说:“思想学术的发展是需要自由与方便的。……‘只有在开阔的天地里,自由的空气中,肥沃的土壤上,乃能开放光华灿烂的文化之花,结成甘美宜人的学术之果。’”[6]380然而,儒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结果是,虽然儒家思想得到了弘扬,但学术界形成了思想专制;此种格局不但限制了学术进步,而且也阻碍了文化发展。因此,要促进学术进步,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打破“独尊儒术”的格局,进而破除思想学术专制。质言之,把儒学“定为一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张申府说:
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罢黜百家,定为一尊,严门锁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6]633
其二,“孔家店”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在他看来,“饮食男女”四个字乃人的自然本性,故亦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说:“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吗?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得法,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餍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世界不从此长治久安了吗?”[6]43然而,虽然儒家对此有所了解,但其认识却远不到位。具体来讲,儒家虽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它又极力倡导“礼教”,以束缚并压制人的自然本性。由此来讲,儒学实际上乃“误尽苍生”之学。张申府说:“孔仲尼,孟子舆,总算很看到这个了,所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所以说‘食色性也’。然而他们对付这个的方法,只有礼乐。乐自要紧,礼便只有流弊。后来出了迂阔的宋儒,说什么‘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两句话恰恰与人心的两个根本相反!似乎要误尽苍生了,然而苍生岂肯受它误!”[6]43-44因此,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应着眼于人的自然本性,修正“误尽苍生”的传统儒学。他说:
从打多暂就有人想改造社会!那个人不想世界长治久安?可是直到现在还逃不出一治一乱的话,或且“更有甚焉”。这个情景只是原因想改造的人看不到这个人性的根本事实,或是不敢看到,再不就是看到一点了,处置仍未得法,暂安一时,长久还糟。……现在还有想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么?第一,你们要大起胆子,睁开眼睛,敢于看到这个人心的根本事实![6]44
三
张申府认为,虽然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否认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为‘大哉’的。不过,‘大哉’也就是他最适当的称誉。若以他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孔子只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若以为教主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6]145而且,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伟人,而且亦是全世界的伟人。张申府说:“无论如何,他不但是中国的伟大人物,也是世界的伟大人物。假使世界之纪念哥白尼、伽离略(即伽利略——引者)、牛顿,而不纪念孔夫子,这个世界,无论如何,不会是圆满完全的。”[6]633-634因此,不能对孔子的思想视而不见,不能把孔子思想的精华“糟蹋净尽”。他说:“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蹋净尽?”[6]181依着张申府的理解,“孔家店”之弊端并不源于孔子,一些思想糟粕也不应该归于孔子,孔子只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最不幸”的人。他说:
孔子实在是中国一个最不幸的人,有最圆融切实的教义,而难索解人。却被利用了两千年,至今不得解放。一方又被种种的恶名于一身。[6]145
张申府的意思是,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一定要注意鉴别并继承其中的合理成分;对待孔子和儒家思想亦应如此。他说:“诚然,孔子及其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逃的时代限制。但逻辑与几何又何尝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科学法以及辩证唯物论也何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6]633就孔子思想来看,其一些思想确有合理成分,且具有恒久的价值;这些思想可被现代社会所利用,并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过去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6]181-182实际上,孔子思想不仅可以为中国利用,亦可贡献于全世界。他说:“孔子被历代帝王利用,也利用得够多了,够久的了。今日还不该伦(应为“轮”——引者)到人民也来‘利用’他?用他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象征。而况今日全世界正可以有他带路。”[6]633正是因此,孔子是应该纪念的,其思想亦是应该继承的。张申府说:
尤其没有孔子所代表的仁,不但文化将不成其为文化,人也将不成人。孔子有这样重要意义……还不该纪念庆祝么?……其实孔子的可以纪念,值得纪念,应该纪念,本不待申说。[6]632-633
当然,孔子思想应该继承的内容并非“孔门儒教”,而是指其合理的具有恒久价值的内容。在张申府看来,此内容乃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不过,继承的前提是先将其“解放”出来,此即“救出孔夫子”的真义。由此可见,所谓“救出孔夫子”,所针对的是“孔子的真传统”,指把孔子从“圣坛”上请下来,恢复其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本来面目”;指把儒学从“独尊”之位上请下来,研究并继承其有价值的思想精华。他说:“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打倒了对孔子的崇拜,可以自由研究了,再无所谓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说,孔子的真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伟大,才真会被认识。”[6]633“……这才真正可以见出大哉孔子,也才可以看出孔子的真价值,真正值得效法与纪念处。于是,孔子也才和同样害人害了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一样,被救出来。”[6]633质言之,应将孔子思想的“真传统”诠释出来,贡献于现代中国乃至全人类。张申府说:“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6]181为此,他还说:
为矫正“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6]304
张申府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并非嬴政、刘彻、李世民、朱元璋等帝王,也非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人,而是儒学的创立者孔子,因为中国文化“所以立者”“可以立者”和“值得立者”均源于孔子。他说:“一个国家要立国于斯世,必有所以立者,必有可以立者,必有值得立者,也可以说,必有其代表的人物。代表中国的最大人物,断然是孔子,而不是嬴政、刘彻……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6]633由此来讲,孔子不仅不应该被打倒,而且也不可能被打倒。他说:“狂妄者说,‘打倒孔家店’。孔家本无店,要打倒哪里?我尝纠正说,‘救出孔夫子’。仲尼本自在,救也用不着。”[6]364既然如此,就应努力弘扬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他说:“中国学人,今日对于文化,至少负有三桩不可旁贷的任务。即须,一、本着最新最进步的观点彻底检讨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理想,阐发自己从来未经发扬的真传统……”[6]691在张申府看来,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正名”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其二,“中庸”所表达的辩证法;其三,“仁”所表达的崇高人格理想。
其一,关于“正名”。在张申府看来,“正名”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其理论内涵乃为政之要。所谓“正名”,主要包括如下内涵:第一是“清楚实在”,指言语思想的清楚实在。他说:“中国现在固然有种种的急切的需要,但一个最切要的实是思想言语的清楚而实在。清楚的最后标准也是在实上,所以实尤其根本。孔子尝重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其实要名正言顺也在清楚实在”[6]237。第二是“客观”,即实事求是。他说:“乱世急务之一是正名。……正名与客观也是相关联的。方法上的客观,本在:是什么就认识为什么。正名所图则在:名为什么便应当是什么,真是什么乃名为什么。不然者,君不君,臣不臣……本不是匪而名为匪,不是乱而名为乱,而剿之。结果如何?”[6]174-175第三是“循实”,即遵循事实。他说:“孔子谈治国开始于正名。我则认为与其说正名,无宁更切实些说循实。”[6]297第四是“核实”,即名实相符。他说:“孔子的正名真不失为政首的为要。——正名实在就是要核实。”[6]355依着张申府的理解,“正名”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他说:
中国古人曾经注重过正名。这就是逻辑一部分的应有事。假如今日相信民主的人,主张民主的人,而不先正名,而不防止名字的滥用,而不杜塞自己信念主张的变成八股,变成滥调,变成口头禅,变成敲门砖,那结果一定是一个谎言……那结果将一定是一个天大的哄骗。[6]504
其二,关于“中庸”。在张申府看来,“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所谓“中庸”,并非机械的“折中”,亦非固定不变的“执中”,而是指“适度”即“时中”。他说:“中:准也,极也,合也,洽当也,恰好也,恰到好处也,火候纯青也。中就是射的,就是正鹄,也就是射中(读重)。最重要,必须记取的是:中是一个圈(口),而不是一个点。但吾相信时中,而非折中、执中。”[6]437具体来讲,“中庸”的实质乃辩证法。他说:“中与易都是辩证的道理。中为人的行动的标准。易表示了宇宙实像。而且中国的易是说明天地万物,而非指的观念思想,尤合乎辩证唯物的意思。所以我尝说,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6]253之所以说“中庸”乃“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在于它已成为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他说:“美是一种所谓价值。……在这地方,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是恰好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和,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6]337对于“中庸”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张申府的评价颇高。他说:
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6]364
其三,关于“仁”。在张申府看来,“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指人之为人的准则。他说:“仁从二人,成群之本。仁者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为人处世之最高准则,是为人最应操守之中。仁,行起来就是忠与恕。”[6]410“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准则,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他说:“仁是人与人间最亲切的关系。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谓生生之谓仁,所谓仁是相人偶。社会不过人的关系的集合。最高理想的社会定是仁的社会。仁字从二人。承认己外有人,是人做人的起码点。也是人类社会,人能组成社会的最起码点。”[6]253正因为如此,“仁”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可满足自己需要。即为避免受别人的迫害,人乃需要“仁”。他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人之勿迫害己。”[6]88第二,可利于整个社会。即人先是为自己考虑,但同时也须考虑别人,这样人们才能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可实现和平。他说:“仁,首在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所以,仁及忠恕,都是假定有他人,都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的。”[6]423在此意义上说,“仁”乃孔子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贡献。张申府说:“孔子代表中国的好文化。……中国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仁,这自应以孔子为代表。”[6]632他还说:
仁是人间的最高的理想,仁是人与人间最好的关系,仁是中国文明最大的贡献。[6]318
四
由前述可知,“正名”“中庸”“仁”乃孔子之“真传统”,且“真传统”为中国文化“所以立者”“可以立者”和“值得立者”。换言之,这些“真传统”不仅支撑了传统儒学,而且支撑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来讲,孔子的“真传统”乃中国文化之“可以纪念的东西”。张申府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此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6]181但是,中国文化不能满足于此,儒学亦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中国文化还须发展,人类文化还须发展。否则,儒学便会仅仅是“可以纪念的东西”,而“不值得长久存在”。质言之,儒学之具有恒久价值的“真传统”虽有其历史贡献,虽可作为未来发展的资源,但面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它仍有“可尽”与“应尽”的责任。张申府说:“无论如何,可以把他(指孔子——引者)作为一个象征。而况今日全世界正可以有他带路。”[6]633他还说:
中国学人于此,是有他可尽与应尽的责任的。……中国旧来未得发扬的真传统上,中国旧来未得践履的人生哲学上,未尝无一日之长。西洋文化今日正走到一个尽头,中国真传统人生哲学上的一日之长,很可能就是今日世界文化的需要,而为今日世界文化新综合的必要成分之一。[6]691
张申府的意思是,儒学不能停留于继承和弘扬“真传统”,而更需要创新与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的“整理国故”颇有微词。他说:“近年的‘整理国故’,纵令也有不可没之微功,但终不能不说是近年害得中国学人最苦的一件事。一固在其把一部分向上的精力不用在大自然或人类社会里而耗在故纸堆中。二尤在其把中国本有的东西隐然都认为故的,好像新的只有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6]182具体来讲,儒学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它有责任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创新,以对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价值之源。用张申府的话讲,面对现实和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历史上的孔子”,更需要“这个时代的孔子”。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他也会如此做的。张申府说:“今日需要的孔子,自必是这个时代的。而孔子之恰好,本在他是圣之时者,知道易,知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6]182那么,“这个时代的孔子”所指为何呢?
就儒学的基本理路来讲,如前所引,张申府认为其乃一种“人生哲学”。既然儒学为“人生哲学”,它就必为“哲学”。关于作为“人生哲学”的儒学的发展,张申府是立足于“哲学”来思考的,因为哲学乃文化的核心。他说:“中国今日确需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理想。……供给这种理想的,就今不止哲学,却以哲学为首要。”[6]169那么,何谓“哲学”呢?“哲学”乃“智慧之学”。他说:“哲学就是学哲,哲学最大的社会功用就是使人哲。……哲就是明哲,就是智慧。”[6]689具体来讲,哲学作为关于“宇宙运动的一般规律之学”[6]151,其意义包括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其一是“哲学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指导”;其二是“哲学在把言语弄清楚”[6]151。当然,在这两个方面当中,前者乃根本,而这个根本落脚于“人生意义”问题。他说:“照这个最高指导说,哲学的能影响人生本已不待言说。”[6]151“要回答这个人生意义的问题,第一先应该分开‘是’的方面与‘应’的方面,……‘是’的方面就是事实方面;‘应’的方面,则是道德方面。”[6]159关于“哲学”的重要性,张申府还说:
除非人不行动,人要行动,人要自觉地行动,便不能不有观点、做法、路线、归宿。这些其实无一不受对于宇宙估量的影响。……一个人的哲学固然不免受他的生理与生活的规定,但既有了他的哲学,他的行动就再也难逃他的哲学的限制。[6]152
张申府认为,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儒学若要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从而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价值之源,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如何缩短甚至消弥这个距离呢?他说:“我始终相信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6]133为此,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观点,即会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辩证唯物论,从而创建一种综合的、全新的哲学。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6]434然而,很显然,“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乃儒学所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不仅需要哲学史家,更需要哲学家;由哲学家来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他说:
现在中国,需要种种。而其中之一必是中国的哲学家。所谓中国哲学家者,一不是中国哲学史家。二也不是住在中国的治西洋哲学的人。三更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之伦。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中国的哲学家,必乃是有最新最切实的知识,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而发扬之,而履践之,而参照中国的哲学,而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者。[6]180
五
对于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张申府认为应当“重新估价”,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在他看来,“孔家店”在限制学术的自由、束缚人的自然本性等方面确实有应该批判之处。此乃“打倒孔家店”之所指。不过,孔子思想中又实有一些具有恒久价值的“真传统”,诸如“正名”“中庸”“仁”三个方面。因此,在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进程中,应该把“真传统”承继并发扬下去。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仅仅承继并发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面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质言之,针对现实社会之种种问题,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乃儒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而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乃一个方向。此乃“救出孔夫子”之所指。总而言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夏晓虹,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3.
[2]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7.
[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78.
[4] 胡适.吴虞文录·序[M].合肥:黄山书社,2008:4.
[5] 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J].学衡,1922(3):20-32.
[6]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7] 汤志军.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
【责任编辑吴姣】
OverthrowingtheDrossofConfucianismandAdoptingtheEssenceofConfucius’Thoughts——On Zhang Shenfu’s View of Confucianism
CHENG Zh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
Confronting 20th century’s currents of criticizing Confucianism and worshiping Confucius, Zhang Shenfu held that these two currents of thoughts should be reevaluated--the dros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essence of Confucius' thoughts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Zhang Shenfu, the dross of Confucianism should be overthrown, while the essence of Confucius' thoughts should be adopted. However,in order t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only adopting and promoting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is far from enough. To solve current issues, Confucianism needs to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other word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Confucius’ thoughts should be adopted, but it also needs to be studied in innovative ways. In conclusion, overthrowing the dross of Confucianism and adopting the essence of Confucius' thoughts are Zhang Shenfu’s complete view of Confucianism.
Zhang Shenfu; dross of Confucianism; Confucius; view of Confucianism
B261
A
1005-6378(2017)05-0036-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07
2017-04-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儒学史”(14FZX0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台湾‘鹅湖学派’研究”(13YJA720004)
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儒学、中西比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