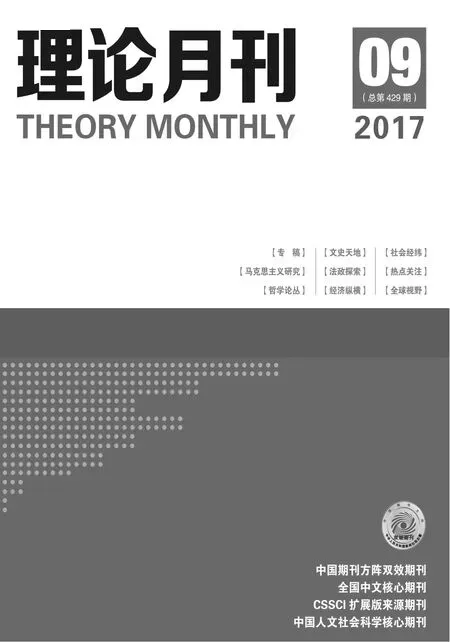间性文化记忆:丝绸之路跨国界线性申遗的核心价值
□李 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间性文化记忆:丝绸之路跨国界线性申遗的核心价值
□李 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使得中国和中亚五国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经济相对稳定的协作共同体。丝绸之路线性跨国申遗的核心价值,即是通过对沿线国家共同历史记忆的唤起,以及间性文化的共时效应打破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精神隔膜,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以及为沿线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互动与合作奠定必须的精神基础。
丝绸之路;间性文化;线性申遗;核心价值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首次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构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域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和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描绘了一幅连接欧亚非的经济大走廊蓝图,此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基于这一倡议,充分认识这条母线的文化价值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显然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
1 地缘文化圈与地理经济圈的构建
1.1 难产的“新丝绸之路”与积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丝绸之路申遗注入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愿望。这一构想的提出并非完全出于自身内部的需求,它与其时世界大环境的经济趋势和美国国家战略的转移有着对应关系。
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高达9.8%,是美国财政扩张最大的一年。因此美国将全球地区战略进行了调整,从中东相对撤出,战略重心东移转向“重返亚太”,并力图确保西非和拉美的“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在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为此,美国希望寻找到一个新时期的全球经济解决方案,希图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施加影响力和价值观。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其主旨是加强与印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等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创建一个新的协作平台。更为深层的意义是通过 “经贸与过境”所形成的经济纽带,使这些地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达到利用经济影响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目的[1]。然而,“新丝绸之路”计划实施伊始便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巴基斯坦与美国、印度和阿富汗关系的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在架构“新丝绸之路”计划之时将印度设定为“中心作用”[2],导致巴基斯坦方面曾侧面表态抵制“新丝绸之路”计划。而印度方面也对此计划持审慎态度,不希望美国利用巴基斯坦来制衡印度[3],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2011年2月,印巴两国原则同意重启全面对话程序,但由于长期互不信任的状态,致使两方面在对话中对彼此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并无实质性进展,两国中心利益的诉求远未达成共识,看似“对话”了的印巴和平进程往往是“前进一小步、后退一大步”。此外,俄罗斯的态度对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俄罗斯不希望美国在中亚地区建立排他性影响。在阿富汗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呈现两面性,在希望美国长期陷入阿富汗胶着状态的同时,也在加强缓和与阿富汗的双边关系[4],同时也希望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显然“新丝绸之路”计划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打通贸易过境中的障碍壁垒,更重要的是需要地区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相对稳定的联合关系。而计划的开始阶段即面临巨大的挑战,不但政治联合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经济合作也难以凝聚。
2012年之后,世界格局的渐趋复杂,中国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美国加大亚洲控制力度的同时,中国也在寻找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2013年中国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即是为了打破美国所设定的地缘政治关系,而确立的以文化带动经济的联合共同体机制。通过近三年的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经济的联合体倡议,不论从合作方式上抑或实施效果上,显然要比“新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方针更具操作性和远见性。
1.2 “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
两汉时期所建立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贯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陆上大通道。不但促进了沿线各民族和区域文化、经济的交融,还形成了“丝路文明”这一文化概念,成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为古丝绸之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这条沉睡千年的丝绸之路在今天重新焕发出它的巨大价值。
近几年形成的大国地缘政治形势正在趋于区域化,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也在调整,试图通过结盟来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而俄罗斯也在积极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加速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显然会对平衡民族局势,稳定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具有明确的协调意义。金融危机后,全球格局处于调整中,发达国家以自身为中心极力构建经济利益圈,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随着我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前提下,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平等对话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虽然这一倡议所涵盖的区域与其他经济合作体在利益和合作形式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但中国所倡议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一开始即考虑到民族平等、地缘平衡、区域协作等内在因素。因此,习近平在关于周边外交政策上强调:对于中外合作要以包容的心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5]。从而能够为丝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交融,提供一个广泛的无差异化兼容的对等合作平台。
2 基于优势互补的产业经济空间构架
2.1 国内线性经济区域城市群构架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为汉唐期间连接中、欧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大通道而命名。“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主要商业贸易通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然在使用,它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它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之路,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伊始,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焕发了人们对这条纽带的兴趣。
丝绸之路线性申遗的首要问题是确认沿线主要代表性文化遗产,对于这项工程,中国申遗主导部门基于德尔菲法选择相关专家对丝路重点遗迹的“文化属性”“空间位置”“历史时间”“区域尺度”进行了多次排除法确定,首先确认了中国境内长安至天山三条廊道的18个重要遗迹点。其中的新疆段的主要遗迹为:交河故城遗址、高昌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遗迹;甘肃段的主要遗迹为:玉门关遗址、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陕西段的主要遗迹为: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遗迹、小雁塔遗迹、兴教寺塔遗迹、彬县大佛寺石窟、张骞墓。这些确定的18个典型文化遗产在丝路中国段形成了一个连续完整的线性文化遗产网络,同时,这些遗迹也是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人口迁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也是反映丝路沿线各区域文明发展的“动态”网络系统。
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提出伊始,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关中天水经济带、银川沿黄经济带、兰州青海经济线、银川平原经济区、酒泉嘉峪关玉门关经济线等区域,迅速形成经济联动城市群。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覆盖率低、人口密度低。其整体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前,全国城镇化呈现为东高西低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分别为56.4%、53.4%、44.9%[6],同时在西部经济体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关中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只有近4000亿元,显然,打造西部经济城市群的关联建设对我国整体经济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要提升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提升西部城市群的建设,打造沿线经济带贸易交流通道,形成完整互补的线性经济带。显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构想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从宏观上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同时在整体经济构架和全球经济战略上,起到了政策叠加的积极效应。
自“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与丝绸之路相携的西部节点城市积极打造经济梯度构建,经过总体规划,各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从本地区现实出发,优先发展主导经济体建设,同时带动产业转移升级,通过产业梯度推移模式带动低梯度区域产业发展。从西部资源和全国整体经济布局而言,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能源战略地位,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为纽带,形成以有色金属、采矿、石油化工、电力、机器制造等为主的重工业产业集群格局。同时,在西部经济短期增长点的构建中,“围绕仓储运输、商贸物流、区域金融、旅游集散和文化交流等产业进行空间布局,”形成了陕西的整体枢纽战略;甘肃的大景区开发战略;新疆的链接定位战略;兰州新区的国家增长极战略等[7]。
2.2 丝路沿线线性经济区域国家群构架
我国之所以没有在丝路申遗伊始即提出经济开发计划,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经济压力相对较小,随着内销经济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提升,我国急需提升出口市场的竞争力来缓解国内经济矛盾,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激烈和地缘经济的微妙变化,提升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此意义而言,我国必须打开西北和西南交通路径,减小国际贸易的时间成本和经济交易成本。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对能源需求量的增大,也需要打通“丝绸之路”来实现能源保障。我国80%的原油进口完全依赖马六甲海峡,随着国际政治的复杂化趋势加剧,这条能源经济脐带的危险度逐渐显现出来,显然,如果在今天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国能源进口依然依赖单一渠道,将会十分危险。而“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如中亚、西亚以及俄罗斯等区域大多是油气资源丰富地带,因此,重新建立“丝绸之路”构架,对实现我国能源安全和进口的多元化具有显要的现实意义。
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架就沿线国家层面而言,从中国沿线国家至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省,再到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土库曼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通过俄罗斯、波兰、德国,最后到达荷兰鹿特丹港。沿线城市大都是一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各自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经济群构架。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的优势产业主要为石油天然气开采、冶金和深加工、交通运输和电力工业、通讯等,占总工业比为39%;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从地理位置来看处在中亚五国的交汇地区,其优势产业主要为采矿业、冶金、水电、化学工业、轻工业,占总工业比为26%;土库曼斯坦西南部以阿什哈巴德为中心,优势产业主要为石油天然气开发、电力、化学工业、纺织业、农牧业,占总工业比为48%;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以塔什干为中心,石油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为支柱产业,占总工业比为32%;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其地理优势明显,因此,其优势产业除采矿业、电力、煤炭外主要发展交通运输产业,优势产业占总工业比为26%[8]。
从优势产能来看,中亚五国的优势产业与我国丝绸之路西部沿线的主要产能,均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机械制造和有色金属等方面,优势效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显然可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为中国及中亚的能源安全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对亚太经济圈的协作合作奠定了先期合作基础。同时,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有效合作,是将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连接的基础保障,通过充分发挥丝路沿线城市节点的产业协作,形成经济城市群规模效应。从而形成线性互动网络产业合协作模式和优势互补的产业梯度建设模式。同时,城市群的有效衔接也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产生优势扩散效应。
3 基于共同记忆的合作前提
3.1 古今两条线性经济带的契合
跨国经济联合体成功的最大障碍即是区域民族和区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协同问题。当代世界不同民族之间正经历着多重转型,首先是地缘民族的相互影响力的转换,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历史转换。在信息化的今天,地域文化的交流空前便利,各地域民族无论在纵向质的演进抑或横向量的交换都达到即时交流的状态。从理论上来看,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必然产生更多的共同性因素,产生更多的同化相融现象。然而从地区政治经济角度而言,这种理论并不符合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在相互并不信任的地区经济合作中,每一个个体都在努力将有利于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其他的合作者,使得看似牢固的经济共同体往往会由于一些小摩擦而瓦解。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同时,即关注到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协调对跨国经济合作体的关键作用。
2013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年会上提出“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机制,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会议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CICA)第四次峰会上再次强调国际合作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并着重提出在国际协作日益密切的形势下,不论强弱或富贫,合作体之间应在利益交融的前提下安危共济,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可见,中国的跨区域合作战略方针充分认识到眼前利益不能使各个合作体形成牢固的归属感,合作体之间不能仅仅依靠短期经济利益来维系,这种基于密切合作之上的归属感,必然需要各方对区域文明的认同感和文化认知度来维系。2015年习近平在当年度博鳌论坛年会上对“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更加深入的阐释[9],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要有所担当,以正能量面对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重义[10]。“命运共同体”是跨地区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通过相互之间的文化、情感的积极培育,稳步推进国家之间“坏情绪”的修复能力[11],从而加强共利联盟的凝聚力,最终达到区域层面上的整合发展。同时,“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还提出了国家主权让渡的尝试性共识约定,从心理方向为地区国家提供了相互探讨的理论空间,消弭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合作疑虑。特别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升华了区域“命运共同体”,显示了中国对构建“共情”世界的意愿[12]。
人本主义创始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ir)的“共情”理论,是从深层意义上阐释国际交流信任危机的解决办法,其主旨即是在双方或多方交往中,各方能从对方角度以最大限度地理解对方,为对方的行为寻找行为合理性理由,如此,首先在心理上接受对方,进而达到合作的密切与共赢。可见,中国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正是基于“命运共同体”中显见的“共情”理论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基础即是基于 “古代丝绸之路”所建立起来的各区域、各民族所共有的“丝路文明”文化共同概念。正是依托古、今两条丝绸之路的共合性,以及两千年来所培育出的文化共性和“共情”积淀,才使得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体制具有了明确的心理操作基础。在这一原则下,丝绸之路跨国界线性申遗就更具现实意义,加大力度推进申遗进程和深入的文化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顺利实施的国际战略基础。因此在今天,充分认识这一母线的文化价值对“一带一路”的构建具有明确的积极意义。
3.2 “一带一路经济”延展的核心基础
就表面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线性节点设定,看似限定了较窄的一条条状区域,实际上我国在提出这一构架的时候,并未将其设计为一条封闭的合作形式,只是将这条经济合作线路作为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协作战略的先导实验。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合作体系,它向所有愿意参与的区域国家开放[13],它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区域合作机制。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希望在区域合作中占有优势地位,从而确立振兴本民族的强国富民的理想。正因为每个国家的独立意识,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都会产生向各自利好的方向的意愿,而矛盾的产生则是必然现象。因此,能否有效迅速地化解矛盾,是区域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西方许多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巨大威胁,“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14]这一理论的背后显现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思想。我们看到,近十年来类似“新丝绸之路”的计划等,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经济联合体往往持有“主—客”相对思维观念,这种不平等的对话方式必然会导致主体中心主义,致使合作各方产生信任危机和文化抵触情绪,使得“计划”在受到危机之时,整个构架势必整体涣散。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描绘了一幅连接欧亚非、辐射40余个国家30多亿人口、世界上最大最具广阔潜力的经济文化大网络蓝图。从空间上打破了这一点对点的区域性西式理论,并由于这一线路所具有的历史协作基础,奠定了丝绸之路的现代意义。基于中国国家战略的丝绸之路线性跨国申遗的核心价值,即是通过对沿线国家共同历史记忆的唤起,以及间性文化的共时效应打破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精神隔膜,为“一带一路”计划顺利实施,以及为沿线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互动与合作奠定必须的精神基础。
[1]吴兆礼.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2(7):19.
[2]ROBERTO,BLAKE JR.Looking Ahead:U.S-India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Transpacific Century[EB/OL].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1/174139.htm.
[3]SUBHASH KAPILA.South Asia 2011:Strategic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United States[EB/OL].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papers47/paper4603.html.
[4]赵华胜.俄罗斯与阿富汗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1(3):39.
[5]刘锦前,舒丽娟.“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跨界民族”交融发展问题析论:兼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共情”能力构建[C]//新常态与大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497-510.
[6]赵锋.丝绸之路沿线十大潜力城市群加速升级[N].中国经营报,2013-12-23:A16.
[7][8]郭爱君,毛锦凰.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3,44.
[9]共谱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华章:解读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8/c_127632688.htm.
[10]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jit.
[11]SCOTT H.H emenov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in R ate of A ffect Change:S tudies in effective C hronomet T j[J].J 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 ocial P sychology,2003,85(1):121-131,504.
[12]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文汇报(香港).2017-01-02(7).
[13]杜尚泽,黄培昭.习近平出席中英工商峰会并致辞[N].人民日报,2015-10-22(01).
[14]LESTER B.PERRSON.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es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83.
责任编辑 李利克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9.014
I122
A
1004-0544(2017)09-0080-05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6XKG005)。
李杰(1970-),男,天津,艺术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新媒体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