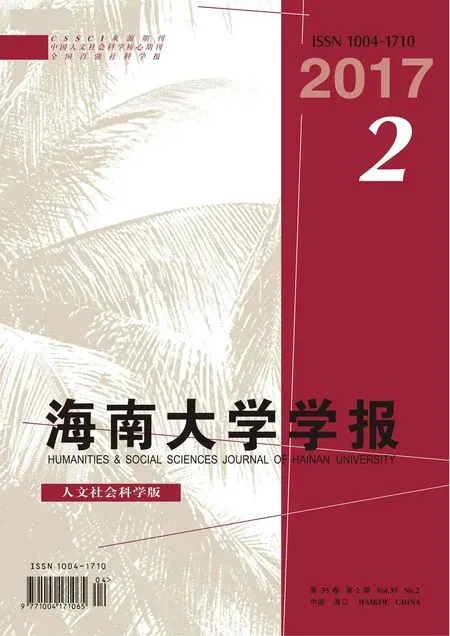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范式”与解释学重构
——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城市理论的比较研究
赫曦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范式”与解释学重构
——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城市理论的比较研究
赫曦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围绕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和方法论展开,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典型的分析模式。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范式”是将城市视为社会关系的组成,进而建构一种非理论的、具体的普遍性以应对日常生活与城市革命的挑战;在解释学方面也表现出由从传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转变为对本体论的关切,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强调城市世界之呈现是基于对空间中社会关系的把握,基于对资本、劳动力和国家权力的分析,需要将客观存在放置于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下。这消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二分法,进而确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话语权。
人文主义;结构主义;范式;重构
基于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城市阐释的多元化努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呈现出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不同版本。自从资本主义批判进程开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城市现象看作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持不同的观点。城市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阶段,如人类生态学和城市实践派将城市规划批判视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第二阶段,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代表思想之外创造理论阶段。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批判始终指向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和城市实践,主要围绕着决定论和人文主义两个方向不断延伸。在人文主义方法论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将城市危机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的核心。另一个方面,决定论的方法论以卡斯特的思想作为起点。两种研究方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主要关注了空间生产和日常生活,而后者则将工人运动与城市斗争的关系摆在了分析的首位。但是,两种研究方法也有共同点,它们都认为“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城市已经成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具体展开与实现。城市权利是空间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统一、资格权利与行为权利的统一、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统一[1]。
虽然存在不同的立场,但是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不同的城市理论重构路径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它们分别在什么意义上对解释学进行了“重构”,不同的重构努力是否切近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了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不同取向,进而揭示它们在解释学重构中的贡献与局限。
一
在当今世界,任何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观念,任何试图空间化当前理论或者任何将自己的理论包含进空间关注的社会理论都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某种理论的合成或者叠加,空间分析已经成为一个理论的完整的、本质的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如果空间的隐喻和属性被广泛使用,并且将它构想成只是一个社会进程的容器或者表面,那么不同空间的差别将不再重要,人类活动所承担的角色会被历史辩证法的时间进程所定义,空间只不过是理论整合的一个部分。这种处理方法会使空间现象被处理成为社会进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知识和实践,而时间才是一切社会进程的逻辑起点。相反,如果一个理论将空间放在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空间最小化理论会被转化为另一个理论,那就是哈维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如果我们认同这种做法,无论是当前社会理论的空间解释还是存在的理论延伸进入空间都已经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研究的“范式”,为审视城市认识的主观性基础提供了可行的切入点,它表明城市研究也是以“世界观”而非“事实”为出发点。20世纪50~60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向黑尔格哲学,以此来回击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Marcuse)、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本杰明(Benjamin)等人。他们声称,通过再次确认社会中自主意识行为者的个体意识,把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推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规律中。这种批判主要是由于结构主义的优势地位造成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场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运动成为了法国知识界的主要潮流,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一股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胫而走,并大肆发展。结构主义用一种依靠与个人的行为处境、与存在主义主题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件的根源。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阿尔都塞,他通过保护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观念,以及有关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相对独立的批判性理论洞见,使之免遭政治经济学的伤害。另外,由于辩证法聚焦于矛盾,结构主义者也往往追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危机基础予以重视。这场旷日持久的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影响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也在城市学研究界形成了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分野。
二
自1968年以来,列斐伏尔发表了大量有关城市状况的作品。他认为在当代进行城市研究,可以采用一种重视研究当代社会中的空间特性、关系等的拓扑学的方法,进行一种哲学的整体性的研究[2]。城市主义已经超越了城市,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组[3]94。因此,在列斐伏尔的思考中,“空间实践”被提升到与重组社会关系的努力并列重要的程度上,而且他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理论观点。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特点是不单考虑了城市是什么,而且展望了它可能成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历史主义色彩,因此他的著作没有受到阿尔都塞主义者的欢迎。更进一步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他错了,他假设了一种分析模式,空间关系被视为城市社会中一种独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判断受到普遍抨击。但在后期的作品《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进而奠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列斐伏尔认为任何表现都是意识形态的,如果它直接或间接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作用,那么意识形态与实践密不可分。他还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无论思想路线怎样,它都对革命行动的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列斐伏尔反对结构主义者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方面也没有特权,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混杂着真理、错误和虚伪。列斐伏尔认为意识形态与“有关革命实践影响的理论和那些保护政治一致性和相互牵制的理论”[3]16有一定关联。根据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社会实践的政治理论。他反对仅仅用学术和分析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卡斯特坚持用集体消费的分析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样,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策略,首先思考关于什么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另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政治中。
在城市主义方面,列斐伏尔试图建构一系列思想“可以鼓励激进的行动来反对他认为是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新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4]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和城市规划有着技术性特征,将空间视为纯粹的科学对象。城市理论及实践和规划,反对包括空间在内的政治力量,并将政治看作不合理的存在,仅仅是基本空间形态的生产。因此,存在主义也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坚持要通过空间的非政治问题和空间的使用来维持现状,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使用城市空间和空间蔓延产生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断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城市空间,以及城市的现实不能简单地被构想为生产和消费场所的一个总和……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陆的城市空间的安排增加了生产力,正如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行业里的装备和机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一个人使用空间就像一个人使用机器一样。”[5]245这种主张可以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生产方式由两类物质对象组成,第一类是劳动力,第二类是经过劳动力加工的对象,如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方式之类的东西。这些工具被用于生产。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认为:“在这一主题下,我们解决了这些为了主要运作表现而形成的对象……其他一些对象,尽管自身不是工具,但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像建筑、楼房、码头、公路和土地,都包括在这一组里面。”[6]因此,建成环境成为了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尤其是劳动力生产方式。空间的再生产仅仅是指这一方面。但与把空间仅仅视为生产方式相矛盾,列斐伏尔以及其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是一种生产力。如科恩(Cohen)所指出的:“空间有资格加入生产力这个序列。空间的所有者明确地在经济结构中给予了空间一个席位。即使一块空间不能满足这样的标准,它的管理可能产生经济权力,因为它可被其他生产的东西填充,或因为它可以通过生产者发生转换。”[7]这一观点,被列斐伏尔进行了深化与完善,他认为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描绘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城市这一媒介,社会再生产了它自身。对列斐伏尔来说,为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空间秩序连接控制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它对空间的使用得以生存,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强化的空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8]空间关系的辨证属性与生产模式的外部属性在列斐伏尔的表述中有了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空间与城市的认识,空间表现除了有革命性的特征外,空间的生产与所有权关系和物质关系相联系,形成了资产阶级生产模式的核心。
与将空间理解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纯粹科学对象相反,列斐伏尔认为批判空间的政治理论被政治化了,因为“空间形式是政治的产物,并且它行使着政治功能”。“空间的生产可以被联系到任何形式的生产机制中”[9]。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理解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是一门很重要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关于空间的科学。列斐伏尔建议“建立矛盾过程的辩证法,为城市问题提供政治斗争的基础”。空间生产中的基本矛盾是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的,政治斗争反映了个人和集体的策略。
列斐伏尔城市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解释资本主义长时间存在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通过征服和整合空间而维持,空间在很长的时间都被认为是消极的地理环境或是空洞的地理存在。它已经变为一种机械的存在。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被生产,现在正在变为一种新的稀缺,和水、阳光和其他资源一样,被当作同质的和可计量的商品被创造和使用。正如桑德(Saunder)指出的,城市革命的主题被创造,类似于工业革命中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资本主义手工业转变的历史一样重要。现在,城市社会被创造,城乡的物理分界已经不再重要。作为日常生活的批判,列斐伏尔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方面。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城市在全球空间背景下,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场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通过日复一日的使用空间得以再生产,因为空间被资本和附属于它的逻辑所捕获”[10]。空间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地点,并且“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进而控制空间的生产,并且再生产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和城市革命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矛盾,城市革命的分裂和人口的去中心化,使经济和政治力量远离中心。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弱点和日常生活被传播到了边缘地区。因此,由于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割裂,资本阶级霸权受到了边缘地区的挑战。政治斗争的不断加剧,在中心和边缘之间产生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也表达为人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持续关切。另外,作为乐观主义者的列斐伏尔也认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也卷入了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探讨。城市危机是存在主义资本主义面临的中心问题,并且资本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可以被看作是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之间的斗争。列斐伏尔对城市危机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策略有一定程度的暗示。第一,建议劳动力必须为了社会需要而进行生产和使用;第二,边缘通常是被动地连接到生产力运动中,日常生活的生产组织要根据自我管理再排列。自我管理还导致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废除。新城市社会有一定优势和潜在的人类自由。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空间控制和日常生活及空间技术思想的斗争取得胜利,人类潜在的自由将会得到实现。
根据列斐伏尔的论断,城市不仅仅是一种建成环境,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题。如卡斯特一样,他强调再生产在实现家庭、劳动力社会化和生产三个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列斐伏尔对财产关系很感兴趣,认为财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维系和反对国家政治斗争的起点。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在征服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力量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财产关系而不是集体消费领域的国家干预。和卡斯特不同,列斐伏尔不只是转变了日常生活的角色,而且认为空间的剧烈转变也是必要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转变问题应同时被探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列斐伏尔人文主义城市思想的主要特点:第一,城市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与私有财产有着十分相似的矛盾关系,是社会关系掌握着与城市需要有关的行为,它与城市用于获取财富的方式保持一致。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城市在生产模式中与资本和劳动力具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而且城市还是标识社会矛盾的重要源泉,城市的地位作为一种生产力意味着它是一个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城市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还是一种关系的产物,城市本身还是一个消费对象;第三,城市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通过对城市的使用,确保其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整体的同意和部分的隔离。它由此称为一种管理上的控制,甚至称为政治的空间。因此,城市在组织形式上的表现除了层级上的构建,城市设计也相应地表现为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其结果也显而易见,城市关系刻画了存在于社会形态中的再生产,并在层级结构上管理国家和政府的实践;最后,阶级斗争称为城市空间的必要部署,换言之,是存在于城市中的不和谐与冲突,这其中既包括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也包含非经济因素的冲突。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在城市中的体现,城市空间被无限碎片化了,形成了各种层级的空间形式,私人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居住空间,甚至全球化空间应运而生。这种空间活动可以视为是空间爆炸形成的重要后果,空间逐渐成为层级化的社会关系。社会中不同层级的公民和团体在这种精密调节的空间差异中导致了各种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这种冲突在不同的空间区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不论是在个人、社区、区域还是全球区域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国家能够维持它们造成的这种无序、矛盾的空间。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目睹了这一爆炸性的空间。以当前生活层面来看,空间正在四处爆炸,不管是生活空间、私人空间、学术空间、监狱空间、武装空间或历史空间。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意识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在城市的层面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城市的爆炸,还看到了他们全部的想要涵盖城市现象的管理框架。从区域的层面来看,这一外围边缘正在为了他们的自治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而奋斗……最后,从国际层面来看,不仅是所谓的超越国家的公司行为,而且那些伟大的世界战略,都必然在准备营造出新的爆炸空间。”[11]290因此,空间对象产生的冲突实际已经打破了所谓的阶级界限,因为它不单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因此,他宣称,城市现象——当它已经通过阶级对象表现出来时,就不能再通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探讨了。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只能从理论上具体说明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抽象空间,但是却制约了以经济为主导的种种关系。因此,需要通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把握城市,因为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使用以及一种抽象空间的征服。所以他总结到:“空间不仅仅是经济,其中,所有的部分都是可交换的并且有交换价值。空间不仅仅是为了同质化社会各部分的一件政治工具。正相反,空间保留了一种模式,在同类性质的国家统治下,在资产阶级经济中,一个永恒的使用价值的原型不断抵抗交换价值的普遍原理。空间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更是一种时间,它在根本上与时间联系着,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基本的使用价值。时间已经在现代社会的空间中消失了。”[11]291城市需要用辩证的方法来掌握,因为它既是一个具体的抽象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物质,“任何事物——尽管是微不足道的——其主观和客观的方面,其行为与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这些孤立的客体已经与自然界分离了……每一种产物、每一个客体都因此转向了一个通往自然界,另一个通往人。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既定物质的具体性,当它称为我们行为的一部分时,通过抵抗它或征服它,但它仍然是具体的。它借助于它的定义、可衡量的界限被抽象化了,也因为它可以进入一种社会存在,成为其他类似客体之中的一个客体,同时成为除了它的物质性以外整个系列的新的关系的承担者。”[12]因此,理解城市必须要把握作为一个具体的抽象概念的多重证明的空间是如何生产的,这也正是列斐伏尔研究的核心所在。
三
卡斯特在研究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之后,试图“在空间理论中找到占领城市社会学的空间”。 他揭示了“消费社会”历史情境下城市的本质、功能、过程和意义[13]。对他而言,在知识中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至关重要,如同阿尔都塞在建构结构主义时所作的那样,他建议严格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建议在争论中应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总和的表现来分析。那么,通过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并通过他们的结合与源于它们的社会实践的种种因素来研究它的具体形式。在研究中,卡斯特一直在寻找理论上的研究对象,能够提供一种“在空间理论范围内,城市理论被界定为城市本身专有的社会结构理论”[5]156,他呼吁回到城市空间的本质所带来的理论问题——现代社会的空间形式中来寻找答案。在这里,空间涵盖了在工作生产中所有潜在的社会关系。所以,他指出:“提出空间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相当于在一种社会结构实例与社会结构元素之间进行单元定义,构想它们的种种关系。为了使术语更加具体化,城市的界定包含着一种单元的认定,既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实例,也不是政治司法上的实例,或是经济上的实例。”[5]235
第一,卡斯特认为“没有现存的领域可以被认为是城市”,他坚决反对传统城乡在空间和文化方面的二分法。他反对将城市化看作是工业化的文化表达。同时,卡斯特还指出城市社会自治组织在当今社会不可能被发现,作为理论对象,“共同体”不仅仅是被城市地区包围的地点。这里,皮克万斯(Pickvance)的观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卡斯特和他持相反的观点,因为他反对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对立。他对城市理论研究对象的选择是研究城市现实,认为城市是“空间和集体消费的关系”。集体消费是为了给城市理论以确切分析而使用的分析工具。
第二,卡斯特和列斐伏尔一样,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卡斯特认为存在主义之所以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就没有建立现实社会的科学分析基础。城市进程被解释为个人行动,人类主体或人类意识的概念被意识形态实践所生产,而不是科学。相似的,城市管理方面的著作,决策者在理论中有相同的角色。个人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派别而不是社会的整体被关注。卡斯特认为如果意识形态得以实现,从本质上要依赖于隐喻的自由,无论是真实的客体还是理论的客体都需要科学的分析。对于城市空间的科学分析,卡斯特认为真实的客体是集体消费的真实空间单元,空间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元素的消费进程,包含着劳动力体系中的最基本资源。通过分析理论客体的角色,真实的客体被阐述,回应了整体理论体系。城市系统是形成社会基本元素的节点,城市是“劳动力居住的单元”或“集体消费的单元”。城市不能被定义为经济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或与生产相关的方面。什么是消费?对于城市而言意味着在生产中公司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公司在生产进程中起的角色可以在劳动力再生产进程中的城市单元里实现。
尽管如此,科学需要分析城市现象,卡斯特寻找了很多城市化理论中相对保守的观点,如人类生态学和沃斯(Wirth)的城市化理论。人类生态主义者的生态系统和沃斯关于大小、密度和异质的概念,提供了调查研究的特别理论领域。帕克(Park)和沃斯反对人类主题的概念,并试图发展决定进程的理论。对于帕克而言,整合是一个理论客体,同时认为整体有特殊的文化内容。但是,卡斯特认为他们的理论客体都不足以发展出有差异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需要用经验研究阐述城市现象。
卡斯特的著作《城市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事实上试图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去分析列斐伏尔的理论,他认为所有的结构性体系,如晚期资本主义,包括他们内部自身对应于更大的结构性时间体系,都是通过相似的规律在运行的。所以,社会秩序是可以根据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模式来进行分析的。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秩序的子系统——城市综合体系——也可以这样分析。但是,列斐伏尔是完全反对结构主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结构与政治和思想结构相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卡斯特追随阿尔都塞的观点使用经济手段去认识城市,认为经济层面的城市由生产和劳动力方式构成,前者还用来分析地区问题,后者用来分析城市单元。地域层面的分析反映了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导致的矛盾,空间的生产则忽视了城市的特殊性。社会空间关系是由经济结构主导的,因为根据阿尔都塞的先验图式,这恰恰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模式。因此,卡斯特也用经济因素来定义城市,因为这种定义符合了阿尔都塞分析的必备条件。在他独具特色的分析模式中,他区分了经济结构中的两个基本元素:生产工具和劳动能力。
卡斯特主要关注了集体消费的进程,集体消费为生产力再生产提供了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支持。如戈特迪纳指出的,卡斯特主要关注点转向集体消费进程意味着他开始处理城市问题的相关理论而不是空间理论。关于马丁代尔(Martindale),戈特迪纳认为卡斯特使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城市,他们将城市看作用社会病理学实现的地点,而不是生产的空间。卡斯特主要的兴趣不是城市空间如何被生产出来,而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和城市问题如何产生。
卡斯特集体消费的概念被作为城市政治研究领域中唯一的理论被迪内斯(Dunleacy)和桑德斯(Saunders)的城市社会学所接受。但是对于卡斯特自己而言,他对城市政治的主要兴趣在于城市社会运动。城市社会运动被看作是解决利润率下降问题的一般危机理论来探讨,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败的结果。生产方式和国家不得不为了阶级斗争的空间化结合而接受检验。这种运动是现实的标志,阶级斗争已经从工作地点转向了共同体生活。阶级斗争的方向和目标从直接要求涨工资转向无目标方向。换言之,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向集中到消费领域,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范畴。在这里,国家作为消费的调节器,成为城市政治的本质。
卡斯特主张群众层面的政治斗争,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一种阶级斗争。他认为:“城市问题空间分析的核心是一种城市政治研究,也就是说,意味着城市与阶级斗争领域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关联,其结果是,作为政治干预的一种实例(国家机器)——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和中心,也是问题所在。”[5]244由此可见,城市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城市政治的基本点,卡斯特致力于研究城市内部政治行为存在的方式,并试图去解释它。国家以扩大中产阶级数量来干预这种斗争,尽管中产阶级本身也片段化了。但是,地区国家的干预形成了冲突,因为国家干预创造了新的不平等。根据戈特迪纳的看法,这里卡斯特理论的本质表现出来,这种不平等和阶级关系之间没有联系,而是与消费过程的地位相一致。我们以它自身的特质面对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新结果。因此,城市社会运动不是这种新不平等的根源,而是一个结果。城市社会运动表现了从工人领域到社区生活空间的一种替代,因此阶级斗争已经偏离了其历史上对过剩财富按需分配的这种关心,尤其是工人阶级滋生的再生产方式。卡斯特认为:由于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建立起一个集中的规范过程(通过公司),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整体的消费过程的编排者;就是所谓的城市政治的根源。总之,卡斯特的政治冲突理论是以阶级冲突的形式为基础,被迫迁移到社区,并涉及与劳动能力再生产紧密相关的需求考虑。因此,他的城市政治运动既没有反映阶级冲突,也没有反映消费领域的国家干预。
在反资本主义斗争新形式方面,卡斯特对城市社会运动的特殊贡献在于他能聚集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通过整合不同阶层群体进入斗争进行分析。卡斯特的主要假设是纯粹的城市实践不能以一己之力成为改革者,只有将实践输入到其他领域,使更多的人加入,才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新结果。城市社会运动可以也必须在新社会结构的影响方面被重新定义。总而言之,卡斯特的结构主义城市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阿尔都塞方法对建成环境生产解释的一种践行;第二,它表现出了救助“城市”的尝试,通过从理论上来定义城市是建成环境结构体系内的一个空间单元,来表达城市单元的特殊性与现代社会及其危机的关联,进而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途径。
四
纵观城市理论的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传统,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话语权。正如沙朗·佐京所评价的那样,无论是运用人文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对城市进行剖析,它们在解释学重构中的共同特点是“将城市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城市,其主要轮廓是由资本积累、投资策略的节律和劳动力的补充提供所支配的大范围经济力量来决定的;其次,是努力澄清城市社会运动的特点和解放的诸多可能。这类城市社会运动,对诸如工会和政党一类的工人阶级暴动的传统场所来说,或是补充,或是替代。”[14]在研究中,两种方法除了猛烈地抨击了古尔纳德的二分法,在充分强调社会的总体性之外,还冲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过分依赖,用更多的篇幅研究城市的本体论,这使得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诸多弊病。
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城市理论也存在着视域的局限。人文主义的城市理论关心的是如何创造生机勃勃的乌托邦,并将城市实践当做对政治实践的刺激,接受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城市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消失的观点。都市可能性的实现完全是一个自愿实践的问题,通过将一种已经断言的历史进步与都市化及其附属的空间关系相结合,进而创造了一种城市的偶像崇拜。人文主义城市理论通过将包含于日常生活中的城市空间关系进行简单的机制整合,来理解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赋予了空间关系以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中心地位。正如列斐伏尔所表述的那样:“城市……也许是一种形式,邂逅的形式,将社会生活的素有因素聚集起来的形式,从地球上的果实……到象征和所谓文化作品……不存在没有一个中心的城市现实;商业的、象征的、信息的、决策的,等等。以这一形式,城市拥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同时性。”[15]
结构主义的城市理论一直存在着结构决定论的顽疾,由于过度强调结构的核心作用,在界定城市的功能和本质的过程中,结构主义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淡化了社会认同感以及社群对城市变迁的作用,结构性概念掩盖了主体的重要性,当我们运用结构主义来分析城市时,不得不面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无法调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同时,卡斯特将太多的精力放置于集体消费和国家权力的分析,而对资本积累的主题涉及甚少,这也是哈维对他进行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哈维看来,城市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塑造人的能动性,又为人的能动性所塑造的社会维度,对资本积累的研究正是沟通两者之间的重要桥梁。
总而言之,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虽然构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语境中,但作为重要的社会分析范畴和方法,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也有着诸多有价值的启示。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西方思潮中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理论,指引我们思考如何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如何确定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怎样更好地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城市观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亟待解决和论证的。
[1] 陈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4(1):85.
[2] 强乃社.列斐伏尔空间视野下的都市社会理论[J].学习与探索,2014(9):24-29.
[3]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4] 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248.
[5] 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7.
[6] Oskar Lange.Political Economy(Vol1)[M].New York:Pergamon Press,2012:4.
[7] 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51.
[8] Henf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M].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3:126.
[9]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8-9.
[10] Henf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Lonclon:Wiley-Black well,1992:123.
[11] Henfi Lefebvre.Space:Socail Product and Use Value[M].New York:Irvington Publishers,1979.
[12] Henf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M].London:Cape,1939:119.
[13] 王志刚.曼纽尔·卡斯特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1):90-96.
[14] Sharon Zukin. 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J].Theory and Society,1980(9):45-50.
[15] Henri Lefebvre. Le Droit a La Ville[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8:206.
[责任编辑:张文光]
Paradigm and Hermeneutic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Urban Theory: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umanist and Structuralist Urban Theories
HE Xi-ying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Jili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Changchun 130033, China)
Marxist urban study centers around the approach and method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dually forming two typical analytic modes of humanism and structuralism. The paradigm of Marxist urban study regards the city as the composition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further constructing a non-theoretical and specific universal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in the daily life and urban revolution. In terms of hermeneutics, it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udies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o the concerns for ontology. Both humanism and structuralism emphasize that the display of urban world is based on the mastery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space. And the analyses based on the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national power involve considering objective existence in the general analytic framework. Thu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chotomy of traditional Marxism is eliminated while the urban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is also established.
humanism; structuralism;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2016-10-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YJA810005);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60418044FG)
赫曦滢(1983-),女,满族,吉林长春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A 81
A
1004-1710(2017)02-0051-07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解读
——解读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