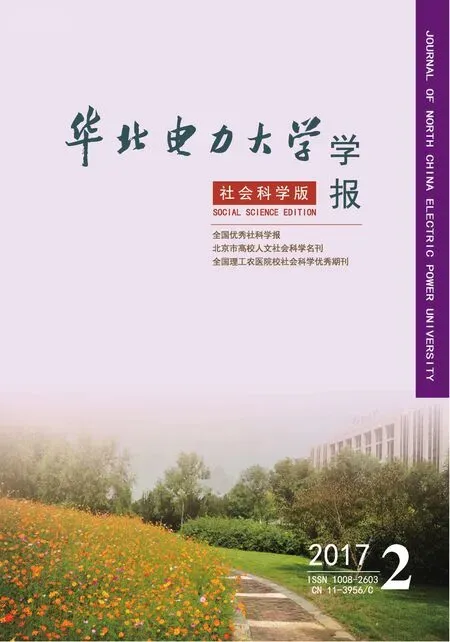儒家仁学理论的功能剖析及其当代启示
黄成华
(广东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儒家仁学理论的功能剖析及其当代启示
黄成华
(广东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儒家仁学理论是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封建宗法制是儒家仁学理论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儒家仁学理论无论在家庭治理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重视儒家文化建设,做好儒家仁学理论与公民社会的对接。
儒家;仁学;和谐社会;启示
当今中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的关键阶段。改革中的利益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震荡、矛盾加剧和人心不稳。如何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为现代化实践中的攻坚克难进行理论准备,成为当下学人的一致努力方向。
一、重视儒家仁学理论的现实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儒家仁学理论作为人类先民的智慧结晶,是缓和社会矛盾、弥合社会伤痕的文化纽带,反映了人类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体现了人际交往乃至国际交往的一般要求。儒家仁学理论作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性话语,对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必将具有范导型的意义。
儒家思想以仁爱为价值追求,把人自然流露的仁爱情感经过复杂的理论加工,上升为人的自然义务,使得仁爱理论成为具有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复合体。仁爱实践被抽象和概括成形式自洽、内容丰富、理论完善的体系,并化身成中华民族的话语系统和行为准则,积淀成人类璀璨文化宝库中的精髓。“调查显示,当前我国社会最重要的五种德性依次为:爱(占78.2%)、诚信(占72.0%)、责任(占69.4%)、正义(占52.0%)、宽容(占47.8%)。”[1]血缘宗法制以及奠基于其上的儒家仁学思想,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而影响至今,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话语指南和行动指针,并从根本上影响了未来的文化走向。个体以家庭为本位,以对家庭成员的爱为基础,再逐步推演到更广泛的人群。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个体至善推动社会至善,是儒家仁学理论倡导泛爱所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儒家仁学理论有关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业已内置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每个个体都应该将仁爱作为修身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道德圆满,成贤、成圣和成王,并且将仁爱的对象由家庭成员辐射到社会成员,以个体美德来维护社会公德,弘扬社会正气。
二、儒家仁学理论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
儒家仁学理论是封建宗法制土壤上结出的硕果,是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精髓部分,也是中国先贤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仁爱思想孕育于先秦时期,并充分吸收前人的思想精华,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儒家仁爱思想饱受历史风雨的洗礼,历经几千年传承而不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而集中记载仁爱思想的儒家著作也成为彪炳史册的经典文献和传世之作。儒家仁学理论建构起以仁爱为核心的等级性的纲常伦理规范体系,虽然该理论当仁不让地以维护封建宗法制为己任,但也包含有哲学大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价值取向。其所蕴含的价值时至今日仍然熠熠闪烁,成为当下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理想。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把仁爱作为自身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儒家仁学话语系统固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德性要求,但本质上是以“仁”为基础的,“仁”当之无愧地居于首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韩愈认为,“博爱谓之仁”。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达到109次。每个个体都有必要成为“仁者”。仁爱是自然流露的道德情感,也是道德教化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兼具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涵义。“在《论语》中,‘仁’既是一种德,又是一切德。作为一种德,其要义是‘爱人’;作为一切德,它是全德之名,能行恭、宽、信、敏、惠诸德于天下,便是‘仁’;因此,一切正当行为都是“仁”之表现,也发端于‘仁’。”[2]仁爱能够增加个体的亲和力,造就出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没有仁爱,社会就没有凝聚力,就会引发族群的对立乃至撕裂。仁爱不但应用于家庭,而且应用于社会;不但是家庭伦理要求,而且是政治伦理要求;不但是世俗伦理要求,而且是宗教伦理要求;不但有世俗性维度,而且有超越性维度。仁爱成为儒家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精神预设,并在家庭(小家)与国家(大家)之间不断地进行话语切换。这是中国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特征的集中表现之一。
先秦社会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以生物性遗传为核心的自然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出内外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治理秩序。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血缘宗法制的社会结构。血缘宗法制在农业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工商业的欠发达状态使得先秦社会缺乏瓦解血缘宗法制的社会结构的外生力量。这使得先秦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始终未受到冲击和瓦解,而得以长期延续下来,并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血缘宗法制将血缘关系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抒发了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情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复原始文明的表现。仁爱的自然表达遵循一定的位序,血缘的亲疏远近成为仁爱殊异的决定性因素。个体以血缘为基础,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空变幻中进行身份识别和角色认同,既能在历时性中回溯生命根源,合理界定“我”的身份,确定个体的历史渊源关系,也能在共时性中厘清关系亲疏,合理界定“我们”的范围,确定个体的现实交往边界。
三、儒家仁学理论的治理功能
(一)儒家仁学理论在家庭治理中的功能
儒家仁学理论依靠血缘性道德情感来进行家庭治理、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建构出适应农业社会需要的自然秩序。血缘宗法制以家庭为本位,以姓氏为标识进行人群的自然区分,对家庭内与家庭外、姓氏内与姓氏外的人群进行区别对待,并形成“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九族概念。仁爱的空间分布遵循由近到远、由此及彼的原则,以家庭为中心,不断地向外衍射。随着衍射范围的扩展,仁爱的程度也遭到稀释,最终形成内外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格局。
血缘是界定“我们”的重要参照标准,同时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据。家庭是个体情感和社会关系赖以维系的存在物,也是个体道德成长的现实基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子,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据此,中国人历来对家特别看重,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度高,家庭血缘关系对个体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仁爱首先应用于家庭。家庭是实践儒家仁爱理论的起始点,是仁爱训练的首发场所,对培养仁爱意识影响力最强。家庭血缘关系的权重远远压过其他关系类型,并逐步形成了家本位的思想观念,发展出温情脉脉的亲情伦理。每个个体都处于血缘纽带的连结中,其所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决定于其名份。故而,每个个体都极为看中其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血缘社会产生了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和信仰。这使得个体一方面处于宗族血亲势力的庇护之下,依靠家元共同体来抵御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风险,另一方面也处于宗族血亲的压制之下。当家庭之爱与社会之爱相冲突时,往往把家庭之爱置于首位。家庭关系相对于社会关系具有优先地位。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在一隐一直之中,彰显的是血缘亲情,遮蔽的是是非曲直。个体有了赖以依靠的靠山,即使犯错误,也会得到家庭成员的庇护。每个个体都有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而缺乏仁爱的个体则会成为家族仇恨甚至惩罚的对象。为了保持家族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在宗族内部有着严格的管理规范,否则,仁爱作为一种美德就会消失。对个体的最高惩罚就是剥夺其应有的名份。当家族需要对某些人施予重罚时,往往通过逐出家门来部分或全部取消其身份。儒家仁学理论在崇尚“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上,建构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秩序。男性长者处于家庭的核心地位,是家庭资源的拥有者和家庭事务的最终裁决者。家长的权威不可冒犯,父权制的家庭治理结构得到了传统身份伦理的辩护,甚至形成了老龄霸权。
仁爱内化为每个个体的内在道德良知,成为其内在属性,变成判断其是否为人的道德标准。没有仁,人无异于衣冠禽兽。“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家庭成员间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家和万事兴)。(仁与孝的关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藤文公上》)“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这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家庭关系。孝更是作为仁的集中体现,是家庭伦理的根本性要求之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更是通过一定的礼制来彰显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的焦虑与西方对宗教信仰断层的焦虑一样,具有终极忧患的文化意义。个体被融入滔滔不绝的生命之流,是生命链条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儒家的血缘具有准宗教意义;另一方面,儒家的仁学理论获得了宗教因果报应理论的支撑。这使得在血缘社会中培养出来的“孝悌”,不但是世俗性道德情感的要求,也是宗教性道德情感的体现。延续祖先的血脉,是每个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保持家庭延续性的家庭使命,也是继承原始文明的文化使命。在家庭伦理方面,形成父权制的家庭模式,要求子女“父母在,不远游”,在居住模式的选择上以血缘家庭为核心,活动半径以每个时代的交通工具为衡量尺度,以便于为父母养老送终。家庭养老的模式圈定了子女的活动对象和范围,包括就业、婚配、安家、社交等。孝是悌的基础,悌是孝的延伸。“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世》)仁爱把从“畏天命”的外在他律性要求转换成个体的内在自律性要求。仁爱作为一种“天命”,既得到以家庭血缘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的辩护,也得到以天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的辩护。“天命”的存在改变了仁爱的属性,使仁爱既是一种自然义务,又是一种超自然义务;既是世俗性的要求,又是神圣性的要求。这种人伦与天伦共通、天人感应的道德要求使得仁学理论具有了世俗超越性的维度。
(二)儒家仁学理论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
儒家仁学理论对原始社会形成的氏族传统进行了历史性改造,把氏族传统改造成进行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资源,建构“天下归仁”的秩序。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仁爱是家庭成员的自然义务,是社会风尚的要求,也是统治者制定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血缘是维系人际关系的自然纽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血缘宗法制由家庭而复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衍生出诸多的血缘伦理规则,奠定了社会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五伦’是中国伦理的典范。‘五伦’之中,君臣、朋友是人伦,即社会伦理关系;父子、兄弟是天伦,即家庭伦理关系;而夫妇一伦,则介于天伦与人伦之间,连接着天伦与人伦。‘五伦’的基本原理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君臣比父子,朋友比兄弟,而夫妇则比于一切男女关系。社会伦理始源于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根源于家庭自然本德。”[3]123-134基于血缘而产生的权力往往是先验性(超验性)特权。这种先验性特权在维护家庭内部的男权、夫权、父权时,也维护了从父权延伸出的族权、封建皇权等传统权力关系;在维护家庭稳定时,也维护了传统君主政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王权与父权具有同构性,拥有相似的“中心——边缘”结构。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差异是自然的差异,而基于血缘建构的封建等级秩序是自然秩序,符合自然正义。在这种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尊卑贵贱的差等性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儒家宗法体系为每个个体都明确了名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并通过相应的奖惩体系要求每个个体各司其职,安守本分,言行举止符合自身的身份和地位要求。这种血缘宗法制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人际纽带,也积淀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基因。
仁不但以“亲亲”之道维护着家庭秩序,同时也以“忠恕”之道维护着社会治理秩序。传统中国选用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方式,将仁爱由自然血缘关系拓展到社会人际关系,并固定为社会礼仪,建立起家国同构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法哲学分析中,黑格尔不仅确认家庭‘是’而且论证家庭‘为何是’伦理世界基础的问题。他认为,‘伦理实体’有三种形态:‘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家庭之所以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是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直接基础,根本原因在于它以‘爱’为规定。‘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这种‘爱’的直接性是人的伦理实体性成为可能的最初源泉。‘爱’的本性是扬弃自我的抽象独立性而与他人相统一,从而使伦理实体的形成成为可能。”[3]123-134社会的统治秩序是以宗法血亲体制为基础进行安排的,如传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在农业社会产生的儒家仁学理论必然体现出血缘亲疏远近关系来界定人际关系特点,并相应决定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伦列之爱”由血缘关系决定。儒家仁爱理论依据血缘进行差等性的社会治理结构的架构,根据血缘亲疏远近把对社会上的人群界定为至亲、姻亲、异族、异邦,构建出尊卑贵贱、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等级关系格局。就个体而言,虽然其人际交往圈子包含家庭式交往、家族式交往、宗族式交往、地缘式交往等,但与不同人群的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却随着交往范围的拓展而呈现递减状态,其中起支配性作用的考量因素就是血缘的亲疏远近。这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此人际关系格局奠定了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对血亲的认可,成为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血亲因素甚至成为判断敌我的标准,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朋友,为了获得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仁爱,更进一步深化彼此的关系,或者歃血为盟,互相换帖,结拜为兄弟,或者为子女订立娃娃亲,把朋友之情发展到血缘亲属之情。封建统治者维护的等级统治秩序同样具有自然属性。如政治伦理方面,在政治人选的任命上,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西方的贤人政治在中国遭到排斥。在政治治理手段的选择上,通常蕴含着“仁政”、“德治”的道德诉求,“修己安人”,标榜“以孝治天下”,从血缘伦理中提炼总结出社会治理方式。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外为了消除与异族的隔阂和纷争,多采取政治联姻的方式,对内为了笼络人心,给予宠臣赐姓的恩赐。为了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与矛盾,通婚就成了最佳选择,小到不同家庭间的通婚,大到不同国家间的通婚。
儒家敬畏天,强调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虽来自五湖四海,但“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就把仁爱的范围拓展到了全社会,从家庭小世界走向众生大世界,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在使仁爱具有泛爱论的道德情感立场时,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也使仁爱拥有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儒家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更把仁爱从人类社会拓展至自然界。儒家仁学思想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特定人群,甚至超越了人类,使得家庭成为社会乃至国家治理秩序的策源地。这些超越性的特质使得儒家思想得以长盛不衰。
四、儒家仁学理论的评价
以儒家为典型代表的智慧先民在当时有限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条件下,积极进行社会治理理论的拓荒式探讨,形成了高度完备的儒家仁学理论体系,催生出具有辉煌历史的儒家文明。儒家仁学理论是先民对社会治理秩序的系统性总结和概括,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仁学理论的内涵比较丰富,形成了内容庞大、结构精巧、运作规范的理论体系;涵盖了从认识论层面的人之为人的心理认知、价值定位,到实践论层面的人伦秩序之基础、安邦定国之良策,再到本体论层面的万事万物的始基,宗教层面的天命不可违及通过仁爱来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事实上,儒家仁学理论就其现实指向而言,更加具有生命力。其一经兴起,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仁爱既是个体道德自主性的体现,也是社会伦理的客观要求。血缘认同是基于感性而自然生成的。但这种血缘认同所指的是群体认同,而非个体认同,因为个体要依附于群体。就此而言,血缘认同适应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为了维护群体的存续,就非常有必要强调群体成员间的相互团结。
儒家仁学理论以血缘来建构人类治理文明体系,将血缘有无作为人际交往中情感强弱判断的绝对标准,并积淀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缘文化情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烙上“伦理型文化”的印记,并成为文化内核;通过上尊下卑、男尊女卑、老尊幼卑的身份制度安排,达到“和”的局面。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生活方式催生出先民不成熟的心态。儒家仁学理论由于将血缘关系作为理论根基,这使其局限性与其鲜明特点一样突出,在进一步拓展社会影响力方面障碍重重,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在如此兵荒马乱、群雄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儒家学者却无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闭门造车,不适时宜地抛出“仁爱”的学说,以整合社会、化解矛盾。这些学者虽然惯于批判,自觉地履行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并以社会的良心而自居,却缺乏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改造社会的热情。儒家仁学理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功效,对于处于分化阶段的社会各阶层无疑是一剂治病良药。尤其对在社会底层苦苦煎熬的民众而言,儒家仁学理论慰藉了心灵,麻痹了精神斗志。儒家仁学理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则在压迫与剥削劳苦大众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阶级交往的手段。
五、儒家仁学理论的当代启示
儒家仁学理论为了建构社会运行的秩序,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个体通过仁爱的道德努力达到家和国的伦理认同的治理文明路径,开辟了有别于西方友爱论的独特精神文化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为了建构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充分发挥仁爱思想的社会治理作用,克服仁爱思想的缺陷和不足,使仁爱思想成为世界性的话语表达,树立世界文明的参照系,施加全球性的影响,就要树立战略意识,对儒家仁学理论进行现代转换,以便与新的时空场域相适应。
(一)重视家文化建设
“儒家‘仁’的对象主要指向亲人之爱、朋友之爱、上下级之爱、其他种族或国度的陌生人之爱乃至对物之爱。”[4]但家庭却是仁爱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始基。中国人对家庭具有天然的道德情感。“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这一迄今为止人类最为漫长、最为重大的历史转型中,中国文明最成功的方面,是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了人类经千万年积累的智慧,这就是以血缘关系组织社会生活并以此为根基安身立命。”[5]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含若干社会子系统。小家庭和谐了,大社会才能和谐。一方面,要继续捍卫家庭本位的文化根基,发挥爱家、顾家和护家的热情,提高个体德性;另一方面,要从身份纲常伦理发展到权利伦理,在儒家仁学理论中融入现代元素。这是儒家仁学理论运行的个体性保障。儒家仁学理论要求通过“求诸己”的道德努力,成圣成王,以个体至善促进社会至善。
中国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历来是中华民族所看重的人伦美德。“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孝经·圣治章第九》)为老龄人养老送终,使其能够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这在中国人看来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应该推崇备至。“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祭义》)普天之下,尽孝行孝,概莫能外。“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庶人章第六》)“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礼记·王制》)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人享有的社会特权逐步增多。“六十而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礼记·曲礼上》)数典忘祖,则是大逆不道之举。“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章第九》)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孝道,有效拓展老龄人慈善事业,推动社会朝大同社会迈进。老龄人日益成为弱势群体,成为被关怀照顾的重要人群。要关注和解决老龄人的贫困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这关系到老龄人能不能体面地、有尊严地活在世上。人常言,人老了可能不会赚钱,但绝对会花钱。老龄群体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骗致贫的现象有所凸显。要做好老龄人的扶贫扶困工作,设立老龄人扶贫济困资金;建立老龄人大病重病救助医疗保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对老龄人的大笔资金周转要进行监控,并进行适当的管制,防止老龄人上当受骗。组织志愿者定点帮扶独居老人和失独家庭的老人,逢年过节时对鳏寡孤独老人进行家庭陪护。组织社会热心人士到敬老院、养老院等地方献爱心。要给老龄人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在精神上帮助老龄人更好地融入生活世界,防范老龄人因知识陈旧而引发生命与生活的脱节。以社区为单位,成立老龄人学习机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接受社会力量捐助成立免费的老龄大学。精神有障碍的老龄人、老年痴呆症患者等,更加需要专业医护人员的对症治疗。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等重症人群,进行临终关怀,发挥医务人员、志愿者、宗教界人士等的作用,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帮助病人完成最后的道谢、道歉、道别等人生礼节,克服病人对于彼岸世界的恐惧感,让病人舒坦地离开人世,圆满地进行人生谢幕。有些医疗机构甚至帮助临终病人提前召开追悼会,提供机会让其与亲人、朋友一一惜别。
(二)做好儒家仁学理论与公民社会的对接
儒家仁学理论具有超阶级的历史远见,要求个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但却缺乏平等精神。儒家仁学理论的差等性是由维系先秦农业社会的血缘关系所决定的,是传统社会身份等级关系的典型写照。仁爱的差等性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到了近代中国,尽管受到以“打倒孔家店”为典型特征的反传统的影响、冲击和消解,但依然保留有旧传统。传统社会,个体还饱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传统观念的制约,乐意给予困难的亲属一定的无偿经济资助,却对陌生人心存抵牾,不愿意把慈善的范围扩大到陌生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对同类的关爱已经突破了民族、阶级、种族等狭隘观念的限制,对“他者”的认同从先验性的情感认同发展到经验性的理性认同。这表征了全人类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关爱范围朝两个方面突破,一是打破了物种的限制,逐步关爱动植物等生命,特别是提出动物权利等崭新范畴,建立遍布全球的生态自然保护区,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合作;另一则是突破了民族、阶级、种族等狭隘观念的限制,打破了陌生人与熟人之间的分野,促使人类日益朝合作共同体方向发展。而仁爱作为形成合作共同体的天然力量,显然已经先行一步。“要使传统的‘仁’实现现代转向,就必须在公民道德教育的背景上,着力打破血缘、家族的狭隘性,把爱与关怀扩大到社会成员之中去。这样,仁爱原则才可能成为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有益资源。”[6]要不失时机地推进血缘社会向公民社会发展,将血缘关系拓展到公民关系,由血缘逻辑转变到公民逻辑,让仁爱思想在公民社会大放异彩。
[1] 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
[2] 樊浩.〈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3(3):125-140.
[3] 樊浩.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23-134+208.
[4] 王翠华.儒家仁学与古希腊友爱论:比较及启示[J],现代哲学,2014(2):103-108.
[5] 樊浩.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及其精神图像[J].哲学研究,2015(1):106-113.
[6] 王宏维.加强道德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的人际和谐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5(6):17-22.
(责任编辑:杜红琴)
The Function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HUANG Cheng-hua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523808,China)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i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to innovate the social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is 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 matter in the family governance or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culture, and complete the docking between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and the civil society.
the confuciam; the benevolence theory; the harmonious society; enlightenment
2016-12-30
黄成华,男,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G64;B222
A
1008-2603(2017)02-0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