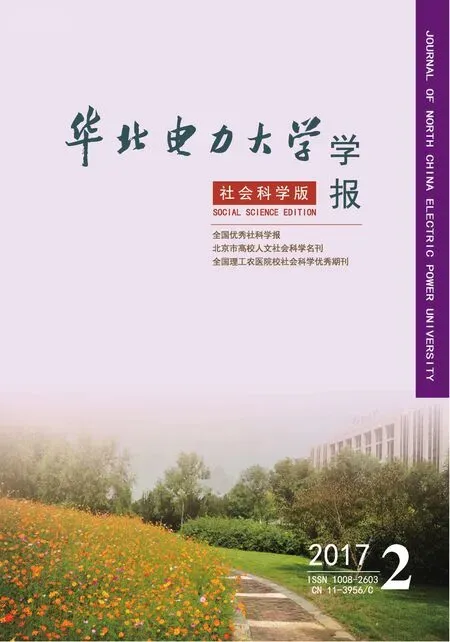《一千零一夜》之译者主体性研究
马祯妮
(新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一千零一夜》之译者主体性研究
马祯妮
(新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该研究对清末民初一直到当代《一千零一夜》众多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本做了历时性描述,围绕周桂笙、周作人、奚若、纳训、郅溥浩译者们的译本序言做了一一介绍与讨论,借由译序比较可靠的文字材料考察了译者的主体性在对原作的选取、对原作的评价、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读者意识和文化身份等方面的表现,不仅弥补了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对《一千零一夜》译者序言的缺失,而且对丰富和发展《一千零一夜》文学经典具有开创性意义。
译者主体性;译者序言;历时性描述;文学经典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模式的产生,翻译研究开始朝着“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发展,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随着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罗宾森(Douglas Robinson)、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翻译理论学者的出现,打破了译者隐身的教条,译者的地位不再被贬为传统的“舌人”、“媒婆”、“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而随着主体性的出场,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译者不但能与原作者相提并论,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还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试图征服原文、超越原文,争取在翻译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按照王友贵教授的界定是指“译者在原作选择、原作评价、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身份建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1]既然译者的研究涉及方面广泛,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使我们很难准确把握翻译家当时翻译时的内心情感,那么我们唯有通过文字和译作本身这类比较可靠的文字材料才能较为准确地窥探出译者的思想和情感。
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副文本[2]概念时,将其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围文本(epitext)两类,其中前者包括标题、序、跋、注释、插图、目录、封面等,后者包括相关采访、信件、日记等。这些副文本能帮助我们走进译者的世界,认识、了解到译者主体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而其中译者序是研究译者思想非常宝贵的资料,最能集中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最具代表性。译者序不仅能体现出译者自己对原文意义的理解,还可以为读者答疑解疑,便于读者在译学中了解到读者的总体指导思想、翻译目标、翻译动机、态度、立场和策略等。译者序恰如其分地搭建起译者与读者对话、交流的桥梁。
在古代阿拉伯文学中,中国译介最早、译本最多、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翻译家,花费了大量心血与汗水,他们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谱写了阿拉伯与中国之间文学文化交流的宏伟篇章。《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谭》,是世界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一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是阿拉伯人民留给全人类的一份极宝贵的文学遗产。它反映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生活现实,显示了古代阿拉伯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点。
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国内研究较多围绕原文本和译本的渊源做简单的介绍,缺少专门研究译本中译者序的研究。我的《一千零一夜》翻译版本繁多,译家如林,已经持续了一百余年,该译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清末民初由文言文英、日转译阶段;20年代到40年代,白话文英译本转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纳训、郅溥浩为代表的译自阿拉伯语的选译本和全译本阶段。
一、周桂笙译者序言
晚清的翻译界出现一种常见的问题即“译书家声气不通,不相为谋”,致使一书多译,虽异名而同物。其中《一千零一夜》译本在晚清便出现了多个译本。《一千零一夜》首次译入中国的译者是周桂笙(1873—1936),上海南汇人,原名树奎,笔名另署桂生、新庵、惺庵、新新子、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他的文学生涯始于甲午战后,从1900年起周桂笙为吴趼人主编的上海《采风报》节译《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1902年又为上海《寓言报》翻译了《公主》、《乡女人》、《猫狗成亲》等十五篇短篇小说。[3]上述译作都被收入《新庵谐译初编》,并于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印行。《新庵谐译初编》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一千零一夜》(即《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两篇,下卷有《猫鼠成亲》等十五篇西方童话、寓言与故事。在《渔者》卷末,周氏加入了按语:“按以上《渔者》一节,亦希腊才演说之辞。姊妹倡和,愈说愈奇,使王虽欲不听不可得也……书名本为《阿拉伯夜谈笑录》,《一千零一夜》其俗称也。新庵识。”[4]这段对故事内容和缘起的简要介绍可以算作这部文学作品在中国最早的评述性文字。
周桂笙在《新庵谐译初编》的自序中写道:
迩者朝廷既下变法之诏,国民尤切自强之望,而有志之士,眷怀时局,深考其故,以为非求输入文明之术,断难变化固执之性,于是而翻西文、译东籍尚矣。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要皆觉世庸民之作,堪备开启智慧之功。洋洋乎盛矣,不可谓非翻译者之与有其功也。[5]
译序的文字中“觉世”、“开启智慧”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译者的主体性服务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对源文本的改造是译者主体性在“觉世”、“开启智慧”书写的目的框架下进行的,译者的翻译《一千零一夜》与《渔者》都是围绕他的目的所展开的,即一方面表达他欲藉翻译作桥梁输入异域文明,另一方面想开发民智以实现救国于贫弱的抱负。
二、周作人译者序言
《天方夜谭》中有一篇著名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被周作人挑出并先行翻译。1904年8月11日在《女子世界》杂志社开始连载,以“萍云女士”为署名,将其译为《侠女奴》,彼时他18岁多。该译作于1905年3月19日译毕,1905年6月由上海小说林社与女子世界社联合出版《侠女奴》单行本1906年3月再版。笔者查证了《侠女奴》的译本,[6]发现译本里并未出现译者序言,不过通过对周作人本人零星表述的梳理,我们仍有所收获。对此详尽的记述在周作人的《学校生活的一叶》一文里,22岁的周作人回顾自己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欣喜得到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三先令半的插图本时写道:“《天方夜谭》里的《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和删节。”[7]透过这段周作人早期翻译心路历程的书写,我们发现催生周作人主体性意识的萌发是他本人的趣味,愿意把这次试笔当作一个最初的翻译尝试,由此也开始了周作人的翻译生涯。正因为译者具有选择原作的权利,周作人不以“删改”原作为病反而解释道:“第一是阿里巴巴死后,他的兄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妇,这本是古代传下来的闪姆族的习惯,却认为不合礼教,所以把它删除了。其次是那个女奴,本来凯辛将她作为儿媳,译文里却故意的改变得行踪奇异,说是‘不知所终’”[8]。周作人历来被学界冠以“译文忠实”的美称,但在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翻译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无不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虽然周作人把翻译当作“五四”文化启蒙的手段之一,向异域另寻新宗,他承认开放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但是在传递阿拉伯文化的过程中,在接受外国文化的时候,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也是有选择的,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精神传统,对与本国文化相冲突的阿拉伯文化,面对“男尊女卑”的情况,出于悲天悯世的情怀和同情妇孺的衷肠,对传统束缚女子人格独立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并倡导女性独立、男女平等,这些也正契合了“五四”知识界所要变革的两性伦理观。周作人的这段解释说明他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更重视译本的社会效用而非对原文本无条件的忠实。不仅如此,周作人在《<侠女奴>说明》中写道:“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9]“侠”、“女”二字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译者本人当时在译介作品时是打算借异域文学中机智勇敢,具有叛逆精神的曼绮波斯女性激发国人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热情。
三、奚若译者序言
此后根据英文转译的《天方夜谭》由奚若翻译而成。奚若(1880-1915),系江苏吴县人,字伯绶,笔名天翼,早年东吴大学肄业后曾留学美国,归国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董事并有多种译述问世。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英译本《天方夜谭》共4册,包括五十个故事,约三十五万字,虽然仍然不是《一千零一夜》的全译本,却已是当时相对最完整、篇幅最大的文言译本。奚若根据英文转译的《天方夜谭》很受人推崇,不仅篇幅远远超过周桂笙和周作人的译本,而且在《序言》里如此严谨地介绍原著源流和相关背景资料,这在20世纪初充斥着错译、漏译、删改、增译等严重违背翻译规范现象的中国译坛,是难能可贵的。
此译本曾连载于《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后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收入《说部丛书》、《万有文库》。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绍钧(叶圣陶)校注的奚若的《天方夜谭》,再版至少6次。1930年这个出版二十多年的文言译本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成为《一千零一夜》发行较大,影响较广的一个译本。奚若转译的《天方夜谭》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成,叶绍钧(叶圣陶)为其撰长序,在评价其文学价值时指出该译文“运用古文,非常纯熟而不流入迂腐;气韵渊雅;造句时有新铸而不觉得生硬,只见爽利。”[10]11奚若译本出自英人冷氏,即Edward William Lane译本。奚若在译序里考证了该故事的出处,断定此书在古代波斯、埃及民间流传,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一千零一夜》这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提到渔夫打出的四色鱼,就是教徒变的四色鱼,在奚若看来“考纪元千三百一年驻埃及之回教王尝命各教徒各以首巾之色为表识,则实非凭虚之说”[10]1。
在译者序里还提到“此书为回教国中最早之说部,而回部之法制教俗,多足以资考证。所列故事,虽多涉鬼神怪,近于《搜神》、《述异》之流。而或穷状世态,或微文剌讥,读者当于言外得其用意。”[10]1奚若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在谈论外国小说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中国传统小说《搜神》、《述异》作为比衬的背景。奚若对《一千零一夜》是高度认可的,他认为作品中充满传奇神话色彩的异闻,实则是用讽刺的口吻抨击社会悲惨现状的一种手段,并告诫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应从字里行间中读出书中言外之意,书中所倡导的积极进取、不安现状、勇于探索的精神。奚若在译序里还提到:
“若夫繙译各本,自法人葛兰德译为法文,实是编输入欧洲之始。后英人史各脱、魏爱德取而重译,踵之者为富斯德氏。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冷氏则复取阿剌伯原本译之,并加诠释,为诸译本冠。外尚有汤森氏鲍尔敦氏、麦克拿登氏、巴士鲁氏、巴拉克氏诸本,然视冷氏本皆逊之。今所据者为罗利治刊行本,原于冷氏,故较他本为独优”。”[10]2
这里奚若不仅介绍了《一千零一夜》在国外的德法英等欧洲各译本与其大致发源时间,而且对欧译本做了优劣评价,并陈述自己选取冷氏译本的缘由。初稿译出后“复讨论润色,必期无漏无溢,不敢稍参以卤莽理杂之词,谨以质诸当世知言君子”[10]2。不管是译者对读者负责任也好,还是对其翻译手段做的一番解释也罢,译序中陈述了奚若本人当初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所秉持的严谨态度,但因忌于自己不能将原作的艺术魅力传神地译出,在措辞上尤为谨慎,不敢以不合适的词语将其破坏,于是便用最质朴的方式翻译。这篇译序可称为我国早期研究《一千零一夜》的精粹之作。
四、纳训译者序言
纳训(1911-1989)先生,回族,云南通海人,1941年毕业于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回国后从事翻译,他的译本经历了抗战前和抗战后曲折的翻译历程。早在40年代,也就是1940年2月到1941年11月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便出版过纳训先生译自阿拉伯文的《天方夜谭》5册版本,共50万余字。但真正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并奠定其重要地位的是50年代翻译的三卷本。如果说译者的主体性发挥会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译者的稿酬制度、署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那么相比较,幸运的是1954年的制度、法规,文学文化系统在没有削弱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同时,反而客观上更有力地推动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1954年纳训先生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上深受茅盾报告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鼓舞,有感于“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在中国至今还没有较满意的译本,”深受新时代党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关心与重视,受邀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的“翻译选题草案”,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的真切体会和民族意识潜移默化的熏陶,纳训学先生当之无愧受此重任,毅然决然地抱定抛开之前粗糙的旧译本由阿拉伯原文忠实、高标准、高质量重译的决心。纳训先生依据艾博·安突涅校勘编辑的版本,为了译好这部选本“对难译的句子,总是绞尽脑汁地进行推敲,有时要拿出几个翻译方案,通过比较然后再择其优而取之。”[11]纳训先生并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翻译任务的,相反是出自本心,历时两年半的夜以继日于1956年下半年最终完成了《一千零一夜》三卷的翻译,共80余万字,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7月至1984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纳训的六卷“全译本”,约230万字。译作的成功问世见证了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发挥,由此也奠定了纳训在中国译坛阿拉伯文学翻译的重要地位。
纳训先生1957年3月写的《一千零一夜》序言提到,“该书的来源无从考证,原型有可能来自“波斯”,有可能来自印度。故事来源许多民间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增加直至最终定型成为现在的版本。”[12]1-4译序里提到,因为《一千零一夜》的中文译本大多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故而“一鳞半爪,看不出原作的全貌和规模。”[12]1-48月出版的为埃及童话家卡密尔·铿辽涅先生为儿童编写的儿童故事《一千0一夜的故事》“译者的话”中介绍“因为故事是阿拉伯人在夜里讲述的,而古时中国人称阿拉伯为天方国,所以一千0一夜被译为天方夜谈。”[13]在这则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译者重译此书的目的,参考的译本以及“天方夜谈”译名由来的原因,序言里的这些文字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纳训译者提供了帮助,由译者本人写出的译序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五、郅溥浩译者序言
从阿拉伯文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还有郅溥浩,1939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先后在大马士革大学、开罗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译者的主体性发挥表现在其对原作的评价方面。郅溥浩尤为称赞的是“《一千零一夜》是古代阿拉伯的一部文学名著,也是阿拉伯人民贡献给世界文苑的一株闪烁的异彩的奇葩”,说它“故事跌宕起伏,变幻莫测”,[14]6说它“故事套故事的框架结构是该书的一大艺术特色”,说它“诗文并茂,语言大众化”,[14]6同时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该作品的精神价值及主要内容,“它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现了对美与善的褒扬,对丑与恶的摈斥;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勇敢,”[14]3-5但瑕不掩瑜的是该作品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宗教色彩过于浓重,对妇女存在某种偏见,有的故事比较粗俗,显得重复。”[14]6
在译者序言里谈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来源是一部名叫《赫扎尔·艾福萨纳》(又名《一千个故事》)的波斯故事集,而这个集子里的许多故事都来源于印度。说书人对里面的故事不断加工、润饰,吸收新故事和传说,后来被伊拉克人哲赫舍亚里收集、编纂,“以一夜为单位,每夜一个完整的故事,”[15]2但由于只编纂到四百八十夜便去世了,这本书被当作雏形保留了下来。在谈到此书的特色时,由于里面的故事经历了阿拉伯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故事类型具有鲜明的阿拉伯色彩。译者还谈到在对“真主”和“安拉”的称谓上,不同译者的使用不同,“但词义相同,故而没有作改动”[15]8。译者尊重原文的阿拉伯特色,作为阿拉伯文学研究者郅溥浩,其一丝不苟、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呈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译者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作为文化传播者,其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的更多差异性与同一性认识,他比较了作品中的故事与中国的某些民间故事的相似或类似,如“中国唐朝孙《幻异志》中《铁板三娘子》与本书中《巴西姆王子和赵赫兰公主》里的一则故事几乎完全相同,”[15]7这为不同民族和国度间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六、结语
翻译长久以来以规范研究为主体,但随着对翻译认识逐渐深入,原先由翻译规范性的研究开始转向描写性研究,而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主体地位愈来愈受到重视,正如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把翻译过程研究和翻译实践研究相结合起来,如此这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被操纵的复杂过程:例如翻译的文本是如何被选择的,译者在选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译者运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制定标准等。”[16]本文通过清末民初一直到当代《一千零一夜》众多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本做的历时考察,其中包括周桂笙、周作人、奚若、纳训、郅溥浩译者们的序言,发现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在译者选择原作、评价原作、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方面表现了出来。对译序所展现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经历的思维过程,译者面临的诸多选择、诸多取舍的关注,都有助于我们客观公正的认识译者这个主体。译者主体性的角度使我们不但更为充分地了解《一千零一夜》译本的发展脉络,详实的译序重现了译者们当时的翻译情景和动机等,而且对我们重构《一千零一夜》文学经典,丰富和发展《一千零一夜》文本具有开创性意义。
[1] 王友贵.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J].外国语言文学,2007(1):40-46.
[2] 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王飚.中国文学通史:第七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43.
[4] 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九卷)[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329.
[5]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34.
[6]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11集第28卷·翻译文学集3 [C].上海:上海书店,1991:359-382.
[7] 尚海,夏小飞.周作人小品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1.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107.
[9] 周作人.<侠女奴>说明[M]//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9:41.
[10] 叶绍钧,校注.天方夜谭序[M].奚若,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11] 锁昕翔.纳训评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270.
[12] 纳训.一千零一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13] 铿辽涅. 一千0一夜的故事[M].纳训,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1.
[14] 郅溥浩.一千零一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15] 郅溥浩.一千零一夜[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2.
[16]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123.
(责任编辑:王 荻)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tudy ofTheThousandandOneNights
MA Zhen-n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 Jiang Normal University,Wulumuqi 830054, China)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ever before has been paid to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gives a diachronic description of representative versions ofTheThousandandOneNights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ll today by introducing and discussing the following translators′ preface, Zhou Guisheng, Zhou Zuoren, Xiruo, Naxün and Zhi Puhao. Such reliable materials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aspects of original material selection, evaluation of the original, translators′ cultural awareness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warene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c. On the one hand, it can fill the gap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ors′ preface in the book ofTheThousandandOneN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n initiating significance in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literature classics ofTheThousandandOneNight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or′s preface; diachronic description; literature classics
2017-01-13
马祯妮,女,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
H059
A
1008-2603(2017)02-0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