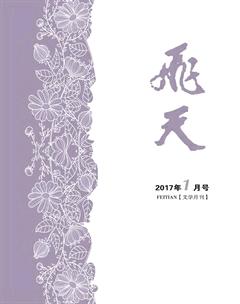老 兵
朱东
9.3阅兵前夕,组织安排我提前去看望抗战老兵。
名册中多了五六个名字,我问原由。民政局的同事说,中央的政策落实了,但凡打过小日本的,都颁发抗日纪念奖章,发放抚恤金。所以有几个仍健在的国民党老兵经核实入册了。
我瞬间想起了我的二伯,要是他能亲耳听到这些话该多好!
一
小时候就知道二伯有些故事。
二伯身材魁梧,质朴厚道,慈眉善目。但有一个缺憾,他的左眼瞎了。
平时村里的人见到他打招呼时都叫他阿二哥,而他不在场时,人们则私下称他“单眼佬”。二伯有意无意中听到这种称呼,从来没发怒,连半点愠色都没有。我想他的平静中有宽容,也有无奈吧。
而且因为这个特点,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少背地里都称他“独眼二哥”。
小时候看电影,有独眼龙角色的,百分之百是诡计多端、凶残狡诈的形象。因此,“独眼二哥”这个绰号一直让我很纠结,二伯毕竟是父亲的堂兄。每次听到这些称呼,我心里都很不爽,往往向他们投去恨恨的一瞥。
父亲排行六,二伯排行二,所以叫他二伯。我问父亲,为啥二伯的眼睛瞎了一个?
当时父亲叹了口气说,那是在当国民党兵时,打仗打瞎的……你二伯,这辈子不容易!他摸了摸我的小光头继续说,还有,在村里的花名册里,他和我同名呢!你长大了,多孝顺二伯……
原来二伯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但这段历史并不光彩,他毕竟是国民党的兵。在六七十年代那种政治环境,这个身份无论如何都带有负面的形象,甚至是讳莫如深的。
二
记忆中的二伯,不爱主动和人说话,很少像我其他叔伯那样时常聚在一起,喝得脸红脖子粗,说着让大姑娘红着脸躲开的粗话,吆喝着,一副快意恩仇的样子。但只要别人先和他打了招呼,他那只独眼就会闪过一丝光芒,感觉他整个人都振作起来,挺一挺腰板热切地回应着。村子里的人都喜欢找他帮忙,帮着到邻村找兽医看个猪病,到镇上集市捎回点特产,病了帮出几天工、耕几天田,他是来者不拒,而且总是乐呵呵的,仿佛来找他帮忙的人都是他的贵人,热情得让人心里好暖,反倒像是帮了他的忙似的。
除了每天劳作,年复一年地耙田整地、挑担施肥等重体力活外,他还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打草鞋,每每有空便坐在门前的大榕树下,边乘凉边用干稻草编织草鞋。金黄的稻草编出的也是一双金黄的草鞋,每打好一双便挂在土墙的木钉上,等到墙壁上挂满一长串草鞋的时候,他便用扁担挑上草鞋到街上卖,所得到的钱便用来买盐油酱醋。
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我看见二伯一个人赤膊在树底下专注地打草鞋,便好奇地走过去。他没有和我搭话,我也习惯了他的沉默,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一招一式。
二伯坐在大树底下的石条上,低着头,弯着腰,一个脚踩踏着尚未编织好的草鞋雏型,两个手则交互有序地穿插着摆弄稻草,动作娴熟而灵巧,似乎天生就是编草鞋的行家里手。我惊诧他高超的手艺,侧头仰慕地望着他。这时,我意外地发现他古铜色的臂膀上有一道长而深的伤痕,伤痕的上端还呈三叉状开裂,边缘则是隆起的肉坨,像一条肥大的蚯蚓,尾端被截成了三段,重生成三条小蚯蚓。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过?我用手指着那道伤疤,惊奇地问,二伯,您的臂膀怎么啦?
这瞎了的眼睛和隆起的肉坨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我追问并屏住呼吸迫切等待答案,就像在草丛里伺狩一只小白兔。
二伯一直很宠爱我,看到我这样好奇,冲我微微一笑,并停下手中的活,拍了拍身边的石凳,示意我坐下来,然后向我讲述。
当年,二伯才二十出头,宽肩大耳,血气方刚,有一天他和同村的五十六公因放田水的事闹起了疙瘩,先是对骂,谁都不让谁,局势不能自控,一老一少竟抡起彼此手中的铁锹对打起来。打斗中,二伯的铁锹铲中了五十六公的前额,顿时血流如注。五十六公随即吆喝着他家的几个兄弟迅速赶来,二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打伤人是要吃官司的。二伯打斗时胆子不小,伤人后却后怕不已,跑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但这毕竟不是辦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正为如何逃脱这官司发愁,恰巧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国民政府要招兵!
他觉得这是个好门路,既可逃脱这场官司,还可以找到一条生计。他觉得自己没什么能耐,但有的是力气,当兵打仗说不准还可成为英雄。因此,没有多想,就兀自跑到征兵点报名。
长官问他叫啥名字,他才想起,自己没上过学,父母按排行,一生下来就叫他阿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阿二,因而他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排名。
长官,我叫阿二。二伯怔怔地说。
不行!入伍是要有一个正式名字的,就是你读书时起的大名——书名,这个书名在村公所是登记备案了的,不懂回去问问你爹娘吧!
不管二伯怎么恳求,长官就是不通融。
无奈,二伯只好趁夜色苍茫之时偷溜回家,将自己当兵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父母听了后商量了片刻。二伯的娘叹了口气说,咱们家境不好,又遇上这等麻烦事,当兵入伍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如果长官要你,你就去吧!
娘,可是长官说当兵是要有书名的,是登记在册的,用排名是报不了名的。二伯不安地解释道。
你没上过一天学,谁曾想到给你起什么书名?更说不上什么登记备案了。二伯娘看了二伯爹一眼,接着说,他爹,你看怎么办?
站在一旁的二伯爹一时也不知所措,在房里来回踱了几步,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是啊,怎么就没给他起个书名呢?
说着说着,忽然二伯爹眼前一亮说,有了有了!你堂弟阿六不是上过三个月的私塾么?他肯定起过名。
一贯老实巴交的二伯爹,此刻也有了不老实的念头。
为了儿子的出路,二伯爹悄悄找到父亲,神秘地问,阿六弟,你读过几天书,想问问你起了个什么好名字?
父亲不加思索地说,有啥好不好的,我的书名叫张林,怎么啦?
也没什么,就问问而已。
二伯爹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悄然离开。
回到家里二伯爹压低声调说,我问了,阿六弟书名叫张林,这个名字是登记了的,在村里也肯定查得到名册,你就用这个名顶替去报名吧,明早趁天还没亮前就走,省得招惹五十六公。
当晚二伯娘便将二伯的几件旧衣服整理了一下,打了一个小包裹,备了几个烤红薯。第二天天色还灰蒙蒙的,便上路往乡里的征兵点赶。
有了正式的书名,二伯不费什么周折也就顺利入伍了。
二伯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后,便投入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一杆枪、一顶帽、一双鞋,一次次冒着枪林弹雨,进行着残酷的拼杀,身上累累的伤痕,记载着他当年的勇猛。
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淞沪会战中的一次正面阻击战。与日军厮杀之近,他几乎可以看到进攻第一排日军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日军为了配合地面作战,派了很强劲的空中支援。他的左臂膀被炸裂成树丫状,左眼被炸,连眼珠子都找不到。
但侥幸的是每一次的厮杀之后都能活着回来,跟无数死难的战友相较,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于他战场上的勇敢表现,即便有勇无谋,以他的累累伤痕还是获得了副连长的军职。
抗战胜利后,他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可以回家,可以见到久违的父母,可以娶妻生子,可以成家立业了。
遗憾的是内战的烽火又熊熊燃起,他再一次被派往战场。
这次,面对的敌人是自己的同胞。兄弟相煎,情何以堪?他没有了与日寇相搏的赳赳斗志,也没了视死如归的激昂情怀。他的战友一个个死去,他们的战场一个个丢失。在气势如虹的解放大军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二伯也因为消极作战而丢了军职,又回到了起点,成了一名普通士兵。
在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攻势下,昔日的蒋家王朝纷纷瓦解,蒋介石无奈地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台湾一隅,二伯也跟随着这群乌合之众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
台湾这块富饶的土地留给二伯印象最深的当数甘蔗,那大片大片的甘蔗林长得葱茏茂盛,蔗秆粗得像桁条。
然而随着时光飞逝,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怀与日俱增,每当月轮高挂、涛声拍岸之时,遥望海峡对岸,一种叶落归根的情结缠绵着他折磨着他,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战友竟不谋而合,冒死开了小差,架着木舟劈波斩浪偷渡茫茫海峡,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思盼已久的故乡。
故乡并非他想象中的温柔乡,自踏上故里的那一刻,苍凉与感伤便无情地向他袭来,爹娘都已离开了人世,妹妹也远嫁他乡,他成了一个孤男,一个受了伤、瞎了眼的国民党逃兵。
左眼彻底瞎了,这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无比的苦痛。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却没有让二伯成为英雄。
五十六公并没有找二伯的麻烦,是因为他早已上了天堂。但在刚解放的年代,二伯这个国民党的逃兵无论如何都是难有立足之地的。破败的旧祖房,简陋得再也无法简陋的家什,让他在孤寂与寥落中度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组织都不需要他,他成了没有人喜欢的残疾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瓜田月下,荷锄播耕,即使平淡,却也安然,比起昔日的刀光剑影、出生入死,不知要强多少倍!所以,二伯对平淡的生活安之若素。
在偏僻的农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然是万古不变的规律,即使是瞎眼的二伯也不能脱俗,年近四十的二伯开始计划传宗接代的事情。他是独苗一个,再不找老婆生子,恐怕要绝了,这叫无尾无后,老了没人照顾,终了没人上香。对于长在农村的男人来说,那是何等的没面子。
二伯乐于助人的优点帮上了他的忙。且不说即便在极左的年代也没有人想到他是坏人,也从没挨过批斗,比起文革期间那些被批斗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他要幸运得多了,更重要的是村里人都为他的终身大事牵线搭桥,朴实的村民都心疼这位善良的老兵,希望帮助他延续香火。
村里的热心大妈为他托过不少媒,但女方了解到他是个单眼佬,而且是个国民党逃兵时,都打住了,一来是怕牵连,二来也怕生出来的后代也是瞎的。擔心后代是瞎子显然是愚味无知,而怕牵连却是现实的,随时都可能发生。
就这样几回惊喜,几回失望,女人还是没有跑到他的床上。
有一天,同村的阿大嫂拉二伯到墙檐的偏角处,喜形于色地告诉二伯,阿二哥,前日我得到一个消息,邻乡李村有个王姓女人,三十多岁,她老公是地主,两年前被人批斗打死了,现在一人带着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一男一女,你看要得不?
二伯略沉思了一下,脸上颤出微微的笑意,有点羞涩,有点惶惑,对阿大嫂说,她愿意吗?
呀!阿二哥,只要你开金口,我就去帮你提亲去。
那就先谢谢大嫂了!
谢什么啊,你帮了我们那么多,谢你还来不及呢。你等着好消息吧!
第二天,阿大嫂就找到了联络人,一道去了李村。
王姓女人名叫王英,中等身材,不瘦不胖,虽然年纪不大,但生活的坎坷和辛酸让她略显沧桑,沉静中带有几分抑郁,见了提亲的大嫂心里忐忑,是福是祸,心中狐疑。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已经有了一次痛苦的经历,自然对这件人生大事感同身受,不期望嫁得好,但愿是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就该是一扇厚实的门板、是一副宽大的肩膀、是一座巍然的大山。
王英迟疑地望了一下大嫂,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听道,他人怎样?
不怎样,老男人,年近四十,家里就他一个人,当过兵,打过仗,瞎了一只眼。
王英有点吃惊:当过兵?打过仗?还瞎了一只眼?
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又问,他德性怎样?
说到这个呀,他什么都不怎样,就这个好,方圆十里谁不知道阿二哥呀?人老实巴交,勤劳轻快,乐于助人,全村上下,哪家他没帮过忙?就凭这点我就乐意为他提亲。
那我拖男带女,地主家庭,他嫌不?
嫌啥呀?这些情况我都跟他说过了,再嫌他就没老婆了。你呢?
我不图别的,只要他老实可靠对娃子好就行了,好歹有个照应。
算是造化了,既然这样,你还要去看看他家门吗?
他不嫌我,我也不嫌他,家门就不用看了。
那就收拾收拾,选个吉日就过门吧!大嫂一边唠叨一边用手端起王英给她准备的米汤,送到嘴边,说,跑了半天,腿也累了,嘴也干了,饭不吃你的,水总要喝口吧!说着,咕嚅咕嚅地将米汤往喉咙里灌。末了,用手将嘴一抹,随即又将手在裤子上一擦,说,我走了,家里还有活,你等着吧,到时叫村里人来接你们。
王英还想留大嫂吃饭,而大嫂那双麻利的大脚早已踏出大门,和联络人一道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赶了。
没有太多的周折,二伯的大事就算搞定了。
过了十多天,王英带着儿女和一些家什来到了二伯的家里。第一次见面,既是约会,也是结亲。按当地习俗,供过香、拜过堂、烧过炮、发过糖,就算夫妻了。虽然仪式简单,但二伯娶亲,新人到来,还是引起了村里男女老少的关注,大家怀着好奇的心,聚拢到二伯的家门口围观,看看新娘的样子,漂不漂亮?善不善良?腰腿壮不壮?腰粗腿壮在农村是劳动好手的标志呢!
大家经过一番评头论足,欣慰的眼神中夹着赞许,说阿二哥还是有福气哦!总算苦尽甘来了!
一群小孩得了喜糖还久久不愿离去,这难免让二伯婶有些尴尬,毕竟第一次到新家,还没有来得及找个独处的空间和新郎寒暄几句。
为此事张罗了一整天的大嫂也是过来人,对新婚夫妻还是有独到的理解,于是走到孩子面前,叉开双手,像赶鸭子似地大声训道,都走开走开,新娘要休息了,这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就回去问问你爹你妈!
于是一群孩子便一哄而散。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俩勤勉耕耘,寒来暑往,过着恬静而安定的日子。
但多年过去了,二伯婶一直没有能怀上二伯的孩子,二伯传宗接代的愿望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在传统观念中,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才是真正的传后人,老婆带来的儿子算什么啊?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说不准长大成人了还要跑回老家去。那岂不是白养了?
在农村中,跟母亲改嫁上门的儿子往往被称为“带闺子”,是很受人歧视的,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带闺子”长大后,都回归原来出生的地方。二伯这种隐忧是存在的,但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认命。有时二伯胡思乱想,是不是他在战场上杀了人,积下了罪孽,老天以此来惩罚他,让他断子绝孙?
现实就这样不容置疑,有时还得认命。二伯在困惑中,还是得到了些许安慰,那就是二伯婶带来的那双儿女还算懂事听话,对二伯尊敬有加,姓氏也由原来的李姓改跟二伯姓张,这是对二伯的莫大安抚。有一次大儿子张兵见二伯不开心,好像看出了二伯的心事,于是对二伯说,二叔,长大了我会好好照顾您的!这句话让二伯十分舒坦,他沉闷的脸陡然绽放笑容,乐呵呵地用手拍着张兵的肩膀说,好小子,老了就得靠你了!
张兵听后,用坚毅的目光看着二伯,默默地连连点头,说,二叔,您放心,我会的!
就是这样几句简单的交流,让二伯的观念来了个大转弯,他不再认为自己没有接班人了。他将这对儿女当成自已的亲骨肉,尽管夫妻俩含辛茹苦,但感到有了奔头,也其乐融融。一对孩子也在他们的供养下,很快长大成人,男婚女嫁。
二伯的故事讲完了,我对二伯的瞎眼和伤疤产生了敬畏。我抚摸着那条大蚯蚓和三条小蚯蚓,崇拜地对二伯说,你就是我在课本儿里学习过的战斗英雄!以后,我不许人家再叫你什么“独眼龙”了,谁要是再说你是逃兵,我就和他们急!
二伯眨了数下眼紧紧看着我,他的单眼湿润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老男人的眼神,竟然这样温暖,充满了感激,还有欲哭的冲动。
他叹了口气,把手里做好的鞋子塞在我手里,说,憨子,把这双鞋带回去给你爸,就说是他二哥送给他的,谢谢他教出个这么懂事的侄子!
我不肯收,二伯执意要给我,且很固执,并说,二伯不是战斗英雄,但也不愿意别人叫我逃兵,可惜……政府不承认啊!二伯的心病只有你这憨子懂!什么时候你这句话也能从政府的人嘴里说出来,二伯这辈子才值啊!
三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问题也摆上了重要的议题。退伍军人的优抚政策不断出台,抚恤金也逐年水漲船高,凡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战争的退伍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生活补贴,每个月的政府补助,对生活在农村的退伍军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村几个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都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吸引了村里不少老人羡慕的目光。
作为老兵的二伯能不看到?尽管瞎了一只眼,他心里还是很亮堂的,但没人来过问他,谁叫自己站错了队?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啊!当年怎么就稀里糊涂当了国民党的兵?尽管二伯在抗日战场上也曾奋勇杀敌,杀过不少日军,为抗日战争流过血、流过汗,差点还掉了命,可谓九死一生。但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后来掉转枪口和共产党对着干,也是身不由己,并非自己所愿,他有错吗?他能改变得了吗?
但想归想,现实归现实。谁叫自已也打过共产党?这就是宿命,不得不承认啊!想到这些,二伯心里虽有纠结,但似乎也想通了。他依旧重复着那些固化的劳作,耙田、整地、挑担……还有编草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年四季默默地、平平淡淡地度着自己的时日。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给沉寂多年的大陆国民党老兵带来了一阵惊喜,讲话中第一次明确表示,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抗击过日军,都是有功之臣,都不应忘却。落实到政策层面,不少地方的国民党老兵获得了补助。
二伯得知这一消息,心中充满了兴奋,不仅仅是因为有实惠的补助金,更重要的是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当年不惜流血牺牲之念,打生打死图的是什么?却在打败日寇之后的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歧视,被社会淡漠。想到这些,不禁百感交集,是苦是甜,是悲是喜,一时无从分辨,或许是悲喜交织,或许是甘苦糅合,他心里一阵酸楚,身子一阵抽动,抑制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泪水,包含了他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积淀了多少的压抑与无奈。多少怨?昨夜梦魂中……
民政部门为了落实政策,进行登记核实。有一天,民政干部登门拜访二伯,这让二伯喜出望外,期待着的光明时刻就要到来。
民政干部问,阿二哥,你有士兵证吗?
二伯没有多想,就说,过去曾有过,但在文革时期怕牵连烧了。
没有证件也可,但有谁能证明你抗日呢?
三沙乡官村的李龙、李平都是跟我一起参军打仗的,也是一起回到大陆的,你可问问他们。
他们还健在吗?
前几年还在,还在街上碰过头,一起商量过我们这些老兵的事情,但他们身体都不好,都八十几岁了。
那你去找找他们,要他们做个证人,最好写个证明,拿到乡民政所找我们,证据核实了,我们就按政策办事。
二伯连连点头,说,好!好!这个不难,他们会为我作证的。
第二天一早,二伯踏着朝阳,心情特别的晴朗,一路往三沙乡官村赶。
到了官村,见了一个中年人便问,小兄弟,李龙伯家住哪呀?
中年人也算热情,用手往一栋简朴的土坯砖屋指,说,那就是李龙伯家,不过李龙伯前年过世了,你有事找他?
二伯一愣,心里一沉,怎么就去世了?真是死得不是时候啊!
接着又问,李平伯家呢?
中年人答道,李平伯家去年全都搬到镇里去居住了,不过李平伯几个月前也过世了!
听完中年人的回答,二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木然地望了一眼中年人,连谢都没及谢,转过头去,默默地往回走。
他辛苦了一辈子,眼看有了盼头,可现在却拿不出证明,天意啊!
除了这两个人,世上再没有谁能为自己作证了。二伯一阵迷茫,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是国民党老兵,曾为抗日救国拿过枪、抡过刀、杀过小日本。如果就此止步,他于心何甘?且不说那些补助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回他的尊严。几十年的冤大头,他受尽了歧视,今天迎来了正名时刻,他不能错过呀!
几天之后,我回村办事。他听说之后,当夜就来到我家,和我说了这些遭遇。我这时已经是一位国家干部,对于二伯来说,我的意见就犹如他当年颠簸在海上逃回大陆时紧握在手里的指南针。
他看着我,就像多年前依赖指南针寻找方向。我沉吟了一会儿,想到了他被打瞎的眼睛、他臂膀上的大小蚯蚓、他的满身弹伤,这不是最好的明证吗?
第二天,二伯按照我的授意,找了村里两个与他年岁相当的老人,一道来到了乡民政所,找到了那天向他了解情况的两位民政干部。
民政干部问他,阿二哥,这两位老伯就是你所说的证人,一同与你参军打仗的国民党老兵?
不,不是!那两位老兵我去找了,但都去世了。
那怎么办啊?谁还能证明?
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二伯称干部为领导,并用手指着自己一只瞎了的眼睛说,这个能证明吗?
那是什么时候受伤的?
就是在淞沪会战时被日军炸伤的。二伯边说着边捋起左手的袖子,向干部展示臂膀上隆起的肉蚯蚓,继续说,这处伤也是那次战役中被弹片炸裂的,还流了不少血。接着又打开衣裳,露出腹部的多处伤痕。
干部点了点头,谁能证明呢?
二伯急切地答道,我这两位同村的老弟当年都知道我参加了国民党部队,解放后我从台湾回到大陆时,我曾多次向他们讲过我参战的经历,讲过我的眼被打瞎和我的臂膀受伤的过程,他们是知道的。
那两位老者频频点头称道。一个老者说,二哥讲的情况都是事实,解放后他多次跟我们讲过参军战斗受伤的情况。另一个老者插话道,二哥是个大好人,政府应当为他考虑考虑,我们村几个当过兵的没有受过伤,但都落实了政策,况且二哥受了那么多的伤。说完,他们三个都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两位民政干部。
显然他们都被这些疤痕触动了。一个民政干部说,几十年前的事情,要找证据的确也是不容易的,许多国民党老兵都有你类似的情况,在文革那个年代谁还敢保留这些国民党士兵证?这不是找死吗?相关的知情人也大多散失,或不在人世了。
二伯听后,说,你这位领导讲得好,句句在理,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不是我说得好,事实的确如此,正因为这些复杂的特殊的原因,相关文件的实施细则也照顾到了这种情况,如当事人能将抗日的事实讲清楚,讲得与历史能吻合也可作为证据予以确认。
二伯激动得眉毛、胡子都在抖动,连声说,谢谢!谢谢!
另一位干部补充道,这样吧,我们将你的情况再向上呈报,待核准了,再通知你过来填写相关表格,你回去等好消息吧!
三个人唯唯诺诺谢过民政干部,走出了民政所。
回到村里,以感谢大家帮忙为名,二伯竟然请客,把平时帮助过他的叔伯们都请到他家喝酒。
饭桌上大家都知道了民政所干部松口的好消息,一个老者道,二哥,这可见天日了,委屈了这么多年,应当是有好报了。
另一老者道,这回好了,名声正了,还会得到一笔补偿,恭喜二哥啊!
二伯道,這事还多亏你们大家的帮忙,替我说了这么多好话,不然结果还真是难料呀!
七叔关心地问,二哥,估计会有多少补贴啊?
八叔也插话了,我估计不少!不用再从日到黑地编草鞋卖了!还够二哥天天吃肉喝酒的!
喝了半碗白酒的二伯已经非常亢奋,脸涨得很红,碗里的酒映照得他那只还看得见的眼水汪汪的。听到大家这些议论,他重重地放下了手中的碗道:
我啊,为这件事折腾了那么久,主要还是想正个名、出口气,至于那些补贴,我想不必计较,不管多少,我全都捐给我们村里的小学,为娃子们买些书籍和文具。
酒席上的村民都静了下来,都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二伯,刚才插话的八叔又说,二哥,你家并不富裕,而你却有这个想法真不简单!过去我们小看你了,都以为你一直为钱而奔波。
二伯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和胸膛,仿佛是要平复情绪顺一下酒气,又仿佛是要提起情绪将藏在心里数十年的话从心窝里掏出来。
——兄弟!二哥比起那些早死的战友,这辈子已经活得够长!但就是还差一个说法,如果真能像今天那两位同志说的,我这辈子才叫活得值!
钱算什么!比得上眼睛重要?比得上自己的子女重要?我不稀罕钱,我只要大家伙不戳我脊梁骨,说我是逃兵……再说了,把钱捐给村里的娃,都好好读书,都到城里做干部,和鬼佬们讲英语,让他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能耐,别老想着再欺负我们……
不善言辞的二伯讲到这里意犹未尽,又不知再说些什么,他端起酒碗,环视大家,闷头一扬脖子,喝干了碗里的酒。
大家逐渐理解他心里的想法,同情他的苦楚。八叔站起身端起酒坛,帮他又满上了一碗。有一个疑问藏在心里,借着酒性,小心翼翼地问,二哥,如果留在台湾,可能你的待遇会好些,你,后悔不?
二伯拍拍八叔的肩膀,示意他坐下。大家的眼光都凝聚在二伯身上,他却久久没有开口。他端起酒碗,头低了下去。大家以为他要喝了再说,都等着。
结果他没喝,而是缓缓地放下了碗,从裤腰带里哆嗦着解下一坨物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旧的指南针,它的盖盒和沿边都因为被日夜摩挲而褪了色,但它依然洁亮光泽,仿佛用此来炫耀主人对它的疼爱。
——说起要偷渡回来,我们哥几个那时心里也在犯嘀咕,茫茫大海,哪见得到头?又是在夜里,别说是被部队发现了让我们吃枪子儿,就是一个大浪也会送我们去见阎王,要不就是找不到方向,在海里漂个十天八天,漂到别国的地盘里去了——
可是当我们偷到长官的这个指南针以后,我们就铁了心了——死也要死在故乡!不能死在故乡,也要死在回故乡的路上!在台湾,就是再好的待遇,我们一分钟也不想多呆,这种滋味儿,你们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的人,不能体会……
又是一阵沉默,我父亲率先举起了酒碗,说,二哥,我心里埋怨过你冒我的名去参加国民党……现在我要说的是,不管干部怎么划分,你都是条好汉!英雄!
对,对,你就是战斗英雄!为我们村争了光!大家纷纷附和,给二伯敬酒。二伯来者不拒,一碗一碗地干,在他仰头的时候,还数次顺便拭干了快流到腮边的泪水。
打这天以后,二伯明显比以前开朗了,脸上总带着开心的笑容,见面也主动和大家打招呼,大家也觉得跟他的心都更近了,他不再是村里一个不合群可有可无的“单眼佬”,叔伯们频繁邀他聚,他也乐意整上两盅,侃侃他在战场上如何出生入死,说说他和战友们苦中作乐的零碎记忆。
父亲说听得最多的就是——老子不是逃兵!老子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一点不含糊,冲上去就踢他的裤裆——我让那狗日的断子绝孙!——可是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啊!谁不是爹娘身上掉下的肉?说不准对面那个就是邻村的兄弟,爹娘都还等着我们回去孝顺呢……
四
一个多月过去了,民政所捎话给二伯,让他到所里去一趟,二伯听后一脸的喜悦,每根皱纹都在绽笑,眉毛和胡子又一次颤抖,屋前的阳光格外明媚。
二伯带着难得的好心情又一次踏进了乡民政所的大门,接待他的依然是那两位民政干部,他们的态度和蔼,见了二伯仍是客气地请二伯坐下,并送上一杯开水。
一位干部说,阿二哥啊,你的事情我们向上面报告了,上级审核后回话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了解。
二伯心神不宁,急切地问,是什么问题呀?
民政干部盯着二伯,认真地说,你老实讲,当年你跟共产党打过吗?
二伯心里一下子乱了方寸,这个问题一直是他多年来的心病,他回到大陆后,最怕别人有意无意提起这件事,这是他的痛处,他一直不敢向别人说出这件事,村里的人也没有谁知道,与他一同去参加国民党部队的李龙、李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同一个连队,但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共产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们也重新被整编,并不在同一连队,败退到台湾后,命运又把他们搅在了一块,也正因为老乡的缘故,他们才敢一起合伙商量,一起冒险偷渡回到大陆。如今这两个老战友都相继作古,还有谁知道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呢?
二伯一时不知所措,谈吐明显结巴,无法回答民政干部。
民政干部见他脸露难色,沉默了好一会仍没答上来,便开导道,你仔细想想,和共产党打过没有?上级只是需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另一位民政干部道,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即便跟共产党打过,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奇怪,你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这也许怪不了你。中央领导不是说了嘛,只要抗日有功,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值得引以为荣。你将这个事情讲清楚,我们将情况补充后再报,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只是个手续问题。
二伯将信将疑,即便如此,他也说不了谎,他压根就没想说谎。
我承认,那时也和解放军打过,放过枪,开过炮,这都是迫于万分无奈,打心眼里就不想跟自己的同胞打,所以我和很多战友一样一直是消极应付,漫无目的地举枪乱射,险些误伤自己的同伴,后来也因此被削掉军职,差点还掉了脑袋。
干部听后,默默地作了记录,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二伯很想为自己辩解,但是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嚅嗫着,不停地咽口水。
民政干部见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便打圆场道,就这样吧,你先回家去,等好消息吧!
回村里以后,他那刚被唤醒的开朗又一天一天凋谢下去了,他时常一个人呆坐在村头的榕树下,眺望着村口的方向,期待着什么。年迈的他已经没有力气编草鞋了,只是逢人跟他聊天,他就说,我不是逃兵……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整整过了半年,依然没有消息。
此时,二伯已经九十三岁。他急切而焦虑地等待着,越等越不是滋味,于是便无端地揣摩,是不是因为自己说了和共产党打过仗一事,让这事黄了?
他再也等不及了,索性拖着年迈的身体又一次来到民政所,想问个究竟。
到了民政所,却不见过去认识的那两位民政干部,而是两副新面孔,其中有一个是中年妇女。两位干部都在忙碌着查找资料。
二伯低声地问,同志,过去在你们这里上班的那两位领导呢?
一位干部回答道,你找他们有啥事?
二伯道,我是国民党抗日老兵,书名叫张林,排名叫阿二哥,我想来打听一下,抗日老兵的政策落实了没有?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叫张林的阿二哥?是想来找补助金的吧?这个事我听说过,但具体情况我不懂,你要了解,你只能找他俩去。
他俩在哪呢?
妇女干部看着这个穿着简朴、不修边幅的老者,有点不耐烦,冷冷地回了一句:到监狱里去找吧,他们合伙贪污坐牢去了。
二伯听后,头脑一阵眩晕,心头一堵。跑了这么久,就这样一个结果?是政策落实不了?还是落实了政策却被贪官从中作梗截住了?他已无法考究,也无力考究。
他看了看两位民政干部,微微地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上,退出了民政所。
乘上公交车后,二伯一聲不吭,两眼木然地望着窗外。半个时辰后公交车在村公所停下,他下了车,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屯里走。
村公所离屯里还有三公里,一条山道蜿蜒其间,刚走几分钟,二伯才发现天变了脸,雷声轰隆着,道道电光撕裂着沉重的铅云,怒潮般的云涛如烧开了的沸水,奔腾着、翻滚着。不一会,大雨便倾盆而泻,整个大地似乎都在抖动,烟雨横斜,山色空濛……
二伯似乎对滂沱的大雨已不在乎,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他的路,狂风夹着大雨横扫着他枯老的身躯,他晃着身子,吃力地在风雨中前行,到了一个山坡的坎上,两脚突然打滑,一个趔趄,摔了下去……
当阵雨过后被村人发现送回家时,二伯已奄奄一息,他喃喃地说着自己不是逃兵,还有要捐赠给小学的补助金……
二伯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五
我握着手里的花名册,心里想,慰问老兵的事情真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绝不能让更多的老兵像我二伯那样死不瞑目,带着遗憾去另一个世界。
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在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那天,去二伯坟前敬上两杯酒。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