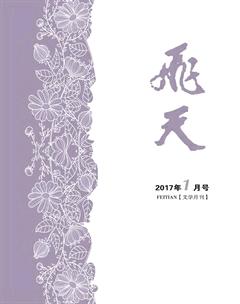女士,留步
晓雅
有人抱着狗乞讨,那只狗所表现出的忧伤一点儿也不比主人少。英子把一盒饼干放在乞讨者的面前,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英子不管他是不是职业性的忧伤。巴黎大街上有那么多心事重重然而却相当克制的脸,他们在行色匆匆的人群里或者在某一扇窗玻璃后面。
从巴黎圣母院回来的路上,歇脚的工夫,英子在叽叽喳喳的说笑里看着对面,大树落光了叶子,状如铁丝的小枝丫向天空放射出一朵朵灰色的烟花。小广场有个不大不小的自由女神。在英子的手机屏上,女神手里石头的火炬正朝向一树烟花。小王,表妹的那个同事,把头凑过来说,拍得不错。英子说,这个像好看。小王摇了摇头:带你们去公墓,那里面是漂亮女人博物馆。小王于是被簇拥着去公墓了,英子的影子也簇拥着他。小王是好旅伴,不嫌弃她们婆婆妈妈,还愿意帮大家背包、找路。
这个大公墓里埋着英雄、主教、天才、富豪,也有本分的工程师、刚发了财还未来得及享受的小商人。在那些普通人家的墓前雕塑上,英子看到了那些活在石头里的女人,她们在石头里哭泣,鸽子在她们生动的脸上、衣褶复杂的身上和茂密的头发上洒下了一层又一层鸽粪,她们却只顾在石头里哭泣,不仅哭泣,还将叹息从石头里散发出来,弄得这些冰冷的石头无法死去。
英子随着自己的影子在返回的路上和他们一起进了一个小教堂歇脚,他们起身时,英子需要大哭一场,把刚才石头里的气息排泄一下,于是,她看着大家都出去了,就抽泣起来,开始呜呜咽咽,最后就放声大哭。在她觉得痛快的时候,耳边叮叮当当响动起来——门口的吉普赛人进来,拿着乞讨盒子在英子的耳朵边不停晃荡。英子止住悲声,长长地出了口气,又尴尬又无奈地看了一眼。
在哭,你没看见吗?英子心里想。英子的眼中是疑问、委屈和不满。英子看到了一张没有光泽的脸,乱糟糟的头发藏在头巾里,那样子让英子觉得她也许很饿。英子拿出一个硬币放在她的罐头盒里,然后安定了一下情绪,站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觉得可以出去了。她想那个乞讨者的职责大概就是提醒哭泣的人们,要为自己的生活谢恩,因为至少扔掉一两个硬币也不至于就失去了活路要饿肚子。英子想,像她一样需要大哭一场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也许那个乞讨者已经习惯了。
表妹他们正在阳光下叽叽喳喳,英子感到安慰,在叽叽喳喳里飘回住处。
他们住在蒙马特附近,条件差些,但是开了暖气,房间还是暖洋洋的。大家都吃了东西,也都轮流洗了澡。房间里有个小阳台,街灯亮起来,路上人很少,楼下街角有一个小酒吧,分别向三个方向开着门,等着不确定的客人。大家在外面晾毛巾和袜子,出去时冷空气会让人突然激灵一下,但只要关好门,房间里就温暖如春。躺在床上,英子闭着眼睛听他们拿出手机评论照片、发短信、打电话或者整理东西。有伴儿真好,英子感激地想,不用自己躺在黑暗里。她觉得和表妹一起来玩是明智之举。
表妹来里昂参加展会,借着工作之便,几个同事跟老板多要了一周,老板很爽快地准了假,反正里昂以外的一切费用自理。
在里昂的那几天,英子帮他们准备晚餐,其他忙就幫不上。她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巴士来到了郊外,她是从市中心上的车,并不知道目的地在郊外,也不在乎目的地。车在终点站停了,司机看着她。她下了车,哪里也没去,等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又乘同一辆车回来了。窗外有几座高大的厂房,厂房后面是丘陵缓坡、褐色的荒地,往后有树林,树林又接着荒地。路过一段溪水,对岸有旧房子,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人骑车闪过。英子穿着她粉紫色的抓绒外套,如果高一些,倒像个工人,可她瘦小,脸色苍白,头发也不多,那样子像是贫血。她的手不自觉地会在心口停下,总想摸摸心脏那个位置。
英子晚餐前要回去。她从没有来过欧洲,他们先到米兰,当晚就坐夜车到里昂来了。
在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英子像个有感觉的影子,飘在清冷的塞纳河岸,飘过晚上灯光耀金的凯旋门附近,也飘到阴天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过巴黎……英子对巴黎有自己的看法,喜欢巴黎,在他们议论的时候也点头称赞或者再补充点儿见解,但她是个影子。
一个月前,表妹问要不要同行,英子想都不想就加入进来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半年了,她和屋里的旧家具一起,从湿热的夏天坐到冬天,冬天阳光进不到房间,她在幽暗的房间里从早待到晚,晚上才出去散步,邻居在电梯里碰到:好久不见!……英子堆起笑容,她感谢人家的关心,但她说话的时候,头皮、耳朵、脸颊和下巴都在嘎巴作响,好像生锈的机器重新启动,人家看着她的嘴,又看着她的脸,感到惊讶。
英子和表妹一行四人一男三女在香港机场碰头。上了飞机,表妹四人一路没停,瓜子花生、苹果香蕉,制造了好几袋垃圾,中间还有两餐,英子不知道在国际航班上可以这么肆无忌惮,至少表面上没人表示不满。她没有食欲,她庆幸表妹被小吃占着嘴,不来询问她的近况。表妹聪明,不问则已,一问都是要害。十二个小时的飞行,英子睡不着,在熄灯的机舱里睁眼坐着。然后米兰、里昂、巴黎,她每晚都不睡,也不累。白天,她随着大家飘来飘去,或者快,或者慢。
在巴黎飘了一周,大年三十的晚上,英子跟着大家飘落在了香港机场。大巴把旅客运到上水,小王以最快的速度指点晕头转向的女人们到了联检大厅。英子和表妹在几分钟之内匆忙分手,表妹他们要赶最后一趟回广州的火车,跟家人共度除夕。英子也要尽快跟上人流坐上回深圳的中巴。
中间,行李在车上,英子飘在人们中间步行入关,又上车。到了罗湖,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停运,英子飘上出租回到家时已经夜里一点了。
出发去机场之前,英子往阳台看了一眼,灯关好了,窗也关好了。
英子把手摸向身后,双肩包的侧袋里有一把伞。护照、身份证、手机都在小包里,水杯带了,零钱带了。
现在,她又抬头看了一眼,她摸了摸口袋,钥匙在衣袋里。阳台上门窗紧闭,灯黑着。她进了小区大门,保安问,回来了?去哪了?英子从嘴角牵出四分五裂的笑容,送上一盒糖果。她进了电梯,出了电梯,感应灯亮起来。她开了防盗门、木门,开了灯,房间一切依旧,地板上有一只袜子,是她自己掉的,桌布褶皱都没有变,就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她应该烧水、去卫生间、把电视打开、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去铺床、淋浴,彻底放松睡上一觉,然后起床,去一趟菜市场,吃个早餐,去公园晒晒太阳溜达一下,去超市买点儿东西,她应该像个新人一样……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英子还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想到家人走时冷冷地说,不爱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理由。英子在心里说。她想,我也不爱丁丁了,它老了,一身的病,可是我能把它扔了吗?英子也看出来了,家人早就想把丁丁扔了,他是个狠得下心的人。
他们去签字的时候,英子看到家人的眼睛在她签字的一刹那大放异彩,他紧闭着嘴,但在心里,他欢呼雀跃。他解放了,他激动万分!就像八年前他从他前妻那里拿到签字一样,他拿到签字的第一分钟就欣喜若狂打来电话:宝贝,我离婚了!英子当时就觉得身上的泥胎绳索全部脱落,卸掉了一副重重的枷锁,身心内外恢复了活力。她虽然不是导致他们分开的那个第三者,但当时他还没有离婚。他为了一个英子没有见过面的女人和妻子分居了三年,离开故乡,又与那个女人分手,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遇到了英子。
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多年里,他从不给前妻电话,前妻被橡皮擦掉了,只有一抹痕迹。英子此后也要成为那样的痕迹。英子一想到自己突然被家人变成了痕迹,不寒而栗。
分开的半年里,英子听到过一些传言。有一次英子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持续了十多分钟,那是脑溢血的前兆。她对传话的人心生恶感。但那次之后英子想通了,不爱不需要理由,离开却需要借口,家人的内心是愧疚的,他需要台阶,他所说的不实之词不过是些借口,需要借口的人是值得同情的。
但英子的理性并不能阻止她很快成为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
巴黎并不能电击英子的灵魂。三点了,英子还坐在客厅里。最后一段热火朝天的鞭炮炸响时送来的火药味还在空气里留恋着没有消散,再过两个小时,新年的第一声鞭炮又要来了。鞭炮是禁不住的,人们想要一除晦气的冲动总是大过禁令。
英子是什么时候木僵地躺下睡着的,她自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她做了一个好梦,一张十分善良的脸,令她感动万分,心口的余热还在,她的头皮松软了一些,肩膀和背部都不那么疼了,她像被松绑的囚犯似的,在自己的肩膀和手腕上摸了摸,又动了动腿,膝盖和脚腕都活动了一下。英子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面,她看到了自己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这些东西,说上来就上来了,根本没有商量呀!英子看着镜子里这个不仅有白发和皱纹,还带着一种洗也洗不掉的晦气的女人,觉得陌生和反感。英子端详自己的时候,那个令她产生了深深感动的梦境,就被她不小心忘掉了。忘掉了梦境,那一点让她走出家门的热情便熄灭了。她站在镜子前面,对着一張自己都难以找到来龙去脉的脸,回想着家人离开时那冷漠厌恶的表情。也许是因为这样一张脸,家人才会在离婚签字的当天晚上,只放了一小瓶速效救心丸在她的房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但,竟然有人叫她“女士”,那个乞讨者叫她“女士”。此时,她感激起来。
在蒙马特高地下面,一段长台阶开始的地方,有一个高台,本来应该站着一个塑像,人们经过塑像走完台阶,就可以进入高处的圣心堂,去参观这古老的建筑,看里面的彩色玫瑰窗、壁画和大柱子,然后站在外面俯瞰巴黎,巴黎老区的高度还和一百多年前一样,除了个别现代建筑和有限的几个高大脚手架比较突出之外,其余都以矜持的姿态在同一高度里保持着沉默。本该站着塑像的地方站着一个乞讨者,脸上涂着白色颜料,在冷风里扮演圣人,是个老圣人,他的棕色的头发和单薄的白色袍子被风吹乱,令他有些手忙脚乱。他要去照顾衣袍,有些狼狈。英子夹在众人里飘下来的时候,他正弯腰把风吹起来的袍子往下拽,想把自己的腿遮盖起来。英子从他身边过去,把一枚硬币掏出来,仍进了那个盒子,叮当一声吓了他一跳,也吓了自己一跳。英子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除了自己扔下的这枚五毛钱的硬币,里面是空的。她怀着一丝愧疚飘下台阶,身后,那个被她叮当一声吓到的人站起来了,他不去管白袍子和乱发了。
“女士!女士!请您留步!”
乞丐的声音很亮,众人回头,英子也回头。英子这时已经走出了十来米,那人正把两只手伸向这个方向,他看到英子回头站住了,把手缓缓地收回去,放在下巴下方,抱在胸前,抬起头望着高处,又低下头,身体稍微旋转了一个角度,将头与肩对着英子,刹那间陷入了深深的悲哀。英子听到了周围人们低声的惊叹。英子看着他,那完全是一尊雕像,活着的雕像,比那些哭泣的女人更加动人的雕像,雕像里没有眼泪,只有深深的能叫醒石头的悲伤。英子的心动了,她正要从一个影子的状态苏醒的时候,被小王和表妹催促着往前走了,表妹给那个乞丐一个飞吻,很多人都给他飞吻。英子迟疑地转身,一步一回头,跟着众人飘走了。
英子看着镜子,觉得能从镜子里看到那个乞讨者,那个乞讨者不再是臃肿的老人。她想着那一声“女士”。如果再有机会,她想为那一声“女士”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他,他也许跟自己一样,需要一个拥抱。
英子在新年的早晨需要一个拥抱,这是真的。她自己抱着自己,没法体会到拥抱的感觉。她想起了丁丁。丁丁被寄养在海边一个狗场。她立刻洗了脸、煮了面,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换上皮鞋出门了。早晨的鞭炮已经响过了,炸响竟然没有把她吵醒,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这是半年来最不费力的出门,她要去接丁丁,要去紧紧地拥抱丁丁,作为一只狗,丁丁是此时唯一能给她拥抱的家庭成员。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