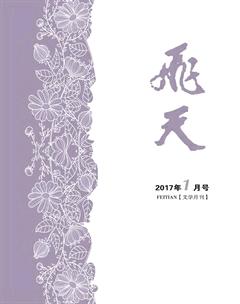好 感
高平
感情上的事,确实有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此也就很难写出来。那次与一位女孩的相遇,既谈不上是奇遇,更不能说是艳遇,只平平淡淡的偶遇,时隔三十多年了,我总是不能忘却。是遗憾、是愧疚、是感动还是欣慰?混杂在一起,无法用理智分清,想要作出何种结论都不准确。
那一年的夏季,我坐火车去北大荒采访,邻座是一位中年男子,态度随和,待人热情,也很健谈。当他知道了我的职业和此行的目的以后突然高兴起来:
“那你要去佳木斯唠?”
“是啊,要先去那里的农垦局报个到。”
“太好了!佳木斯水电局有我的一个学生,她叫郭菊,人很好,是毕业以后分配到那里的,你见一见。我写封信,你带去。”
他叫裘西岩,是东北水利学院的教授,自然也是桃李满天下。他写好信交给我,没有封口,也许是因为火车上没有胶水、浆糊之类,或者觉得信中的内容无可保密之处。但我对此并无好奇心,更要严守道德底线,一直到把信交到郭菊手里,也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我住进佳木斯宾馆以后,到农垦局办了手续,打听到水利局就在附近,为了及早完成受人之托,便去寻找裘教授的学生。
水利局门外挂着醒目的大木牌,很容易就找到了。它是个坐西朝东的大院子,办公高楼和平房宿舍都在里边。传达室的人把我领到了女职工宿舍门口,说了声:“郭菊就在这嘎哒,您进去吧。”
因为天热,又是白日,宿舍的门大开着。这是一间大屋子,摆了好几张床和桌子,坐着四五个年轻的女同志,很悠闲的样子。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是星期日,大家正都待在屋里闲着没事。
在她们好奇的目光的聚焦下,我环视着大家轻声地问:
“哪位是郭菊同志?”
“我是。”
她的声音比我更轻。在她站起来的瞬间,我对她的总体印象立刻凝结为一个字:柔。中等稍微偏低一点的身材,略显瘦弱一点的体质,白净的瓜子脸上没施任何脂粉,一看就可以断定是那种沉默寡言、安详文静、笑不露齿的女子。
她直视我的目光顷刻间由惊疑转换为友好,还含有一丝羞涩。
“你有位老师叫裘西岩吧?”我想验明正身。
“对,他是我的大学老师。”
“他托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我把信递了过去。她的女同事们纷纷招呼我坐下,有人倒了一杯水给我。郭菊在低头看信,大家看看我,又看看她,肯定在做着各种猜想。出于礼貌,我来时穿的是正装,在好几双雌目的齐射下,不由得不自然起来,有了出汗的感觉。
郭菊看完了信,抬起头来,大概发现了我的局促,对我微笑了一下,半天没说出什么话来。我想从她的问话或表情中探知信中写的什么,但无所收获。
“你什么时候到的?”她终于开口问我话了。
“今天上午刚到。”
“以前没来过吧?”
“是第一次来佳木斯。”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在这里没什么事。”
“这地方很美,我带你观光一下我们的市容吧。”
“好的,谢谢你!”
我们走出了大门。
我想她可能对于他的老师和我有问题要问,因为宿舍里人多,说话不便,所以借着观光市容在外面聊聊,可是她竟然一直陪着我散步,什么话也不说,甚至很少抬头,只是指過这是斯大林大街、那是人民公园。如果作为导游员,是绝对不称职的。
她的脚步十分缓慢而轻盈,像一只猫静悄悄地跟在我的身边。我几次想打破这种沉默,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也许她在等待我的问话,可我又能问她什么呢?我只是给人家带了一封信,信带到任务就完成了,再问些什么、打听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不礼貌的。所以我也同她一样缺言少语。
街上行人很少,车辆更少。后半晌阳光已经渐弱,人行道上的树阴铺着时浓时淡的影子地毯,在城市中少有这种无声的惬意。
我们就这样走着,越来越慢地走着,什么也不看地走着,什么也不想地走着,为一块儿走着而走着,为享受走着而走着。
后来,走到我居住的宾馆门口,我们停了下来。分手时,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去北大荒了。
晚饭之前,我正在房间里看本地的报纸《佳木斯通讯》(那时还没有改为日报),电话铃响了。我很奇怪,谁会把电话打到这里呢?
“是李记者吗?”女孩子的声音。
“是,我是李敬。您是哪位?”
“我是郭菊,水利局的。”
“噢噢,小郭同志……”
“今天晚上我请您看电影好吗?票已经买了。”
这大概是对我带信的报答吧。人家票都买了,晚上我也没什么事,就爽快地答应了。
我准时到达了电影院。郭菊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她身旁还跟着两位女同志,一位也就二十几岁,和她年龄差不多,另一位是中年妇女,比我小不了几岁。郭菊介绍说都是她的同事。中年妇女一直端详着我,善意地笑着,好像老熟人一样。
看到郭菊带来了两个同伴,我心中泛起了一层不悦的涟漪,我怀疑她对我存有戒心,会不会是怕我在电影院暗淡的光线里对她有什么非礼的动作。咳,你既然请我看电影,却又不信任我,特意找来了保镖,何苦呢?你固然是个可爱的女孩,但我自知对你是不该有非分之想的。
就坐以后,中年妇女和我攀谈起来。
“你口音很重,不是本地人吧?”她说的口音很重指的是非东北人的口音。我说的是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当然不含有东北味儿。
“我是陕西人。”
“多大岁数了?”
“四十八。”我如实回答。
“结婚了吗?”毫无疑问,她属于说话单刀直入、痛快直爽的那类东北老娘们儿。对她的这句问话我感到有些意外,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能不结婚吗?也许她的意思是我离婚了,老婆不在了,现在是单身。
“结了。”
“有孩子吗?”
“有。”
她停止了询问。直到电影演完她再也没有说话。
看来她不是郭菊请来的“保镖”,而是来替郭菊“问案”的。
电影演的是什么,现在我已经毫无印象,只是模糊地记得好像叫《雪地英雄》。
我怀疑是裘教授的那封信仓促中没写清楚,被郭菊误认为我是老师给她介绍的对象;也许是她的同事替她操心过分,当机立断地安排了这场当面考察。不然为什么要问我年龄大小和有无家室呢?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都一一如实地回答。这样,如果真有此种误会,就可以豁然冰释了。一个短短的生活小插曲也就必定会到此戛然终止。
第二天清早,我刚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发,电话铃又响了,没想到打电话的人仍然是郭菊。
她说:“我在上班,就在电话里给你送行吧。祝你一路平安!”她的声音平静而甜美。
看来,她是个重视友谊的女孩。
我也珍惜这种友谊,在北大荒给她写了一封致谢的信。
采访结束以后,我回到了佳木斯。想来想去还是不打扰她为好,所以直到要离开宾馆的最后时刻,我才打电话告诉她,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一会儿要去火车站,就此告别了。
我来到火车站前,远远就望见广场上矗立的纪念碑,碑下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手里提着很大的粉红色的袋子,鼓鼓的。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她腼腆地微笑着,把手提袋交给我,只说了一句:“路上吃。”
我不能拒绝,如果拒绝将会是对她极大的伤害。我接过手提袋,它相当的沉重。我的心也同样沉重,是沉重的感激、沉重的感动。
她看到还有农垦局的几个人在为我送行,便没有加入送我上车的队伍,轻轻地转身、悄悄地走了。
车开以后,我检看郭菊送我的食品,甜的、咸的、软的、硬的、绵的、脆的,应有尽有,五味俱全!
……
算来,她可能已经当了奶奶了,头发也该是花白的了,但是这类猜测和想象是模糊不清的。在我清晰的记忆中,不,在我的眼前,她永远是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手提着一大袋食品,站在纪念碑前,腼腆地朝我微笑着。
她也成了一座纪念碑。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