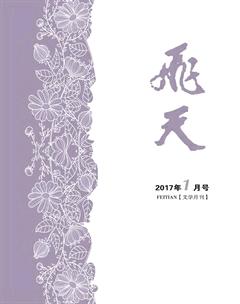世上到处都是山
曹永
昌龙背着包裹,顺着山路往回走。
跑出去六年,昌龙到底还是回来了。昌龙不仅回来了,他还带回不少钱,就藏在包裹里面。山路像条笨拙的蟒蛇,慢慢朝岩羊湾方向爬去。虽然现在看不到那个叫岩羊湾的村寨,但昌龙知道,再走两个小时,它就会冒出来。
想起岩羊湾,昌龙无端有点难受。那里到处是陡峭的山崖,目光刚刚伸出去,马上就被弹回来,似乎要把人弹个跟头。以前在村里,昌龙经常坐在门槛上撑着下巴胡想。昌龙觉得,生活在那种没滋没味的地方,简直跟牲口差不多。
世世代代,岩羊湾的人始终被关押在深山里面,一辈子不能离开。多少年来,只有昌龙成功逃出去。但现在,他又跑回来了。昌龙背着包裹,顶着剧烈的阳光,顺着山路往回走。
翻过垭口就看到那所麻疯病院了。很多年前,这里流传麻疯病。那时候麻疯病很难治,大家害怕传染,就把病人赶出去。后来建起麻疯院,那些流落荒野的病人才得到治疗。有一次,昌龙跑到麻疯院,没想到里面居然还有几个老人。那些老人手足残缺,脸上坑坑洼洼,把昌龙吓了一跳。
看到麻疯院,昌龙就心里发毛。他赶紧收回目光,埋头往前走。路边长着几棵树。那些树全都半死不活。在这种鬼地方,树也活得很艰难,它们无法尽情生长。树枝上挂着叶片,但不多,稀稀疏疏。树皮很厚,黑不溜秋,绽着无数裂纹,像饥饿的嘴巴那样张着。
昌龙停住脚步,他在看那些树。昌龙心里怪怪的,说不出到底是啥滋味。第一次把来凤带到岩羊湾,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姑妈嫁到黑土河,昌龙去那边走亲戚。姑妈就给他做媒,把来凤介绍给他。
来凤家遭了火灾,家里只剩她一个。昌龙第二次去黑土河就把来凤领回来了,当时他们就走这条路。从岩羊湾出来,也只有这条路。昌龙走在前面,来凤跟在后面。有时候,昌龙会拧头朝后边看。来凤害羞,总是惊惊慌慌,脸红得跟什么似的。
昌龙记得,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回头问,累不累,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来凤没吭声,但看到昌龙朝树边走,她也跟过来了。昌龙搬块石头,让来凤在上面坐。来凤不坐,她低着头,几根手指绞在一起。
来凤的身上有股什么味道,香喷喷的。昌龙想问,但没好意思。他闻着那股香味,嘴里渴得要命。后来,他舔着嘴唇说,要不然,我们还是走吧?来凤就跟在他的后边,像只温顺的猫。
岩羊湾被山崖夹在深沟里面,偏远闭塞,外边很少有姑娘愿意嫁进来。看到昌龙带回个漂亮媳妇,大家惊讶得好半天没合拢嘴。那时,昌龙对生活很满意,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跑出去。
太阳很厉害,把风烤热了。风吹的时候,仿佛火苗在他的身上舔了一下。昌龙确实有这种感觉。昌龙抬起胳膊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继续顶着恶毒的太阳往前走。他身上汗淋淋的,连衣裳都浸透了。
经过苏戈寨时,昌龙看到路边蹲着个放牲口的老者。那个老者戴着顶树叶编的帽子,手里拿着根枝条。两头牛甩着尾巴,悠闲地吃草。几只山羊亮着红屁股,在树丛里钻来钻去。它们拱得树丛乱颤。
老半天没看到人,昌龙想跟放牲口的老者打招呼,但他只是这样想。昌龙晓得,苏戈寨的村民历来看不起他们。苏戈寨简直把他们当成麻疯病人,路上碰到,也似乎从来没给过好脸色。昌龙不是个小气的人,但他实在忍受不住那种轻蔑的眼神。
昌龙的头皮被太阳晒得隐隐作痛,头发差不多燃烧起来了。昌龙东奔西走,在外面奔波六年,但现在,他又跑回来了。昌龙背着包裹,里面藏着他的血汗钱。他顶着亮晃晃的太阳,顺着山路往回走。
野草伏在地上,看起来像是枯死了,其实没有。它们把根须扎进泥土,頑强生长。周围仍然是山,有的山连树都不长,上面尽是乱七八糟的石头。有的山上虽然零零散散地长着几棵树,但很不成材,比庄稼高不了多少。前面有堵岩石,像被烟火醺过,黑糊糊的。
昌龙家屋后的崖壁,就这样黑糊糊的。他家在贵州和云南的交界处。两省的界线,是中间的洛泽河。两边的山崖,像群抵架的牛,拼命冲撞。那条河水呢,俨然是从伤口里面挤出来的血,缓缓从山缝淌出来。
岩羊湾就在河滩上,地势狭窄。来凤是个有主张的人,她看到门口没有场坝,就在侧面打主意。她把旁边的树砍掉,让昌龙搬石头,在那里修石坎,然后自己背土来填。半个月的时间,硬生生让她弄出一块场坝来。
来凤很勤快,差不多每天早上她都会提着扫把,弯腰打扫场坝。庄稼收成时,她就在上面晒红豆和菜籽之类的东西。甚至,她还从山上刨来几株兰草,用破桶栽在场坝边,每天给它们淋水。兰草开花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昌龙不知道,那块场坝到底变成啥模样了。昌龙已经跑出去六年。现在,他就像条快要烤熟的鱼,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往回走。山路弯来扭去,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路边尽是乱石堆子,几棵树从石缝里钻出来。
昌龙他们在崖顶上种洋芋,在河边种苞谷红豆。河边水分足,土地也肥,其它地方的苞谷只有肩膀高时,岩羊湾的苞谷已经成熟了。河边不仅能种苞谷,还适合种蔬菜。每年春天,河边的庄稼地总是绿油油的。
岩羊湾收成好,但没钱用,村民穷得吃盐都成问题。他们想把粮食背到外边卖,但几座山崖挡在眼前。那根细长的路,像绳索似的绑在半山上。山崖左奔右突,差不多把路绷断了。这里的许多老人,他们生在山沟沟,也将死在山沟沟,生活一辈子,硬是没能迈出半步。
这条路实在不好走,有好几个地方,他们只能扒着岩石,侧着身体挤过去。要想背粮食去外边卖,豆腐都能盘成肉价钱。没有法子,大家只能拿粮食喂猪。猪崽不仅吃粮食,还吃他们的血汗。他们从早到晚拿着勺子喂猪,硬是把勺子摸得溜光水滑。
看着猪慢慢肥了,他们想赶到外边去卖。但没想到,猪的那身肥肉也成了累赘。赶到街上时,人和猪都汗水淋漓。人没啥要紧,但猪趴在地上,横竖不肯起来。人家过来看看,再也不肯开价,都说像是瘟猪。卖不掉猪,他们只能赶回去。几年前曾发生过一桩要命的事情,赶到半路,竟然把猪活活累死了。
昌龙挣不到钱,曾打过山草药的主意。他像只猿猴,在悬崖上到处乱蹿,到处挖天麻、和尚头、大鸡子、剌午甲,还有何首乌之类的东西。药材挖了半麻袋,但没能卖脱,全都扔在屋檐下边。药味不怎么好闻,昌龙索性把它搂成一团,甩手扔出去了。
要是没碰上灾害,岩羊湾总能有个好收成,但其它地方的人就是瞧不起。这让大家无比难受。尤其是昌龙他们,年轻气盛,浑身憋着火,总想张嘴骂人,更想提起拳头打架。刚开始,他们不清楚自己怎么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后来就渐渐明白了,他们知道都怨这个鬼地方。他们试过修路,但终究没干成。
岩羊湾的村民像一群关在圈里的山羊,撞破脑壳也无法冲出去。这些年来,逃出去的只有昌龙,但现在他又跑回来了。汗水把昌龙的头发浸湿,紧紧贴在额头上,让他多少有点不舒服。地势很陡,仿佛这条路一直伸向地狱。
路边有块石头,只有屁股那么高,生得很平整。昌龙记得,以前跟来凤背东西到街上卖,走到这个地方,他们总会歇脚。每次,昌龙刚刚把背箩放稳,来凤就拿着手帕过来给他擦汗。来凤说,你看你,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来凤走过来的时候,身上有股什么味道,就是第一次闻到的那种,怪模怪样的。昌龙迷恋那种味道,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现在看到那块石头,他又想起来了。他觉得那股味道好像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虫子似的在鼻孔里拱来拱去。
昌龙看看那块石头,抬脚把一块泥疙瘩踢进路边的草丛,继续朝前走。不時地,昌龙会吐两口唾沫。这地方风沙大,尘土不停地往脸上扑。他感到嘴里有沙子,牙齿总会磨出噌噌的响声。风一直没停止,也许它会一下这样吹下去。
远处飘来一团黑云,挡住阳光,昌龙感到有些凉爽。昌龙抬起头,正猜测是不是要落雨,那团黑云就慢吞吞地飘走了。岩羊湾最怕的不是旱灾,而是洪灾。上方落雨,山水涌到河里,洪水就会涨起来,淹没河边的庄稼地。
昌龙的爹娘都是洪水卷走的。那次,雨水下得铺天盖地,河水浊黄,大得吓人。昌龙的爹用竹竿绑着铁钩,站在岸上捞柴。岩羊湾最缺的不仅是钱,还缺煤炭。他们买到煤炭后,搬运成了大问题。
岩羊湾不通公路,他们只能自己背。无论哪家买煤炭,都要叫上全村的劳动力。几十个村民背着煤炭,爬山下崖,走成一串。男人出去背煤,女人就在家里帮忙做饭。每次搬煤炭,都要出动整个岩羊湾的人,简直像办酒席一样热闹。
看见涨水,昌龙他爹赶忙往河边跑,准备多捞点柴。昌龙他娘提着麻绳,跟在后面背柴。他娘刚走到河边,突然听到上面传来哗啦的响声。她抬起头,发现一条水缸粗的东西黑糊糊地横在河面上。
河流就像遇到堤坝,下半截水势减缓,上半截却波涛汹涌。他娘吓得差点尿裤子,慌忙叫喊。但风很紧,洪水也大,他爹根本听不到。他娘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准备把男人拽回来。没想到,刚跑过去,那条拦在河面的东西就翻滚几下,骤然沉到水底。洪水随即奔涌而来,把昌龙的爹娘卷走了。
昌龙顺着河边寻找了两天,硬是没能找到爹娘的尸体。昌龙想起就难受,以前的时候,爹娘老担心他找不到媳妇。后来娶到来凤,他们又催昌龙赶紧生娃娃。他们说,到这年纪,啥都不想了,只想抱孙子。
昌龙被逼得受不了,就天天抱着来凤折腾。来凤是个好女人,无论昌龙怎么鼓捣,都不气恼。她轻轻往昌龙的怀里钻,温顺得像只母羊。昌龙搂着来凤,恨不能把她勒进自己的身体。他们折腾了几个月,来凤的肚皮终于慢慢鼓起来了。昌龙的爹娘想抱孙子,但还没来得及,洪水就把他们卷走了。
所有的事情,昌龙都记得清清楚楚。刚出事那段时间,他难受得命。他像疯掉似的,抱起石头朝河里乱砸。河面溅起水花,河水被他砸得咕嘟响。后来,昌龙在半坡上修了两个衣冠冢。
昌龙整整六年没回家了。他已经想过,这次回去就再也不出来了,以后,每年清明节都要给爹娘上坟烧香。这会儿,昌龙正背着行李,顺着山路往前走。阳光粗暴地烤着大地,昌龙感到脚板隐隐发烫,仿佛踩在烧过的石板上。
前面是那堵悬崖。崖壁上端长着几棵树,它们用根须拼命抓着岩石缝隙。任何风雨,都让它们颤颤巍巍。昌龙感到心里毛躁躁的,有点不舒服,他晓得这是什么缘故。来凤就是死在这里的。
那天晚上,来凤肚子疼,让他赶紧喊接生婆。昌龙明白怎么回事,慌慌张张往外边跑。接生婆像在鸡屁股里面摸蛋一样,把手伸进来凤的肚子。她摸到的结果是,来凤难产,需要送到卫生院抢救。
昌龙找来几个邻居,用门板抬着来凤朝石门走。开始,大家走得很急。爬上山坡,他们的速度就慢下来了。昌龙看到大家慢吞吞的,简直急坏了,央求说,你们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喘气说,路太烂了,实在挪不动。昌龙急得嘴上冒泡,跺脚说,唉呀!
来凤躺在门板上,嘶声叫喊。昌龙说,来凤,你莫喊,你喊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来凤用手抠着门板说,我有点忍不住。昌龙说,听到你喊,我就想从崖上跳下去!来凤说,我的肚子疼得要命,恐怕撑不下去了。昌龙焦急地说,你在说胡话哩,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来凤很听话,昌龙让她别喊,她就紧紧闭着嘴巴。来凤全身汗淋淋的,好像还有血,因为有什么粘稠的东西顺着门板滴到昌龙的身上。来凤没再叫喊,但她的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昌龙听得难受,恨不得找把镰刀把自己的耳朵割掉。
月亮苍白地挂在天上,比死人的脸还难看。门板像嘴巴似的咬住肩膀,他们走得很艰难。来凤躺在门板上,仿佛睡着了。远处的树林有雀子叫,呜呜的很难听。雀子叫的声音像娃娃哭,这让他们觉得很不吉利。
昌龙他们汗流浃背地走着。他们要去一个叫石门的乡镇,那里有医院。路很难走,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大家几乎不去那个地方。山岩像两堵墙壁,猛地夹过来,让人感到快要活不成了。走在这种地方,总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其实,另一座山还很远。
暗淡的火把在风里不停地摇晃,似乎马上就要熄掉。尽管昌龙急得火烧火燎,但地势陡峭,根本走不动。前面的路紧紧地贴着悬崖,非常危险。他们没胆量抬着门板从上面走过。从这个地方摔下去,顶多能找回几根骨头。
昌龙急得像屁股着火,干脆把媳妇搂到背上,吭哧吭哧地往前走。走过悬崖,他挥着手,催促大家快把门板扛过去。后面的人跟过去,刚把门板放在地上,来凤就抽搐起来了。他们吓了一跳。前面好大工夫,她都那么躺着,没想到现在全身乱抖,看起来说不出的痛苦。
大家慌了,围在旁边不晓得怎么办。来凤伸出手,似乎要抓住什么东西。她的声音渐趋微弱,最后两只脚蹬了几下,慢慢停止抽动。昌龙抓着那只僵在半空的手,哆嗦说,来凤,你莫吓我,我胆子小啊!听到没有?你快点起来呀!来凤躺在门板上纹丝不动,没有半点起来的意思。
昌龙双手抱着脑壳,喉咙里像堵塞着什么东西,呜呜地响。大家劝他不要伤心了,先把尸体抬回去。昌龙哭丧着脸说,一定要送到石門,也许还有救!他们摇头说,没有用了,已经咽气了。昌龙就蹲在地上哭,声音不高,但听起来很悲惨。
路边的杂树和野草正在努力生长,凉飕飕的空气里飘荡着复杂的味道。突然,昌龙抬起手,不停地抽自己的耳光。他们急忙拽住说,你不要这样,就算打死自己,她也不会活过来了。昌龙痛苦地说,都怨我,是我把她害死了!他们安慰说,要怨就怨这条路,要是及时送到医院,你媳妇就不会死了。
昌龙咬牙切齿地看着那条路,恨不得扑下去啃几口。
来凤死掉以后,连续好多天,昌龙都蹲在那块场坝上,两只眼睛红彤彤的。他用手抠地上的泥块,差不多把指甲抠掉了。昌龙总想起来凤的模样。来凤很温顺,就像一只猫,老往他的怀里拱。
昌龙仰着脖子,蹲在那里胡看。岩羊湾挤在一条峡谷里,地势不怎么宽敞。站在崖顶上,看到山沟是长长的几道。但从崖脚往上看,简直就恐怖了。总觉得被两边的山崖挤压着,几乎透不过气来了。
昌龙知道,归根结底都怨这条路,要是道路通畅,事情就不会弄成这样了。这些陡峭的山崖,让岩羊湾与世隔绝。这里的村民,像得麻疯病似的,以前被世界所抛弃,以后还将永远遭到抛弃。看着周围的山崖,昌龙憋屈得跟什么似的。
昌龙把手插进头发,用力撕扯,恨不得连脑袋一起揪下来。此前,昌龙过得浑浑噩噩,当他揪下几缕头发后,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昌龙准备修路,他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修通这条路。拿定主意,昌龙就跑出了岩羊湾。他在外边奔波六年。现在,到底还是回来了。
翻过前面的山梁,就能看到岩羊湾了。昌龙有些激动,他紧走几步,顺着山坡往上爬。多少年来,祖祖辈辈始终困在前面的深山旮旯,如同闷在水缸里,最后全被活活憋死。昌龙早就寒透心了,他打算硬从岩石上破出一条路来。
昌龙准备先修路基,再慢慢把路面拓宽。他已经豁出去了,决定把以后的光阴全都用来修路。活在这种地方,实在太煎熬了。昌龙希望这条路早点接通外面的世界,让大家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昌龙绷着两条粗黑的眉毛,使劲往上爬。登上山梁后,昌龙满脸惊愕,像被什么东西砸中脑袋,他身体摇晃了几下,慢慢瘫在地上了。昌龙用手捂着脸,全身颤抖。他看到远处的山崖上,赫然挂着一条公路……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