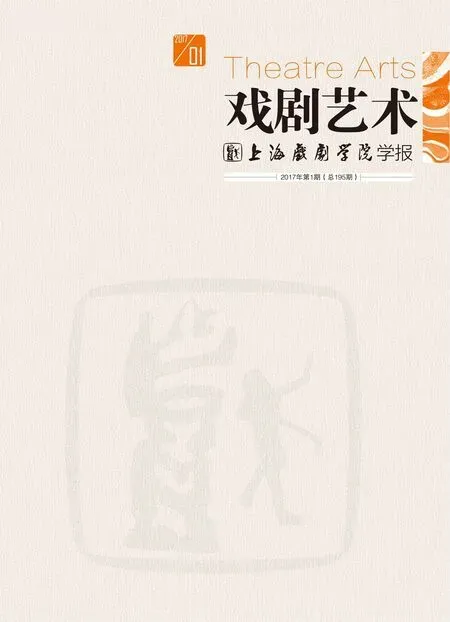从娱乐到礼乐:顺治朝演剧政策研究
■刘 薇
从娱乐到礼乐:顺治朝演剧政策研究
■刘 薇
顺治朝乃明清易代特殊时期,此一时代的演剧政策将直接影响康乾及以后诸朝演剧的发展,对其展开研究有益于对清代演剧史变迁的整体把握。从清军入关以后诸多史实材料出发,可发现顺治朝演剧政策存在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以顺治八年(1651)亲政为界。多尔衮当政时期,并无完整有序的演剧政策,顺治亲政后才逐渐加强对演剧的管理。这一转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演剧本身具备的时代特点是转变的直接原因,而满汉礼乐风俗地位的转变则是此时演剧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
顺治朝 演剧政策 娱乐 礼乐
演剧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具体是指朝廷针对演剧活动而实施的管理策略,而官方的演剧政策终将影响演剧发展的趋势,所以十分有必要进行细致的研究。顺治朝承明清鼎革,开康乾盛世,诸多制度存留激烈的时代变革痕迹,而演剧政策作为文化制度的一部分,不可能毫无变化。但现今研究普遍认为顺治朝并未明显对演剧实施管理措施,清历朝演剧规模与政策也非接续、效仿顺治朝。正是这一结论导致目前对顺治朝演剧历史探究的搁浅,最终将阻碍我们对演剧史上“清初演剧进入徘徊期”①这一现象的深层理解。本文即从清军入关以后诸多史实材料出发,以期考明顺治一朝演剧政策的变化。而演剧政策的变化又有十分复杂的因素,与当时的演剧环境有关,同时也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而两者又受政治时局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描述顺治朝演剧政策变化的基础上,还将从社会环境以及礼乐文化中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
一、顺治朝演剧政策的变化
顺治朝并未设立过专门管理演剧的机构,内廷戏曲档案对这一时段演剧情况的记载亦属空白,朝廷下达的有关演剧的政令也是寥寥,所以顺治朝往往被认为无暇顾及仪典安排与礼乐之事,其对演剧活动亦无定制。但经仔细考证便可发现,入关之初的两位统治者——多尔衮与顺治帝都已关注演剧,且两者在位期间的演剧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多尔衮时期的演剧政策
清廷入关之初由多尔衮当政,此时演剧政策混沌不明,这尤其体现在宫廷乐署的设置上。清代制度仿拓前朝,对音乐的管理亦大体如此,但在清初多尔衮时乐署设立存有不妥之处。明代宫廷音乐实际上由太常寺、礼部教坊司、内廷钟鼓司三分而掌。在明前中期,朝廷音乐机构主要是太常寺与教坊司,但此时太常的职权已逐渐让归于礼部,且其基本性质也由独立机构变为依附礼部而存在的机构。相较太常寺职能转移礼部,此时礼部教坊司则掌天下乐籍,据《明会典》载:“凡遇年终……教坊司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类送礼部收查。”[1](P.179)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则曰:“祠部,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籍其人。”[2](P.686)可知礼部总管各类工人户籍,而乐籍的调配、教习与审核,实际由教坊司管理。这种种的变化标志着“教坊司已经取代太常的礼乐功能,成为朝廷上宣下化的礼乐机构之一”[3](P.88)。到了明代中后期,南戏俗乐兴起,便又有钟鼓司执掌宫中戏剧承应,钟鼓司的设立虽然助长了宫中俗乐大盛,但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雅俗乐署分立的基本原则。但清初多尔衮时只设立“太常”“教坊司”两个乐署,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国初亦设教坊司。而朝会宴享所奏所用俗曲词者,盖沿明代之旧也。我朝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太常乐员例用道士,教坊则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凡坛庙祭祀各乐,太常寺掌之;朝会宴享各乐,教坊司承应。[4](P.6375)
可知清代早期只设立太常与教坊,太常专掌坛庙祭祀乐,这是承袭以往的制度。而此时教坊司功能更为复杂:相对于太常为祭祀雅乐专设,教坊司则有朝会宴享俗部乐的特色。但教坊司所管辖范围又不仅是俗乐,同时也涉及宫悬礼仪大乐,《清会典事例》记载:
(顺治元年)又定,凡宫悬大乐,皆教坊司奏之,设正九品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名,色长十有七名,歌工九十八名。[5](P.263)
大约清初雅俗之乐皆归教坊掌管,由教坊司代管演剧是不争的事实,清初的演剧没有固定专门的机构管理。而教坊的设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有学者曾指出清代依据明制设教坊的不妥之处,认为教坊司管理人员的职官品秩一依明朝之旧,最高管理者奉銮仍为正九品,“如此畸低的职衔却全面掌管清初整个宫廷的音乐活动,未免名不符实”[6](P.178)。以职衔低的教坊管理整个宫廷音乐确实不妥,更重要的是,教坊司作为乐官总管包括演剧在内的宫廷雅俗之乐,这意味着清初延续了明末雅俗失范的制度,清初演剧制度的不完备由此可窥得一二。
多尔衮时代一方面沿明制设教坊司掌管雅俗之乐,将演剧等俗乐混在宫悬大乐之中一并管理,可知其无心纠正明末以来雅俗乐之失范;而另一方面,多尔衮时期也继承了入关之前满人对汉人演剧的态度,将其视作娱乐之事。顺治七年(1650)三月,多尔衮对礼部颁谕,认为以往攻无不克,都是擅长骑射之功,今虽天下一统“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司法治罪”[7](P.385)。可知多尔衮时期满族统治者还是将汉人的演剧视作误人子弟之事,对其抱有很大戒心,更谈不上将其纳入礼乐制度之中,对民众施以教化。
总之,多尔衮当政时期演剧制度并不完备。其一,制度虽大体仿明代,但只置教坊司作为音乐总管机构,不设钟鼓司之类的专门演剧机构。再者,政府对演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误人子弟”的丝竹娱乐之事上,无意对演剧活动进行管控,更谈不上以演剧来上宣下化。
(二)顺治亲政以来演剧政策的变化
顺治八年(1651)时,顺治帝亲政,欲加强对演剧的管理,最主要体现在对宫廷演剧活动的管控上。清承明制而立,清入关之初的演剧制度与明却并不相同,明代设立教坊司与钟鼓司,分掌外廷雅乐与禁中俗乐,多尔衮时期只设教坊司,从而使得雅俗乐杂列,外廷与禁中用乐混淆。顺治亲政以来,有意在演剧方面做出改变。首先乃效仿明代重置钟鼓司,顺治十一年(1654),裁内务府,置十三衙门,其中就有钟鼓司。虽然钟鼓司职能逐渐变成了分掌礼仪乐舞,而不再参与宫中戏曲演出事务,但钟鼓司本身的设立,就代表顺治有意像明代那样,使雅俗乐分立,演剧能有专门的机构。除此之外钟鼓司的设立更是表示顺治帝希望将蔚然兴起的南戏诸腔等俗乐纳入到官方礼乐系统,这一过程最终虽由升平署完成,但此时顺治帝设立钟鼓司不能不说是对多尔衮时期乐署职能混乱的一种反拨。其次,顺治帝还将俗乐的承应由教坊司女乐改为内监。清初承明之旧设教坊司,由教坊司掌管宫中音乐、舞蹈等事宜,使用女乐承应,《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凡宫内行礼宴会,用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坊女乐二十四名,于宫内序立奏乐。”[5](P.263)另瘦禅在《南府沿革记》上亦说:“有清初年,典章均沿明制,曾于东四牌楼本司胡同地方,敕设教坊司,专供宫中喜庆寿安,朝廷大典,奏演戏,辄由本司恭领乐宫女乐等人敬谨供奉。”[8](P.144)顺治初年用女乐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内宫太监“数止千余”,明末宫廷的数百名习艺太监已在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城时流散,凡宫内行礼宴会用乐、演剧只好由教坊司带领女优承应。顺治亲政后屡次将筵宴奏乐的乐人由女乐改为太监,《大清会典事例》谓:“(顺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司女乐入宫承应,更用内监四十八名,”[5](P.263)邓之诚在 《骨董琐记》中亦有相似记载:
顺治初,沿明制设教坊司。凡东朝行礼筵宴,用领乐官妻四名。领女乐二十四名,女乐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随钟鼓司引进,在宫内排列作乐。八年,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官承应,用太监四十八名。十二年(1655),仍用女乐。 至十六年复改用太监,遂为定制。[9](P.185)
这说明顺治帝有意恢复类似明代钟鼓司——由宦官统领之乐署,但这同时也透露出顺治复立钟鼓司目的不纯:顺治欲将女乐手中的音乐演奏权转移至太监手中,而太监在朝廷权力系统中,乃是附庸君主,是作为皇帝的家臣存在,这也就是将原属于外朝教坊司的部分音乐掌握权收归皇帝之手。
顺治亲政以来这种逐渐加强君主对演剧活动控制的政策,很快就扩大到加强对全国演剧活动的管控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顺治亲政期间颁布的有关演剧的禁约。顺治九年(1652)提出,“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10](P.584),此为清廷第一次颁布禁琐语淫词令,这已经涉及对演剧文本的控制。十三年(1656)以后,集权归还顺治手中,其对演剧制度的控制更加直接。十四年(1657)“理学名臣”汤斌在陕西潼关按察副使任上颁布关中禁约,规定擅编歌谣剧戏、依律定罪,禁恶风以安良善事[11](P.339),这是目前可知的清代官方第一条禁赛戏令。此类禁约,可看作是顺治朝收紧演剧环境的一个信号。其次,由“丁酉科场案”牵连出一系列查毁演剧、监督文士演剧活动的事件,亦从侧面反映出顺治帝欲加强控制民间演剧活动。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舞弊,被严惩查处,包括顺天、江南、河南、山西、山东五闱。从主司、房考,到考中的士子,清初名士如丁澎、陆庆曾、吴兆骞等,皆入案中,或斩决诛戮,或谪戍边疆,无以数计,影响深远,伴随丁酉科场案的调查,《万金记》《钧天乐》等传奇作品也遭受审查禁毁。董含《三冈识略》曾载《万金记》遭查一事,“前此,江陵书肆刻传奇,名《万金记》,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狱”[12](P.339)。此案令顺治帝震怒的焦点并非造谣失实之事,而是《万金记》中有影射朝廷的内容,因为此案主考官早在《万金记》发现前已被治罪。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以演剧评说朝廷政事的行为已不为顺治帝容忍,在顺治帝看来,演剧活动已然不只是娱乐而已,是关系到国家统治的文化活动。尤侗亦因《万金记》牵连其中,通过其自记中的记述可知地方官曾奉命侦查《万金记》作剧人姓名[13](P.260),并“大索诸伶治之”,对像尤侗一样家有梨园之士绅的予以监视。而尤侗里中上演《钧天乐》传奇,因其中有刺科场语,地方官亦疑为《万金记》,遂要抓捕尤侗,可见因查《万金记》一案,确实查杀了许多优伶,而且自明代后期以来大盛的家班,也遭到监视与打击。值得关注的还有一点,在江南因“《万金记》案”环境恶劣之时,尤侗却逃往政治中心北京,得以避祸。这难免让人猜想此案中的禁戏、查戏事件,是针对晚明清初以来,越发脱离礼教秩序的江南社会。明清两朝易代、鼎革,势必会对士大夫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其结果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在清初,保守的文人学士力图把僵硬的道德准则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周启荣所言,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江南来自绅士和商人家庭的妇女不仅是文学、文化的消费者,而且是创造者。但自清初以后,妇女已被告诫不要阅读白话小说,不要看戏,不要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公众场合男女混杂。1而之前汤斌禁戏亦是站在“礼仪人生之大闲”的立场上针对“俗流弊已极”的情况进行整改。
二、顺治朝演剧政策变化的原因探究
经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顺治朝演剧政策确有变化,在多尔衮时期,演剧仅被视为娱乐活动,政府管理非常混乱。顺治亲政以后,便逐渐加强对演剧的管理。这一变化与清朝初年政治与文化息息相关,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倾向。下面将从顺治朝演剧本身的时代特点,以及礼乐制度的转变两个角度揭示演剧政策变化的原因。
(一)顺治朝演剧与悼明、反清等活动关系密切
顺治朝演剧政策逐渐收紧的迹象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革下,演剧本身体现出的特点有关。此时许多演剧的创作都暗寓着思念故明与幽怨满清的情感,有些演剧还直接鼓动了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这极有可能是迫使顺治朝收紧对演剧管理的直接原因。
顺治朝演剧的作者,大多是由明入清的遗民,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是这时演剧主题表达的首选。顺治六年(1649),丁耀亢《赤松游》传奇完成,写张良辅汉除暴秦的故事,以汉影射清,抒写易代之际亡国之士的悲凉情怀。根据其《作赤松游本末时》记载:“昔吾友王子房慕韩留侯之为人,……余悲子房之亡,欲作赤松以申其志。”[14](P.90)可知丁耀亢与王子房曾山中结社,为至交,明崇祯十六年(1643)王子房抗清战死,故其作杂剧纪念友人,怀念故国。朱英传奇《倒鸳鸯》作于顺治七年前不久,是借男女之情,写清兵南下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抒发作者对于亡国的悲愤感情。顺治十年(1653)七月,《秣陵春》传奇有成稿,传达对整个人生的空幻之感。创作于顺治朝时的类似表达故国之思的传奇作品还有很多,如《万里圆》《一品爵》之类。另外顺治朝时,许多杂剧的创作也以明清易代的情感为主,这从邹式金所编杂剧单剧选本《杂剧新编》可窥探一二。《杂剧新编》初刻于康熙元年(1662),自为小引亦署“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故其成书当在顺治十八年(1661),其所收的清杂剧亦多是写于顺治朝。该书又名《杂剧三集》,所谓“三集”,系承继明沈泰所编《盛名杂剧》初集、二集,以示不忘故朝之意。该选本主要择选明末清初的杂剧作品,又以清初顺治朝的杂剧为主,收录十九名作者的三十三部作品②,这些杂剧可分四种“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学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几乎从不同角度都反映了明清易代的惆怅、忧思、愤懑。可见顺治朝时,无论是传奇的创作还是杂剧的创作,都或深或浅地寄寓了对故明的怨思与对清军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许多演剧活动与反清起义有直接关系。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在南昌反正抗清,《江变纪略》对此有所记载:
(王得仁)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蓄伶优,教歌儿数十人。私居时时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后唐张饮,数令优人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至王得仁反清投明时,要换明代衣冠,仓促中只好拿优伶的戏服穿上,时服色变易已久,仓猝求冠带不能具,尽取之优伶箱中。[15](P.119)
另外清廷广东提督李成栋下定决心反清投明(1648年)与其部队中演戏有关。徐鼐《小腆纪年附考》载:
爱妾张氏,陈子壮之妾也,成栋艳而纳之,年余不欢。偶演剧,张氏见之而笑,成栋诘之,氏曰:“为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成栋遂邃起而著明冠服,氏取镜照之,成栋欢跃。氏察知之,因怂恿焉成栋抚几曰:“怜此云间眷属也。”时成栋眷属犹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独享富贵乎?请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栋大哭曰:“女足乎是矣。”拜而殓之。[16](P.583)
李成栋反清复明,正式起事是借助端午演出优伶所穿的大明衣冠而发难。《丹午杂记》还记有定国因观伶人演武侯出师事,感而归明,后屡攻缅甸欲救桂王即得此志[17](P.28)。可见顺治元年推行剃发令以来,满人强迫汉人改换发式、衣冠,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但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而在此时,优伶们可借演戏之便,以汉人的衣冠装饰,这就很容易勾起看戏的汉人对故国的怀念,对清人的不满,抗清起义的此起彼伏,原因非常复杂,但演剧在此时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抗清活动,聚合起义队伍的作用不应忽视。
(二)满汉礼乐文化地位发生改变
顺治朝收紧对演剧的控制,还有礼乐制度深层次上的原因。多尔衮时便无意改变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谕令故明官员:“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7](P.57-58)。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而对于礼乐制定亦从未停滞,顺治元年(1644),便确定了圜丘大祀、方泽大祀、祈榖大祀、太庙大祀、社稷大祀的具体礼仪制度。在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三年(1647)间,大祀、中祀等基本格局形成,亦定下了清朝乐制的基本格局,对祭祀乐、卤簿乐、部分朝仪乐、宴乐等都有所规定,可以说这一时期对汉族儒家礼乐制度效仿颇为努力。但在承袭汉族礼乐文化的同时,满洲原生祭祀文化作为满洲文化的象征,并未被舍弃。入关不久,满洲统治者即着手建立全面的祭神祭天礼制。 顺治元年(1644)九月己亥,建堂子于玉河桥东[7](P.86)。 顺治二年(1645)制元旦堂子祭礼,规定每年元旦“如皇上亲诣行礼,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及外藩来朝亲王以下、贝勒以上,俱赴太和门齐集”[18](P.3358-3359)。元旦祭祀堂子、春秋立杆致祭的满洲风俗得到保存。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一日,和硕肃亲王遣赴四川剿张献忠,摄政王多尔衮率众王、贝勒、贝子、大臣等先拜堂子之后,送出正阳门[19](P.259)。顺治六年(1649)十月十六日“皇父摄政王率大军征讨蒙古,上亲送之,往谒堂子”[20](P.54),出征等祭堂子礼仪得到保存。可见在问鼎中原后,面对汉族礼乐的全面渗透,满洲风俗并未禁绝。同时满汉礼俗还发生了争执,顺治二年(1645)三月庚申,礼部奏言“四月初八日,系佛诞之期,旧例于是日浴佛,而故明并无此例,得旨仍照旧例浴佛,多罗郡王以上俱往祭,是日著停刑,禁止赛神屠宰,各旗满洲蒙古汉军俱照例传谕”[7](P.134)。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丙午,“礼部请各坛及太庙读祝停读汉文,止读满文,仍增设满读祝官八员,一切典礼俱照国朝旧制行”[7](P.165)。这两次满汉祭祀礼仪之争,都是满族风俗获取胜利,说明此时满洲礼俗并未因承袭明制而消失,且在满汉礼仪之争中占得上风。
但自亲政以来,顺治立志恢复故明礼乐制度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既是维稳帝位的实际需求,又体现出其成为多民族国家君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开始逐次完善衙司建制,十一年(1654)复设内十三衙门,乙卯谕礼部:“内府事物殷繁,须各司分理乃止,设十三衙门。”[7](P.681)十二年(1655)十月,恢复尚宝司衙门。十五年(1658)七月,顺治帝又下令改内三院为内阁并另设翰林院。与此同时在礼乐方面,对汉族礼乐与满洲原生礼俗的地位进行调整与定位。十三年(1656)三月,顺治帝定大军出征班师礼,但俱无拜堂子或拜天典礼的踪迹。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礼部官员请在元旦拜堂子,顺治帝则曰:“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蹭堂子,以后著永远停止!”[7](P.819)在顺治十三年(1656)前,虽然堂庙礼仪已开始分散堂子祭天独一而尊崇的地位,但堂子祭祀在最初还是被制度化保留,充当国家祭祀文化的重要角色。十三年(1656)之前,顺治亲自参加七次满洲祭祀,但从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发生重要变化。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礼部以征云南上奏出兵仪式,顺治帝更是明确宣布,“既因祭太庙斋戒不必筵宴,其诣堂子著永行停止”[7](P.891)。顺治在十三年(1656)免行堂子祭祀后,却并未减轻对汉族祭祀礼仪的重视。可见其在满汉礼俗文化的竞争中,选择了以汉人的礼乐制度为主。这两种对满汉礼乐文化不同的倾斜源自于最高统治者自我定位的不同。在顺治朝前期,实际当权者多尔衮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满族征服者的利益,其身份认同仍然是满族人的首领,与此相佐的主要国策亦是“首崇满洲”。顺治帝亲政后,强调以满汉一统多民族国家君主身份治国,这一点在顺治帝的政治理想中也可看出,顺治十年(1653)正月,顺治入内院阅《通鉴》,问历代帝王何帝为优,陈名夏推唐太宗,顺治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7](P.567)其以历代汉族贤君来鞭策自己,并对明太祖推崇不已,这明显可看出顺治帝对自己的定位不只是满族的首领,而最高统治者的自我定位与治国政策,最终影响到其对满汉礼乐文化的选择。
自多尔衮至顺治亲政,满清经历了由满汉礼乐文化相互竞争,而满族风俗占上风的情况转为以儒法立国,尊崇汉人礼乐制度的过程。当顺治帝首选以礼乐制度治国后,演剧将被看成宣传礼乐教化的媒介,而不只是娱乐的工具,加强对演剧的管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结 论
顺治朝的演剧政策有逐渐收紧的趋势,以顺治八年(1651)亲政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多尔衮当政,演剧制度不完备。此时只置教坊司作为音乐总管机构,但延续了教坊司在明代后期已兼掌雅俗之乐的混乱情况,不设钟鼓司之类的专门演剧机构。再者,政府对演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误人子弟”的丝竹娱乐之事上,无意对演剧活动进行管控,更谈不上以演剧来上宣下化。顺治帝亲政以来,逐渐加强对演剧的管理。在内朝,恢复设立钟鼓司,同时将女乐手中的音乐演奏权转移至太监手中,意欲设立由自己掌握的专门演剧机构。在外朝,开始控制演剧活动,颁布禁琐语淫词令,颁布演剧禁约,并对明末清初以来依然发达的江南演剧活动进行控制打击,意图将演剧制度纳入集权管理的范畴。
顺治朝演剧政策的改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直接原因:清初演剧创作与演出,直接或间接与悼念故明的思潮,以及此起彼伏的反清起义有关,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加强管理。其二是制度的原因:自多尔衮至顺治亲政,满清经历了由满汉礼乐文化相互竞争,而满族风俗占上风的情况转为以儒法立国,尊崇汉人礼乐制度的过程。当顺治帝欲以儒家礼乐制度立国,演剧将被看成宣传礼乐教化的媒介,加强对演剧的管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注 释:
①此一“徘徊”主要是指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初呈现退化,但并未消失,而是艰难曲折地前行着。具体可参看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395页)中关于清前中期文学与戏曲发展概况的研究。
②这三十三篇杂剧分别为:吴伟业《通天台》《临春阁》,尤侗《读离骚》《吊琵琶》,邹兑金《空唐话》,南山逸史《半臂寒》《长公妹》《中郎女》《京兆眉》《翠钿缘》,郑瑜《鹦鹉洲》《汨罗江》《黄鹤楼》《滕王阁》,周如壁《孤鸿影》《梦幻缘》,査继佐《续西厢》,碧蕉轩主人《不了缘》,张源《樱桃宴》,薛旦《昭君梦》,土室道民《鲠诗谶》,邹式金《风流冢》,黄家舒《城南寺》,陆世廉《西台记》,堵廷棻《卫花符》,茅僧昙《苏园翁》《秦廷筑》《金门戟》《闹门神》《双合欢》,孟称舜《眼儿媚》,张龙文《旗亭宴》,孙源文《饿方朔》。
[1](明)申时行等撰.明会典[A].续修四库全书第 791 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3]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刘锦藻编纂.清朝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5](清)王杰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A].续修四库全书第80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黄敏学.清代宫廷音乐管理体制的时代特征及其近代转型[J].江淮论坛,2011(6).
[7]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瘦禅.南府沿革记[J].中国公论,1939(2).
[9]邓之诚.骨董琐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0](清)素尔纳.钦定学政全书[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828 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清)汤斌.汤斌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2](清)董含.三冈识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3](清)尤侗.钧天乐自记[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册[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4](清)丁耀亢.作赤松游本末[A].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Z].合肥:黄山书社,2008.
[15](明)徐世溥.江城纪略[A].清.邵廷釆.东南纪事(外十二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6]徐鼐撰.王崇武校.小腆纪年附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7](清)叶廷琯.楙花盦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8]康熙朝大清会典[M].北京:线装书局,2006.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 CHOW KAI-WING,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4.
Title:From Entertainment to Li-Yue:A Study of the Policy on Theatre in the Reign of Shunzhi
Author:Liu Wei
The Reign of Shunzhi is a speci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The policies on theatre during this tim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in the later periods.A study of these policies is helpful for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atrical history in the Qing Dynasty.In the voluminous materials after the Qing army’s invasion of Shanhai Guan,we can find obvious changes in policies on theatre during Shunzhi’s reign,and the eighth year (1651) was a turning point as Shunzhi came to power at that time.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Shunzhi,when Dorgon was in power,there was no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policy on theatre.For many reasons Emperor Shunzhi began to strengthen his control of the theat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ama itself was a direct reason,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us of li-yue (ritual and music) and Manchu custom.
the reign of Shunzhi;policy on theatre;entertainment;li-yue(ritual and music)
J80
A
0257-943X(2017)01-0085-09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