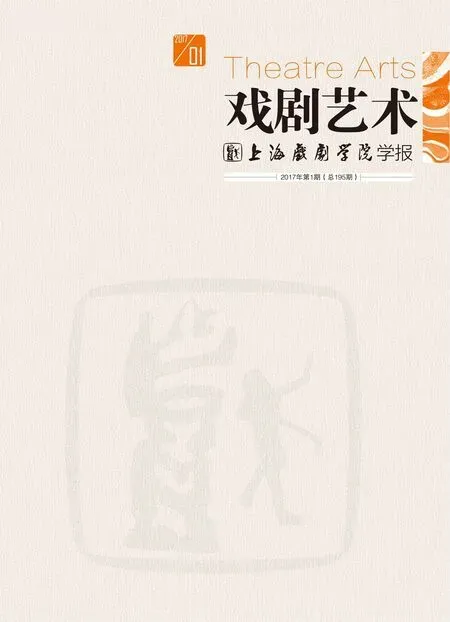论抗战时期上海话剧的职业演剧
■计 敏
论抗战时期上海话剧的职业演剧
■计 敏
在以往的中国话剧史书写中,抗战时期上海的职业话剧经常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对于职业化、商业化演剧的轻视是长期以来“左翼思维”的结果。本文从战时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都市大众戏剧的视角,以及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三方面,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评价。检视上海话剧演剧史上的这段黄金时期,对于今天戏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抗战时期 上海话剧 职业演剧 都市大众戏剧 商业与艺术
中国话剧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渐趋成熟,无论从剧本创作、舞台表导演艺术水准,还是职业演剧的兴起来看,当时的话剧已经展露出作为五四新文化硕果之一的良好势头。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却打破了这一进程,迫使中国话剧在艰难的环境下重构格局。所幸的是,由于战乱导致的剧团、剧人向全国的转移扩大,以及话剧自身的轻便特色与群体性的剧场效应,在抗战中其他文化样式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话剧反而获得了意外的发展空间,也因此造就了话剧史上空前的繁荣。
上海原是中国话剧的发祥地与演剧中心。抗战初期,上海组织的12个救亡演剧队中有10个队,以及另外一些剧团都先后离开上海,奔赴各地,后来大多数剧人集中到了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也有一部分到了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留在上海的及陆续新加盟的话剧人却没有落寞自弃,而是在险恶的“孤岛”与沦陷区环境中继续奋斗,虽然从创作与演出的声势、规模和质量上难与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比肩,却也形成了上海话剧演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并且带动与促进了京剧、越剧、沪剧等戏曲剧种的演出活跃。
然而,面对这段特殊时期上海职业演剧异常繁盛的历史,以往的中国话剧史缺少正面书写,学界更是疏于客观研究。尽管近些年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在史料的发掘和重新评价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有部分可喜的学术成果问世,但仍留有很大的梳理与研究的空间。
一、职业演剧:历史的再评价
抗战八年间的上海话剧,无论前一段的“孤岛”(1937年11月—1941年12月)时期,还是之后的“沦陷”时期,都没有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化与物质生活的艰辛而萎缩,相反日益趋向活跃,甚至在1943—1945年间达到了高潮。当时参与创作和演出的戏剧家顾仲彝后来曾回忆说,那几年“电影院亦争着改为剧院,上演话剧。胜利前一年是话剧演出最旺盛的一年,最多有十三个戏院同时上演话剧”[1](P.195)。这种盛况也可以从沪上最大的《申报》所刊登的戏剧广告中窥见一斑。如某一个晚上就同时有《香妃》《原野》《飘》《浮生六记》《弄真成假》《清宫怨》《爱我今宵》等7台话剧在不同剧场上演①。如此规模的话剧演出,即使在今天也很难企及。在当时热演剧目的编导中不乏阿英、于伶、李健吾、柯灵、杨绛、黄佐临、费穆、朱端钧、顾仲彝等大家。当然,也有大量为应付商业性演出的平庸之作,这在数量众多的职业演剧中在所难免。
既然抗战时期上海戏剧(尤其话剧)演出的繁盛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为何长期以来被主流戏剧史家所忽略和轻视呢?原因很简单,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演剧继承着五四及“左翼”戏剧的斗争传统,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戏剧虽幼稚粗糙,但直接服务于抗战与革命事业,两者历来受到高度评价与重点研究,而唯独上海这8年的演剧活动因为与职业化、商业化相关,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用“畸形的繁荣”一言以贬之。这是长期以来“左翼思维”造成的结果。
中国话剧与职业化、商业化确实有一种历史性的纠结。早年的文明新戏从一开始就着力于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的社会改良作用,到辛亥革命失败后转向了恶性的商业竞争,终于走向堕落。针对这个教训,五四以后的戏剧人大力提倡非职业化的“爱美的”戏剧,现代话剧得以在小剧场探索中逐步形成。但一种戏剧形态的成熟终究不能停留于业余演剧的水准,于是1933年,戏剧家唐槐秋在上海创办了现代话剧第一个职业演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把《茶花女》《雷雨》《日出》等剧演红了各地。但这一可贵的尝试也因其非左翼的面貌和较浓重的商业气息,受到许多非议和排斥,历来评价不高。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曾和职业化演剧保持一定距离的左翼戏剧,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也悄悄地向职业化靠拢了。1935年初,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剧联”针对几年来演剧内容过激,因而经常遭到当局禁压的情况,提出了改弦更张的演剧方针——以公开的大剧场演出为主,争取长期占领话剧舞台。于是,同年以原左翼剧人为班底成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名为“业余”,实则开始了半职业化的演剧,《娜拉》《大雷雨》《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名剧一度风靡沪上。这些表面上不带鲜明政治倾向性的戏剧演出,既提高了话剧舞台艺术的水平,又培养了战前上海的市民观众群。中国旅行剧团和业余剧人协会为话剧的全面职业化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是突然而至的“七七”事变,人们期待的“话剧职业化年”(1937)必将掀起职业演剧的一波新高潮。
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上海的话剧因战乱而沉寂,此后,以上海剧艺社(简称“上剧”)为代表的职业演剧又一次燃起热焰。“上剧”有明显的左翼背景,其领导人于伶就是左翼时期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也是中共地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上剧”成立之初(1938年7月)只是一个业余的演剧团体,这个以“中法联谊会”名义在法租界注册的剧团,无固定剧场和演出周期,靠招股集资维持开支,也无法实行薪酬制度。但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成功转型为影响很大的职业剧团,堪称“孤岛”剧运的中流砥柱。实践让“上剧”成员体会到职业化是推进剧运的必由之路,正如剧团的一位骨干成员吴琛说的,“在这一个年头的工作实践中,使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一个新的要求。这就是:‘要使中国戏剧进步,必须职业化。’职业化的目的是争取长期演出,争取大量观众,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推进戏剧运动走到更高的阶段”[2]。在“上剧”的带动下,“中旅”、新艺剧社、天风剧社等大剧场职业公演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其指导下的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更是创造了群众戏剧如火如荼的新气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后,职业话剧一度受到抑制,却很快出人意料地“反弹”。上海剧艺社虽已解散,但黄佐临等领导的苦干剧团、费穆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团,以及“中旅”、新艺剧团、联艺剧团、华艺剧团、美艺剧团、同茂演剧(国华)等职业演剧团体层出不穷,先后多达20余个,而且形成了商业化竞争的热闹局面。
为什么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会走上职业化、商业化的道路,形成与重庆精英戏剧、延安革命戏剧不同的特色呢?原因正在于上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土壤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孤岛”到沦陷时期,上海恶劣的政治氛围,使得左翼传统的、倾向性鲜明的戏剧无法公开上演。如果说“孤岛”时期还可以借助租界的地理条件,以一些历史题材戏如《明末遗恨》《李秀成殉国》《大明英烈传》《梁红玉》等曲折地表达爱国抗日的主题,那么在日本侵略者直接统治的情况下,连这样的自由也不再拥有,所以,沦陷时期只能选择商业性比较强而意识形态比较弱的剧目来演出,其中大量的是中外经典的搬演或名著改编,如《三千金》《荒岛英雄》《大马戏团》《飘》《浮生六记》,少数原创也是杨绛、周贻白的反映市民家庭生活的作品,如《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阳关三叠》等。
虽然大量的商演剧目难免鱼龙混杂,演出中为了票房而损害艺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历史地看,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这种营业性的演剧毫无价值。热爱戏剧的学者赵景深当时在给大后方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比较客观地介绍过上海职业演剧的情况:
还可以向你告慰的,就是在上海的剧人至少大部分甚至全部是营业性的,什么红楼梦式,通俗小说的利用,杂耍化婆媳斗争式,一窝蜂地专就生意眼着想,有坏处也有好处,他们可以不必有政治关系,靠卖票收入就可以维持生活,一个编剧或导演一本戏两三万以上的收入还算是普通的。[3]
在特殊环境下维持生计是最重要的,无法生存,何来发展?当上海剧艺社转向职业化演剧之初,于伶写出《女子公寓》《花溅泪》等通俗剧以应付演出需要时,他内心仍感到委屈与困惑,因为他理想中紧跟时代的戏剧应该更有思想锋芒。但远在重庆却对上海文艺状况十分了解的夏衍,对“孤岛”环境下的职业化演剧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写信给于伶,认为“此时此地”的剧运是对戏剧人的一种“磨炼”,是“‘抗战建剧’的必要过程”[4]。
其次,职业演剧的兴起,也是适应了战时环境下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战争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所以一旦“孤岛”情势相对趋稳,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便重新抬头,至于上海沦陷后,在艰难与屈辱的生活中,话剧更加成为一种大众的精神激励与心灵抚慰的代偿品。
战时的演剧与市民文化活动的紧密联系还可以在“孤岛”群众业余戏剧的空前活跃中得到印证。虽然抗战初期大量剧人的西迁使上海的话剧中心地位不复存在,但话剧在上海的艺术根底与群众基础依然十分深厚。1938年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成立后,“沪上各行各业和学校的剧团纷纷加盟,剧团最多时达到120个左右”[5](P.128)。业余戏剧活动如此普及,为随即兴起的职业演剧高潮进一步培养了大量观众,其中的骨干分子还成了职业剧团补充艺术人才的重要来源。
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拥有更大观众群体的电影业撤向西南后方,余下的被日伪当局所据有;文学与出版业也因战时条件的限制而有所萎缩,市民们开始把文化娱乐的重心转向了话剧。至沦陷时期,好莱坞电影完全被禁,上海原先的影院纷纷改为戏院。卡尔登、辣斐、璇宫、兰心、金城、光华、金都、巴黎、绿宝、丽华等成为演话剧的主要阵地。这些设施先进完备,采取商业化经营模式的现代剧场,给职业化演剧提供了硬件方面的保障。但还是不够用,甚至一度发生剧团之间争夺演出场所的“剧场荒”。
第三,战时上海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制约着戏剧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以其特殊的经济、政治状态刺激着职业演剧的生长。“孤岛”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周边沦陷区的富商巨贾携带大量资金来到这里,在实业与贸易投资受阻的情况下,上海的游资迅速增长,“截至1940年5月底,竟达到50亿元之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投机,蓬勃兴起的文化娱乐业也是他们投资的方向。上海的经济逆风而上,呈现出反常的繁荣。同时,从1938年春季起,大批避难的市民涌入租界,半年多的时间里,租界人口翻了一番,达到近500万,其中青壮年占了很大比例,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各行业补充了廉价的劳动力,还拉动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消费”[5](P.111-112)。这就使抗战时期上海的商业性演剧不仅获得了资金来源,同时拥有了广阔的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连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也看中了办职业剧团的商机,插手投资和管理,这就是当时不少剧团都有“荣记”背景的原因。
从政治环境上看,“孤岛”时期英、美、法租界当局虽然不想因抗日爱国的演剧惹恼日本人,却也乐见租界内文化生活的活跃,以示他们治下的领地与日占区的不同。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租界的日本侵略军发现“不夜城”上海陷入一片漆黑,为显示这一东方大都市变成了“王道乐土”,更加繁荣,他们下令各类商场、戏院、舞厅、游乐场重新开张营业。对于占领区的中国人,他们一面采用残酷的高压统治,一面又施行怀柔政策,允许甚至“鼓励”不带政治色彩,不直接反日的文化活动存在,以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这在客观上也给职业化演剧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许多营业性剧团就是在这一缝隙中生长起来的。
当时上海地缘政治之复杂,常常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1942年之后,有些汉奸竟然也出资或疏通关系来“支持”进步的演剧,曾亲历其境的戏剧家李健吾在战后的一次“文艺检讨座谈会”上披露过:“当时剧本的出版是无须审查的,演出才须审查。说来也很好笑,到了抗战后期,许多汉奸鉴于局势不利,竟有以投资演出富于正义感的话剧电影,来谋赎罪的投机观念。所以,有许多戏,原来不与敌伪勾结的人不敢演出,很多倒是由汉奸支持而演出的。因此,在沦陷期间,其他文艺部门充满了汉奸气息,惟有话剧倒很多值得一看的。”他由此为商业演剧进行了辩护,“当时内地方面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了,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若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只有与敌伪勾结的‘政治化’了。”[6]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脱离了当时的语境片面地贬低商业演剧的价值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大众戏剧:都市文化的新视角
当时上海商业性话剧的兴盛,不仅出于政治的逼迫与资本的渗入,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说,在这一特殊时期,话剧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一个表征而兴起,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他在研究30—40年代上海“新都市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当年推进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强大动力就是所谓的“上海摩登”。“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7](P.7)。因此,“上海摩登”不仅表现在洋房、汽车、银行、商厦、舞厅、赌场这类与西方大都会接轨的物质文化层面,更深入到市民大众的精神领域,诸如时尚报刊、通俗小说,以及剧场、影院、咖啡馆等新的公共文化传播空间。可以说,“摩登”的文学、电影和戏剧,才是真正渗透着启蒙现代性的文化形式。
如前所述,抗战爆发使得上海业已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发生一时的萎顿,但时局相对稳定之后,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急待一种新的娱乐文化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在电影业、出版业受到了压制和破坏的情况下,话剧这种原本带有精英文化性质,无法与电影、小说等进行市场竞争的形式,以它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迅速的收益,还有它与电影的紧密联系(比如有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剧目,有吸引观众的剧影双栖“明星”等),很快填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市场空缺,并且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被赋予了一种更为通俗的大众文化的性质。这与重庆等大后方城市的社会条件与文化状态是颇不相同的。
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时尚流行性。时尚文化常常被看作是肤浅和速朽的文化,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会包含着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此时此地”大众内心情绪与欲求的文化信息。如同30年代都市文化中的“革命”曾是一个时髦,在“孤岛”乃至沦陷时期,“抗战”也成了市民大众心目中流行的一种崇高的概念。上海剧艺社等上演的一些历史剧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就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以浓烈的民族国家激情喊出了风起云涌的时代呼声,而且民族国家观念的传达本身就是市民意识和市民情趣的直接体现。1939年阿英的《明末遗恨》连演64场,打破了以往话剧演出的记录,也让濒临经济危机的“上剧”一举翻身。何以如此?当时被称为“四小导演”之一的胡导解释说:“孤岛上人们的爱国情怀已经憋了两年多了!当舞台上的孙克咸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时,观众心里就和‘他’共同吟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当舞台上男男女女仁人志士举兵起义时,观众也感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8](P.101)著名演员石挥在1941年“中旅”演出《花木兰》时,也在报纸上发文公开表示:“《花木兰》的上演,不是‘我们赚钱,观众看戏’那样公式般的把戏,我们是希望在上海女人群中,击起一个不同凡响的激动!它能波及到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女人群中去!”[9]即使到上海全面沦陷之后,仍有《岳飞》②《文天祥》等历史剧出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大众流行意识的合流,是如何通过大众戏剧满足战时市民群众的心理需求的。
当然,抗战时期的上海不可能都演这类明显渗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剧目,尤其在日伪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剧目淡化了政治色彩,力求符合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性特点。这类商业戏剧面对演出市场,自产自销,自负盈亏,通过新编剧目的不断推出和保留剧目的轮番上演,仅以演剧的票房收人就可维持剧团的生存和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从演出剧目的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现实和改编三大类:
第一类历史故事传说题材,从最初的直接表达爱国抗战主题、歌颂民族英雄的历史剧,逐步转向根据历史故事编写的古装戏、清装戏。推出这类剧目最多的要数“上剧”“中旅”,如《明末遗恨》(《葛嫩娘》)、《大明英烈传》《洪宣娇》《李香君》《花木兰》等,以及费穆领导的天风剧团、上海艺术剧团,如《清宫怨》《杨贵妃》《陈圆圆》《浮生六记》《蔡松坡》《王昭君》等。其他剧团较有影响的古装戏还有“新艺”的《海国英雄》《杨娥传》,“苦干”的《林冲》《美人计》等。 阿英、姚克、周贻白、费穆、吴永刚都是善于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编导。
当时话剧舞台上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涌现并非偶然。首先是现实题材的创作受到钳制,风险更大,在抗战后方的重庆尚且如此,何况环境险恶的上海?因此创作者纷纷从历史中找寻与现实有某种契合点的素材;其次,历史故事和人物本身渗透着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和气质,有些还是从戏曲搬演过来的,与观众有天然的亲和力。而这些古装戏中所表现的尽是没落王朝的哀伤、末路英雄的悲愤,尤其是那些被卷入战乱的女人的不幸命运与奋力抗争,确实能激起战时大众内心的强烈共鸣,不少剧目一演再演,深受观众欢迎。
第二类现实题材戏剧的创作在当时是相对薄弱的。从客观上说,抗战初期的话剧人大转移,使得留沪的剧作家锐减。于伶是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主力,他在上海剧艺社时期陆续写了《女子公寓》《花溅泪》,尤其是《夜上海》一剧,以质朴平淡的笔调描写了“孤岛”的社会生活面貌,以血淋淋的现实警示民众要“坚持着活下去”,但绝不能出卖灵魂。这是标志于伶剧作风格成熟的一部代表作。于伶在沦陷之前就离开了上海,留在职业演剧圈内的李健吾、顾仲彝、周贻白、柯灵等人则疲于应付新剧目的推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改编上,没有时间思考和创作现实剧,何况严酷的环境使直面社会的戏剧几无生存的可能。周贻白为“中旅”和绿宝剧场写的一些戏多为适应商演的家庭戏、公馆戏,如《绿窗红泪》《阳关三叠》等,从伦理道德角度展现家庭中的经济纠纷、男女关系,迎合市民阶层观众的兴趣。
有质量的一些现实题材作品一方面来自大后方的剧作家,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张骏祥的《小城故事》等;另一方面,上海繁盛的职业演剧也激起一些文学作家和教授们“逢场作戏”的兴趣,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改成话剧上演;杨绛写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四个剧本,虽然也是取材上海市民生活,却生动地展示了战时社会的人情冷暖、人性异化,独特的幽默讽刺风格被李健吾称为可与丁西林的喜剧媲美,演出的效果也很不错。杨绛曾表示,这些喜剧可以看作“在漫漫长夜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10]。 另外,石华父(陈麟瑞)、徐也热衷于剧本创作,前者的《职业妇女》,后者的《孤岛的狂笑》都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类为各种改编剧目。这是商业演出中缓解原创作品紧缺的常见策略,占据演出剧目的大多数。改编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外国名剧;二是中国著名小说。原著有的是经典,非经典的也是影响广泛的成功之作,因此很容易把文学、戏剧的爱好者吸引到剧场里来;现成的精彩故事与人物又使改编相对便利一些。
上海从上世纪初开始就有“西化”传统,普通市民也把欣赏外来形式的话剧、电影看作一种时髦,知识分子更是对外国作品趋之若鹜,这些都构成了“海派”文化的一部分。在抗战时期的职业演剧中,有留洋背景,或是作家、学者身份的编导往往喜欢也擅长作外国名剧等的翻译、改编,如黄佐临的《荒岛英雄》(《可敬的克莱顿》)、《梁上君子》,李健吾的《金小玉》(《托斯卡》)、《乱世英雄》(《马克白》),顾仲彝的《人之初》(《窦巴兹》)、《三千金》(《李尔王》)、《生财有道》(《吝啬鬼》),师陀的《大马戏团》(《吃耳光的人》)、《夜店》(《底层》,与柯灵合作),柯灵还把好莱坞电影《飘》搬上了舞台,这些都是外国剧目改编中的佼佼者。也许是为了优化接受效果,当时对外国作品盛行“改译”的方法,即将原作的人物、故事都换成中国的,有的改动很大,在那些爱与欲的角逐背后有人性的审视与批判。当然,也有一些纯粹“凑数”的二三流作品改编,比较肤浅平庸。
改编本土小说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最早在沪上引起轰动的是吴天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由上海剧艺社创纪录地连演127场,成为“孤岛”后期盛况空前的一次演出,观众人数大大超过此后曹禺的《家》。吴天的改编本场面热闹,采取全景式的视角展示了高家年轻人的不幸爱情,在大家庭即将倾塌的背景中表达了浓重的凄凉、无奈的悲剧气氛,与当时上海迷茫的社会心态十分契合,使观众产生心有戚戚之感。在纯文学的改编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中法剧社、“中旅”等剧团多次上演,由许幸之和田汉先后改编鲁迅《阿Q正传》的两个话剧本。
不过,根据通俗流行小说改编的《秋海棠》《情天恨》《三笑》《啼笑因缘》等贴近一般市民的作品还是占有更高的上座率。其中,费穆、黄佐临、顾仲彝联合原作者秦瘦鸥编导,石挥主演的《秋海棠》,创造了上海职业话剧史上的最高上座记录,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5月连演了200多场③,观众逾18万人次,虽票价高达30元一张还是买不到,黑市价翻了近一倍,而且带出了越剧、京剧、电影、评弹等的“秋海棠热”,成为市民们一时议论的话题。为什么一部“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改编演出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沦陷区上海的象征标志”[11](P.211)呢?有分析指出主角的艺名“秋海棠”形似中国地图,隐含着国家被侵占、吞噬的寓意,因此引起观众的联想和感叹[11](P.218-219);而小说家张爱玲则认为:
《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中国的写实派新戏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12]
张爱玲指出该剧成功地借助于传统戏曲的魅力是有道理的,而她称《秋海棠》为“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更是准确地看到了大众戏剧的平民世俗化特征。由此可以说,中国话剧历来纠结的“大众化”问题,在抗战时期的上海职业演剧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张爱玲所说的“民间”和我们讨论的“大众”,并非左翼文化所指的“普罗大众”即产业工人,当时的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温饱尚且有虞,遑论进入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这里的“大众”是指受过初中级以上教育,从事非体力劳动并有中等以上收入的市民大众,只有他们才有精神文化的追求和消费能力。
这一点还可以从当时上海文明戏的重新崛起得到印证。文明戏作为一种早期话剧的形式,自20年代被现代话剧取代了主流地位后逐步衰落,直到本时期大众文化娱乐市场形成后才又迅速活跃起来。当“上剧”、天风等剧团还在为缺乏固定演出场地发愁时,一批曾经从事文明戏与早期电影的戏剧人,已经聚集在新新公司附设的绿宝剧场、东方饭店附设的东方书场等地,进行场、团合一的商业演出了。绿宝剧场的演出阵容是相当整齐的,编、导、演、舞美设计一应俱全,他们以“改良文明戏”“通俗话剧”的名义演出,以普通小市民阶层为目标观众(尤其是女性),多从家庭、爱情、伦理、传奇、武侠等题材入手,大量改编鸳蝴派小说、黑幕小说,并从戏曲剧目中汲取资源,颇有早期文明戏之遗风,不过在格调上力图提高,为此,他们还搬演了《雷雨》《日出》《伪君子》《葛嫩娘》《家》《女子公寓》等现代话剧,邀请顾梦鹤去剧团排戏,聘请阿英、周贻白担任兼职编剧。尽管部分对文明戏抱有偏见的左翼剧人比较排斥绿宝、东方,但后者占有演出市场的很大份额(从当时报纸的广告可明显看到),以明显的消闲娱乐性深受一般市民观众喜爱,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正统”的话剧人士中也有对此予以赞赏的,如黄佐临1940年初到上海就去绿宝剧场看戏,肯定了演员们“抓得住观众的反应”,“演技的纯熟和动作的有起接”,“演戏的从容”,并表示“我并不想把话剧和他们分有什么鸿沟,虽然大家对我的意见也许不大满意”[13]。可以想见,佐临后来在“上剧”“苦干”搞通俗喜剧时就有他们的启发和影响。
三、艺术与商业:博弈中的坚守
柯灵曾经对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的社会做过如下描述:
斗争是多角形的:对日本侵略者,对汉奸,对妥协投降倾向,对乌烟瘴气、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还有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斗争的锋芒有如幅射。光与暗,红与黑,热与冷,崇高与猥琐,圣洁与卑污,慷慨激昂与陆离光怪,组成一幅对列鲜明、色彩强烈而布局繁复的图画。[14]
这种情形决定了当时上海的职业话剧走向市场必然是一条艰难的泥淖之路。说它艰难,是因为从业人员始终面对政治的高压,随时可能被日本宪兵队“传唤”,甚至羁押,或者受到汉奸势力的种种蛊惑利诱。但绝大多数话剧人经受住了考验,虽是商业化演剧也保持着独立性,不和敌伪合作。另一方面,在资本运作的体系下,话剧人还要抵制金钱的腐蚀,不为营利而媚俗,坚守艺术的良知。尽管有环境造成的某种扭曲,有商业化带来的某些弊病,但应该说在这一由剧场、剧团、观众、媒体、评论界共同构成的文化公共空间里,基本面还是健康的,并不能用所谓“畸形的繁荣”加以概括。从表面上看,抗战时期的职业演剧与1914年文明戏的“甲寅中兴”有点相似,两者都面临生存的压力,而本时期环境的压迫更甚,那么为什么职业化、商业化演剧并没有像当年的文明戏一样走向堕落呢?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有一批较高素质与修养的艺术家,如剧作家于伶、阿英、李健吾、顾仲彝等;被誉为“四大导演”的黄佐临、费穆、朱端钧、吴仞之,以及吴琛、洪谟、胡导等年轻一代导演;演员方面也有很多优秀人才如男演员石挥、刘琼、韩非、张伐、孙道临、戴耘、冯喆、白穆、章杰、严俊、路明、乔奇、黄宗江等,女演员唐若青、夏霞、蓝兰、章曼萍、沈敏、英茵、上官云珠、丹妮、蒋天流、黄宗英、孙景璐等,其中半数以上为剧影两栖的“明星”,这样强大的阵容是文明戏时期完全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无论出身、教育背景如何不同,在政治上都有爱国这道底线,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追求,所以在泥淖般的社会环境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职业演剧看似远离政治的内容与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让敌伪当局失去了干涉的理由,从而成功实现了对权力宰制的规避;同时,对艺术底线的坚守,也成功抵御了资本势力和文化痞子的操控。尤其是作为最有影响的剧团领导人于伶(“上剧”)、唐槐秋(“中旅”)、黄佐临(苦干剧团)、费穆(艺术剧团)等,都是能在“乱花迷眼”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的艺术家,虽然难免有各种票房赢利上的考虑,但在这场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中,他们始终没有为了生意眼而放弃艺术心。反观“甲寅中兴”时期的文明戏,商业化并非其堕落的原因,恰恰因为他们不是用艺术,而是艺术以外的东西“卖钱”,或者说文明戏及其从业者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和艺术追求。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当时职业演剧的主创人员对艺术的坚守,可以从他们选择、编排剧目和力求形成自身风格的努力中看出。比如,上海剧艺社以于伶的“孤岛”现实剧与阿英的南明历史剧双珠辉映,夺得了上海职业演剧的制高点。沦陷时期费穆的艺术剧团和黄佐临的苦干剧团也是以各自艺术特色吸引大批观众。电影导演出身的费穆把话剧舞台的电影化与戏曲化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别出心裁地运用乐队伴奏,充满诗意地排演了《清宫怨》《杨贵妃》等新历史剧。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又是一番风貌,他和李健吾、顾仲彝等把外国名剧改编得有声有色,用“中国化”的改译使之更贴近市民观众。在《荒岛英雄》《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钦差大臣》)等剧中,佐临还探索了他喜爱的通俗喜剧手法。
戏剧的编导固然重要,但舞台呈现最终要靠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曾被评为“话剧皇帝”的石挥可说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好的演员之一,而他的艺术锤炼、升华的过程就是在上海抗战时期的职业演剧中完成的。石挥从观察生活出发,钻研表演技巧,善于多侧面地创造性格丰满的角色。比如他扮演的《大马戏团》中的老无赖慕容天锡、《金小玉》中的警察厅长、《夜店》中的落难公子金不换等,一个个都生动鲜活。在前述费穆、黄佐临等编导的《秋海棠》里,石挥饰演的秋海棠更是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命运多舛的京剧名伶形象,尤其表现他老年落魄的场面非常感人,如潦倒的秋海棠在后台忍不住指点一个青年旦角的唱腔时,遭到那人的抢白:“你是谁?”秋海棠随即连说了三声“我是谁?”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撕裂人心,最后他哽咽地把话噎住……那种荣辱沉浮、悲怆无语被石挥演绎得动人心魄!著名演员赵丹当年看过演出后感叹地说:“这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契诃夫式的《天鹅哀歌》,带有契诃夫的味道。”[15]正是在这些优秀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下,一部通俗言情小说被打造成情感充沛、艺术上乘的精品;也正是剧中所透露的那种爱情摧毁、落寞飘零、骨肉亲情、悲苦无奈的人世沧桑之感,深深地触动了那个时代观众的内心之痛。因此也可以说,艺术上的高尚追求和精湛造诣,使得《秋海棠》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标志。
“中旅”的台柱唐若青也是在职业演剧中磨砺出来的好演员。她饰演的侍萍(鲁妈)、陈白露、茶花女在观众中是有口皆碑的,抗战时期塑造的葛嫩娘、洪宣娇、李香君等历史剧女性形象又使她赢得了“话剧皇后”之誉。唐若青饰演的葛嫩娘英气逼人,几乎每幕都有斥责奸佞的场面,尤其高潮“被俘”一场,面对敌寇嬉笑怒骂,侃侃而言,一大段台词铿锵有力,时而如火山爆发,时而如江水滔滔,每演至此,观众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唐若青善于掌握观众心理,也善于运用技巧增强艺术效果,表演上激情充沛,又能准确把握分寸和节奏,做到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她后来沾染了某些“明星作风”,是由于“中旅”的商业色彩过于浓厚养成的。从总体上看,抗战时期上海职业话剧的表演、导演等舞台艺术的水准可圈可点。绝大多数的演职人员并不认为商业演出可以降低标准,糊弄观众,而是尽力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其中的职业精神与艺术自觉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戏剧人学习借鉴的。如果说有缺点,主要表现在原创剧本跟不上剧目轮换的需要,许多改编作品的质量也差强人意,不能给舞台艺术提供更大的发挥余地。
其次,抗战时期上海职业演剧也形成了较为健康的外部舆论场。作为都市大众传媒的报刊、电台对话剧的关注和评论非常及时。随便翻开当时的《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等有影响的报纸,都能看到戏剧类的副刊、专栏上大量刊登的戏剧介绍、评论文章。几乎每一出新戏推出,批评的声音随之鹊起,褒贬自由,众声喧哗。此外,戏剧专业杂志如《剧场艺术》《杂志》《剧场新闻》《戏剧与文学》《小剧场》等也纷纷创办,话剧舆论的倡导为开展职业演剧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戏剧评论通过媒体影响着观众,也以“舆论”作用于剧团和剧目生产。进入40年代以后,上海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剧评家,如麦耶(董乐山)、兰(关露)、邹啸(赵景深)、康心(叶明)、孟度(钱英郁)等。他们一方面积极提倡话剧的商业化,认为“商业化不独可以巩固话剧的地位,还可以迫着它走上改进的路。因为既然商业化了,话剧就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该使买主买了没有冤枉花钱的感觉”[16]。另一方面,对于商业戏剧出现的问题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批评一些剧团的“生意眼”“耍噱头”,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艺术的不良倾向,即使对有威望的费穆、黄佐临导演的某些戏同样敢于质疑。青年剧评家麦耶更是写文章批评“中旅”多年来没有演过一个像样的剧本,一直在翻曹禺的老戏,后来又随波逐流大演历史戏、家庭时事戏、侦探戏。在《姊妹心》的演出中,演员各自为政,互不合作,台上动作随便,看不出导演的存在,“日益步上文明戏之途了”!并大声疾呼:“这是一条死亡之路,如果中旅仍然继续《姊妹心》的演出态度而不加反省,对于自甘落伍者,我们,观众们,将毫不加以同情与可惜,不管中旅过去有多么光荣的历史。”[17]
有些剧评家虽与话剧圈相当熟悉,但写起剧评来仍是尖锐的,据实褒贬,以理服人,表现出可贵的独立批评精神。由于大部分文章不是商业炒作式的宣传,而是坚持原则的批评,因此对职业演剧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商业戏剧滑向低级庸俗、粗制滥造歧路的作用。戏剧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戏剧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既有艺术家的艺术良知和自我约束,又有评论家在舆论场上公正的批评和守护,这是上海抗战时期职业化、商业化演剧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也是这段历史给予当下戏剧市场健康发展的有益启示。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戏剧与电影的互动关系研究(1905-1949)》(项目编号:15YJAZH026)的阶段性成果;上海市高峰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建设计划(项目编号:SH1510GFXK)成果之一]
注 释:
① 见《申报》1943年10月14日广告栏。
②《岳飞》一剧上演不久即遭禁演。1943年12月3日,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致伪市第一警局手谕称:“中国青年剧艺社在大上海大戏院演出的话剧《岳飞》‘有伤国策’,禁止上演。”见李涛:《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一书“附录二:上海职业话剧大事记”(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③ 根据1942年12月24日至1943年5月10日《申报》中刊登的广告,得出统计数据。
[1]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A].顾仲彝戏剧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2]吴琛.两年半来的上海剧艺社[J].剧艺,1941(1).
[3]赵景深.最近上海的话剧[J].戏剧时代,1944,1(6).
[4]夏衍.论“此时此地”的剧运——复于伶[J].剧场艺术,1939(7).
[5]丁罗男.上海话剧百年史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J].上海文化,1946(6).
[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胡导.干戏七十年杂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9]石挥.此时此地演《花木兰》[N].中美日报(“艺林”副刊),1941-1-7.
[10]杨绛.喜剧二种·后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1]卲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J].古今,1943(11).
[13]叶明朱.“小城故事”导演佐临先生访问记[J].剧场新闻,1940(3,4).
[14]柯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小引[J].读书,1981(12).
[15]赵丹.表演探索(续)[J].戏剧艺术,1979(3、4).
[16]乐山.话剧应该商业化[J].万象·十月戏剧专号,1943,3(4).
[17]麦耶.评《红楼梦》及其他[J].杂志,1944,13(4).
Title:Professional Theatre in Shanghai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Period
Author:Ji Min
Chinese modern drama was often neglected both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Period,during which professional and commercial performances were long looked down upon in the “left-wing” thinking mode.This paper reevaluates that phase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restraint in wartime,the urban popular theatre,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Reevaluating that golden period of modern drama in Shanghai is helpful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theatrical market.
anti-Japanese period;Shanghai drama;professional theatre;urban popular theatre;commence and art
J80
A
0257-943X(2017)01-0033-12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