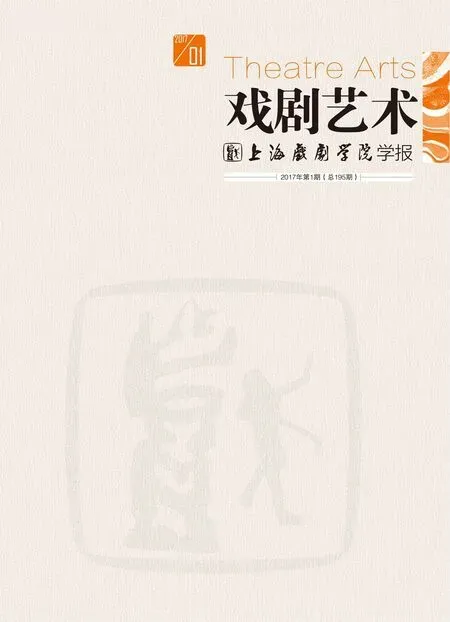崇古与尊今的较量
——清代戏曲批评史的一个脉络
■黄桂娥
崇古与尊今的较量
——清代戏曲批评史的一个脉络
■黄桂娥
在清代两百多年戏曲批评的历史中,存在着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崇古”与“尊今”两个思想势力的较量。崇古,是力求戏曲在形式表现、情感主旨等方面,向戏曲典范时代——元代寻求重振的根据与元素;尊今,是指以现今中的“我”作为戏曲艺术创作、表现与审美判断的主体,要求戏曲走出传统,顺应当今。“崇古”和“尊今”这两股对立的思想势力,在清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发生较量的实质,其实是清代艺术前现代与现代发生断裂的一种表现。
宗元 雅与俗 情与理 花雅之争
纵览清代两百多年戏曲批评思想的历史,充斥着两股势力的争锋较量,它们是“崇尚古曲典范”与“尊重现今新创”。清初,士大夫反思明政权覆亡的同时,认识到明末那种即将冲破一切阀限的艺术和人格,正是亡国的征兆。在清儒看来,晚明艺术“妄”“弱”“狂”“鬼”等病丛生,已无足取。借古以拯弊成为他们致力于复兴的共同意识。对于戏曲来说,其复古必然是复戏曲繁荣的元代之古。加之明代戏曲的种种流弊,元曲自然地成为戏曲创作与批评的典范。持此思想观念的戏曲家们对元曲大力推举,认为元曲是戏曲发展的最高成就,无法超越。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当中,时时以元曲为标准。但清代还有另一种文化背景:明末个性解放伦理思想的延续、新变;理、气崇实学术思想的理路;士商混淆、文人的布衣心态,这些则为“彰今”的戏曲批评势力,提供了萌发土壤。这一派的势力,都是在肯定元曲的基础之上,为戏曲寻找崭新发展的出路。他们有时会拿这种新变来比附元曲,以寻求存在的依据。因为“元曲是一种雅俗兼济之美,因此无论是雅是俗,清文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渊源”[1]。“崇古”与“尊今”这两股对立的戏曲批评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作用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或激烈较量或趋于缓和,由此构成了清代戏曲批评历史的波澜壮阔的景象。
一
“崇古宗元”是清初剧坛的主流思想,张大复在《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凡例》中说:“曲创自胡元,故选词定谱者,自当以元曲为圭臬。”[2](P.12)追本溯源成为这一派的共同追求。正如徐大椿所说:“后世之所以治不遵古者,乐先亡也。乐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谓欲求乐之本者,先从人声始。”[3](P.57)他认为这个“人声”的典范在元曲那里,所以多从元曲那里进行“人声”的正本清源之工作。但沈自晋偏偏对“崇古”提出强烈的抗议。在《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中,他讲述了和朋友冯子犹的分歧。朋友冯子犹编了一本词谱,还没编完就过世,托遗愿请他续编。他看了很是不满,认为朋友厚古薄今:“诸家种种新裁,……竟一词未及。独沉酣于古,而未遑寄兴于今耶?抑何轻置名流也!”[2](P.76)沈自晋将冯子犹划入“考古者”阵营,自己则站在“从今者”的阵营里。他认为:考古,则曲家有法可依,近于古人意旨,让人安定。但考古者之书,容易让人“置之覆瓿”;从今,则有利于增强曲子的应变能力,从而得到快速流传。从今者之书,也便于广泛施教。
清初“古今之争”的思想较量,主要体现在尤侗与李渔、毛声山与金圣叹之间。同为“古”与“今”之争,但他们又各有区别。尤侗与李渔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文野之争”;而毛声山与金圣叹之间的争锋,主要体现为“情理之争”。
尤侗在写给李渔的《名词选胜序》中,明确地阐述其词曲主张:“予独谓能为曲者,方能为词,能为词者,方能为诗。”[2](P.460)由此可见,尤侗将曲的地位看得很高。为何这样说呢?他在《叶九来乐府序》中有详细的阐说:“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歌诗,以鸣其不平。顾诗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抑扬含吐,言不尽意,则忧愁抑郁之思终无自而申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极致而后已。”[2](P.457)尤侗意谓戏曲比诗歌更能代人鸣不平之志,而在这点上曲又比词更加“淋漓尽致”。可惜当时的流行观念与他相左:“至于手舞足蹈,则秦声赵瑟,郑卫递代,观者目摇神愕,而作者忧愁抑郁之思为之一快。然千载而下,读其书,想其无聊寄寓之怀,忾然有余悲焉。而一二俗人,乃以俳优小技目之,不亦异乎?”[2](P.458)时人将曲子仅仅视为一种演艺人员的小技,他表示反对。但是,他所崇尚的曲子是怎样的呢?尤侗在其《艮斋杂说》中说:“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予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2](P.449)在写给毛氏的《第七才子书序》中亦言:“才人之作,至传奇末矣,然元人杂剧五百余本,明之南词,乃不可更仆数,大半街谈巷说,荒唐乎鬼神,缠绵乎男女,使人目摇心荡,随波而溺;求其情文曲致,哀乐移人,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者,万不获一也。”[2](P.462)这些观点有失于偏颇,但也表明尤侗宗元的思想,他认为明代戏曲的成就完全不能与元代相比。
与尤侗宗元的戏曲思想不同,李渔认为现今的作品比古人的作品更吸引人,因此其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古代的作品,放到今天,需求量很小,要争取大多数观众,只能新创:“盖演古戏,……只可悦知音数人之耳,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听古乐而思卧,听新乐而忘倦。”[4](P.89)在审美内涵方面,他认为固定的艺术审美趣味是不存在的,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人们的特殊审美需求,因此戏曲作品应该照顾目前观众的审美趣味,通过与时俱进的创新,使得观众重新在剧中找到新的共鸣,那才是正途:“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传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4](P.94)世道、人心、情态都是变化的,传奇的创作也应该随生活现实的变化而改变。李渔还论证了人们能接受旧剧的原因:“演新剧如看时文,妙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演旧剧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之可爱者,……非宝其本质如常,宝其能新而善变也。”[4](P.93)旧剧若有价值,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今天人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人们可以根据现今的体验,去解读、体悟其中的“新”,所以旧剧的价值能够历久而常新。李渔还在作品的题材内容、审美内涵与价值功能方面,强调“今”的重要性。在题材方面,李渔认为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眼见耳闻的东西,包涵了最能动人的魅力要素,可以为戏曲提供丰富的题材。“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4](P.29)
关于创作的动机,尤侗主张借古人之事来传达“我”之情绪,其实这是将“我”消融在古人世界中的一种方式。在《李笠翁〈闲情偶寄〉序》中,尤侗表达了戏曲声色之道用之于寄托的思想:“声色者,才人之寄旅。……我思古人,如子胥吹箫,正平挝鼓,叔夜弹琴,季长弄笛,王维为琵琶弟子,和凝称曲子相公,以至京兆画眉,幼舆折齿,子建傅粉,相如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载之衲衣乞食,此皆绝世才人,落魄无聊,有所托而逃焉。犹之行百里者,车殆马烦,寄旅客舍已而。”[5]由于对元人的创作心存钦慕向往之情,尤侗喜欢模仿元人的创作手法。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一些非议,尤侗感到很无奈:“予穷愁多暇,间为元人曲子,长歌当哭,而览者不察遂谓有所讽刺,群而哗之。夫以优伶末技尚不容于世,如此若以西厢之曲造为八股之文,向非特达之知。”[5]尤侗以“西厢”作时文《临去秋波那一转》之事影响很大,褒贬不一,但尤侗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趣。
与尤侗将自我投射进入古代不同,李渔将现今之“我”的感受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在《一家言》中表达了他的写作原则:“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侯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翼于其中也。……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为我”是一种实现自我的内在动力。李渔认为现今活生生存在着的自我,其力量远胜古人。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贵浅显”中,说道:“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觅古人。”创作不是我寻觅古人的足迹,而是发古人未发而想发的声音。李渔嘲笑没有创新的创作是“效颦之妇”“碎补之衲衣”“合成之汤药”,这些比喻是相当尖刻辛辣的。他还豪情万丈地提出:“我力足以降古人。”
毛声山与金圣叹之间的争锋是很明显的。金圣叹写了一本《第六才子书批西厢记》之后,毛声山很不满,他写了一本《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他写此书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与金圣叹针锋相对。《西厢记》与《琵琶记》两剧在元曲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是戏曲“之祖”“之宗”,也是元曲两种不同风格的代表。金圣叹批西厢,但并不宗元,毛声山批琵琶,却具有鲜明的宗元思想。毛声山为世无知高嘉之才的现状感到痛惜,并为他终将有永世之知己而充满信心:“屈于一时之无知己,而终当伸于数百年以后之知己。”[2](P.467)所以,他愿意“以今日之才许东嘉”。
金圣叹不仅因狂傲的性格丢掉了脑袋,他点评的《西厢记》也被后人目为怪文。正如徐世昌《晚清诗话》卷三十三所云:“明季钟伯敬、谭友夏诸人,评泊诗文,喜以诙诡之话,庸耳俗目,为之倾眩。圣叹扩而广之,上攀经史,下甄传奇小说,皆以己意评泊。数百年流传不绝。阳五伴侣,世以为贤,殆其类欤!”原来,金圣叹的评点,是蛊惑人心的一己之言。异族易主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敏感的士人宛如处在走投无路的穷境中,就会恸哭古代与现今、古人与我的分离永隔;就会恸哭我的孤零破碎,我为什么而存在、在荒谬中何处获得存在的痛楚。这就是金圣叹在评点西厢时的“己意”。他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中说道:“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我,不见古人。……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2](P.117-118)
在这段文字里,金圣叹提出一个无解的问题:古人是否和我的境遇一样?答案无处寻觅,所以他能做的,只是把他的感受、他的体验、他的视域记录下来。这正是金圣叹进行戏曲批评的内在动机。自认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的金氏,在评点中带有极强的主体性。从“恸哭古人”和“留赠后人”两则序文中即可看出,金氏主动将自身置于戏曲文本演进的时间序列中,兼任起体贴古人的“知音”与体贴后人的“知心”双重角色,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完成他阐释与传承的使命。
与金圣叹批评《西厢记》动机是为了安顿自我不同,毛声山批评《琵琶记》的动机,是为了重振元代这一戏曲典范的影响力。他认为同时代的人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琵琶》的妙处,流传的俗本中有很多错误。他认为天下最冤者,莫冤于古人之文被后人改坏,而以讹传讹,而《琵琶》正在遭受这种命运。所以他批评《琵琶记》的动机,就是要“一洗古人之冤”。因此,他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自序》中告诉人们,他深感《琵琶记》虽是绝世妙文,却缺乏善解之人,以故一般人虽是习见习闻,无人不知,无人不读,却是“未曾得读”,因此他衷心期盼与天下人“共读”该书。“采辑前人评语”,将王世贞、汤显祖、徐渭、李蛰、王思任、陈继儒、冯梦龙等几位明代《琵琶记》评者的批语一一列出,“以质高明”,形成一种古今对话的“批评空间”,以作为自己评论的基础与读者评量的参照。
金圣叹批西厢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崇情,认为爱情是天地间精气、日月中灵魂,男女相爱和相悦是其自然本性。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琴心总评》中云:“夫张生,绝代之才子也,双文,绝代之佳人也。以绝代之才子惊见有绝代之佳人,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必至之情也。即以绝代之佳人惊闻有绝代之才子,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亦必至之情也。”[2](P.159)
清初评点家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合评的《第七才子琵琶记》,对才子佳人之情持贬抑态度。他们认为《琵琶》有两点胜过,一是文胜,二是情胜。毛氏曰:“所谓文胜者何也?曰:《西厢》为妙文,《琵琶》亦为妙文。然《西厢》文中,往往杂用方言土语……。而《琵琶》无之,亦有似乎采风,则言不遗乎里巷,而歌雅则语多出于荐绅。……《西厢》之文艳,乃艳不离野者……文不胜质;《琵琶》之文真,乃真而能典者,……质极而文。”[2](P.465)原来,《西厢》文艳又俚野,文不胜质;琵琶之文,文真而能典,文能胜质。
毛氏认为《琵琶记》中的情感,胜于《西厢记》中的情感。所胜何处?他说:“西厢言情,琵琶亦言情。然西厢之情,则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约之情也;琵琶之情,则孝子贤妻敦伦重谊缠绵悱恻之情也。”[2](P.465)西厢之情有坏人心性之嫌,而琵琶之情则有养性之功效。毛氏认为琵琶之情最大的特点,是能动人但不妖人:“琵琶高人一头处,妙在将妻恋夫、夫恋妻,都写作子恋父母,妇恋姑舅。……此不淫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仪者也。”[2](P.484)它的特点就是平淡自然,这种美不事雕绘,意蕴深厚。它给人的感受是自然平淡,雅洁纯净。如果将《西厢记》比作是“风”,《琵琶记》则是“雅”;捧《西厢》而弃《琵琶》,这就像登风而废雅一样,毫无道理。总体看,毛氏认为:“《琵琶》歌曲之妙,妙在看去直是说话,唱之则协律吕,平淡之中有至文焉。”[2](P.472)毛氏认为《琵琶》是元曲不事雕琢、率直自然风格的集中体现,理应成为今天戏曲创造、欣赏的楷模。
二
清中期,花雅之争的深层,折射出的仍然是崇古与尊今之争。凌廷堪可以算做是崇古的代表。凌廷堪对当时传奇创作文辞化的现象极为不满,认为大批文辞之士“悍然下笔,漫然成编,或诩秾艳,或矜考据,谓之为诗也可,谓之为词也可,即谓之为文也亦无不可,独谓之为曲则不可”[6](P.193)。他一边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正本清源,一边期望通过批评时弊,使得戏曲发展重回正途。凌廷堪的复古与宗元思想主要体现在《与程时斋论曲书》。他以简洁峻朗的笔墨,将金元以来至清中叶古典戏曲的源流、发展及变迁,梳理得十分清晰,基本描摹出了古典戏曲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他认为不同的时代各有其代表的戏曲样式,但其体格每况愈下,即所谓“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他指出:“盖北曲以清空古质为主,而南曲为北曲之末流,虽曰意取缠绵,然亦不外乎清空古质也。”[7](P.24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凌廷堪一方面肯定明清传奇“意取缠绵”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尚元北杂剧而贱明清传奇的倾向。“自明以来,家操楚调,户擅吴歈,南曲浸盛,而北曲微矣。虽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而亡。何则?北曲自元人而后,绝少问津,间而作者,亦皆不甚逾闲,无黎丘野狐之惑人。”[7](P.193)究其原因,则在于凌廷堪认为元明清北杂剧作家度曲有法,而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数人虽热衷于传奇创作,却又不能真正按照戏曲艺术的特殊规律进行创作,结果使传奇创作虽盛而衰,失去了北曲原来的精神实质。他开出的药方是:“有豪杰之士兴,取元人而法之,复古亦易为力。”[7](P.240)即谨遵元曲规范,重倡元曲审美特征,主张言辞的自然本色,既不雕饰,又不鄙俗。
焦循充分注意到时代变迁和艺术走向之间的关系,他长期居于扬州乡间,远离统治阶级的趣味,不受传统崇雅扶正思想的影响,大量接触花部演出,这使得他成为拥护花部戏曲的代表性力量。焦循所生活的时代,雅部已不敌花部。一般的学士却固执地无视这种现实,继续视雅部为正宗,鄙视花部演出。统治者也表示惊恐不安,并严厉禁止大部分的花部演出。焦循却与上层观念相违拗,他认为花部应当与雅部并重,甚至更推崇花部。他在《花部农谭》中说:“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但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7](P.472)他还大胆断言:“彼谓花部不及昆曲者,鄙夫之见也。”[7](P.476)
关于推崇花部的原因,焦循说:“……盖吴音繁褥,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多男女猥亵,……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7](P.472)他分别从戏曲的文本层面、舞台演出层面、观众接受层面,比较了花部与雅部的特点,指出花部更有魅力。在《花部农谭》中,焦循将一些花部戏与雅部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其往往能超过雅部的作品。他称赞《铁邱坟》“妙味无穷”,比雅部的《八义记》高出许多,因为前者“嬉笑怒骂,好不热闹”,后者却只能“直抄袭太史公,不且板拙无聊乎?”[7](P.473)昆曲比较僵化板拙,缺乏创新能力,而花部则灵活多样,变化无穷。
焦循对于元曲的成就也持肯定的态度,但他通过考证戏曲的源头,发现了戏曲之本根,在于“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是优人与观众的密切互动。而且上古优人的这一技术,“于今无异耳”(焦循《剧说》)。也就是说,“今日”演员的表演技术,是上古之优的延续,是戏曲之本。焦循始终把戏曲当做是舞台表演的艺术,观众是否存在与喜爱,是戏剧的生命线。失去观众的戏剧,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他说:“……前一日演《双珠·天打》(昆曲),观者视之漠然;明日演《清风亭》(花部),其始无不切齿,既而无不大快,铙鼓既歇,相视肃然,归而称说,浃旬未已”。[6](P.476)不能动人的戏曲,说明一定是表演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能动人的戏,一定是它的表演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从这个观念看去,焦循自然得出了花部代表戏曲新的生命力的结论。
针对当时官方明令压制花部戏曲,提倡日趋贵族化的雅部昆曲,焦循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曲论观点。《易余龠录》记载:“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8](P.124)他将宋金以来出现的“曲”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演变中来考察,把元曲和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六朝隋的五言诗、唐代的律诗、宋人的词相提并论,并把戏曲家关汉卿等人与屈原、李白、杜甫并列,充分肯定了戏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一步,他认为花部是时代的产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为当时“曲之所胜”,积极肯定其应有地位。
焦循等人在内的大批经学家,在美学观念上己偏向尊今薄古。在学术思想中,焦循提出了“求通”“求变”学说,即以通达洞明、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他说道:“圣贤之学,以日新为要。”又说:“因事转移,随时通变,吾心确有权衡,此真义内也。”[9](P.746)焦循认为人能变通才性善,不能变通,性就不善。他还认为圣人之言是不定的,因为一时定的一些规制,后世不一定行得通。规制能定一时,但不能定千万世;能定一人,但不能定所有人。所以圣人也重视变通之学。这种求通、求变的学术思想,正是其孕育“代有所胜”戏曲观的关键。
三
清晚期,“崇古”与“尊今”这两股势力在国家的内忧外患中,失去了偏执一隅的锋芒。在国势飘摇和外来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出于民族身份认同与坚守的心理诉求,同一文化内部的各种矛盾成为次要矛盾。这导致戏曲批评领域里,持续了近两百多年的古今较量渐趋缓和。这一趋势在戏曲家杨恩寿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在《词余丛话序》中表达了他对“古”与“今”的认识:“古有乐,今亦有乐。古乐云亡,舍今奚从?而今日之乐,大而清庙、明堂、燕享、祭祀,小而櫵歌、牧笛、妇孺讴吟,凡有声音,皆可谓乐。以此为乐,则弟子可学矣。……以为古之乐,则吾不知,若今之乐,亦观止而不敢复请。”[10](P.525)古代的乐再好,但已遥不可及;今天的乐不管怎样,随处可得。古不可见,又舍弃现今,前路如何继续?杨恩寿选择重视现今的实绩,对“古”只是保留一些敬畏。
清中期的花雅之争,到此时胜负已明。雅部败落,不得不走向江南以外的地区,适应各个地方的本土化发展。杨恩寿则对花、雅不偏不倚,提出了著名的“戏不拘昆乱”的观念。他说:“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玺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11](P.17)他不仅重视对戏曲文本层面的把握,也极为重视戏曲的舞台效果。而雅部与花部孰优孰劣,关键就是一个表演的问题。只要场上表演好,观众欢迎,管它雅部与花部,都可以是好的。杨恩寿对演员的表演非常重视。如同治壬戌年四月朔日记评祥泰班首席演员喜红演的《吃醋》:“始则貌为恭敬,继则醉态逼真;迨返家时,恶语、怒语、忿语、浪语、亵语、骂妾语、咒夫语、讽叔语,千态万状,一时并作,而台下笑声不绝,即旁观之村姑闺秀,红女白婆,亦喝采焉。”(杨恩寿《坦园日记》)若舞台效果不佳,管它雅部与花部,都可以是差的。“不拘昆乱”,这体现了他把戏曲当作一种表演艺术来看待。在其所观看的戏曲中,像这样的剧作如《买胭脂》《调叔》《借妻》《拾镯》《挑帘》等,从题目上看,大多也都属于焦循所认为的“男女猥亵”的题材,但是杨恩寿则是从表演技艺的角度,或者从这类题材恰有的舞台效果来给以肯定,并不以道德的标准来横加约束。
杨恩寿好戏成癖,有大量的观剧经验累积,对昆曲和湖南地方戏的舞台演出都非常熟悉。在梧州三角嘴看到粤东天乐部在河岸演《六国封相》时,他赞叹的是以简陋的舞台演出这种百人登场的宏大场面,所不满意的只是以当地方言演出而难以听懂。昆曲经过数百年发展,自吴中流传到其他地域时,其声律不可能不作出适当改变,否则当地人无法听懂。对此,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提出了“不必拘拘工尺也”的观念。他认为古人制曲神明规矩,“无定而有定,有定仍无定也。”[10](P.531)但今天的人却不必如此:“诸律原可通,不必拘拘工尺也。”[10](P.531)昆曲传奇的创作,在吴江派影响下,历来强调格律的谨严,才情与法度发生了矛盾。杨恩寿提出“不拘工尺”是尊重戏曲发展现状的一种表现。作为湖南人,杨恩寿又酷爱花部戏,显然更难以按纯正的昆曲格律创作传奇,与其削足适履,不如不拘工尺,从这个角度看,杨恩寿的观点是比较通达的。
在杨恩寿看来,理想的作品是怎样的呢?我们且看他对李渔作品的评价:“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词余丛话》)一方面指出其浅显通俗的特征,认为“直拙可笑”,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佩服李渔在脚色安排、排场结构、插科打诨等方面安排极为巧妙。在杨恩寿看来,如果李渔在这些优点的基础上,再加强戏曲题材的历史厚重感,像王夫之、吴伟业、嵇永仁、尤侗等人那样,能够抒发深沉的历史感怀的话,就成为完美之作了,但是这只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
杨恩寿在《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中,原封不动地引录了大量李渔的曲论。他对李渔曲论中的“独先结构”“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等观念都有吸收 。杨恩寿以李渔戏曲理论为基础对戏曲作品进行评析,对于理论丰富而例证相对薄弱的李渔戏曲理论,无疑是一种发展。然而,他对李渔戏曲鄙俚无文、直拙浅显,是颇有微词的。杨恩寿对辞藻的要求,整体上是偏向于以汤显祖为圭臬,强调辞藻格调应高,反对俚俗直拙的词风。杨恩寿在评点曲文时,经常用到的赞语是“灵妙”“灵通”“慷慨”“高调”等,他对阮大铖的评价,可以说是他对辞藻要求的具体反映:“圆海词笔,灵妙无匹,不得以人废言,虽不能上抗临川,何至下同湖上。”(《坦园日记》)从这段评论看,杨恩寿认为“词笔”的最上者,是汤显祖;其次为阮大铖;而最下者,则是李渔。
清代戏曲批评史中出现的“崇古”与“尊今”的较量,不计异族统治对其的干扰,其实质是前现代与现代发生断裂的表现。中国的清代被认为处于早期现代性阶段,因为16世纪的社会情况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经验有繁衍延伸关系[12](P.24)。侯外庐把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形态归结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说:“在十六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13](P.179)关于清初启蒙的主题,学者指出主要有三个:祛魅、立人、改制。一些士人们不再沉溺于冥想,放弃鄙视形相的作风,转而求物物之理,注重实行;他们破除了经典独断论的理论根基,不再盲从。绝对之理开始被排斥,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和禁忌也被解除,使得独立自主的追求成为可能;他们开始对独裁专制统治合理性产生怀疑,民主观念初露端倪。万物由气一体化生的思想,也使他们有了初步的生命平等的意识。
现代性发生后,必然带来前现代与现代的分野,并预设了生活世界在现代时期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断裂是多方面的,但构成一切断裂的宏大基础则是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迅速消逝、或者更恰当地说,不是作为人类整体历史的突然中断,而是传统的精神理念、价值规则、思维途径,甚至包括传统的实在事物在本质上的转换和隐退。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的“恸哭古人”中,表达了他对这种断裂的体验。当一种延续性的传统信仰被中断后,一些人不能适应这种断裂,复古的思潮就会兴起,如尤侗、毛声山、凌廷堪等。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更加彷徨无依,他们企图通过重振元代戏曲的典范形态于当世,以此维护一种前现代的集体理性。但另一些人却迅速接受了启蒙,他们期望从传统的权威之下出走,这在李渔的剧论中有所体现。焦循以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念看待戏曲发展,正是其启蒙哲学思想在戏曲中的延伸。当然,像杨恩寿那样,停留在前现代与现代的界点上,注定了他的戏曲思想有点平庸、无力。
[1]刘建欣.明清戏曲宗元研究[D].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4.
[2]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3]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二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4](清)李渔.闲情偶寄[M].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清)尤侗.黄九烟秋波六义序[A].西堂杂俎二集[C].清康熙刻本.
[6](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C].北京:中华书局,1998.
[7]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8]任中敏编.新曲苑[C].北京:中华书局,1940.
[9](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四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11](清)杨恩寿.杨恩寿集·坦园日记(卷一)[C].长沙:岳麓书社,2010.
[12](美)乔迅.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M].上海:三联书店,2010.
[13]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Title:A Contest Between “Worshipping the Ancient” and “Advocating the Present”:an Evolution of Chinese Xiqu Criticism in the Qing Dynasty
Author:Huang Gui-e
Dur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Xiqu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over two hundred years,there was an evolution,that is,a contest between “worshipping the ancient” and “advocating the present”. “Worshipping the ancient” referred to reviving Xiqu in a stylistic form and emotional motif by tracing back to theoretic bases and elements in the Yuan Dynasty,the classic epoch of Xiqu;“advocating the present” referred to take the current “I” as the subject of artistic creation,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in Xiqu,which required Xiqu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 and conform to the current times. “Worshipping the ancient” and “advocating the present” as two opposing ideological forces manifested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social contex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The nature of their contes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fracture between the pre-modern and modern arts of the Qing Dynasty.
worship for the classics in the Yuan Dynasty;elegance and secularity;emotion and reason;the contest between local Xiqu and Kunqu
J80
A
0257-943X(2017)01-0076-09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