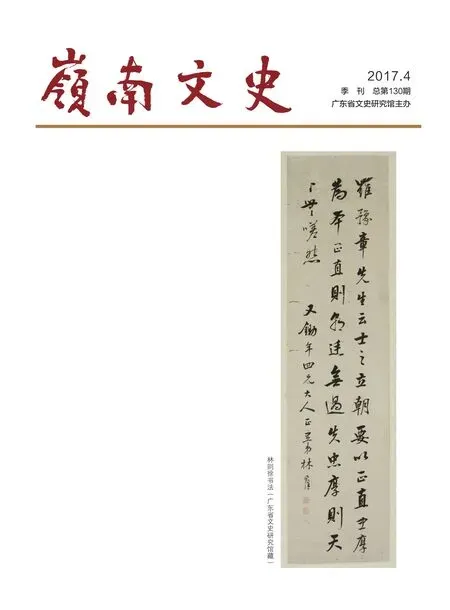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近代地理学史观探析
隋文丽 王 彬 司徒尚纪
梁启超被誉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术家。自从20个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不断深入,已取得丰硕成果,且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集中在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晚年政治活动、文化思想等方面。[1]但同时,梁启超也是一位近代地理学的引入者和倡导者,被誉为近代的地理史学专家。[2]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2)广东省新会县熊(音同泥)子乡茶坑村,卒于民国18年(1929)。他既是19世纪末的殿军,亦是20世纪初新史学的开创者。因此,在他身上既有着旧的封建社会思想的痕迹,也有着生气勃勃的新社会的敏锐思维,实为新旧世纪、新旧社会更替之际的见证。[3]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急需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下开展的“洋务”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和知识介绍进来,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走向衰落和终结。“其中以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和学术思想贡献最大,他以敏锐的目光、活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深入研究了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打破了沿革地理独占我国传统地理学主流地位,开一代新风。”[4]
一 对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引进和介绍
梁启超对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引进和介绍主要表现在人地关系方面,即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它是把自然环境当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据北京大学王恩涌先生研究,最早的人地关系见解是希腊学者希波拉底在其所著的《论空气、水和地方》中,提到的人的性格与气候关系。至十八九世纪时,法国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巴克尔对此论点作了深入解说。但真正把地理环境决定论系统研究和带来广泛影响的则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和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拉采尔深受当时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5]森普尔则在其所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一书对拉氏观点作宣传和系统发挥。最后使得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席卷全世界的理论学说。“不仅影响到地理学,而且波及到社会学及哲学等领域”。人地相关论思想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地理学思想,它强调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二者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较早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一生著述丰厚,共计1100万字。[6]而这其中的地理方面的著述(包括对西方具有地理学思想学者的介绍和在部分史论中涉及的地理学看法)却大部分都集中在1902年前后的廖廖十数篇。但是,就是在这不多的字里行间里却蕴藏着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端的巨大贡献。他杂糅了孟德斯鸠、黑格尔和巴克儿等人的思想,先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清议报》上发表《饮冰室自由书(第三)》,其中以《孟德思鸠之学说》为题,简要介绍孟德斯鸠的生平和政治学说,并涉及其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法律者,以适合于其邦之政体旨趣为主。不宁惟是,又当适于其国之地势及风土之寒热,又当适于其国之广狭,乃与邻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肥瘠,及民之所业,或农或收或者说商贾,各各相异。”[7]在这里看似梁启并未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作过多的评论和解释,但这里显然已涉及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大势论》等来阐述地理对历史、气候对文明的影响。在这里梁启超已集中阐述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并通过世界、亚洲和我国来具体分析地理对历史、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如他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8]在随后的《地理及年代》《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中,梁启超继续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给以介绍和阐述。但是在其引进和介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中,梁启超也并不是一味的推崇,而是有批判的吸收,注意到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以及相互间作用。[9]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而且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和生产方式,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并不起决定作用,关键是人类本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地理学界后来出现的人地相关理论。如他指出:“专从此(地理环境)方面观察,遂可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10]又指出:“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界限,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11]在这里,梁启超已明确提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改造环境”能力的相关关系。
总之,晚清率先运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研究地理学特别是中国文化地理的是梁启超,成就最大者也是梁启超,加之他出众的才华,和那支“常带感情”的神来之笔,使他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12]
二 发动维新运动,倡导和开展近代地理学教育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恰是中国社会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瓜分中国的过程,民族危机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为了救国图存,梁启超从爱国、救国的立场提出教育的重要性。“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极于教育。”而要办好教育,必须要有 明确的目的,必须知宗旨、择宗旨、定宗旨。没有宗旨,便无完备之教育;而没有完备之教育,则不能造就完备之国民。[13]为此,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引进来,梁启超向国人介绍了古代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和近代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的教育,以便从中取得借鉴,并要求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主办新式学校,按照西方的课程标准教育学生。事实上,根据赵荣先生的研究,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至清末,许多西方近代地理著作已被翻译、编著过来,国内也已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了国内地理学的发展,[14]国内一些有志之士也开始接受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此情况下,梁启超于1898年联合康有为发动维新运动,光绪帝于是年6月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在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高等学堂政科课程包括中外舆地课,由中外教授教习,学制三年。而且根据郭双林先生研究,晚清设立的各种学堂中,除个别专业外,地理学为普通学校的必修课程。其所用教材,虽有编有译,所讲内容,均主要以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为主。[15]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经学、文学、格致、农、商5科都设地理课程。1906年,清政府又制定《优级师范选科章程》,规定本科开设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各洲分论、地质、地文和人文地理等课程;预科每周要学习世界地理。以上规定,20世纪初陆续在有关学校贯彻执行。[16]可以说梁启超功不可没。
三 培养了一批地理学人才,编译和出版了一批地理学著作和教材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和倡导下,中国一些有志之士也开始接触和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的教育,参与到学习和传播过程当中来。1902年,光绪帝宣布变法不久,京师大学堂即“新政”措施之一,是年开办,规定设置舆地课程,这是中国政府正式规定在高等学校设置地理课程之始。并于是年起招收学生(师范馆79名,仕学馆57名)。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九年间,共有毕业生306名,未毕业生约230名,都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17]迨到《奏定学堂章程》颁行,新建改建学堂又再度兴起,至1909年广东全省新式学堂多达1694所,学生86437人,[18]其中大部分都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地理学教育。事实上,至1903年11月,清政府已被迫减少科举取士,改为以学堂取士。至1905年8月彻底废除科举后,全国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据当时教育部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学堂37888所,在校学生1024988人;至1912年,全国学堂又增至87272所,在校学生2933870人。另据中华教育改造社在1924年刊布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所载,至1907年为883218人,1908年为1144299人,1909年为1536909人。[19]同时,各学堂对地理教材的需求也迫在眉睫且数量不断增加,全国对地理教材的编纂和出版不断涌现。事实上,在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传入中国后,国内就出现了对此阐述的文章。根据郭双林先生的研究,在清末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中,明显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色彩的文章就达20多篇。而晚清编写的许多地理教科书中,尤以邹代钧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张相文的《新编地文学》、臧励龢的《新体中国地理》、谢洪赉的《瀛环全志》影响较大,且不同程度地带有地理环境论的色彩。[20]随后,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和1910年创办的《地学杂志》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总之,在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作为介绍和引进功不可没,特别是他对西方人地关系的阐述。一方面,他看到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看到了地理环境的优劣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用精神的力量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另一方面,梁启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不仅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性已有觉察,而且也初步看到了“改造环境”的“心力”,仍然要受到物质环境的制约。[21]尽管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还是较为科学、较为系统的,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还是非常突出的。[22]而更为宝贵的是在他们一批人的影响下,随后的晚清出现一大批致力于近代地理教育和研究的人才,为中国真正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注释:
[1]张衍前、于志国:《近年来梁启超研究综述》。载《文史哲》1996年第2期,第P94-99页。
[2][4][9]司徒尚纪编著:《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第71-78页,2003。
[3]廖菊楝:《试论梁启超方志观》。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哲社版)》,第32卷,2003年第2期,第P21-25页。
[5]王恩涌等编著:《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第48-49页,1995。
[6]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页。1986。而据台湾学者张朋园说:梁启超“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百万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绪论》第3页)。
[7]转引司徒尚纪编著:《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第73页。
[8]《饮冰室文集》之六。
[10]《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
[11]《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
[12]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2000。
[13]《饮冰室文集》之九。
[14][16]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第7-9页,1998。
[15][20]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3、58页,2000年。
[17]熊宁;《本世纪前半叶我国近代地理教育初探》。载《地理研究》,1987年第1期。
[18]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59页,1993。
[19]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271-272页。
[21]钟珍维、万发云著:《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第119页,1986。
[22]曹诗图、王衍用:《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与其学术思想》,载《地理科学》,总16卷,1996年第1期,第P5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