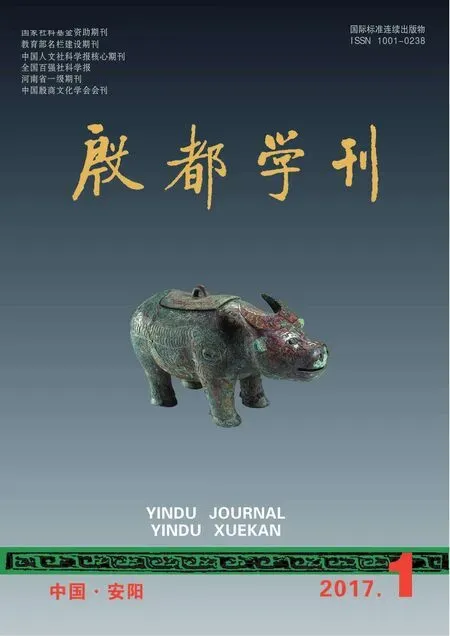从小林形象塑造看刘震云的胸襟与气度
焦会生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从小林形象塑造看刘震云的胸襟与气度
焦会生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刘震云通过小林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出他艺术创作的胸襟与气度,即同情并理解小林之异化,“反讽”并“抗议”造成小林异化的现实环境。这种胸襟与气度和现代启蒙者“狂人”与古代士大夫精神相比,还远不够雄远和高逸,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小林;刘震云;胸襟;气度
小林是著名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奉献给当代文坛的为环境压抑而异化的知识精英典型形象。它诞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深切的关注,尤其是被著名导演冯小刚以“一地鸡毛”为名搬上银幕以后,更是引起广泛的重视。深入研究其形象特征并由此探究作者艺术创作的胸襟与气度,对于研究当代作家的责任与使命不无裨益。
一、小林形象特征
小林是刘震云在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精心塑造的知识精英典型形象,是一个被恶劣的现实处境所异化而走向平庸的堕落者和妥协者,是一个丧失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而遁入俗世的随波逐流者和混世者,是一个为日常琐事磨蚀而日渐变得心灵沙漠化的薄情者与冷漠者。
首先,小林是一个屈从于现实环境而逐步放弃自我个性而走向平庸的堕落者和妥协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为了入党,为了升官,他被迫放弃自己的自由个性,而违心地融入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现实环境,以期达到自己改善生存处境的目的。
在《单位》里,小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国家机关做了一名小公务员,成了国家体制内的一分子。他原本是一个孩子气十足,自由惯了的人,以说话随意、行为不拘而著称。然而,在“单位”里一切都是以“官”或者说“权力”为本位的。个人生存条件的优劣,人生的荣辱浮沉,均围绕着“官位”和“权力”而旋转,“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在单位混得如何,升官成为人们竭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因此为了升官,人们在这里使尽各种招数,什么巴结奉迎,什么尔虞我诈,什么投其所好,什么投机钻营……应有尽有。在这种环境里,小林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适应并学习这里的一切。“从此小林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他虽然十分讨厌女老乔,但女老乔是党小组长,掌管着他入党的事情,为了入党,为了升官,他“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和她的狐臭,夏天再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日一次挨着她的身子和她谈心”;他虽然极不情愿帮刚升为副局长的老张搬家,但还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甚至还积极主动地为张副局长家刷马桶、倒垃圾桶。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提级、升官、改善生存条件的目的。正如他对老婆所说:“我何尝想帮这些王八蛋搬家?可为了咱们早搬家,就得去给人家搬家!” 可见,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主动地克制自己的个性而违心地去适应现实环境,成了一个堕落者和妥协者。
其次,小林是一个迫于生活重负逐步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而日渐融化于庸俗不堪的尘世的混世者。如果说《单位》侧重描写“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对人所产生的磨损与销蚀力量,那么,《一地鸡毛》则着重描写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精神磨砺与变化;如果说《单位》着重表现工作环境对小林自我个性的侵蚀,那么《一地鸡毛》则着重表现家庭生活环境对他个性的磨损。这种磨损更渗透进他的私人生存空间,使他在更本己的层面上彻底摈弃自我意识。[1]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也是小说描述的第一个故事。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琐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鸡毛小事”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房子、孩子、蜂窝煤、保姆、老家来人、爱国菜等等。对所有这些琐事的叙写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一地鸡毛”由此成为这篇小说最为突出最具特征性的审美意象。“一地鸡毛”这个意象深刻揭示了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人为无数日常生活琐事所拖累,所异化,形成令人无可奈何的“烦恼人生”。这些生活琐事造成了对人的最大磨损。正如作者所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2]这些一地鸡毛一样的日常生活琐事,无不渗透着某种社会权力关系,无不证明着小林的“没有本事”,无不磨蚀着知识分子公务员小林的个性。
小林与无数大学毕业生一样,“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不放在眼里”。但参加工作步入社会之后,每天奔波在单位、家庭两点一线之间,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为房子发愁,为滴水偷水脸红,为孩子入托求人,为老婆调工作送礼……他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在无数的摸爬滚打中,难以有机会从容地听从于内心,而不得不坠入到无边的生存网络之中,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1因而书也不想看了,世界杯足球赛也不能看了,理想抱负也化为泡影,故而“很快就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从而认同了大学同学“小李白”“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的观点,“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最终得出结论:“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可见,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被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1]
再次,小林是一个为日常琐事磨蚀而日渐变得心灵沙漠化的薄情者与冷漠者。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的磨损之下,心灵日渐沙漠化,精神世界日渐萎缩,变得冷漠而无情。当看到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小学老师的死讯时,他难受了一天,可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就把老师给忘了。当查水表的瘸老头央求他办批文时,“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最终,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在收受了查水表老头的贿赂后,就把批文给办了。小林由此得到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加入其中”就是不仅认可了原先自己所不耻的行为,而且放弃了自己的操守和理想。“小林感到就好象是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物质生活生存空间狭窄,物质资源贫乏,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因此人们渴望改善生存状态,而在这种“渴望”之中致使小林这个典型人物由一个思想单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转变为失去理想和操守,心灵日渐沙漠化的小市民。
总之,小林是一个为外在环境所挤压、所剥夺、所磨损、所销蚀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形象。其成长过程,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变异的过程。随着他的成长,他逐渐丧失独立个性和远大理想,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与担当,丧失公务员所应有的表率示范作用,而一步步混入小市民之间并成为平庸世俗的混世者。由此形成了小林的悲剧命运。
二、作者叙述立场
那么,对于小林这样一个悲剧命运,作者刘震云是持什么态度呢?或者说他的叙述立场是什么呢?
首先,作者对小林的悲剧命运充满了同情与悲悯。无论是《单位》还是《一地鸡毛》,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小林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悲悯。小林是从农村考上大学进到城里并进入国家机关的小公务员,由于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且无权无势,所以生活状态十分拮据。从在单位里“打水扫地”的地位,到日常生活中的“二等公民”的感觉,从“分房难”,到“调动难”、“入托难”,无不体现出作者对小林生活艰难的同情、理解与悲悯。
作者之所以这样,我们应该从他的人生经验和体验中去寻找原因。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清代学者王夫之也说,任何作家创作都有一个“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铁门限”,[3]郁达夫认为“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的”。[4]这些论断说明,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以其所熟悉的生活为蓝本的。刘震云这位来自河南民间的著名作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苦难有着极其深刻的体验”,[5]对权力给人造成的压抑与伤害深恶痛绝。这一点在他的《塔铺》、《新兵连》、《头人》、《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中多有表现。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河南籍作家,如周大新(《向上的台阶》)、阎连科(《瑶沟人的梦》、《黑猪毛白猪毛》)、刘庆邦(《新房》)等一样,感受深重。就《单位》和《一地鸡毛》来说,也是这样,刘震云与小林一样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刘震云和小林都成长生活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从农村考上大学,留在京城,且进入体制内工作。因此,他真切地描写了小林的奋斗史,挣扎史,并声称小林的“见识相当了不起,我是把他当做一个英雄来写的”[6]。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小林身上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看到作者对小林的同情、理解与悲悯。
其次,作者对造成小林悲剧的社会环境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抗议”。[7]在作者笔下,小林虽为大学毕业生,虽为小公务员,但其物质生活条件或说满足生存需要的基本条件与普通市民一样窘迫。在《单位》中小林由于住房逼仄、工资微薄、人微言轻,几乎举步维艰,由此意识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分量,为此他不得不谋求在单位里提级长工资,不得不改变从前大学生的自由脾性,向过去深恶痛绝的世俗关系下的人与事低头,进而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毫无自我特点的小市民。《一地鸡毛》基本上承续了这个思路。只不过“单位”里的生存压力扩展到整个生活中去。为了老婆工作调动得去送礼,为了孩子入托得去求人,为了孩子上幼儿园得给阿姨送炭火……老婆单位通班车是沾了人家单位头头小姨子的光,孩子入托是沾了“对门‘印度女人’的丈夫”的光,自己像个“二等公民”,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龌龊……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权力体系对人的压抑与制约。小林就是在如此的摸爬滚打中,不得已而坠入到无边的生存网络中,从而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滑向平庸和贫瘠,生存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过程。
刘震云运用冷静客观的叙述,活生生地勾画出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处境,揭示出这处境的荒谬。小林的沦落是当时那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小林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反映了那时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困窘的生存状态。生存空间逼仄,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除了权力体制的压抑之外,人们还要受到诸如吃穿住行的羁绊,因而人们对改善生存环境提出了强烈要求。刘震云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切,从而揭露并抗议了现实环境的恶劣。这种揭露与抗议“来自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绝望”[8],由此也就意味着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艰难的保持。
总之,刘震云对小林的悲剧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对造成其悲剧命运的现实环境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抗议,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三、由小林看刘震云的胸襟与气度
胸襟指志趣、抱负等;气度指气魄风度。在这里是指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境界。刘震云通过小林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出他艺术创作的胸襟与气度,即同情并理解小林之异化,“反讽”[9]并“抗议”造成小林异化的现实环境。
小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公务员,其胸襟与气度怎么样呢?概括地讲,小林既没有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更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是缺少雄远高逸的胸襟与气度的。
首先,小林作为生活于二十世纪后期的知识精英,与生活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狂人”(鲁迅《狂人日记》)相比,在胸襟与气度上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狂人”作为“人国”理想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以其历史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深刻的虚无感和痛苦而清醒的罪人意识,完成了“五四”时期奋发扬厉而又苍凉绝望的中国式启蒙者的角色定位。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使得普通民众视之为“狂人”;而小林则在“官本位”和“金钱”本位的双重围困中,放弃理想,一步步把自己混同于普通民众,丢失“启蒙精神”,最终“加入其中”,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10]当代著名作家方方曾经描写了三代知识分子形象,第一代有节操,有气节,有担当,正义凛然;第二代屈服于外在压力而放弃理想,被迫丧失个性与操守,变得浑浑噩噩;第三代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自动放弃理想,拥抱现实,成了地地道道的小市民。鲁迅笔下的“狂人”与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不正是这第一代和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吗?因此,与“狂人”相比,小林是一种蜕变,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退步。
其次,小林作为知识精英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相比,缺少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融合。孟子曾经强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1]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志向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12]可见,像孔子、孟子那样胸怀家国,寄情天下,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才是大胸襟,大气度。在小林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胸襟与气度。
对小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的作者的胸襟与气度自然与小林相近。正如他七十多岁的小学老师对他所说的,你写的书不如孔子写的书,“差在胸襟气度”。[13]
如上所述,作者精心描绘了知识精英小林被异化的悲剧,同时把小林异化的原因归结于现实生存环境,并过分强调了知识精英异化的被迫性,过分强调了外在环境对人性的挤压与塑造,从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环境对人的制约固然重要,但人自身的选择与追求更为重要。正如文艺复兴时哲学家乔万尼·比科·米兰多拉在《人类尊严论》中所说,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赐就是选择的自由与独立的意志。下至禽兽,上至圣人,人无所不能。[14]关键在你怎么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环境而放松对人自身内在修为的重视。对作家来讲,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15]“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16]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刘震云曾说道:“我不是那种要坚持什么,不妥协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帮别人指出道路的作家……”。[17]他还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17]这些自白可以看出他的胸襟与气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有许多评论家在评价刘震云时都充分肯定他对现实的反讽和抗议。比如:“刘震云是一位把中国文学传统中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艺术和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暴露艺术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兼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的反讽意味的小说家。”[18]又如:“刘震云的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世俗冲击的各种变化,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面对世俗压力从抗拒、挣扎到屈从、沉沦的姿态变化,从而揭示出他们身上传统人格理想的消隐与消解,呼唤着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理想的重建。”[19]再比如:“他对物质至上和权力至上的抗议,意图即在构建人的精神的存在”。[7]反讽、抗议和呼唤并不是引领与重建。“放弃了对知识分子崇高的心路历程的追述,只是着力于刻画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19]只能是作家精神的迷失与消隐。
作家不仅要揭示与抗议,更要引领与构建。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0]习近平同志殷切希望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21]刘震云自己也说:“我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不仅是过去和现在,更应该是未来,他们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共同聚焦,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22]我们相信作者能够提升自己的胸襟与气度,把这个创作理念落实到他的创作中去。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13-317.
[2]刘震云.磨损与丧失[J].中篇小说选刊,1991,(2):88.
[3]王夫之 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4]郁达夫.达夫日记集·日记文学[Z].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四年版. 1.
[5]姚晓雷.刘震云论[J].文艺争鸣,2007,(12):122-132.
[6]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J].名作欣赏,2011,(5):92-98.
[7]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4):44-56.
[8]陈思和,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J].作家,1994,(10):69-74.
[9]陈晓明.漫评刘震云的小说[J].文艺争鸣,1992,(1):69-72.
[10]杜玉梅.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J].东岳论丛,2006,(5):193-194.
[11]孟子.孟子·梁惠王上[Z].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12]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润州谢上表[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90.
[13]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J].名作欣赏,2011,(5):92-96.
[14]麦吉尔 王志远.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散文[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1453.
[15]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
[16]王充.论衡·别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22.
[17]张英.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N].南方周末,2004/02/05.
[18]於可训.小说家档案[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346.
[19]苗祎.传统人格理想的消隐与重建——论刘震云小说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4):147-149.
[20]鲁迅.鲁迅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59.
[21]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30/c64094-28915395.html 2016年12月20日访问.
[22]刘震云.文学梦与知识分子[J].甘肃社会科学,2013,(5):9-12.
[责任编辑:舟舵]
2016-12-01
焦会生(1961- ),男,河南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7)01-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