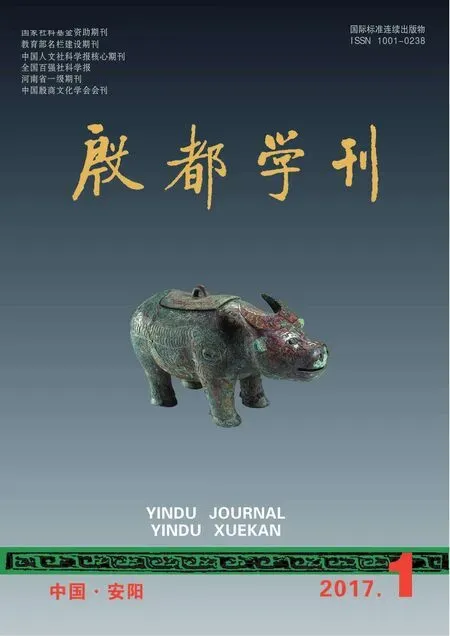中原作家群新论
何 弘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中原作家群新论
何 弘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中原作家群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庞大创作群体,大致包括两类作家,一类是坚守在河南本土的作家,一类是生活、工作在外地的河南籍作家。中原文化氤氲了河南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而中原作家群在文学创作中则形成了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注重对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基调,在题材上则以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为基本内容,在表现上则以厚重而风格多样为基本特点。
中原作家群;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儿童文学
中原作家群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庞大创作群体,大致包括两类作家,一类是坚守在河南本土的作家,一类是生活、工作在外地的河南籍作家。就目前仍然活跃的作家来说,坚守在河南的有田中禾、二月河、李佩甫、郑彦英、张宇、邵丽、乔叶等,而北京等地发展的则有周大新、刘震云、刘庆邦、朱秀海、阎连科、柳建伟、李洱、梁鸿等,都在全国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发端后的30多年时间里,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省曾涌现出了一批包括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周作人等在内的文学巨匠,可以说浙江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原作家群的兴起与壮大差不多是一个可以和浙江作家群在现代文学史上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论活跃作家的数量、创作成就以及实力和影响,鲜有地域性创作群体能与之匹敌。
对于中原作家群的兴起,在直观的理解中,通常认为源于中原文化的博大深厚。的确,中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核心在此形成并逐渐向外辐射。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到东北、北方、南方、西北、西南、岭南、塞外这些概念的时候,隐含的前提即是对中原中心地位的肯定,其中不仅有地理意义上的认知,也有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认同。然而,如果文化的源远流长就可以保证文学的繁荣的话,何以中原在南宋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学一直处于低潮呢?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宋以后中央政权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冲突,谁能解决好这对矛盾,就能够实现对中国的统治,于是政治中心向北偏移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处的北京一带;而南方随着中原文化的进入,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并因较少经受战火和自然灾害而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于是,中原虽处于地理上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反倒从中心退居边缘。加之理学的兴起对文学的压制,中原渐成理学重镇而文学渐趋萧条。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这个时期俗文学兴起,戏剧、小说繁荣,而原本处于重要地位的诗文写作则在今天书写文学史时不再被重视。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今天去看待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时,感觉中原文学处于低谷之中。
与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失去相伴随的,是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战火的不断蹂躏。从宋金对峙开始,拉锯式展开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政权争夺,中原每次都是主要战场,加上黄河的屡次泛滥改道,使苦难成为中原人最基本的人生体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中原自古以来都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区,儒家文化特别是更深传统的长期浸润,使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套微妙而复杂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而战争的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的一次次逃难等,又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有着丰富的故事性。像边关大漠这样的地区,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给人的感受通常相对直观而强烈,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诗情,比较适合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表达。而中原这样文化传统深厚、人际关系复杂、故事丰富的地区,则为小说发育提供了肥沃的优质土壤。李敬泽2017年2月25号在接受河南日报“中原风会客厅”采访时谈到,河南作家在说起自己和身边人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一次平常的聊天,他们都会讲得极富故事性、趣味性,他们是天生的小说家。李敬泽的话虽然带有些调侃的意味,但某种意义上确实揭示了河南小说繁荣的内在成因。
长期的苦难体验,长期的不屈抗争,使河南人形成了直面苦难、坚忍不拔的生存态度,同时又不可避免形成了机智以及狡黠投机的性格。这使得河南人面对苦难时既有勇于正视,顽强不屈的一面,又有善于变通以求生生不息的一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河南人特有幽默和坚韧,他们敢于自嘲,甚至敢于自黑。据说很多讽刺河南人的段子实际上都是出自河南人的创造。而这样一种能够直面苦难、笑对苦难、敢于自嘲的河南人,往往在土气的外表和略带自卑的心态下,有着一种内在的大气和厚重。
河南人的这种性格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就是形成了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注重对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基调,在题材上则以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为基本内容,在表现上则以厚重而风格多样为基本特点。这样的创作特征从中国新文学发端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像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师陀的《果园城记》、姚雪垠《长夜》到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乔典运的《无字》《满票》、田中禾的《匪首》、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张宇的《疼痛与抚摸》以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第二十幕》、刘庆邦《遍地月光》《黄泥地》、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都是如此。这样的创作特点也延续到了更年轻一辈作家的身上,比如李洱,虽然以先锋写作的姿态步入文坛,在叙事探索上走得很远,但他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关切和对价值与意义的追求。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乔叶的《拆楼记》《认罪书》等同样表达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梁鸿则通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等反映了当下农村普遍的现实。
新时期以来,中原作家群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态势,但创作并非不存在问题。特别是前些年,一些年轻作家在父辈作家巨大身影的笼罩下,失去了自我,以为重复李佩甫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就可以取得成功。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年轻作家的创作,仍然以农村现实为基本描写对象,但其写作无非是在重复前辈作家的经验,与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其实已有了很大的隔膜。这成为一些作家难以很快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近几年来,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一批年轻的作家在继承中原作家群优秀传统的同时,表现出了新的特点,逐渐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6年,河南省文学院根据当下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选取安庆、尉然、宫林、张运涛、赵文辉、李清源、陈宏伟、南飞雁(以出生年月为序)等八位小说家集中进行研讨,名为“中原八金刚”。参加会议的评论家陈福民、张燕玲、李国平等对其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当然,河南活跃的年轻作家不只这八位,比如专业作家赵大河、赵瑜等未包括在内,女作家未包括在内。
八位作家中,南飞雁是“八零后”,但表现却相对成熟。他的写作主要以机关普通公务员为描写对象,表达他们面对复杂人际关系时微妙的内心体验和生存现实。虽然是“八零后”作家,南飞雁的创作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显然有着很大区别,他的写作表现出了一种与其年龄不对应的成熟。南飞雁写作其实起步很早,他大学时代即以长篇写作步入文坛,并连续创作了多部作品。但此后他及时调整节奏,放慢了脚步,开始扎扎实实进行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量虽然不大,作品质量却有了极大的飞跃,开始真正被文坛认可。
相对于南飞雁的“少年老成”,安庆要算是“大器晚成”了。他早先以小小说写作起步,但引起广泛关注却是转入中短篇写作以后的事。他前几年的《加油站》,近年来的《扎民出门》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安庆是年轻一辈作家中少有的注重语言美感的作家,而且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细腻独到,对人物内心的揭示深刻敏锐。
陈宏伟和李清源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两位年轻作家。仿佛是忽然之间,他们即以各自颇具才情的写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陈宏伟的写作主要表现的是豫南小城的普通人物,他以其对人情世故和人性的深刻体察,使看似普普通通的生活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味。比如他获得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的《一次相聚》*本文对几篇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作品的评价使用了由本文作者最终定稿的该奖授奖词的一些说法。,即通过同学聚会这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以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生动描写,对人物外部言行与内心真实相扭曲的精准表达,呈现了当代人内心的焦灼、匮乏及隐秘的渴望,对人性的挖掘深入独特,结构布局精妙,人物感情真实饱满,显示了深厚的叙事潜力和超拔的文学才华。 李清源的写作则更多对命运的探究和精神的探索。其获得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的作品《苏让的救赎》,在小人物物质、精神、情感、甚至命运的不可解脱的尴尬中,深味体察、倔强叩问生存逼仄的诸般缘由,又以天真慈爱、温暖宽谅之心观照世人,寻求让人栖居身心之处所,表现出作者异乎寻常的冷静态度和敏锐直接切入社会人心深度地带的能力。
同样来自周口的尉然和宫林,都以写农村生活见长,但作品风格却大异其趣。尉然的作品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他在对生活夸张以至荒诞的表现中,对农村生活的现实和底层人的命运做出了有力的表达和深刻的揭示。而宫林的写作则更为质朴,他更多是以正面强攻的姿态来真实表现农村生活的现实和生活在其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相对而言,宫林的写作更多带有河南前辈作家的表现特征。
张运涛的写作相对而言不那么拘泥于题材的限制。他的写作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相对突出,一个是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表达相对真实而准确,一个是善于讲故事。这两个特点使张运涛的写作相对来说较为顺畅。也正因此,张运涛的写作不是那么着意于社会宽阔度的把握,更多是对个体的深入把握。
赵文辉是一位浸淫小小说多年后来转入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对农村现实的洞悉与表达是其小说写作的基调。第二届杜甫文学奖评选中,赵文辉以其小小说集《苦水玫瑰》而获奖。虽说是小小说集,但其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内容与表现特点也大体如此。其创作更多是其对底层生活的洞悉而做出了扎实的表达。赵文辉的写作非常朴实,但朴实其实也是一种力量,它常常能让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变得动人心扉,具有强烈的感染能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原八金刚”之外,赵大河这些年在从事电视剧、话剧等剧本创作的同时,写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个人意识和表达能力来说,赵大河是相当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注重叙事的先锋文学精神在赵大河这里仍然有着鲜明的体现。第二届杜甫文学奖,赵大河以短篇小说《浮生一日》而获奖。《浮生一日》在想象性叙事中穿插对人物的现场寻访,在虚构与现实的交错中,通过冷峻利索的叙事展现了动荡时代中个体命运不可预测的悲剧性,揭示了个体生命和大时代之间看不见的关联,表现出对历史与个体命运间关系的智性理解,以及对叙事艺术的高度追求。
赵瑜的写作相对来说则显得更为轻巧。其表现特点是常常从日常生活细小的切口入手去表现当下人物的生存和心理状态。获得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的《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是这样一篇作品。作品值得称道在于他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揭示。
而女作家孙瑜,更多以女性的视角关注生活,作品的表达相对轻盈。其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的小说《危险时请敲碎玻璃》通过丰盛而敏锐的直觉逼近生活中的人心本相,表现了当前高校知识分子紧张而难以言喻的种种压抑和无奈。视角独特、构思巧妙,是孙瑜写作的特点。
此外,更年轻的作家如张艳庭、尚攀、智啊威、墨柳等也都开始显露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
长篇小说这些年河南各地都不断有新作问世。除专业作家的创作之外,历史小说依然在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中程韬光以其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的持续书写而引起关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有很多,但总体而言,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年轻作家还为数不多。
河南是小小说创作的重镇,拥有一支庞大的小小说创作队伍。近年来张晓林以其笔记小说创作引起关注。其描写宋代书法家群体 的 《书法菩提》荣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作品通过对宋代书法家群体的全面描写,生动、鲜活地塑造了一系列立体、成长的人物形象,在还原宋代历史场景的同时,揭示了至今不变而又复杂微妙的人性,表现出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韵味,作品继承中国笔记小说的精神气质,使笔记小说在现代背景下重新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书法菩提》之后,张晓林又创作了《夷门民国书法人物》系列。
河南的散文写作这些年也相当活跃。除王剑冰等专业散文作家之外,不少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也都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更可喜的是,近年来,河南有一批年轻的散文写作者崭露头角。第二届杜甫文学奖,散文类获奖的就是三位以前很少被大家关注到的写作者。阿慧的《羊来羊去》通过对乡村种种不同场景及其中人和事的扎实描写,表现了乡村文化朴实而有温度的真实,人与物之间不分彼此共同生活着的欢乐与痛楚,在字里行间中流溢出作者的心境身影,使作品氤氲出一种浸人心脾的气韵和感人的力量。韩晓民的《民间记忆》以真正民间记忆的方式记录了正在延续也正在消亡着的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乡俗生活,表现了中原农村民间文化的原始面貌和普通生灵的淳朴状态,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写作功底和厚实的生活积累。叶灵的《秦淮水骨》通过对一些历史文化片段带有生命感受和当下印迹的描写,散发着女性特有的人性温度,是历史文化个案面前个体的心灵回声,显示出一种宏阔悠远之美和与历史文化对话的乐趣。而纪实类获奖作品,如陈峻峰的《闽南纪行》,青青的《落红记》等其实也可以归入大散文的范畴。《闽南纪行》以当今中原文人的视野来考察祖辈南迁的历史及其对于闽南文化生态形成带来的影响,并关注了在大地上繁衍生息的仍然在迁徙之中的人群,表现了作者阔大的胸怀、气度以及重新面对历史和传统时的智慧与勇气。《落红记》基于个人视角审视萧红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知识女性,对其一生的考察蕴含着对于近百年来女性命运的思索,作品生动、细腻,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起来,成为民族文化现代进程中的一面镜子,闪现着映照未来的精神之光。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胡亚才的《水的血脉》,作品通过对家乡风土人情的书写,表现出一种浸润于血脉中的精神追求。而河南众多散文作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冯杰的写作,这位诗书画俱佳的写作者,在对一花一草一食一物的信手书写中,使作品充盈着盎然的诗意和别样的意味,很可欣赏把玩。
河南的诗歌创作形成了郑州、信阳、平顶山、周口、开封等多个群体。在河南的众多诗人中,蓝蓝之后,扶桑表现得非常突出,她更多通过日常的生活意象书写个人的内心生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而第二届杜甫文学奖获奖的三部诗集,高金光的《人间呼吸》以本色而深切的笔触,写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在被拔根的过程中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通过对临终母亲在故土和新土之间催人泪下的两难表达,表现了作者移民之子的诚挚情感,最终完成了对于时代生活深处个体命运无愧于故土和历史的表达。温青的《天堂云》从宏大的时空观中看待灾难,在极端情境中表达对世界万物的温煦理解,是对于灾难的肃穆和神性表达,具有明亮、温暖、向上的品格和神性、诗性的灵光,是一部厚重的心灵之作。吴元成的《花木状》以诗人的敏感、植物学家的认真,对北方常见的各种花木完成了带着诗人独特的生命记忆与体温的诗性表达,使常见的花木在诗人灵动、闪回、机智的笔端,呈现出新的姿容和意味,表现出诗人对自然、人文和时代生活深入而独到的思考。
儿童文学方面,孟宪明以其《念书的孩子》《青石臼》《花儿与歌声》持续书写着农村儿童,引起了广泛关注。肖定丽也屡有佳作问世,同时周志勇、潘红亮、韩宏蓓、原草等也开始引起关注。
特别需要提起的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这里主要是指网络类型小说写作,目前我省的庚新、度寒、高阳、苏迷凉、九哼、豫西山人等都相当活跃。但相对而言,与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相比,我省网络作家中的大神级写作者还相对较少。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文学评论在多年相对沉闷之后,近年来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河南省文学院与信阳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院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主要针对中原作家群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成效显著,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一批高校年轻老师的加入,使河南的文学评论出现了新的气象。
作为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创作群体,中原作家群在不同的时代贡献出了不同的优秀作品。在今天这么一个以文化的繁荣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原作家群理应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使中原作家群保持其持久的辉煌和荣耀。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原作家群依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舟舵]
《殷都学刊》作为河南为数不多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地处中原大地,有责任和义务为河南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016-11-26
何弘(1967—),男,河南新野人,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7)01-0028-05
编者按: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河南文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起着引领、主导的作用。宋以后,河南文学的地位渐趋边缘化,但是其中的文学传统、文学精神并没有间断,一直绵延至今,并经过现当代河南作家的卓绝努力,“河南豫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当前,地域文学研究蔚然成风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河南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河南的文学研究却略显不足,尤其是专门研究河南文学的载体更是少之又少。
由河南省作家协会和《殷都学刊》共同开设的“河南文学研究”,旨在展示河南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挖掘河南文学的宝贵资源,促进河南文学的快速发展,提升河南文学的整体形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个研究河南文学的平台,为河南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提供一块学术园地。愿这块园地成为河南作家的朋友,河南文学研究的沃土!
——以广西高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