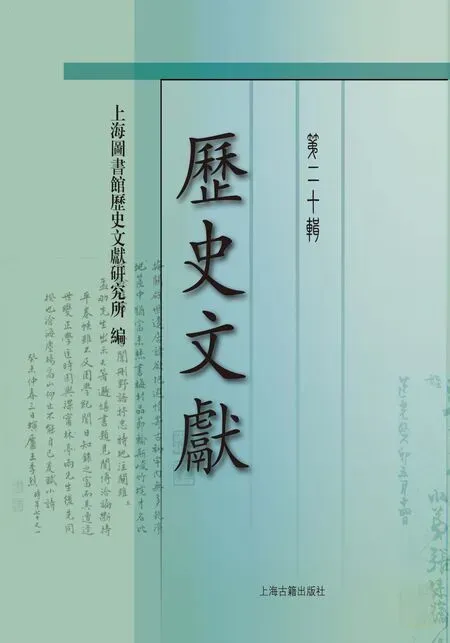遯堪書題
□ 張爾田撰 王繼雄整理
《遯堪書題》者,錢塘張爾田先生讀書題識之彙册,由其門人王鍾翰輯録成帙,其顛末王氏於卷前識語中述之已詳。書總一册,以“念黄手鈔”藍格十行稿紙抄録。封面有鄧之誠簽題:“遯堪書題 王鍾翰手鈔本 戊寅十一月之誠署。”鈐有“鄧之誠”朱文方印。卷首依次有王季烈、郭則澐、余嘉錫三家親筆題辭,其中王氏題辭後鈐“王季烈印”白文、“君九長生”朱文兩方印,余氏題辭後鈐“余嘉錫印”白文、“季豫”朱文兩方印。
又是册首頁鈐有“龍沐勛印”白文、“忍寒詞客”朱文兩方印,卷端又有“榆生珍藏”朱文方印,則此册最終歸藏龍榆生。按張、龍二人雖年齒相懸,但忘年相交十數載,情誼匪淺。①兩人於詞學頗多切磋,張對龍青眼有加,有以身後文字託付之意,②則張氏於此册所録重加校訂後逕付龍氏,或即意在託其理董,如此推測,或爲不妄。
張爾田早歲以詞章名,後潛心研學,頗有造述。《書題》收録張氏讀書題識三十七種,凡二萬言。所録各則,雖屬讀書時“信筆及之”,“頗多傷時之語”,但談藝論世,文采斐然,其於明季清初史事考訂諸條,旁徵博引,更見精審。
王氏鈔竣此書,時在民國二十七年,即以全文發表於《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五期,名曰《張孟劬先生遯堪書題》。校諸鈔本,排印本無王季烈等三家題記,蓋發表在先,諸家題辭在後,亦未施標點,惟《跋吴注梅村詩集》諸條,以落款日期先後排序,較鈔本之淩亂爲勝。
《書題》發表後,張爾田復親筆於此册重行校改增補,故是册可視爲張氏書題的修訂定稿。
今據上海圖書館所藏《遯堪書題》王鍾翰鈔本加以標點,張爾田校補文字均增入相應各條,卷前諸家題辭一併迻録,要以全帙呈覽同好,庶免遺珠之憾。
掩關辟世遣居諸,欲把遐情寄古初。宇内無多乾浄地,篋中猶富未焚書。梅村品節輸斯峻,竹垞才名比有餘。往事宫闈删野語,抒忠特地注《關雎》。
孟劬先生出示大箸《遯堪書題》,見聞博洽,論斷持平,卷帙雖不及《困學紀聞》、《日知録》之富,而其遭逢世變,正學匡時,固與深甯、亭林兩先生後先同揆也。滄海塵揚,高山仰止,不能自已,爰賦小詩。 癸未仲春三日,螾廬王季烈,時年七十又一。
世非吾世也。吾世安在?在吾心史。或二三交舊,促膝抵几,縱話曩昔,亦髣髴遇之。比心史久輟,又鮮可談者,忽忽若失,聞遯堪徙居城西,亟詣之談,乃益洽。臨分出眎是册,蓋於所讀書有所觸發,輒信手筆之,其事爲前代之事,其志則遯堪之志也。連犿若《談藂》,謹覈類《心史》,吾世庽焉矣。積暵欝(忡)中,就緑陰展卷讀之,煩襟一洗,歡喜讚嘆,因贅數言。太歲在玄黓敦牂,皋月哉生魄日,郭則澐識於遯圃。
《遯堪書題》者,錢唐張孟劬先生於所讀書偶有寄意,隨手書之簡端,雖與解題提要殊科,要亦有所發明。本遯世無悶之旨,自號曰遯堪,足以見其高尚之志矣。先生早歲詞章之名噪大江南北,既乃研讀經史諸子,兼及教乘,深入無間。晚參史局,然後專心乙部,以迄於今,巍然爲史學大師。所著書若《史微》足以見其史識,若《李義山年譜》足以見其考核史事之精,若《清后妃傳稿》尤足見史筆謹嚴,上媲班、范,非近世毛西河諸人所能望見肩背。先生之學,信可謂精且博矣,而純德篤行,尤足矜式後進。經師、人師之稱,豈偶然哉。鍾翰游學舊都,幸立門下,資性魯愚,何足仰測高深,然親炙日久,質疑問難,每受誨言而後知先生謙德尤不可及也。嘗借讀藏書,愛其題識,私録爲副,更欲廣之同人。既得三四十種,先生知之,不以爲善也,曰此乃少年信筆及之,烏足示人。堅請再三,始獲贊許,然其他題識尚多,祕弗許再窺矣。或謂此數十紙中頗多傷時之語,所謂春秋伏臈,仍懷故國之衣冠;歌詠篇章,不載興朝之歲月。然此先生一人志行,非欲强以教人,讀者分别觀之,但味其熟精經史、《騷》《選》之理,出言吐氣,雍容研錬,未嘗非學爲文辭之一助,因進以窺先生平日讀書勤劬,考訂不倦,則所以示我後進以準的者爲更多也。 二十七年九月門人東安王鍾翰謹識。
題 辭
孟劬先生蚤爲名士,晚作逸民,際桑海之交,秉西山之節,明夷艱貞,遯世無悶,天懷高曠,悠然自得,如羲皇以上人。然而登山臨水,則百感交集,當歌對酒,則一往情深,慷慨激發,作爲篇章,莫不橅事興懷,用意深婉,其旨遠,其辭微,蓋《小雅》之遺,賢人君子發憤之所作也。此《遯堪書題》一卷,皆其平日讀書時隨筆題識,雖非所經意,然觀其低徊往復,因物託興,有憂世之心焉,非徒寫興亡之感而已。書中諸跋於梅村、牧齋頗有所獎借,而尤酷嗜梅村詩集,以爲身世之感異代同符。讀者疑先生何猥自卑下如此,余謂此蓋先生牢騷不平之氣,感於物而動,故斷章取義,隨事寄託,以抒其哀,猶之白樂天發憤於潯陽老妓云爾。不然,以彼二子之爲人,曾不足爲先生之徒隸,況肯引以自喻乎。先生跋《初學集》云:“每誦其遺篇,惜其人,未嘗不愛想其才。”可見先生之知人論世,不阿私所好,而亦不没其所長,此詩人忠厚之意也。余辱先生推許甚厚,自謂知先生者莫余若,故發其微旨如此,爲讀者告焉。 時癸未孟夏月,武陵余嘉錫題於北平寓廬。
遯 堪 書 題
錢唐張爾田撰
門人王鍾翰録
跋《吴注梅村詩集》坿補箋五十三條
余年十五,從先君行篋探得《吴詩集覽》舊槧本,愛玩永日,先母憐之,命恣所閲。生平治史,尤熟於明季故實,自兹始也。我生不辰,晚遇艱屯,改朔移朝,草間偷活,而斯編乃若豫爲之兆者。歲在癸秋,應聘蘭臺,白鶴東來,空餘華表,銅駝北望,還見長安,身世之感,異代同符,今又十五年矣。老革騰騫,纖民熾盛,寄身已漏之舟,流涕將沈之陸,舊集重温,緣纓霑臉,不知淚之何從也。丁卯七月遯堪居士題記。
陵谷貿遷,桑海一概,梅村易簀之命,茹苦含悲,殆不欲作第一流想矣。余生晚季,遭逢世革,早歲彈冠,委贄人國,今兹抱甕,屈跡泥塗,十七年中爲口奔走,鳩史東華,授經北胄,存遺獻於皇餘,庶斯文於聖滅,欲標靈預同物之勞,不潔子容詭對之跡,静言身世,與先生其何以異。所不同者,未面閏朝耳。昔姚察《陳書·序儒林傳》云:“衣冠殄盡,寇賊未寧,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采綴,蓋梁之遺儒也。”每諷斯言,悲積陳古。異時知舊儻不死我,立一圓石,題曰“有清遺儒某某之墓”,足矣。息壤在彼,用敢附書。戊辰四月張爾田記。
聞之吾鄉邵蕙西先生言,曾見史可法奏報北都降賊諸臣有吴偉業名。《墓表》但云“丁嗣父艱”,《行狀》云“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梅村”,《年譜》於是年事亦語焉未詳,若有所諱者。然梅村南中曾登朝一月,解學龍所定逆案亦不及梅村,豈已湔雪歟。當時道路阻隔,擾攘之際,相傳有誤,容或有之,然亦南燼佚聞也。丁卯七月十八日燈下記。
《靳氏集覽》引古多舛,而搜孴本事實較詳備。程迓亭《箋》遺聞墜掌,尤資津逮,惜但有稿本未刊,後歸黄蕘圃、汪閬原兩家,近年流落坊市,余曾見之。此《注》未免太求雅簡,故世間仍行《集覽》有以也。頗思取二注及梅村家藏稿本《年譜》重治一通,而世亂方殷,經籍道熄,蟄居窟室,絶學孤危,視古人炳燭之明,用志不紛者,又一時矣。念之輒復慨然。丁卯七月遯堪再記。
生平於國朝詩極耆梅村、漁洋二家,吴詩於先母帷中讀之,故尤纏綿於心,集中名篇略能背誦。所蓄爲集覽本,枚庵箋注,徵引詳塙,遠軼靳氏,可媲惠氏《精華録訓纂》。舊得一本,旋復失去,今年於海上乃復收之。天方喪亂,小雅寢微,麥秀之感,豈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屬車一去,如聞黄竹之謡;華屋何存,空下雍門之泣。追懷曩緒,都成悲端,雖長歌不能當哭矣。丁卯六月張爾田記。
丁卯秋觀我生室重讀一過。集中諸作要以長慶體爲工,風骨不逮四傑,聲情駘宕,上掩元白,而蒼涼激楚過之,或疑其俗調太多,實則此體正不嫌俗,但視其驅使何如耳。陳雲伯輩效之,遂淪惡下,於此見梅村真不可及。五古若清涼山諸詩亦堪繼武,七律未脱七子窠臼,絶句則自檜以下矣。赤祲稽天,息影窮藪,輒復書之。
《吴梅村先生行狀》:“乙酉南中召拜少詹事”
談遷《北游録》:“順治乙未八月乙酉,是日御試詹翰四十八人,表一,疏一,判一。其表目上親征朝鮮,國王率其臣民降,群臣賀表。丙戌過吴太史所,太史口誦其表,極贍麗。”案梅村表文亦載《北游録·紀聞》。
“雅善書,尺蹏便面,人争藏弆以爲榮”
談遷《北游録》:“過吴太史所。昨夕上傳吴太史及庶吉士嚴子餐沅、行人張稚恭恂各作畫以進。太史方點染山水,明日共進。時朝廷好畫,先是户部尚書戴明説、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畫進。”案觀此則梅村又善畫,不獨善書也。
“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
談遷《北游録·紀聞》:“駿公先生又工詩餘,善填詞,所作《秣陵春傳奇》今行。嘗作《賀新郎》一闋:‘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没。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洒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膓千結。追往恨、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絶。早悲若、重來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説。人世事,幾完缺。’”案孺木以順治十一年甲午入都見梅村,《録》中所記皆其時事,則《賀新郎》詞蓋早作,世以爲絶筆,非也。
《吴門遇劉雪舫》
五古長篇鋪敍如《北征》、《南山》皆風骨高騫,主賓凝互,故意境最高。梅村大都平衍,不過微之《昔游》之比耳,然而宛轉含淒,靡靡入妙,使傷心人讀之涕下,真情真景亦後來所難追步者。此首與《遇南廂叟》一篇在集中皆入妙,亦可謂異曲同工矣。
《送何省齋》
頽放冗蔓,長慶之遺。
“君家好兄弟”
《明季南略》:“何亮工南真,桐城人,宰相何如寵孫也。亮工少有逸才,爲史道鄰幕賓,史答攝政王書乃其手筆。順治丁酉舉孝廉,家南京武定橋。”
《清涼山讚佛詩》
此爲董鄂貴妃作也。妃薨於順治十七年八月,翌年正月世祖賓天,王文靖實親承末命,見於韓菼所作《行狀》。陳其年《詠史詩》:“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此紀實也。梅村此詠,鼎湖寓言,或當時傳聞之異,然詩特工麗。近有言於内閣舊檔發見順治二十一年題本者,余猶疑之。
近人陳援庵据《茆溪和尚語録》證明世祖及董鄂貴妃皆火葬,茆溪即當時下火之一僧也,吴詩疑案得此乃定。火葬本滿洲舊俗,日本傳抄《三朝實録》:“順治元年八月甲子,小祥,以國禮焚化大行皇帝梓宫。丙寅葬大行皇帝,中宫太后率衆妃及公主等詣焚所,舉哀畢,捧龍體安窀穸内,由中階升陵殿。葬畢,名昭陵,是太宗已火葬。”國初諸王如多尔衮等亦皆火葬,故外間有“焚骨揚灰”之謡。當時本不以爲嫌。後來修《實録》書,以其與中國禮教有碍,始諱之也。
“陛下壽萬年”
世祖信佛,當時必有傳爲不死之説者。木陳和尚有《骨龕侍香記》一書,乾隆間以其妖言詔燬之。梅村所詠,或具其中,恨不能一證也。
“從官進哀誄,黄紙抄名入”
徐健庵《憺園集》“送程周量出守桂林”詩註:“周量官内秘書撰文,曾進《端敬皇后誄》,爲孝陵所賞。”据此詩“從官進哀誄,黄紙抄名入”句,是當時進誄者不祗程可則一人也。
“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
《世祖實録》:“順治十七年十一月,諭端敬皇后彌留時,諄諄以矜恤秋決爲言,朕是以體上天好生之德,見在監候各犯,概從減等;應秋決者,今年俱停止。”“微聞”二句指此。
“南望倉舒墳”
倉舒墳謂董鄂貴妃所生皇四子榮親王。王生甫四月,順治十五年正月薨,見《世祖實録》。
“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
漢武學仙,章皇信佛,身局九重,神游八極,瑶池黄竹之謡,蒼梧白雲之想,寫來疑是疑非,滿紙俱化烟霧矣,不得作實事解也。
“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
觀“房星”二句,蓋謂乘輿未出而遽賓天也。前段假道安銜命勸其脱屣人寰,故以此兩句作轉捩,所謂“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也。第四首“色空兩不住”亦以此意作結,所云寓言,信矣。
“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
善財洞當在清涼山。此二句明言神游而非親到矣,是全詩點睛處,奈何解者不察,尚謂此山曾駐蹕耶。惜吴氏未注所出,容當詳考。《集覽》引《甬東游記》,未是。
《集覽》“房星”注引《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房星明則王者明。”考《晉書·天文志》但云:“房爲天駟,亦曰天廄,主開閉畜藏。房星明則王者明。”其“明堂,布政之宫”乃指角外三星,不知《集覽》何以合而爲一,宜後人誤據解作帝星不動,而有法王行遯之疑也。吴注引《史記》注房星“主車駕”,得之。
房星近心,心爲明堂,故宋均注《詩緯記曆樞》云:“房既近心,爲明堂,又爲天府及天駟也。”《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實本此,但非本誼,本誼仍以主車駕爲正訓耳,注家未能分析。
“色空兩不住”
此首寫其陟降,所謂“翠華想像空山裏”也,而以“色空兩不住”一點,何等超妙。若以鴻都方士之寓言,解作西山老佛之疑史,恐非詩人本旨。
《琵琶行》
集中七古,此爲第一。中段寫琵琶聲激楚鬱盤,古音錯落,殆駕元白而上之,近人學長慶體者所不能爲。
《王郎曲》
此是長慶體之卑卑者,著語淡宕,故不惡,若更刻畫,便入魔道矣。奈何近人專喜此種。
談遷《北游録》:“過吴太史所,太史近作《王郎曲》。吴人王稼,本徐勿齋歌兒也。亂後隸巡撫土國寶,怙勢自恣。國寶死,逃入燕。今再至,年三十,而江南薦紳好其音不衰,强太史作《王郎曲》。先是,太史善病,每坐晤對,今病良已,詩繪自娱,因曰:‘文詞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語似雅實俗,有出於俗而實雅,未易辨也。’余聞之,瞿然有省。”案梅村此詩似雅實俗,孺木所記,其殆善於解嘲歟?
“古來絶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
都多唐韵不通,此用俗音取協。梅村詩用韵往往可議,蓋漸染明季填曲家不學之病也。
《蕭史青門曲》:“神廟榮昌主尚存”
今内閣舊檔有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養臣榮昌大長公主揭帖,是榮昌入本朝始薨也。
“盡歎周郎曾入選,俄驚秦女遽登仙。青青寒食東風柳,彰義門邊冷墓田。”
談遷《北游録》引孫承澤《春明夢餘録》曰:“公主名徽媞,甲申年十五,傷右臂肩際。明年九月成婚。丁亥卒。公主葬周氏宅旁,今地賜豐盛王,垣之不可入。在廣寧門内。周世顯,父國輔。”
《通元老人龍腹竹歌》
通元老人,湯若望也。談遷《北游録》:“入宣武門稍左天主堂訪西人湯道未若望,大西洋歐邏巴人,萬曆戊午,航海從江浙入燕。故相上海錢文定龍錫以治曆薦。今湯官太常寺卿,領欽天監事,敕封通元教師,年六十有三,霜髯拂領。”《疇人傳》作“敕賜通微教師”,誤,當據此訂之。
彭孫貽《客舍偶聞》:“利瑪竇精天文律曆,以西洋曆法論改曆事,湯若望等續成之,名《崇禎曆書》。世祖定鼎北京,遂用之,名《時憲曆》,賜若望號通元國師,賜一品服。”
《田家鐵獅歌》
談遷《北游録》:“入宣武門大街,久之道側鐵獅二,元元貞十年彰德路造,先朝都督田弘遇賜第,獅當其門。今門堙而獅如故也。吴駿公嘗作歌。”
“盧溝城雉對西山,橋上征人竟不還。枉刻蹲獅七十二,桑乾流水自潺潺。”
《北游録·紀聞》:“蘆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有八。”
《題崔青蚓洗象圖》
《北游録》:“過吴太史所,云往時大興孫清隱有高節,畫山水人物,追蹤古人,亡子。甲申遭亂,餒死。其畫多傳。太史題其洗象圖。”孫清隱即崔青蚓音訛,孺木殆聽之未審也。
《臨淮老妓行》
談遷《北游録》:“午遇吴太史所,太史作《臨淮老妓行》甫脱稿,云良鄉伎冬兒善南謳,入外戚田都督弘遇家。弘遇卒,都督劉澤清購得之,爲教諸姬四十餘人,冬兒尤姝麗。甲申國變,澤清欲偵二王存否,冬兒請身往,易戎飾而北至田氏,知二王不幸,還報澤清,因從鎮淮安。澤清漁於色,書佐某亡罪殺之,收其妻。明年澤清降燕,而攝政王賜侍女三人,皆經御者,澤清不避也。居久之,内一人告變,攝政王録問,及故書佐之妻,澤清謂書佐罪當死,故妻明其非罪,且摘澤清私居冠角巾諸不法事。澤清誅,下冬兒刑部。時尚書湯嘗飲劉氏,識之,以非劉氏家人,原平康也,得不坐,外嫁焉。吴太史語訖,示以詩云云。”此梅村口述也,較注家爲詳,宜附載之。
《七夕即事》
帷簿之事,跡涉曖昧,無從證明,史多不書,乃其慎也。詩則不妨,或一事之偶聞,或一時之託興,悱惻纏綿,而以微語出之,襍事秘辛,未嘗不可與正史同傳。若欲取以證史,以若明若暗之詞,易共聞共見之實,則繆矣。箋梅村詩者當知此意。
江陰夏閏枝語余此詩詠孝莊下嫁事也。細味此詩,實無下嫁之事,乃因多爾衮納肅王妃而傳訛者,余撰《清后妃傳稿》已辨之,且其時乃順治七年正月,非七夕事也,惟順治十一年静妃廢,旋聘孝惠爲妃,六月册立爲后,與詩“重將聘洛神”相合,所謂“祗今漢武帝,新起集靈臺”也。多爾衮未正位,安得以漢武爲比。第四首“花萼”四句當有本事,今無可考,要之必非指孝莊也。
湯若望《日記》:“世祖一寵妃乃一親王亡妻,此親王□辱其妻,爲世祖所責,氣憤而死,世祖遂納其妻。”寵妃不知所指何人,似可與花□□相印證,但湯若望日記乃近日德人重譯,其真贗尚須待考耳。
程迓亭箋謂此詩詠董鄂貴妃事。第四首“淮南”二句指貴妃先喪皇子也,然董鄂妃薨逝在順治十七年八月,似與七夕無涉,仍當闕疑。
又案孝莊無下嫁事,而宫中秘事容或有之。亡友王静安曾見舊檔案審訊多爾衮黨與,有一供詞涉及無禮太后事,惜未全記。此詩所詠,殆指是歟?“重將聘洛神”謂納肅王妃也,“沈香”二句其新孔嘉之感。三首極寫深宫望幸之意,而以“夜如何”作結,所謂詩人微詞也。第四首則多爾衮薨逝,“南内無人牽牛,誰候正頂淮王”兩句也。如此解之,詩意全通。首句“西王母”一點透出作詩本旨,正不必作下嫁解也,似亦可備一説,然宫禁深嚴,外間傳聞豈能盡實。嘗見《北游録》載梅村談論,按之事實,亦多有未碻者,終不如就詩論詩,泛作宫怨,較無穿鑿耳。
《雜感》:“聞説朝廷罷上都,中原民田未全蘇。”
《甌北詩話》云:“順治七年攝政王以京師暑熱,欲另建京城於灤州,派天下錢糧一千六百萬。是年王薨,世祖章皇帝特詔免此加派,其已輸官者准抵次年錢糧。”所謂罷上都,正指此事也。
“珠玉空江鬼哭高”
《甌北詩話》云:“張獻忠亂蜀時聚金銀寶玉,測江水深處,開支流以涸之,於江底作大穴,以金寶填其中,仍放江流復故道,名之曰‘水藏’,所謂‘珠玉空江鬼哭高’也。”
“取兵遼海哥舒翰”
哥舒翰無取兵遼海事,聞之故老,“哥舒翰”乃“桑維翰”之訛。詩以桑維翰通使契丹比吴三桂之請兵我朝,當時或有所諱也,亦烏桓作烏瓛之類矣。
《國學》:“伏挺徒增感遇心。”
《梁書》:“伏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静。時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梅村之出,由海寧、溧陽二相所薦,故詩用挺事。注引《南史》,未詳詩意。
《江上》
全謝山《定西侯張名振墓表》:“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焦,遥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上游有蠟書,請爲内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癸巳爲順治十年,甲午順治十一年,此詩所詠者是也,非指十六年鄭成功陷鎮江事。
《李退庵侍御奉使湖南從兵間探衡山洞壑諸勝歸省還吴詩以送之》
聞之故老云,侍御之先開藥肆於洞庭東山,侍御即山居讀書,應試則仍回原籍,故注云“吾吴之洞庭人”。
《太湖備考·選舉志》中載:“東山李敬,順治二年乙酉科舉人,四年丁亥吕宫榜進士,江寧籍。”
《送趙友沂下第南歸》
談遷《北游録》:“求吴太史書二綾,蓋方庵二南所懇太史昨秋送趙生南歸詩:‘趙氏只應完白璧,燕臺今已重黄金。’二南甚愛其句,特書焉。”
《即事》
談遷《北游録》:“先是,傳詞林十四人修《順治大訓》於外宅,吴駿公太史與焉。”又云:“初正月末,太史召入南苑纂修《内政輯要》。在南苑時再被召,知其抱疴,放歸,則二月之八日也。”此詩蓋梅村召赴南苑修書時所賦。
《北游録》又一條云:“吴太史家幹至,云昨召入南海子纂修《孝經衍義》,同官六人,總裁者涿州也。”
《長安雜詠之二》
順治九年,達賴喇嘛入覲,世祖敕居黄寺。此詩所詠是也。
《思陵長公主輓詩》
《北游録》引張宸《記事》云:“甲申春,上議降主,時中選者兩周君,其一即都尉也。其一人内臣糾家嘏失謹,即掖群内侍環都尉,驩曰:‘貴人貴人,是無疑矣。’順治二年詔故選子弟,都尉君應詔赴。是時有市人子張姓者冒選應。既得之矣,召内廷,給筆札,各書所從來。市人子書祖若父皆市儈,則大叱去,曰:‘皇帝女配屠沽兒子?’命都尉書,則書父太僕公,祖儀部公,高、曾以下皆簪纓。遂大喜,曰:‘是矣!’即故武清侯之第,賜金錢斗車,莊一區,田若干頃,具湯沐,成吉禮焉。時乙酉六月上浣事也。公主喜詩文,善鍼飪,視都尉君加禮。御臧獲吴語,隱處即飲泣,呼皇父皇母,泣盡繼以血,以是坐羸疾。懷娠五月,於丙戌八月十八日薨,淑齡十有七耳。都尉藏所遺像,右頰三劍痕,即上所擊也。老内侍見輒拜,曰眉似先帝云。”
《讀史偶述》
此數首皆我朝入關後襍詠,金鑾祕事,都市瑣聞,懷舊話今,咸有故實,非爲前朝捃逸也。
其十二“寂寂空垣宿烏驚”
《癸巳存稿》:“今世襲墨爾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恩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内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噶喇廟)。吴梅村《讀史偶述》詩其地址俱合。”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産人口給信王,故詩曰“空垣”也。
“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
《甌北詩話》云:“南城本明英宗北狩歸所居,本朝攝政王以爲府第。朝事皆王總理,故百僚每日會此。”順治七年王薨,故云“七載金縢”也。
彭孫貽《客舍偶聞》:“墨勒根王初稱攝政王,次稱皇父,繼而稱聖旨,適大同堅守,九王親赴,行間道病而殂,其事甚秘。胡良輔與索尼、蘇克撒哈等合謀,盡誅九王子孫,焚王骨,揚灰,世祖始克親政。”案焚骨揚灰事亦見吴三桂反時上聖祖書。睿王實薨於哈喇城,非大同。姜瓖之役,胡良輔即内監,吴良輔其時尚未攬權,皆傳聞之誤。
《讀史有感》
《讀史》八首亦爲董鄂貴妃作,可與《清涼山讚佛詩》參觀。
其五
此首分明寫出胭脂山畔女兒狀態。近有妄人以董小宛强附會董鄂貴妃,俗語不實,流爲丹青。無論年不相及,而南人嬌弱,亦豈有射雕好身手耶。陳其年水繪舊客,其《讀史》詩亦云:“董承嬌女拜充華。”無一語涉及如皋,可以互證也。
《偶得之二》
《甌北詩話》云:“此首乃順治九年拏獲京師大猾李應試、潘文學二人正法之事。”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之八》:“墓門深更阻侯門。”
結句蓋言零落之悲甚於攀折之苦耳。若果生入天家,死留青冢,複室永蒼,又豈侯門之足擬耶。梅村最講詩律,不應用典不倫,固知捫龠之談不可信也。
《古意》
《古意》六首,蓋爲世祖廢后博爾濟吉特氏作。后於順治十年八月降静妃,改居側宫,見《世祖實録》。此詩殆世祖崩後作,其時静妃當尚在也。
《仿唐人本事詩》
《世祖實録》:“順治十三年六月,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勳嫡裔,淑順端莊,宜立爲東宫皇妃,候旨行册封禮。”第一首指此,《古意》六首則爲静妃作也。
跋《皇明通紀》金陵摘星樓本
此書多載野聞,不盡據《明實録》,自萬曆中葉始流布,清瀾未必盡見,故賅洽遠不及弇山,惟其敍述謹嚴,議論迂而不腐,在野史中要爲可取。乾隆時此書曾列入禁燬,故傳本絶稀,細閲之,亦殊不見違礙之處,中間所記建州兵事數條,亦復語焉不詳,不知何以罹焚坑之禍也。是本舊藏獨山莫氏,余得於滬上。甲子夏四月記。
《憺園集》謂此書本梁文康之弟億所作,故多譽兄之言,考書中惟載文康不草詔事,不無溢美,然亦本之《鴻猷録》。清瀾非盜人書者,要之,所采私家野記既多,失於勘正耳。孟劬再記。
《野獲編》:“隆慶間給事中李貴和上言:‘我朝列聖《實録》皆經儒臣纂修,藏在秘府,陳建以草莽借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況時更二百年,地隔萬餘里,乃以一人聞見,熒惑衆聽,臧否時賢,若不禁絶,爲國是害非淺,乞下禮部追焚原板,仍諭史館勿得采用。’從之。但板行已久,俗儒淺學多剽其略以誇博洽,至是始命焚毁,而海内傳誦如故也。近日復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是清瀾此書當日已遭禁網,此萬曆刻本殆即所謂重刻精工者。清瀾理學之士,非良史才,其識議亦不過劉時舉輩一流,乃區區短書,明清兩朝再罹五厄,而仍傳於世,亦云幸已。孟劬重閲題記。
跋《郁離子》照曠閣本
青田此書已開明人摹古風氣,然較諸嘉隆小品,尚有雅趣,惟多列子目,殊乖體例。六朝以降,子學絶矣,有志成就者不過如是,資爲好文者漁獵,亦弗滅也。甲子夏得於滬上博古齋,遯堪居士記。
青田文殊有骨力,而學則襍霸,同時潛溪、正學其才皆足以著書,所成者大都短篇,學限之也。嘉隆以後一變而入於贗,高者摹周秦貌,爲有道之言;其下者江湖譎觚,榛稗弗剪。國朝考據家出,盡取矯誣者易之,涂轍一軌於正,而文事趨俗,又不如前。三百年來有意自成一子如《激書》、《潛書》等不過數種,人亦罕道之者,學無本原而勇於襲古,未有不躓者也。學是矣,而病徵於文,則亦不能以行遠,二者交譏,成家之書所由難覯與。是書雖未洞極奥微,而雋永不窮,頗可憙,爲饜芻豢者一思螺蛤時復得少佳趣。展閲竟,輒書於第一卷之尾。
跋《元遺山詩集箋注》南潯瑞松堂本
自古亡國桑海之際,歌采薇,蓐螻蟻,大都氣類相感,易於繫結。遺山不幸爲金源碩孑,雪涕南冠,其言哀婉,而其志則隱矣。余生不辰,學行無似,而身世之遇乃若或同之。昔遺山慨故國舊聞,自我放失,汲汲焉欲以文獻爲己任,又上書元世祖,力護儒教。今則《實録》雖存,而仇敵罵譏,有甚於放失者,邪説殄行,猾夏之言,不出諸異族,竟見之於服古誦數之徒,比之遺山所遭,不尤酷耶。青編絶筆,誰傳據亂之書;白首離群,遂瞑銜冤之目。惟差足自慰者,則崔立之碑少此一事耳。遺山詩刻最多,而北研箋注墜聞瑣掌,搜孴較詳,志事顯晦,賴以考見。此本曾藏丹徒趙氏,尚是初印,每一展誦,彌襟慨然。乙丑秋七月遯堪張爾田題記。
跋《定盦文集》同治七年刻本
余髫辮誦定盦文慈母帷中,中間肴饌百家,整齊六籍,籀三千年史氏之簡,與定盦涂轍或合或不。年三十矣,治文章家言斐然,不自揆度,成《史微》三十餘篇,既殺青可繕寫,世或以定盦託我,謝未遑也。雖然,定盦之文奇而吾之文正,定盦之文隱而吾之文由隱以至顯。定盦文圓而神,法天;吾之文方以智,效地。至於覃微極思,遠見前覩,則未知於定盦何如也。會稽竹箭,東南之美,得一定盦而余小子乃恢其緒,斯亦足以自慰矣。赤眚稽天,坤軸將毁,藏山之業粗成,襄陵之禍已及。魂魄一去,便同秋草,日暮塗殫,聊復書之。丁卯二月遯堪居士張爾田記。
《定盦文初集》、《續集》當出自定,故最精美。《古史鉤沈論》壬癸之際,胎觀皆非一世之言,即考訂蒙古輿地等,文類覈實,有資國掌,所謂“老波瀾”者。其後平湖朱氏刻《補編》,多少作及不經意之作,詣力未醇,可存者寡。坊間所行尚有《讀内典》諸篇,亦未能閎深,大抵皆棄滓也。當道光之季,席乾嘉豐熾之敝,舉國酣嬉,學者鑚尋故紙,苦志疲精於襞績之中,殆不知戴而游者爲何世,患氣所乘,横潰已伏。乃有人焉,發寐於天,斯亦異歟。老氏有言:“前識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非亂之首,亦無以貴前識。今去定盦不及百年,吁其譣矣。愚者不察,不能原亂之何以首,而乃傅過於前識者,故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也。定盦猶幸以其文傳,是則定盦之哲也,悲夫。丁卯二月遯堪再記。
余少好定盦文,今老矣,好益篤,嘗衡三百年文士之卓卓者,汪容甫及定盦而已。容甫文從經出,定盦文從子出。容甫學漢魏,不寫放其貌而取其神;定盦學周秦,不規橅其辭而得其意。是二家皆與古代興者也。定盦憂患來世,其言尤危苦,語極諔詭,意藴沈悲。天方降瘥吴會,豐昌之土淪爲山越,衰病徂年,鍵户獨處,炳燭誦斯集,迴憶三十年前,又一人間世矣。所以哲者不苟作,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詎不信歟。丁卯元夕燈下記。
光緒庚子,余年二十餘,居舊京,遭拳寇俶擾,避地白浮邨,即集中《記昌平山水》所謂“百泉”也。行篋盡捐,獨以此書自隨,繁憂猥懣,取代萱樹轍環,所届亦未嘗一日而離,到今春丁卯,三十年矣。老逢世革,煢然草際,横政殄行,再罹赭亂,文武之道既盡,生死之路皆窮。炳燭餘光,發我寤思,斯册也。殆將與身偕殉歟。海上觀我生室讀重記歲月。
跋《定盦文集》道光原刻本
定盦史識出於天授,幼爲段金壇外孫,從受訓故,從劉申受治《公羊春秋》,又與江子蘭游,聞彭尺木佛學緒言,讀《大藏》,與程大理同文講求四裔掌故之學。學不名一家,而皆能洞入其奥藏,寤思孤創,一用以資爲文,故其文千光百怪,奔迸四出,九流諸子,靡所不涉。同時魏默深雖竭力追逐,未能或之先也。然要其得力造端,則亦實從《唐文粹》蜕化得來。凡學漢魏之文,其變也無有不匯歸於《文粹》者,特定盦天分高,不貌襲而神與之合,淺識者易爲其所怵耳。世人競尚桐城,但見八家以後之古文,詆之爲贗品,亦固其宜。文如居士得原槧本,屬陳君公睦手録蘭甫先生評語,命爲題志,余因著定盦之學術淵源如此,使後之人無徒以怪目定盦也。張爾田記。
跋《韓詩外傳》亦有生齋校刊本
《韓詩外傳》以趙校本爲最善,此味辛先生親贈合河康綸釣者,卷首有其題識。考李申耆所作《康公太夫人顧氏神道碑》,綸釣爲廣東巡撫紹鏞兄,官至通政司參議,一門華膴,籍甚當時。是册曾藏繆筱珊丈許,丈下世,遺書散盡,余乃得之。嗟乎,泰壇毁矣,泯夏滔天,赤祲若墨,神州奥區,淪爲鼠壤,白屋且薪,青箱何有。重是承平故物,篝燈披誦,但增衰泫。丁卯春客海上觀我生室讀記之。張爾田。
跋《陸士衡文集》明正德覆宋本
二陸集宋槧難觀,此正德影倣,所謂下真跡一等也。汪士賢本即從此出。吴興陸氏據宋刻校勘異同數處,今刊《群書拾補》中,可以迻録。此爲漁洋舊藏,余得之京肆者。世亂方殷,文藝淪喪,惵惵黔黎,傾羲靡旦,斷流之禍,劇於典午。辰且非我,遑言長物,五百年故楮,會與玄陸同盡耳。丁卯仲春蟄居山越之鄉,蒿目羅剎之化,重展舊集,輒復書之。遯堪居士張爾田記於海上觀我生室。
跋《抱朴子》嘉慶癸酉金陵道署本
《抱朴子内篇》孫校最善,《外篇》乃繼昌校刊,精審遠不逮,惟《外篇》附校勘記及佚文,爲平津館本所無耳。稚川之學,饌飫百家,博辨是其長擅,而閎深遜之,然文極優美,有《論衡》風趣。魏晉之間,經術告謝,子學肇興,今載列《意林》等書者無慮十餘家,求其卓然與《抱朴》匹,卒亦無有,然則此書不可謂非九流之後勁也。赤熛疾威,黔首昏墊,逃名九罭,已無視月之儒,猾夏一朝,遽改經天之步。大藥未成,浩劫已及,沖舉之術無階,元素之業墜地,鑽閲終篇,龍鍾横集。丁卯春爾田記。
跋《讒書》拜經樓正本
唐之季也,大盜移國,諸方幅裂,一時清流,群醜梁德,寄命偏朝,若韋莊、王定保、羅隱輩皆是,惟韓致光客南安依王審知,雖預上賓,皭然不滓,翛乎遠已。余昔有詩云:“臥聽除書萬里天,紅巾鳳蠟淚淒然。江東祗有羅昭諫,卻説燕臺費料錢。”蓋惜之也。《讒書》五卷,其言未能閎深,大抵舉子行卷之作。隱連不得志,於有司緝之以洩憤耳。文奇崛猥懣,頗襍纎俗,晚唐之末流,而亂世之頽響也。然而有望治之思焉,是其不可磨滅也歟。丁卯秋養病海澨得此書,記之。張爾田筆。
丁卯七月晦海上觀我生室讀,適聞陪都被兵,赤徒星迸,天疾有定之威,人懷其蘇之望,幸揜蓬蓽,理亂非我。是夕微涼,病中竟數紙,頗窺文術異同,炳燭之明,蕭然室處,重親丹槧,亦餘生一樂也,因題之卷尾。孟劬記。
跋《真誥》明萬曆刻本
右《真誥》二十卷,分類七,始運題象,終翼真檢,《敍録》云:“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曰‘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誥也。”案紀文達《筆記》謂扶乩起於宋,或謂請紫姑爲乩之始。《夢溪筆談》言博士王綸家有《紫姑神集》,即今之乩詩。實則此術古巫覡皆優爲之,特巫覡降神,但憑口傳,祝由治病,乃其先例。祝字從口,交神會意,祝由略如西方之催眠術,再進則能符籙矣。今道家諸符似籀似篆,諗知出秦漢之際,又再進則有能章草者矣。此書載楊羲、許謐及其子玉斧所書諸真降神事,有詩有諭有問答,即乩之濫觴也。楊、許二氏殆精是術者,溺道者一切以爲真,而儒者又斥之爲妄,而豈知彼固神秘之一端歟。神仙家《漢·藝文志》載入方伎,本醫之支流,而巫又爲之源。《論語》巫醫並舉,而巫先於醫,厥理可推。後世方伎專重服食導引,或假巫覡之術以神之,張角太平道、張陵五斗米道,其始皆以治病惑愚民,尚不失其初意。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云:“米巫兇虐,續蠢青羌。”《隸釋》謂米巫指張修與張魯是也。米巫之稱至當,碑立於建安十年,此當時人所目者,後乃諱巫而稱之道耳。陵造作道書,始主以五千言都習,然道書出魏晉間者,或談黄白,或演符禁,雖以長生爲歸墟,猶不甚附會老莊,老莊貴養生,理與醫通,故道書援之,又墨家古祝史之術,《抱朴子》記道書有《墨子枕中五行記》,是雖僞造之迹,尚有統緒可尋。亦絶不苦録佛經。《魏書·釋老志》稱張陵傳天官章,其稱劫數頗類佛經。案此乃依附緯候,景射内典,是竊佛最隱秀者。其後陸修静、寇謙之輩出,乃益靡耳。《隋·經籍志》著録道經三百餘部,其中當有出於神秘如乩之所爲者,故《志》云:“所説之經,皆禀元一之氣,自然而有是也。然亦有人所依託者,自昔已不能區别,蓋雜糅久矣。”六朝太平道寖亡,士流所奉皆五斗米道。此書相傳陶隱居揆輯,亦鵠鳴羽翼。書中晉代年月以長術推之多覈,《梁書》稱隱居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秪史官是用,是其人本長步算,至於蠲塵澡累,詄蕩多文,麗詞褥旨,芬然溢目,使人尚可考見古代靈學之一斑,較之宋元方士陰陽郛廓之談,要爲近古也。戊辰閏月寫似湖南先生,張爾田書於浦上觀我生室。
跋《水經注箋》萬曆刻本
《水經注》前明行世者,以黄省曾、吴琯二刻爲最善,鬱儀王孫又據二本爲之箋校,精博實出其上。乾隆間戴東原校官本,雖依《永樂大典》,而左右采獲,擇善而從,往往與之闇合。先是,趙東潛病朱箋疏略,爲《水經注釋》,又作《刊誤》十二卷,而槧本乃在。其後别本流行,多符官校,遂有竊趙襲戴之疑。學者承習新書,怠窺舊録,飲水忘源,吁可歎矣。今春得見此本,詳碻誠不及近儒,而創通大較,厥功甚勤,不有朱氏,戴、趙二家亦不能憑藉成其業也。庶存託始之真,以備思誤之適,後之覽者或無瞢焉。戊辰三月張爾田記。
跋《晉略》道光己亥刻本
保緒此書有聲當世,鄉前輩譚復堂亦極稱之。觀其穿穴群籍,錯綜本始,敍事簡而有力,下筆質而不俚,雖襲舊典,獨見鎔裁,洵乎别史之良已。屬文律度,思規六朝,捶字造語,頗復不類,承輓季文敝俗,尚未能盡滌變流,競則有餘,追大雅而不逮,道麗之辭,無聞焉爾,斯其類歟。然當嘉道之末,嵬儒淺夫,群溺於考據襞績之學,成家宏作,有此斐然,亦可謂不自詭隨者也。我生不天,老逢世革,横政肆威,纖民熾盛,崇非禮之言,滅禋聖之典,經籍道厄,甚於典午。昔魚豢表隗禧七人爲魏儒宗而論之曰:“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每味其言,未嘗不悲之。炳燭餘明,寄之吟諷,聊以亂思遺老,亦庶幾後之觀者知余業焉。戊辰三月遯堪居士張爾田記。
書中諸論卓有風軌,雖學六代,神思不侔,良由隸典太纖而用字近獷故也。何謂纖?陳畫餅以餽餒,集蓉裳以禦冬是已。何謂獷?鯨吞鯢啖,鼈跋怒是已。昌黎嘗言爲文宜略識字,而所作横空盤硬,往往失於帖妥,其流至《曹成王碑》而極矣。初唐四傑結體淺俗,然尚不至於纖,五季四六繁興,斯敝遂多。何則?獷實古文之末歧,而纖又麗詞之衰響也。必去此二失,方可與言六朝,惜周氏生嘉道間,未曾講求及此,獨其駢散不分,文筆互用,深得古人潛氣内轉之妙耳。見稱於時,固其宜也。孟劬再記。
跋《經義圖説》嘉慶己卯裛露軒本
此書蓋爲當時帖經而作,考訂不甚有法,惟徵引諸儒舊説尚不墜策括腐陋結習。塾學恥不知經,宜穆堂先生歎絶倫也。嗟乎,天步初更,侮聖滅典,今又一時矣。前經往誥,尚有墜地之痛,遑論舉業。每讀此書一過,想見士生承平服古藏修之樂,惟今之人不尚,有舊言之,歎息彌襟。南宋坊刻《重言重意九經》,世尚多寶之者,然則是書雖兔園册子,亦乾嘉文物之所繫,又安可以敝帚而棄之哉。近見此類書甚夥,輒復收存記之。戊辰夏張爾田。
此書多據《周禮》爲説,兼采及宋明諸儒舊解,每一制度必詳其義,雖所列之圖不甚可據,然較之考古家專蔽於名物度數者,轉復勝之。桐城人士治經,宗程朱而不廢義理,此書殆猶有其鄉先輩風烈者與。孟劬記。
跋《初學集箋注》玉詔堂刻本
牧齋文非駢非散,蕪音凡藻,不脱明季俳習,而詩則沈博騫翥,浩瀚流行,在當日卓然爲一大家。遭時禁燬,江漢文章,不能與梅邨斑管同其論定,要其風采自足千古,又豈區區文網所得而錮之。遵王親承硯席,藏書滿家,詩中故實,尚多有未盡舉其出處者,虞山腹笥,故應獨步。余生也晚,每誦其遺篇,惜其人,未嘗不愛想其才。滄海横流,今又改朔矣。棲閑守志之業無聞,刮語燔書之禍再見,士習舶來之文,家乏世寶之典,羽陵片蠹,流傳日希,彌足珍異。此本曾藏獨山莫氏,有其朱印,惜《有學集》缺首六卷,當由藏家畏遭時忌抽去,而《初學》一集特完,遂買得之。掃地焚香,寄之吟詠,固猶勝於《蘭亭》落水之阨也。己巳小春錢唐張爾田題記於觀我生室。
跋《綏寇紀略》時寶堂原刻本
明季野史多淩襍無體,惟梅邨此書具有史裁,敍事詳核。其述武陵功罪,不徇黨見,尤爲精采,足裨正史。全謝山譏其爲降賊之張縉彦出脱,且疑出鄒漪竄改,由今觀之,殊不盡然。大抵玄黄之際,草野愛憎,往往與當事者異趣,是非互陳,而微其詞,斯良史也。三百年來史學衰替,士皆溺於考古,成家斐然之書或不爲人所重視,甚且從而詆之,亦可慨矣。此書剪裁有法,簡絜詳盡,文尚典縟,殆非梅邨不能爲。照曠閣有重刻本,據原稿校改多處,然《虞淵沈》爲梅邨未竟之業,張氏所補亦不類,要仍以斯本爲較古也。張爾田記。
朱竹垞稱,梅邨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萬壽宫輯此書,以三字標目,倣蘇鶚、何光薳例,蓋梅邨未官本朝,所作繫情文史,亂思遺老,出山本非其志。今者麥秀殷墟,棘埋晉陌,滔天之禍,劇於汴水,妖亂之志,誰續廣陵。篝燈勘此書一過,又不禁感慨繫之矣。張爾田海上觀我生室讀。
談遷孺木以順治十一年入都,所著《北游録》有一條云:“三月辛丑,吴太史示流寇輯略。”蓋即此書原名也,則書出梅邨手益信。孟劬再記。
明季記流寇事者多種,皆不甚傳。彭仲謀《流寇志》全謝山尚見之,然謝山摘其失實處甚夥。蓋賊情萬變,傳聞異詞,苟非身在局中,自亦不能無誤。要之,巷談道聽,恒不如朝聞者之較碻,則以邸鈔疏報雖多諱飾,終不能大遠於事實也。梅邨成書於朝,固與野紀不同,此其所以傳歟。孟劬。
全謝山述林太常蠒菴之言,謂此書一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邨得之,遂以行世,殊非覈論。案梅邨自號鹿樵生,見所作《玉京道人傳》,《鎮洋縣志》亦云梅邨有鹿樵書舍,則非出他人之手可知。大抵梅邨此書憑藉資料必有所本,而又參以邸報奏牘,精心結撰,抒軸自别,此則可信者也。余最愛其敍述精采處筆健味腴,深得《史》、《漢》神髓。法必從古而事不偝今,後惟魏默深《聖武記》有此意趣耳。惜此本有缺葉脱字,當求善本一補之。横流方羊,六籍湮阨,嵫景西曖,寄諸敝帚,每覽遺篇,增我永喟。己巳十月孟劬再記。
全謝山跋此書謂:“鄒漪議論附見《綏寇紀略》者,頗爲李明睿粉飾,又譏其盛稱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爲光時亨所阻。”今案鄒氏案語見之於本書者,惟首卷曾引明睿之言,稱之爲吾師,他無所見,豈謝山所譏,見其所著《明季遺聞》中歟,抑或此書别一稿本也。君子不以人廢言,謂之粉飾,亦殊過當,鄒漪生平之壞,恐不在是也。孱守生坿記。
《九江哀》
此篇敍良玉少年及從侯恂事,多本之侯朝宗所作《寧南侯傳》。朝宗之傳雖不無文飾,然神采飛動,直逼腐遷,實爲桀作。而梅邨又與朝宗交善,觀其集中《楚兩生行》及《贈蘇昆生絶句》,其嗟歎於寧南也至矣。馬、阮敺東林,反使良玉收其名,一時清議固應如是。謝山治史,好惡過情,乃謂此書不出梅邨手筆,此未細考梅邨平時言論者也。厚誣前輩,可謂疏矣。彼鄒漪者因人成事,豈可與其師較優絀,迴護梅邨而妄以竄改坐之,亦獨何哉。孟劬閲竟再誌。
鄒漪刻此書在當日幾得禍,梁曜北有跋云:“鄒流綺以故人子弟之義,賣屋剞劂,因借當事姓名參評,逮繫獄,禍幾不測。舉家號哭,悉焚他書,笥橐一空。施愚山、曹秋岳諸公力爲解捄,乃得釋。其實書中絶無觸犯處也,蓋自莊氏史禍發生,談勝朝軼事者多懼羅織,加以官吏誅求,仇家告訐,文網之密,孰不寒心。此本無參評姓氏,殆已抽去,刻書列參評人名,本明代結習,而株連者動興大獄,鄒氏之觸忌以此,非必其書之果有違礙也。嗟乎,漢禁挾書,周設監謗,由今觀之,亦復奚益,徒爲藏家增其價值耳。”
跋《揚子法言》石硯齋重刊宋本
王逸稱雄書襍錯而無主,然論不詭於聖人。宏範依違儒玄,不寄情於一異,其於揚旨,掇之而已。群言鉤釽,亂極於今,將復欲恢弘聖緒,則此書爲先,匪獨其文之懿也。辛未首夏得本於故京記之,張爾田畏吾邨舍書。
宏範注清言溢目,大類皇侃《論語疏》,其論老氏絶學,非爲教之權,莊生妙寄,失處中之照。晉人尚玄,斯唱居然詣理音義一卷,殆是治平監學刊定所加,秦説謂五代宋初人作,未的。四月晦重記。孟劬。
子雲寂寞,既演玄文,又吐法言。兩漢篇家,純儒者寡,惟《中論》差堪庶幾耳。辛未間薄游舊京,得本於廠客。目眚彌時,鑽閲莫津,曾靡處度之,方懼罹興嗣之酷,隨身大牛篋,殆與苴潰同栖矣,絫欷奈何。孟劬。
跋《洛陽伽藍記》乙卯誦芬室本
羊衒之此書遒麗峻絜,雅與酈亭並美,劉知幾稱其有子注,今無可考。吴若準本乃依此説讀定,蓋用全謝山校《水經注》例也,不知六朝文妙正在敍事委細,脈絡蟬聯,若一簡之内正書錯注,魚貫齊行,語未斷而已生,文逐句而輒作,求諸古隽,意不其然,書缺有間矣,無爲苟便綴學,顛倒曩籍也。辛未五月,爾田書於海甸郊廬。
跋《述學》原刻本
容甫清劭之才,高漸六代,遒文澹采,懿美天然,而特多考訂之篇,豈所謂局於時者耶。集中《左氏春秋釋疑》卓有史識,《老子考異》意存翻案,純搆釀辭,斯爲最下,《墨子序》破立無準,輕彼家邱,亦非好通,而盛賞到今,信乎識曲聽真,貴在牙曠。此本原槧有江都薛氏藏印,辛未得於舊京,篋中所弆,斯爲第三本矣,記之。爾田。
容甫文出入經誥,無意寫放,而動合自然,其尤美者有魏晉之風,所次《廣陵通典》古茂似道將《華陽》,考訂諸篇吐辭温潤,不尚朴直,亦皆稱是。宋元已降,鮮能及之。余以衰晚,薄游舊輦,世方滅典,天將喪文,撫兹遺編,誰契元賞。異代相望,歎息彌襟。辛未五月爾田重記。
跋《河套志》寓園刻本
河套本中國地,自宋金淪於西夏,元滅夏,置中興等路,後廢,屬東勝等州。一代建設,史不能詳。明初因元制,設堡戍,天順後蒙古漸强,出没其間,中葉遂爲吉能俺答盤踞之區。此書略於套内駐牧情形,而於邊防險要較詳,惟好發議論,則明季餘習也。卷首有題識,署款弘謀,當是陳文恭手筆。此書成於乾隆七年,而八年文恭任陝撫,蓋陳君以贈文恭,而文恭又轉贈他人者。辛未九月爾田記。
跋《庚子京朝紀變》傳鈔本
此書又名《庚子傳信録》,湘南李希聖亦元著。李君官京曹,庚子後時從朱古微諸公游訪逸聞,筆成此書。余家曾有舊排本,無序跋,無撰人,詢諸古微丈,始知之。今此書多一序,殆後來託名歟。庚子之變,紀載頗多,惟此較翔實,能洞悉朝局。李君著有《雁影齋詩》,吴伯宛爲刻入《松鄰叢書》。壬申三月文如居士出此見示,記之。爾田。
跋《佳夢軒叢著》五石齋鈔本
《佳夢軒叢著》共十一種,宗室奕賡撰,紀先朝内廷掌故綦詳,在天潢著述中可以儷弘旺《通志綱要》、昭槤《歗亭雜録》。《清語人名譯漢》二卷爲研治國語之津梁,《侍衛瑣言》一卷多親歷之談。侍衛,滿洲語謂之蝦,而此譯作轄,典雅可誦。其餘遺聞墜掌尤草野所不能盡知者,足備史家考覈之資。書成於道光間而無刻本,文如居士得於故都人家,命精楷書者録此副墨。居士博通史乘,多藏秘笈,宜其於此編有奇嗜也。壬申孟夏張爾田校讀一過并記。
跋《春秋繁露》嘉慶乙亥蜚雲閣本
淩氏《公羊》之學當有所受,據洪梧序:“曉樓從游阮侍郎之門,誨之曰:‘武進劉君申受,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公羊》,與之講習,庶幾得其體要。’於是所見益廣,所業益進,三載歸,《蕃露》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則淩氏固亦常州之傳也。其後再傳而爲陳卓人實事求是,今文之學遂與古文考據家方駕。後又有皮鹿門本之以治他經,疏通西京墜誼,其源皆導於此。近有序皮氏書者,溝宋劉、龔、魏諸儒於陳、皮之外,知大誼而撥微言,殆非篤論。此注創通弘恉,統緒可尋,實較蘇輿疏證爲有家法,非徒斤斤訓詁名物者比。惟引書多不具出處,蹈明人陋習,未免貽餅師之誚耳。董仲舒書與先秦諸子頏頡,治之者必綜貫名理,觸類比物,方能窺其奥藏。惜乎淩氏章句之儒,所得僅此,然以視世之假今文家言敢於邪説誣民者,則又不可同日語矣。孟劬讀記。
跋《春秋繁露義證》宣統庚戌刊本
余曩纂《史微》,頗救正今古文家末流之失,蘇氏書與余書同時而出,其疏通《公羊》大誼,時有與余説不謀而合者,而持論多傷於固,又以改制受命新王諸口説一切素王權濟之微恉,悉舉而歸諸漢儒篤時之言,不知聖人遠見前覩,固非爲一姓告也,特一姓亦不能外耳。龔定庵有言:“大撓作甲子,一歲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斯爲通識,謂劉宋諸儒鑿之使深,今又矯之使淺,其爲失真也,均寧有異乎。其他類是者多,是此書之一病,要其隨文詮釋,大體完善,則固優於淩氏遠矣。《蕃露》無善本,《公羊》又易爲奇衰所託,得此差正津涂。此書舊所未見,今始獲寓目,記之壬申夏五,孟劬漫筆。
跋《元史新編》光緒乙巳慎微堂本
先朝治元史者數家,邵戒三、錢竹汀創通大例,洪文卿暨屠敬山先生多見西籍,綜理日密,然皆未遑卒業。壬申夏爲沈乙盦丈校補《蒙古源流事證》,始得見默深書,書成於洪、屠二家之前,疏舛在所不免,而文筆之優乃過之。近柯鳳蓀《新元史》名盛一時,踵事者固易爲功,以余觀之,亦未大遠於此書也。又有曾廉者著《元書》,益庳庳無足道。默深諸書皆蟠天際淵,博肆或未能盡純,自見湘儒本色,要其獨到之處不可掩也。乾嘉以來經師多,史才少,斐然之作,又豈易覯。此書爲其晚年傑著,精進不懈,前輩治學,固皆如是。爾田病中讀記。
跋《秋笳集》原刻本無卷數
漢槎詩清綺,有初唐風而體弱,沈鬱不足,當日輦下盛以才推之,哀其遇耳。柏鸞適越,歌惟《五噫》,仲悌度遼,書傳一紙,窮荒馬角,絶塞蛾眉,適以成就其名,文人遭際,非不幸也。漢槎入關有《酬健庵見贈》之作,沈歸愚所謂感激中自存身分者也。今附録於此: 金燈簾幕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别淚,重來京洛是衰顔。脱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卻嗟行戍日,鴉青江畔渡潺湲。癸酉夏得於故京,記之。爾田。
跋《蒙古世系譜》鈔本
文如居士示我博西齋舊鈔《蒙古世系譜》,取以與《蒙古源流》相較,無大出入,惟十二强汗之名此書獨具,今略釋之。一,泰綽忒之君塔爾呼代,泰綽忒即泰亦赤兀惕。塔爾呼代,其酋塔兒忽台也。二,溪里爾都忒朱爾懇之君塞臣白溪,朱爾懇即主兒乞,一作月兒斤;塞臣白溪,其酋薛徹别乞;溪里爾都忒,莎兒哈秃對音,即拉施特書所稱莎兒哈秃月兒乞也。三,古爾頒墨爾格忒之君託克託白溪,墨爾格忒即蔑兒乞,託克託白溪則部長脱黑脱,拉施特書之託克塔别乞;蔑兒乞,三種;古爾頒,蒙古語三也。四,克雷忒之君翁汙克列惕,王罕也。五,釵溪拉忒之君扎木哈,扎木哈姓扎只剌氏,釵溪拉特即扎只剌也。六,哈爾拉古忒之君阿爾薩朗,則合爾魯兀惕阿兒思蘭汗也。七,威勒忒之君呼圖哈白溪,威勒忒即衛剌特,呼圖哈白溪則拉施特書衛剌特酋忽都哈别乞也。八,和里土默特之君布都惠達爾漢,和里土默特即豁里秃馬惕,其官人歹都秃勒,此布都惠達爾漢,音雖微異,略近之也。九,威古忒之君衣忒古忒,威古忒即畏兀種;衣忒古忒,畏兀酋亦都兀惕也。十,迺滿之君太陽,乃蠻塔陽汗也。十一,他他拉之君墨古親搜爾圖,他他拉即塔塔兒,墨古親搜爾圖則塔塔兒酋蔑古真薛兀勒圖也。十二,六朱爾漆代之君象崇,朱爾漆代即主兒只歹,爲朱里真對音,六謂六部,即《松漠紀聞》所稱女真六部。象崇、想昆對音,又作詳穩,官名,非人名,此非指翁汙子鮮昆,殆因女真愛王事而傳訛也。十二强汗之中塔兒忽台、薛徹别乞爲造攻自亳之始,扎木哈與太祖争霸,王罕塔惕雄長齊盟,皆嘗大用兵力,可謂强矣。其他諸酋未必皆是勍敵,此蓋蒙人相傳舊説如是。寫質居士,聊以備考元初掌故者之一助。甲戌秋張爾田跋。
跋《虞淵沈》中、下篇原鈔本
此梅邨《綏寇紀略》卷末《虞淵沈》原稿也。取張本勘對,殊多異同之處,而此本爲優。鄒漪刻《虞淵沈》但載災異數條,而於李自成之破燕京、烈皇之殉國概未之及,與全書殊不類。此本較詳,亦但載烈皇時事,且多漳泉海寇等,各篇體例仍覺雜亂,不能倫序,頗疑此是梅邨修書時之長編,而《虞淵沈》實未竟之緒。梅邨於順治壬辰館嘉禾輯此書,其後出山,或因有所避忌,遂絶筆歟。梅邨此書原名《流寇輯略》,見談遷《北游録》,文如先生得此於北京,假觀記之。丙子六月張爾田書於尊術顯士之室。
跋《永憲録》五石齋鈔本
此書取材似全據邸抄奏報,朝廷典禮則采自《會典》諸書,遺事則參之以舊聞,可資掌故者甚多,然亦間有誤處。惟年月前後以《東華録》對勘,頗多不符,當由隨手翦録,排比成書,未遑參照所致。今但以意校正一二,未能詳也。文如先生從舊鈔本録副見示,人間恐無第三本矣。丁丑元夕張爾田扶病記。
雍正以前有塘報,有小抄,較後來邸報爲詳。此書所采似大半取之於是。又乾隆初元亦不似後此文字禁嚴,而當日通行名詞亦尚有沿滿洲舊稱者。此書得以據事直書,不加文飾,而舊談瑣故,尤多異聞,如戴名世南山一獄係理密親王發覺,而趙申喬始劾之,此皆後人所不知者。惜多病,不能取《東華録》及各種説部一一細勘耳。
又案此書名《永憲録》,疑專紀世宗憲皇帝一朝事,其起於康熙六十一年者,以世宗即位於是年也,頗疑雍正六年後必尚有數卷,而此鈔本或有殘缺亦未可知,質之文如先生,以爲何如。爾田又記。
跋《東陵盜案彙編》鉛印本
此楊璉真伽後一大變,甲帳珠襦,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讀漁洋“君王淚灑思陵地”詩,興感又不同矣。編者據事詳録,足爲異日考冬青痛史之資,殆亦有心人也。丁丑春假之五石齋,循覽記之。孟劬。
《古微堂内外集》淮南局刻本
國朝湘學皆導源船山,實以宋儒義理爲恒幹,默深雖治今文家言,亦未能免。即其高談兵食,侈論鹽河,識局一時,亦是永康、永嘉一輩,見解去西京家法尚遠。世與定庵並稱龔魏,徒以其文耳,實則兩家從入之涂貌同心異。定庵綜貫九流,多窈眇之思。默深史才優於敍事,是其所長,然文中頗喜剽竊定庵語,殊不可解,豈默深愛其文,遂襲而用之耶?此不能以實齋“言公”例之,魏不及龔,其差數正在此,彼流俗毁譽但見其表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孟劬燈下閲。
古老相傳,默深牧高郵時日坐一齋治元史,墻有梨樹,小兒攀枝墜死,默深兀然不知。及粤寇起,倉黄不知所爲。以書本見解而坐談經濟多類此。我朝承雍乾積威之後,以訖於道光,事變日殷,文網漸弛,朝廷已有不能統御言論之勢。考據陳言既感無用,書生乃折而講時務,放言改爲。世或以末流變法之禍歸咎龔魏,實亦時會使然。要其文章務爲恢奇,如天馬不受銜勒,一脱桐城窠臼,固自有其不朽者在,未可以悠悠之口横議之也。龔魏兩家學詣不必盡同,而思想之開放則同,今日視之已爲前魚,然在當日則亦莫能有三也已。丁丑十月重温一過,記之册尾。孟劬。
跋《秦邊紀略》同治壬申敬義齋本
此書載虜情及山川險阨出於親歷,故最詳,譯語皆從其舊,與乾隆間官本改定者不同,然頗有訛字,豈舊鈔如是未校耶?張石洲著《蒙古遊牧記》惜未見此,其《近疆西夷傳》可補官書所未備,沈乙盦丈曾注之,余爲編入《海日樓乙部叢著》中。辛未客北都,得於廠估,記之。爾田。
姚春木《晚學齋集·顧祖禹傳略》:“江夏劉湘煃嘗校祖禹書十餘年,魏禧弟子梁份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煃得圖以校梁書宛合,疑即份舊本,顧與祖禹書頗齟齬,湘煃合訂爲《秦邊紀略異同考》。份傳禧學,不仕,爲西邊大帥上客,其書僅存。”是此書梁份著也。份字質人,明餘遺隱,抱經世之志,遭時禁忌,故不欲彰顯其名。耐安氏舊注謂江右黄君所集,黄、梁蓋音近致訛。此吴氏刻本,與《灰盡集》所載頗多詳略,蓋傳鈔非出一源也。沈乙庵丈有合校本,考之最詳,惜不得湘煃舊圖及所著《異同考》一覈之。丁丑十二月畏吾邨舍讀。孟劬。
跋《乖庵文録》光緒三十四年傳刻本
晦鳴先生余師也,冷署潛郎,窮邊塞主,晚而從事史局十餘年,夢奠而後,篋稿叢殘,遺書遂不可問。余嘗輓以一聯云:“猶及史闕文三千牘,破硯冰髭,衆生願盡知將喪;重歌妾薄命十五年,塵瓻寒淚,一老天胡不憖遺。”今文如居士持示此册,仰瞻文藻,謦欬如接,師資日遠,記莂自慙,泫然書之。戊寅避俀難同客西郊。張爾田記。
跋《文心雕龍》乾隆三年養素堂本
《文心》一書六代覃奥,黄注行世最廣,而敷析淵旨多未洞微,考證疏舛,亦似稗販,蓋猶未脱明季注家結習,然視浦釋《史通》則雅絜矣。其後孫詒讓有校記,刊《札迻》中,吾友李審言有補註。聞江安傅氏藏元槧本,近燉煌新出唐寫本殘卷。往見吴興蔣氏樂地盦一明本,遠在胡孝轅本上,有明人識語,審爲正德倣元刻。亂離斯瘼,故篋叢殘,惜未能細勘也。此本初印,紙色古香可玩。爾田記。
跋《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重刻本
孟子有言:“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七十子後學治經皆如是,惟西漢今文家學獨得其傳。莊先生深於今文家法,然亦不盡墨守今文家之言,故所著書皆攄其所自得,期符乎古聖之心,幡天際淵,與道大適,文辭古茂,賈董之儔,不必以考據家陳言議其失得,校其離合也。先生猶子葆琛氏及劉、宋諸儒皆從先生出,始以今文學起其家。其别子爲江都淩氏,傳陳卓人。先生門人有孔廣森、邵晉涵,廣森别名他師,晉涵頗究心義訓,不欲以考據學自畫,是爲先生之道與浙學棣通之始。其後仁和龔氏、邵陽魏氏皆私淑而有得者,以其所術一變至史,龔氏之後爲譚仲秀,魏氏之後又有皮鹿門,然而儗諸先生則有間矣。道之精微,通於神明,信乎弘之者在人與。余生平治學涂轍宗會稽章氏,而於先生書則服膺無間然。循誦再周,記之。爾田。
跋《東塾讀書記》原刻本
道光中葉以還,學術思想漸變,治經者感考據之無用而又無術以易之,於是宋儒義理之學乃始緣隙復萌。蘭甫溝通漢宋,亦其一也。《記》中箴砭時流,極有精到之處,而識解未融,斷案多傷於固,鄭朱並主。異中取同,自是蘭甫所見如此,兩家歸趣未必盡然。所采群書先求貫串,再下己意,頗可爲讀書法。《毛詩》、小學數卷最佳,諸子最下。然亦間有誤處,如《穀梁》宣十五年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税畝之災也。非如非隱也之非,譏也。言蝝何以書?譏災也。譏何災?譏税畝之災也。”文義本甚明,乃以爲此駁公羊之説,而謂范注爲不通,殆所謂意過其通者非歟?其他類此者尚多。考古須察癥結,義解各有其方,不能綜觀而但割裂他説以就己見,最爲承學者之害。蘭甫尚不至此,然已微染考據家間執習氣,苟非通識,孰能辨之。爾田讀於觀我生室。
跋《金壇獄案》琉璃廠鉛印本
金壇通海一案起於紳與諸生交搆,而金壇令任體坤貪忍實成之。姚文僖《邃雅堂集》有《金壇十生事略》,據金壇公是録較此爲詳,云令乞邑紳蔣超、李銘常及大受明試爲介,謁撫丹陽。銘常多行不法,獨超謙恭樂善,時亦與焉。又云方明倫堂會議日,超至泮宫,失足墮溝中,乃返,故不及於難,可補此書所未備。虎臣以詞科巍望,晚耽禪帨,浪跡峨嵋,而終自謂前身老僧,蓋亦有託而逃,是又一陸講山矣。漁洋《蜀道集》有《懷蔣修撰虎臣》詩。《年譜》漁洋順治十八年三月赴江寧讞海寇陷宣城、金壇、儀真諸大案,皆於良善力爲保全,虎臣之不及於難,漁洋疑有力焉,而詩中未之及,殆諱之也。孟劬。
① 龍榆生回憶初識張爾田“約在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間”,張氏下世在一九四五年,兩人相交有十六七年。其實張爾田於龍榆生爲父執,龍生母亡後曾爲做家傳,且所編大學教課講義龍榆生一九一五年左右即已讀到,故張氏其名龍氏當早已熟稔。詳見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第7、11、261頁,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張暉: 《龍榆生先生年譜》,第97頁注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