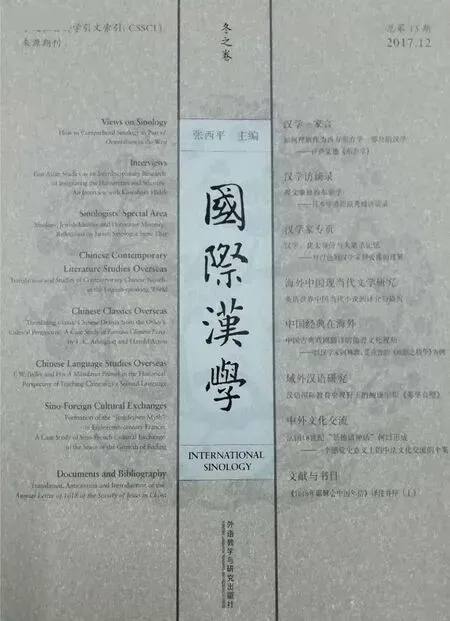理文兼修的东亚学—日本学者川原秀城访谈录
□
王雯璐(以下简称“王”):您的研究主要涉及东亚的思想史和科学史两个大的领域,请您谈谈您从事这两方面研究的契机。
川原秀城(以下简称“川原”):我主要想从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第一是我个人的求学经历。我197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后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开始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习与研究。由于有这样的教育背景,虽然转入了哲学研究,但我对理科所抱有的强烈兴趣一直存在。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我主要受教于汤浅幸孙(1917—2003)先生。汤浅幸孙先生很喜欢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社会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有一部分是音乐社会学,所谓音乐社会学,就是使用音乐来研究思想的变迁。同样的道理,我是用科学来研究思想。科学史方面,我师从薮内清(1906—2000)先生。薮内清先生的专业原为宇宙物理学,从事精密科学的分析,后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大家。薮内清先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是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思想。跟从这些先生学习的经历,使我意识到可以用思想学科之外的方法和知识来从事思想史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的传统。因为我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中国哲学史专业专攻接受教育,这一传统对我的研究有影响。京都大学中国学有理科、文科兼修的传统,如曾在史学科中设置地理学讲座等。我认为最能代表这一传统的就是地理学学者小川琢治(1870—1941),他父亲是纪伊田边藩的儒学者浅井笃(生卒年不详)。众所周知,地理学主要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小川琢治毕业于东京大学地质学科,在京都大学兼任理科(地质矿物学)和文科(地理学讲座)的老师,在两个领域都教授课程,著有《支那历史地理研究》《数理地理学》等。他对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影响很大。小川琢治的儿子中有三位著名学者,分别是次子贝塚茂树(1904—1987)、三子汤川秀树(1907—1981)、四子小川环树(1910—1993)。其中贝塚茂树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的著名学者,小川环树是京大文学部中国文学的重要学者,汤川秀树在京大理学部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可以说,在小川琢治身上可以看到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兼修的传统,而我正是受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也是我经常说的,我认为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近代以前尤其明显。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学凡》中称,理学即哲学,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科学上的变化变迁可以说和思想上的变化变迁是并行甚至是合一的,如此,科学研究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思想研究上,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另一方面,思想的变迁和发展是很难把握的,和思想相比较而言,科学的发展则非常清晰。如此一来,对于科学发展的分析能够为思想研究提供极好的思路,所以我是将研究思想史/哲学史作为最终目的进行科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意在将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应用在思想史研究中。换句话说,我认为科学史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前提。虽然在研究中没有直接谈及这一点,但是这可以说是统领我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针。
因为上面所说的三方面的影响,科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在我的研究中一直是并行的状态。我对自己研究的定位是东亚哲学史,但是用思想史和科学史两个方面来表述更容易让人理解。
王:《中国的科学思想—两汉天学考》是您早期的代表作,您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时代上来说是集中在两汉。近十几年来您关注到明清之际借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在西学研究领域发表了众多成果,如您对戴震、梅文鼎等受西学影响的清代学者以及对《律历渊源》等传教士参与编纂的书籍的研究。请您谈谈您开始西学研究的契机。
川原:我开始西学研究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前面提到的汤浅幸孙先生以前在授课时,就一直鼓励提倡我们从事清学(清代的学问)的研究,课程中我们也研读了不少清代的文献,可以说我在学生时代对清代学术一直都非常关注。此外,求学期间我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留学,当时关照我的学习和生活的是对梅文鼎很有研究的刘钝(曾任国际科技史学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席)。我当时读了他的一些研究著作,也直接和他有很多交流,逐渐产生了兴趣,虽然我是用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和他的角度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清代的科学产生了兴趣。
上面可以说是一方面。第二,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于欧洲传入的学术(西学、西教),一改以往单一的宗教史的研究角度,出现了一大批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不同于以往关注基督教如何传入中国这样的宗教史视角,而是关注西欧学术的传入对中国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也受了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风潮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在课程中对相关研究有所涉及,参加我的课程的年轻后辈中也有不少从事西学研究的,在和这些学术后辈们的讨论切磋中,我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其中安大玉有关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对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确立哲学传教路线的影响的研究可以说给了我极大的学术冲击。此外,新居洋子关注中学西传,石井刚的研究重心虽在清末民国,对这一时代的西学也多有涉足。还有我的朋友渡边纯成先生,他是数学学者,利用满语文献分析东西方学术的交流。他们都是现在日本西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王:在刚刚提到的您的早期著作《中国的科学思想—两汉天学考》中,您谈到“科学”和“思想”的关系时称,“古今中西,哲学(广义)乃至思想和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广义)密不可分,哲学中都有科学哲学的传统”。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以及中国科学史研究)中未受重视的科学思想,从科学与哲学/思想的结点及其互相影响的视角,分析董仲舒、司马迁、刘歆等汉代学者科学思想以及人文学中自然科学的要素。这里,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请您阐述一下这里的“科学思想史”和思想史研究、科学史研究的关系吗?
川原:科学史研究主要有科学学说史、科学社会史、科学思想史这大三分支。中国科学史研究中最薄弱、研究最不足的可以说是科学思想史这一分支。我从很早开始就专注这一领域。实质上来说,“科学思想史”既是科学史研究也是思想史研究。前面也谈到过的,我认为科学史研究其实也是思想史研究,或者说,科学史研究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存在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思想史研究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成果呢?科学书自古就和哲学书、历史书、文学书并列其位,从古至今我们都不缺乏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和追问。以汉代为例,思想界的硕学对天学、历算学也有专门研究,刘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尽管他是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向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我认为思想史学者对他的思想的研究非常薄弱,没能够准确说明刘歆的历史地位。理由很简单,刘歆传世的著作仅有《三统历》和保存于《汉书·艺文志》中的《七略》,而过去对《三统历》研究不足。我在《中国的科学思想—两汉天学考》中的“刘歆的三统哲学”一章中,专门探讨了《三统历》及其科学思想。比如,刘歆以《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为根据,主张律历结合的正当性,以儒学的方式说明了《三统历》用律的黄钟管9寸规定了历法计算的基本定数81。刘歆的理论得到了当时儒学界的绝对支持,其结果就是该理论被奉为规范且成为后世定说。我认为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刘歆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好的说明。
王:您近期主持编著有《西学东渐与东亚》一书,可以说代表着日本西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下面几个问题主要以这本著作的内容为中心。书中提出了“文明的对话”这一概念,用以指称明末清初东西思想交流频繁且广泛的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明清王朝对西方的外交行政、中国乃至东亚文人学者对汉译及满译西欧书的阅读与研究等。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以及作为研究框架如何应用在目前的西学研究中。
川原:“文明的对话”主要是指这一东西两大文明相对平等且和平的开展交流对话的时期。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冲突,时而也有教案发生,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对推行适应主义政策的耶稣会士是持包容态度的,这使得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士大夫能够对包括宗教在内的西欧文明整体展开广泛的对话,双方出于对新知识的好奇心相互接触、交往并展开论争,孕育出大量学术成果。
如果仅仅从传统的宗教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话,容易受到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二元对立的影响,而陷入对峙的状态,同时相对轻视西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我是从文化史研究角度进入这个领域的,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有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也有我对日本基督教传教流血的历史的思考。从文化史视角入手,很容易看到利玛窦等人以及中国传教史的不同之处。“对话”的框架使我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从而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研究题目、新的研究成果。
对话意味着开放的交流,参与对话的双方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变化。耶稣会士的立场在不断变化,中国文人在和耶稣会士的交往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新的信息,他们的态度不断产生变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双方都逐渐在变质。尽管利玛窦对中国传教贡献极大,但梵蒂冈教廷未将利玛窦册封为圣人,而同一时期来到东亚传教的沙勿略(Françisco de Xavier,1506—1552)位列圣人,我认为原因就是利玛窦的变化(变质),而变化的原因就是对话。当今我们不断强调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我认为利玛窦面对异文化时所采取的灵活的态度恰恰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我提出“文明的对话”这一概念就是想要强调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所进行的交流与对话以及双方因对话而发生的思想上的变化。这一时期之前,可以说欧洲和中国对对方的思想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不关心的。因为相互接触进而实现了对话,双方都意识到了本质上存在互相共通的东西。前面讲过,传统的宗教史研究容易走向对峙,把焦点放在“阴谋”“策略”上面。但如果从“文明的对话”的框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交流中双方都各自拿出了自身文化当中的精华,这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互相尊重,虽然对不同意的部分也有所批判,但总的来说互相都是真挚的。在这样的对话中,二者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进而促成了新兴文化—清代学术的产生。
王:您在著作中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天主教称为“西教”,将传教士带到东亚的科学技术称为“西学”,并且认为虽然西学和西教作为一个整体传播到东亚,但是对于东亚(尤其是中国清代)的士大夫来说,西学与西教层次不同,二者之间,无疑西学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构成来看,西学东渐中“西学”包括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音乐等学术,但是也有如柴田笃先生的《明末天主教与死生观》这样论及《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所包含的天主教思想与中国思想碰撞的文章。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明清之际包括利玛窦《天主实义》、艾儒略《西学凡》《职方外纪》等在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天主教思想的书籍,采用了“西学汉籍”或“汉文西学经典”等这样的总称,当然,日本的先行研究中也曾将这些书统称为“汉文西学书”“汉译西学书”等。您对于“西学”这一学术概念的范畴是如何定义的呢?明清天主教思想是否能纳入广义的“西学”内呢?
川原:我自身的理解基本上如这里所说,“西学”是指西方科学,“西教”是指基督教。把西学和西教一概而论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理解是不同的。当时文人士大夫明显没有意识到哲学中也包括科学,从最开始就认为科学只是传教的手段,科学和宗教是分离开来的。如果从中国的视点出发,强调西学是理所当然的,混为一谈则绕回到了传教史的思路中去。我在研究中尽可能清楚地区分这两方面,用“西学”来指称西方科学,当然,这里的科学是广义上的科学,逻辑学、伦理学等都包括在内,“西教”指基督教。
我认为给概念下定义需要非常谨慎,我在研究中并没有采用如法国学术传统中的,先下精确定义再在严格规定的范畴之内进行论述的方式,我认为应该在特定的文脉中来使用定义。但同时,我也同意在研究中要明确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所以我对当时传到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做了“西学”和“西教”的区分,把这个作为研究的前提。至于“汉译西学书”等概念中把宗教的东西也包含在内,我个人是持开放态度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确实如你提问中所指出的,或许有些许模糊的处理。但我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理解,从中国文化中“西学”如何被理解出发来进行研究。
王:本书的主题虽说是“西欧学术的东渐与中国、朝鲜、日本”,您在书中绪章中也谈及了西学传入东亚后,除了对中国清代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朝鲜的实学、日本的兰学有影响。但纵观全书的内容,各位学者的研究重心还是在中国,对西学传入中国后再进入日本、韩国的“二次传播”谈及较少。您认为如何能够更加全面论述西学在东亚范围内的影响?同时请您谈谈汉译西学书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播和接受。
川原:如果在更广的视野下来看“西学”与东亚的话,确实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囊括进来。比如日本在“吉利支丹时代”(キリシタン時代)①指起于基督教传入日本,至因禁教令而起的大规模迫害为止的时代,大约可认为起自1549年沙勿略到达日本,截至1639年幕府颁布一系列禁教令后彻底禁止葡萄牙籍船舶来航。—访问人注并非没有学问传入。一般认为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并不重视“知识传教”,更多是一种“大众传教”,因为传教路线的不同,学问的重要性和中国传教比起来相对较弱,但并非完全没有。近年来发现的16世纪末期在日本的耶稣会学院曾作为教材使用的《讲义要纲》(Compendium)中就包含有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存在拉丁文本及日文本,目前还能看到日本人小林谦贞(1601—1684)在17世纪后期基于该书第一部分“天球论”著成的《二仪略说》②该书目前已影印出版,见上智大学キリシタン文庫監修・編集:『イエズス会日本コレジヨの講義要綱 (コンペンディウム)』,东京:大空社,1997年。—访问人注。这一部分在考虑东亚对西学的接受时是需要考虑进来的。韩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因为韩国现在信基督教者数量大,反映在研究上,可以说基本上是以宗教史为中心的。有关西学的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等相关的汉文著作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还有大量满语文献有待研究,这也是研究西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渡边纯成有一些研究成果。同时越南、蒙古对于西学的接受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
有关在中国出版的汉译西学书传入到日本、韩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即你这里所谓的西学知识的“二次传播”,确实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日本对西学的接受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区分清楚二者并恰当衡量、评价不同途径的影响及其程度,需要文献学的基础研究的积累,对书目的调查、整理、判定是首先要做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期待将来的进展。
王:近年来,随着中外学者对梵蒂冈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耶稣会档案馆、徐家汇图书馆等国内外藏书机构的文献、档案的整理及再公布,大批学者进入西学研究的领域。日本学者比较早就进入中国西学史研究领域,佐伯好郎(1871—1965)、后藤末雄(1886—1967)、薮内清、矢泽利彦(1914—2008)等前辈学者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您认为和欧美、中国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相比,日本学者在进行西学研究上的视角有何独特性?
川原:我较早开始进行西学研究与我对日本“吉利支丹时代”的阅读和思考是有关系的,我是从日本的角度首先关注到耶稣会士带到东亚的宗教和学问。在日本及中国,基督教和西方学术都是借由耶稣会士传入,这一点上两国是相似的,日本这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早,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吉利支丹研究”这一门大学问,但相对的,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开始得比较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我最初的问题意识之一。
耶稣会士进入日本的时间比进入中国早,日本受西方学问影响的时期早于中国,而且日本人受的影响与中国稍有不同,日本人脑海中的“耶稣会士”形象不同于中国人,当然也不同于作为传播者的欧洲人。日本的传教史是充满敌意的、流血的历史,大批信徒殉教而死,这样的历史事实至今还以小说、“踏绘”等实物的形式留存在日本人的记忆当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利玛窦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身份以及意识到在中国发生的中西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是与日本的历史对照而形成的认识。从我个人来说,我的老家是九州久留米市,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在日本活动期间就曾经在这里停留过,现在这里还留存着江户时代“潜伏吉利支丹”(隠れキリシタン)①指江户时代严厉的禁教令下表面弃教实际上潜伏起来维持信仰活动的信徒及其组织。—访问人注墓地,可以说耶稣会士在日本的活动以及日本“吉利支丹时代”的历史对日本人来说是离自己生活很近、非常具体的感受和记忆。
同时,日本学者在从事中国西学史研究的时候,并非只利用中国的文献,比如在思考耶稣会是一种具有何种性质的组织等问题时,也会对耶稣会士在日本活动的文献加以考察。这当然也促使日本学者具有了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虽然在研究中或许未直接论及,但日本学者实际上是把传教士在日本的活动置于研究背景的位置。明末耶稣会的中国传教是在日本管区长指挥下开展的,其发展必然和日本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7—1598)时期的基督教史有关联并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日本的情况来谈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是不可能的。
王:您对朝鲜的思想也有诸多研究,您的著作《朝鲜数学史—朱子学的展开及其终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吗?
川原:朝鲜思想一直都是我想要研究的内容。前面也谈到了,思想史其实研究起来有其难度,朝鲜思想史也是如此,尤其是朝鲜曾被日本侵占,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朝鲜研究对于日本来说最初是殖民地研究。战后,语言、历史的研究脱离了殖民色彩,为日本学术界所接受,但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被接受,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朝鲜学者高桥亨(1878—1967)。高桥亨曾经任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机构朝鲜总督府的高官,他对朝鲜思想的研究和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使得后来只要从事朝鲜思想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他联系起来,让人联想起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研究。但若是把这样一段历史放在一旁,只考虑朝鲜思想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朝鲜作为我们的邻国,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这与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思想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必须研究朝鲜思想,而且必须批判、超越高桥亨的殖民主义背景。再回到前面说过的研究范式,我做思想史的研究是从科学史入手,首先搭建大的框架,再逐渐进入思想史的领域。《朝鲜数学史》可以说是这个大计划的第一步,最终的目标是朝鲜思想史研究。
王:也就是说您对朝鲜思想史的研究的直接目的可以说是希望超越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高桥亨对吗?
川原: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高桥亨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扎实的,不易超越。但是我从科学史入手,这和高桥亨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多年来,我撰写了不少和朝鲜科学史、思想史相关的论文,逐渐也对其整体情况有了些许自己的认识,但是还在不断耕耘,可以说还处在研究的过程中吧。
王:您至2015年退休以前一直任教于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可以请您谈谈您曾经任教的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在汉学(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重点和特征吗?
川原: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的前身是中国哲学研究室,最早可以追溯到东京大学创校初期设立的汉文学科,是和东京大学有着一样长的历史的研究科。研究室的学术传统可以说是对“东亚学”的重视。东亚各国在历史过程中孕育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与中国相关的学问,如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汉学、朝鲜李朝(1392—1910)的中国学,这些和中国本土的明清时代的学术或者此前的学术传统不完全一样。如何厘清这些和中国相关的学问在东亚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位置,也是这里所说的东亚学的一个重心。研究室有专攻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学者,但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产生的中国学问,如日本儒学、朝鲜朱子学等也是这个研究室的重要方向。
王:本次的“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您在内,共有来自国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各自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请您结合本次会议,谈一谈您对西学研究的展望。
川原:有关这个问题,在最前面也已经略微谈到过。在那个时代,来到东亚的耶稣会士代表了当时欧洲最高知识分子的水平,他们来自欧洲各个国家,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希腊语、拉丁语是基本教养,葡萄牙语也是重要的共通语,再加之自己的母语,使用语言的情况非常复杂。来到东亚的耶稣会士同时还是语言能力过人的精英,他们中间出现了汉语专家、满文专家、日语专家。他们使用各种语言撰写的各种著作、报告、信件,今天保存在世界各地。由于这样丰富而复杂的文献情况,想要弄清有关这个时代、这个群体的学问的全体面貌,凭借一人之力是远远不能实现的,只能合作,开展共同研究。当然,开展协作时的磨合也需要智慧,不管是以这段历史的发生地中国为中心开展合作,还是以传教士出发的原点欧洲为中心开展合作,关键是必须认识到这是必须齐心协力来做的学问。
有着各自的学术传统、带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的学者,通过共同研究齐聚一堂,展现出这个领域研究的多样性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仅从宗教史出发还是仅从文化史出发来研究这个领域,终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文献学的方法、科学史的方法也是不可欠缺的。我认为应该通过“对话”,这一当时的传教士们的态度,来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合作。比如从宗教史入手来研究的学者需要了解到当时包括数学、天文学、伦理学等在内的“西学”对中国文人以及东亚各国的文人学者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不能忽略这方面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积极与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展开对话。
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同发掘、整理、分享资料。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台湾、欧洲等地的学者共同合作,整理出版了大量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我觉得这是极其有益的,我自身也受益匪浅。比如在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新编天主实录》重新面世之时,我们才真正明确把握到最初罗明坚以佛僧的角度传教的实态。总之,到目前为止学者之间的合作已经有不少积累,我非常期待将来大家也可以继续齐聚一堂展开讨论与对话,共同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