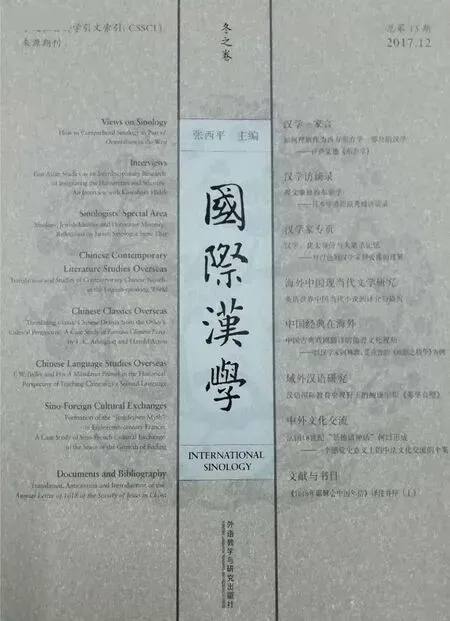中国古典戏剧翻译的他者文化视角
——以汉学家阿林敦、艾克敦的《戏剧之精华》为例*
□
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走进18世纪的西方文化一直为我国学界关注,视之为中国戏剧艺术普遍价值存在的象征。然而,这部戏的“走出去”也伴随着不解。该剧并非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作,即以同一时期的《西厢记》而论,其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可能都在其上。西人漠视“一流”,青睐“二流”,其对中国戏剧艺术的认知水平令人生疑。不过这种疑虑应该归咎于考察问题的单一文化视角的局限。如果跨出中国文化边界,从西方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戏剧,又将得出何种结论,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国家机构推动的古典戏剧外译实践中,中国的一元文化视角特征比较明显。从20世纪50年代国家外文局主导的几部戏剧的翻译,至20世纪80年代后北京大学等高校教师的翻译,及至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翻译,从原文文本选择到文本翻译策略都具有这种特征。原文本都是当今中国文化认同的经典文本,翻译文本与原文本高度相似。这一做法,似乎理所当然。可是,这些外译文本对目标文化的影响,对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大小或有无,换言之,中国文学(文化)外译行为的目标达到与否,目前还不能确定。对这些问题做出结论,还需要他者文化,或跨文化视角,中国文化的单一视角有局限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是跨文化行为这一命题的认同。仅以一种视角考察文本跨文化转换与这种行为的跨文化属性不相匹配,这种行为的分析需要超越单一的自我文化视角。20世纪30年代两位西方汉学家出版的《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①该译本的大部分皮黄戏原文出自《戏典》(伶音馆主编,上海中央书店印行,1936年出版);昆曲基于韩世昌的文本译出,散见于《六十种古曲》(汲古阁,1935年出版)。参见管兴忠、马会娟:《胡同贵族中国梦—艾克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外语学刊》2016年第2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他者文化视角,对认识单一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应有启迪。
一、《戏剧之精华》的原文本选择
《戏剧之精华》是中国古典戏剧的译文集,译者为阿林敦(L.C.Arlington,1859—1942)和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1937年由罗素和罗素(Russell & Russell)公司在当时的北平第一次发行。阿林敦为中国政府雇员,也是中国戏剧的研究者,1879年始居北京,至该书第一次发行时他在中国已生活了近60年,此前独自出版过专著《中国戏剧》(TheChinese Drama: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Shanghai:Benjamin Blom,1930),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戏剧的起源、角色、服装、化妆、舞台特征等。另一位译者艾克敦是一位年轻诗人,1932年来北京居住,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文学、诗歌,与北京的学术圈多有交往。他的另一部重要译作是《现代中国诗歌》(Modern Chinese Poetry)。与阿林敦一样,他对中国戏剧同样入迷,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北京戏迷。两人对中国戏剧都经历了从接触到入迷进而到研究的过程,最终均成为颇有成就的中国戏剧研究者。
《戏剧之精华》收录了33部中国古典戏曲译文,选译的原文之多是其翻译文本选择的第一个特点。当时北京地区的常演剧目有50多部,这33部是其中较为常见的。译者表示,译作所选的剧目达到了当时中国全国常演剧目的50%。这在其他中国古典戏剧译者包括西方的汉学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译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译一两部,从未像他俩这样选择了如此之多的文本加以翻译。按上述数据推算,当时全国常演剧目应为60多部。基于何种考虑,《戏剧之精华》译者从中选择了这33部,这是有待分析的问题。
该译作的文本选择体现于文本主题与艺术水平两个维度。从文本主题维度上看,忠孝节义、道德教化类剧目占了《戏剧之精华》的一大部分。《九更天》讲述仆人牺牲亲生女儿救赎主人,是忠义观念的化身;《一捧雪》主人逢冤,仆人舍命以救,异曲同工。《玉碑亭》男女主人公恪守道德规范,终得报偿,是节妇义男的经典。
《戏剧之精华》文本主题的选择与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译者包括西方汉学家的做法存在显著区别。阿林敦、艾克敦选择了较多的忠孝节义、道德教化剧目,这是当时中国古典戏剧舞台的主流剧目。而中国的翻译家以及其他的西方汉学家更为倾心的却是爱情题材的作品,昆曲《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白蛇传》《霸王别姬》等是这些译者的首选文本。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发行的十一部中国古典戏剧英译本中这些剧目也占了大部分。《戏剧之精华》中此类题材却不被待见,相反则是战争题材戏较多,如《长坂坡》《群英会》《战宛城》等取材三国故事的戏就有7部。战争题材的戏大多通过文臣武将的心机计谋、刚毅勇猛表现他们的忠肝义胆。就文本题材而言,这更接近当时中国古典戏剧的舞台现实。其他译者钟情的爱情题材并没有进入两位译者的法眼。《戏剧之精华》译者放弃爱情题材而选其他题材彰显了其独特的翻译动机,客观公允地向西方观众反映中国的戏曲舞台现实,按照中国戏剧舞台的本来面目选择翻译文本可能是他们的主要关切。
从与其他译者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戏剧之精华》文本选择视角的不同,而其具体文本的翻译策略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特征。《戏剧之精华》33部剧目的翻译及相关的介绍与评介差别很大,一些剧目的主要角色简介、道白、唱词等都全部译出;另一些仅仅翻译了剧情概要、部分唱段及主要角色姓名。这种差别化的翻译策略表明不同剧目受译者关注的程度存在差别。这与通常的中国戏剧文本统一的翻译策略明显不同。《战宛城》《群英会》《庆顶珠》《九更天》《一捧雪》《奇双会》《翠屏山》《汾河湾》都给予了详细翻译;而《尼姑思凡》《打城隍》《天河配》《铜网阵》《王华卖父》《五花洞》等却属于简要的翻译。两相比较,译者对中国戏剧的所谓代表性剧目厚此薄彼的态度一目了然。显然,这种差别化的翻译与译者的文化视角紧密相关。
在《戏剧之精华》入选剧目的另一维度—艺术维度上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舞台演出和戏剧音乐两方面的价值。该书中,有些三国题材的剧目入选不仅因为文本主题属于当时舞台演出的主流剧目,而演员表演的精湛超群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译者的相关评介中也说明了这点。如关于《战宛城》,译者写道“该戏的演员精英荟萃,他们中的任一位演员都足以使整个演出精彩夺目,……演员的服装别出心裁,意味深长—曹操着女人服装,满是喜感;张绣着孝服刺杀婶母。……武生演员的刀枪剑戟,身手拳脚,模仿搏斗,动作迅捷,身段柔软,无以复加。”①L.C.Arlington and Harold Acton, Famous Chinese Plays.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37, p.24.关于《长坂坡》,译者对舞台展示的战争场面叫绝,“……演出节奏鲜明;场面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其中。”②Ibid., p.37.这些描述表明一点,演员的表演是中国戏剧艺术精华的集中体现,这些剧目反映了中国戏剧的这种特征,因而入选的理由是该剧目演员的知名度及其表演的艺术水准。这反映了译者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准确把握及原文本选择的独到思考。
《捉放曹》的表演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最为深刻,曹操的残忍暴虐、冷酷无情被演员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表演打动了观众,因此成了入选的理由。《玉堂春》则因为其现实主义价值而被选中。由于中国的古典戏剧大多具有超现实的意蕴,该剧属于少数的现实主义题材,其入选是因其题材的独特,它展示了中国传统戏曲题材的多样性。译者表示,外国观众应该喜欢这部戏,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现实主义题材。中国传统戏曲中,它最接近生活的真实。③Ibid., p.419.所以尽管该戏属于少数题材,但对上了西方观众的口味,还是被译者选中,这是译者文本选择的目标文化取向特征的表现。
代表性的戏剧音乐是原文本艺术维度的另一方面,《尼姑思凡》属于这种类型。该剧的音乐以译者看来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代表了中国戏剧音乐的最高水准,因此而入选。《尼姑思凡》可能兼具文本主题与艺术,即音乐两方面之长,而另一些剧本音乐的艺术水准自身可能就打动了挑剔的译者。
该译本给出了9部戏的主要音乐唱段。译者认为,中国戏剧以综合艺术形式见长,相对西方戏剧的单一艺术形式,这是其精彩之处,所以戏剧音乐应该得到表现。这些音乐以五线谱记谱,附加在相应剧目的译文上,有的是一个完整的唱段,有的只有几行曲谱。这些曲谱与译文自身的简繁不一致,简要翻译的给了曲谱,详细翻译的却不一定有曲谱。音乐被看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音乐与译文的匹配在其他的中国戏曲翻译中多被忽略。这里《戏剧之精华》刻意表现的是中国戏剧区别于西方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形态。
音乐是中国戏剧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译文如果放弃了音乐,目标语观众看到的就是残缺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戏剧的艺术特征因而将大打折扣。这对于志在使西方观众见识中国戏剧艺术全貌的译者而言,可能是难以容忍的缺憾。译者附加的9部戏曲的音乐片段很难说就能弥补外译中国戏剧艺术的不足,但这种管中窥豹的方式至少为西方观众提供了领略中国戏剧音乐的机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完整性。这也是译者“将外国读者放在心上” 这种目标语翻译取向的再次体现。
译者给出了部分唱段的曲谱并不代表他们服膺中国戏剧音乐,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戏剧音乐过于喧闹,而且尽管节奏鲜明,但易使人昏睡,中国最好的音乐完全不是这样。这不仅是译者的个人评价,更是西方文化比较普遍的看法。之所以收入这些曲谱,是为了客观地展示真实的中国戏剧艺术,并不担心因此而有悖自己的初衷,因为中国戏剧艺术的精彩之处在于其各种表演艺术的完整统一。这应该是基于不同文化视角才能得到的印象。
阿林敦、艾克敦两位译者长时间生活在北京,亲身体验了舞台上的中国古典戏剧,他们对中国戏剧艺术的理解是直接的、全面的,也是深刻的,这在西方文化中少有人及。完整地介绍中国戏剧艺术的真实面目,使西方文化能正确地体会与己不同的艺术形式,获得异域文化的艺术体验,可能是两位译者的文化诉求,这一诉求的产生源于其观察问题的文化立场与视角。
二、《戏剧之精华》的文本翻译过程
译者的翻译过程是其西方文化视角的具体表现。《戏剧之精华》译文多有删节、添加、结构调整等特点。这样做的目的是“剔除一些平淡乏味的,甚至是重复的叙述”。④Ibid., preface, p.xii.“剔除”的依据当然是目标文化的美学观;另一方面这种调整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吻合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根据西方的戏剧观念,中国戏剧往往不合逻辑,这在习惯上看重戏剧情节的逻辑关系的西方观众看来有怪异之感,有时无法容忍。不过中国观众对此仿佛视而不见,他们认为戏剧的魅力在于名角的知名度、演唱水平。中国北方,尤以北京地区为代表,戏曲欣赏称为“听戏”,在剧场里闭目倾听名角的演唱,就是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形象表述,而演员的表演、化妆、服装、布景、灯光等方面相对而言不那么受关注。
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戏剧演出的文化语境,当翻译为英文时,这种语境就发生了变化,观众的美学观念、欣赏习惯发生了变化。如何适应新的文化语境,翻译文本做出何种调整,译者的文化视角就显出了作用。
对原文的相关部分进行删除或添加在《戏剧之精华》文本翻译中比较常见,《奇双会》的译文中,不止一处出现这类情形。原文本的第一场讲述了金星神仙与鹗神在上天安排主人公李奇在人间的运数。金星神仙讲述李奇狱中受难期限已满,今日是他父女相见之日,因此命鹗神降落县衙引导他们,鹗神领命。这场戏旨在申明,人间运数皆为天定。这样的场面符合中国文化的宿命心理,观众往往欣然接受,并不感觉有何不妥。而两位译者则跳出了中国文化视角,从西方的美学观念对这一场演出的价值加以解读。他们认为这场戏与全剧的剧情关联不大。假使在译文中留保这一场,译文文本的完整性、连贯性可能受损。更有甚者这种刻意添加的神仙戏看上去荒诞滑稽,不符合西方观众的欣赏预期。因此两位译者的译文中这一场仅仅给出了概述,剧情直接由第二场开始。他们的这种解读与该剧的另一译本,二者的差别更为明显。这部戏的另一英译文本是1935年《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上姚莘农的译文,这一场被完整译出。姚译剧名为“Madame Cassia (桂枝夫人)”,以剧中女主角名字命名。①Yao Hsin-nung, “Madame Cassia,” T’ien Hsia Monthly, 1935, Vol.1, No.4, pp.540—584.阿、艾译为“Chi Shuang-Hui, An Extraordinary Twin Meeting”。原文第六场,李奇的儿子、时为八府巡按的李保童处置了冤案制造者后,家人团聚,父亲李奇与儿子、女儿、女婿细叙家常,其中的多行对话涉及生活、官场现状,以及父亲的感慨等。这一段阿、艾译文里没有出现,姚译文却悉数保留。另一处明显删节出现在第二场开始。鹗神再次出现在李奇监房,告知受金星神之命查询冤情,李奇哭诉,女儿桂枝遂听到有人深夜哭泣。阿、艾的译文直接由桂枝在县衙家中听到李奇哭声开始。李奇向鹗神哭冤的部分删除后,情节的发展更为直截了当。李奇这场戏的译文还有译者的添加。第二场狱卒进入监室向李奇索钱,原文写道:
禁子:自你进入监门以来从没见你花过一个小钱,今天把你叫来,或是有钱有钞的,拿出些来也好给我使用使用吓。
李奇:哎呀大哥吓,想老犯人遭此不白之冤枉,所有家产被杨氏霸占去了,哪有银钱送与大哥使用,望大哥行个方便罢。
禁子:好吓来一个行事方便,来两个行事方便,那我也方便不了那么多吓。告诉你说,有银子趁早拿出来,要是没有,今儿我就活活地打死你。②《曲谱选刊·奇双会》,北京:中华书局,1922年,第1731—1732页。
译文:
Warder There is no oil for the lamps,money is needed.If you have any,it is high time to hand it over.
Li Chi In such dire straits how can I produce money?
Warder Just listen to this: Those who dwell on mountains depend on timber for living;those who dwell by a river depend upon waters.Never mind how much it is, you have got to pay up; otherwise, look out yourself! I’ll give you a taste of ankle squeezers, and even worse.③Yao, op.cit., p.543.
可以看出译文为狱卒增加了索钱的借口,no oil for the lamps,尽管说的人和听的人心知肚明属于无稽之谈,但这比起原文直来直去的强索听上去至少婉转了一些。添加的这一句,丰富了狱卒的心理活动,其形象个性得到增强。随后译文添加的内容使这一效果更为显著,即, those who dwell on mountains depend upon timber for living;those who dwell by a river depend upon waters(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句听上去像监犯索钱是监牢的惯例,并非我狱卒独出心裁。犯人不给狱卒银钱倒有些不合规矩了。狱卒贪婪、强词夺理的形象跃然纸上。中国的古典戏曲中,狱卒已被定型为卑贱下作、不择手段的一类人,他们的形象已被脸谱化。显然译者以不同的视角看到了中国戏剧人物模式化的不足,为了克服这点,他们有意添加了译文,以增强人物的个性。
原剧中李奇叙述杨氏攫取家产的部分先后出现两次,《戏剧之精华》删去一次。而在姚译文中,两段内容都被译出。姚译文更看重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而《戏剧之精华》则看重目标语观众的戏剧体验。两种取向形成了两种翻译策略,反映了两种文化视角。阿、艾的文化视角在“译者前言”中谈到姚氏译文时有过明确表述:姚译文细腻入微,有学术翻译的味道(sensitive and scholarly translation),是否收入他的译文我们有所犹豫,但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理念—以外国戏剧观众为取向(with foreign playgoers in our mind)。①Arlington and Acton, op.cit., p.xxx.
类似的增删操本在该译本的另一些剧目中也经常出现,如《打鱼杀家》《九更天》等都有类似情形。
对原文进行结构次序的调整是两位译者的又一翻译特点。《群英会》全剧结构就做了这种调整。《群英会》原文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大致顺序是,周瑜设局(为谋害孔明让他去截取曹操军粮),蒋干盗书,诛杀大将(曹操诛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周、孔定计,打黄盖,草船借箭,借东风,曹军大败。阿林敦、艾克敦的译文结构是,以孔明草船借箭开始,随后是打黄盖,之后是蒋干盗书,最后是借东风曹军大败。删掉几个场次并调整次序后,译文的情节简化明晰,统帅的文韬武略,谋臣的神机妙算,武将的忠义赤诚等得以凸显,全剧的英雄群像被显著拔高。很明显这是西方文化对《群英会》的解读,而中国文化的解读则褒贬互见,全面褒奖了心机近乎神仙的孔明,部分贬抑了雄才大略却心胸狭小的周瑜。
译文对原文的增删、结构调整处处表现了译者的他者文化视角,但这类操作在其他的翻译中也经常出现,不能说是《戏剧之精华》译者他者文化视角的独特表现。而最能体现这两位译者解读视角的要首推他们对中国戏剧人物与西方历史人物的比较。这种比较本质上是译者建构了两种文化经验的连接通道,为西方观众理解中国文化确立了文化心理基础,这是译者创立的最为有效的文化障碍克服手段。这些被比较的西方文化人物早已内化于西方观众的头脑,沉淀为西方文化经验的组成部分。译者诉诸这种文化经验,中国戏剧和西方文化就形成了心灵沟通,目标语接受者进入中国戏曲的文化世界就具备了文化心理基础。《玉堂春》中的女主角苏三对爱的执著,仿佛就是巴黎的曼农·莱斯科(Manon Lescaut,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歌剧《曼农·莱斯科》中的女主角)的中国版,因而拨动了观众的心弦(the figure that stirs the heart)。②Ibid., p.419.两部剧中的女主角都是各自文化中挚爱情感的化身,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在译著成书的年代,由于文化的隔阂,西方文化对中国戏剧存在偏见。与这种偏见不同,译者对《玉堂春》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显然这是西方式的解读,否则,《玉堂春》这部中国戏的艺术价值不会是现实主义,而仍然是一部道德剧。译者认为,这部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与其他中国戏相比,它的人物不落俗套,鲜活生动。卖花的金哥、狱卒崇公道心地善良、古道热肠,难得一见,如果遇上优秀的演员,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熟人。③Ibid.接下来译者表示:该剧超越了那种刻板的儒家伦理道德剧(above the strait-jacket Confucian moralityplays),因此,西方文化关于中国戏剧往往单调重复的看法在《玉堂春》这部戏中是站不住脚的。④Ibid.
在《捉放曹》的评介中,对曹操的个性,译者用了狡诈、残忍、丧失人伦、自负等九个形容词。为使西方观众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人物,译者再次借用西方观众熟悉的历史人物,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与曹操的个性相比。这为西方观众确立了一个理解人物的参照点,使他们自身的文化经验能够得以参与到异域文化人物理解的过程中去。对该剧另一人物陈宫的评价,西方话语特征一目了然,“公正地讲,陈宫性格懦弱,他人的巧言令色使其背叛了自己的朝廷,这是个机会主义者。”①Ibid., p.151.译者认为《群英会》处处体现了心机计谋,即使《普林西比岛》(del Principe)的作者面对此剧中比比皆是的口是心非之人也要自愧不如。②Ibid., p.210.这种解读是译者他者文化视角的客观印证,也是译者无法摆脱的文化立场的体现。他们的他者文化解读被用于两种文化的连接沟通,克服中西戏剧的文化隔膜,这是《戏剧之精华》对中国戏剧外译的重要启示。
结论
文学(文化)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它一方面联结原文文本,另一方面联结译文文本。不同于单一文化边界内的行为,通常主要受单一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都对这种翻译行为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单一文化内的行为它具有跨文化特征,这就要求采用多元文化视角分析问题。目前中国戏剧,或者文学(文化)翻译存在不少疑惑,主要原因是对这种行为的跨文化本质缺乏深入的认识,“走出去”的翻译依然没有摆脱原文本与译文本一致性关系的羁绊,从自我文化出发选择自我喜爱的文本,忽视了目标文化的感受,没能走出单一的自我文化视角的局限,因此对基于他者文化视角的翻译行为不解大于理解。当下“走出去”的翻译实践中这类情形不乏其例。20世纪中期,我国文学史上并无大名的唐代诗人寒山在美国颇受青睐,成为美国社会所知不多的中国诗人中较受关注的一位。中美文化对中国诗人的接受不同,很明显,这与两种文化的不同视角有关。
跨文化交流的要义是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他者文化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何感受,翻译时必须清楚。这就需要进入他者文化视角,以他者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从他者视角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走出去”,这是文学外译行为能否实现其行为目标的前提。
《戏剧之精华》深化了我们对他者文化视角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翻译“走出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自我文化视角的局限。同时译者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他者文化解读,使我们能够得到先前单一视角无法得到的东西,这又促使我们对原文本进行反思,对原文本的认识也由此得以深入。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转向他者文化视角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文化,当然我们也难以放弃,而是要坚持多元文化立场,在自我文化基础上观照他者文化,在两种文化间不断切换,用两种文化视角不断比较分析,由此获得不同的文化体验。中国文化将这种认识过程概括为“和实生物”,两种不同的事物接触,不是一种化掉另一种,也不是两种的单纯融合,而是“和”之后生成新的事物,事物由此不断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对事物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和实生物”是跨文化交流应有的情怀,也可视作中国文化“走出去”转向他者文化视角,或跨文化视角的中国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