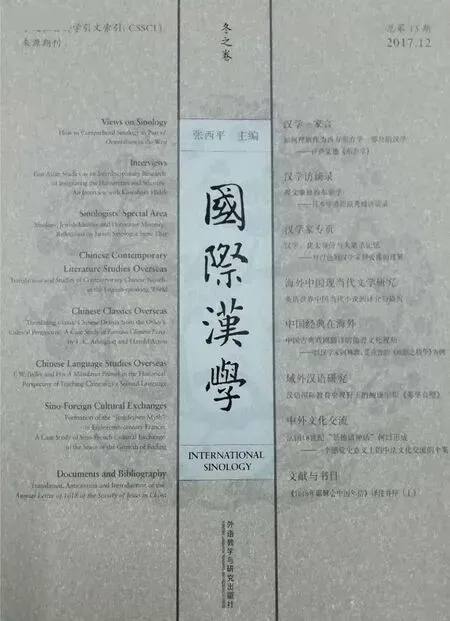如何理解作为西方东方学一部分的汉学—评萨义德《东方学》
□
一、萨义德的《东方学》
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后到美国求学,1963年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使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东方学》这本书运用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理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的东方学的产生以及伴随着的对东方的想象,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主义……指几个相互重叠的领域:首先,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变化着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具有四千年历史的一种关系;第二,自19世纪初始专门研究诸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学科;第三,关于世界上目前非常重要、政治上紧迫的一个叫作东方的地区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想和幻想。东方主义这三个方面的相对公分母就是把西方和东方相分隔的那条界限。”①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萨义德认为,虽然当代西方的东方学的成果和知识绝大部分是非政治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的,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②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但实际上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都会有意无意地卷入阶级与不同信仰体系之争,这样政治就必然对其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于是,他就问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是否参与了帝国主义的传统,参与了西方对东方的任意的划定,对东方形象的塑造。这是可以肯定的。由此,他认为东方学的兴起、发展和强大就和政治、和西方对东方一系列政治活动联在一起,它再也不是纯学术的了。
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他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建立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urch Council of Vienne)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Bologna)、阿维农(Avignon)和萨拉曼卡(Salamanca)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在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当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土地从35%扩大到了85%时,西方的东方学也随着这种扩张而急速地发展起来。在西方东方学的发展过程中,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这一权利与范围不仅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关于东方的精确而确定的知识,而且生产出有着自身生命的第二位的知识—这些知识隐藏在‘东方的’故事、关于神秘东方的神话、亚洲是不可理喻的这类观念中,被基尔南(V.G.Kiernan)恰当地称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③同上,第65页。这就是说,东方始终作为“他者”存在于西方之外,西方的东方学在获取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同时,将东方东方化,在东方学的理论中,一边是西方人,一边是东方人,前者是理性的,爱好和平,宽容大度,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但东方人没有这些特点,他们所具有的是相反的特点,这样,西方基督教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对东方进行了改编。
在18世纪欧洲扩张的过程中,东方学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但这绝不意味着基督教那种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被简单地消除了,而是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东方学通过自己的知识重构了东方。萨义德认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东方学同样“还保存着一种重构的宗教欲望,一种自然化了的超自然论,此乃东方学话语中根深蒂固的本性。”①同上,第157页。
这就是说,18世纪后西方的东方学虽然按照一种实证的方法开始研究东方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使东方学完全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再不是基督教神学下的东方学,而是世俗化了的、科学的东方学。关于东方的一切研究方法都是东方学家们创造的,在这种方法下,东方再生。但在萨义德看来这一切并非像东方学家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由于将东方带进了现代性之中,东方学家获得了为其方法和立场进行吹嘘的资本,自己仿佛成了世俗的创世者,就像上帝创造旧世界一样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东方学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东方的客观知识,而是从以前继承过来的,为语言学这样的学科所世俗化、重新处理、重新构建的一套结构,而这些结构本身又是自然化、现代化和世俗化了的基督教超自然论的替代品(或变体)。”②同上,第158页。这里萨义德对18世纪后的西方东方学持同样的批判态度,更直接地说:“说现代东方学一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危言耸听。”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有两个基本的论点支撑着他的论述:第一,任何学术都是受制于其发生的文化,因此其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西方的东方学发生在西方学术环境中,所以,它必然受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如他所说:“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其次,学术性和想象性写作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其形象、假设和意图的限制的;最后,像学术形态的东方学这样一门‘科学’所带来的进展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③同上,第257页。这实际是他对福柯话语理论以及知识和权力关系理论的运用,从后现代的立场质疑东方学的合法性。
第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反观自己的文化对立面。萨义德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④同上,第426—427页。
根据这两个基本观点,通过对西方东方学的历史和文本的考察,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东方学所塑造的东方形象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学是西方东方知识的提供者,他们所介绍的东方不仅作为一种知识,同时也作为西方的社会文化影响了西方的文化界。萨义德说:“作为一种表述西方体制化的东方知识的学科,东方学同时在东方、东方学家和西方的东方学‘消费者’这三个方向施加其力量。”⑤同上,第86页。
所以,在《东方学》中,萨义德除了考察西方东方学的历史以外,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东方,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西方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对东方做出了不同的形象想象。在福楼拜那里,东方成为使西方再生的地方,“现代人在不断进步,欧洲会通过亚洲而获得新生”。在布瓦尔(Alexis Bouvard,1767—1843)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那里,印度所代表的东方成为克服西方物质主义的灵丹妙药,西方文化会在印度文化中再生。而在19世纪的一些西方思想家眼中,东方又成为其反衬的代表,西方代表着进步、文明,而印度、中国只能代表着落后、愚昧。
这样,他认为,在东方学中的东方已经不是真正自然的东方,而是西方东方学所塑造出来的东方,“‘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①同上,第6—7页。当然,自然的东方依然存在,但在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东方学中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为西方而存在,作为西方他者的存在,是人为存在的东方。
第二,东方学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萨义德试图通过东方学的历史研究,说明在东方学的知识的背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权力是如何塑造知识、影响知识和决定知识的。19世纪后,西方的东方学得到快速的发展,像法国的亚洲研究会(Société Asiatique)、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德国东方研究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美国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员急速增长,各国东方学教授的位置增加,研究东方的刊物增加。但在这种学术繁荣的背后是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扩展,是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的利益的入侵。东方学不仅仅在自己的观念上受到西方每一个时期思想的影响,同时,在实际的知识运作和知识产生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所在国家力量的影响。东方学和其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骡、马、象、牛听命于车夫,车夫听命于中士,中士听命于中尉,中尉听命于上尉,上尉听命于少校,少校听命于上校,上校听命于准将,准将听命于上将,上将听命于总督,总督听命于女王。”萨义德说“东方学就像这一假想的怪异的控制链”。东方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它受制于西方的国家利益,它是为西方的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的。
第三,东方学是学术的失败。根据上面两条的分析,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学没能与人类经验相认同,也没有将这一地区的经验视为人类经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对东方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②同上,第421页。
二、西方汉学和《东方学》
我们为何用这些篇幅来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呢?《东方学》和我们这里所讲的汉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和萨义德的《东方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西方汉学在学科上隶属于西方的东方学,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主要讲的是西方的阿拉伯学、伊斯兰学,而且在时间上是以19世纪为主的。但他在书中也涉及汉学,他在书中也多次谈到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汉学、中国学包括在他所讲的东方学之中是明确无误的。这样,在我们从事西方汉学的研究时,萨义德所提出的对西方东方学的评论和看法我们就不能回避。
其次,西方汉学(中国学)家已经注意到萨义德的理论,并成为他们变革自己研究方法的重要的理论根据,这点美国当代中国学家柯文(Paul A.Cohen)讲得很清楚,柯文在对他之前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展开批评时说:“我们尽可不必同意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所有批评,不过仍然可以接受他的比较概括的见解,即认为一切智力上的探讨,一切求知的过程,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③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页。如果要理解柯文的中国学研究模式,了解萨义德是个必需的前提。
同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按照萨义德的理论来评价域外汉学。有的学者认为“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虚构与想象,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盖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隐秘而不易察觉。”①参见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汉学可以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服务于而且强化了这种殖民扩张的需要。”②参见张松建:《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这些学者完全按照《东方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西方汉学,认为“汉学与其说是假设客观真理的‘科学’,不如说是具有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叙事’”③参见《汉学或“汉学主义”》。。如果按照《东方学》的分析,在西方的东方学中有一种“东方主义”,那么,在西方汉学中也同样有一个“汉学主义”,这种“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一样,只是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毫无真理可言。④参见顾明栋著,张强等译:《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如果以上可以成立,他们顺理成章地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汉学研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热情有余,反思不足,根本在于从未对西方汉学的合法性做过反思,他们将其称为“自我汉学化”,如同萨义德说过的“自我东方化”一样。这样,对汉学的翻译和介绍很可能成为“学术殖民”运动。在这些学者看来,“起劲地介绍西方汉学的中国学者们似乎患上了一种‘集体遗忘症’,对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被西方殖民的那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也是出于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想得到快乐,如果他能够避免痛苦的话,不过,我却想冒昧地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与西方殖民扩张这二者之间的若明若暗的呼应关系,未能从西方支配性的殖民话语中走出来,以清明的理性、辩证的精神和审慎的文化历史观,对待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⑤参见《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
这样,我们看到,如果不回答萨义德以及对汉学质疑的学者的这些问题,我们不仅无法揭示海外中国学(汉学)的变迁,而且国内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合法性也不再存在,我们对西方汉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就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成为在制造“学术殖民运动”。问题如此严重,对这些问题必须回答。
三、对《东方学》的思考
不可否认,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对长期以来的欧洲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系统研究,是对西方殖民时代所开始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的批评。西方不仅仅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奴役和压迫了东方,而且在文化和学术上形成了一整套对东方的奴役和压迫,一种文化的歧视。萨义德的立足点在西方,通过对东方主义的批评来批判西方主流文化在其社会生活、文学作品、思想观念上对东方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是东方主义与东方的关系,不是历史地求证东方主义的观点是否适用东方,也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而是专门研究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它也是一种西方统治、重新建构和支配东方的话语。”⑥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展开批判时,尽管文风犀利,但在理论上有自身的问题。
首先,纯粹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萨义德根据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和福柯的理论揭示了西方东方学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东方学的产生与西方殖民扩张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但纯粹知识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纯粹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萨义德的说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说“当代西方(在此我主要指美国)产生的具有决定影响的知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的,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①《东方学》,第13页。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说没有人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那些自称纯学术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知识”,“文学与文化常常被假定为与政治甚至与历史没有任何牵连;但对我来说常常并非如此,我对东方学的研究使我确信(而且我希望也能使我的文学研究同行们确信):社会和文化只能放在一起研究。”②同上,第36页。萨义德的这个理论矛盾的原因在于“他拜过的两个老师的思想不一致,这就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③丹尼斯·波特:《东方主义及其问题》,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45页。
从理论上说,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受到其固有的潜在的政治意识的影响,这点维柯(Giovanni B.Vico,1668—1744)说得对,人类历史是人自身创造的历史,对其的研究不可能像研究自然对象那样。但这样一种联系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它和学术的联系是深层次的、间接的。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公共意识,一种集体的认知,因此作为个体学术研究的纯学术和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区别。完全不承认学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幼稚的;将学术和政治完全等同,混淆二者的区别,将学术政治化是片面的。
实际上,萨义德受到尼采(Friedrich W.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从根本上否认真理与知识,认为任何真理都是幻象。④《东方学》,第259页。萨义德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对于任何事物,真正的再现是否可能。”⑤艾贾兹·阿赫默德:《东方主义及其后》,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62页。这就是说,真实的陈述可能吗?这个问题说明不仅由于学术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从而使学术失去真理性,而且任何人文学术的言说方式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的东方学言说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学术上再现东方,无论是整体上的研究还是个别方面的研究,都是一种再现。如果这种再现是不可能的,整个学术就不再具有真理性。任何知识和真理都是一种陈述,都是在理论上的再现,如果这个根本点受到怀疑,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和真理都要受到怀疑。
而从理论上看,萨义德的这两个方面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强调学术、知识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将学术、知识与政治混同化、一体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任何对事物陈述的知识、真理都是虚幻,都是不可靠的,对以实证为特点的19世纪以来的所有知识和真理形态表示怀疑,对以此为基础的西方东方学的知识和认识形式做根本的否认。萨义德在理论上面临的这些问题显而易见。
其次,纯粹知识和想象之间的关系。萨义德认为,东方是西方的他者,是西方精神的投影,是西方的想象。这样,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东方只是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正的东方。“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东方学是一种狂热的妄想,是另一种知识类型,比如说,与普通的历史知识不同的知识类型。”⑥《东方学》,第93页。实际上,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东方学家,一个是东方学的消费者(按萨义德的说法),不可否认在东方学家那里也存在想象,但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出现。而在东方学的消费者那里,他们根据东方学家提供的知识做艺术的、文学的、戏剧的再创造,从而构成大众化的东方想象。尽管,在东方学家那里也有想象的部分,但不可否认,他们仍然提供了关于东方的基本的、常识性的知识。在谈到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时,萨义德常常以“东方学的消费者”的作品来做分析。实际上,东方学家那里作为知识形态的东方和“东方学的消费者”的艺术家、文学家那里作为艺术和文学形态的东方是相互联系而有区别的。在前者那里主要是作为知识形态的东方,在后者那里主要是作为想象的东方。萨义德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更多是以后者代替前者,用想象的东方代替知识的东方,将想象和知识混为一谈。因此,将整个西方的东方学虚无化,将整个西方的东方学知识虚无化,从近代西方东方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样看显然是偏激的。
实际上,萨义德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摇摆不定的。他所关心的是那种在本质主义的思维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东方学,对东方学的学术努力和成果他并不完全反对。如他说的“我之所以要反对我所称的东方学,并非因为它是以古代文本为基础对东方语言、社会和民族所展开的研究,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东方学是从一个毫无批评意识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处理多元、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的……尽管有东方学家试图对作为一种公正客观的学术努力的东方学与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进行微妙区分,然而却不可能单方面地与东方学以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为开端的现代全球化新阶段所得以产生的总体帝国主义语境分开。”①《东方学》,第428—429页。作为公正客观的东方学术和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之间的区分,他说得并不清楚,他关心的只是作为思想体系的东方学。实际上,他本人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的细节并不很了解。
四、对汉学研究批评者的回应
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的批评基本上套用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理论,将“东方主义”转换成“汉学主义”,由此展开了对西方文化中的“汉学主义”的批判。
首先,他们认为“汉学”转变为“汉学主义”的根本点在于:汉学并不具有客观性,它只是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些批评者认为“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究竟是‘真理’还是‘神话’?究竟是一个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西方的中国研究某一个时期出现想当然的误解或虚构,尚可以就那段历史讨论那段,如果这种误解反复出现,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不外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汉学,而应该怀疑西方汉学或中国研究这一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合法性问题。或许汉学的所谓的‘客观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汉学更像是一种‘叙事’,一种能动主动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的现实,而是在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创造表现意义。”②参见《汉学或“汉学主义”》。
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究竟是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研究,还是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是问题的核心。批评者其实并无多少创造性,不过是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换一下,将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变为对汉学的批判而已。
我们不否认西方汉学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和西方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都受到当时西方社会主导思想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传教士汉学阶段,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是在传教学的框架中展开的,宗教的热情直接影响了他们研究的深度。但这并未影响这些传教士们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比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时代的游记汉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他们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它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中确有想象的成分,但同时也有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的报道和研究,这二者是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并不能笼统地说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一副浪漫的图画,毫无真实可言。西方汉学在“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西域研究,高本汉(Klas B.J.Karlgren,1889—1978)的中国语言研究,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蒙古史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了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所有中国研究者的认可。虽然,即使在专业汉学时期,汉学仍摆脱不掉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样的影响绝不像这些批评者所说的“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正确:“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的表现技巧……”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国内的汉学研究批评者不过跟着萨义德的话说,将整个西方汉学研究归为意识形态,否认其学术的客观性。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考方法,同时,这样的结论也是很随意的。西方汉学几百年来在对中国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成果,从汉学来看,这是个常识。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一股脑地把西方汉学统统说成意识形态而扔在一边,或者毫不分析地把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捧上天,而是具体地分析在不同的时代,西方汉学和其时代的关系,对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哪些是真实的知识,哪些是想象的成分,哪些是当时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哪些是他们对中国研究的贡献。这二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从哲学理论上讲,后现代的认知理论,尽管解释了知识与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从权力等角度说明知识与客观现实联系的条件性,但并不能由此而完全否认19世纪以来在实证主义思想下人类所获得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后现代的认知理论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新解释知识的角度而已,如果完全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见,完全采用这些批评者照搬的后现代理论,那么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要遭到彻底的摒弃。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源于西方,几乎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必然具有文化上的边界,并且,必然与更大的、和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话语结构结合在一起。因此,对此除了“批判性”的摒弃之外,任何汲取都会受到怀疑。
其次,这些批评者在对汉学的批评中将西方汉学发展的复杂历史简单化、概念化。这些批评者认为“早期汉学经历了一个‘赋、比、兴’阶段。‘赋’指关于中国的信息大量的介绍铺陈;‘比’指牵强比附中国与西方;‘兴’指借助被美化的中国形象,表达自己的宗教或世俗理想。商人们贩运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的时候,传教士们贩运‘孔夫子的哲学’或‘中国的道德神学’。传教士美化的中国形象成为哲学家启蒙批判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中国的道德政治或开明君主典范。汉学被绞进启蒙文化的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汉学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①同上。实际上欧洲早期对中国的研究要比这里说的“赋、比、兴”三个阶段复杂得多。来华传教士不仅有欧洲语言的著作,也有大量的中文著作,传教士汉学家不仅参与了欧洲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也参与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欧洲早期汉学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在知识层面上也同样产生了影响,而这些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西方早期汉学在知识和思想上对欧洲近代东方知识与思想影响的研究刚刚开始,例如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这些批评者们肯定没有好好读过,他们只是看了一些只言片语的英文介绍,就开始做这样的评论,这在学术上是很不严肃的。这些汉学研究的批评者对欧洲早期汉学著作,特别是传教士汉学原著的阅读和研究是很有限的。
在谈到19世纪的汉学时,他们说:“经典汉学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纯粹文本中的中国。这种学科假设的真正意义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没有现实性的国家,一种已经死去的文明。”②同上。这样的判断只是揭示了西方19世纪汉学的一个方面,西方专业汉学诞生后在研究上的进展,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和变化要比这样的概括复杂得多。这种对西方汉学的概括既没有把握住西方19世纪汉学的特点,更谈不上对整个西方汉学的把握。历史的实际情况是,19世纪西方的汉学研究并不都是将中国文明看成木乃伊式的文明,对现实的中国研究是19世纪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最早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后来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中国出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都在研究当时现实的中国,对中国文明的看法也有多种观点。可以这样说,这些批评者对西方汉学历史了解得很不全面,对基本的著作、基本的人物大都没有做真正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从宏观上正确地把握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和各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19世纪的西方汉学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其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些文章谈起西方汉学来很潇洒,走笔几百年,轻松自如。但实际上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历史并未深入研究,理论太多,个案研究太少;宏观概括太多,具体文本研究薄弱;研究理论跟着西方走,少有创造,这是目前汉学研究批评者的主要特点。
最后,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和介绍,这是我们和汉学研究批评者的重要分歧。
这些批评者认为:“汉学包含着‘汉学主义’,汉学的知识合法性出现危机,这种危机还不限于西方汉学,还可能危及中国对西方汉学的译介研究的学术理念,甚至可能质疑到中国学术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说,西方汉学本身是“汉学主义”,在学术上没有合法性,因而今天在中国介绍西方汉学也同样没有合法性,这真是危言耸听。事情并未结束,批评者认为,汉学的译介还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观念殖民”。因为在介绍西方汉学时使中国学术“不仅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的世界秩序,也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学术观念的世界秩序。中国的现代思想化首先认同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与进步观念,然后才认同西方自由进步与中国专制停滞的观念。自由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观念,既意味着一种世界知识秩序,又意味着一种世界权力秩序。自由进步使西方野蛮的冲击变得合理甚至正义,专制停滞使中国的衰败混乱变成某种历史必然的惩罚。在这种汉学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西方用中国文明作为‘他者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却从这个‘他者形象’中认同自身,汉学叙事既为中国的现代化展示了某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又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埋伏下致命的文化陷阱。西方的文化霸权通过学术话语方式达成。”①同上。
这样的分析和推断正反映了批评者对西方汉学的表面了解,因为西方汉学的思想背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是很不相同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涉及西方汉学的各个时期、各个不同的国家,这位批评者所说的那种西方汉学著作中所包含的“自由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观念”主要是19世纪西方汉学的一种重要思想背景(在19世纪也不可一概而论),在17—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主导的不是这样的观念,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著作中就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在当代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中则有着完全相反的理论倾向和思想背景,例如美国当代中国学的研究著作中有不少学者所持的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恰好和这位批评者所说的相反。因此,用西方汉学一个时期的思想倾向或特点,来批评当前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说明批评者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西方汉学的历史和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文不对题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出,认真地做好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从文本和人物入手,展开扎扎实实的学术史研究是多么的重要。没有扎实的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就做宏大叙事,没有深入的个案研究就做一般性的概括和结论,这正是这位批评者的问题所在。
批评者认为“必须警惕汉学与汉学译介研究中的‘汉学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汉学热,由于缺乏学科批判意识造成的‘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紧迫的问题”,“学界无意识的‘自我汉学化’,实际上是学术文化的自我异化,非批判性的译介研究最终将成为汉学主义的一部分,成为西方学术文化霸权的工具。……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的译介研究,在没有明确学科意识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学术殖民’运动”。②同上。
提出学科的批判意识是对的,对西方汉学进行翻译和介绍的同时也应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一直是笔者的立场。但这里有两点要加以说明:
第一,首先要做好翻译和介绍工作,而后才能展开批判性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前一时期主要的任务是翻译和介绍,如果连西方汉学的基本著作都不了解,如何进行批判性研究呢?从汉学研究的批评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西方汉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才使批评者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在没有了解西方汉学的基本情况下的批判大多是会产生问题的。因此,目前展开对西方汉学的批判性研究固然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但从整个学科的发展来看,对西方汉学主要著作和人物的研究,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仍是当前我们所要继续展开的工作,这项工作仍是刚刚开始。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中国学术的研究。严绍璗先生在谈到海外汉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①参见严绍璗:《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第五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汉学的存在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在西方汉学的各个时期,无论在思想背景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与批判的地方,但绝不像这些批评者所说,整个西方汉学都“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这样的结论是对汉学研究的无知。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汉学的存在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绝不是说在西方思想文化进程中有“汉学主义”,我们对汉学的介绍就会造成对“中国学术的殖民”。对西方汉学著作的介绍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无论是将其作为学术的对象,还是作为批判研究的对象,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都刺激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排斥西方汉学著作,显然是一种狭隘的学术心态。当下,我们提倡文化自觉,自然要梳理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这点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就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站在中国文化立场对西方汉学展开批判性阅读与对话将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萨义德的书出版后在东方产生了他想象不到的结果,他在自己书的再版后记中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②《东方学》,第426页。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身份或认同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复合性的,这一点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空前加剧、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尤显明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什么是纯粹的、绝对的、本真的族性或认同。”③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这样的理解也完全可以用于汉学研究,那些对汉学研究进行批评的学者,借着萨义德的理论,将对汉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看作是“学术殖民”,似乎没有这些汉学著作,中国学术或许更纯粹。他们似乎站在一种更加维护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立场上,实际上,这恰恰是萨义德所反对的那种将“西方”和“东方”本质化的认识,这里不过表现为将中国学术和汉学本质化,使之对立而已。
学术的发展如同文化的发展一样,正是在与不同文化的交锋、相遇与融合中,自身的文化得到发展,中国学术也正是在与包括汉学在内的各种学术形态的对话、交锋、批判中得到发展。引进、介绍就是对话的开始,翻译、介绍就是文化和学术多元融合的开始。这些批评者套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用对“学术殖民”的警觉表达其对中国学术的认同,实际上这是在确立一种新的东方与西方、中国学术与汉学的二元对立,或者说他们实际上“在延续并强化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和族性观念,后者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要解构的”④同上,第194页。。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批评者在理论上并无任何的创造,他们不过是在重复着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而且这种重复是走了样的重复,是对《东方学》的一种扭曲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