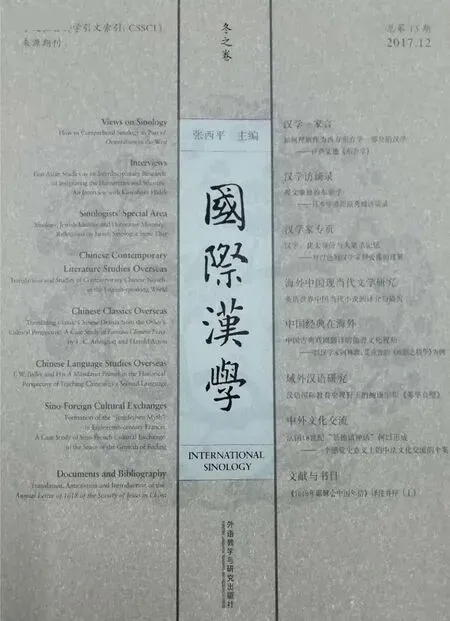汉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
汉学在中国曾有多种含义与理解。它最早产生于汉代,乃是对《诗经》等儒家经典的注释、诠解和研究。汉代兴盛的儒家经典研究被简称为汉学,它相对于后来宋代的儒家经典研究—宋学,它们同时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汉学、宋学。此外,历史上也曾把对汉民族史上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简称为汉学,但这一说法影响很小。
在今天的学术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学,显然是指海外—中国本土(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对这个学问的概念名称,也即我们中国学术界该如何命名和称呼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却很有必要做些辨析和澄清。原因是,迄今为止,对汉学这个名称,学界似乎还有不少缠绕不清、难以明辨之处,以致出现了概念模糊或名称混杂的现象,如在汉学名称出现的同时,还有海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域外汉学、西方汉学,以及中国学、支那学、契丹学等等,各种名词多样纷呈,再加上国学与汉学的关系,一般人恐怕真的一时难以厘清。这种概念混乱的现象,显然很不利于中国本土汉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更遑论它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了。故此,笔者有意对这些概念予以适当的阐释与辨析,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国学与汉学
首先,在辨析上述这些概念名词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国学与汉学的区别。所谓国学,是中国人对研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学问的总称,这个学问所包含的内容,应该广涉文学、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科学、艺术、教育、军事、宗教、民俗等多个学科。一般来说,它所涵盖的时间,乃是中国古代,即清末近代之前,或谓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而汉学则不同,它指的是外国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这种学问涉及的时间,一般也指古代,中国清朝末年之前。具体一点说,汉学,顾名思义,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汉民族文化的学问,英语为Sinology,这是它之所以被称为汉学的原因,但严格意义上,它实际上还应包括古代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少数民族,这样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也才切合汉学本身的概念内涵。它所涉及的学科,基本上与国学一样,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民俗等,时间上涵盖自上古至20世纪之前,学术资料上则包括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所有文献,及无文字记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汉学与相关术语
因汉学一词的出现及命名,习惯成自然,人们实际上也就认可了这一概念,即凡说及汉学,必定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一般不会与国学相混。但问题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与汉学相关的一连串学术名词,如海外汉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西方汉学等,又有点令人难以辨别了,究竟何种称法合乎实际?还是这诸多加前缀的名词都符合客观实际?其实,这些名词的内涵都是指汉学—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由于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或谓是中国人命名外国人所从事的研究中国的学问,故而人们习惯上也就在名称上加上了限定性的语词,或海外,或域外,或国际,或西方,或世界。但实际上,从概念上说,这些在汉学一词前附加的限定性语词,都是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所附加的带有地理范畴的含义,其实都不必要,也不需要。当我们说汉学时,它所指的内涵意义,即中国本土之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当我们称某人(外国人)是汉学家,大家都知道,这显然是指外国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绝不会指中国本土的学者;中国本土这方面的学者,不会称汉学家,只可称国学家。由此,所谓海外、域外、西方、国际乃至世界,实际上都是一个所指—中国本土之外,我们明确了汉学本身的含义,它是中国本土以外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地理范畴本身也就明确了,与这些名词前所加前缀概念内涵重复。可见,在汉学一词之前再加海外、域外、国际等语词,实在是多余的。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汉学在欧洲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但究其实,游记汉学时代—也即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时代,只是将其游历东方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载录于册,而后在欧洲传播,还远谈不上汉学。而传教士汉学,实质上是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传教士们,翻译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传播到了欧洲。这些译著,一般来说,本身没有涉及专门的研究。因而,笔者以为,所谓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只能说是欧洲汉学的胚胎,或萌芽与滥觞,还不是汉学本身。真正可以称得上汉学的,也即,真正开始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科学从事实质性研究的,乃是法国汉学家们。是法国的一批学者,率先开创了欧洲乃至世界汉学的新纪元,他们在巴黎和里昂等地的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所,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同时产生了名副其实的汉学教授。法国的汉学研究,学者之众、成果之丰,堪称欧洲乃至世界汉学之最—至少在20世纪中叶及之前都是如此。此后,汉学被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被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等)学界列为一门学科,在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展。
至于支那学,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出现的名词,它显然带有歧视色彩,那是因为日本其时想要摆脱传统中国的影响,学习并效仿欧美,甚至试图脱亚入欧,因而对中国这个东亚汉文化圈的宗主国,产生了歧视乃至排斥,支那这个名称本身即带有歧视性质,支那学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契丹学,则是欧洲一度对研究中国学问的代称,这是因为在中国大约宋元之后的时期,欧洲一些人对遥远东方中国还不太了解,以为是契丹国,故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契丹学。(也有一种说法,契丹,读音上与China相近,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即指中国。)
三、汉学与中国学
问题是,汉学这个称法产生以后,在20世纪中叶之前,世界上并没有异议,特别是在中国,海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均称作汉学。但到20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了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还继续被称为汉学,而研究中国现代的学问,则开始被称为中国学—这主要是指对现代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等的研究,尤以政治为主。这个现象大约发端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以哈佛为基地,建立了美国也是北美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其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的近现代,特别专注于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研究(主要是现代),推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论著(这当中包括一批中国留美学者的论著),此后,国际上便随之而兴起了研究现代中国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
本来,中国学名称的出现,与汉学并不矛盾—汉学专门研究古代中国,中国学专门研究现代中国。国际上一般认为,法国的汉学和美国的中国学,几乎井水不犯河水,二者之间并无取代关系,有的只是继承与发展关系,而且,中国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乃是政治(旁及文化),不同于汉学,主要在于文化。但是,在我们中国学术界,对此却出现了不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对中国研究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和不断创新的结果,是一种研究空间的重组和研究典范的转移,因而认为,应将研究中国的所有学问,不管古代现代,统称为中国学。于是,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举办有关汉学的会议,要在汉学一词后加上括号,特别注上中国学,因为主办者怕引起误会和不必要的争论,二者并举,或二者兼顾,可减少麻烦。这就引发了概念的混乱与自相矛盾。
笔者以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固然有因时代变化和区域不同而出现研究重点转移的现象,但这本身并不妨碍学问的客观分野。须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毕竟不同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客观内在的联系,但二者所侧重的内容毕竟有区别,尤其是研究的宗旨完全不同,我们不可将其一锅端。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现代中国,并非着重于文化研究,而更重要的乃是出于政治需要或经济目的;而研究古代中国,侧重点往往在于文化,包括思想、历史和文学。故而,将对中国的研究,按时代区别传统与现代,还是相对合理的—即,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统称为汉学;凡研究现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等,统称为中国学。这样既利于区分,又不至于概念混淆。
四、汉学研究与中国学研究
对汉学的研究,称为汉学研究,这实际上是专门针对中国学者的研究而言,也即,中国学者对外国人所从事的汉学进行研究,是谓汉学研究。同样,中国学者对外国人所从事的中国学进行研究,称为中国学研究。这样,也就明确了,所谓海外汉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并不是中国人对外国汉学的研究,而是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国人只是在其名称上添加了地理方位的修饰语而已,从内涵实质看,这些修饰语,实在是多余的。
首部德文全译本《三国演义》出版
《三国演义》(Die Drei Reiche)首个德文全译本于2017年初由德国菲舍尔出版社(S.Fischer)出版。至此,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已有两部德文全译本,另外一部是2016年出版的《西游记》(Die Reise in den Westen),由德国汉学家林小发(Eva Lüdi Kong)翻译。
这本德文全译本《三国演义》的译者是德国当代汉学家尹芳夏(Eva Schestag)。她从2011年起正式接受出版社委托翻译这部文学巨著。在之后的六年中,她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在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麓的“楼仁译者之家”,尹芳夏几乎从翻译之外的一切事物中脱身,除了在书房伏案工作,主要的休闲就是山中徒步。
“翻译一部如此重要、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国文学经典带给我责任感,也带给我挑战”,她说。尹芳夏因为对中国古文的喜爱而走上汉学之路,曾在慕尼黑、南京、苏黎世、中国台湾等地学习汉学。提到将《三国演义》译为德文的原因,尹芳夏说,《三国演义》讲述的故事是四大名著中最古老的。在语言方面,这部小说也是四大名著中最“古雅”的。但德国一直没有该书全译本。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在20世纪中期仅翻译了《三国演义》120回中的35回。(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