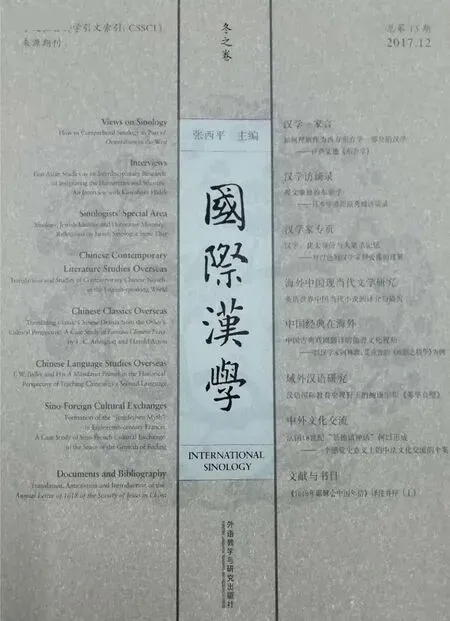笹川种郎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
□
一
中国学者对笹川种郎并不陌生,作为国内首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他的文学史卷首题记中提及:“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①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自序一》,收录于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林传甲以此表明,他的中国文学史参考了日本笹川种郎之作。②孙景尧在《真赝同“时好”—首部中国文学史辨》(载《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0—180页)中认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界有仿日本之风气,当时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成为一种“时好”。陈国球指出,尽管林传甲标榜模仿笹川种郎所著,但此二书实际内容关联不大,甚至文学观念相左,参阅陈国球:《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第170—175页。由于林著在中国流传较广,因此笹川种郎随之在中国声名远播,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学者误以为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是日本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这是由于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成中文,题为《历朝文学史》,1904年在中国出版,而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直至1913年才由上海开智公司出版,二者前后相差十年。③郭廷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事实上,笹川种郎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写得很清楚,“详论先秦文学的著作有知友藤田丰八的《先秦文学》,中国文学史方面有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各朝代杰出文人的传记可参见同仁合著的《中国文学大纲》。”④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日本:博文馆,1898年,第2页。此书序言中提及的“同仁合著的《中国文学大纲》”,由笹川种郎、白河鲤洋、大町桂月、藤田丰八、田冈岭云五人合著,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7—1904年出版。由此可知,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在笹川种郎之前。
笹川种郎(1870—1949),1870年生于日本东京,号临风。其父笹川义洁,曾为日本幕府旧臣。笹川种郎早年就读于日本爱知县中学,据他回忆,当时学校所用教科书均为舶来的洋书,开设的课程有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等。他的汉学素养最初来源于母亲与祖母,年纪稍长,便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入中学前已具有一定汉学基础。1893年,笹川种郎从日本第三高等中学文科毕业,同年进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国史科,于1896年毕业。在东大期间,笹川种郎为《东亚说林》《东亚学院讲义录》等杂志撰稿,担任《帝国文学》杂志编辑,并与藤田丰八、田冈岭云、小柳司气太等合作发行了《江湖文学》杂志。①川合康三主编:《中国的文学史观》,日本:创文社,2002年,第37页,西上胜执笔。
从东大毕业不久,笹川种郎撰写了《中国小说戏曲小史》(1897)。受欧洲戏曲小说研究风气的影响,他以中国戏曲小说研究为起点,一年后又推出《中国文学史》,开辟专章叙述中国戏曲小说,肯定戏曲小说的价值。此后,他还与白河鲤洋、大町桂月、藤田丰八、田冈岭云合作完成《中国文学大纲》(1897—1904),执笔孟子、曹植、杜甫、李渔、汤显祖、元好问卷。
总体而言,笹川种郎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中国俗文学。除《中国文学史》以外,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西厢记解读》(《帝国文学》,1896年第2卷第9、10号)、《李渔的戏曲论》(《江湖文学》,1897)、《元代戏曲〈琵琶记〉》(《江湖文学》,1897)、《汤显祖〈南柯记〉》(《帝国文学》,1897),并编译了《琵琶记物语》(1939,博多成象堂)等。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有:《评金圣叹》(《帝国杂志》,1896年第2卷第3、4号)、《读云翘传》(《文学界》,1896)、《金陵十二钗》(《江湖文学》,1896)、《元以前的小说》(《太阳》,1896)、《〈水浒传〉翻译》(改造社,1930)等。
在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家中,笹川种郎是较早认识到中国戏曲小说价值的学者。如果将他与同期日本的古城贞吉、中国的林传甲加以比较,会发现他们的文学观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从人性人情及世态风俗的角度考察文学,对戏曲小说的价值予以肯定,后者则依据传统文学评价的尺度,对戏曲小说持否定排斥态度,如古城贞吉认为,“戏曲小说被排斥于文学之外,并非偶然之事。”②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日本:东京劝学会藏版,1902年,余论,第585页。林传甲甚至痛斥笹川种郎将戏曲小说写入文学史中,认为此做法有悖于传统,应将戏曲小说归于风俗史:
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风俗史》,余亦欲萃“中国风俗史”,别为一史。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③《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10页。
当时将戏曲小说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的,并不限于林传甲与古城贞吉,这是早期中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日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儒学伦理纲常为主导,投映到文学研究上,便是重诗词文赋轻戏曲小说,甚至将戏曲小说视为有伤风化,此种观念在明治初期仍较普遍。笹川种郎未囿于旧识,而是追随欧洲文学研究的风气,以新视野开拓戏曲小说研究领域,首次将戏曲小说写入文学史,这在当时实为创举。
然而,笹川种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甫一出版,便遭到日本国民文学派的反对。日本国民文学派以日本民族国家为前提,认为中国小说戏曲并无价值,宣称“中国文学的思想对我国国民文学的进步并无裨益,除去历史意义,其价值不值得称道。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只能是纯粹历史意义上的研究”④高山樗牛:《中国文学的价值》,日本:《太阳》杂志,明治三十年九月号。转引自高津孝:《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11年12月。。不仅是国民文学派,学友大町桂月也对此书的学术性提出质疑,此种质疑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对作者本人中国文学功底的质疑,其二是对中国文学本身的价值持怀疑态度。⑤明治三十年(1897)七月十日,桂滨月下渔郎(大町桂月)在《帝国文学》第三卷第七号刊出书评《评〈先秦文学〉和〈中国小说戏曲小史〉》。转引自黄仕忠:《笹川临风与他的中国戏曲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针对大町桂月所言,笹川种郎从两方面予以反驳。
第一,关于中国小说戏曲是否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笹川种郎明确表示,中国戏曲足以与欧洲并驰,日本戏曲也有负于中国之处。他认为,中国戏曲小说的价值毋庸置疑,如《水浒传》即为东西方少有的雄篇大作,日本曲亭马琴的《八犬传》其实并未学得《水浒传》之精髓。①笹川种郎:《答大町桂月》,《日本人》第四十七号,1897年7月12日。转引自《笹川临风与他的中国戏曲研究》。
第二,针对大町桂月对笹川种郎学术功底的质疑,笹川种郎回应说,自己学识尚浅,因此略述其史,只为抛砖引玉,引起同好对中国小说戏曲价值的关注。他表示,此书有与众不同之见,且撰写小说戏曲史是前人不曾有之事,因此具有一定价值。他表示,日后博览,会再写大作。
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客观地评论中国文学并非易事。日本国民文学派否定中国文学的价值,扬言汉学阻碍了日本文明开化的步伐,此言论在日本明治时代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对笹川种郎文学史的批评,实际上包含了一定民族主义情绪。可见,对民族主义的克服与超越,是明治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文学史家也难以避免。
二
一年后,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戏曲小说仍为此书的叙述重点。笹川种郎在此书自序中说:“悠悠四千年中国文学的历史并非三百余页稿纸所能誊写,此书旨在让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之概观。……就目前中国文学研究日渐兴盛来看,实乃日本学界值得庆幸之事,本人撰写此书之目的正是为研究中国文学导引入门。”②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第2页。如其所言,在日本急剧想要脱亚入欧的时代,兴起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虽有些不可思议,但的确是值得庆幸之事。较之此前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中国文学史》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其中国戏曲小说观,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戏曲小说发展的问题,笹川种郎认为,戏曲小说是中国文学特色,虽然起源很早,但发展颇为缓慢,至元代始逐渐发达起来。他认为,制约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北方文学一统天下,而北方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儒学。由于儒学的影响,即使戏曲小说在发展全盛的元明清时期,也始终未脱离劝善诫恶、经世济国之说。《琵琶记》与《西厢记》虽为南北曲巨擘,却难以与欧洲、日本戏剧相比,儒学制约为根本原因:
读者从上至先秦下至宋代的中国文学一路读过来,可曾引起什么异样的情感?我至此还没有写一章关于中国小说戏曲的内容,然而中国文学的特色其实正在于小说戏曲。相较欧洲文学史及日本文学史,中国的小说戏曲为何会如此寂寥?
要而言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寂寥是由于北方思想一统天下的缘故。北方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其势力遍披华林,因此形成对小说戏曲的轻侮之风。戏曲小说被视为末道小技,此乃儒者之眼所见。视文章为经国之伟业者,视戏曲小说如同尘芥,甚至是败风坏俗之毒物。不唯儒家思想诞生的北方地区戏曲小说不发达,南方情况亦大抵如此。元朝以降,戏曲小说始日渐发达,即便如此,戏曲小说仍未摆脱儒家思想之束缚,可谓熔铸于儒家固有铸型之中。清朝的李笠翁以戏曲家闻名,其言“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传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云:“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由是看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乃劝善诫恶之助,古代小说戏曲在中国的不发达亦与此有关。③同上,第259—261页。
笹川种郎认为,儒学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制约,不仅在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中国小说起源虽久但发展始终迟缓,也是由于儒学的影响:
中国小说戏曲的源流久远,古有庄子的寓言、方士虞初的小说九百,且周末汉初设有稗官。然汉魏间有《穆天子传》《飞燕外传》,却未有小说界之进步。唐朝的裴铏著有《传奇》,尽管唐传奇的《昆仑奴传》《红线传》等奇事异闻多为后世戏曲创作的蓝本,然而唐传奇仍不能视为中国戏曲小说发达之标志。中国小说戏曲的真正发达实为元朝,何其迟迟也。①同上。
除小说外,笹川种郎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也进行了概述,在他看来,戏曲与小说一样发展迟滞:
宋代是杂剧产生的重要时期,如同通俗小说起始于宋代,词至宋代一转而为曲,杂剧由此出,为戏曲之嚆矢。乐府一转而为词,词一转而为曲。②参阅清代李调元的《雨村曲话》,其中引《弦索辨讹》:“三百篇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由元散曲而促成杂剧,所谓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继之以戏曲。宋代杂剧为说唱,至金代乃为院本、杂剧、诸宫调。或称“院本”,或称“杂剧”,名异而实同。曲分南北二曲,金元入主中原后多用胡乐,其音嘈杂凄切。所谓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③“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此句出自王世贞的《艺苑厄言》。王世贞认为:“曲者,词之变”,“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北曲的特色是劲切雄丽,南曲的特色是清俏柔远;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曲字少调缓,缓处见眼;北曲辞情多声情少,南曲辞情少声情多,北曲力在弦索,宜和歌,南曲在磨调,宜独奏。④此处关于北曲与南曲区别的论述,皆出自明朝王世贞的《曲藻》。……群英编杂剧共五百五十六本,其中元杂剧五百三十五本,无名氏一百七十本,娼夫十一本,⑤有关元杂剧的统计,元至正年间钟嗣成的《录鬼簿》著录元杂剧 458 种;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代杂剧 535 种;明万历年间臧懋循《元曲选》所列“元群英所撰杂剧” 549 本,因其中有 33 本是明人所作,故实载元杂剧作品 516 本,计 512 种;当代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所载“元杂剧全目”,共收录元杂剧剧目 736 种。而尤以《元人百种》为重。⑥《元人百种》即《元曲选》,元代杂剧选集,明万历年间臧懋循编,收录元人杂剧近百种。其中北曲之最为《西厢记》,南曲之最为《琵琶记》。《西厢记》的蓝本是唐朝元稹的《会真记》,一说《西厢记》为关汉卿所著,另有《西厢记》为王实甫所著之说,似应从后说。总计十六折,尽管其角色单纯,一片情话,但是词采超绝,被誉为千古绝调并非夸张。
第二,笹川种郎以纯美学的眼光来评价中国戏曲小说,突出了戏曲小说作为文学的独立价值。笹川种郎指出,裴铏所辑唐传奇数量不少,如《红线传》《昆仑奴传》等,且多为后世戏曲的蓝本,但并不能将此视为唐代戏曲小说发达的标志,戏曲小说的真正成熟期其实是在元代,这是由于自元代起,戏曲小说才开始描绘市井百姓的生活,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与人情,从而获得了真正的文学价值。他以《西厢记》和《琵琶记》为中心,展开对戏曲美学的评价。二者相较,他更倾向于《西厢记》,叙述《西厢记》的篇幅远多于《琵琶记》,有关《西厢记》的内容多达8页,而《琵琶记》仅有2页。
他引用金评西厢,以《庄子》《孟子》《国策》《史记》之直承《左传》,来映衬《西厢记》出色的艺术手法,并引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原文,赞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左传》之文,庄生有其骀宕,《孟子》七篇有其奇峭,《国策》有其匝致,圣叹别有《批孟子》、《批国策》,欲呈教。太史公有其巍嶷。夫庄生、《孟子》、《国策》、太史公又何足多道,吾独不意《西厢记》,传奇也,而亦用其法。然则作《西厢记》者,其人真以鸿钧为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者也。⑦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第262—263页。
他赞赏金圣叹所评,称《西厢记》“词采超绝”“千古绝调”,并认为北曲之最为《西厢记》,南曲之最为《琵琶记》,但《琵琶记》的创作主旨与故事情节,终不及《西厢记》。
笹川种郎在《中国文学史》中引用了《西厢记》第4本第4折全文,不过未注明底本,其中不乏错漏之处。为展示原貌,现以暖红室所刻《凌濛初鉴定西厢记》为底本,与笹川种郎所引《西厢记》部分加以对照(见表1)。

表1 《西厢记》第4本第4折对照表

(续上表)
笹川种郎引《西厢记》原文之后,对《琵琶记》与《西厢记》的价值进行了比较,认为《西厢记》的价值远在《琵琶记》之上。他引用清代毛声山对高明《琵琶记》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论,并对毛声山的观点予以强烈指责,称毛氏所言为“妄语”,认为毛氏称《琵琶记》胜于《西厢记》归根结底是源于儒教思想,而以儒教的劝善惩恶观来评论文学纯属无稽之谈:
毛声山称西厢好色词淫,琵琶则是乱世怨悱之音。西厢近风,琵琶近雅,琵琶之胜于西厢,一曰情胜,二曰文胜。西厢的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私期密约之情;琵琶是孝子贤妻、敦伦重谊、缠绵悱恻之情,故琵琶之情胜于西厢之情。西厢是妙文,琵琶也是妙文,然而西厢多方言俚语杂用,而琵琶则无,故琵琶之文亦胜于西厢。无论如何,孝子贤妻敦伦重谊缠绵悱恻之情胜于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私期密约之情。由声山此言观之,来自于儒教见地,令人难以理解琵琶胜于西厢的理据。以是否有方言俚语来评价戏曲的高低,是将戏曲视为正史经书,此话纯为妄语。然汤显祖所言,“《琵琶记》都在性情上着工夫,不以词调巧倩长”之说,乃千古不灭的评语。①同上,第268—269页。
从纯粹的美学文学出发,他认为《西厢记》反映了最真实的人性与人情,词采华美而意境悠远,在儒学色彩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因此具有特殊的艺术震撼力,并视《西厢记》为元曲中之最上品。久保天随在评《西厢记》时,同样以“情”为出发点,表达了与此大致相同的观点,且同样援引毛声山评西厢的原文,以此批驳毛氏评论存在的偏见,指出将方言俚语用于戏曲并不损害戏曲的价值。
总体而言,笹川种郎评述小说的出发点,在于作品是否反映人性与人情,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之美。基于同样的认识,他认为《水浒传》的价值远在《三国演义》之上,他赞赏《水浒传》的意趣与文辞,称之为“壮绝快绝”之作:
宋朝兴起话本小说,亦有混杂俗语之演义。尤其是《大宋宣和遗事》,元朝的《水浒传》正是以此书作为蓝本。至于《水浒传》,可将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百二十回本作为正本来看。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争议纷纷而难有定论,我认为不如从施耐庵所著之说。《水浒传》首尾贯通,三十六个人物跃然纸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之快事。不仅趣向深远,文辞也雄浑爽利,称得上是壮绝快绝的大文辞。
与《水浒传》并称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相传为罗贯中所作,但未必可信。据《续文献通考》,此人非罗贯中,而是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有数十种,《三国演义》是据正史的史实敷衍而成,其角色拙劣,文辞亦拙劣,无法与《水浒传》相提并论,且其真本存在与否难以定论。如谢肇淛认为《三国演义》“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①明末以前,文人对《三国演义》评价一直不高,汪道昆即认为其“雅俗相牵,有妨正史”(《水浒传序》),谢肇淛亦斥其“俚而无味”(《五杂俎》),胡应麟进而将其与《水浒传》相比,说“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庄岳委谈》),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有人将两书合刊,《三国演义》地位才得以提高。与此相比,《水浒传》则自明中叶就得到著名文人的高度评价,从文坛前辈文徵明到唐宋派的唐顺之、王慎中以及崔铣、熊过、陈束、汪道昆直至杰出思想家李贽、公安派袁宏道、竟陵派锺惺以及评点家叶昼等,无不对《水浒传》极加推崇称赏。正是由于称赞者皆为当时思想界、文学界著名人物,因而造成《水浒传》“上自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邑,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的流传盛况。参阅许总:《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
从人性与人情的角度出发,除《水浒传》外,笹川种郎还对清朝小说《金云翘传》颇为赞赏。他认为:“《金云翘传》没有《红楼梦》之错杂、《金瓶梅》之淫猥,篇幅短小而情节连贯,除《水浒传》《西游记》以外,如果让我对有意欣赏中国小说的人士推荐,那么我一定会推荐《金云翘传》。”②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第270页。
从纯美学的角度评价戏曲小说,无疑是受到近代欧洲小说戏曲研究风气的影响,并促成了日本近代文学观的转变。自明治后期开始,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戏曲。此与江户时期以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国古典研究,以及对小说戏曲的日文翻译与训读,无论是研究性质还是研究对象,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明治时期如同一道分水岭,从此时起,日本不再将中国文化作为统治者和庶民共有的知识给养,而是将其转化为纯粹的美学批评及欧洲实证主义为主导的学术研究。③日本江户时期,由于与中国贸易交往的实际需求,曾出现唐通事一职。唐通事即对日本江户时代在长崎、萨摩藩、琉球的日中贸易中从事汉译人员的通称,其学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是《水浒传》《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但只是用于阅读或学习汉语口语。
第三,笹川种郎将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的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理论依据,着重从种族、环境、时代三方面来叙述中国文学。他开篇便从中国文明的起源谈起,并探讨了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如中国文明、中国的人种、南方人种与北方人种的差异、拜自然的习俗、家长制度的发达、生存竞争的激烈、自尊自大的风气、中国文学的特质、中国的文字等。从中不难看出,丹纳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对他产生的影响。
笹川种郎首先谈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中国人种的关系。他由古老的中国文明谈起,“洋洋江河流域孕育了璀璨的文化,其文明之花已经盛开四千年之久。不惟中国四千万大众受此文明之光的恩惠,更传入朝鲜,惠及日本”④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第1页。。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是由于国土广阔,人种复杂。中国有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等众多民族,而开拓中国古代文化的是黄河流域居住的汉人种,“汉人种居于北方,文化首先起源于此,形成了古代历史的中心,是谱写了古代历史的人民”①同上,第2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分别列举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并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
笹川种郎认为,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实际上是不同的人种,具有不同的特质:
如果将北方人种与南方人种加以比较,会发现南北两个种族全然不同,其相貌、其骨骼、其语言都不同。究其本质,南方人种爱想象,北方人种重实际。燕赵古来多悲歌慷慨之士,是由于他们有感于时事,悲歌击筑,不平则鸣,荆轲入秦刺秦王,皆关心时政之缘故。而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太虚说,庄子的人生观,几乎都远离现实,属于典型的南方人种的特质。楚国怪力乱神之说颇多,且辞赋起源于南方,可见南方人种想象之丰富,因此他们也深懂诗趣。②同上,第3页。
在笹川种郎看来,中国南北文学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南北人种之间的差别。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特质完全不同,南方人爱想象,北方人重实际。庄子是南方文学的代表,其作品曼妙虚无,远离现实社会人生。北方文学则以孔子为代表,现世与时政是北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且多慷慨悲凉之作,此与北方人重实际的特质有关。
笹川种郎认为,风俗习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学作品,因此他不厌其烦地罗列琐碎的生活习惯,试图从中找到其对人的性格、思维及文学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中描述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各种习俗:
南方人用床,北方人用炕。南方人常食鲜果、鸡肉、鱼肉,喜欢吃腌猪腿,炖肉的汤是清汤;北方人的肉汤是浑汤,喜食苹果、鲜猪肉、鸭肉和羊肉;南方人食姜,北方人食蒜;南方人喜食怪味,北方人喜食卤味。总之,从服装、饮食、日用品来看,南方与北方的风俗完全不同。③同上。
他还从中国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考察地理环境对北方人性格及习俗的影响:
北方山岳崔嵬,视野开阔,山高野旷,有大陆风光之雄伟。然而北方气候寒冷,有衣食不足之忧,因此北方人的性格偏重实际,这种性格实乃北方自然产物匮乏所致。然而无论自然的伟大还是刻薄,民众总有惧怕自然之心,于是有拜天之习俗,祭祀山川之风气。……要而言之,拜自然的习俗是源于对自然的恐怖。拜自然的习俗伴随着崇古的观念,孕育了家长制度的胚胎,从而助长了统治权力与势力。④同上,第4页。
笹川种郎还认为,与日本不同,中国文学总体上具有一种庄严崇高的风调与夸张的风格,此为地理环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之所以庄严崇高,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山川雄伟,其投射于文学便产生了庄严崇高之感,尽管南方文学为中国文学加入了绮丽之调,然而中国文学整体上仍是庄严夸张。”⑤同上,第10页。他举例说,司马迁《史记》中的垓下之战,项羽对赤泉侯怒目圆睁,结果赤泉侯人马俱惊,狂逃至数里之外。在诗歌中,李白《秋浦歌》的“白发三千丈”、《北风行》中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皆是典型的运用夸张之作,也是地理环境作用于文学之例。⑥同上,第11页。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均可以从中找到地理环境的影子,由于中国国土辽阔,中国文学整体上有雄浑壮阔之感,“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叙事文、议论文、诗歌,往往充溢着庄严的格调与雄大的风格,彰显出中国文学的异彩陆离”⑦同上。。
在此基础上,笹川种郎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基础是拜天与祭祖,构成中国人精神核心的三要素则是“孝行、亲权与祖先崇拜”,此亦为中国儒学影响所致。笹川种郎认为,中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没有产生过规模宏大的史诗,而几乎与中国产生《诗经》的同时,古希腊却产生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也产生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对此他有如下论述:
中国北方人种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其影响极其深远。北方人种有理想主义倾向,同时也具有实际主义倾向,因此儒教产生于北方。……创造了儒教的北方人种的文学是实用主义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实用的文学。诸如历史散文、策论自古以来就不乏名篇大作,而具有理想主义的戏曲小说则相对式微。而历史散文、策论也难以脱离儒教,所谓诗,所谓叙事散文,常渗透着儒教的思想。中国古代少有雄浑的叙事诗,少有小说戏曲的大作,正是基于此原因。①同上,第10页。
此外,由于中国崇古之风兴盛,因此滥用典故,存在一味复古、拟古之势,造成夸张之风盛行。他举例说,明代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堪称是与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相媲美的名篇佳作,然而《永和宫词》通篇充斥典故,不仅吴梅村如此,历来文人皆争相以典故来夸耀文采。笹川种郎认为,正是由于崇古之风盛行,拟古文之作大行其道,从而制约了俗文学的发展。尽管元代戏曲日渐发达,然而即使在元代戏曲中也充斥着各种典故。他还认为,之所以在元代才迎来小说戏曲的黄金时期,是由于元代统治者作为外来民族,没有接受北方文明的教化而被称之为“朔北野人”,由于“朔北野人”受北方文明的束缚较少,元代的小说戏曲才得以发展起来,而元代戏曲小说的兴盛使得“中国文坛的文风至此一变”。②同上,第3页。
笹川种郎指出,在地理、环境、人种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中国文学具有很强的排外性。中国文学接受周边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极少,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学发达的缘故,实际上也是由于中国文学的排外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学对朝鲜、日本等邻国的文学影响很大,反之中国文学极少接受朝鲜、日本等国文学,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中几乎找不到接受他国文学的痕迹。
三
最后,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笹川种郎对中国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中,笹川种郎基本上按照朝代顺序加以分期,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九期。笹川种郎表示,“之所以基本上按照朝代顺序来分期,是为了体现每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充分呈现每个时代的文学特色。”③同上,第15页。其中,第一期是春秋以前、第二期是春秋战国时代、第三期是两汉、第四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五期是唐朝、第六期是宋朝、第七期是金元、第八期是明朝、第九期是清朝。在笹川种郎看来,三千年的中国文学不断在走一种循环复古的道路,他举例说,“宋代的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的回复,清代的考证学是汉唐训诂学的回复,但是这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复古”,“与此同时,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又在不断否定前朝的文学,比如对先秦的诸子横议纵说,汉唐的章句训诂是作为其反面出现的。宋代提出的性理说则反对汉唐的章句训诂,而清朝的考据学则反对宋朝的性理说。”④同上,第17页。笹川种郎意识到“复古”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并指出不同朝代的文学复古现象存在着内在关联,但是他并未认识到,复古其实是一种创新,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几乎每一次文学革新均是以复古的形式呈现。
笹川种郎之后的中国文学史,大多能将戏曲小说纳入文学史的叙述范围,不能不说与笹川种郎所做的尝试有关。尽管江户时期,日本也曾出现过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的兴盛,当时日本在日中贸易中大量购入中国书籍,由此而兴起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训读与翻译,体现出自上而下对中国俗文学的关注。然而此时兴起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热潮,则与江户时期并无直接关联,而是受欧洲对中国戏曲小说译介与研究的启发。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明确提出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有其独立的价值,主张小说只受艺术规律的制约,不从属于任何其他目的,对劝善惩恶的传统文学观予以彻底批判。1891年森槐南在东京“文学会”上,以“中国戏曲一斑”为题对中国戏曲进行演讲,倡导中国戏曲的研究价值。笹川种郎正是在此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文学史领域戏曲小说研究的先驱。
在中国文学史家中,笹川种郎应该属于大器早成的,他27岁即出版了《中国小说戏曲小史》,第二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但是以研究中国戏曲小说起步的笹川种郎,后来却转向研究日本史和日本美术史,并未继续中国俗文学研究。有学者指出,此种学术转型作为当时一种普遍现象,只能说明此时期俗文学研究尚未形成体系,真正出现以中国俗文学研究为终生事业的学者,要等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国立最高学府开设中国文学专业之后。①张真:《笹川临风学术生涯及其中国俗文学研究述论》,《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小说戏曲小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作家作品的叙述,也不仅在于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思考,更在于改变了长久以来唯诗文论的传统文学观。可以说,明治时期以笹川种郎的戏曲小说研究为契机,迎来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反观中国本土,尽管明末清初曾出现过李渔这样的戏曲大家,实际上却仍偏重于词采和音律,将戏曲当作诗、词或曲的一种特殊样式来欣赏与品味,以诗词的“抒情性”来评价戏曲,忽略了戏曲艺术的自身特点,因此其本质无异于传统诗话与词话。②杜书瀛:《论李渔戏曲美学的突破性贡献》,《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李渔以外,其他戏曲评论之著,同样基于评点序跋,难以形成完整体系。中国真正迎来俗文学研究的自觉年代,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了。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
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交换生来到复旦大学,跟从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卜正民教授著述丰富,著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1993)、《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2008)、《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1998)、《明清历史的地理动因》(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1988)等书,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1989)、《中国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 1997)、《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1999)、《鸦片政权》(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2000)、《民族行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2000)等。(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