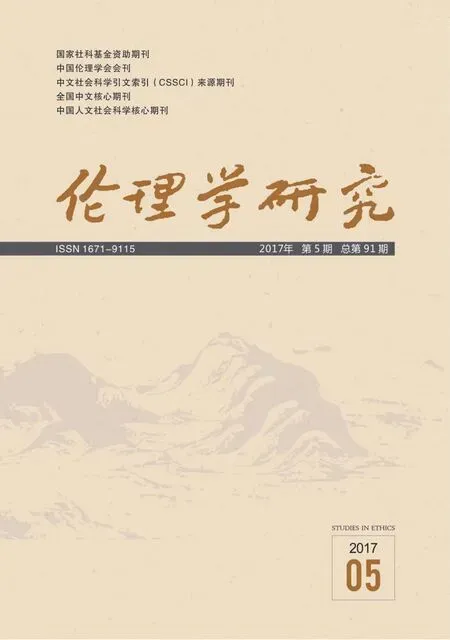论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张 虎
论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张 虎
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自然不平等;正义;自然抓阄;运气平等;内格尔
不同的人在智力、体力、相貌、勇气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常常被看作基因决定和先天形成的,所以它也被称做自然差异(natural difference),与之相关的不平等也被称作自然不平等(natural inequality)。传统观点认为自然不平等的不利一方遭遇的是厄运(misfortune),而不是非正义(injustice),因为这种乍看起来像不公正的现象不能归咎于任何人或整个社会体制,并且在自然的强力面前,人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如果没有我们能做的,也就没有我们应当做的。柏拉图就比喻说上天在铸造人的时候分别使用了黄金、白银、铁和铜以致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德性,而正义在于顺应而不是对抗这种差别[1](P131)。马克思也认为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2](P364)。但是罗尔斯指出,“自然资质的分布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或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3](P78),那么一种社会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实呢?应该宽容或默认还是积极地干预以减轻它们的影响?
一、自然抓阄与差别原则
就自然不平等问题来说,以诺奇克为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心力量等自然能力拥有所有权(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并且该权利必须得到其他人或社会体制的完全尊重。这种观点实际上来自洛克,洛克认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4](P18)。洛克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认为只要满足一定条件,自我所有权可以引申出私有财产权。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体制应该放任自然差异的社会影响,容许自然不平等的出现,那种试图减轻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政策是对自我所有权的侵犯。这种观点断言人们对自己的自然能力拥有所有权,但并没有对此提供充分的论证或辩护。
自由意志主义的体制类似罗尔斯批判过的“自然的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后者奉行“职位向人才开放”(careers open to tal-ents),要求在法律上消除阻碍人们获得机会平等的相关因素。罗尔斯指出自然的自由体系“由于除了保持必要的背景制度所需要的之外,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的或相近的社会条件,资源的最初分配就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3](P56)。“社会偶然因素”指一个人的社会出身,亦即他的阶级和家庭背景;“自然偶然因素”指一个人的自然资质或禀赋,尤其是他的先天能力。罗尔斯之所以称它们是偶然和任意的,是因为它们不是主体自身所能选择和决定的:某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又从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他又有什么样的自然资质,这些左右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都不是其本人能够主动选择的,他只能被动承受。
用威廉姆斯举的一个例子可以表明社会偶然因素的非正义性:在某个社会中武士阶层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该群体原来只依身体强健的程度从富人子弟中选拔;现在机会平等的社会改革得以贯彻,职位开始向人才开放,所有社会阶层的成员都有参选武士的资格了;但是结果出人意料,富人仍垄断了武士资格,原因是富裕家庭竭力给其年轻成员提供最好的营养条件和最专业的身体素质训练,这样即使他们的体力天分与其贫困竞争者类似,他们也更容易胜出[5](P99-100)。自然的自由体系保证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机会平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人们在这种体系中获得了参与生存“竞赛”的资格,但却不一定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社会出身这种偶然因素极大地决定了一个人的胜出机会。针对社会偶然因素,罗尔斯提出了“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原则:
“假定有一种自然禀赋的分布,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3](P56-57)
促进公平的机会平等,社会尤其需要为所有成员提供就他们能力所及来说同等质量的教育条件,以打破阶级或阶层藩篱,增加社会流动性。
批判了自然的自由体系,罗尔斯又进一步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后者只做到了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指出,“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布决定”[3](P57)。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平等只是减轻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没有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们命运的摆布,但是“对一出生就含着银匙(silver spoon)可讲的同样适用于一出生就带有黄金基因(golden genes)”[6](P309)。罗尔斯用“自然抓阄”(natural lottery)一词来形容自然偶然因素的特质。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自然资质或禀赋,从一般的观点看既非主要决定于社会环境的塑造,亦非主要决定于主体自身的选择,而更多地是由基因这样的自然因素决定的,是对主体自身来说像抓阄一样碰运气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却会深刻地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因此,自然偶然因素引起的不平等也是不公平的,有人就指出,“自然抓阄冒犯了我们是因为它把道德存在当作自然物体来对待”[7](P76)。
罗尔斯认为“我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出发点一样”[3](P79),那么如何应对自然偶然因素呢?罗尔斯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差别原则,其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8](P56)。这样的不平等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和自然偶然因素造成的,并因而从上述的道德立场来看是任意的,但罗尔斯认为只要它们被从另一种道德立场来看不任意的目标所辩护,它们就不是不公平的,这个不任意的目标就是要有利于社会中的最不利群体。因此差别原则鼓励智力、体力等天资卓越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允许他们获得足够的经济报偿,只要由此形成的不平等能够增加处境最差的群体的利益。这里,罗尔斯实际上通过差别原则实现了一种转换,即把自然抓阄的结果转换成了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的资产(common asset):“差别原则实际上代表这样一种同意:即把天赋的分布看作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共同资产,可以共享这种由这种天赋分布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社会与经济利益”[3](P77-78)。从自然抓阄到共同的资产,罗尔斯指出了社会制度处理自然差异这种事实的正义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放任它的影响,而是利用它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说,“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同意相互分享各自的命运”[9](P97)。
二、遗传运气与运气平等
罗尔斯用差别原则来处理自然不平等,这在一些人看来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平等从原则上说是一个个人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群体处境的问题”[10](P114)。自然差异只存在于不同个人之间,公正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不平等也应该落实到单个人,而不能以某个独断地划定的社会群体作为受惠的对象;另一方面,罗尔斯对社会中处境最差群体的界定“完全依据于人们所拥有的那些社会的基本益品,如权利、机会、财富等等。他没有把人们所拥有的那些自然的基本益品作为确定最不利者的因素”[11](P133),这里“自然的基本益品”指的就是人们的自然禀赋。而自然禀赋差的人不一定拥有较少的社会基本益品,也不一定被划到最不利群体中而从社会中受惠,因此“罗尔斯的方案仍然默认了任意因素对人们命运的极大影响”[11](P133)。
那么如何减轻自然抓阄对不同个人命运的不同影响呢?除了差别原则,还有几种方案摆在人们面前。一种方案要求直接减小社会成员在禀赋方面的差异,比如强制聪明人戴上造成智障的耳机,在身强体壮者的脖子上挂上沉重的沙包,刮掉面容姣好者的眉毛,迫使他们戴上“红鼻子”和黑色的暴牙牙套等等[12](P315-318)。这种拉平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品质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仅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不过,近年来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倒使“基因平等”(genetic equality)成为一种可以希求的图景。不是将所有人的自然能力拉得一样差,基因技术很有希望把所有人的自然能力改造得一样好。但是布坎南等人指出基因平等的主张忽视了自然资质之价值的社会相对性和价值多元主义的事实,因此是有问题的[13](P79-81)。另一种方案不是直接拉平或干预自然抓阄的结果,而是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对所有社会成员聚合的“能力池”拥有平等的一份。这种方案可能意味着禀赋卓越者要与禀赋较差者分享自己的才能(例如,在一定时间内,后者可以对前者如何使用他的能力下命令),也可能意味着禀赋卓越者要在某种限度内无偿地运用自己的才能来增进全体社会的利益,而不管他是否愿意。因此,这种方案使禀赋卓越者很难追求自己偏爱的好生活理念,使他们陷入了德沃金所说的“人才的奴隶制”(the slavery of the talented)。
区别于上述方案,德沃金提出了资源平等的主张。这种平等要符合人际间的妒忌检验(envy test),即至少就每个人的一生来讲,他们都不会宁愿选择别人的资源份额而不要自己的。这里的资源既包括一些外在的物质资源,也包括人的精神和生理能力,因为后者同样可以为每个人的人生追求“提供手段或形成妨碍”[10](P79)。但是不同于物质资源,能力“不能进行控制和转移,即使技术上可以办得到”[10](P77)。为了通过妒忌检验,德沃金提出用可控和可转移的物质资源来平衡不同人的能力资源差异对其命运的差别化影响,这就要求社会用物质资源来补偿自然资质较差者所承受的自然劣势,改善他们的人生处境。当然,这里的补偿既不是使先天残疾或智障者变得和常人一样好,也不是差别原则那样的举措,虽然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3](P77)。德沃金提出最好找出一种方法,“把职业造成的公平的财富差别和不公平的财富差别区分开。不公平的差别是可归因于遗传运气、另一些人不拥有的、使某些人富足的技能——如果他们具备这些技能,他们也会充分加以运用——的差别”[10](P90)。资源平等即要求设计一种税制,对析出的这种不公平的财富差别进行公平地再分配,把自然不平等中有利一方的资源转移补偿给不利一方。针对各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德沃金为实现这种资源补偿设想了一种“保险”策略:在“无知之幕”中,人们知道他们可能遭受的身体残疾、该残疾的发生机率以及自己的人格特质等信息,而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这种残疾以及自己人格特质的社会价值等信息;这时有平等支付能力的人们为自己可能会有的霉运投保,社会将模拟这种投保结果而设计一种税收制度以从处于自然优势的人那里征收“保费”,转移补偿给处于自然劣势的人做“保金”。
受德沃金影响,当代很多平等主义思想家都将他们的平等观建立在抵制道德偶然因素(自然偶然因素只是其中一种)的基础上,例如拉科夫斯基就认为在一些限制条件下,“没有人应该仅仅由于一些其本人并没有冒险招致的偶然事件而比别人拥有更少的有用资源和机会”[14](P1)。对于发生的这种非正义现象,拉科夫斯基也认为应该在因偶然因素获利和失利的人之间执行资源的补偿转移,以平等化原生运气的影响,这样的平等观被称做运气平等(equality of fortune)或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
运气平等主张补偿处于不应得的劣势境况的人,这使其显得极富人道主义色彩,但安德森指出它通不过任何平等主义理论都必须通过的最基本的测试——“对所有公民表达平等尊敬和关怀”[15](P289)。运气平等的一个失败之处正是它的补偿要求,这种补偿实际上构造了一种等级关系,为自然偶然因素所抛弃的不幸者在这里是低贱的,为其所眷顾的幸运儿则是高贵的,前者对后者的态度是妒忌(正如资源平等所表明的),后者对前者的态度是怜悯,这一对相适应的态度都与尊敬人相矛盾。来看一下安德森认为运气平等的体制会给予相貌丑陋和社交困难者的补偿理由:
“你对你周围的人来说如此令人反感以致没人想做你的朋友或情侣,这有多悲哀啊!我们不会通过做你的朋友或结婚对象来补偿你——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交往自由——但是你可以挥霍我们这些美丽可爱的人儿所提供的这些物质利益以在悲惨的孤独中聊以自慰。谁知道呢?没准儿一旦潜在的约会对象发现你变富了,你或许就不再是爱情中的失意者了。”[15](P305)
社会对个人能力和品质等的这种价值判断是极具冒犯性和侮辱性的:
“即使所有人认为A如此地丑陋或不招人喜欢以致他们都更偏爱迷人的B的性格,也不关国家的事去在这种私下的判断上盖上官方承认的公章。如果被很多同伴看作社交中的傻瓜是让人丢脸的,考虑一下国家把这种私下的判断提到公开承认的位置,并为了公正治理的目的而将其看作事实该有多侮辱人。”[15](P305-306)
德沃金等人曾指出差别原则没有把自然资质状况作为最不利群体的一个评判标准,但是社会体制要想对所有公民表达平等尊敬和关怀,就不能随便对个人的身心能力、性格品质等做差别化的价值判断。
运气平等把自然禀赋的不平等分配看作是非正义的,安德森以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为例驳斥了这种观点[16](P8-10)。在该影片中,莫扎特粗鲁乖张,但其作曲才华胜过了宫廷乐师萨里埃利,后者妒忌莫扎特的音乐天赋以致痛苦而发狂。莫扎特和萨里埃利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是否是非正义的呢?安德森认为作非正义的判断要找出三种因素:对某人利益的伤害、这种非正义的负责方以及有资格抱怨负责方并提出相应诉求的另一方。萨里埃利因莫扎特拥有超过自己的音乐天赋而痛苦,这其实是妒忌感在作祟,但是“妒忌是恶毒的,因为妒忌别人的人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基础上”[16](P8),所以妒忌感在正义理论中算不上一种伤害,非正义判断的第一个因素也就不存在;第三个因素同样不存在,因为既然不存在对其利益的伤害,无论萨里埃利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资格抱怨他们的天赋比莫扎特差;第二个因素是非正义的负责方,这是莫扎特本人吗?是否应该禁止他显露超过萨里埃利的才华呢?这里立即让人回想起拉平自然能力的荒谬做法,莫扎特当然可以拒绝这种无理要求。除了莫扎特,这种非正义的负责方就应该是上帝了,上帝没有像萨里埃利所抱怨地那样根据人的德性水平来分配自然才能,或者说至少没有公平地分配给萨里埃利同莫扎特同等的自然能力,因此似乎应该承担纠正这种非正义之责。如果这说得通,运气平等实际上就具有很浓的神学背景,安德森指出,“运气平等主义者抱怨原生运气不平等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不公平或非正义,一旦去掉神学背景,他们诉求的就是没有意义的直觉”[16](P10),这种直觉在世俗伦理中没有位置。
三、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自然不平等是非正义的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了解一下正义的本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处于比其他道德价值更优先的地位。一种社会制度应当首先满足正义的要求,避免和消除非正义,即使这样做可能与其他的价值追求相冲突。所以规定正义的边界要小心谨慎,因为其“覆盖社会体制的程度将决定正义社会中正当地追求其他价值的剩余空间”[6](P303),正义统摄的范围越广,社会实现其他价值理想的可选择空间就越小。
内格尔区分了应对自然不平等的两种义务论正义观。一种认为正义的空间十分有限——只是规定了自由选择的正当性和强迫、歧视等行为的非正当性,而把人类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看作与正义无关的既定条件或事实。这些既定条件或事实构成了人类行为的起始背景,正义或非正义的判断只与这种背景中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有关。所以这种正义观对自然不平等持道德中立态度,它是前面提及的自由意志主义和自然的自由体系所应用的。与此相对的另一种正义观则极大地拓展了正义的边界,它认为“非正义不仅在于某些干涉,也在于容忍——不去改变容许某些背景条件造成不平等影响的体系”[6](P313),它把第一种观点看作与正义无涉的阶级、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等因素也拉入了正义的规范领域,要求积极地减轻甚至抵消它们的不平等影响。运气平等的背后就是这种正义观。
内格尔认为第一种正义观划做既定条件的范围太大,留给正义的空间太小,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他也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第二种正义观,他认为如果不平等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社会就应承担减轻它的义务。但就自然不平等来说,“因为引起不平等的人际差异不是社会而是自然造成的,所以避免这种结果的社会责任并不清楚”[6](P305)。为了说明这一点,内格尔让我们假想一种特殊的致病基因在人群中随机分布,携带者会在某个时期发病身亡,他的问题是正义是否要求社会补偿这些自然劣势的承受者,或者说社会给他们提供不了昂贵的救治手段是否是非正义的。内格尔认为,“因为正是自然给他们造成的打击,一个没有有效地纠正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并没有非正义之耻”[6](P315)。这些人的厄运不是社会而是自然造成的,这里也就不存在不计代价地补偿或救治他们的正义要求。当然这不是说社会应该对他们完全冷漠,正义之外还有人道关怀等其他道德价值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形,这只是说自然限制了正义的延伸界限,正义本身并不要求人们相互分享各自的命运或非选择的运气。
内格尔认为罗尔斯的观点中也有与此相近的成分,“罗尔斯明显认为不平等的一些起因比另一些更不正义”[6](P310)。他的第二条正义原则就把针对社会偶然因素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置于“词典式”优于差别原则的位置,这说明他似乎承认自然抓阄导致的不平等在不公平的程度上弱于阶级和家庭背景等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
在像内格尔那样以责任归属为根据圈定正义的边界之前,就自然不平等来说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还需要认真反思——其真的主要归咎于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吗?或者说社会在自然不平等的产生中真的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吗?有两点需要立即引起注意,一是智愚、强弱、美丑等能力或品质并不完全决定于基因,“通常来讲,基因组与细胞、组织、器官、整个身体以及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以产生我们感兴趣的各种禀赋——才能或残疾”[17](P197)。生物个体具有哪种性状不是固定不移和难以改变的,具有相同基因序列的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性状,“反应规范”(norm of reaction)一词在遗传学中指的就是相同基因对不同环境的反应幅度。自然能力或品质有社会层面的起因,这可以通过一个极端的例子看出来:苯丙酮尿症患者的智力低下,该病有基因方面的根源,但也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如果合理控制膳食中苯丙氨酸的含量,患者就不会表现这样的病症。二是自然能力或品质的价值不是确定不变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比如阅读障碍有生理学方面的原因,但在尚未发明文字的社会中就不构成一种缺陷,强壮的体格曾经对谋生非常有用,但在后工业社会中只有这种素质的劳动者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自然能力不是由自然完全决定的,自然差异也不会直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所谓的自然不平等都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都是自然差异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在确定自然还是社会应该为某种不平等负责时需要小心谨慎。以下是三种很容易归咎于自然的不平等,它们的背后都潜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
首先是性别不平等。女性的生存处境比男性差,这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内格尔指出男女之间纯粹的自然差异不会使任何一方处于劣势,与性别不平等更为相关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容纳生育事实的方式所形成的差异”[6](P316)。女性能够怀孕、生产和哺育小孩,但是社会期望还要求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照看老人和小孩,在经济上依靠男性养家等等,从而把她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了家庭内部,而整个社会体制也相应地减少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会,造成了她们面临的尴尬境地。社会对性别不平等的产生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作用尤其表现在即便一些女性没有小孩和不需要做家务,她们的人生前景也会受到同样的不利影响。所以引发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不是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而是像阶级或等级一样的社会因素。阶级造成了能力相同但出身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流行的社会期望造成了能力相同但性别不同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它们都阻碍了公平的机会平等,减轻它们的影响是正义的要求。
其次是残疾人所承受的不平等。一般的观点将这种不平等归咎于残疾人自身的生理特质,亦即残疾本身,但是近年来平等主义理论界逐渐意识到残疾的“社会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社会环境没有充分地包容残疾人的生理特质,没有为他们提供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方式,从而造成了他们与一般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比如一些瘫痪者的文字编辑能力很强,但是很难获得相关公司的雇佣,因为工作场所的设计常常没有为他们的自由移动提供方便(比如写字楼入口缺少供轮椅通过的坡道);语音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减少了聋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而互联网投合一般大众的设计也使盲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的不利影响有时是间接和隐秘的,比如大街上安置文字而非盲文指示牌看似增加了一般人的便利,没有恶化盲人的处境。但是一方面盲人的出行将变得相对更难,另一方面关于出行时间和守时的社会期望也会随着指示牌的安置而变得更为严苛,这些都使残疾人的社会生活变得更为不利[18](P596)。残疾的社会模式要求社会反思和改变它的惯常安排,增加它对不同群体的包容性,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对残疾人的生理特质进行纠正或补偿,如前文所指,后面这种策略可能是冒犯人和侮辱人的。
最后是能力不同的人们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能力不同,教育的可接受程度也不同,有的人本科毕业之后还能接受研究生教育,有的人高中阶段的学业就难以应对了,因此公平的机会平等要求社会为能力相同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默认能力不同的人享有不平等的教育机会。这里按能力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等级的教育体系似乎是正当的,内格尔即指出,“教育个人至其能力所及是合理的目标,如果在追求合理目标时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异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不平等就不是非正义的”[6](P316)。然而这种不平等也可能隐含着社会因素的很大贡献,前面提及的反应规范就给出了很好的启示——能力可能不是学习成就的唯一函数,教育环境也可能发挥着重要影响。某种僵化的教育体制可能只适合某些人的学习风格而不适合另一些人,后者在另一种教育体制下也能取得很好的学习成就。因此日常生活中家长或教师就要谨慎用这样的理由把问题推给孩子的天资或懒惰:同样的学习条件,为什么你同学的成绩好,你的成绩就差呢?他们更应该追问的是这样的问题:每个孩子的学习风格不一样,社会是否提供了包容这些不同风格的灵活多样的教育环境呢?
四、结 语
内格尔认为研究不平等时应该防止正义的越界:不平等如果主要归咎于社会则是非正义的,归咎于自然则不是非正义的。然而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社会因素在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形成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即便内格尔所举的先天疾病的例子也是如此,这里初看是基因缺陷造成了患者的不利处境,但是如果这种疾病是可治愈的,而社会没有投入充足的研究基金来寻找救治方案,那么该病患者所承受的不平等就不能只归咎于自然。所以很多自然不平等需要重新拉回正义的规范领域,社会应该承担减轻这些不平等的义务。然而这种立场与运气平等仍然存在着重要区别:一方面,对不平等的责任追踪为社会提供了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论理由;另一方面,强调对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是对单个人的生理特征的补偿或纠正也保证了对所有公民的平等尊重。总而言之,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自然的力量随着社会化的深入而在不断减弱,对待通常所谓的自然不平等,一定不能夸大自然的影响而忽视社会的作用,正像卢梭所说,人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差别极其小于在社会状态中的差别,自然的不平等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极大地加深了[19](P107)。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何怀宏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Bernard A.O.Williams.The Idea of E-quality[A].Louis P.Pojman,Robert Westmoreland.Equality:Selected Readings[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91-102.
[6]ThomasNagel.JusticeandNature[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7,17(2).
[7]Anthony T. Kronman. Talent Pooling[J].Nomos,1981,23(HUMAN RIGHTS):58-79.
[8]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1]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12]Kurt Vonnegut,Jr..Harrison Bergeron[A].Louis P. Pojman,Robert Westmoreland. Equality:Selected Readings[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15-318.
[13]Allen Buchanan,et al. From Chance to Choice:Genetics and Justice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4]Eric Rakowski.Equal Justic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15]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J].Ethics,1999,109(2):287-337.
[16]Elizabeth Anderson.Th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between Luck Egalitarians and Relational Egalitarians[J].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2010,Supplementary Volume 36:1-23.
[17]Alexander Rosenberg.The Political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Endowments:Some Considerations[A].Darwinism in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95-225.
[18]Sean Aas,David Wasserman. Natural and Social Inequality:Disability and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J].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2016,13(5):576-601.
[19]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张 虎,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自由与制度研究”(16CZX002);山东社会科学院自选课题“当代西方平等主义理论中的起点公平概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