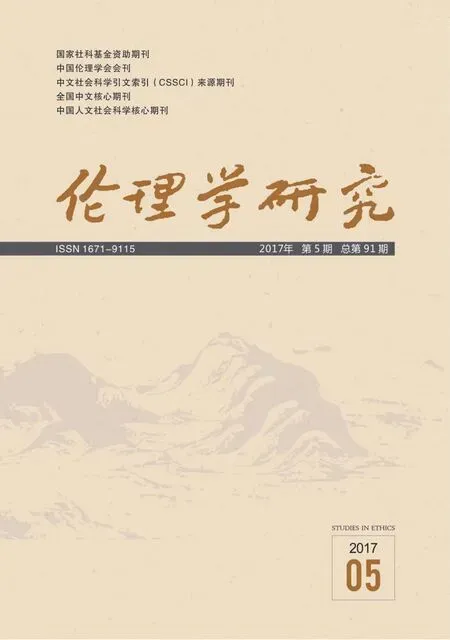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夏天静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夏天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梁漱溟;乡村组织;伦理本位;新乡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危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混战,给中国政治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导致乡村经济衰落,日趋崩溃。在追寻探索“中国往何处去”的种种方案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社会的新出路。梁漱溟认为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面对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局面,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道路和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俄国革命道路均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只能走伦理之路”[1],融合中西,从乡村入手重建中国新社会的构造。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2](P166)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概括,也成为其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梁漱溟得出中国社会的改造即乡村建设道路只能走伦理之路的结论,正是源自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定性分析。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特性
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倚重家庭源自于集团生活的缺乏。从团体与个人关系的角度对比中西社会,西方社会或有重在个人的“个人本位”(如英美两国),或有重在团体的“社会本位”(如俄国);中国人却既无团体观念,又无个人观念,恰恰从“团体-个人”的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开来,以伦理组织社会。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宗教,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将中西方社会置于不同的发展轨迹上。西方社会以宗教开启集团生活,中国社会则以道德代替宗教,开启了家庭伦理生活。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梁漱溟认为,家庭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因缺乏西方宗教形态的集团生活,存在于集团生活中的“团体-个人”关系消隐于传统中国社会,就将家庭关系自然显露出来。家人是中国人天然的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人一生下来便在关系之中,并将始终在关系中生活,不能离开。父母是最先有的,然后有兄弟姐妹;长大成年后,有夫(或妻)有子女,并与家族中人相互关联;踏入社会,又有了师徒、东伙、乡邻、朋友等等关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每个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P30)。因此,梁漱溟指出,“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2](P168)。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关系为核心推广发挥,以家庭恩谊推准于社会,以伦理组织起整个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展开,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和夫妻关系延伸开来,逐渐形成一个人四面八方或近或远数不尽的关系,种种关系皆是伦理。其中,比照“父子关系”而来的“君臣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关系,比照“兄弟关系”而来的“朋友关系”则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之“夫妻关系”,即由父子、兄弟和夫妻的三种基本家庭关系推衍出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基本五伦。从而举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将发乎家庭亲情骨肉的相关之情延及全社会,将全社会的人互相联锁起来。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4](P82)。于是,没有宗教集团生活的中国传统社会,以一个人初生的家庭为起点和中心,由“个人-个人”关系层层推演出伦理本位,而西方社会以集团生活反复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之间。
再次,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重在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实质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4](P189),这种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2](P168)。相与之人,无论相交的深浅、相处的久暂,都自然互有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父子乃至伦理上的任何一方皆自然互有应尽之义。“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4](P82)这“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人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存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人际关系来定义个人的,如父之于子、子之于父,人在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二是伦理本位即义务本位,互以对方为重,即向里用力。当人与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时,要从自身解决,向里反省、自责、克己、让人,牺牲自己,为对方着想。
最后,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俗维持社会。社会无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梁漱溟认为,“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2](P179)。伦理化的社会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延展开来,使人与人之间互有情谊,同时又互尽义务,形成礼俗社会。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盛行,人与人处于相对竞争的关系,必须依赖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则倚重礼俗来维持社会,习俗将家庭中亲其所亲的骨肉之谊推广于其他,师徒、伙东等关系或比于父子之关系,朋友、同侪等关系或比于兄弟之关系,其情益亲,其义益重。
综上所述,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从家庭至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均出现了伦理化的特质,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固有精神:“一即伦理,尚情谊;一即人生向上,尚义理。”[2](P259)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和认识,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梁漱溟理论思考的落实之处。在伦理本位的认识分析基础之上,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也不是“贫、愚、弱、私”,而是“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出现了“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其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2](P161)。
二、新乡村组织的伦理基础与构造
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团体生活的,中国人天生也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的。鸦片战争之后,外来的经济竞争逼迫中国人从散漫往团体组织里去,却在民国初年《临时约法》公布之后出现旋即被破坏之事实。梁漱溟由此指出西方政治制度虽好,但简单地照搬执行,“看着社会如白纸一般,看社会中人软面条无异,可以任凭染色,任凭改变”[2](P21),实则大谬不然。订立约法者未能认识到“中国人习惯于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适合”[2](P21)。梁漱溟坚守“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中国固有精神,将“伦理情谊”融合入西方团体组织之中,形著于新礼俗构建新组织,辅以近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合作、对外相联之义;同时需补充培育中国人在团体生活中缺乏的个人观念和团体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而以教育启发乡民们的组织自觉为目标而设立的乡农学校①,就成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由此可见,新的乡村组织是乡民们依照新礼俗自觉组织起来的由贤智之士领导的合作社。乡民之间的“自觉合作”是组织动力,旧乡约改造而来的“新礼俗”是组织基础,进步于取决多数的“崇尚贤智”是组织原则,这就与西方团体组织的强制、法制和民治区别开来,也使新乡村组织与中国当时的乡公所等地方自治组织相比,具有了一系列新的伦理特征。
1.依新礼俗规约新组织
从伦理本位的社会认识出发,梁漱溟坚持以礼俗而非法律来规范新组织。相较于西方社会的集团生活,中国社会更倚重家庭家族。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靠法律,而传统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将来仍要如此,“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面颁行法律”[2](P276)。对此,梁漱溟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统一的国家无力颁布统一的法律;二是中国人的伦理习惯使然。因此,他认为中国新乡村建设是不可能依靠强力的法律,而是从个人义务出发、依靠新礼俗来教育启发乡民自觉组织团体。
梁漱溟认为“新组织即一新礼俗”,新礼俗即对清朝陆桴亭旧式乡约改造后的新乡约。梁漱溟推崇清朝陆桴亭《治乡三约》中积极的乡治思想,因其将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善恶劝诫的道德内容由虚变实,倡导举办社学、社仓和保甲等教育、经济、政治组织机构。在此旧乡约的基础之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补充改造:一由消极的顾恤提出积极的生产合作,即建立经济合作社;二将偏乎个善向上提升至社会改造,即建立新组织;三从邻里族党拓展至社会联合,即建设新社会。由是观之,梁漱溟的新礼俗就是添加了合作、改造和联合之义的新乡约,新乡村组织必须集教育、经济和政治功能于一体。
在新礼俗的推行上,梁漱溟不主张明清时期旧式乡约依仗政治力量的强制推行,推崇效仿宋朝吕和叔首倡的由邻里族党等社会团体自觉发起的方式。乡民们本就生活在邻里族党之中,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个人想要过得好,就必须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将邻里族党间的关系处理好。乡村经济的衰败迫使乡民们由经济上的合作需要而求增进相互间的关系,在新乡约的引导之下自觉由散漫走进团体里去。
2.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的新关系
新组织的建立,对于没有集团生活经验的中国人,“仿佛在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五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2](P308)。梁漱溟从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出发,摒弃西方近代集团生活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提出适合于中国社会的基于义务本位的“团体—个人”观。
梁漱溟认为,“我们来组织乡村的时候,大体上是要像乡约一样,大家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2](P329-330)。完全从个人权利出发,无法促使原本散漫的中国人自觉地往团体中去,另一方面也抛开了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与中国固有精神不合,无法引导乡民们自动结成新的组织。只有从伦理本位出发,以义务本位来定义团体中“个人—个人”、“团体—个人”的关系,才能形成中国人能接受的团体。在梁漱溟看来,新乡村组织必须从传统伦理情谊出发,强调关系中个人对他人的义务、个人对团体的义务,向内用力,通过互相尊重、互相扶助、互相勉励才能结成团体,形成合作。
3.以相对论伦理主义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
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家庭,没有团体,更没有团体生活中的个人,因此在新乡村组织的建设中,既要培育乡民的团体观念,又要培育乡民的个人观念。但这两方面要求是相互矛盾的,以致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以实现新乡村组织在中西具体事实上的沟通调和。在团体组织与个人权利的矛盾中,“我们发挥伦理思想的结果,个人一定要尊重团体,尽其应尽之义;团体一定尊重个人,使得其应得之自由平等”[2](P308)。这样一来,中国人原本在团体观念与个人观念方面都不够,而伦理适足以补充了这两面。
在个人观念方面,梁漱溟从伦理本位出发,将“互以对方为重”即“尊重对方”确立为处理个人对团体、个人对他人的一个道德原则,具体体现在公民权、平等权和自由权的中西融合上。
其一,新组织中的新公民权。伦理情谊是中国固有精神之一,即义务本位,说的是“我有什么义务”,这与西方政治里公民权强调的“我有什么权利”相冲突。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来调和中西,按西方观点,“个人既认为是自己的权利便非要不可”,这是从自己出发;而按中国道理,“从分子说是个人对团体应尽的义务”,这却是从对方出发。这时可将权利调转过来说,以对方为重,话从对方说过来,道理从对方讲过来——即“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2](P294)。
其二,新组织中的新自由权。中国人过去缺乏团体社会,没有团体干涉,没有认识到自由,应该补充确立起自由观念。梁漱溟不主张西方社会的“天赋人权”,而是结合“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将自由与中国固有精神相结合,一是融合伦理情谊之义,强调自由是从对方来的,“自由是团体给你的,团体为尊重个人所以才给你自由”[2](P299);二是合乎人生向上之意,指明“团体给你自由是给你开出一个机会,让你发展你的个性,发挥你的长处,去创造新文化”[2](P299)。新的自由观念与中国精神完全相合而不冲突,合乎伦理又合乎人生向上。
其三,新组织中的新平等观。梁漱溟认为,新团体中大家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但这一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在承认天然等差基础之上的平等。“一种是从看重理性、尊尚贤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2](P296)两个等差都是天然不可少的,均是从中国的固有精神中来。中国固有精神之一是人生向上之意,人生必然应该向上追求,以贤能、智慧为目标,故必然要有等差;中国固有精神之二是重伦理情谊,子女天然地对父母要尊敬,晚辈天然地对长辈要尊敬,也是自然要有的等差。在梁漱溟看来,这两个等差是自然而然的,与平等并不冲突。
团体观念方面,梁漱溟强调要求新组织中的乡民具备团体生活之习惯。他认为,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直言中国人缺乏西方人在团体生活中的“公德”[2](P194),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公德概念,认为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公德细分为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制精神四个方面[3](P68)。
在乡民“公德”的补充培育方面,梁漱溟尤其重视西方团体多数主动与中国精神的融合,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或“多数政治的人治”[2](P292)。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固有精神中有“人生向上”的要求,即提倡尊贤尚智,就是说事情的处理一定要听从贤者智者的话。但在团体组织中,尊贤尚智带来的“人治”与西方团体中多数表决的“法治”相冲突。梁漱溟首先坚持“在一团体中,多数分子对于团体生活应作有力参加”[2](P292)。意为团队中的多数分子对团体的事情主动用心思用智慧;然后在“团体分子有力参加”的基础上调和进尊贤尚智的中国精神。结果是,一方面确实是多数政治,因为多数是主动参加而非被动;另一方面,又以贤明的人为最高。
总之,在新乡村组织中,梁漱溟坚持“伦理本位”的出发点,以中国传统的固有精神融合入西方团体,从个人义务出发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伦理,培育乡民的个人观念和团体观念,建立了一个情谊化的新组织。
三、新乡村组织的伦理困境及反思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梁漱溟希望能“老根发新芽”,在有形的乡村“根”和无形的传统伦理“根”中融入西方的平等权利观,并补充培育团体公共生活中的公德伦理,生发出新乡村组织的“芽”。中国传统社会重私德而无公德,公德概念的提出始于梁启超的《新民说》。他指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5](P113)。传统中国社会孕育更多的是建立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以五伦为代表的私德伦理,公德的补充培育成为新乡村组织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梁漱溟是真正将梁公开启的公德观念引入到乡村建设中的实践者,但其从伦理本位出发,融合中西确立“团体-个人”中的伦理关系时,忽视了在时代变迁中应有的转换。第一,忽略了传统社会与新组织团体中“个人—个人”关系的内涵不同。传统伦理关系中是以“己”为中心形成亲疏厚薄不等的与他人的差序关系,而人人平等则是新组织团体中的关系特征;传统伦理关系中的交往产生于熟人之间,而新组织在范围上大大突破了熟人圈,建立起广泛的陌生或半陌生的人际交往。第二,忽略了新组织团体生活的公共性,将新组织中多出的“团体-个人”关系与传统五伦关系平行,在新一伦关系中简单推衍传统伦理原则。传统伦理中的关系如父—子,两者是一一对应而独立的;但在新组织中,团体由众多个人组成,个人属于团体,立体的从属关系不同于传统平面化的独立相对关系。第三,忽略了公共生活的形成发展对公德伦理关系生发的基础性作用。传统社会的私人生活是五伦关系的基础,公德伦理关系则必须是在公共生活的正常发展基础之上产生和形成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591)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7](P99)。忽视私德、公德形成的社会生活基础条件,无法真正培育出新组织团体的公德伦理。
在梁漱溟由传统五伦的私德规范扩展至公共生活领域时,其伦理本位主义的出发点,使得“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首先,在公共观念的生发上,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强调“此一人对彼一人”的“一对一”关系,而个人关系的简单叠加是无法生发出“团体—个人”关系之中的公共观念的。无论是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还是其推广出的朋友关系、君臣关系,其实质依然是“个人—个人”的关系。“个人—个人”关系存在于私人关系中,而“团体—个人”关系中多出的公共空间,是无法由私德来规范和调节的。其次,在公民权利的保障上,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强调的是一种义务关系,个人权利以“尊重对方”的道德原则来实现,将我的权利视为他人的义务,权利的保障没有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因而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保障制度。最后,在法治精神的确立上,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难以调和情与法的冲突与矛盾。
基于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七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建立了乡学、村学,以教育引进自治,在开发民智、改善风俗、振兴产业、发展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其批判审视中西文化,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思考今天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然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成也伦理,败也伦理”。他既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础作用及其中伦理文化的重要影响,却又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8],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今天我们同样面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和发展,如何在乡村道德建设中汲取传统伦理的有益资源,同时契合当前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仍是值得探究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注 释]
①乡农学校又称“村学”、“乡学”,后者是在取得地方自治实验权之后的组织名称。在没有取得地方自治实验权的地区,由私人举办的乡农学校并不与当时现行法令冲突,因此乡农学校成为梁漱溟阐述其新乡村组织的通常提法。
[1]赖志凌.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伦理特质及其当代困境——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一[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 3卷(2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5]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王露璐,吕甜甜.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夏天静,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乡村伦理研究”(15ZDB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