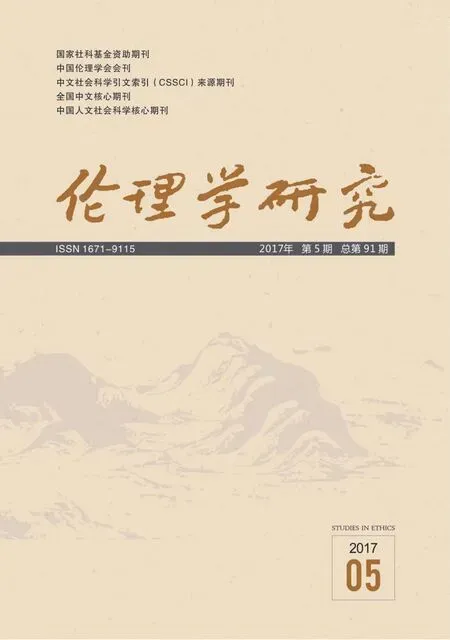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
——以罗尔斯为视角
余 露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
——以罗尔斯为视角
余 露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政治社会实践联合体政治正义共享目的政治认同
大多自由主义者都提倡特定类型的国家中立(state neutrality)①。这一原则强调“公共的政策、制度等应该平等地包容所有值得的善观念”[1](P126),它并不要求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影响是中立的,而是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在对待不同的善观念时要恪守中立的立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巨擘,罗尔斯典范地诠释了中立原则,并试图借此探讨理性多元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然而,罗尔斯又旗帜鲜明地指出,良序政治社会建立而践行正义的制度是一种伟大的内在善,是公民所应共享的终极目的。因此,对罗尔斯而言,如何理解价值中立与共享目的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还引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限度何在?共享目的在政治社会中有何作用?
本文将从罗尔斯出发,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找寻答案。首先,文章将在第一部分通过概述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来呈现他对中立原则的持续追求,进而指出罗尔斯并未因此落入“私人社会”的窠臼,他认为政治社会的公民持有某种具有内在善的共享目的。然而,第二部分将指出,由于共享目的对于内在善的强调,它的确与中立原则构成了紧张关系。于是,理解政治社会的善与中立原则之间的张力,将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在第三部分,我们通过进一步剖析发现,中立原则与共享目的的和解倚赖于公民共享的自由价值,政治社会实际上在两个层次上拥有共享目的。最后,本文将尝试性地探究共享目的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以彰显共享目的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
一、政治社会的善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国家决不能偏袒任何完备性学说及其相关的善观念。”[2](P202)罗尔斯自觉地秉承自由主义的这一原则,努力地确保政治自由主义在目的上的中立性:基本制度的设计并不旨在鼓励特定的完备性学说。正是这一追求,促使罗尔斯将对正义的“稳定性证明”从“一致性论证”调整为“重叠共识论证”。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稳定性提供的证明被称为“一致性论证”。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道德心理学角度描绘良序社会的成员如何经由权威道德、社团道德和原则道德获得正义感;第二阶段关注正义感与善观念怎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正义结构。第二阶段最基本、最核心的论证是由康德式的解释给出的,它将一种特殊的人性和道德能力指派给人们——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并认为实现这一人性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将正义感(按照正义原则行事的欲望)作为调节性的欲望。换言之,选择正义原则并按其行动,是内含于人性的要求。罗尔斯试图借助这一论证表明,人们在原初状态下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具有稳定性:即当无知之幕揭开,人们进入到由正义原则支配的政治社会中,他们会形成正义感并依据正义原则行动,当正义原则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自觉地让利益受正义原则的规导。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人们会遵循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规定了在不同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之间以及它们所属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进行调解的协议”[3](P173)。
然而,一致性论证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及所属文化形态间的差异,因为康德式的论证将一种特殊的道德人格赋予人们,这种道德人格确保人们“接受相同的正义观,并似乎还接受相同的完备性学说,那个正义观正是此学说的一部分,以及是从此学说中推导出来的”[4](P554)。在这里,“正当原则的证成……是奠基于某种特定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界定了什么是人最重要的‘好’,并促使人有最高序的欲望去实践人的本性”。这种对人的诠释是完备性的,“它界定人的本质,限定人理解自我的方式,规定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如何看待自身与他人的伦理关系”[5](P201-202)。但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可能就完备性的人性学说达成一致的看法。罗尔斯自己就曾设想例外情形:“假定即使在一个良序社会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肯定其正义感不是一种善。假定由于他们的目标和需要以及他们本性的特有性质,对善的弱描述不能成为他们保持这种调节性情操的充分理由。”[3](P455)也就是说,在罗尔斯看来,虽然道德人格确保了正义感具有压倒性的动机地位,但仍有一些人不依正义原则行事。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援引道德人格的普遍性来指责这些人不合乎理性,进而将他们排除在社会合作系统的考量之外,但这难免武断。“或许罗尔斯认为,‘康德式的解释’只在那些相信它的人身上才是动机性的力量。”[6](P887)那如何应对这些反对者呢?巴里指出罗尔斯只有两条路:走向重叠共识论证;退回霍布斯,援用惩罚手段强迫反对者遵从正义原则。罗尔斯并不否认惩罚性手段的作用,但“稳定性问题并不是让那些反对某一观念的人来分享该观念的问题,或者说,如有必要的话,通过有效制裁让他们遵循该观念来行动的问题”[4](P553)。更为严重的是,它违背了中立原则的要求,并没有公平正义地处理不同宗教和道德学说之间的冲突。于是,罗尔斯走向了“重叠共识论证”。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试图利用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交迭共识)来为正义原则的稳定性作论证。这一论证指出,民主社会的公民能就政治的正义观念经由临时协定、宪法共识形成重叠共识,并以此调节因所持有的多元化完备性学说而导致的在政治领域的矛盾。更进一步,由于政治价值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它们又兼容于公民的完备性学说,所以它们具有压倒其他一切价值的优先性。随着政治合作因重叠共识不断取得成功,政治正义观念的稳定性便得到了保证。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因为康德式的解释“没有考虑多元论的境况”而不具现实性,罗尔斯放弃“一致性论证”,走向了“重叠共识论证”。这背后的动力正是对中立性的追求。罗尔斯竭力避免将稳定性论证建基于某一独特的善观念(如康德式的人性),而试图中立地、无偏倚地对待所有完备性的道德学说、哲学学说和宗教学说。
这似乎让罗尔斯陷入了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个人和小型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目的,政治制度安排仅仅被视作达致特殊目的的手段,“正如每个人在沿着公路旅行时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地”[3](P412)。但在罗尔斯看来,并非如此。他指出,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有被其公民共享的目的,即由正义观念(原则)所规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实现了人们的利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善,它本身就是善的,它的成功实施是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的最终目的。古德曼(Gutmann)在评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时曾说:“如果我们假定,按照定义,我们的认同由善构成,那么我们就必须将正义感看作认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我承诺将他人视作平等的人并因此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恰如我作为犹太人并因此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逾越节一样,都是我的认同的基本部分。”[7](P311,note14)罗尔斯极其赞许古德曼的看法,认为他的说法“肯定是正确的”,“互相以正义对待这种终极目的是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8](P240页脚注)。
罗尔斯的这一基本立场贯穿了其思想始终,并没有随着稳定性论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指出,“人们事实上分享着最终目的,他们把他们共同的制度和活动看作自身就是善的”[3](P413)。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遵循正义制度、将正义感置于动机系统的顶层是实现人性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们会认可正义制度、正义观念并意愿按其行事。这样,我们进入到一种“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们从彼此的由自由的制度激发的美德和个性中得到享受,同时,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善是人类完整活动的一个因素,这种活动的整个系统是大家都赞成的并且给每个人都带来快乐”[3](P414)。在其本科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中,青年罗尔斯指出,人格只有在因信而结合的宗教共同体中得以体现。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类似的断言,“一个良序社会的成员们有共同合作以便以正义原则允许的方式实现他自己的和他人的本性这一共同目标,……正是通过维护这些公共的安排,人才能最好地表现他们的本性,才能获得对每个人可能的最广泛的调节性美德”[3](P417-418)。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依旧认为,良序社会中的公民拥有着共同的终极目的:“他们……认肯相同的政治正义观念。这意味着他们共享一个非常基本的政治目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具有高度的优先性:即支持正义制度的目的及因此而相互承认对方之正义的目的,更不必说许多也必定为他们所共享并通过其政治安排来实现的其他目的。此外,政治的正义目的也许是公民相互间最基本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最基本的目的来表现他们构想成为的那种个人。”[2](P214-215)只是,罗尔斯不再谈及人性,更不强调共同体是实现人性的必要条件,而是认为,无论公民自身持有怎样的完备性学说,他们都会就“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基本的正义问题②达成重叠共识,而这一共识的核心是政治正义观念。受正义观念规定的宪法根本就构成了公民共享的根本目的,这样的政治社会便是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这一社会在两个方面是善的。在个体的意义上,它对于个人而言是善的。一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实践两种道德能力是善的;二是因为,“该社会确保他们享有正义的善和相互尊重与自尊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的意义上,共享的目的需要许多人的合作方可达到,“建立并长期成功地运行理性而正义的……民主制度……乃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善,值得我们尊重”[2](P216)。
二、共享目的的中立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共享目的发生了与稳定性论证的转向相应的变化,它不再诉诸于以康德式的人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它的内涵却始终如一、前后一致:首先,良序社会应该建立并践行理性而正义的民主制度,这是公民应该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其次,这一目的并不仅仅在工具性的意义上为善——有助于个体过上好的生活,它更是一种内在善,正义相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善;再次,这一目的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
罗尔斯这一立场让人心生疑问: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中立的呢?德沃金曾如此谈论中立性:“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任何关于好生活或赋予生活以价值的特殊观念。”[9](P191)如果对政府一般结构和政治运行进行规定的根本原则必须体现某种内在善,公民必须在应然的意义上共享着某种终极目的,这样的政治社会到底与有着完善主义倾向的、严格的政治共同体又有何区别呢?
罗尔斯指出,良序的民主社会显然不同于共同体,共同体是依靠完备性学说统一起来的、特殊类型的联合体(association);而政治社会却有着与联合体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民主社会是“完全而封闭的社会系统”——“在它自足且给予人类生活的所有主要目的以合适地位这一意义上,它是完全的。……它……又是封闭性的,……人们只能由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2](P42)。这一特征被后来的学者深为诟病,“现实中如过江之鲫的移民浪潮足以证明,即使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中,‘社会成员资格’也并不都是先行给定的,而是有相当部分由主体自愿选择的”[10](P165)。但周濂后续的讨论实际上提供了理解罗尔斯的进路:罗尔斯所强调的是“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以法律地位’来界定的公民身份”[10](P170-171)。而且,罗尔斯并非在实然的意义上言及公民在现实政治社会中获得公民身份,而只是在应然的意义上指出良序社会的成员应被视为“平等而自由的公民”——“这些正义原则必须在市民社会的背景制度中给予基本自由和机会以优先性,它们使我们能够首先成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根据这种身份将我们的角色理解为个人”[2](P42)。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的完全性得以理解:只要兼容于政治的正义观念,公民由其完备性学说所界定的各式各样的特殊的终极目的就具有平等的地位,受正义观念规制的宪法为公民形成、修改、追求其特殊善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支持。
其次,良序的民主社会“没有任何……在完备性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目的和目标”,它只有“宪法意义上的特殊社会目的,在宪法前言中所陈述的那些目的……必须归于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及其公共理性的名目之下”[2](P41-43)。
在讨论完两者的区别之后,罗尔斯增加了这样一个脚注:“本节对社会与联合体所作的区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迈克·奥克肖特……对实践联合体与目的性联合体所作的区分。”[2](P43页脚注)
在《论人的行为》一书中,迈克·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区分了两种模式的联合体:事业联合体(enterprise association)和公民联合体(civil association)。事业联合体是人们在追求“某些共同的目的、某些共同获得的实质性事态或某些持续地被满足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系。在其中,践行者(agent)是由于共同地追求某些想象的或渴望的共同满足而关联起来的,他们将需求之满足作为共同目的加以承认,也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摆脱这种关系。奥克肖特进一步指出,只要事业联合体的目的不是转瞬即逝或者被确信会被形式化所损害,那联合体中的践行者就会承认某些规则或类规则的安排具有权威性。但这些规则并不能确认更不用说定义一个联合体,它们与联合体的目的相关联,是实现联合体目的的手段。公民联合体则不同,它是践行者因实践(practice)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共同地认可某些慎思(如用法或规则)并在自主选择的行为中明智地遵守这些慎思。公民联合体有两个重要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关系,人们是因使用共同的“语言”或同样的表达而非因拥有同样的信念、目的或利益而形成的联合体;其次,它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并非因为所有使用者都有着同等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都关心相同的技能并被指定具有相同的地位[11](P112-122)。
特里·纳丁(Terry Nardin)指出,罗尔斯所描述的政治社会并非如其所言是“公民联合体”(“实践联合体”),而恰恰相反,他笔下的政治社会是“事业联合体”(“目的联合体”),因为“国家似乎就是个体联合起来追求共享目标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规则仅仅是那种追求的手段,它们只有在服务于个体利益的意义上才对联合体具有约束力。罗尔斯不仅将制度也将社会本身理解为个体间的‘社会合作图式’,规则只有在个体从参与社会合作中获得‘公平份额’的意义上才具有权威性”[12](P263)。
罗尔斯回应道,纳丁抓错了重点。关键点不在于政治社会是一种合作图式,而在于合作的方式及其取得的成就:良序的民主社会里,“人们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来进行合作的,他们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在理想的情形下)是一种具有正义背景制度的公正的基本机构,这些背景制度是实现正义原则并给公民提供着满足他们作为公民之需求的全能目的性手段的背景制度。他们的合作是确保他们相互间的政治正义。而在联合体中,人们是作为联合体的成员来进行合作的,他们所要实现的正是驱使他们加入该联合体的动机,而这一点又会随着他们从一个联合体到另一个联合体而发生改变。作为公民,他们合作实现的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正义目的;而作为一联合体的成员,他们合作实现的目的却分属于他们各自持有的不同的完备性善观念”[2](P43页脚注)。结合之前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理解罗尔斯的回应,罗尔斯从未将良序社会仅仅看作达致个体善观念的工具,而是认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内在善,这种内在善并不因个体所持有的特殊善观念而有所差异或发生改变。
罗尔斯认为,他所提倡的政治社会只能是公民联合体或者实践联合体。这样的政治社会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方面,公民有各自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完备性善观念,他们仅仅就“宪法根本”所依据的政治正义原则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也是政治社会所共享的目的;另一方面,人们在这一联合体中被平等地对待,社会的基本制度给予了每个个体公平的基本善,以确保他们两种最高阶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实现自己特殊的善观念。
也就是说,在罗尔斯看来,即便政治社会将正义原则视为共享的终极目的,但这一目的并不偏袒或鼓励任一特定的完备性学说,它赋予了一切合乎理性的善观念以平等的地位,因而它仍是价值中立的。如第一部分所说,这种中立性的诉求促成了罗尔斯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在《罗尔斯后期正义理论研究》一书中,杨晓畅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前后期之间有四个重要的变化:性质从奠基于康德式道德主体观念之上的完备性学说转变为独立于诸完备性学说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方式从道德建构主义转变为政治建构主义;外延从“作为公平的正义”之两个原则扩展为“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家族”;作用则在保留规范引导社会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为公共证成奠基的功用[13](P143)。其中,最核心的变化当属性质的转变——从伦理正义走向政治正义。“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现代民主社会提供一种普遍合理的社会公正伦理学基础支持,其理论核心是建立一套既能确保个人自由又能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正义’本身……既是其社会正义伦理的理念基始,又成为罗尔斯心中建构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14](P623-624)也就是说,《正义论》时期,正义原则不仅规范着制度,还带着浓郁的价值属性。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明确地宣称,他要“寻求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一正义观念有三个特征:首先,它适用于现代立宪民主制度结构;其次,它独立于一切完备性学说;再次,它的内容是借助隐含在民主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重叠共识理念得到表达的[2](P11-14)。罗尔斯一再强调,政治正义适应的政治领域是个独立的领域,它无需以任何完备性学说为前提,而它与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关系则留待每个公民自己解决。似乎,罗尔斯后期所推崇的正义观念已尽可能地抹去了价值性。换而言之,作为共享目的的正义原则与中立价值达成了完全的和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三、共享目的与政治认同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引入科特·拜尔(Kurt Baier)的一对重要概念。在《正义与政治哲学之目的》一文中,拜尔区分了“正义概念的观念”(a conception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和“正义的观念(或原则或标准)”(a conception or principle or criterion of justice)。“正义概念的观念”指对“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拥有正义概念意指什么”的看法,正义概念(the concept of justice)是一个规范的道德观念,它将正义和非正义行为区分开来。在拜尔看来,安克鲁-撒克逊语言共同体有单一且内在一致的正义概念,但哲学家就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即不同的观念。“正义的观念”是罗尔斯的术语,它是关于“如何才能满足正义之道德要求”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拜尔指出,“我们已经就正义的观念存在共识,虽然我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没认识到这是关于我们正义概念的正确观念。”这一共识就是公平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tability),这一原则只包括程序性的政治宪法原则,“我们已有的宪法共识似乎足以支持稳定的社会统一”[15]。
借助拜尔的区分和评述,我们可以推测,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所彰显的“价值中立”是有限度的:“价值中立”只是针对诸多“正义概念的观念”的中立,其背后有着更为底层的、共享的“正义概念”。这一推测可以得到两方面证据的支持。第一,罗尔斯一再强调重叠共识要从隐含于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根本性直觉出发,而且,在重叠共识的形成过程中,罗尔斯纳入了很多实质性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比如赋予了公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甚至将这些价值诉求视作讨论的起点。第二,罗尔斯对多元性的考虑也是有所限制的:并非所有的善观念都可以被纳入到政治考量中去,只有那些合乎理性的善观念才被允许。正如墨菲(Mouffe)所指出的,罗尔斯对合乎理性的学说和不合乎理性的学说间的区分,实际上是“在接受自由主义原则和反对这些原则的学说间划了条界限”,有些完备性学说之所以被视作不合乎理性的,只是因为它们“会在公共领域危及自由主义原则的支配地位”[16](P4)。实际上,罗尔斯自己曾清晰地表明过这一立场。在《重叠共识理念》一文中,他说,政治正义观念可能不止一个,但“适合立宪政体的任何可行的政治正义观念,事实上必须是自由主义的”[4](P482-483)。罗尔斯的理论针对的是特定类型的宪政民主国家,这类国家是“自由主义化”的国家,自由及其相关价值作为底层的价值已深深植根在公共的政治文化当中,被人们所共享。正如周保松所言,在“自由主义化”的民主社会,其中的多元宗教学说、道德学说都已“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内化成信仰的一部分。这些理念包括道德平等、个人自主、基本权利和宽容等。经过这样的转化,他们不再觉得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是不得已的政治和道德妥协,而视之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5](P248)。
论述至此,我们发现了罗尔斯思想中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一个层次是“显性的”,即持有多元的完备性学说的公民以政治的正义观念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活动为共享目的;另一层次是“隐性的”,即民主宪政国家或良序的政治社会里,公民共享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及其他相关价值。在隐性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上,显性的共享目的确实可以与中立原则相容,因为它并不偏袒也不给任何特殊的完备性学说以优先性。完备性的学说只要接受自由主义原则,就可以在政治领域中获得平等的考量。与之相应,中立性是一个“范围概念”(range concept),在罗尔斯那里,中立性的范围“通过只纳入普遍原则所允许的生活方式而排除另一些生活方式来彰显”[17](P502)。
正是借助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罗尔斯完成了稳定性论证,也达致了公民对于良序社会的政治认同。稳定性论证是依靠重叠共识论证完成的。而人们之所以能就正义原则及其制度形成重叠共识,是因为他们共享着自由及相关价值,相互以正义相待是“自由主义化”的内在要求。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基础之上的稳定性,“它的目标是希望取得合理且理性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的接受,并因此诉诸于他们的自由公共理性”[4](P552)。而这正是契约论者处理政治认同问题的进路。“Rawls理论关注的不是认同问题,然而它的若干重要概念——如‘交叠共识’……却是自由主义者谈论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工具。”[18](P114)
一般而言,政治认同即个体对政治组织的认可、归属和效忠③,它表现在个体对政治组织的根本原则的接受并自觉地依其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契约论者在应然的意义上追问政治认同何以达成,即政治组织满足何种条件才会被其治下的成员所认可和接受。这并非“实际的被接受”,而是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10](P150)。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对于稳定性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在处理政治认同问题。一致性论证和重叠共识论证表明,“有理由期望全体公民都能够赞成的方式”,便是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对《正义论》时期的罗尔斯而言,作为权力的行使主体,国家唯有凭借正义原则方可得到其成员的认可。更准确地说,只有当国家的立宪、立法以及实操都符合正义原则时,国家才可能获取其治下人们的认同,因为这是与人性相契合的。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否认了一致性论证,但其核心立场却未发生变化。“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的政治价值仍被视作为一系列基本问题——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提供了理想的答案,也就是说,当国家的宪法根本——“具体规定政府一般结构和政治过程之根本;具体规定公民的平等之基本权利和自由”——符合“作为公平的正义”时,国家就会得到公民的认肯,因为公民能就政治正义原则形成重叠共识并接受其调节。
在罗尔斯的文本中,正义的稳定性与政治认同是紧密关联的。共享着自由价值的公民们对民主宪政国家达致政治认同是借助稳定性论证呈现的。而一旦政治认同达成,正义的稳定性也得以确保。“‘政治认同’就是指一个人对这些政治价值的接受与肯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部分成员愿意实践上述民主社会的政治德性,以之作为彼此解决社会争议的凭借,则政治共同体就获得公民们的认可,也获得了稳定。”[18](P116)
如果本文的讨论是可接受的,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中立性”是一个“范围概念”,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只有“值得的善观念”才会被平等地对待,“值得”最外围的边界是由其共享的自由主义的价值所框定的,其内部范围又因自由主义者各自倚重的价值而有所差异;二是,政治社会必定会有共享目的,显性的制度共识(或原则共识)和隐性的价值共识,缺一不可,这是公民对政治社会达致政治认同的基础。
[注 释]
①Peter Balint区分了三种形式的中立,即证成中立、意图/目的中立和结果中立(neutrality of justification,intent and outcome),参见 Peter Balint,“IdentityClaims:WhyLiberalNeutralityisthe Solution,Not the Problem”,Political Studies,2015,Vol.63,pp.495-509。本文因关涉罗尔斯,故只讨论前两者,而不考虑现实影响和结果。实际上,罗尔斯在拉莫尔(Larmore)启发下也做过类似区分:程序中立(procedural neutrality)、目的中立(neutrality of aim)和效果/影响中立(neutrality of affect or influence)。参见罗尔斯:《罗尔斯论文集》,第517-520页。
②在罗尔斯看来,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包括两类:(1)对政府一般结构和政治运行过程进行规定的根本原则;(2)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详细讨论参见《政治自由主义》第六讲第五节“宪法根本的理念”。
③政治认同依据认同对象可区分为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等不同类型。但因本文的话题仅仅关涉罗尔斯,其文本聚焦于政治社会;而且,现代政治中,国家是政治的主要活动场域、也被公认为是一定疆域内使用强制性权力最合适甚至唯一合适的组织,所以,本文将“政治认同”简单地等同于“国家认同”。本文不使用“国家认同”一词,是因为“国家”一词意义含糊,易引起争论。
[1]FrankLovettandGregoryWhitfield.Republicanism,Perfectionism and Neutrali 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ume 24,Number 1,2016,pp.120-134.
[2]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M].陈肖生,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5]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Brian Barry.JohnRawlsandthe Search for Stability[J].Ethics,Vol.105,No.4(Jul.,1995).
[7]Amy Gutmann.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ism[J].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14,No.3,1985.
[8]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Ronald Dworkin.Liberalism[J].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0]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1]Michael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2]Terry Nardin.Law,Morality and the Relations of States,Princeton[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13]杨晓畅.罗尔斯后期正义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4]万俊人.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建构[M].政治自由主义(附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5]Kurt Baier.Justice and the Ai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J].Ethics,Vol.99,No.4,1989.
[16]Chantal Mouffe.The Limits of John Rawls'Pluralism[J].Theoria: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Vol.56,No.118,2009.
[17]Peter Balint.Identity Claims:Why LiberalNeutrality is theSolution,Not the Problem[J].Political Studies,2015,Vol.63.
[18]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M].台北: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余 露,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系讲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共享思想研究中心成员。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政治认同视域下的爱国美德研究”(17B177);湖南师范大学共享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17G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