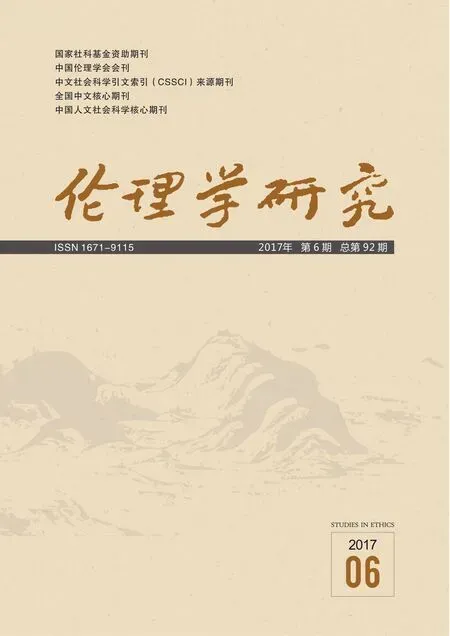斯多亚伦理学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吗?
——从二者对(幸福)的界定来看
田书峰
斯多亚伦理学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吗?
田书峰
斯多亚伦理学是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仍具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表现在朗(A.A.Long)与桑德巴赫(F.H.Sandbach)所持的对立的观点上,朗认为斯多亚伦理学是对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内部未解的矛盾和张力的一种回应和解决的尝试;而桑德巴赫则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并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而二者的术语重合不能作为有力证据,因为柏拉图哲学也同样使用过相同术语。本文意在借助斯多亚学派的创立者芝诺对幸福和德性的看法而重新审视这个难题,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朗和桑德巴赫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因为朗所列举的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重合或对应的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穷尽二者的关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对具体的斯多亚主义者的伦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反驳的依据本身也不能作为充足的理由。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的影响可以通过芝诺对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分析可见一斑。
伦理学;幸福;德性;斯多亚;亚里士多德
一、引 言
毋庸置疑,斯多亚伦理学仍然是古希腊德性伦理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因为斯多亚主义者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是将幸福(εδαιμονα)作为人的所有行动的最后目的(λο,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一切别的都是为了它才被做,而它不再是为了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清楚斯多亚伦理学或幸福论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只是将斯多亚幸福论看作是古希腊幸福论传统的一种延续并不能解释它是否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幸福论,如此它对于后者就有一种依赖性;抑或是它根本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而是独立地发展出自己的幸福论,也就是说斯多亚伦理学具有原创性或独立性,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没有解决的内部问题或矛盾进行了清楚的阐释,因此对后者并没有依赖性。按照第一种观点,斯多亚伦理学只是借用了很多亚里士多德或其漫步学派的伦理观点,如果没有后者的影响,斯多亚伦理学是无法被理解的,因此斯多亚伦理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有一种依赖性①。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斯多亚伦理学的陈述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变得更加清晰易懂,并不是用一些生涩艰深的术语来诠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②。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影响这个问题只能从对斯多亚主义者的具体伦理思想分析中来看,尤其是从二者对于幸福和德性的观点入手,通过对比更能把握二者的关系的真实脉络。但是,如果想要弄清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斯多亚主义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为按照一些学述史家(doxographer)的看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曾经在地窖里被掩埋200年左右的时间,如此,斯多亚学派根本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著作的。接下来,笔者试着主要从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n:前336年-前264年)、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3-前 43)、狄杜牧斯(Arius Didymus:公元前1世纪中叶)对于 εδαιμον α(幸福)的观点来看他们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关系。
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历史失传问题
那些支持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学派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学者通常诉诸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失传论证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历史上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学园内部的秘传作品(esoteric),另一种是为公众而写的外传作品(exoteric),这些外传作品大部分是一些对话,但是,这些作品全部失传;只有所谓的秘传作品流传下来③。这也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Corpus Aristotelicum)。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内部的学园作品在历史中的流传曾经有过将近200年的失传,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疑难,那些斯多亚学主义者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呢?斯特拉波(Strabo,64/63 BC–c.?24 AD),普鲁塔克(Plutarch,c.AD 46–AD 120)与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200-250)都曾经记载过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前371-前287年)死后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的命运和所藏书籍的去向。根据拉尔修的记载,特奥弗拉斯特在去世时并没有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藏书及手稿交给学园的继承者斯特拉托(Strato of Lampsacus,335–c.269 BC),而是交给了他的同事斯凯珀西斯的涅琉斯(Neleus of Scepsis),他便把这些藏书和手稿带到了自己的家乡-斯凯珀西斯。他的后人为了躲避当时皇家对扩建帕加马图书馆(Pergamon Library)而发动的收缴私人藏书运动,就把这些书籍储藏在一个地窖中,直到公元前1世纪初才被特奥斯的阿佩里孔(Appelicon of Teos)从涅琉斯的后人手中买下了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藏书和手稿④,这些藏书后来又被罗马的苏拉将军当作战利品的一部分从雅典带回罗马,而苏拉将军的图书馆管理员泰让尼奥(Tyrannio)将这些藏书匆忙加以整理,很快就公之于众,流传开来。后来,罗德岛的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cus of Rhodes)又重新对这些作品进行整理编撰,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Corpus Aristotelicum(亚里士多德全集)⑤。从斯特拉波的描述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特奥弗拉斯特在公元前287年过世一直到苏拉将军在公元前86年将这些著作重新公之于众的200年间,漫步学派内部除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对外的公众作品外就没有什么内部的学园秘传作品可读。对于这个观点,很多学者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尽管我们承认这个地窖的故事是真实的,并且涅琉斯带着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学园秘传作品而离开了雅典,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著作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初立伊始时并不被人所知。一个理由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安德罗尼科斯编辑的版本只有一个资料来源,那就是阿佩里孔买下的被虫蛀而受损的并在错漏百出的情况下就被出版的版本(Edition A1),那么,安德罗尼科斯的版本(Edition A2)又有什么优越之处和权威之处呢?因为,如果安德罗尼科斯没有其他的版本来源与阿佩里孔的版本进行核对的话,那么,他的版本至多也只能算是依据受损的不完整的Edition A1而进行的个人遐想或明显书写错误的纠正而已,也就是Edition A2与Edition A1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一个可能性就是,漫步学派内部不可能对亚里士多德的每个著作只有一个手抄本⑥。尼尔森(Nielsen)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学友罗德岛的欧德慕斯(Eudemus of Rhodes)在亚里士多德死后带着很多不少的学园作品离开雅典返回罗德岛。欧德慕斯不仅向特奥弗拉斯特就《物理学》第五卷中的一段正确读法讨教过,而且他还藏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编辑了《欧德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另外,罗德岛在公元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曾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研习的重镇之一,从这几点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作品不可能在特奥弗拉斯特死后便在雅典销声匿迹了,斯特拉波和普鲁塔克的记载不足以能证明亚里士多德著作或至少是伦理著作失传200年的说法⑦。
事实上,在斯多白乌斯(Stobaeus:生活公元5世纪)编撰的有关古典哲学流派概略或纲要《物理学与伦理学摘录》(Eclogae)第II卷第116-152节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有关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漫步学派的伦理学的概览(summary),这个总览的作者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中期的一位名叫狄杜牧斯(Arius Didymus: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斯多亚主义者。他更多地用斯多亚学派的伦理语言来描述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的伦理思想。我们如何解释狄杜牧斯的这种作法呢?对这一现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要么狄杜牧斯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并不十分了解,而只是随意地选用了斯多亚学派惯用的语词来解释漫步学派的伦理学(mindless eclecticism);要么他其实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谙熟于心,只是为了适应当时更为流行的哲学语词来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已⑧。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已经熟被人知了么?根据历史记载,最早的有关《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引用是在西塞罗的《论善恶的目的》(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的第五卷第12章中,背景是讨论漫步学派对于至善(supreme good)的观点。西塞罗对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引用说明斯多亚学派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早有了解,他认为斯多亚学派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术语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给他披上一层新的衣服而已,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冲突只是在于论证方式。西塞罗的这种调和论主要来源于一位叫做安提奥胡斯(Antiochus of Ascalon:前125-前68年)的柏拉图学园派主义者。他反对中期柏拉图学园的创立者阿尔则西劳斯(Arcesilaus:前315-前240年)的怀疑论立场⑨,而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斯多亚伦理学在有关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严格的分歧。他认为特奥弗拉斯特作为亚里士多德漫步学园的第一任继承者虽然反对幸福完全在智者的能力掌控之下,强调外在的厄运或好运可以毁坏或提升幸福,但是这并不表示,斯多亚学派伦理学就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完全相悖。相反,西塞罗与安提奥胡斯在公元前79年同时在雅典留学,西塞罗将他视为“统一派或调和派”(unitarianism)的代表。无论如何,西塞罗和狄蒂姆斯的叙述证实了斯多亚学派在其早期就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有所涉猎和研究。
三、芝诺与亚里士多德论幸福
1.桑德巴赫(Sandbach)对朗(Long)的批判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幸福观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影响么?斯多亚主义的幸福观是源自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么?按照桑德巴赫(F.H.Sandbach)与安东尼(Kenny Anthony)的看法,任何尝试证明亚里士多德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想法都是个人的凭空想象,并且注定会失败。与之相反的是,朗(A.A.Long)在“亚里士多德对斯多亚学派的遗产”一文中列举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深远影响⑫。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影响的第一个方面是有关外在的善事物与德性以及幸福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虽然不能与外在的善等同(比如,财富、出身优越、名声或荣誉等),而是幸福更在于人的内在德性,但是,人需要具有一些外在的善来完成某些德性行动(比如慷慨的行动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富),具备外在的善可以成就更为完满的幸福,完满的幸福需要具有外在的善⑬。而斯多亚学派则认为,外在的善根本不是真正的善,而是只有那些伦理上的善,即德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善。幸福与德性具有绝对性,幸福并不直接与外在的善相关,而只是与使我们在外在的善事物中做出选择的德性相关。尽管外在的善对于某些德性来说提供了一个使其运作的条件,但是,拥有外在的善并不必然是德性的条件,因为在伦理之外并没有什么善。那些自然的善对于一个志在度高尚的道德生活的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理由是,只有美德或德性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伦理选择的善(the good of the ethical choice)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我们的伦理选择是符合理性的,它的价值是源自于建基在神性的存在秩序(divine order of the being)之上的善⑭。朗(A.A.Long)认为,在有关外在的善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斯多亚伦理学提供了一个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案。但是,桑德巴赫(Sandbach)强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很多关于什么才是构成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的讨论⑮。而且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前396-前314)就认为,幸福生活虽然主要取决于德性,但是如若没有外在的善,人也很难达到完满的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关幸福的观点是对前人的观点的改进,而斯多亚伦理学则开始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论点,即唯有德性才与幸福相关,而外在的善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幸福。根据朗(Long)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有关什么是德性行动的条件以及一个人如何成为具有德性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一个符合德性的行动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知道自己所做的;(2)选择这个行动,且为了行动自身的原因而选择;(3)出于一种坚固而不会改变的习性。Long认为,斯多亚伦理学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上述三个条件。Sandbach对上述三个方面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对于这三个条件的理解并不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一致。首先芝诺认为,拥有(明知性)就是拥有 φρóνησι(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而拥有φρóνησι就是拥有诸种德性。但是,这明显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因为一个人具有语法的知识,就能够进行拼写,但一个人知道如何慷慨,但并不等于他就一定具有慷慨的德性。而对于προαιρομενο(选择)来说,单从其词源学上(προ:在…之前,αιρομενο,决定,择取)就能看出这是指在不同的可能性面前择取自己想要的,即这是一种明辨后的行动,而不需要单独而特别地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而第三种德性习性的非变易性则更是源自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之独创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快乐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EN X中将快乐定义为“使实现活动变为完整性的东西,不是作为一种内在的伦理品性,而是作为一种随附的目的来起作用的,就像美丽完善着青春年华”⑰。但是,桑德巴赫(Sandbach)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并未将快乐视为目的,而是达到了目的之后的结果。虽然二者具有某种相似性,但这并不表示斯多亚伦理学有关快乐的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桑德巴赫(Sandbach)虽然也接受朗(A.A.Long)提出的斯多亚伦理学在上述三个方面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吻合或相对应,但是桑德巴赫却否认这种吻合就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实质性的深远影响。桑德巴赫对朗的反驳主要是依据在二者之间的三种吻合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早已有过相关的讨论,比如很多吻合的术语早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就出现过,或者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过关于什么才是组成幸福的本质性要素的讨论(ENI 9.1098b23)。但是,只是通过一些与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哲学术语之吻合是否就能充分地证明这些术语就是源自柏拉图传统?如果这种表面术语吻合所表达的概念在实际的问题框架中并不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吻合也并不能作为一个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术语背后的伦理学源自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柏拉图传统。
2.芝诺论幸福与德性
虽然桑德巴赫(Sanbach)对朗(Long)所主张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影响的三个方面一一加以驳斥,但是,他的驳斥并非完全中肯适宜,我的观点是,虽然我们并不具有直接的文本证据来证明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早期的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且只是依靠一些漫步学派伦理学与斯多亚伦理学之间的术语重合或本质性的命题对应很难证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哲学传统影响另一种的方式,即把早期斯多亚学派的某些伦理观点视作是对漫步学派伦理学内部所包含的一些未解问题或张力的回应⑱。这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张力就是有关幸福作为自足而完整的至善与外在的和身体的善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对于德性行动与幸福的本质性理解方面。在EN I 7.1097b20-21,幸福被界定为“完善而自足的,因为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达到的最后目的。”幸福是完满的,因为人所选择的一切都是为了幸福这个最后目的,而幸福自身不再为任何其他目的。它又是自足的,因为它足以使整个生活变得有价值⑲。这种张力就表现在亚里士多德试图保全如下两种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德性才是幸福的主要组成因素;另一方面又强调外在的不幸会损毁幸福,或缺乏外在的善会减少幸福(EN 1099b2-5),而拥有外在的或身体的善会增加幸福。芝诺否定任何外在的或身体的善是真正的善,而只有伦理上的善或德性才是真正的善,芝诺试图通过确立德性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仍然在德性的至高地位与外在的和身体的善之间有所徘徊不定,那么芝诺就是斩钉截铁地“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即外在的善(财富、名誉、权利、朋友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幸福的本质性组成部分,它们只是具有某种价值的东西,而只有德性才是构成幸福的本质性要素。显然,芝诺对幸福的这种解读是最小化的解读(见注释20),但是,问题是,斯多亚伦理学如何来解释这种绝对而突兀的主张?如果我们理解了芝诺对人的幸福和德性的本质定义,也许这种最小化的解读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那么决绝或不近乎人情了。
虽然根据拉尔修的记载,芝诺曾经写过很多著作,但是,不幸的是,无一作品被保留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拉尔修,西塞罗等人的记载而重构他的伦理思想。芝诺将幸福界定为“符合自然地生活”⑳,并按此原则而将人的行为或行动分为符合自然的适宜行动和德性的完美行动。按照芝诺的看法,那些符合自然的事物值得人们欲求或选择,相反那些不符合自然的东西就应该被舍弃。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符合自然的原则而对事物进行选择或舍弃的时候,他也就具有了能够进行符合自然的适宜行动了,但是,这仍然还没有达到德性的完美行动,因为符合德性的完美行动需要行动者具备几个条件:为了正确的理性、出于不可变易的习性、向着一个固定的自为目的,就像一个有智慧的人计划他的生活一样。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行动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获得一定的外在的善而值得称道,而是因为这些行动本身就是具有德性的,是自为的目的。所以一个符合自然的适宜行动在外表上与德性的完美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前者在本质上并不能与后者等同,因为后者需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正好与亚里士多德在EN II 4.1105a31-35所列举的三个条件吻合。而朗(Long)也注意到,斯多亚学派在符合自然的适宜行动与德性的完美行动之间所做出的区分与亚里士多德在与德性行动相合的行动(acts in accord with the virtues)与源自德性的行动(acts that flow from the virtues)之间的区分相对应㉑,朗就将这种对应理解为早期斯多亚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回应。尽管桑德巴赫反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但是朗始终坚持早期斯多亚伦理学不可能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桑德巴赫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伦理学在希腊化时期并不被人所知,而有关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地窖被掩埋几乎200年的文本流传故事则更加帮助桑德巴赫取消这最后的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联系。
四、结 语
对于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是对斯多亚伦理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桑德巴赫和朗的观点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对的立场,前者基于亚里士多德作品集的流传断裂和存在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伦理学传统而坚持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并未受到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尽管有些时候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术语吻合或者主题呼应的现象;而后者则认为这种术语吻合和主题呼应的现象并不能通过比亚里士多德更早的伦理学传统的存在而轻易地被否定,虽然我们并不具有任何直接的文本证据或历史记录来证明二者之间有过怎样的联系和碰撞,但是,至少可以通过一些核心的伦理命题而推论出斯多亚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内部所蕴含着的未解矛盾的一种回应或者解决的尝试。本人通过具体分析芝诺对德性和幸福的观点而发现朗和桑德巴赫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因为朗所列举的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重合或对应的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穷尽二者的关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对具体的斯多亚主义者的伦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反驳的依据本身也不能作为充足的理由。实际上,芝诺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内部的问题或张力,并尝试回应或解决。这个问题或张力就是德性和外在的善对幸福的作用或意义,如果说,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保全德性对于幸福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想保全外在的或身体的善会增加或破坏幸福而不得不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处境,那么芝诺通过否定外在的善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目的论意义上的善解决了这种模棱两可,因为真正的善只限于伦理上的善,即德性。但是,这并不否认外在的善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外在的或身体的善始终是为终极价值——幸福服务的,而构成幸福的本质性或建构性要素只能是德性。
[注 释]
① Long,A.A.(1968),“Aristotle’s Legacy to Stoic Ethics”,in:Boulletin of the Insititute of Classical Study,15,pp. 75-85. See also:Long,A.A.,Stoic Studies,Oxford Univ.Press 1996.
②Irwin,T.(1999),“Virtue,Praise and Success:Stoic Response to Aristotle”,Monist I,59-79.Sandbach,F. H.,Aristotle and the Stoics,Cambridge Univ.Press 1985.
③4See:Bobonich,Chris,Aristotle’s Ethical Treatises,in: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ed. by Richard Kraut,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12-29.
④阿佩里孔是一位富商,后成为希腊公民,是公元前1世纪有名的图书收藏家,他主要搜集那些稀少的重要的图书。
⑤斯特拉波在自己的《地理学》中这样写道:“涅琉斯不仅听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课,而且还继承了特奥弗拉斯特的图书馆,其中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因为亚里士多德不仅将自己的图书馆,也将自己的学园托付给了特奥弗拉斯特(亚里士多德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位收集书籍的人,他还教埃及国王如何组建图书馆),特奥弗拉斯特将图书馆交给了涅琉斯,他将这些书带到了斯凯普西斯(Scepsis),并传给自己的继承者。因为他们并不是哲学家,只是随便堆放起来,没有好好管理。当他们听说统治该城的阿塔里克国王正在为建立帕加马图书馆而急切地四处寻找书籍,他们就将图书藏到地窖里,这些图书就被地窖的潮湿和蛀虫所损毁,后来,涅琉斯家人就将这些图书高价卖给了特奥斯的阿佩里孔。但是,阿佩里孔更是一个图书爱好者,而不是智慧爱好者。因此,他试图制造新的抄本以修复那些受损的书籍,但是,他还没有填补缺漏,就出版了错误百出的版本。如此,那些特奥弗拉斯特之后的早期漫步学派除了少数公开作品之外,并没有什么文本可读,因此不能真正地从事哲学,只是泛泛而谈一些普遍性的东西。相反,自从那些书籍出现之后,他们的继承者算得上更好的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由于手抄本中错漏百出,所以显得大部分在似是而非地谈论哲学。罗马对此贡献很多。因为阿佩里孔一死,攻陷雅典的苏拉就立即将他的藏书运往罗马。文法家泰让尼奥(Tyrannio)——一位热爱亚里士多德的人,通过讨好图书馆长而有机会接触到这批书籍。一些书商雇用了糟糕的抄写员,他们并没有校对抄本,在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那些为了出售而被抄写的书籍上。”参:溥林: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笺释,以晚期希腊评注为线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24-30页。斯特拉波:《地理学》(Geographica),第13卷第1章第54节。
另外,普鲁塔克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苏拉(Sulla)将军将藏有亚里士多德与特奥弗拉斯特的大部分作品的特奥斯的阿佩里孔(Appelicon of Teos)的图书馆据为己有。图书馆的藏书被运到罗马后,泰让尼奥(Tyrannio)着手整理这些藏书,而罗德岛的安德若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从他那里获得了手稿,并公之于众,他制作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目录也流行起来。漫步学派的长者都是卓有成就的学问家,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与特奥夫拉斯特的作品既不是在数量上那么多,也没有被正确地抄写下来,因为内琉斯的所有藏书都被转交给了那些平庸无奇的人,他们并不是哲学家(普鲁塔克,《平行传记》中的《苏拉传》第26节。Sulla 26)”。同样,拉尔修也记载了特奥弗拉斯特的遗嘱:“我把全部书卷遗赠给涅琉斯。我把花园,散步长廊以及连接花园的房屋全都遗赠给我下面提及的这些朋友,只要他们愿意总在那里共同研究文学和哲学,既然不可能所有人老是住在一起。当然,任何人都不得转让这些财产和据为己有,而只是方便使用,就像公共庙宇一样,并亲密友好地住在一起,只要恰当公正就行。”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希汉对照本),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3页。
⑥Nielsen,Karen Margreth,The Nicomachean Ethic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in:The Reception of Aristotle’s Ethics,ed. By Jon Miller,Cambridge 2012.pp.15-18.
⑦Nielsen(2012),pp.17.
⑧ See:Annas,J.,“The Hellenistic Version of Aristotle’s Ethics,”Monist,I,pp.80-97.1990.
⑨根据莱尔修(Diogenes Laërtius)的分法,柏拉图学园总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以柏拉图为首的早期学园(387BC-266BC):柏拉图离世后由斯彪西(Speusippus,347–339 BC)接管,然后是塞诺克拉特斯(Xenocrates,339–314 BC)接着是珀来莫( Polemo,314–269 BC)和克拉特斯(Crates,c.269–266 BC)。(2)以阿尔采西劳斯(Arcesilaus)为首的中期柏拉图学园(266BC-160BC);(3) 以吕西德斯(Lacydes) 为首的第三时期(160BC-84BC)。
⑩亚里士多德用了四个有名的论证来证明最好的或最完美的生活就是灵魂的符合理智德性—智慧的沉思生活,这四个论证是:标准论证(Criteria-argument,EN X 7.1177a19-b26);本有论证 (oikeion-argument,X 7.1178a4-8);神性论证(argument from divinity,X 8.1178b7-32);与神具有最大的友谊论证(theophilestatos argument X 9.1179a22-32)。这四个论证足以证明沉思智慧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首要幸福(primary Eudaimonia)。
⑪对于次好的幸福也有两种解读,排他性的解读认为政治的德性生活只是在一种引申的(derivative sense)意义上是幸福,因为它缺乏沉思;而包容性的解读则认为政治的德性生活在其自身也具有幸福特性,只不过是在一种比沉思较弱的意义上来说。
⑫ Long,A.A.,“Aristotle’s Legacy to Stoic Ethic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y,15,pp.72-85.
⑬ EN X 9.1178b33-1179a33;EN I 9,1099a31-1099b8.
⑮EN I 9.1098b23. 见:Sandbach,F.H.,Aristotle and the Stoics,Cambriadge 1985.pp.24-31.
⑯《理想国》444c;503c;537c.
⑰EN X 4.1174b31.
⑱ 参 :Irwin,T.,“Virtue,Praise and Success:Stoic Response to Aristotle,”Monist,I,pp.59-79.
⑲对于这种幸福的界定可以有不同的解读:(1)最大化解读:幸福不需要任何其他额外的善,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外在的善(比如财富、朋友、社会地位)、身体的善(健康、力量)和灵魂的善(德性)。(2)最小化解读:幸福与非伦理的善(外在的善和身体的善)并没有什么直接相关性,真正的善仅仅限于德性。(3)有限性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外在和身体的善,我们就可以过一种自足的完善的幸福生活,任何其他的善并不会增加幸福。因为幸福并不在于拥有这些善,而是在于以适宜的方式或德性的方式寻找并利用这些善。参:Nielsen(2012),pp.21f.
⑳ 拉 尔 修 (2010 年),VII 87;Cicero,On Moral Ends,trans. R. Woolf,commentary J. Ann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㉑Long (1968),pp.77.
田书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SKXJS201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