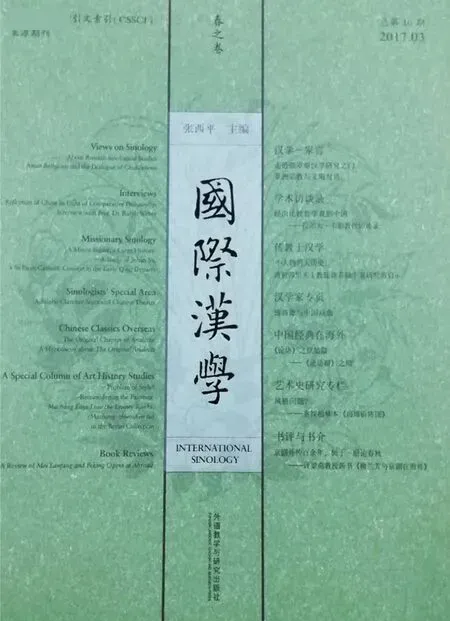筚路蓝缕译诗路—译诗名家施颖洲
□
施颖洲是菲华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长期担任报社总编,耄耋之年犹笔耕不辍,钟情译诗,译有《世界诗选》与《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作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与翻译家,他致力于菲华文艺的繁荣和中外诗歌的译介,功不可没。
一、实至而名归
施颖洲1919年生于福建晋江,3岁时随父母移居菲律宾。他自幼喜爱文学,从上小学起就沉湎于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常被选为佳作而展出于学校的展览橱窗。1933年,年仅14岁的他就在《民众》周刊发表了文章,且是“连成年作家也不易驾驭好的投枪匕首般的杂文”①李君哲:《海外华文文学札记》,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1935年,他开始在《华侨商报》副刊发表诗歌。1937年,他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在《公理报》的周刊《文艺先锋》上刊出,每周一首。1945年马尼拉光复后,任《新时代》英文报总编辑,1946年任《中正日报》总编辑,1949年《中正日报》与《大华日报》合并为《大中华日报》,他仍任总编辑。1950年当选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51年始主编《文联》季刊。1963年被菲政府教育部长罗细士誉为“模范华侨”,被司法部长誉为“现代孔子”—赞誉似已登峰造极。1964年获“国际桂冠诗人协会”所授“诗人—黎刹学家奖”,1966年再获“国际桂冠诗人协会”授予的“诗人—翻译家奖”。1968年、1970年两次获“中正文化奖金”文学奖。1973年任《联合日报》总编辑。1982年组织“菲华文艺协会”,主编会刊《菲华文艺》。1985年当选“亚洲华文作家协会”总会副会长。多次受邀赴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澳门、美国等地演讲,还长期担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菲分会”名誉会长。
施颖洲被称为“菲华文坛上资深的老报人、老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艺活动家”②吴奕锜:《回望与寻找》,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54页。,可谓实至名归。自1945年马尼拉光复时任《新时代》英文报总编辑始,先后任《中正日报》《大中华日报》《联合日报》等报总编辑,凡六十余年,为 “世界报业史上任期最久的总编辑”③施颖洲:《文学之旅》,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刊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为《话梦录》专栏撰稿十九年,言逾五百万;八十岁高龄犹辛勤耕耘,每日一篇随笔见报,无愧“老报人”“老作家”之称。自十六岁起陆续发表新诗与传统诗,翻译英诗及唐诗,先后出版《世界名诗选译》《现代名诗选译》《古典名诗选译》《莎翁声籁》《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等,无愧“诗人”“翻译家”之谓。他先后主编《文联》《菲华文艺》等文学刊物,编选各种诗歌散文小说等文集,还筹备“世界诗人大会”,成立“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联合会”“菲华文艺协会”等文艺组织,倡办“文艺讲习会”,培养造就菲华文学艺术一代新人。他为菲华文艺的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无愧“文艺活动家”之誉。
《菲律宾华文报史稿》谈到施颖洲,评价十分中肯公允:
有人称他是菲华文坛泰斗,严格来说,就作品的质量而论,有商榷的余地,但就他长期从事文艺活动和对文艺事业的热爱来说,则是无人能及的。他已届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精神可嘉。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26本书,有中国大陆出版的,有香港出版的,有台湾出版的,林林总总,著作等身,堪称文坛老将。①赵振祥等:《菲律宾华文报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二、译诗求尽善
施颖洲二十岁之前就萌生了翻译诗歌的想法,有了汉译“世界诗选”并英译“中国诗选”的宏伟计划。在完成《世界名诗选译》《现代名诗选译》《古典名诗选译》《莎翁声籁》等书之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开始英译中国古典诗词。他发觉中诗英译与英诗中译并无二致。他翻译的《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在亚太地区广为流传,享有极高的赞誉。其中,林启祥教授赞誉他的翻译“完美无疵,功力炉火纯青,成就远在前人之上。最难得的,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又能再现原诗的意境、神韵,堪称传神的佳译”。②林启祥:《林启祥创作集》,马尼拉:菲华文艺协会,2008年,第179页。诗人罗门说:
施先生中外文的造诣与学识均佳,而兼有诗人的气质与文人修养,持有一支认真、稳健、精确,与典丽的译笔,能自如与有把握地将那些辉煌神妙的诗境,全然展放出来,保存它们的精美与不灭的光辉,使这部译诗显得完美与杰出。③施颖洲:《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第221页。
诗人张英敏甚至推崇他“确实前无古人,且亦可能后无来者”④同上。。
施译汉诗能享有极高的赞誉,是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首先是译者雄厚的语言功底。施颖洲生活在中英双语环境,从小喜爱古典文学,并大量阅读新文艺书刊,嗜书又苦读造就了他中英文翻译基础。其次是他对译诗孜孜追求。他“一步一个脚印,寒暑易节,从不间断,殚精竭虑,千锤百炼,反复筛选,精益求精,‘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终于‘将诗人的灵魂注入翻译家的躯体’,使他的译诗达致炉火纯青之境地”。⑤潘亚暾:《〈施颖洲文选〉序》,《华文文学》1993年第1期,第68页。此外,施颖洲在多年的译诗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译诗理论与译诗标准,在《译诗理论与实践》《谈译诗》《译诗的艺术》《译诗抒怀》等文章中曾有系统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些理论阐述,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探讨上,而是具体化为自己翻译实践中的操作规范,从而树立起自己独特的翻译观和翻译风格,赢得了国内外翻译界人士的好评。可以说,正是良好的翻译理论修养造就了施颖洲不同一般的翻译才能并且获得了可喜的成功。”⑥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三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在《世界诗选》的“自序”里,施颖洲简洁地表述了自己的译诗理论:
我的译诗标准只有一个:忠实。
……译诗各方面都要完全忠实于原作。……
一首忠实、理想的译诗,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一)译诗应该忠实地译出原诗字句全部的意思,是及格的意译,也是及格的直译;
(二)译诗应像原诗一样是一首好诗,保持原诗的种种特点。
品评译诗,首先应该将它拿来与原诗对读,看它有没有将原诗的全部意思忠实地译出;其次,便看它是不是好诗,像原诗一样的好诗。通过两重考验,才是好的译诗。
……
译诗必须力求:(一)字字确切,句句忠实,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是及格的直译,也是及格的意译。(二)节奏优美,犹如原诗。例如,用英诗抑扬五音节格律译中文七言。(三)音韵悦人如原诗。例如,依照原诗押韵的方式。(四)保持笔法,风格,情调,意境等等。(五)再现原诗境界、神韵,好像原诗一样是一首好诗。①施颖洲:《世界诗选·自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翻译的本质就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语义与风格上都要对等,因此,忠实是翻译的必然要求。没有忠实则无以言翻译。把忠实作为翻译的标准乃至唯一标准,都是正确无比的。然而,忠实作为翻译的唯一标准,体现在翻译实践中,还存在着方向与层面问题,即忠实于形式还是忠实于内容的问题,以及在字词层面、句子层面还是语篇层面忠实的问题。施颖洲在谈到“标准只有一个”之后又提出了“两个条件”“五个力求”,也是大标准的细化问题。
三、《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
书中收录施译诗词120首,体裁上有绝句也有律诗,还有歌行体与词曲。其中唐代诗词占绝大部分,有97首,五代5首,宋代16首,另外收晋代、元代各1首。选诗涵盖唐代诗人42位,名家皆有多首入选,如李白15首、王维10首、杜甫8首、杜牧6首、李商隐6首、白居易5首。宋代16首,包括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范仲淹、晏殊、欧阳修、黄庭坚、秦观、陈与义等10位。选诗多是读者常见的耳熟能详的名诗,也有几首稍显偏僻。
在《谈译诗》一文中,施颖洲曾谈到了《世界名诗选译》一书是“怎样选诗”的。诗入选要过“三关”:“第一关,必须是名诗,……是大诗人的代表作或名作……第二关,必须是译者喜欢的好诗。名诗当然是好诗,但有的名诗我却不认为好诗,也就不译。……第三关,必须是译者有把握译出的。”②《文学之旅》,第46页。
当然,汉诗英译时的选诗,未必照搬汉译世界名诗的标准,但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从第二关“译者喜欢”看,选诗带有译者自己的判断乃至好恶。从第三关“有把握译出”看,为了保证译诗质量,好诗却难译的不选也是确定的。晋代陶潜的《饮酒》与元代马致远的《秋思》超出唐诗宋词范围,则以“另一章”的标签入选。从入选诗词可以看出,《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这本英译中诗选集,是译者从自己翻译的古典诗词中选择自己欣赏的翻译佳作。它不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宋诗选注》等书那样过于注重选诗的覆盖面、代表性、经典程度等。即使选译汉诗志在向外国读者呈现唐诗宋词精华,译者选诗仍可有自己的判断与标准。
四、诗词英译的得失
1.施译的特色
施颖洲英译汉诗的突出特点是,以英文格律诗来译汉语格律诗,注重节奏与押韵,并努力保持原诗的形式。
对于保持汉诗节奏,施颖洲基于自己多年的译诗经验认为:“用英文抑扬四音步译中文五言诗,抑扬五音步译中文七言,最为适合,恰到好处。”③《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第21页。因为“英文的前置词(preposition)与冠词(article)在中文是通常被省略的。把汉诗翻成英诗的时候,不得不把这些补上。由是他很巧妙地腾出三个空位,把原有的五音变为八音,七音变为十音。这是他的发现和创举。”④林启祥:《知不可为而为》,《马尼拉联合日报》副刊《菲华文艺》,2007年4月13日。
施译还力求保持原诗的押韵方式。“《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一百二十首,首首照原诗押韵。例如:王翰七绝《凉州词》,押韵方式是AABA,第一行、第二行及第四行押一韵。英译也是照原诗位置三行押韵。”⑤《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第21页。施颖洲在《自序》中这样介绍道。
忠实于原诗的形式,除依照原诗押韵外,还体现在英译模仿汉诗的对仗、倒装等,如译“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句为“In alien country,hairs turn white; On native land, mountains look green”①同上,第108—109页。;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句为“Fame—by my writings I have won? Rank—now old and sick, I’m aground”②同上,第89页。。甚至碰到汉诗名词罗列意象叠加的,英译也有意舍弃完整句子,如“野渡无人舟自横”句译为“Wild ferry.No man.A boat swings across”,而没有译成“At a deserted ferry, a boat swings across”。③同上,第112页。
2.忠实的方向与层面
“译诗标准只有一个:忠实。……各方面都要完全忠实于原作。”这话本身驳无可驳。程镇球曾说:“我们认为翻译标准或翻译原则归纳为从内容到风格都忠实于原文就够了。”④程镇球:《翻译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62页。钱钟书认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⑤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1页。翻译的标准,用“忠实”一个词概括足矣,但详细分解,存在着忠实于内容还是忠实于形式的区别,就忠实于内容而言,还存在着字词、句义和语篇等不同层面。
例如,陶渊明《饮酒》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句的翻译:
施颖洲译:No noise of coach or horse sounds here.
许渊冲译:There’s noise of wheels and hoofs,but I hear not.
许渊冲在《谈陶诗英译》一文中详细对比了这两种译法:
比较一下两种译文,可以说施译的“无车马喧”,译得“字字精确”。许译把“车”译成wheels(车轮),把“马”译成hoofs(马蹄),是不是“避重就轻,爱惜思力”呢?我的看法是:车轮马蹄更重动态,施译相形之下,反倒更注重静态。所以我不是“避重就轻”,反倒是避易就难,再“思”而译的。这句诗最重要的是个“无”字,“无”有两种解释:一是客观上真没有“车马喧”,一是主观上听不见“车马喧”。⑥许渊冲:《谈陶诗英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6期,第57页。
从接下来的两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来看,陶渊明“结庐”并非偏僻之地,而是“在人境”,确有“车马喧”,只是他听而不闻而已。
这种限于字词层面“字字精确”,从语篇层面考察时,其不妥之处就不难看出了。
3.译诗的内容与形式
诗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节奏与韵式等形式构成了诗的风格与神韵,因此译诗要在正确达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模拟出原诗的形式。
由于汉英的节奏与声调平仄有关,而英语的节奏与语音的轻重有关,语言差异使得汉诗英译无法将汉语节奏平行移植,用英语音步来勉强对应汉诗的音组。施译用英语抑扬四音步译汉语五言诗,抑扬五音步译汉语七言诗。抑扬四音步即每行八音节,抑扬五音步即每行十音节,事先规定了每行音节数,回旋余地少,时常遇到长句需压缩和短句需伸长的勉强情形。
汉英语言差异也决定了汉诗英译在保持韵式上要相对难一些。“用拥有大量同音、近音字的汉语模拟任何语言中的种种韵式都不难做到;反之,用英语等西方语言模拟汉语诗的一韵到底就难乎其难了。”⑦傅浩:《说诗解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一首诗有多种诗意组成部分,如诗的长短、性质、意象多寡、语言的密度、运用的诗歌技巧等,韵式只是其一,而且,“语言密度愈高,意象、典故愈多的诗,脚韵所占的诗意组成‘百分比’就愈小”,⑧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却时常成了左右诗意的东西。译者为了押韵可能要搜肠刮肚,选用与诗意不协调的俚语或冷僻古字而致以词害意,有时会为韵脚而倒装句子,使译诗读起来佶屈聱牙,失去了自然顺畅。
孔慧怡在《谈中诗英译与翻译批评》一文里说:
如果译者以不懂中文的人为读者对象,他注重的是译文究竟算不算得上是诗,而不是原文中某一词某一字是否规规矩矩地搬到译文里;反过来说,如果译者小心翼翼地按“规矩”行事:原文有脚韵,译文必须有脚韵;原文有某一个字,译文必须有其对等词,而且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译者注重的是把中国读者所知的中国诗学规则以英文重现,而不是译诗作为一首“诗”给英语读者的印象。①孔慧怡:《谈中诗英译与翻译批评》,《外国语》1991年第5期,第22—23页。
就是说,把中国古典诗词介绍到外国,给不懂中文的人看,在他们眼里,像不像一首英文诗或许比是否传递出诗词形式更重要。
译诗若能传递出原诗的诗意,又模拟出原诗的格律形式,戴着脚镣跳舞而舞得飘逸轻盈,实属难能可贵。
4.理想的译诗
“理想的译诗,应该字字确切,句句忠实,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不能画蛇添足,也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马虎译字修辞。”②《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第17页。施颖洲提出的译诗理想是完美无瑕的,以此衡量自己的译诗,可谓高标准,以此评价他人,则有苛刻之嫌。有此完美的译诗理想,译诗并不能因之而完美。如施颖洲引用作为“译句忠实,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例子的一句:
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结句:
天上人间!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of Men!③同上,第19页。
“天上人间”句有不同解说。“有的说指的是从前像在天上,而今落降人间……也有人认为是天差地远,天地之隔的。我们结合上下文来看,天上人间,实际上是天人之隔,……是永久相隔的意思。”④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第11—12页。英译只是“天上”与“人间”的并列,并没有译出“天差地远”之意。如果译“肝胆胡越”一词,就当译出由近如肝胆变成远如胡越的意思来,而不能简单地将四物并列。
实际上,译诗的理想越完美,实现起来越难。既要正确理解原诗,把握诗意妙处,又要用另一语言恰当而充分地表达出来;既要在听觉上模拟原诗的节奏与韵律,又要在视觉上体现原诗的匀称齐整之美。面面俱到即面面受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削足适履几乎不可避免。译诗尤其是格律诗,可以说是“削足适履”的艺术,一路趋向完美却又处处留着遗憾。孔慧怡曾得出一个相当客观的结论:
在我作为《译丛》主编这十年里,看了近千首英译中诗,翻译方法形形色色,投稿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现象是最明显不过的:英语没有达到母语水平的人,尝试押韵而成功的例子一个也没有,而即使英语是母语的人所作的尝试,也是失败远远多于成功的。⑤孔慧怡:《译诗应否用韵的几点考虑》,《外国语》1997年第4期,第43页。
言译诗“一字不易”“天衣无缝”,除了极少数的妙手偶得之外,多是过甚其词的谬赞。
5.得失寸心知
《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书前书后都罗列着海外名家赞语。杨德豫在《绝妙好译》中称赞施译李白《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施先生译文:
At dawn I left Po-ti, high in clouds gay;
Sailed thousand li to Kiang-ling in a day.
As apes yelled ceaselessly on either shore,
The skiff slid myriad mount ranges away!
原诗每句七言,译诗每行抑扬格五音步。原诗第一、第二、四行押韵,译诗同样。洋溢于原诗的那种清爽愉悦、兴会飙举的心情,在译诗中同样表达得淋漓尽致。细心的读者若将两诗的词语逐一对照,便不难发现:原诗的每一个字在译诗中都有着落,译诗的每一个字在原诗中都有来历。真是铢两悉称,毫厘不爽!
诗人导演孙瑜翻译这一首诗时,曾解释说,“当诗人由死刑减为放逐时,沿长江经三峡到了白帝城,忽然特赦令来了,喜出望外地就买棹回江陵了”。①林健民:《林健民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这说明“一日还”不是指来去双程,但确实有“回江陵”的含义在,用“sail…to”只是“航行到”,并没有译出“还”字来。可见,说“原诗的每一个字在译诗中都有着落”还是太绝对了。
序言中的美言与信函中的称赞都是可以理解的。要公正准确地评论译诗的优劣得失的确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涉及每个词译得是否到位,对每个诗行和每一句子的理解与表达是否妥帖与恰如其分,而且还有整体效果和人言人殊的问题等等。”②黄杲炘:《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然而,译诗又并非没有标准而人言人殊,所以不能信口褒贬。
施颖洲在《自序》里说“字字确切,句句忠实”,“节奏优美如同原诗”“音韵悦人媲美原诗”,“终于为英译诗词走出一条崭新道路”,“我深信,《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将为译诗艺术翻开划时代的一页”。然而,译诗之优劣并不取决于译者的自信与否,就如:
李光地《榕树语录》正编卷三○尝评杜甫:“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杜甫于诗亦“怀盈自足”,不似陆机之“遗恨终篇”,然二家文章正不以此为优劣也。③《管锥编》,第1205页。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于2016年8月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第93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谭凯(Nicolas Tackett)是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对于10世纪(唐宋时期)中国的贵族——数个世纪以来曾统领中国的“门阀大族”的完全消亡迷惑不解。本专著作者采用崭新的数字化方法来分析庞大的来源文献,试图揭示这个谜团的谜底。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数千份近几十年来挖掘出来的墓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认真研究过,同时充分利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阐释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这些分析还被辅之以大量采自于墓志铭、简牍与诗歌的逸事,以重现生活于千年之前的男女。该著认为,唐朝贵族适应7—8世纪社会、经济与制度方面变迁的能力要比此前所估计的强得多。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洗劫首都长安后的三十年动荡期,贵族大量被杀,其政治影响力才得以终结。本著尚未见有中译本出版。(秋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