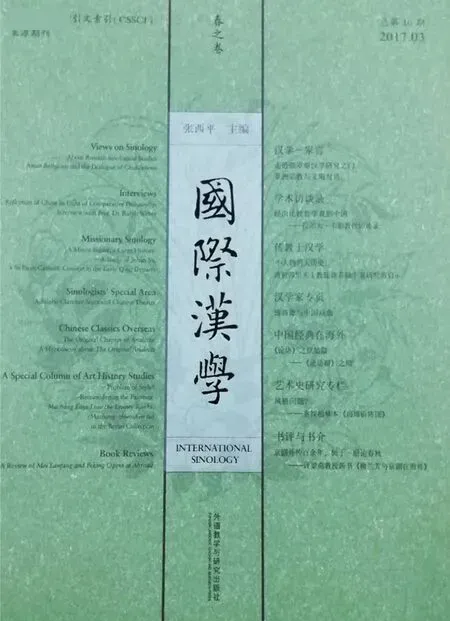亚洲宗教与文明对话
□
亚洲文明最为典型的特点就体现在亚洲是世界宗教的摇篮,以亚洲宗教原创性和多样性为代表的宗教精神探求是亚洲价值之源,亦是东方智慧的奥妙之所在。从精神意义上探索,亚洲宗教理解上接“天道”;从自然意义上体悟,亚洲宗教流传则下连“水源”;其世界观念且以人为本,相信上下打通、神人感应。在亚洲各种宗教中,虽然大多涉及对“天”之仰望和对“天道”的思索,如中国儒教“敬天”所论之“上天”“皇天上帝”,道教所言“天之神道”,印度教所信奉的宇宙本原及最高主宰“梵天”,佛教所向往的“西天净土”等,形成“民所瞻仰”之“天”,却没有西方形上思维那种绝对的“二元分殊”,而主张“究天人之际”,相信有“通贯天人”之道。因此,亚洲没有朝西方宗教哲学那种逻辑性、思辨性之“形而上学”的方向发展,但展示出其“天人合一”“梵我同一”的模糊性、神秘性的“整体哲学”,以这种独特思维风格与西方思想鲜明对照,各有千秋。亚洲宗教虽然意识到了终极实在“道可道,非常道”的绝对另一体之彼岸性,却坚持“问天”“言道”,不可为而为之、不能言而试之,于是就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迥异的“人道”与“天道”、“人文”与“天文”、“人学”与“天学”的呼应及联结。这种东方思想传统的开拓及发展,遂使亚洲虽然呈现出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宗教多样性,却仍能多元求同,保持一种难以言尽、却可心悟的和合、统一、整体之状。由此观之,亚洲宗教思想的对话和沟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积极活跃,也都更有成效。各教之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复杂关联不能截然分离和撇清。
在古希腊罗马传统中,其哲学思维讲究一种“物性”,追求其“固体”之本原,凸显为“物之哲学”,故其形成的思维逻辑颇有“阳刚”之气,原则性强,但应变能力不够,因此训练出其逻辑、思辨的方法以供实用。与之对比,亚洲思想在其自然关联上则主张一种“水流”,突出其变化、发展,且任运而行、随遇而安,显露为“水之哲学”,其思考方式体现“阴柔”之美。老子说“上善若水”,而水乃生命之源,人类许多文明来源都有“母亲河”之说,这在亚洲最为典型。对比东西方,亚洲思想之源有着更多的宗教情怀,更加突出其灵性特色。
正是这种亚洲宗教传统,对人类宗教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在思考这种对水与文明、与宗教的关联时,西方思想家孔汉思(Hans Küng)曾与华裔哲学家秦家懿对话,由此提出了“三大宗教河系”理论,他看到了人类主要宗教的起源与流传都与一些大河流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从中得以体悟人类生命及灵性的意义。
按照孔汉思的描述,第一大宗教河系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即古代两河流域产生了被称为“亚伯拉罕传统”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犹太教最初之源的游牧部落的雨神崇拜演进为绝对一神的信仰,形成与当地多种宗教的碰撞或融合。犹太教既是迄今犹存的最古老的绝对一神教,也是为人类奉献了“立约”文化精神的宗教。基督教虽然强调神圣与世俗的绝对分离,却发展出“父”“子”“灵”神圣“三位一体”和“知”“信”“行”实践“三位一体”的整体观,从而实际在根本上已动摇了其主张的“二元分殊”。伊斯兰教则以其抽象、无形的神圣观和洁净、神秘的灵修观而独步世界,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福乐智慧”。其实在两河流域相关地区还产生了主张二元神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后的摩尼教,以善恶二元对立来倡导“光明”所象征的“善思”“善言”和“善行”。而基督教的东传也曾深受这种波斯古教的影响,最早来华的基督教(史称景教)即与此相关。第二大宗教河系即恒河流域,早期也包括今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产生了吠陀宗教、古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这些代表印度文明的神秘型宗教本身也是一种多元共构的存在,各教之间多有联系,教内各派更是很难加以清楚区分,其神秘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明显展示,尤其是有着印度文化极为独特的沉思默想,并且发展出动静紧密结合的修行实践,其“思”有空无、因明等论,其“修”则有瑜伽、禅修等为,以此形成了印度文明的“奥义”及其典型特色。而且,印度教也与前述宗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整体观,包括“梵天”“湿婆”“毗湿奴”之“三神一体”,以及“天界”“空界”“地界”之“三界一体”。佛教则是以其革新之态应运而生,在“观”中达“觉”,于“思”中领“悟”,强调的是洞观人生的“觉悟”,追求的是超越生死的“涅槃”,告诫人会以其业报而对应其往世、今生与来世,决定其在世界命运迥异之“轮回”,故需“悟”透苦、集、灭、道而“觉”。若往更深层次挖掘,则可发现印度宗教的意义还在于它很早就有着沟通亚洲与欧洲文明的作用,雅利安人的迁徙,印欧文化的交织,在哲学和宗教上早就有了东西方的神秘对话及有机融合。此后,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又与印度教融合而形成了锡克教;其宗教多样性在对话、交流中的汇聚融合,彰显了聚多为一、合二为一的亚洲思维特征。第三大宗教河系即黄河、长江流域,诞生了儒教、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日本受儒道影响进而又发展出神道教。这些中国、日本宗教讲究贤者智慧,人格修行,注重心性,追求的是精神修养和灵性升华,主要以“道法自然”、修行养性来独善其身或以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兼济天下,不强调宗教礼仪规矩,重实践以彰显人格魅力,所以有着“敬神明却远之,成圣人而躬行”的特点。中国宗教中的神学底蕴并不突出,但其修身养性的人学意向则极为明显,而且人可与神相通,“士”可由贤至圣,并得以神化,其神圣并联而不绝对区分,君子既有积极作为亦可逍遥洒脱。此外,其属世而实用、模糊而神秘的信仰特色曾使基督教传统百思而不得其解,对之虽有贬损却又不得不敬佩。
如前所述,亚洲宗教的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其个性的张扬、特色的宣示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第一大宗教河系注重的主要是人—神关系,但其绝对一神观最终导致了神—人分隔的彼岸意识,尤其是基督教结合古希腊思辨传统而另辟蹊径,与其本源的亚洲传统故而渐行渐远,以致其成熟之体重返亚洲时被视为“西洋之教”;第二大宗教河系突出的主要是人—灵关系,大千世界乃其升华或堕落的轮回,灵与肉的纠结缠绵有其前因后果,人生故有其特殊缘起和缘分,以此则可解读人世的阴晴圆缺、潮起潮落,其时空的整体观念通过强调这种“永恒的轮回”而得以充分表达;第三大宗教河系则主要突出人—心关系,“头上的星空”逐渐淡去,“心中的道德律”却得以强化,其结果是追求神秘“天道”的“形上”之学逐渐转为突出人格“修炼”的“心性”之学;在其尘世交往中,儒、释、道得以通融而有“三教合一”之果,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也是模糊其多样性而能够如鱼得水、逢凶化吉。这种东方神秘主义与中国人道主义的奇特结合,使刻意于体系建设的黑格尔等认为中国无哲学,而只有一种理性不足的神秘感悟。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以基督教为圭臬,则认为中国无宗教,儒家思想因在世俗社会的沉淀而未有旨在超越的宗教那种完美,西方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全力翻译了《四书》《五经》,却认为孔子儒家重人间之“诚”,而轻超然之“信”。这样,亚洲的精神世界对西方思想家而言似隔了一层而看不透、说不明,文化差异在哲学、宗教的理解上显露出来。
总之,这三大宗教河系产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提供了人类灵性精神的基本范畴和思维特征;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大河系都在亚洲,亚洲故而为人类文明宗教之源,此地产生了多种宗教,是世界宗教之源,而且为宗教多样性之集大成。今天世界留存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源自这三大宗教河系,所谓“西方宗教”主要也不过是作为源自亚洲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发展使然。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宗教的多样性有其辐射性,实际上已经扩大为全球影响。但其多元有合、多样共聚仍主要在亚洲文化传统中保留下来,从而达致亚洲宗教的整体圆融精神,形成亚洲宗教价值观与众不同之处。从文明类型的宗教来看,古希腊罗马曾有其悠久的宗教传统,其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一可以代表欧洲文明的宗教体系并没有流传下来,其思想内容及某些信仰特点则被来自亚洲的基督教涵容。同样,古埃及的宗教亦曾达到鼎盛,形成过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核心的非洲宗教文明,其关于死后生活的生动描述极有特色,但它仍然没有逃掉夭折的命运。值得玩味的是,这三大河系之外的古代文明宗教都未流传下来,欧洲、非洲发源的宗教发展都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中止,而与它们在历史长河的流失相对比,亚洲三大河系的诸种宗教却奇迹般地得以留存,而且迄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真实,尽管其缘由、因果可以得到各种解释,而事实就是这样鲜明。人类的这一文明传统及其精神传承在亚洲的凸显,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高度评价亚洲文明对话及其价值体系的意义。
除了原住民宗教和部分新兴宗教之外,当前世界上非常活跃的主要宗教基本上都诞生于亚洲,它们首先铸就了亚洲文明模式及其传统延续的格局,此后才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复杂发展,并且有了东方、西方宗教之别,其间亦有了不同政治及意识形态体系的复杂交织。但基于其发展根源,亚洲宗教文明可以在当今文明对话中超越东西方,起到避免或减少文明冲突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主动沟通、建设性对话,以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来化解矛盾,求得共存。中国作为亚洲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以其绵延五千多年而未中断的文明积淀,理应在这种亚洲宗教理解、文明对话中发挥积极甚至引领作用。这当然需要今日中国本身练好内功,厘清其认知思路,正视其宗教存在极其悠久的文明传统,承认其积极价值和重要社会作用;如果否认中国古今的宗教存在及其历史作用,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自身的宗教,那么就会在找寻中华文化自知、自觉时失去自我,也就失去了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开展宗教文明对话的前提及可能。实际上,亚洲文明对话中有很大比重乃宗教文明对话,亚洲各国各族大多以宗教文明为其主要文明和其文明的标志,因此,没有对宗教文化的考量,我们的文明对话则无从开展,相应的文化战略也会空洞软弱。对文明多样性的体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宗教多样性的认知,如果没有以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宗教,在亚洲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对话中就会失语,其回避宗教的文明讨论也只会被边缘化。同理,我们的文明对话旨在各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由此而达文明和谐;但如果没有对宗教的和谐相待,文明和谐则是一句空话,而我们的社会和谐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有宗教误解、宗教冲突的社会,其和谐只能是一种奢望。
今天,我们人类有着更大的志向,正以“全球化”的共在而争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而这种共建恰恰就应该是多元文化的共处。高科技处境中的“地球村”让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亲近”,多元文明频频相遇,各种文化密切交往,不同宗教亦无法回避;但这种“亲近”并不必然带来“亲密”,相反,由于曾有的距离感已不再存在,这种“亲近”会使人油然而生出“拥挤感”,近距离的“交往”也容易变为“交锋”,其结果可能会是“拥挤的地球村”,让人感到“恐惧”。当代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与博弈,使文明对话的环境更趋复杂,但这种对话、沟通、达成和解、求得共存也更为必要。人类的共存需要我们必须具有共处的智慧,而亚洲多元共处则可先行,以此来解决当下迫切需要了断的问题,为人类的对话共存提供成功经验、避免文明冲突两败俱伤的教训。在此,我们应积极推动亚洲文明对话,号召亚洲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以实现亚洲的和谐及和平。
反思亚洲宗教交往与文明对话,我们有着很多的经验教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以其广泛传播而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在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中起过关键性作用。亚洲诸多宗教并不是完全孤立、封闭的发展,而是处于不断的相遇、碰撞、摩擦、交流、互渗之中,有着“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景观。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中国化”发展,既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又充实了这些宗教自身。其实,这种“中国化”代表着双重审视,从这些世界宗教的视角乃其本土化、本色化、在地化、处境化的选择,从中国社会的视角则是这些世界宗教融入中国,成为中国宗教一员的标志,是其中国特色的彰显。此外,在今天许多亚洲国家中也都留下了这些宗教的文化印痕、信仰足迹。佛教从尼泊尔、印度传往亚洲各国,形成其南传、北传、藏传等模式;在中国兴起的佛教各派则传往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地,成为这些宗派的祖庭之所在。基督教在亚洲各地则导致其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的分殊,有着其地域化、本土化、处境化的风采。伊斯兰教则在其东传中铸就了许多亚洲国家及地域的民俗民风,形成对许多民族传统及其文化意识的熏染,使今天亚洲伊斯兰文化绚丽多姿。即使是作为民族信仰的犹太教、印度教和儒教、道教等亦超出了其本民族之限,而将其精神要素广为传播,如犹太文化的全球影响,印度教文化对中国的感染,以及儒教、道教给世界带来的惊讶和吸引人的魅力,甚至古代波斯宗教的深层次影响也在许多地区今日犹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文化,正是对这段文明传播历史的回顾、总结与弘扬。
不可否认,各宗教对抗、文明冲突也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灾祸。因为不同意文化的多样性并尝试用武力消除其差异性,相关民族之间、宗教之间、教派之间也出现了尖锐冲突和残酷战争,由此带来的痛苦和创伤造成了难以目睹的惨象、酿成了种种人间悲剧。今天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局势仍未根本改变,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民族和宗教冲突及相关纷争并没有消停,甚至还在升级、在不断恶化,由此使相关地区的人们从失望转为绝望,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其结果,国际政治因为民族宗教因素而更为敏感,人类共在秩序因各持己见而更加难建。当对话变成独白、当相互尊重变为各执己见、当善意倾听转向颐指气使,共在对话的讲台则会失去平衡,而与之相呼应的将是社会动荡再起,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种“对抗”的结局或是弱肉强食,或是两败俱伤,人民失去尊严,人类走向倒退。今天,我们依旧面对着这一严峻形势,宗教之间的贬低、竞争,宗教内外的偏见、冲突,使亚洲成为了危险的火药桶,让人们感到“地上无平安”。而要减少战争威胁,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努力,尤其是亚洲人民首当其冲,不可推责。我们已经意识到,沿“相互冲突”之路走下去,其实只有彻底毁灭一个结局。为了拯救人类、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回到“对话”之路,必须以这种“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关联来提倡对话、促成沟通、达到和解。为此,处在冲突漩涡之中的亚洲人民乃义不容辞,因首当其冲故需挺身而出,做化解矛盾、消除危机的筑桥者和修路者。
在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民族生存与国家发展的要求下,亚洲已经有过各种谈判与合作,政治家及外交家们穿梭而行、纵横捭阖,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如果这种合作与联盟仅为权宜之计,只是功利需求,那么其根基就不会稳固,其合作也难以持久。所以,这种对话与合作有必要往深层面发展,即在精神、信仰、意识、价值层面寻求理解、沟通与合作、共处。如果能减少这些文化深处的矛盾与冲突,寻得相对共识或共同之点,或许亚洲共在会更为和谐,世界局势亦会更加稳定。
不言而喻,在对精神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上,亚洲文明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尚不可能形成统一整体,故此还必须保持其多样多元之现状,而这与东方智慧所倡导的整体观并不矛盾。亚洲文化从来没有主张消灭个殊性、去除差异性的绝对整合,而乃倡导文化多样性及社会多元存在之共聚,彼此力争相互尊重、相安无事。东方文化的辩证法是有机整合、张弛有度、充满弹性的整体辩证法,其整体的内涵不是绝对“一”之空洞,而乃无限“多”之共构,因而是丰富的而不是空白的。这种亚洲文化共同体即允许“各美其美”,进而争取“美美与共”。对此,亚洲各种文明特别是其宗教文明都可提供其丰富的智慧和资源。
寻求亚洲文明的共享和共构,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都要求我们尽量找出不同文明的可能共同性,即发现大家所能公认的共同点和不同文化得以汇聚的契合点,为此还需要回避矛盾、协调分歧、防止冲突的共在之智慧。对此,根深蒂固、历史悠久的中国儒家传统能够提供一定的启迪或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中国儒家文明实质上是主张有机共构、形成和谐整体的和合文明。其“天容万物”“海纳百川”之境界源自阴阳共处的“太极”理念及其合二为一的“和合”哲学,这使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体而多元”的“中和之道”,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和合智慧”。这种观念被视为顺“天道”、有“天理”之神圣思想,而其对“多样性中的统一”之凸显亦为今天“全球化文明”的理念奠定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上“世界大同”“协和万邦”之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这种体现中华文明之本真的精神元素在儒家发展中得以系统化、体系化,成为中国社会维系其长久整合之普遍共识的文化基因。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亚洲文明有机共构,乃其重要代表和体现。以这种儒家理念作为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支撑,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坎坷、命运多蹇,有过复杂的风云变幻、社会变迁,却始终保持了这种多元通和、多元一统的精神传统,坚持其“整体性”“内涵式”和“共构型”的文化发展,倡导并高扬这种和谐共融之文明。儒家的经学是中华古代文献之整合,儒家的礼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及其规范之整合,而儒家的仁学则是其思想、道德及人伦理想之整合。代表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儒家以这种允许不同、包容差异、承认多样的圆融、共构、整体之思想精神一以贯之,在宗教境界上主张“天人合一”,在哲学追求上主张“知行合一”,在人格升华上主张“心性合一”,相信在这种整体、整合之中天人感应、神俗互动,“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故而在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上并无截然之分,而有复杂串联。其对“天”乃“信”,对“人”则“诚”,二者共构的“诚信”哲学提供了政治上必被“恭敬”或“敬畏”的“王者之道”,旨在达到“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的理想效果。由此而论,儒家的“天学”与“心学”乃有机共构,以此双翼而翱翔在天上、人间,其超越境界乃宗教意蕴的,而其现实关怀又不离世俗政治。儒家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国教”而为儒教,也正是中华整体文化中非常典型的“政教共同体”。仅此意义而言,区分儒学是宗教还是政治,并无绝对的必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宗教既为教、亦为政,彼此可分亦可合,其辩证意义即在于儒家乃追求超越自我的精神现象和献身社会治理的政治现象之共构,而这在其他亚洲宗教中也可找到许多相似之处。
多元求同、多样致和的理想境界是“人类一家”“世界大同”,这在近现代同样是诞生在亚洲的巴哈伊教中进而得到了集中体现。本来,巴哈伊教在中国社会处境中曾被译为“大同教”,但因其信者发现当时许多宗教也有“大同教”之称,如佛教、儒教,甚至相关民间宗教等,故而不得不放弃其意译而保留其音译。或许,这就是亚洲宗教及亚洲文明所共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多元中的真正之“同”在绝对意义上可能仅为一种理想境界,让人永远向往和梦寻,具有其精神动力的价值。但“和”则是可以做到的,值得去努力争取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同”的理想化为“和”的现实,形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通和关联。亚洲宗教文化在“多元化”“多样性”中对话交流,在其存在意义上争取聚同共构,这正是人类未来共存的智慧之思、可为之举。为此,儒家文明可以提供借鉴和参考、对照。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和合”哲学传统及思维定式,在传统中华思想的整合中曾起到引领作用,具有标杆意义。中华文明参与当今亚洲文明的对话,完全可以基于这种儒家思想宝库而充实自我、厚积薄发。所以,中华民族在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在推动多宗教、多文明积极对话的实践中,应该奉献并发挥这种以儒家传统为主来实现其“和谐社会”之奥秘的“和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