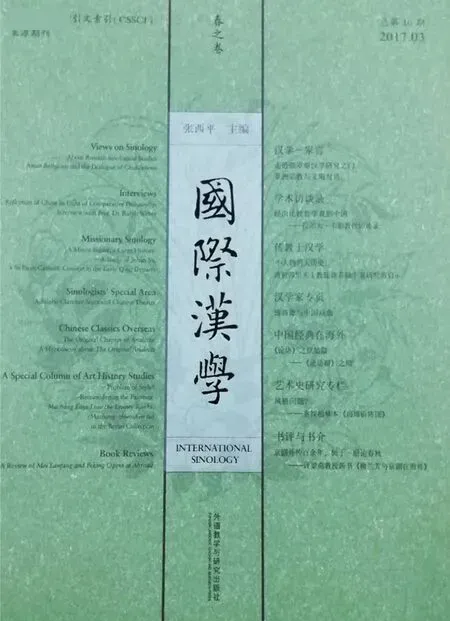施高德与中国戏曲
□
20世纪美国著名的东亚戏剧研究学者,阿道夫·克拉伦斯·施高德(Adolphe Clarence Scott,1909—1985)利用工作身份来到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研究中国戏曲,出版了相关著作,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中国戏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戏曲元素带入美国高校。这一切为中国戏曲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戏曲的译介包括综合概述、难点详解和中西比较,无疑为当今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毋庸置疑,这位著名的东亚戏剧研究学者与中国戏曲有着不解之缘。缘分何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施高德与中国戏曲名角的交往
施高德于1909年出生于英国,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自小对艺术充满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摄影师首次来到亚洲。1948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任进入中国,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负责进行中英两国之间的一些文化交流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戏曲,时常出入戏园子,并获得在后台与演员频繁接触的机会,从而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有了初步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施高德来到香港工作。两年期间对戏曲认识日益加深,他曾写道:“相比之前曾在中国内地培养的戏曲爱好,20世纪50年代早期香港的生活却给我带来了更多戏曲方面的收获。”①A.C.Scott, Actors Are Madmen.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 pp.148—149.相比于先前在内地戏院后台结识的那些名气不大的唱戏艺人,他在香港,却能够与当时中国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张君秋和俞振飞保持一定的交流,尤其是俞振飞和施高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日后施高德再次来到北京也得到了这位老朋友的帮助。他曾在其著作《唱戏的是疯子》(Actors Are Madmer)中如此描述:“俞振飞性格极好,和我成为很好的朋友,经常带着他的妻子来拜访我们。”②Ibid., p.152.作为研究中国戏曲的西方学者,有机会亲身来到中国,与戏曲名角们接触,这一切无疑为施高德日后更好地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施高德有关中国戏曲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图文并茂。这些图片部分来源于梨园界好友的友情提供;还有一些戏曲人物造型和乐器服装的图画素描,穿插在施高德作品中。施高德与丑角王德坤的私人关系甚好,“他时常带着戏服来到我家,为我摆姿势,供我素描以辅助我的研究”。③Ibid., p.159.这些图片帮助西方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戏曲文化。
从另一层面来看,这些资料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传统戏曲的宝贵资料。虽然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土壤,施高德克服了欧洲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平等和包容的心态接触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曾在著作《中国传统戏曲》(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第一卷中前言论述道:“这本作品目的有二,其一为戏曲专业学生提供有关中国传统戏曲舞台方法;其二为他们留下两部经典戏曲资料,今日看来,这些古老的东西似乎将永远地从京剧舞台上消失。”①A.C.Scott, 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 Vol.1.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7, p.v.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新形势,中国戏曲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文革”期间“样板戏”的火热上演,正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样板戏”的推广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政治力量干预和演变的必然结果。施高德第一次进入中国,恰逢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他用自己的笔杆,透过西方“他者”的视野,为我们记录下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形,其中就包括传统戏园子的演出情况、嘈杂的大厅、嗑瓜子观戏的观众、忙碌的服务生等都被施高德一一记录下来,然而这一切在现在的中国戏院早已不见了踪影。1956年,当他再次来到中国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已悄然发生改变,传统的戏曲已经式微。出于对戏曲艺术的热爱,施高德也观看了曹禺解放后创作的新剧本《晴朗的天》。然而,同国内评论界的观点截然不同,施高德对这部新戏的评价很是一般—“表演的道具和服装方面都偏向现实主义,这表明已经深受俄国影响,情节整体冗长并充满了矫揉造作的表演,薄弱的舞台造型……中国传统戏曲非常注重发声,而现代剧院里面却对这一传统压根儿不讲究。”②Scott, op, cit., pp.196—197.施高德两次进入中国内地以及在中国香港工作的经历,相比于其他研究中国戏曲的西方汉学家来说,不论是获得一手材料可靠性,还是实在感受中国社会的变迁,施高德的优势不言自明。
二、将中国戏曲元素带入美国高校
施高德另一重身份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戏剧系教授、翻译家。离开香港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工作若干年。在其众多研究项目中,最具意义的是他安排了1961年《蝴蝶梦》在美国戏曲艺术高等研究院的演出。1963年,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邀请,他创立了亚洲戏曲研究新项目,此课题最初阶段的经费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此期间,施高德还邀请了亚洲艺术家赴美参加表演,也接收培养了一批优秀博士毕业生,这其中包括杨世彭(Daniel.S.P.Yang),毕业后成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教师,亲自导演了京剧《乌龙院》,获得荣誉;荣休后,担任香港话剧剧团艺术总监,他对亚洲戏曲在海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得施高德早已熟悉中国戏曲,但他也深知东西方学生在语言、发音等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在训练学生排练《蝴蝶梦》时,他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方学生演员无需唱咏叹调,慢条斯理地说出与伴奏音乐匹配的台词即可。”③Siyuan, Liu “A.C.Scott,” Asian Theatre Journal, 28.2 (2011): 419.以上种种事例表明,施高德利用其高校研究者的身份,发挥带头作用,一方面将中国戏曲知识介绍给西方高校;另一方面,亲身实践指导学生如何在西方的舞台上搬演中国传统剧目,因地制宜。这一切为中国戏曲在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1985年去世,他仍忙于撰写《世界戏剧之剑桥入门》(The CambridgeGuidetoWorldTheatre)的中国戏曲部分。亚洲戏曲期刊的编辑们公认他为“西方研究亚洲戏曲表演的先驱”④Ibid., p.414.,施高德实至名归。
三、施高德与中国戏曲的译介
如果说施高德是20世纪让中国戏曲走向西方的一位传播者和阐述者,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夸大。这位学者一生都奉献给了亚洲戏曲事业的研究、传播以及译介。施高德对中国戏曲的翻译主要采取直译的方式,这由客观因素所决定。其一,普通的英语读者,不熟悉中国文化,自然对中国历史典故与俚语格言更是一窍不通。其二,取决于作者著书原因。施高德曾在1982年出版的《唱戏的是疯子》著作前言中谈及创作原因:“创作这些远离西方人日常生活的中国戏曲的可能性,既不会让读者费解又有一定的教育性。”①Scott, Actors Are Madmen, p.ix.
施高德对中国戏曲的译介论述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理论,但其翻译观点和见解散见于他所写的序、前言以及附录的文字中。他对中国戏曲的译介采取直译,对故事背景和典故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这无疑会使中文唱词的华彩大打折扣,导致索然无味。施高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对晦涩的风格兴趣全无,一心期望戏曲能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而不是被大量的注释遮掩。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的戏曲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施高德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以下我们将从施高德作品译介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1.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戏曲基本知识
中国文学艺术历史悠久,果实丰硕,但戏曲在西方的认可度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显而易见,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习惯了现实主义舞台风格的西方观众,起初接触到中国戏曲时,对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方式完全摸不着头脑;空旷简易的东方戏曲舞台与西方追求逼真的舞台风格差异迥然;最让西方观众痛苦不堪的是语言,东方戏曲里的台词里填充了历史典故与俚语格言,如果不懂其背后的含义,又何以理解人物对话的真实意图?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情何以堪?重重的困难让中国戏曲走出国门,获得西方世界认可的进程步履维艰。然而,中国传统戏曲正是施高德朝思暮想的东西,他毅然选择了这条路,选择了将中国戏曲译介到西方。
施高德深知向西方大众传播中国戏曲的艰辛。1957年他首先撰写了《中国古典戏剧》(The ClassicalTheaterofChina),对中国戏曲的译介定位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实用手册”。他在前言中开门见山谈到“很有必要尽可能地描述演员们的表演技巧,毕竟这是象征主义的基础,很有必要追寻。除此之外,这也形成了有关戏剧过程的记录,即使现在没有,这个过程也注定会发生许多改变。这种性质的作品,遇见许多特殊术语在所难免,但我将会尽可能的做出解释。”②A.C.Scott, The Classical Theater of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7, preface.我们不难发现,施高德此时对中国戏曲的译介重点集中于介绍,对“京戏”进行了西方“扫盲”,可以称得上是西方读者了解京剧的入门级读物,将京剧的历史、音乐、演员以及角色、技巧、剧目甚至戏园子都一一做了描述。有关中国戏曲这样基础级别又详尽的介绍在西方世界实属少见。但此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对中国戏曲表演中背后所覆盖的中国文化内涵介绍较少。如果说1957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是一本有关中国戏曲的综合性概述,那么1967、1969和1972年施高德撰写的《中国传统戏曲》(共三卷)则是对中国戏曲中著名剧目的详细有针对性的译介。在这三卷著作中,作者总共翻译了《四郎探母》《蝴蝶梦》《思凡》《十五贯》《拾玉镯》和《女起解》六部著名剧目。如果作品只是将故事的情节发展和台词一一机械对照直译,这本著作可以说毫无特色。但是,作者将以上六部戏的人物介绍、服装打扮、故事情节发展以及台词,都一一独立成章地译介出来,西方读者自然很清楚“what”“how”以及“why”,这完全符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逻辑。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先生访美演出归来后,美国观众亲身观看中国精彩戏曲演出的机会甚少,施高德选择将中国著名的剧目详细地介绍给西方,令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他也曾在《中国传统戏曲》第一卷中指出,“对于戏曲专业的学生来说,在纯粹文字描述剧本之前,如果没有对表演因素进行一定的解释和翻译,亚洲戏曲很难被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③Scott, 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1, p.vi.
2.作品中掺杂对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介绍
正如上文中谈到,施高德的作品是对中国戏曲的介绍,不仅仅谈论戏曲演出本身,与戏曲相关的社会现象都一并介绍给读者。不论是针对西方普通读者,还是西方高校戏曲专业的学生,这些都是可供参阅的有关中国戏曲的第一手材料。施高德的作品是针对西方读者有关中国戏曲的参考书,然而真正的亮点是为海内外读者们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画卷,这一切情况正是透过这位西方文化工作者的视阈,再现新旧更替的中国社会的层层涟漪,这些材料也为国内读者看待当时国内情况提供了新的角度。1982年出版的作品《唱戏的是疯子》便是最好的佐证。作者直截了当写道:“此书可作为随笔展开阅读,书中的旅行者将其感受悉数吐露—这位旅行者已经深深融入了戏曲的短暂世界中去,不受其他事物干扰,但这位旅行者也十分幸运能够拥有足够的时间徘徊在旅途中,亲身体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①Scott, Actors Are Madmen, p.x.
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历历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国民党撤退前夕,南京火车站拥挤不堪的人群,他们手提着装有热水瓶和画有龙或金鱼的搪瓷杯;初来南京的作者受到了中国房东热情招待,西方人如何应对频频敬酒;上海电影院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冗长的情节,观众反复流淌的泪水;旧式戏园子里嗑瓜子的看戏人,倒茶送花生的服务生;作者体验了曾被视为传统舞台入侵者的女艺人终于登上戏曲舞台的艰辛;上海大亨杜月笙对中国戏曲界的影响;1948年国内通货膨胀,“当时北京宾馆每日房费高达100万元”②Ibid., p.65.。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梅兰芳先生如何坚持表演《四郎探母》;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北方地区难民大量涌入南京城,国民政府高官收拾行囊准备撤退,处于新旧更替时期的中国百姓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都一一呈现于纸面之上。
3.中西文化的比较意识随处可见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古希腊戏剧和印度古戏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戏剧。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仍活跃在艺术舞台上只有以中国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曲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这位来自西方,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者施高德却对亚洲戏剧情有独钟,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西方的他,当接触到东方的文化时,“对于关注戏曲的人,比较总是存在”。③Ibid., p.38.在施高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比较的例子,如跨国别比较。作者在《唱戏的是疯子》一书中,谈及中国电影部分时,作者以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相比较,它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超西方。施高德并没有就此停笔,他随后展开分析《城市之光》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是源于“现实与想象的相互作用”。④Ibid., p.43.还有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施高德对中国传统戏曲充满了溢美之词—“在设计新式表演的自然主义风格时,须继承旧戏园子的演出在视觉上的连贯和节奏、空间和时间的处理等珍贵的财富。”⑤Ibid., pp.43—44.相比之下,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事业却不尽如人意,“严重缺乏对自然表演以及舞台程序的理解”。⑥Ibid., p.44.施高德对西方写实主义风格再熟悉不过,通过比较,敏锐察觉到中国电影初期拍摄过程的不足。施高德作品中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作者并没有就社会现象的发生展开深层的社会原因探析;其二,影响是相互作用的,但施高德著作中谈的更多是中国戏剧受到西方和苏联写实主义的冲击而发生了变化,很少涉及中国戏曲元素对西方戏剧的影响。施高德对中国传统戏曲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进行了对比。演员是戏曲表演的核心,在《唱戏的是疯子》著作中,他大篇幅描述了过去梨园艺人的成长经历和漫长又艰苦的训练—严格的师父、铁一般的纪律,残酷的体罚不可或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戏曲学校的建立,他认为,演艺学生的培养模式截然不同,此时的学习更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施高德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怀念。
中国传统戏曲的自身特点对西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仅需跨越语言的障碍,还有文化的藩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先生的海外演出使中国戏曲走向海外;20世纪后半期,施高德,这位美国汉学家将中国戏曲介绍给西方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不仅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还为海内外研究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而且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竹内好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鲁迅研究。他追求“在状态之中”的思想方式,抗拒学院知识生产体制,这使得他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化,亦使他如其终生敬仰的鲁迅一样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而不只是“学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在战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继续被研究者引为参照。除了鲁迅研究外,他还在日本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领域,如对丁玲、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的研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他的业绩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以鲁迅研究为基础,他介绍了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的思想,同时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对新中国的历史性和思想性意义作了整体性诠释。所谓竹内模式或者竹内范型,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2016年10月,三联书店推出了竹内好的一部文集《近代的超克》。此书遴选了作者写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包括《鲁迅》《近代的超克》等集结而成,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和知识立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