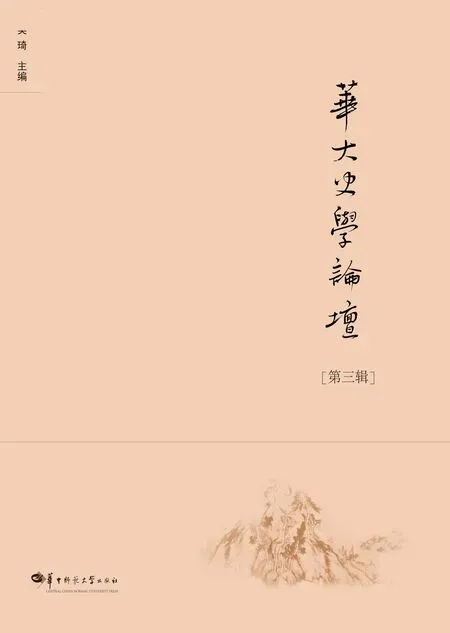嘉道年间漕粮征派中知县、书吏、绅士的利益冲突
——以“钟九闹漕”为例
周 狄
清初至乾隆中期,漕政整治严肃,漕运从交兑起运到交仓都有一整套繁琐严密的管理和监察制度,是漕运的极盛期。自嘉道以后,吏治腐败,官员胥吏视漕运为贪污渊薮,漕弊日显,以致清晚期各种流弊不断侵蚀漕运机体,漕运已成为积重之势[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页;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湖北漕弊由来已久,武昌府告示宣称:“湖北漕务积弊,民苦浮勒,官无经制。其取于民者厚,其交于公者微。类皆中饱于丁船杂费及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151页。在道光朝的崇阳也不例外,道光帝亦说:“湖北崇阳县户书向花户勒索耗银样米由来已久。”[注]《清宣宗实录》卷371,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03页。在官吏与绅民的利益冲突及多种因素综合之下,“钟九闹漕”从诉讼最终走向暴动。
学界对于“钟九闹漕”的研究注重其事件本身对于清代社会矛盾的反映与激化,陈辉甚至认为钟人杰(即钟九)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反清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注]陈辉:《钟人杰起义史实考》,《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41-49页。。也有从历史人类学或法律史学等角度探其发生的原因、实质及影响[注]张小也:《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第103-106页;《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62-170页。。罗丽达与邓建新则注意到地方绅士在闹漕事件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注]罗丽达:《道光年间的崇阳抗粮暴动》,《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78-82页;邓建新:《钟九闹漕: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叙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钟九闹漕”中各层人群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并认为其中的知县、书吏与地方绅士[注]本文对于“绅士”的定义沿用张仲礼的观点。张仲礼依据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来划分绅士集团,其有上层和下层之分,下层绅士则包括生员、捐监生及其他一切有较低功名的人。钟人杰、汪敦族、蔡德章及陈宝铭等闹漕事件的领导者应属于下层绅士(见下文),但是学界对于绅士的定义与内涵尚有争议。张仲礼关于绅士的论述参见其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关于绅士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56页。、普通民众存在利益冲突,其冲突的核心在于漕规,这是导致“钟九闹漕”及其他此起彼伏闹漕事件的根本原因[注]以各层人群利益冲突为考察视角,参考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以及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48-59页。。
一、下层绅士、花户与知县:不满县衙浮收勒折
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到二十二年(1842年)崇阳一共换了五任知县,分别是王观潮、蔡学清、折锦元、金云门和师长治。金太和在道光十六年秋上县城缴纳漕粮时被打,是“钟九闹漕”的导火线,也拉开了下层绅士动员及领导民众反抗官府的序幕。折锦元开仓重复浮收,致金太和再度系狱武昌府,引发钟人杰等率众花户两次拆打粮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元宵节“二打粮房”时,“逆等……手执红旗大书‘官逼民反’统众入城……打毁书差房屋、抢掠资财衣物,踞城三日拆虏无遗”[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钟九闹漕》对“二打粮房”时地方生监与花户围攻县衙、聚众闹漕的情形描述得更为生动:
等到三日一齐来,千万乡民涌上街,喊叫一声齐动手,门片窗棂乱打开,各种物件碎成材。西门打到小东门,砖头瓦片两边分,连墙带脚掀到底,良民铺户放宽心,衙役人家不留存……四城百姓挤满街,一齐吵到大堂来,三班六房都逃散,太爷吓得战筛筛。[注]王旺国整理,饶学刚审定:《钟九闹漕》,崇阳: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1997年,第50-51页。
拆打粮房,钟人杰等也只为逼迫知县重定征漕数额。折公对其无计可施,只能以纳粮时因争论银子成色发生冲突、人多拥挤导致民居毁坏上报。武昌府于是“将折公照人地不宜奏撤,另补委候补知县金云门来署办理此案”[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
金云门因受书吏挟制,上任不到半年而离职。“二打粮房”之后,漕粮章程新立,师长治欲“不思长久之计,拟将新漕办竣,不计盈亏,博一安静之名,拜托而去”。因闻金太和被释无望,花户金青茂、武生陈宝铭等人率众攻克县城并再次围攻县衙,师长治被胁迫至“出槛绊跌卧,抢矛按捺下部不容复起”。钟人杰赶到质问无果,乃“饬党下手”,师长治被杀。
因知县并未直接参与征漕,下层绅士、普通花户不满县衙过于繁重的浮收勒折,最主要是由书吏不择手段的盘剥而引起。魏源指出:“崇阳圜万山中,胥吏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注]魏源:《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见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古微堂外集》第4卷,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68页。书吏在征漕时常与衙役合作浮收,在采访资料中当地的民众说:“当时完粮饷、县里收粮用皮斗,米一装进去就变大了。还有风车风,风出的米不能给农民带回去,一百斤难完七十斤;装进米后,下面就鼓起一个包,而上面还要堆起来(‘淋尖’),所以一斗米上面一个包,下面一个包,一担米只完五升;收米要交米样,样米合格了就完,撒在地上的米不称数;小米、碎米,不熟、不白的米不要,完米时并且斗斛又很大,还用手脚踢。”[注]华中师范学院74级历史系:《钟人杰起义历史资料(一)》,分别为1975年10月27日,程和清口述;1975年10月29日,甘正南口述;1975年11月2日,蔡福田口述;1975年11月3日,王怀瑾口述;1975年11月3日,王怀瑾口述,崇阳:湖北崇阳县档案馆馆藏,1975年。《钟九闹漕》描述书吏压榨行径更有触目惊心的质感:
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饷逢毫厘一分算,米上几合要一升,算盘珠子打死人。粮房柜上一窝蜂,全靠花户米来供,踢斛摇斗乱行抢,三盘样米太不公,羊入虎口痛难忍。左一扯来右一拖,担米抢去半箩多,若有半句话不好,反骂愚民莫啰嗦,打个嘴掌不敢呵。世间最毒是粮房,串成一党恶难当,欺天灭地多诡计,一把升子七寸方,斗米把作七升量。[注]王旺国整理,饶学刚审定:《钟九闹漕》,崇阳: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1997年,第26-27页。
殷堃对下乡催漕书吏也有记述:“沿乡收垫数十文之正款,须数百文差费、饭食、驴脚等款。懦弱之家具酒食不仅肉蛋而已,必致争宰鸡鸭,否则摔盆掷碗,甚有奸淫人妇……此粮差为害之甚。”[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现已无从得知道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崇阳征漕数额,根据道光前后及崇阳周边县推测,道光年间崇阳征漕数额均在5000石以上[注]顺治十四年(1657年)崇阳征漕2243石,九年征漕2465石;雍正七年(1729年)征漕2494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征漕2992石;咸丰七年崇阳征漕5164石,同年通城县征漕6720石,咸宁县征漕6330石,大冶县征漕6562石,蒲圻县征漕9750石,兴国县征漕9871石,江夏县征漕7550石,武昌县征漕8386石。咸丰七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裁减湖北各州县漕规,崇阳周边县经裁减后应征漕额均在5000石以上,所以做此推测。顺治、雍正及乾隆各朝漕额参见: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6-155页;咸丰七年各县漕额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46,《经政志·漕运》,台北:华文书局,1921年,第1106-1107页。。
在整个事件中知县与普通花户都处于弱势地位,而钟人杰等下层绅士“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其地方生监势力强大,以致历任知县也无可奈何。殷堃对此评曰:“崇阳在崇山峻岭之中……山中之民世不及城者居多,鲜知纲常法律,悍滑异常。事平两月已三次围城挟官矣!不知国法何在,政体何存。”[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由此可知,在征漕时知县与下层绅士、花户间接的利益纠葛,是由知县与书吏、书吏与绅士直接的利益冲突导致的。
二、知县与书吏:漕规分配不均
魏源批评折锦元“溃不治事,一惟胥役所为,致两次哄漕”[注]魏源:《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见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古微堂外集》第4卷,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68页。,但实际上历任知县“溃不治事”既表现在不能对挟制官长、盘剥乡民的书吏予以惩戒,又不能阻止地方生监与民众聚众闹漕。而书吏“故虎而冠”不仅体现在对普通民众不择手段的盘剥,更体现在对官长的挟制。历任知县虽是受书吏挟制而“溃不治事”,但知县与书吏在漕运利益的分配中存在着对抗。
王观潮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崇阳知县,其时已是“(书吏)玩官民于掌上,钱漕之弊尤甚”[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蔡学清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代署县事,其时金太和系狱,金瑞生(金太和侄)邀约钟人杰再次往省府控告并获准,省府“一脚提牌到崇阳”调查此事,因蔡学清并未偏袒书吏而且“折狱不尚威猛,感其德者颂好官”[注]同治《崇阳县志》卷6《职官志·知县》,《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深得老百姓拥戴。
折锦元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接任知县。书吏将各种收漕费用推给折锦元,使得“官既不能为之整复旧规,亦只得不诺而诺,遂受书差之挟制”[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金云门于道光二十一年春接任知县。其上任之后,“书差潜匿不出,无熟手承办公事,沿门招致,皆推诿不承”,金云门只好“亲自催科,自给夫役饭食”。因对“二打粮房”一案迟迟未决,而武昌府“控催益急,雪檄频仍,委员接踵”,所以金云门署任未半年就主动离职,以“其(师长治)精明强干必能了理此案为禀请饬即赴任”。师长治于道光二十一年秋接替崇阳知县,上任后也面临着金云门同样的困境,“展转导输,继之以威”,乃至承诺“自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费用悉出于官”,书差“方允许认办”[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
清朝的回避制度使得知县一般由外省人担任,这些知县由于不熟悉当地民情而不得不依靠书吏等衙门职员。在“钟九闹漕”中,书吏承当了知县与普通民众的中介。在漕运陋规的收取中,两者可合作;但在具体的利益分配时,两者存在对抗。
从咸丰七年(1857年)武昌府所发禁革陋规单来看,相对漕运系统层层克扣、剥削,知县与书吏从中获利无几:
计开删除崇阳漕南一切陋规单:院道府厅房差费银八百六十四两六钱三分六厘,钱一千三百七串八百九十三文……起解运费库平银八百两解府……余银当作县中制备征册流水卷票纸扎、书役饭食等项津贴办公之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2-156页。
整个县衙从漕规中得到办公费用才64两,显然无法满足庞杂的公费及个人开销。虽不知知县与书吏围绕征漕所分得漕规的具体数额,但两者在漕规利益分配上存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亦是造成书吏挟制知县的重要原因。对此,知县也趁机打击书吏,“二打粮房”后书吏向折锦元哭诉,折公很是生气:“太爷一见怒满怀,大骂几声众狗差,徇私舞弊一伙党,讹诈乡民太不该,你叫本县怎安排。”折公肯定是为了推脱责任而出此语,不然书吏不会如此不解:“垂头丧气出公门,恼恨折爷无道理,反与乡民一合心,船开不顾岸上人。”[注]王旺国整理,饶学刚审定:《钟九闹漕》,崇阳: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1997年,第56-57页。
知县的“溃不治事”为书吏征漕多加外派、中饱私囊及遣词构讼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地方的下层绅士亦包揽征收乡民漕粮、唆使构讼收敛讼费,其势必与书吏形成利益冲突。
三、书吏与下层绅士:包漕构讼,利益冲突
书吏的盘剥虽是促发闹漕的重要原因,更主要是因钟人杰、陈宝铭和汪敦族等下层绅士[注]钟人杰、陈宝铭与汪敦族均是县学文(武)生,其三人的口供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北京:中华书局,第2-6页。在其中遣词构讼、包揽漕粮与书吏形成利益冲突而起。殷堃在指责书吏下乡盘剥民众的同时,亦提道:“彼之原差勾此之原差串唆构讼,两原差从中落乐利,代理差房并说讼事……甚有原被并未入城而词已雪叠,皆两造主持。”[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上海图书馆馆藏。他们作为民众缴粮完税的中介,或下乡包漕,或遣词构讼,在其中获取高额利润。
同时,魏源、穆彰阿都指出了钟人杰等下层绅士包揽漕粮征收。魏源在批评吏役“故虎而冠”的同时亦指出:“生员钟人杰、金太和[注]金太和可能不是生员,而是普通花户。“金太和家景是比较贫寒的,是个小花户,只有斗米的粮税。”“金太和在武昌府坐牢,要写封信到崇阳给钟九,但不会写字,金太和在纸上用墨(毛)笔,画了个圈子,在圈子里面点了一个红点,表示官府要杀他。”参见华中师范学院74级历史系:《钟人杰起义历史资料(一)》,1975年10月30日,饶少南、杨贻祖口述。者,亦故虎而冠,与其党陈宝铭、汪敦族起而包揽输纳。”[注]魏源:《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见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古微堂外集》第4卷,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68页。穆彰阿在奏折中谈及“钟人杰……与陈宝铭、汪敦族并已正法之金太和等代各堡包揽完纳漕粮”[注]Philip A.Kuhn and John K.Fairbank,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Reading Documents:The Rebelling of ChungJen-Chine,Harvard University,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Research,1986,p.27.。钟人杰、陈宝铭与汪敦族对自己包漕一事也供认不讳,三人的供词中都有“我们因敛收讼费,把持钱漕,与书差构讼”之语。钟人杰更清楚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有素好的陈宝铭、汪敦族们,因把持钱漕,与书差构讼,我就主使向各保花户敛收讼费,从中分肥。”[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2页。虽然《钟九闹漕》对钟人杰等下层绅士包揽漕粮、敛费构讼着墨较少,但通过仔细分析,亦可窥视其收敛讼费的蛛丝马迹。
《钟九闹漕》中只有三处谈到了收敛讼费的情况。道光十七年(1837年)金太和赴省府上控之前,在崇阳县内奔走相告:
崇阳花户听此言,并无一人心不愿,既是老者有此意,大小花户有万千,按照粮饷派银钱。正月走到立夏时,四十八堡尽皆知,崇阳地方都走到,各处花户愿助资,并无一人有推辞。
金太和被押武昌府后,钟人杰、汪敦族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聚费再告:
钟九回复意中人(汪敦族),只为粮案一事情,我今特来邀约你,四人都要一合心,同到乡下派钱文……四人一路摆摆摇,为首出众受辛劳,传明钱文付保正,限定日期把钱交,都是送到白霓桥。
除此之外,殷堃对钟人杰等人聚敛讼费的具体数额有明确记载。金太和上控获准后,“逆等回乡照钱粮每两派钱二百文,计敛讼费二千余千”,“二打粮房”后,“复照纳漕之数每石敛钱一千以备讼费,计敛四千余千”[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据邓建新估计,钟人杰等人聚敛的讼费应当远超过4000两白银。据邓建新考证,咸丰四年(1854年)崇阳额征正耗银14468两,也就是说,“钟人杰两次收敛的讼费大概是当时崇阳一年征税额的三分之一”[注]邓建新:《钟九闹漕: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叙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清代名幕汪辉祖对诉讼费用之重有切身的体会:
谚曰:“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非谓官之必贪,吏之必墨也。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馈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有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呈示之人……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注]汪辉祖:《佐治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由此可见,诉讼一事颇费钱财。
一方面,书吏与钟人杰等下层绅士包揽漕粮均可获益;另一方面,钟人杰等控告官吏征漕多加外派既可聚讼费落利,又能打击书吏包揽漕粮与遣词构讼的行为。咸丰年间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指出了下层绅士包漕、构讼的真实目的:
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其零取于小户者重,整交于官仓者微……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己求财也。[注]胡林翼:《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见王岩熙、王树敏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27,《户政类·赋税》,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419页。
因此,书吏从包揽漕粮、遣词构讼中获利,在与知县的利益产生纠葛的同时,也必然与参与包漕、构讼的下层绅士构成利益冲突。总而言之,在漕粮征收的过程中,知县、书吏与钟人杰等下层绅士和普通民众联系紧密,闹漕事件的发生则反映了此四方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葛与冲突。
四、漕规:三方冲突的核心
简而言之,闹漕事件的发生直接源于官府对民众的浮收勒折。但是,在征漕过程中由于诸多力量或势力的参与,各方的利益充斥其间,闹漕的原因又是多方利益冲突与纠葛的结果。在“钟九闹漕”中,知县、书吏、下层绅士三者之间纠葛和冲突的核心在于漕规,尤其体现在知县与书吏、书吏与下层绅士之间。当时是默许陋规存在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收受陋规不算贪腐,因为其是广泛接受的事实,也在法律的默许之内,不能与别的贪污腐败混淆。政府所能做就是将其与财政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努力将此规范化[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8-50页。。以下,笔者从知县与书吏两个方面论述漕规在地方社会存在的原因。
(一)知县层面
首先,知县薪俸难以应付繁重摊派,其不得不依赖书吏浮收勒折。清初,经厘定全国文武百官的薪俸及办公经费后,崇阳知县年俸44.9两,作为“繁、疲、难”[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2《地理志·武昌府》,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171页。之县公费仅约227两,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后,始有养廉银800两[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0-168页。。知县除额俸45两外,亦有薪银36两、修宅什物银20两,但顺治九年(1652年)均被裁[注]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00,《户部·俸饷》,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第9233页。。瞿同祖指出,知县又有摊分政府费用、填补县财政历年亏空及承担招待上级费用与致送上级各种陋规等繁重开销,以致县官的每年支出费用(包括政府办公经费与僚属佣金)约在五六千两到一万两以上[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7-50页。。据此我们可以推知,仅靠知县的固定收入难以满足繁重的开支。在此种情况下,县官唯靠陋规维持生计及补足办公经费[注]张仲礼估计,知县每年还有约3万两额外收入,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漕务陋规仅是诸多陋规中的一项而已。自雍正实行耗羡归公以来,州县官员收入(主要是养廉银)虽有所增加,但面对巨额摊捐(道光时期普遍用养廉银)及养廉银、薪俸被各种原因克扣的境遇[注]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知县不得不依靠书吏、衙役等浮收勒折。“二打粮房”重定章程之后,折锦元“恼恨崇阳定漕粮,名利两无官难做,又无钱米来扎腰,再到哪里赚分毫”[注]王旺国整理、饶学刚审定:《钟九闹漕》,崇阳: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1997年,第48页。。折公如此“恼恨”,这从侧面反映出了崇阳知县财政困难的现状。
其次,考核严格也使知县力尽完粮。财政上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行政体制内的因素不容忽视。闹漕事件的发生反映了本地存在漕粮难完及浮收勒折的现状,但政府把钱粮之事纳入考核范围,知县又不得随意捏报完满,“外官或钱粮盗案未清冒称考满……者,一并题参治罪”[注]伊桑阿,等纂修:《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0,《吏部·考满》,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第409-410页。。其显然影响仕途升迁。折公在两难之下不得不重复浮收,最后被“人地不宜”撤罢,便是明证。
(二)书吏层面
首先,书吏薪俸少,激起了其对陋规的需求。书吏的公食银和廪粮银先后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元年(1662年)被裁[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此后书吏有无薪俸暂且不论[注]瞿同祖与周保明对书吏是否有薪俸有不同意见,但均认为知县项下书吏薪俸被全裁。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72页;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5-259页。,但需要自负纸笔费用却是事实。田文镜说:“盖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无额设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作弊,若并此挂名津贴亦为革除,则纸笔之费亦无从出矣。”[注]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政·胥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908页。薪俸既全裁,又有纸笔等费,征漕时多加外派可想而知。
其次,层层陋规贪索为书吏浮收提供了动力。在咸丰七年(1857年)禁革的漕规单中,洋洋洒洒一百余项,行政系统、漕运系统、军队的官吏都有规费。书吏在征漕时多加外派收获甚大,但并不都归自己所有。书吏取于民,知县索于书吏,而知县或者书吏又被索于粮道府院,层层剥削、恶性循环,以致“民生日蹙,国计益贫”。
最后,书吏生活贫苦,征漕必图腹饱、“囊饱”,乡民难逃虐待。书吏办事须知县给饭食,其下乡催粮“必致争宰鸡鸭,否则摔盆掷碗”。重定漕粮后,“(花户钱粮)自封投柜不容迟乱,杜绝粮差下乡,书差之弊全除,蠹等岂甘枵腹”[注]殷堃:《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馆藏。。由于生活拮据而产生的扭曲心理,从此也可想见崇阳书吏的生活状况。
在“钟九闹漕”中,官弱吏强是一种现象,而非事情的完全面貌。官吏本是官僚系统中的“一体两翼”,官有品而无能、吏有能而无品,因此官员不得不依靠书吏,而又不能从制度上承认其合理权益,将它整合进官僚体制中来,于是“官弱吏强”的现象才会产生[注]王雪华:《清代官弱吏强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47-354页。。但因直接操纵漕粮浮收而往往成为打击对象。金太和等人到省府控告的是书吏浮收漕粮,钟人杰等人两次拆打粮房的直接对象也是书吏;在暴动爆发之后,钟人杰等人也不忘搜杀王大、余五等书吏;咸丰七年武昌府“出示晓谕”:“自此次定章之后,官吏丁役如敢格外多索,一经访闻或被告发,丁胥立拿杖毙,官则专案严参惩办。”[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在“钟九闹漕”中,知县与书吏为分得漕规而贪索于民,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广而言之,漕规存在的原因涉及清代漕运体制、财政体制以及行政体制等诸多互相紧密联系的因素,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地方政府的贪腐。因此,将其放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钟九闹漕”的爆发虽有其偶然性因素,但漕规体制的腐败是导致闹漕事件的根本原因,以致“闹漕”不限于“钟九”。
五、不只是“钟九闹漕”:漕规存在的影响
“钟九闹漕”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内有涝灾、外有战事的背景下,爆发波及周边州县的闹漕事件,有其偶然性因素。但由于漕运体制积弊日显,嘉道年间闹漕事件此起彼伏[注]具体可参见肖丽红:《闹漕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郑民德:《博弈与冲突:从〈清实录〉看道光朝的闹漕斗争》,《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91-95页。。围绕漕规而形成的多方利益的纠葛、冲突,始终是促使“闹漕”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钟九闹漕”最后走向“破城戗官”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军费骤增,摊派更多,贪索亦重。尤其是道光时期银贵钱贱呈直线上升发展趋势,花户纳粮折色用钱更多[注]倪玉平:《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49页。。再加上道光二十一年春湖北省发生涝灾,崇阳县“霪雨,夏麦(早)熟”;初夏,又发生虫灾:“六月,苗多螟。”嘉道年间崇阳自然灾害频发,嘉庆年间钱粮屡有蠲免,而道光年间对崇阳蠲免仅有一次[注]嘉道年间崇阳灾害发生状况参见:同治《崇阳县志》卷12,《杂记志·灾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5-417页。道光年间蠲免情况亦参见上书,第178-179页。道光年间在道光二十二年才蠲免二十一年钱粮,显然是在暴动之后才抚恤民情。而且道光一朝30年,对崇阳仅免此一次而已。。灾荒之年照常浮收与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自然成为暴乱发生的催化剂。
再者,在清代漕粮案中,钟人杰等下层绅士敛费构讼根本没有合法性,并要受到政府的打击。“文武生员除事关切己及未分家之父兄许其出名告理外,如代人具控作证者,令地方官申详学臣褫革之后,始行审理曲直……〔褫革生名后〕包揽词讼者,加倍治罪。”[注]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635,《刑部·刑律诉讼》,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第2996页。对于其包揽漕粮,道光帝在平息“钟九闹漕”的谕旨中严申“例禁”:“不准地方劣生人等包揽完纳漕粮,以安闾阎法纪。”[注]《清宣宗实录》卷371,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03页。瞿同祖认为,州县官与绅士的利益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州县官与个别绅士间的冲突,而不是与当地绅士整体的冲突[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7页。。在“钟九闹漕”中,就是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个别地方下层绅士与知县、书吏的利益冲突使得闹漕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另一方面,湖北漕弊积重难返:
查湖北各州县额征米数,多者二万余石,少者二千余石,或数百石……每石折收钱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而粮道有漕规,本管道府有漕规,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规;院署有房费,司署有房费,粮道署及本管道府署书吏各有房费。此费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其零取于小户者重,整交于官仓者微……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注]胡林翼:《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见王岩熙、王树敏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27,《户政类·赋税》,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419页。
从刁绅劣监包漕、州县征漕到起解运漕,无不是处处有漕规。
从全国来看,由嘉庆到道光年间,整个漕运体制,由漕粮征收、兑运到京通交仓几乎成了一个贪污网,“夫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22,《食货志·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565页。,有漕八省均难脱此网,沉重的负担最后都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道光年间,各省农民因不满漕粮浮收勒折而致闹漕频发,“今日直省地方,匪待滋事之案,小则聚众拘捕,大则戗官扑城,如湖北之崇阳、湖南之耒阳(闹漕之事在嘉庆末道光初),比年来层见叠出。揆其致衅之由,多缘征漕而起”[注]陈岱霖:《请严革征漕积弊疏》,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6,《吏政·赋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3701页。。在漕弊积深的背景下,无论是“钟九闹漕(或包漕)”,还是匡光文“控漕”(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年)[注]吴琦、肖丽红:《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3-72页。,抑或是叶镛“告漕”(道光七年)[注]赵思渊:《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77-87页。,主要都是地方社会官、吏、绅之间利益冲突激化的必然产物。
反而言之,闹漕事件既反映了官、吏、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恶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促使官员更加庸碌无为、吏治更加腐败的重要“推手”。暴动发生之后,湖广总督裕泰、湖北巡抚赵炳言联名上折:“臣等接阅之下不胜骇异。查崇阳县地处山陬,钟人杰前因包庇程中和挖煤图利,拟徒配逃,查拏未获。纵因与民人挟有夙嫌欲图报复,何至聚众入城抢劫监狱仓库、拒捕捆官?种种狂悖殊堪发指,并恐别有衅端或另有为首之人、该县办理不善所致均未可定。”[注]Philip A.Kuhn and John K.Fairbank,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Reading Documents:The Rebelling of ChungJen-Chine,Harvard University,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Research,1986,p.3.以“不胜骇异”推测事端发生别有缘由,其不熟悉地方民生及政务反而为推脱责任提供了借口。在钟人杰等从“讼漕”走向“闹漕”的过程中,其时崇阳五任知县政绩平平。督抚尚且如此,无怪乎“州县惟知以逢迎、交结上司为急务,遂置公事于不问。视陋规为常例,以缺分美恶,得项多寡,总思满载而归,视民生如膜外。而督抚司道等亦只知收受属员规礼,并不随时督察,上紧严催,而胥吏等,又利于案悬不结。可以两造恣其需索,以致拖累多人。日久尘积,上下相蒙,其毙(弊)已非一日”[注]《清仁宗实录》,嘉庆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298页。。有学者认为,嘉道时期,清朝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的水平,财政危机初步形成,吏治腐败更是把财政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注]倪玉平:《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74-382页。。亦可说,财政危机促使吏治更加腐败。
综上所述,虽“钟九闹漕”的发生有偶然性因素,但“一场战争如同一个火药包的引爆,它需要一根导火线,但爆炸的实际内容却是里面的火药”[注]洪振快:《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显然“火药”便是漕务积弊。在地方史与整体史的关照下,闹漕事件的发生是“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即:地方社会中官、吏、绅、民围绕漕规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当时国内外的社会背景,在多种因素结合之下,其爆发无可避免。“钟九闹漕”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前者是因漕务陋规而引发国内叛乱,后者是因海关陋规而引发国际战争[注]洪振快:《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二者(或者其他闹漕事件)都是财政危机爆发的反映,但两者又不仅仅是财政危机,更是国际经济利益冲突或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与此同时,闹漕事件亦加剧了财政与吏治危机,恶化了地方官吏与绅民的社会关系。
附记:本文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邓建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副教授的资料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