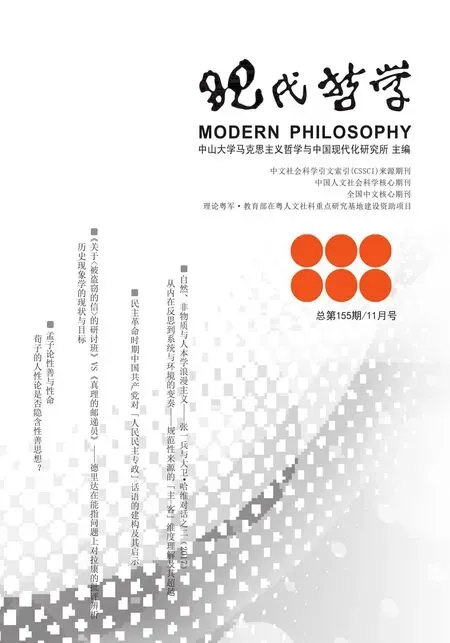荀子的人性论是否隐含性善思想?
陈 林
荀子的人性论是否隐含性善思想?
陈 林
那种认为荀子的人性论隐含性善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持此观点的学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性善”化约式地理解为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二是认为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对于第一点,孟、荀两人都认为“性善”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生而具有为善的能力,二是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此为善的能力自然且必然地表现出善行。在荀子看来,人生而具有的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为善,人之善行只能通过后天学习与努力才能出现。对于第二点,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生而本有之心本身并不具正面价值,其在自然状态下并不能自觉发挥促使人为善的作用,反而易使人流于为恶。
荀子;人性论;性善;性恶
一、问题的缘起
牟宗三曾言“荀子之学,历来无善解”*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193页。,其中又以荀子的人性论为最。如何理解荀子的人性论一直是荀学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荀子亦肯定人性中先天本有推动人为善成圣的能力;因而,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照,荀子人性论中隐含着一种性善思想。以“性善”来定性荀子的人性论可谓极具创新性,但这种理解是否符合荀子思想之本意?本文即尝试对此一问题进行辨析。
那些认为荀子人性论中隐含性善思想的学者提出此观点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文本依据。《荀子·性恶》*下文引《荀子》皆只注篇名。言: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这段话历来为荀学研究者所关注。从字面意思来看,荀子似乎认为每个人都生而具有认知“仁义法正”的“质”和实行“仁义法正”的“具”。如此,与孟子的性善论比照,荀子似乎同孟子一样,也主张人有某种良知、良能。
正是基于这段话,不少学者认为荀子的人性论中隐含着性善思想。如,陈澧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改尧、舜为禹耳,如此则何必自立一说乎?”*[清]陈澧著,钟旭元、魏达纯点校:《东塾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页。戴震言:“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页。罗根泽言:“人‘皆可以为禹’,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还不是性善吗?”*罗根泽:《孟荀论性新释》,《哲学评论》第3卷第4期,1930年。龙宇纯指出:“涂人所具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及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当为天性所本然。用孟子的话说,此可以知之质,及可以能之具,便是良知良能……荀子的‘可以知之质’与孟子的‘良知’或‘是非之心’,便看不出有任何的不同了。”*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64页。刘又铭说:“除了情感、欲望外,‘知’也在荀子所谓人性的范围之内。而且更重要的是,心所能知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仁义法正’……这是具有价值义涵需要价值判断价值抉择的东西,不是客观的概念和知识;因此荀子所谓的心是不能简单归为认知心的……在荀子的思路中蕴涵着一个未曾明说并且通常被忽视的重要成份:人心先天具备了一份素朴的、有待培养的道德直觉。”*刘又铭:《荀子的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汉学研究集刊》总第3期,2006年,第39页。.王楷言:“我们亦可以肯定地说:荀子所说‘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之‘质具’属于性,并且,由于它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内在的主体根据,因而,我们亦可以在此意义上说它是善的……如果将性善的意义界定为主体自身具有道德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荀子人性理论是一种性善论……”*王楷:《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89页。
上述学者论证荀子的人性论隐含性善思想的共同逻辑是: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尽管荀子认为人之为善的直接动力在于后天的“伪”,但此“伪”又是以人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如果把“性善”理解为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则可以如此推论:既然荀子认为人生而本有认知能力,而此认知能力能引导人向善,故而此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就是人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解的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一个潜在预设。此前提条件是,荀子所理解的“性善”是指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此潜在预设是,荀子肯定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问题是,荀子所理解的“性善”是不是指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在荀子那里,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是否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
二、问题的分析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荀子所理解的“性善”是不是指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
当讨论荀子的人性论是否隐含性善思想时,这里的“性善”显然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参照标准。因此,有必要先看看孟子是如何界定“性善”的。对孟子来说,如果问人可以为善的“质具”是什么,那么显然是人人皆生而有的“仁义礼智”之“四德”。但是,仅以“仁义礼智”之“四德”来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是不完整的。《孟子·告子上》*下文引《孟子》皆只注篇名。言: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一般认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孟子对“性善”的一种定义。“其”是指“性”,“情”乃“实”之意*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352 页。。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只要顺着本有之性之实而行,则所发动之行为就是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善。可见,孟子所谓的“性善”除了认为人生而本具“仁义礼智”之“四德”外,还强调人只要顺此本有之“四德”即可在经验现象中成就善的行为。也就是说,人所本有的为善能力与具体的善的行为是一种“自然且必然”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自然且必然”只是在理论意义上的自然与必然或者说是理想状态下的自然与必然。孟子也深刻认识到,尽管人本具善性,但人在现实生活中极易受物欲和私心之遮蔽而并不必然为善。因而,孟子亦言道:“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另外,《告子上》还言: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这里,孟子在同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辩论中以“水无有不下”之喻来言“人无有不善”,同样是强调人之善行的产生是不需外力作用就能自然生发。在孟子看来,水在没有外在力量的作用下,自然且必然向下流;同样,人之“四德”在没有外在因素的干扰下,会自然而然地促使人生发出“四端”之心,并表现出善的行为来。
所以,孟子性善论的内涵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生而有具有为善能力的“仁义礼智”之“四德”;二是此“仁义礼智”之“四德”无需外力作用即可在经验现象中自然且必然地显发为“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之“四心”,进而表现出善的行为。
再看荀子对“性善”的理解。事实上,荀子正是透过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来论证性恶论的正确,而荀子在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中就透露出自己对“性善”的理解。《性恶》言: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可见,在荀子眼中,孟子性善论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性”与“伪”,把本属于“伪”之种种归之于“性”。在荀子看来,所谓“性”是“不可学”与“不可事”的,也就是不需要后天人为学习与努力而天生自然具有的种种;所谓“伪”是“可学而能”与“可事而成”的,也就是天生自然不具备而需要通过后天学习与努力才能有的种种。荀子在这里做出“性”“伪”之分显然是要强调“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而荀子的“礼义”某种意义上就是“善”*荀子对“善”有着不同于孟子的特殊理解,他把“善”定义为“正理平治”。《性恶》言:“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同时,荀子又以“礼义”和“非礼义”来规定“治”和“乱”。《不苟》言:“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 因此,所谓“善”其实就是“礼义”。。因此,荀子在这里实要表明,人之“善”是后天人为教化学习而来的,是出自人之“伪”,而不是如耳聪目明般生于人之“性”。
基于上述“性”“伪”之分,荀子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性善”的理解。《性恶》言: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这里,荀子明确提出自己对“性善”的理解。在荀子看来,人如能做到“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即人仅依凭生而有的自然朴素之材质而不需要借助后天外在力量就可以实现美利,才可以称之为“性善”。荀子举“目明耳聪”之例显然是要表明:如果人心生发出善的行为就如同耳聪目明般,是人的某种生而本具的能力推动的,并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后天外在的人为力量就可以必然实现,那么就可以说人性是善的。换句话说,如果“性善”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善的行为的出现应该像“明不离目”“聪不离耳”一样,是人之天性的一种自然显现,并且无需任何外在力量就在可以在经验现象中得以完满地展现出来。因此,荀子实要强调,所谓“性善”是指“性”与“善”之间是一种“自然且必然”的关系。当然,在荀子看来,人生而具有的质朴之材质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并不会自然呈现出善,反而是“离其朴”“离其资”,人不会像孟子所言那样自然表现出善的行为来,人之善行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努力才能出现。由是可知,荀子认为性善论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生而具有为善的能力;二是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此为善的能力自然且必然地表现出善行。
对比孟、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们对“性善”的形式内涵的界定是相同的。此共同点即如庄锦章(Kimchong Chong)所言,只有道德修养呈现为一有机过程,并且本有的“质具”能自然成长为为善的能力时,才能将“可以为善”的“质具”视为善*Kimchong Chong, “Xunzi’s Systematic Critique of Men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3(2) (Apr.2003), pp.215-233.。
综上可知,那种把“性善”理解为“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的思想,不符合荀子对“性善”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种“化约式”的理解*廖晓炜对“化约式”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有深入阐述,本文之论述主要参照廖晓炜之阐述。参见廖晓炜:《孟、荀人性论异同重探——由荀子对性善说的批评展开》,《哲学与文化》第41卷第10期,2014年。,即仅仅把“性善”理解为人内在具有某种为善能力的“质具”,而没有注意到孟、荀所言的“性善”还强调人生而具有的为善能力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能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为善。因此,从荀子对“性善”的理解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荀子的人性论蕴含着一种性善思想。
再看第二个问题:在荀子那里,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是否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
一般认为,尽管荀子言心主要强调心的认知功能,不同于孟子强调心的道德功能,但心的认知功能正是人能“化性起伪”的内在根据。学者们把荀子这一思想或概括为“以心治性”*参见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24—228页。,或称之为“心伪论”*参见周德良:《荀子心伪论之诠释与重建》,《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08年第4期。,或定性为“心善”*参见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然而,不少人忽略了另外一点: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治理的对象,心要发挥为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更有甚者,人为恶的原因也在于人之心。
荀子所言的“性恶”并不是主要针对“性”中的欲望、情感而言的,而主要针对“性”是否具有礼义而言的。荀子先肯定礼义为价值之所在,然后针对人并非天生自然具有礼义而判断人性为恶。荀子所谓的“恶”只是一个消极概念,并不是说“性”本身是恶的,而只是说其在天生自然状态本无礼义而易流于恶。基于此,不难理解《性恶》中的这段话: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那么,“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性不知礼义”具体又是指人之什么状态呢?一般认为,荀子“性”的内容包括“情”“欲”和“知”“能”两大方面*荀子对“性”作了“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在荀子看来,凡天生自然、生就如此、表现为素朴之种种即是性。“性”的内容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生而具有的反应(“情”)与需求(“欲”);二是人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知”)和实践能力(“能”)。。“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性不知礼义”显然是指人的一种“知”和“能”的状态,而“知”和“能”显然是指心之知和心知之后表现出来的能。所以,“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性不知礼义”要表达的意思是:人心中天生不具备礼义,人之心亦天生不能认知礼义。如此,荀子实把人之行善或为恶归结为人之“心”:“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
事实上,荀子言“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心进行两重区分:一方面认为心属“性”,一方面认为心属“伪”。*参见何淑静:《孟荀道德实践之理论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第47—68页。何淑静对荀子“心”与“性”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把荀子的心作了“心是性”和“心不是性”两重区分。笔者进一步认为,“心不是性”这一说法是一否定的界说,并没有明确表明当心不是性时心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荀子的思想中,“伪”是与“性”相对的概念,因此,“心不是性”就是指“心属伪”。正是这样一种区分使得荀子的道德哲学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属性的“心”是人沦为恶的原因,属伪的“心”是人成就善的根据,而把属性的“心”转化为属伪的“心”就是“化性起伪”的工夫。
那么,此属性之“心”又是如何导致人为恶的呢?《解蔽》言: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
“未尝不……然而有……”的句式表明:“未尝不”描述的是一种生就如此的自然状态,因而属于荀子所言的“性”这一范畴;“然而有”描述的是只有通过后天人为才能达到的状态,因而属于荀子所言的“伪”这一范畴。由文意可知,在荀子看来,心在“知”的功能上天生自然地表现为“藏两动”之状态,而此“藏两动”之心表现出的认知只是人的本能之知,具有很大局限性。
荀子进一步认为,“藏两动”之心在认知上的局限性就表现在极易为“蔽”所遮障,而不能见“大理”。其说: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解蔽》)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解蔽》)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解蔽》)
心不发动其功能,连白黑都不能区分开来,声音都不能听闻进去,更无法辨别“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等“蔽”。当心为这些“蔽”所遮障时,常常两两为患,往往偏于一隅,而无法认识“道”(礼义)之全体大用。如此,心极易形成一种主观认识上之“心术之公患”,即“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在荀子看来,当“藏两动”之心受“蔽”之遮障,再加上各种情感和欲望影响时,其就不能以礼义为标准做出思考、判断和选择。他说:
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解蔽》)
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解蔽》)
这就是说,情感和欲望之放纵会损伤心之思维和精神。此受损伤之思维和精神在做思考和判断之时,就会表现出左右摇摆和迷惑不定。
荀子进一步指出,当“藏两动”之心之思维和精神表现为左右摇摆和迷惑不定时,就极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他说:
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解蔽》)
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解蔽》)
荀子在这里不断强调,当人之心“内倾”“不定”时,心“不足以决庶理”,其抉择亦“必不当”。一旦心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人就会把它外化为具体的恶的行为,社会也就呈现出混乱的状况。对荀子来说,当人生发出恶的行为时,人之为恶的整个“过程”就得以“完成”,此时之恶就是真正的恶。
综上可知,那些认为荀子之心本具价值意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荀子的心本身就是一个有待治理的对象。荀子言人具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和“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亦只是表明心之认知和实践能力“可以”引导人为善,并不表示心本身就是善的。事实上,对荀子来说,此“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和“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要想把握礼义之道是需要经过后天培养才能实现,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虽然荀子并不认为人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正面价值,但他并不否认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转化此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而使其具有价值。因此,荀子最终还是为人走向善保留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通过后天的“治气养心”以实现心由“藏两动”之状态向“虚壹静”之状态的转化。此“转化”的实质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工夫。而化性起伪并不是要化除人的某种负面天性,而是要转化心的选择机能,即所谓“变心易虑以化顺之”(《儒效》)。具体来说,荀子并不是要化除人的情感欲望,而是要化除人之心表现为“唯利之见”(《荣辱》)的选择之“陋”,给人定出一个以礼义为标准的“求之之道”(《荣辱》),以实现自然欲求与社会价值的合理结合。。“荀子根本否认人与生具有道德资质,或说否认人与生具有任何道德意识及道德动力。‘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同时也是可以知‘污漫淫邪’之质、可以能‘污漫淫邪’之具……荀学中的这些潜能乃被动潜能(passive potency),只是一个接受现实的能力……绝非如孟学中所说的仁义礼智式的本心是一主动潜能(active potency)。”*朱晓海:《荀子之心性论》,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第37页。所以,从荀子否定人之心生而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正面价值看,那种认为荀子的人性论隐含性善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三、问题的结论
通过前文论述,我们发现那些认为荀子人性论中隐含性善思想的学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性善”化约式地理解为主体之人生而具有为善的内在价值根源,二是认为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之心生而本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推动人为善的正面价值。对于第一点,我们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孟、荀对“性善”的理解。孟、荀两人对“性善”形式内涵的理解是一样的,两人都认为“性善”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生而具有为善的能力;二是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此为善的能力自然且必然地表现出善行。在荀子看来,人生而具有的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为善,人之善行只能通过后天学习与努力才能出现。对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对荀子而言,人生而本有之心本身并不具正面价值,反而是有待治理的对象。在荀子看来,在无人为作用的自然状态下,人之心容易呈现出“藏两动”的偏蔽状态,其所生发出来的认知功能不但不能认知礼义,反而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并最终生发出恶的行为来。因此,我们认为,那种认为荀子的人性论隐含性善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何界定荀子的人性论呢?尽管荀子认为人之心既是人沦为恶的原因,也是人成就善的根据,但他认为人在无礼义安置的自然状态下容易倾向于顺人之欲、纵人之情而沦为恶,而成就善则需要后天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如果把“善”和“恶”看作天秤的两端,人更容易向“恶”这端倾斜。荀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人性恶。如果非要给荀子的人性论下一个判定,笔者以为还是称之为“性恶论”更符合荀子之本意。荀子对人性的此种判定的落脚点即在强调圣王教化对人类社会实现正理平治的重要意义*周炽成对荀子的圣王教化思想有深入阐述。参见周炽成:《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以荀子与董仲舒为例》,《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一方面强调人性易流于恶,一方面强调圣王教化成善,此两面即构成了荀子人性论的完整体系。
B222.6
A
1000-7660(2017)06-0120-06
陈 林,湖北黄冈人,哲学博士,(南宁 530003)广西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实现研究”(2013MSZ018);广西财经学院学科群建设培育项目“东盟汉语文化圈文化与经济互动研究”之子项目“儒学与东南亚文化”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