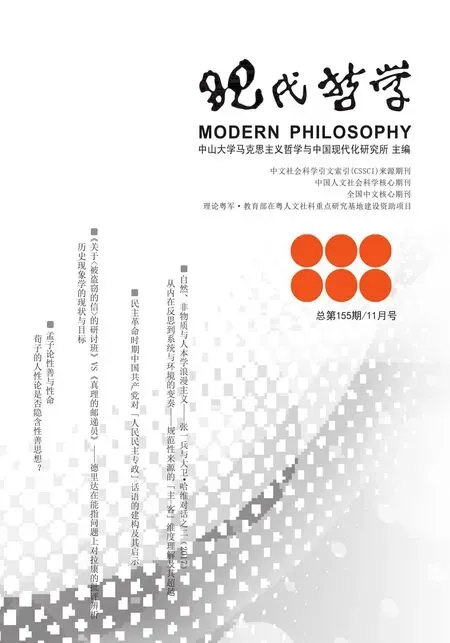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朱庆跃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朱庆跃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包括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了论争与博弈。为了让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及其指导下的“中间道路”是一条岐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何种主义才能将中国引入真正的自由、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主体性力量、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获取真正的自由要选择何种路径等方面给予了理论批判。在理论批判中所积累的诸如高扬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旗帜不动摇、立足具体问题情境以推进理论创新的态度不改变、实行理论批判中差别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方针不丢弃等经验,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及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理论;批判
抗战胜利后,当时国内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除了国共这两大政治势力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并以军事的形式进行斗争之外,广大自由主义者*在卫春回所著的《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序二”中,著名学者郑大华认可和赞同了卫春回从广义层面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界定,即将当时认同宪政、主张自由的人都纳入进去,本文在论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时参考和借鉴了这种思想。相应地,在文中所探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体指那些认同和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不是以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界定标准。也将自己所持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适时转化为建国的政治方案,最典型的就是提出了一条自认为有别于国共两派的“中间道路”。尽管出于反蒋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广大自由主义者采取了团结的态度;但是为了促使其觉醒,也为了让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及其指导下的“中间道路”是一条歧路,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何种主义才能将中国引入真正的自由、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主体性力量、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获取真正的自由要选择何种路径等方面给予了理论批判。今天,从思想史的维度考察1946-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既在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案的科学真理性,从而强有力地回击诸如那种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靠的是军事胜利而非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此类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在于为当下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格局下如何应对沉滓泛起的自由主义等思潮,更加坚定地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一些现实性价值。
一、何种主义才能将中国引入真正的自由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思想理论,和之前的西化派思想一样,更多地是舶来品、是“援西入中”的产物。但不同于前者,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重点进行两个方面调适:一是借用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建国热情高涨的有利时机,将自由主义由原来的一种政治观念和哲学运动转化为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学者顾肃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译林出版社,2013年)专著中,认为自由主义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观念和信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也可以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还可以是一种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二是借鉴当时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世界所出现的自由主义修正潮流(例如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新类型)*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在坚守自由主义理论“内核”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理论“外围”的调整。正是凭借这两个方面的“底气”,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向民众大肆渲染自由主义建国的错误思想。综观这一时期他们的相关言论,他们竭其所能从多维度来正“自由主义”之名、顺“自由主义”之言,以此达到走“中间道路”之事成。
其一,认为自由主义是“进步”的代名词和符号象征。1948年上海《大公报》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强调自由主义不是“空泛的旗帜”、“看风使舵”的舵手。而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可以解释成为“进步主义”,本身内蕴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等基本信念*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93页,第95页,第146—147页。。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另一自由主义者施复亮的认可和赞同。他毫无掩饰地指出,“进步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没有进步,就没有自由主义”*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4页,第516页,第362页。。这些观点的言外之意是,主张自由主义就是追求进步的表现,追求进步就必须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反之,就是倒退、落后的表现。这或多或少蕴含有“道德绑架”或绝对武断的意味。
其二,明确坚持和实践“新”自由主义是当时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趋向,也是中国建立新国家的正确方向。例如,1948年1月天津《大公报》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评价英国工党所实施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国际新趋向,指出其所带来的重大意义在于“给予全世界自由主义者以精神上的振奋,而促进他们联合起来,作更进一步的积极努力的”⑤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93页,第95页,第146—147页。。受这一潮流趋势的影响,当时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张东荪、施复亮、周绶章等,都强调建立新国家需要的不是传统自由主义而是一种“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林建华:《论“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特点》,《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其是在坚守自由、民主“内核”前提下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实行融为一体的“外围”调整。这种“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构建的新国家,充分地“扬”现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长”,而“弃”两种社会形态的“短”,既实现了政治上民主和经济平等,也废除了专制独裁和剥削。“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自由,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取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平等,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合成一条新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是世界各国应走的路,也是中国应走的路!”⑦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4页,第516页,第362页。
其三,指出惟有自由主义才能构建新国家的“本”和思想根基。如张君劢认为自由主义重视“人的发现”,特别是崇尚“理性的意志”,这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本源和哲学基础⑧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93页,第95页,第146—147页。。同时,他还以如何实施好宪政为具体事例,从中外法制史的考察比较中强调只有通过实践自由主义以促使“人民对于他的权利的警觉性”,宪政的第一块基础石方能得以构建并夯实⑨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4页,第516页,第362页。。这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自由主义者希冀通过启蒙以理性立国的进路,在思维逻辑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吻合,呈现出唯理性主义的色彩,即认为旧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源于缺乏理性,相应地务必以理性的恢复和确立以促进新社会的生成。但是,问题在于理性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诸如“构成一个共同体之精神秩序的宗教、道德、价值体系”*秋风:《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7页。以及特别是新社会生产方式的构筑并非仅仅依靠理性就能够完成或实现的。
另外,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还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担负建国指导思想这一问题进行评论。如在《由宪政问题起从比较文化论中国前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中,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的正反面,马克思主义只是个人主义的进一步,本质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民主主义;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解决人权与产权(尤其是豪门资本的问题)这两个密切相联的任务,故建立新国家只能采取“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从而利用此介体将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价值由理想转化为现实。在间接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建国指导性作用的同时,他还直接地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的价值,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变例”,源于其“改采一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社会主义后还保留国家、军队等,这些“与马氏原义甚不相合”*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22页,第346—347页。。相对于张东荪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张君劢、萧公权等自由主义者则完全肯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将中国引入自由的前途中(特别在实现个人自由方面),因为它实质是一种整体或统制、集中主义。如张君劢将苏联的共产主义与英美的民主主义进行比较,指出前者是“唯物的,不承认人性好,而以为人性坏的”,后者“则不管人性好坏,但承认人性是可以讲‘理’的”*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127—128页,第71—72页,第58页。;萧公权强调“正统的社会主义以近代的唯物论为其哲学根据,因此马克斯主义在逻辑上必然否认意志的自由和个人价值”*萧公权:《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世纪评论》2卷5期,1947年8月2日,第7页。。
针对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所持的自由主义建国的错误言论,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因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对此采取迁就或回避的态度,而是给予积极回应。这毕竟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及其实践的现实正当性问题,而且攸关未来的“立国之本”是什么,即以何种主义建立新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批判和深层次的论证。
第一,采取理论比较法,指出相较自由主义而言,坚持科学性、革命批判性和人民性三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和最显著的优越性。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特征的分析,郭沫若以自由民主为例,强调其由于坚持和实践了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性,从而实现了自由民主在理论与事实上的统一。这与当时自由主义者所宣传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明显“泾渭分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呈现出的却是理论与事实上的背离状态。“象苏联那样,人民获得经济平等的国家,岂有没有政治的民主的?假使站在人民的观点上,象美国那样,贫富有天渊的差别……人民没有获得经济的平等,又那能有真正政治的民主?”⑤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22页,第346—347页。讴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特征方面,如伯奇认为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否定了自由经济,否定了资本家的民主,却偏不否定批判精神”⑥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127—128页,第71—72页,第58页。。就当时一些自由主义者声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崇信武力或向两边统治者和革命者同时要自由等错误论调,杜迈之、范承祥、庞欣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既根本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也是对早期自由主义(即反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的自由民主)革命性的消解。“在我们这半殖民地不封建的社会中,承传复杂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是缺乏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主义者的凝固性与积极性的。”⑦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127—128页,第71—72页,第58页。这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征,同时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眼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以抽象的全民性掩盖了浓厚的阶级性。如蔡尚思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当时的苏联为例,认为其“经济是无产阶级共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主持的;所以它的文化也就跟着经济政治而转移,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42页,第416—417页。。潘梓年指出尽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对封建专制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实质终究只是资产阶级,即农业老板和工业老板的民主而非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⑨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42页,第416—417页。。
第二,实施历史考察法,论证自由主义无法担负建立新的中国的历史责任。如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文中,胡绳考察五四以来民主文化运动的实践历程,指出其存在两个弱点:一是脱离中国实际而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文化;二是“文化与人民大众的割离”。*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80页,第417页,第481页。在《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文中,他还以孙中山探索革命的经历作为例,强调其1921年前后在寻求自由民主的路径时由美国转向苏联,就足以表明自由主义不能建立新国家。上述论证在于告诉当时的民众,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被丢入历史的“垃圾堆”里,不在于历史没有给它们机会,而是自身缺乏扮演历史“主角”的能力和水平。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8页。。
第三,运用世情国情分析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新中国既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也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对于前者,如郭沫若指出历史是进化的,自由民主的内涵也伴随着历史的进化而进化,当前之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建立类似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就在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因资本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而畸形为少数人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时代是已经落后了,走在他们前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6页,第59页,第76页,第80页。。对于后者,潘梓年认为当时中国的民众面临着“封建专制的压迫”以及“身受独占资本的这面重枷的巨力压迫”④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80页,第417页,第481页。双重问题,决定了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以及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冯契亦强调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大革命,它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两个特点又必须依存在人民本位这个最根本的特点上,因为“这个民主革命或解放运动,发生于人民世纪,成了人民世纪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相应地经济政治上的革命特点又决定了我们文化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必须以人民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并且“反对以帝王或上帝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也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化”⑤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80页,第417页,第481页。。
除了从上述深层次的理性论证惟有马克思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才能建立新的国家以实现真正的人民自由之外,为了让民众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持思想理论的真实面目,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结合1947前后、1948年中国自由主义的两次亢奋状态,具体分析和揭批了它们的产生背景、实质危害性。如对于内战爆发后,特别是处于白热状态时,自由主义所出现的“高潮”现象,杜迈之认为这在于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内战的实质是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的较量,企图改革现制度来“求治”,这在“客观上正替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扮演着帮闲或帮凶的角色”⑥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6页,第59页,第76页,第80页。。对于1948年内战逐渐明朗化时,自由主义又出现的“热论”,庞欣指出在中国面临一个大变革的前夕抬出“自由主义”这块招牌,更多地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需要,即借自由主义来安抚知识分子恐慌、迟钝和沮丧的心理以及振奋士气人心,也在于安慰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失望和不满⑦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6页,第59页,第76页,第80页。。相应地,它的实质是一种伪自由主义,是假冒为善而实为维护旧秩序的“帮闲帮凶”⑧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6页,第59页,第76页,第80页。。
二、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领导和主体性力量
政治实践活动必然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政治实践活动依靠谁、政治实践活动的方向是什么,特别是政治实践活动为谁服务的问题。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5页。。鉴于此,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领导和主体性力量展开了争论,中国自由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为何以及如何成为领导者、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以及为何成为主体性力量、国共双方为何不能成为领导者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得出了中国自由的真正实现要依靠由自由主义者领导的中间阶层的结论。
关于第一个方面,虽对“自由主义者”的称呼不同*例如,储安平称其为“自由的思想分子”,施存统称其为“中间派”或“自由主义者”,周绶章称其为“自由主义份子”,朱光潜称其为“自由份子”等。,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基本赋予其在实现中国自由民主实践中的领导角色。如储安平认为在忧虑国家前途方面,中国的自由的思想分子不应该有消极的焦愁,而应积极主动地承担“历史上的责任问题”*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40页。。其一,为何能够成为领导者?施存统从当时国内、国际政局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国内政局是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这决定了“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200页。。储安平指出自由的思想分子能成为领导者,不仅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使然”*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9页。,因为国内民众出现了既畏惧共产党的暴力也厌恶国民党的腐化两种极端化趋势,惟有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同上,第40页。。其二,在实践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体现和巩固领导者的地位?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如张东荪主张在联合政府中发挥“平衡与钳制”的作用;储安平强调应该在道德、思想和舆论等方面发力;施存统认为中间派不要局限于发挥“传力机与作业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同上,第310页。。领导作用及其体现方式的多样性探讨,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所进行的建言献策也是多样的。如储安平提出自由主义者要克服“相轻”、“自傲”的“老根性”,要具备看得远、认得清、有气量等政治家所必需的修养,要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等*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8页。。罗隆基则认为自由主义者唯有组建有别于国民党、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方能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因为只有组建中国第三大政党,才可“缓冲国共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215页。。
关于第二个方面,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是否有“中间路线”产生较大歧见,但在是否有“中间阶层”方面总体保持了肯定式的一致。如在《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中,施存统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间阶层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部分,包括新旧两种成分,而新旧两种成分又可分为不同的部分,“今天中国的所谓中间阶层,应当包括民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商从业员,小地主,知识分子以及绝大部分农民”*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14页。。他强调无论是国民党政治集团还是中国共产党所持的主义理论乃至政治路线,都只是体现、维护了国内少数人的利益,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前者代表的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后者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施存统等人提出“中间路线”主张的李平心也指出“第三方面”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因为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但有一定的社会渊源,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历史因缘”*同上,第486—487页。。他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状况为例,强调在既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小农生产在内的小商品生产和宗法家长制的农业自然经济等),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下,深受国际资本和封建势力压迫的民众不可避免地“在数量上,大多数属于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过渡阶层)”*同上,第487页。。在论证“中间阶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中国自由主义者还就自由民主的实现为何要以“中间阶层”为主体性力量进行分析。施存统认为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不是外来恩赐的,而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争取的”*同上,第325页。,只有人民通过自己斗争获得由自己决定的民主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相对于施存统的抽象式论证,李平心的论述较为具体,指出“第三方面”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性力量,是由其自身所具备的优点决定的,即具有能够为民主自由运动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进入觉醒的桥梁、分布广泛的特点易掀起民主自由的巨潮、有利于争民主力量的勃兴等长处*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490页。。总之,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懈余力地论证“中间阶层”这“空泛而模糊的概念”,虽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第98页。,但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他们自己的“私货”:如以此来论证自由主义及其道路方案存在的现实正当合理性,说明自由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企图借用“中间阶层”让自己的理论、主张转变成一种物质力量;用抽象的“全民性”色调来掩盖自身理论及其实践方案的狭隘的“阶级性”本质。
关于第三个方面,对国共双方为何不能成为领导者的分析,实质体现出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通过否定对手从而间接地佐证前两个方面科学性的企图。同时,也折射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激烈性,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其革命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曲折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页。。综合考察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相关言论,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政党的国家立场、政党精神、政党性质和政党形象等层面。如储安平认为共产党“崇奉苏联”的立场,让人担心其努力的意义是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实现,还是为了成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2页。。他还批判共产党的政党精神,认为共产党是个组织严密和过分强调集中的政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同上,第34页。,在其讲究“一致”的统治下,人民很难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国民党统治区域所要解决的是自由民主的“多或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统治区域要解决的是自由民主的“有或无”的问题。他分析了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指出强烈的阶级性致使其不可能体现和维护人民性的自由民主。而孙斯鸣强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相应地“也只有当仁不让,实行共党的一党独裁”*孙斯鸣:《中国政党政治往哪里走?——一党专制乎?两党制乎?多党制乎?》,《世纪评论》1卷16期,1947年4月19日,第9页。,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施存统将“武装政党”这个评语运用到共产党身上,只是“武装”比国民党“小”而已。周鲸文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都是代表少数人的极端性政党,如果说国民党是“庸医”,那么共产党就是不对病的“药”*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551页。。
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性标志是无产阶级是否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就不可能完成。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对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判断预测,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给代表们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反复提醒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要认识到不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我们争领导权,自由资产阶级也会和我们争领导权*《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认识上的未雨绸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面对自由主义者所持的依靠中间阶层的言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对”,就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领导和主体性力量方面对自由主义者开展了如下的批判:
其一,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抹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实现人民自由民主的领导党。如针对自由主义者污蔑中国共产党只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持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统一性。华岗以“石夫”为笔名撰写了《第三方面的新生》,指出中国共产党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解放区由于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广大农民从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不少小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亦从党和解放区里寻找到光明出路,甚至他们中的许多先进分子都愿意“和先进工人阶级并肩作战”而被党吸纳成为“一部分组织成员”*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37页。。针对自由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与法西斯的全能主义相等同的谬论,在《再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文中,杜迈之认为这和过去托派分子的荒谬宣传“如出一辙”;中共过去的实践证明其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因为它通过自己的武力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严格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对现专制独裁政权的一个强力“反动”;在对中共的评价上必须坚持人民利益是否维护和实现为根本的“善”“恶”标准,而不要“抱残守缺地执着于少数的个人政治自由”*同上,第65—66页。。对于自由主义者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毛泽东认为这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在于“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错误在于“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2—1503页。。
其二,揭露了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性,指出自由主义者不具备领导中国实现真正自由民主的品质和能力。如在《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文中,何文俊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评价使用了“自以为是”、“自鸣清高”、“个个自私”等极具“贬义”的词汇。胡绳以“公孙求之”的笔名撰写了《论“第三方面”》一文,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动摇、投机性进行了深刻揭露,评价他们“起伏无常、难得有守贞不贰、全始全终”,要求他们“保持政治节操,甚至比寡妇守节还难得多”*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49页。;强调正是自由这主义者具有动摇、投机性的毛病,导致反动统治势力往往对他们实施“打一下、拉一下”的伎俩*同上,第50页。。他还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思想根源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指出这与他们在思想与生活习惯上“既有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又有从西洋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传统”*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86页。密切相关,明知封建正统观荒谬却还受这种观念的束缚,明知资本主义世界残破万分却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之,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局限性的揭露和分析,并不意味着将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相反,更多地是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错误,从而转变立场,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人民自由民主的实践中。
其三,分析了“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概念对自由主体范围界定的非科学严谨性,明确运用“人民大众”这一概念指称那些担负实现中国民主自由的主体性力量。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者使用的“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所涉及到阶级或阶层的客观存在性并未否定,同时在撰文或作相关报告时也会使用这一概念*以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为例。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在1949年8月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号召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先进的人们要“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但当自由主义者运用这一概念对当时实现中国自由民主的主体性力量进行完整意义的表述,则会表达“质疑”乃至“批判”的态度。
综合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的相关言论,“质疑”或“批判”的根据主要是:第一,认为“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概念将无产阶级排斥在中国自由民主实践的动力之外。“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中到底有哪些阶级或阶层,在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是民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商从业员、小地主、知识分子以及绝大部分农民;二是民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商从业员、小地主、知识分子,不包括绝大部分农民。这两种回答都没有包括中国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无论是自身的特点还是其现实中的实践表现,在当时已充分彰显了其作为推动和实现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基本的动力。第二,指出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表达的只是一种“政治立场”而非“社会身份”,具有极大的抽象、空泛性。如何文俊认为将不同于国共两党政治立场之外的所有人视为中间力量,这实质坚持的是单纯的政治立场划分标准;但政治立场不等同于社会身份,政治立场上的“中间层”不能代表社会身份上的“中间层”,如农村的中间层是中农、城市的中间层是小市民或中小商工业者。“所谓中间团体,他们的政策口号,是代表抽象的‘人民’,不是也不能代表社会的中间层。”*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42页。这实质上表达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相统一作为划分阶级或阶层主要标准的思想。第三,强调自由主义者划分“中间阶层”(或“第三方面”)所坚持的政治标准本身是不科学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如华岗认为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实质上是民主与反民主的较量,而不是所谓的国共政权之争,社会政治层面存在的不是民主力量就是反民主力量,而非自由主义者所分析的存在着“三种力量”,即国国民党力量、共产党力量以及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乔冠华更直接地指出民主和反民主之外可能有“中立”,但“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680页。。基于上述判断根据,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使用“人民大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称)来对中国自由民主实现的主体性力量进行完整意义上的概括。
三、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观。在政治观层级构成中居统摄、支配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要素,对其他要素包括政治理想起到了定向、权变、制衡的作用。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为例,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也依据各自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就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提出诸多设想,如张东荪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施存统的“新资本主义”、萧公权的“自由社会主义”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特别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左玉河、许纪霖都认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来源有二:一是美国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二是英国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前者在20世纪初对中国的影响较大,20世纪中后期后者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同时,许纪霖认为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离不开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而卫春回就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主要思想来源为何是拉斯基思想,从当时中国主要的自由主义者与拉斯基存在教育背景上的渊源关系、拉斯基相关著作在当时中国的译介情况等方面有较为具体的论证。(参见左玉河:《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上述种种设想亦可以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它们的差异只不过在于调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经济平等)过程中两者所采比重和具体方式的不同而已。“自由主义不过是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93页。综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相关言论,政治民主化、经济平等化、军队国家化是这一社会理想在内政的具体呈现。
政治民主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总体上坚持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蓝图设计未来国家的本质制度,同时对这一国家的本质制度在价值层面所体现出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也进行了稍微不同于西方式的“修正”。对于前者,可从当时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获得充分佐证。如张东荪指出未来的中间性政制,在政治方面“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04页。;施存统则明确强调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同上,第299页。。对于后者,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坚守西方自由民主基本价值、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对它们的内涵和形式进行诠释与调整。如就“自由”理念的理解层面,主张尊重个体自由之外也要重视全体自由;坚持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统一性;注重从平等方面理解自由,认为平等是实现自由特别是全体自由的基础*吴恩裕:《自由乎?平等乎?》,《观察》3卷12期,1947年11月15日,第7页。。而就“民主”理念的把握层面,认为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制度,倡导人民本位的政治观;提出代议制这一间接民主形式下也可辅以适当的“直接民主”;认为民主政治是比自由主义更高的一种境界,自由主义只是达到民主的工具*邹文海:《政治民主与自由》,《观察》1卷13期,1946年11月23日,第10页。。就如何体现和反映上述未来国家的本质制度,这一时期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强调应实施由法治、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所支撑的宪政政体。如重视法治上,通过回顾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张君劢指出近代国家的基础就在于“立宪政治”*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54页。,同时认为之所以需要宪法在于来“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各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目的”*同上,第359页。。在分权制衡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如楼邦彦、周鲸文、萧公权等,对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联邦制和单一制政体形式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与分析,指出无论未来中国政府制度以何种形式呈现都需要保持“分权制衡”这一宪政的精义。在主张多党政治上,1948年1月8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明确将“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视为未来民主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五大基本信念之一,就为何要实行多党政治提出了“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是由招标而发生合同关系的”、中国具有幅员辽阔和缺乏现代化基础的国情三个缘由*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94页。。
经济平等化方面:这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所设计的民主社会主义主要经济特征。对于未来社会为何要实行经济平等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平等,自由主义者们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和论述。对于前者,除深受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以及对当时两种主要社会形态各自优劣比较鉴别的结果外,张东荪认为这有助于国内呈现一个“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的良好状态,在国际上也可以让美苏两个大国放心,从而较为有利地获取这两个大国的大量援助*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04页。。而周绶章以心物一元论为哲学基础,着力探讨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的关系,分析实行经济平等的重要性。他强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没有政治自由则经济平等难以持久保持,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到解放;没有经济平等则政治自由根基不会坚实,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处于匮乏状态*同上,第515页。。对于后者,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总体上希冀凭借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其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再采取计划的调节手段来实现经济平等。如蒋硕杰指出私有制特别是独占资本导致独占利润的存在和社会分配不均现象的加剧,随之也造成社会的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滋长。“无论自由主义者,抑社会主义者,对独占式的资本主义没有不认为不当的。”*蒋硕杰:《经济制度之选择》,《新路》1卷3期,1948年5月29日,第8页。吴恩裕则从人类的本性高度论证实施计划经济的必要性,指出“‘计划的’社会乃是人性的要求”*吴恩裕:《由人性上证明计划社会的必要》,《新路》1卷9期,1948年7月1日,第12页。。可见,在思想认识上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分配公道和平等问题,并适时地由古典自由主义的“交换正义观”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观”*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0页。;但不容否定的是,这种经济平等的设想依然被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方案,在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相联系中到底能否奏效令人怀疑。
军队国家化方面: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旨在让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远离政治,从而防止军队成为政治集团或政党独裁的工具*崔三常:《“军队国家化”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语境》,《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11期,第58页。,也在于在最终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受西方“军队国家化”思想的影响,在未来社会的设计上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时还对其所谓的“合理性”进行阐释和分析。施存统以近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实践经验作为参考标准,强调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允许“武装政党”的存在,而对照当时的中国却有两个武装政党,很明显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罗隆基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在一个国家只要政党保持武力,这个国家就绝对不民主,因为“民主的重要运动是‘票柜’代替‘疆场’,‘选举’代替‘战争’”*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214页。。另外,就如何促进“军队国家化”理念转变为一种现实,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进行了思考。如储安平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应在这个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即其应当不宜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而应该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在此基础上“由种种合法的程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24页。。在《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一文中,罗隆基详细列出了各种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方案,并对它们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214页。。
抗战胜利前后,与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包括自由主义者)纷纷提出构建新国家的设想一样,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党的“七大”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即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来实现人民的真正民主自由。相较之前,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践探索,还是其话语宣传方面都有了极大改变。如在实践探索上,之前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谋划,这一时期则集中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计,体现为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升到党的基本纲领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实际,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进行具体化;就新民主主义社会怎么样去建设以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行初步探索。在话语宣传上,改变过去被动、克制的态度,呈现出“由内及外,从党内和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的态势*蒋积伟:《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现代哲学》2016年第6期,第36页。。另外,就自由主义者在当时所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因统一战线和其内容、形式上含有“社会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色彩而给予沉默、附和的态度。相反,为了让民众真正地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民主主义社会的差异性,特别是在比较中深刻地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案的科学真理性,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
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民主化设想,主要集中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质以及分析自由主义者对政党政治的错误理解两个方面。对于前者,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非社会主义的民主,尽管资本主义的民主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上,尤其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毕竟与之前剥削阶级社会的民主一样都是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它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体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如邓初民将民主分成旧型和新型两种,明确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依然是旧型的民主,因为它是“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严重分离的现象,即表面上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给广大人类以民主的权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民未必都能享有,如在法律上规定出版的自由,而在实际上不给以出版的纸张及印刷等都是明显的佐证”*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页。。对于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认为其犯了名与实、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错误,过分追求名与形式,即一味地以政党数量的多少作为判断是否民主的标准,没有从政党本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层面去认识民主政治的本质。如郭沫若批自由主义者是惟名论者,“说民主吧,便死含着一个英美政治形态,以为至少非两大政党对立不足以为民主”*同上,第316页。;杜微认为“英美社会有阶级,人民利益不同,所以产生多党,多党并存,形式民主,内容不一定民主”*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79页。。这一时期广大民众正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民主政治化的批判,再加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亲自参加政治实践,逐渐充分感受到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真正坚持了内容与形式、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批判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平等化设想,主要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经济平等化(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化(资本主义)并重的思想,以及否定了自由主义者为推行经济平等化所设计的具体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对于前者,潘梓年、范承祥、庞欣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依据,指出将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揉合在一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潘梓年斥责自由主义者的相关思想是“空洞的玄理”或“玄虚”,强调“政治与经济绝对分割不开,经济上有了民主决不会政治上还不民主,政治不民主决不会在经济上民主起来”*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412页。。范承祥、庞欣认为硬生生地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的主张是“受了外国(特别是英美两国)的伪自由主义者的流毒”,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自成一整体并且有各自的具体内容,两个历史范畴在逻辑上是不能拿来相提并论的*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78—79页。。这表明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经济平等化(社会主义)与政治民主化(资本主义)并重思想内部所存在困境,而此困境是自由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一是所推行的经济平等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抽象的自由平等原则相违背,这种矛盾如何解决?二是所实行的政治平等(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在政治制度上限制权力来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削弱或消灭造成社会现实不平等的经济根源,这就面临着一个政治层面如何为经济平等化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的问题。对于后者,何文俊指出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英国工党社会经济政策既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无迂回到社会主义之意,其实质“不过是保持资本主义的方法之一而已”*同上,第44页。。范承祥则重点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所吹捧的“混合经济制度”,强调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的不同经济制度在性质、基本结构上都是有严格界限的,彼此不能混合使用;另外,这种“混合经济制度”思想一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家弥尔就玄想过,毫无创新*同上,第79页。;最后,他给“混合经济制度”一个总体性评价是“意图一新劳苦大众的耳目,缓和一下战后劳苦大众要求公平的情绪而已”*同上,第79页。。这意味着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或多或少地认识到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即所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并不代表所有制本身实质的改变;一种所有制不管其采取多少实现形式,这些实现形式最终还是为特定的所有制服务的。
批判自由主义者的军队国家化设想。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促进国内和平进程、团结广大自由主义人士,中国共产党在军队问题上做出让步,改变之前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国家化”阴谋而提出的首要进行政治民主化的主张,代之以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的思想。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这不意味着在原则方面完全认同自由主义者的相关思想。从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军队“化”到何种类型的国家中、什么样的军队才能“化”入国家中,以及如何实行军队国家化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可以明显发现两者有本质差异。在军队“化”到何种类型的国家方面,针对自由主义者一味地强调抽象层面的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指出国家没有抽象层面而只有现实具体的,军队要化到民主的国家中而非专制的国家中。如1946年1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的社论,明确“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这就是说,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在什么样的军队才能“化”入国家中,突出只有人民性的军队才能国家化,非人民性军队首先务必要将其转化为人民性的军队。如胡乔木指出国家化军队与非国家化军队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军队,更重要的在于是否从属于人民、与人民相结合;他认为只有人民性的军队才能解决兵源军费问题,才能内部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和自觉的纪律,才能真正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促进国内的民主和平*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141页。。在1946年谈判期间,周恩来就军事改革方面所提的三点意见十二项办法中,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军队要属于人民”,为此要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46页。。而在如何实行军队国家化方面,无论周恩来提到的包括成立委员会以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等在内的十二项办法,还是1946年初与国民党达成军队国家化政协决议案中所开列的整军原则、以政治军办法、整编办法,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此的真心诚意和务实推进。但对自由主义者所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要多承担责任这类建议,共产党明确给予反对,强调一定要按照合理和平等以及真民主的原则实施。“如果企图按照这种不合理、不平等(也即违反民主的原则、维持国民党一党的特权)的方法来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那就不能得到‘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
四、实现真正的自由要选择何种路径
就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方面,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设想,实质上就是一种改良方案,因为它是“从现代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思性来看资本主义”*张世保:《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代西化思潮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即企图吸纳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来弥补资本主义的不足。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方案是如何贯彻和落实改良的一种表现,那么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还就为什么要选择改良、现实中有无改良的可能进行了论述。
就为什么要选择改良作为实现真正自由的路径方面:考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的相关言论,他们对改良的“正名”不可不谓是多维度的,体现出他们的“用心良苦”。如胡适就从现代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和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等维度,论述改良的必要性。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包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并且其是自由主义的第四个意义*耿云志编:《胡适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3—754页。,强调近代以来民主主义已经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将进步更多地归结为“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同上,第758页。。这种论证思路为当时的其他自由主义者如吴恩裕、李平心等所认可和遵循。吴恩裕明确提出民主政治本质是“同意的政治”,而同意的政治就是“这种治理由人民所同意的治理”*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77页。;李平心指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政争,但是政争应“出发于正大光明的风度”、恪守“原则道义”,否则一味地以暴力等方式只能“暴露自家的阴险猥琐面貌”和“带坏国家纲纪和社会人心”*同上,第492页。。相对于胡适等人注重自由民主理论本身逻辑演绎式的思考,张东荪从中国历史实践的角度探讨改良的必要性,强调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革中唯有政府是一个压榨民众机关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始终未能进入近世文明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树立和实践改良的理念,彻底改变那种认为“天下是打了得来的,所以一切都视如私产”*同上,第213页。的错误思想。而施存统从改良带来的积极性结果进行论证,认为只有实施改良,建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才能给中国现代化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才能“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而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以整个儿的中国作美苏的桥梁”*同上,第319页。。在对改良进行“正名”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还大肆指责或污蔑“革命”等非改良方式。如胡适认为极权政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全体拥护急进而骤变的革命”*耿云志编:《胡适卷》,第757页。,这种革命以“划一”为标准严重地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以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为证强调其必然带来“暴力专制政治”*耿云志编:《胡适卷》,第753页。。
就现实中有无改良的可能性方面:由于一切必然性的出发点皆是一种可能性,即必然性是由现实中的可能性在具备相关的条件后转化而来的*陈明兆、邓世穆、林之满:《必然性与可能性探要》,《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第44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现实可能性也难以讨论历史必然性的问题。鉴于此,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十分重视现实中有无改良可能性的分析。如储安平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探讨现实中改良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在国际层面,他认为美国希望中国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为了这个“安定”的结果,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为既要求中国有“一个强有力而足以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19页。,又希望国家出现大量的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自由主义力量,从而对中央政府实现制衡;在国内层面,他强调二三十年来的内战再加上八年抗战导致国力民力已处于极度凋敝状态,休养生息、和平建设成为民众的首选*同上,第23页。。这种国际状况和国内现实相结合的论证思路,在施存统那里也得到充分体现,只不过具体的论证内容有所差异而已,实质上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现实中存在着改良的大量可能性因素。如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中,施存统指出国际的可能性在于美苏矛盾已缓和,全世界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等;而国内的可能性体现在国内大多数人特别是中间阶层厌恶内战、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上级军官对战争前途已失去信心、国民党政府已站在反动和反人民的方面、国内财政已处危机状态、中共的力量还不能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等五个方面*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197—198页。。另外,为了让人们相信改良可能性的确在现实中存在,施存统、张东荪、周鲸文等强调1946年的政协路线本质上就是一条介于国共之间的以和平改良为手段的中间路线。可见,对改良现实可能性的论证,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自身的领导责任寻找到合理性依据,在他们看来只有自由主义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促使现实可能性向历史必然性的转化。至此三者的相互联系使自由主义者的建立新国家的方案以“自圆其说”形式呈现出来,从而也更带有浓厚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在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积极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案的实践,除了是对自由主义者所持民主社会主义设想的一种直接驳斥,实质上也间接回击了当时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改良路径。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案更多地是“把现代性文化放在一个被反思的位置上”*张世保:《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代西化思潮研究》,第254页。,并且突出了中国现代性的确立需通过革命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前提。另外,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改良路径还进行了针锋相对式地批判,在此基础上大力辩护了“革命”的正当合理性。
批判“改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方面:如针对有的自由主义者将和平改良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的主要特征,胡乔木给予了否定,指出衡量是否是真正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标准在于是否有广大民众的参加*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132页。;斗争方式是否改良,关键还要看反民主的力量是否经常地以一个武装力量的姿态长时期的出现*同上,第130页。;即使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争自由民主的斗争也不是一味以和平改良的形式进行的,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常轨”未形成之前同样经历过武装斗争*同上,第132页。。针对一些自由主义者通过指责中国历史中的农民革命实践来间接佐证改良必要性的论调,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回应。如对于《大公报》编辑王芸生否定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作用而将其视为是争“正统”、“道统”的错误思想,郭沫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在于“打倒‘正统’、‘道统’是糖衣,取消革命是核心。取消革命也是维持‘法统’,也就是‘只许变,不许乱’的《大公报》的一贯的传统”*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341页。。对于自由主义者散布的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破坏了和平改良的政治斗争规则从而造成社会纷乱的错误言论,胡乔木据理力争,强调“不是因为人民不懂政治斗争的规则,而是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根本不让中国人民有从事正规的政治斗争的可能”*同上,第131页。。对于自由主义者以现实中存在中间路线来论证改良的可能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回应,明确现实政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中间路线”,只存在民主与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选择。如陆一远指出历史上任何政治路线只有一时一地是非善恶之分,并无所谓左右之别、中间路线所依据的中间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无确定的基础和社会关系上无独特的性格等,这决定了中间路线不论在实际还是理论上都无立足和存在的根据,内容上也是空洞的、机会主义的*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45—49页。。乔冠华联系1946-1948年中国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就中间路线是否存在进行考察分析,指出1946年中间路线只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到1947年已经破产,1948年则“简直变成了一种反动阴谋的护符,一种加括弧的中间路线”*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682页。。另外,针对施存统将政协路线等同于中间路线以证明中间路线存在的思想,苏平批评其错误在于把政治路线和实现政治路线的手段相混淆,明确当时中国只存在“走政协的民主路线和反政协的反动路线”这两条政治路线而并无第三条的中间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实践的是政协的民主路线,只是在实现路线的方式上由原来的和平方式被迫向武装对抗的方式转化而已*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52—53页。。
在辩护 “革命”的正当合理性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自由主义者所持的以和平改良为主要特征的中间道路的同时,强调真正自由的实现务必要坚持和实践以彻底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为了让广大人民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这条革命路线,重点对为何要采取革命的方式、革命的对象及其目的是什么进行充分论证。就为何要采取革命的方式,潘梓年认为当前中国民众深受封建专制和独占资本的双重压迫,要让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就必须解除这些枷锁*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418页。。庞欣强调革命固然对社会生产力、一般文化水准及人口质量性能方面有危害性,但是评价革命时一定要从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结果来看,即原因方面要看是否是消除一定社会制度下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的迫不得已的手段,结果方面要看是否带来了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束缚了社会生产力*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77页。。在1949年革命即将胜利前夕,针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深受艾奇逊唯心史观的影响*自由主义者深受艾奇逊唯心史观的影响,即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1页。。就革命的对象及其目的是什么方面,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强调革命就是要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命”,就是要建立一个促进和实现民众真正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胡绳在《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文中,同样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两点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基本内容,而为其基本目标”*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2册,辽宁大学,1982年,第21页。,指出前者就是要推翻专制主义统治的根、后者在于获得民族的真正独立。“这两点不实现,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化是断不可能成功的。”*同上,第21页。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建国方案最终被历史淘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理论自身与社会现实有巨大的异质之外,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的理论批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些理性而有力的批判,促使人们对自由主义有了较为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并最终作出了“抛弃”的回答。回顾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实践,可以发现里面蕴含着许多对当前如何进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及怎么样更好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性价值。
第一,高扬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旗帜不动摇。自由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尽管西方意识形态往往以自由民主为标榜,但自由民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从不缺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及其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践追求,不仅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式继承,更是对其的科学性超越。“马克思也是从资本主义谈起,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展开了论述,这是因为如果不对世界变化本身必然性的存在和结果进行彻底的解析,理论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刘乃源:《近代自由主义发展与马克思的批判及超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年,第151页。考察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就会发现正因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其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才占领了理论批判的制高点,拥有了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在当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中,一定要将自由民主视为社会主义重要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武器来对西方自由主义所构成的挑战进行积极回应;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务必坚持阶级性和人民性、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原则,对自由民主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开拓式创新。
第二,立足具体问题情境以推进理论创新的态度不改变。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平等更多地持抽象、形式层面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抽象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相统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剖析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人民大众自由民主难以实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化解决方案。这些思考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其所具有的“接地气”特质也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认可。这告诉我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成为主导乃至主流性意识形态,根本取决于其能否发现并破解中国不同时期、阶段的具体问题情境;而自身能否实现创新发展,也在于是否始终坚持以中国不同时期、阶段的具体问题情境破解实践难题。
第三,实行理论批判中差别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方针不丢弃。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式是多样复杂的,除了自由主义之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挑战的还有国民党的“伪三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与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所采取的彻底批判的方针不同,对当时自由主义所构成的挑战总体是引导、教育式的批判;如果说对自由主义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思想成分采取的是“反击”,那么对文化层面的自由主义则开展了“对话”。另外,还实行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团结教育密切结合的政策。“中共对这些典型人物的重炮轰击,并不等于中共对他们个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只要有一线可能,中共团结、争取的方针都会积极实施。这是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互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不管是对待王芸生还是对待胡适,都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曹建坤:《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6页。在坚持“差别性”的同时也坚持“辩证法”,即积极地“扬弃”自由主义,吸纳其有关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思想文化自由与政治自由、自由与民主和平等之间关系方面的合理性成分。上述理论批判中坚持差别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方针,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B27
A
1000-7660(2017)06-0033-15
朱庆跃,安徽含山人,(淮北 235000)淮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论成研究”(gxypZD2016407)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