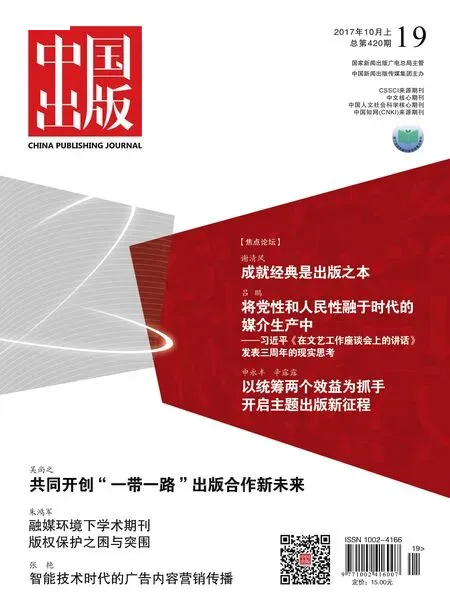公共政策传播中传统纸媒理论战线作用研究
□文│许 磊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本质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针对社会转型问题,为调节社会价值矛盾、避免社会价值冲突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公共政策旨在为“公义”服务,因此,公共政策满意度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文化素养的不断提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及制定过程的意愿逐渐增强。但我国公民的民主能力依然较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学养和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不高,易对公共政策进行误读,并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下被议程设置“反控”现象误导。从从业人员资质和出版内容的深度来看,新媒体目前无法承担培养公民民主能力的重任。因此,传统纸媒应当仁不让地承担培养公民民主能力的责任,通过构建理论战线来深度解读公共政策,深度回应公众的疑问,引导社会价值形成“公义”,提升公共政策满意度。
一、深度回应:公共政策传播中传统纸媒理论战线的基本作用
公共政策转型中,传统纸媒除了应该发挥深度报道的优势外,还应该从专业理论视角来深化解读公共政策,并依据理论逻辑来深度回应公众的质疑,从而潜移默化地提升公众的理论素养,培养公民科学分析公共政策的能力。
1.政策宣传及深化解读
我国传统纸媒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政策宣传的任务。194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就明确指出党报要成为“党政喉舌”和“人民的喉舌”。[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传统纸媒虽然历经政策流变,但其政策宣传作用始终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社会多元价值的出现和公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得到不断的发展,对于公共政策的内容和制定过程不再以执行为落脚点,满足于“知其然”,还立足于政治参与,要求“知其所以然”。由于新媒体平台大多不具有权威性且发布的信息多为转载,因此,传统纸媒应发挥权威媒体作用,利用采访权和直接接触政府信息来源的优势,除了深度报道公共政策内容,还应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学者,从专业的理论层面深化解读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过程,依据理论逻辑来科学预测其影响,从而正确引导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及其影响趋势的认识,指导公民基于公共政策的实践,进一步巩固传统纸媒的权威地位,培养公民在理论框架内对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为公民民主能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2.对公众的深度回应
对公众的深度回应就是要从“隐性回应”到“显性回应”,从“事实回应”到“事实回应+理论回应”。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传统纸媒从未忽视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质疑与回应。以《人民日报》为例,它每天收到的批评、控诉和揭发性信件约占总来信的1/3,没有公开发表的信件也得到了编辑部的重视,甚至成为公共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2]公共政策制定者通过政策调整对公民的质疑进行“隐性回应”,并通过媒体发布政策内容,进行“事实回应”。然而,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深化落实和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回应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提升公共政策满意度的需要。公民需要的回应,是在政府提供充足的信息、实现信息对称的基础上,以协商姿态进行的平等回应。因此,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发挥传统纸媒的版面优势,以“协商”而非“告知”的姿态,及时、高效地对公民的质疑给予“显性回应”。在回应方式上,从法学、行政学、逻辑学等角度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多点定位,通过专业知识及其逻辑框架的应用,以专家的视角和恳切的态度回应公民对公共政策所涉及问题的质疑,询问公民的意见,进行“事实回应+理论回应”,增强回应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减少甚至消除公民的质疑,提高公共政策满意度。
二、风险防控:公共政策传播中传统纸媒理论战线的本质要求
我国公共政策转型中的风险分为碎片化阅读易造成对政策的误读、议程设置“反控”误解和无效讨论导致的“公义”难以形成。传统纸媒要构建理论战线,引导公民理性解读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政策内容和制定过程,引导“公义”的形成。
1.防止公民碎片化阅读易造成对政策的误读
传统纸媒的理论战线作用首先体现为要防止公民碎片化阅读易造成对政策的误读。公共政策的议题程置和内容制定是多学科协作的系统工程,对它的科学解读也需要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新媒体环境下,公民的碎片化阅读获得的是零散的信息,而非完整的知识体系。此外,这种“碎片化”表现为信息的碎片化和阅读时间的碎片化,使得公民难以对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其结论和反应的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专业知识系统是无法自我生成的,需要通过学习来建构。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除了引导公民阅读专著,还应该发挥传统纸媒的权威性优势和版面优势,为公民提供关于公共政策的更加翔实的信息和理论知识,提升公民的理性思考能力,提高公共政策的宣传效率。
2.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议程设置“反控”的误解
传统纸媒的理论战线作用还体现为要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议程设置“反控”的误解。公共政策的议题程置和内容制定的系统性决定了其内部信息的复杂性和信息收集的长期性。这些信息和信息收集工作如果不能通过权威纸媒及时公开,则可能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下,被公民误以为是新媒体平台上议程设置“反控”的成果。如2013年11月正式出台“单独二孩政策”,被误以为是在2013年5月张艺谋涉嫌“超生”事件后,经新媒体发酵而引发议程设置的成果。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我国数家官方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委托,就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开展研究。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已经开展了“单独二孩政策”的试点工作。[3]因此,我国传统纸媒应充分发挥权威媒体的作用,及时、全面地报道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相关工作,争取舆论引导权,确保公民对公共政策具有正确的认识。
3.防控无效“讨论”,引导形成“公义”
传统纸媒的理论战线作用要引导议题形成“公义”。“公义”是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概念,是公民在“众义”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和共同价值理念的共识。在多元价值共存的时代,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内容制定要在“众义”中建构“公义”。在新媒体平台,公民往往由于没有明确的共同价值的引导,因此难以形成“公义”或形成“公义”的效率较低,经常表现为没有核心观点和结果的“讨论”,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利于政治文明建设。伯纳德·科恩认为:“大多数时间里,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4]因此,我国传统纸媒应该对公共政策的价值进行“理论+事实”的阐释,引导公民在一定价值理论框架内就如何形成“公义”进行多轮讨论,最终发布“公义”的内容并监督“公义”的落实。
三、系统强化:公共政策传播中传统纸媒理论战线的生机保障
我国传统纸媒始终为公共政策传播发挥坚实的理论战线作用,但仍要不断引进“源头活水”,从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建设中不断提升自我品牌质量,从人才引进和提升中保证传统纸媒事业始终拥有具有革新眼光的专业人才,不断深化栏目和内容改革,革新自我面貌,才能永葆生机,站在时代的前沿。
1.加强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建设
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过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我国传统纸媒应加强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建设,确保以下目标的实现:①要以理论战线为竞争策略,在全媒体格局中吸引日益致力“深挖”信息的我国公民走上理论深化学习的轨道,为公民提供正确解读和深化理解公共政策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通过长期的理论板块建设提升传统纸媒的品牌效应和权威性,以理论专业性区别于其他媒体,推动我国传统纸媒的专业化发展;②要以理论战线为公共政策的传播质量保驾护航,将纸媒作为公共政策理性协商的平台,致力于通过长期的理论知识普及培养公民的民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提供理性的沟通渠道,以传统纸媒的力量来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确保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③要着眼国际,从全球视角研究我国与他国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制度逻辑,不但要充分研究我国现行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逻辑内涵和制度走向,还要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行政策的逻辑一致性与冲突性,更要对我国公共政策的理论弱点进行弥补和修正,增强理论系统内部的安全性。
2.提升人才队伍的复合式建设
在传统纸媒的人才队伍建设中,首先要培养和选拔政策解读和理论深化人才。我国传统纸媒要发挥理论战线的作用,从理论上正确和深化解读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的传播质量,就需要提升传统纸媒从业者队伍的理论素养。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通过现有从业者的个体或集体学习提升从业者的理论能力,并以竞赛和奖励的方式激励传统纸媒从业者将学习延续下去,如人民日报社连续多年以竞赛形式,鼓励编辑和记者提高业务能力和理论素养。我国既有传统纸媒从业者的政策解读和理论深化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直接转化为传统纸媒内容和工作方式的提升,是最快捷、有效的传统纸媒理论战线提升方法,能够在保证公共政策理论解读和深化的基础上,降低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提高传统纸媒集团的经营效率。
二是在人才招聘和选拔中,对具有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进行重点关注,改革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从而提升我国传统纸媒的理论战线构建能力。随着我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内容制定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其精准解读和准确回应则成为摆在媒体人面前的难题。我国传统纸媒应在人才招聘和选拔中着重寻找具有较强理论能力的人才,组建多学科理论分析小组,通过多学科对同一公共政策的精准解读,提高我国传统纸媒的政策解读质量,并对读者的质疑给予专业学科的回应。
在传统纸媒的人才队伍建设中还要培养和选拔大众传媒和理论普及人才。随着传统纸媒由精英消费品向大众消费品转变,其服务就应以大众的认识能力为基础,提升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有效性。我国传统纸媒在公共政策的传播中,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公民的知识结构相对单一,以应用型知识为主、理论型知识不足的现状,选拔和培养大众传媒和理论普及人才,解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和内容制定的复杂的知识系统,以平实化、生活化、应用型的文字和案例对公共政策的内容、实践形式和可能的影响进行解读,拉近公民与传统纸媒、公共政策的距离,提升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提升公共政策的传播质量。这种大众传媒和理论普及人才应是复合型人才,既对大众传媒的传播机理具有足够的知识,能够通过大众传媒的理论在传统纸媒的应用,实现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在“二次传播”中的最大效能,提高公共政策的整体传播效率,又能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进行平实化、生活化、应用性的转化,达到加强公民的理论水平和提高公民应用能力的目的。
3.现有理论栏目的内容改革
从长远看,传统纸媒的理论战线以专业化、综合化的纸媒为平台,能够在公共政策的深化理解上起到明显的作用,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整体提升。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公民的公共政策理论能力不强,导致公民认为专业政治期刊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差,其受众范围较小,无法实现公共政策有效传播的目的。因此,从具有一定受众的现有传统纸媒的理论栏目的内容改革着手是可尝试的路径。我国传统纸媒在公共政策宣传中的理论栏目内容应该兼具以下特点:①深入浅出的普适性,将晦涩的理论知识与公民生活经验结合,确保复杂的公共政策及其制定理论能被公民接受和吸收,内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能力,能对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分析;②与时俱进的时效性,在理论内容设置上应与实时发生的公共政策议程相关,吸引读者关注理论内容,并以公共政策实例提升公民的理论应用能力;③高屋建瓴的前瞻性,理论栏目涉及的内容应着眼于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并利用理论知识对公共政策连续性的内在机理及现实联系进行深化解读,帮助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进行科学预判,用理论指导公民的实践活动。
四、结论
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提高,通过媒体对公民进行理论知识普及成为了一项任重道远又势在必行的工作。我国传统纸媒具有长期承担理论战线建设工作的传统,并且在长期的公共政策传播中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受众。因此,我国传统纸媒在新形势下进行理论的深化学习和人才、栏目的改革,以此来潜移默化地改变公民阅读习惯和能力,不断提升理论能力和民主能力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