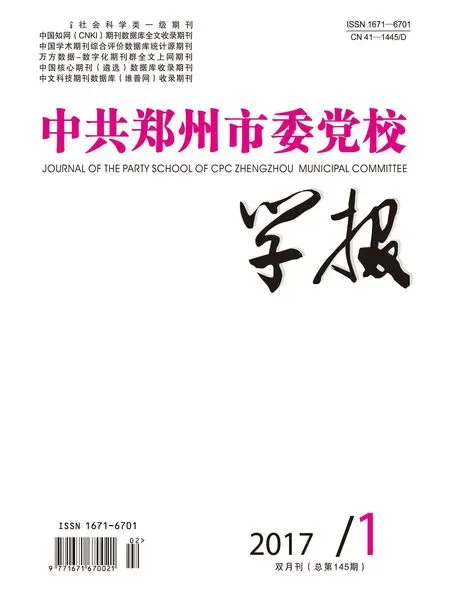试论《孙子兵法》团队管理思想中的人本理性特征
赵庆营
(中共河南省委 办公厅,河南 郑州 450000)
试论《孙子兵法》团队管理思想中的人本理性特征
赵庆营
(中共河南省委 办公厅,河南 郑州 450000)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其核心就是人本理性逐步成为主流。《孙子兵法》的文化立场在当时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神中心主义的先进文化,也是春秋时期萌芽的人本中心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而相对于儒道等政治哲学层面的文化,《孙子兵法》则率先把这种哲学层面的文化应用到实际操作领域。《孙子兵法》的团队管理要素确定了君、将、卒三要素,剔除了神中心主义的神和天意等旧思想。在具体任务的实际操作中,强调主体性、目标性和效率性三原则,正是这种把先进文化彻底贯彻到实际操作中的探索,才奠定了《孙子兵法》作为兵经的地位,并在后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得到广泛认同。
《孙子兵法》;团队管理;人本理性;要素层面;原则维度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齐国军事家孙武所著,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所重视。孙子,名武,字长卿,生卒年不详。《孙子兵法》中的军队统御思想,是当时最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以前的思想,具有突出的超前性和比较优势,并成为后世典范。《孙子兵法》的精髓在于,他把“人”这一要素作为思考活动的核心,取代了夏商以及西周以来把神的旨意作为决策主要依据的现状,体现了高度自觉的人本理性。孙子的思想是对其之前和当时神中心主义的反叛,其人本理性的精神,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军事实践中形成了巨大的时代比较优势,而且对今天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还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孙子思想是春秋时期萌芽的人本中心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上古文明始于夏朝。夏商时期刚刚脱离原始社会,对自然的敬畏还没有摆脱图腾的崇拜。如《史记·夏本纪》就指出其帝王“好方鬼神”。而据称,夏朝最后一个帝王夏桀就“自比子曰”,他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从历史的角度看,夏桀的话并非是简单的狂妄之语,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反映,即把神的意旨作为决策的依据。这种思维模式,到商朝还保留着。如商朝刚建立时遇到大旱,商汤“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显然,商汤虽然是上古明君,但他的决策还是依赖于祈福于上帝的。夏商时期的政权决策可以概括成为“神中心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的经济阶层的兴起和对周王朝中央政权的挑战,问鼎之事频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转向势在必行。西周之初,以君主的“德”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开始了以现实中的“人德”对夏商时期“神中心”的转变。但思想的改造毕竟是缓慢的。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统治阶层的各方面力量,逐渐认识到神中心主义无非是一个幌子,现实中的“人德”,或者叫人本理性才是决胜的关键。这个认识,到春秋末期在知识精英中已成为了一个共识。比如,《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在论及什么是智慧的时候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其罗列的诸多观点,已经没有了上天和神等层面的印记。又如孔子论治理天下的依靠时认为人才是根本,“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可见,孙子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属于百家之一,但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罢了。因此,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的逻辑去理解《孙子兵法》的智慧。
二、《孙子兵法》人本理性的管理要素层面
如果说对于人本理性的讨论,儒道思想还主要侧重在政治和伦理学的层面,那么孙子则是把人本理性思维方式最先嵌入了实际的操作之中。孙子在论述战争的过程中,把人本理性彻底地贯彻到各个环节,没有给神主义的非理性留下一点空间。通观《孙子兵法》全书的管理要素,孙子基本上把它分为君、将、卒三个层面的要素。从现代管理学的视角看,这三个层次中君的层面,相当于高端决策层;将的层面则相当于中层管理层;卒的层面则对应为一线的执行层。对这三个要素的讨论,孙子保持了自觉的人本理性,没有涉及神维度。
1.以“道”为标准讨论为君的必要条件。君在整个活动系统中,是一个幕后的决定者。因为他“是一国的所有者,他根据自己的喜好、观点、才能选择文臣武将治理国家,而文臣武将却极少有选择君的余地”[1]。孙子指出,君要善于用将,要善于授权。提出君要把握全局,但是具体战争则要授权于将军,不能干扰。所谓“受命于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和“将能而君不御”的理念。关于什么样的君是有道的,孙子跳出了夏商周以来影响最大的“君权神授”模式,提出“有道”这样一个理性的概念。什么是有道的君,是那种能够“修道保法”、能够“令民与上同意”的君。这是因为孙子看到真正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上天的保护。这种完全不依靠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在当时是十分难能的。即使放在今天,也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做到。
2.以“知”为标准讨论选将的必要条件。孙子高度重视将在团队活动中的作用。认为好的将领是“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将与君的关系,孙子指出,如果君主能够授权信任,则能胜,否则必败,提出将“听吾计,用之则胜;不听吾计,用之必败”,作为将择君去留的依据。这就把君臣关系完全理性化,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愚忠局限。而对于一个将领的素质,孙子也提出了明确的理性标准。在《计篇》中,孙子明确提出了智、信、仁、勇、严这五个为将之德。这里的智,是指将领对军事活动的判断力;信则指的是将领的职业操守,对于君主的信用,君主把军国大事授予之后,将领要鞠躬尽瘁;仁则是对待下级和士兵的态度,这是作为一个将领如何凝聚军心的一个原则;勇则是临危的决断力和面对挫折的抗打击能力;严则是身体力行和约束下属部卒的能力。在君臣关系层面上,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作为一名良将,作为国之宝,不能盲从君主的指令,而是根据战场实情决定作战与否,不应计较个人得失安危。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孙子对一个将领所需处理的各方面人事关系原则的论述,极其严格地遵循了事物发展规律,表现出高度自觉的人本理性。
3.以“行”为标准讨论用卒的必要条件。孙子认为到,“信、仁、严三者是管理士卒的基本方法”[2]。对于士卒,孙子坚持把做好思想管理工作与坚持从严管控相结合,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管理思想。这种文武之道相济的策略,显示了孙子兵法人力管理的超前性。孙子在对待士卒的管理方面,提出先亲后管的原则。如果士卒还没有归心就严加管控,则会心中不服,不会死命作战;而如果士卒已经归心了,出现错误却不责罚,同样不能作战。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孙子一方面提出要“视卒如婴儿”,要真心关爱士卒,让他们能够与自己同生死;另一方面又提出孩子不能娇惯,如果管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综观孙子对士卒管理的人本理性思想,核心是“严”和“愚”的观念。首先是要严而得其用,如果只是厚爱而称为骄兵,则不能形成力量,所以,《计篇》把“法令孰行”列为重要内容。但是,严只是一个方法,真正激活士卒力量的也需要奖赏。同时要愚而得其专。“能愚士卒之耳目”就是为了让士卒专心于自己的分工,不让他们知道与其分工无关的其他信息,这实际上与现代管理学上的分工思想是相通的。
三、《孙子兵法》人本理性的管理原则维度
《孙子兵法》“不仅揭示了军事领域活动的基本规律,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洞察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3]。他把决定战争胜利的要素,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并以之作为实现“庙算胜”的依据。而从其实现“庙算胜”的要素看,《孙子兵法》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丝神中心主义的痕迹,表现出了远超时代的人文层面的自觉和理性,避免了神中心主义的无知和侥幸。总体看来,孙子思想的人本理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维度。
1.以充分激发将士的主体性为核心。孙子非常重视团队领导精神层面的作用,以确保士兵发自内心的认同,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士卒作战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够释放潜能。孙子实现这个精神认同的手段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爱而得其心。就是“视卒如婴儿”,通过把士卒当成亲骨肉一样的感情投入,让士卒能够切身体会到这种感情,并发自内心的感激,使士率不怀异心而鞠躬尽瘁。第二,信而得其力。信任是最好的激励,是提高决策执行效率的根本。孙子提出“将能而君不御”的思想,就是建立在绝对信任的基础上的。这种信任来源于了解和托付,能够体现君对臣的尊重,也能激发将领部卒主动围绕目标谋划工作的能动性。如果君臣之间互相猜忌,那么既定的战略就不能贯彻。第三,和而助其势。《孙子兵法》专门安排篇章,讨论“势”的概念,这在古代的思想中是非常难得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从内部管理的角度看,这个“势”主要是指下属对领导层的同向认可,以及由此达成的上下级之间的彼此信赖。孙子发现和看重内部人员之间心理层面的默契,在天命观影响很大的那个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以充分发挥目标的引领性为动力。孙子根据将士在整个活动中的方位,切实设定目标,把整个活动奠定在一个有机运作的基础上,实践和贯彻了人本理性的路线。一方面用制度强化执行目标任务。孙子在《计篇》中列举为人君要经略的五件事,最后一条就是“法”,他认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孙子这里所说的法,不仅仅是法律规章,更多的是指军队的组织制度等固化的规范。这种总体节奏性的奖惩,能够传导出极强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提高了中枢指挥意图的贯彻。另一方面,以制度为依据开展全方位效能督促,主要是赏罚公正。孙子洞晓奖赏和惩罚在组织活动中的必要性,提出了“赏不虚设,罚不妄加”的思想。这是因为,孙子看到,带领一个团队,仅仅依靠怀柔,并不能实现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对于未能按照预设目标落实的组织成员,有必要进行制度层面的制约和惩罚。这种惩罚,对于相关组织成员而言是一种引导和责罚,而对于其他遵守指挥意图的组织成员则是一种公正公平。这是确保指挥中枢坚强有力的根本,尤其是孙子洞晓物质激励的重要性,讲出了“取敌之利者,货也”的原则。孙子看到,团队在精神层面的维系和调控固然十分关键,但是物质层面的补偿和激励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群体活动会存在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内部组织系统中,一般而言处于系统顶端的部分,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基本都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上下层之间分配的不平均,往往成为内部分裂的潜在因素。因此,孙子提出,允许士卒在战争过程中通过获取敌人的财物作为补偿,这是一种把士卒个人的利益需求与组织目标结合捆绑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3.以保证任务完成的效率性为突破。孙子指挥军事活动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他对人本理性的精准操作。其操作的精准性,使当时在政治哲学层面萌芽的人本理性精神,在军事学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其在操作层面上的精准,以在决策中紧盯目标、确保高效为核心。简单说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杂于利害”的方法提高组织执行决策的准确性。孙子在《九变篇》中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这里的“杂”字,是指兼顾不偏的意思。孙子把这个兼顾的思想,作为指挥战斗的一个基本原则,避免了因为利诱等外因,干扰判断的客观性。这就等于把指挥者置于一个超脱于单独一方的制高点上,站到鸟瞰敌我双方的高度去谋划战局。孙子把这种利害相杂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自觉运用到团队指挥中去,避免了顾此失彼,对于实现战略意图的贯彻,起到了保障作用。第二,以“形”与“势”为筹措单位,保证对整个活动走向宏观判断和微观执行的统一。“形”和“势”,是对各种细节要素的归纳和提炼而形成的中观层面的结论。孙子在考量对抗双方的力量时,虽然有很多细节性的要素,但是决策筹措的依据是“形”和“势”两个方面。笔者以为,孙子所谈的“势”,实际上是对“形”的一种使用方法。而无论是对表面的组织力量呈现的“形”的考量,还是对“形”后面潜藏的“势”的考量,都是《孙子兵法》中人本理性的体现。
综上,《孙子兵法》在讨论军事组织活动的过程中,跳出了当时的神中心意识,并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始终自觉地贯彻和保持人本理性立场,不仅在当时文化发展进程的层面上呈现了明显的先进性,而且在具体的实际操作层面上也显示了突出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对于今天的人事管理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赵曙明,张燕.《孙子兵法》中的用人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1995,(4).
[2]王小良.《孙子兵法》的用人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0).
[3]王志立.试论《孙子兵法》激励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J].华北水利水电学报(社科版),2008,(6).
[责任编辑 王亚伟]
F272
A
1671-6701(2017)01-0043-04
2016-12-30
赵庆营(1979— ),男,河南濮阳人,硕士,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