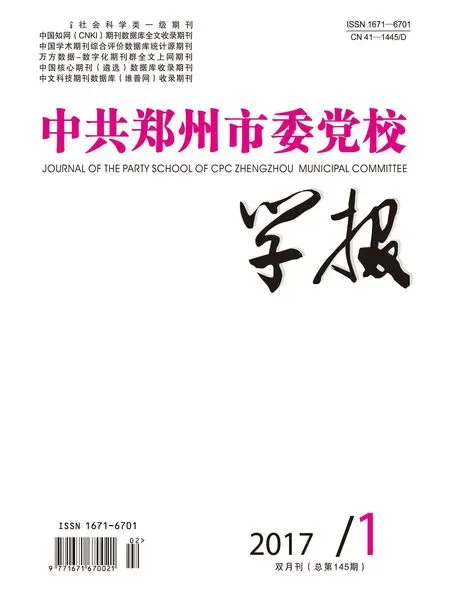王安忆小说中的民间韧性
彭音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市情社情研究室,河南 郑州 450042)
王安忆小说中的民间韧性
彭音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市情社情研究室,河南 郑州 450042)
王安忆的小说对民间生活的演绎主要聚焦于大都市上海,以隐遁于都市各个角落的普通人物作为写作对象,写出了在世事动荡之中,都市里的芸芸众生依然小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天地,在充满日常烟火气的精打细算中,凸显出都市民间市民阶层充满韧性的生活底蕴和维护自我空间的都市民间个性追求。都市市井生活看似平凡琐碎,但都市百姓在相对私人化的空间中有着不甘平庸想过好日子的心劲,有着不为外力影响而追求个性化生活的向往,充分显示出都市民间充满韧性的生存底蕴。
王安忆;小说;都市;民间;韧性
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上海作家王安忆,其小说中对民间生活的演绎主要聚焦于大都市上海,以隐遁于都市各个角落的普通人物作为写作对象,写出了都市里芸芸众生小心经营的生活天地,凸显出都市民间市民阶层充满韧性的生活底蕴和维护自我的都市民间个性追求。陈思和认为:“所谓的都市民间就是隐藏在市民的各自记忆中的文化因素,它的价值观是虚拟性的,并不存在于某个标志性的文化历史遗物中。”[1]与乡土民间社会相对固态的文化、生活模式不同,都市民间文化建构模式是不断地发展变动的,城市聚集的人物来源庞杂,流动性强,从而使都市民间社会的生活模式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但是,平淡务实的生存本能、努力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世俗追求始终存在于追求时尚的芯子里,正如王安忆自己描述的:“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2]
一、充满韧性的都市民间生活底蕴
与相对封闭的乡土民间社会相比,都市民间始终处于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之中,它不停地被动或主动接纳外来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袭扰,都市民间的外表便随着这些文化、物质的不断侵扰而繁复地改变。然而,在都市民间生活的芸芸众生们的务实本性,使得他们在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一直努力与不断变动得外部环境抗衡,表现出充满韧性的都市民间生活的底蕴。正如王安忆所描述的上海,它“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
以务实的态度尽力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是都市百姓应对繁复多变的外在环境袭扰的有效策略。黑格尔说:“市民社会的个体单元,是一个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他并不在乎别人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在市民社会中,伦理社会事实上是走入了极端,并且丧失掉了。”[3]王安忆于1994年发表的《长恨歌》,以隐遁于都市里弄的旧上海小姐王琦瑶为主线,通过由王琦瑶牵涉出的不同时期诸色人物的生活、情感,写出了在政治更迭的历史表面之下,都市民间有条不紊地追求自我享受、尽力创造精致生活的内在芯子。经历了解放战争末期、“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力量的改换和时代潮流的变换,一些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随之改变,但是躲在时代潮流之下,人们还是凭借着生活的小智慧,尽力维持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在作者对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各类市民细水长流的生活细节的描摹中,透露出对平凡的小市民不懈追求个人幸福人生梦想的理解。王安忆赞赏苏青的生活务实态度:“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
在王安忆看来,都市民间的生活看似琐碎,只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乐在其中,那就是一种成功的生存方式,“我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心平气和,承认现实,直面现实,就行了,就胜利了”。在《妹头》中,正如“妹头”这个名字一样,她是一个弄堂里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但她的生活充满了过日子的小心机小智慧,不管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外在的时代风潮与她无关,她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凭借小市民的精明谋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从她不动声色地追求小白、精挑细选地为自己攒嫁妆、“螺蛳壳里做道场”地经营自己的小家,到做服装生意、出国,所有的生活选择都基于妹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尽力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而设定的。“以‘工民’‘商民’为主的市民社会一方面充满了很强的‘自利性’;另一方面,由于根源于农民文化及其所处的地位,又充满了来自乡土气息的人情人性和伦理道德的温情。由于同时具备了‘自利性’与‘乡土性’,二者之间的碰撞与张力使活跃在城市里的市民具有了丰富的多义性”[4]。
直面现实,以充满韧性的心态顺应现实,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是都市百姓应对外在环境袭扰的另一有效策略。都市百姓虽然不顾外来环境的袭扰,只是用心追求过好自己小日子的生活目标,但是外在环境的压力有时也会改变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有时会在外力的裹挟下不由自主地发生转变。《长恨歌》里的程先生,一生谨小慎微,只是用心地经营自己的照相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成特务审查批斗,就连挂在他的照相馆前的照片里的女子们,也被当作特务牵连进去,程先生最终用跳楼终结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程先生是都市民间经不起外来环境袭扰而失败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而王安忆作品中更多的是那些在严酷现实的威逼下努力调整自身心态,以顺应现实接受外在挑战的人们,“它的情调不是控诉和伤感的,而是对现实的接受和适应;作家的笔力,不是去描写时代对人的摧残和迫害,而是注重表现人怎样顺应现实,直面现实,不断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并调整自己的心态平衡”[5]。《胭脂河》中的姐妹俩去部队看望哥哥,不慎被人贩子拐卖,姐妹俩历尽艰难,最终虎口逃生,“这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平时淹没在人海里看不出来,可正是这样的看不出来却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东西,做成了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底子”。《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当选为上海小姐后,被权贵李主任强行包养,李主任无端失踪后,王琦瑶隐姓埋名,在上海里弄中有条不紊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后来与康明逊产生感情,生了私生子,康明逊却不敢承担责任,王琦瑶凭借自己的生活智慧接受了现实,妥帖地解决了麻烦,依旧精打细算地过着精致的生活。王琦瑶接受生活灾难的态度有不得不“认命”的消极妥协成分,但更多的是在灾难已成既定事实后如何接受它、改变它的积极应对的心态,“她判定生活的准则,便是生活本身,她的笔端,时时会流出‘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的生活信念,虽然这并不否定她对真诚、善良、温情、友谊的向往,但她的追求是基于生活现实的,是入世的,是与现实生活相认同的”[6]。
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都市百姓作为社会的底层,在面临外在环境的压力时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他们应对现实压力的积极心态、一心一意过好日子的执着追求凸显了充满韧性的民间生存智慧,“他们是渺小的,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打拼的辛酸与顽强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一个因为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使得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的年代,他们令人感动的心理承受力和自我调节力显示出了健康、积极的生命意义。作家们对这些底层百姓生活的重新发现和理解,也显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不再奢求‘改造国民性’,而是以通达的情怀去理解百姓的不易、底层的艰难”[7]。
二、维护自我的都市民间个性追求
乡土民间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制约,思想与外在行为讲求“中庸”“守拙”,与乡土民间社会不同,都市民间“不需要以家族或种族的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其表现场景也相应地由集体转向了个人,现代都市居民的私人空间的扩大,隐私权益得到保障,民间价值的虚拟特征在个人性的文化形态里得到加强”[8]。
追求时尚、努力营造与众不同的个人化的生活氛围是都市小市民追求精致生活的目标。乡土民间社会的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以家族为特色的生活背景使得每个人必须融入群体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接受群体的检验。而都市民间百姓的生存没有家族的制约,他们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个性化发展便在隐私权益得到保护的背景下得以滋生。“在现代都市文化状态下,生活于其间的居民不像农民那样拥有固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以民风民俗的历史遗物来唤起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记忆,都市居民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下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下”[9]。于是,追求时尚、寻求有特色的个人生活氛围就成了都市市民彰显个性的一种手段,虽然所谓的时尚只不过是旧时尚的循环,但特异于他人、追赶时代潮流的行为彰显了都市百姓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长恨歌》中,王琦瑶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起了年轻一代的注意,因为王琦瑶是年轻人心目中高雅时尚的老上海的化身,王琦瑶与女儿的伙伴张志红成为忘年知己,也是因为两人对上海流行的服饰趋势有着相近的品位。《妹头》中,妹头一家人因为周末出门着装时尚雅致而受到弄堂里其他人家的艳羡,而妹头家人也在这种艳羡的目光中获得了心理满足;妹头结婚准备嫁妆,挑选的被面虽然只能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但花色的雅而不俗、与众不同是妹头下定决心购买的标准;娘家陪嫁的老箱子虽然看起来古旧,但在古旧的背后可以透出来前辈厚实的家底。这些过日子的小心计看起来是小市民们好面子的虚荣心作祟,实则也透露出都市百姓在不宽裕的经济条件下尽可能追求更高品位生活的生存智慧。
都市民间百姓不轻易接受外力的影响,而是以自己追求的生活目标为准绳,寻求自己设定的个性化生存环境。虽然生活条件普普通通甚至捉襟见肘,但都市百姓并不因此就甘心将自己陷入平庸当中、陷入既定的生存环境中自我放逐,而是在烦琐的生活中创造与众不同的生活环境,甚至带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这些市井中的平凡之人在追求理想的脚步中,透露出他们不甘平庸的个性色彩。《米尼》中“我总是在寻找并且企图建设一种命运性的关系,以使我在人群中位置牢固,处境明确,以免遗失自己,陷入渺茫。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人们最容易迷失,道理就是这个”。《启蒙时代》中的抢车团伙老大,虽然所作所为是鸡鸣狗盗之事,但他对人生社会的深邃思索却令人刮目相看;《富萍》中,富萍被奶奶从乡下接到上海,为的是让她嫁给自己的孙子,照顾自己全家,富萍舅妈则打算让富萍嫁给不踏实过日子的娘家侄子光明,而富萍对这些不对等的婚姻并不认同,她以自己的眼光择取了患小儿麻痹症的青年,因为青年的家虽然贫困,但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却善良温厚,那正是富萍希望的温馨的家庭氛围。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一波又一波的时代风浪虽然在来袭时都声势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最终都只是过眼云烟。在老百姓的内心当中,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人间正道。都市市井生活看似平凡琐碎,但都市民间的百姓在相对私人化的空间中有着不甘平庸想过好日子的心劲,有着不为外力影响而执着追求个性化生活的向往,充分显示出都市民间充满韧性的生存底蕴。
[1]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4).
[2]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J].语文世界(初中版),2003,(Z1).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7.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214.
[5][6]张志忠.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谈[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10).
[7]樊星.新时期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J].文学评论,2009,(4).
[8][9]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J].上海文学,1995,(10).
[责任编辑 张敬燕]
I207.42
A
1671-6701(2017)01-0091-04
2016-12-20
彭 音(1975— ),女,河南社旗人,硕士,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市情社情研究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