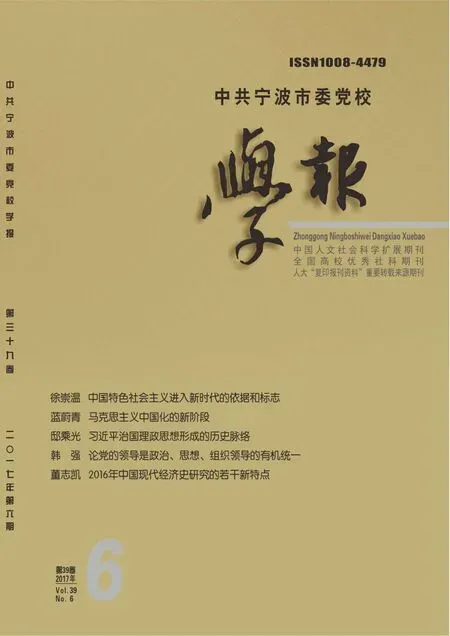陈确的启蒙儒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市 300380)
陈确的启蒙儒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市 300380)
陈确是蕺山门下三杰之一,明末淸初重要的儒家学者、思想家。他治学无所依傍、无所瞻顾,唯是是求,绝不附和雷同,故其思想不仅表现出一种处处标新立异的风格,而且体现出强烈的启蒙特性,反映了中国十七世纪早期启蒙时代精神。陈确的启蒙儒学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末清初;陈确;刘宗周;程朱理学;启蒙儒学;现代意义
“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提出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陈确虽非这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但他富有批判性的儒学思想是与这时代的启蒙精神相呼应的,并且,至今仍有现代意义。
一
陈确首先是一位儒者,只不过他始终有着自身强烈的个性特征,而这又随其思想的成熟性发展而不断升华。在程朱理学被著为功利的社会里,他同无数儒者一样,自小就为准备应试而读《性理全书》一类著作,但他并不悦理学家言。二十岁后屡次科考落榜,“遂薄视一衿,放情山水,恣情声律,韵管谱琴,时共一二知交,吟风弄月亮,超然远寄,有点游舞雩之致。间以双陆围棋,篆刻临池,得心应手,无不穷极其妙”。当时文人社集蔚为风习,但他对盛行的聚徒号众、自树门户,高谈性命、长傲饰非的讲学之风极为反感,斥曰:“不为所当为,而徒呼朋讲学,空言过日,于本身绝无相干。”陈确又是位刚直尚节、不挠于势位的任侠之士。始入庠,太府刘雪诗怜其家贫,意欲周全,他坚辞不受。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海宁乡间“苦墨吏殃民”,他率同学上告官府,却遭追究,失去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他不以为憾,谓:“捐吾生以捄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陈确一生都有着这种特重品节操守的个性特质,且在拜入蕺山门下后,受刘宗周思想深刻影响,对之有更自觉的理性认识,并由对个人品节的注重上升为对民族气节的坚守。他以“君子之于生,无所苟而已”为宗旨而撰作《死节论》,既认为“死合于义之为节,不然,则岡死耳,非节也”,又指出:“向无夷、齐之饿,则天下后世宁复知君臣之义哉!此抗古以来一大砥柱也。”这是很深刻而又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思想。
陈翼曾谓乃父平生之学凡有三变:“始崇尚夫风流,继绚烂夫词章,继又衿厉夫气节,自后一变至道。要其淡功名,薄荣利,则周根原于性天,历盛衰,阅老穉而不渝其初者也。”作为一位儒家学者,陈确的学思确曾有过重大变化,而导致其变化的原因则是他与祝渊一道拜刘宗周为师,并从此深受刘氏影响,此亦诚如陈翼《乾初府君行略》所说:“甲申、乙酉,沧桑变革,动魄惊魂,先君子思俭德避难,挫明用晦,与祝开美同游山阴先生之门,奉先生慎独之教,益从事于闇然之学,而操其功于知善必迁,知过必改,以无歉其所独知,兼动静,合人己,无往而非独,即无往而非慎。已而学益邃,识益卓,则见其胸怀恬旷而践履真笃,议论切实而理致精微。”
陈确好友张元岵说乾初“少年时,遇事任性,衣食言动不能尽戢;游蕺山之门而归,为之一变,安静和好,能以其学教其子弟”。《海宁县志·理学传》也说其“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写性情之技,视为害道而屏绝之;其勇于见义,遇不平而輒发者,亦视为任气而不复蹈。惟皇皇克己内省,黜伪存诚,他不暇顾也”。现代学者更认为正是在刘氏影响下,陈确才“自‘俗学’走向‘道学’”,并将“师从蕺山”视为“乾初一生精神生命中的最大事件”:“此前是‘崇尚夫风流’的倜傥后生,此后逐渐成为‘克己复礼’的好修君子;此前是‘绚烂夫词章’的文士,此后逐渐化为‘为往圣继绝学’的学人;此前是嫻于杂艺的才人,此后成了壹意弘道的‘道学家’;此前是好刚使气、一触即发的气节之士,此后逐渐成为‘素位而行’的中道者;此前从事的是锋芒毕露的‘为人之学’,此后所从事是‘闇然而章’的‘为己之学’。总之,乾初前半生的生命方向是‘旁逸斜出’,从师之后则转为‘敛华就实’。”
这些看法自有其理据,但在注意到“师从蕺山”导致陈确精神生命巨大变化的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他始终是位有着独立个性的儒者,并未像王瑞昌《陈确评传》所说那样圭锋消融而转变成“壹意弘道的‘道学家’”。众所周知,陈确与黄宗羲、张履祥并称为蕺山门下三杰,但高名耆旧的黄宗羲在学术上据守师说,多存道学余枝,故其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中说乾初,“其于圣学,已见头脑。故深中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这是宗羲‘余枝’犹存的证明”。至于张履祥后来转向朱学,成为清初由王返朱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反观陈确,他虽然十分敬重其师,但学说思想上已经破除了理学樊篱,“一往直前不顾利害以推翻理学的宝座”。此外,他与挚友祝渊同时师事刘宗周,但“开美邃于理学,而确素不悦理学家言”。这怎么能说他因“师从蕺山”而变成“壹意弘道的‘道学家’”呢?
事实上,陈确是蕺山门下特立独行的儒者,早年的狂放性格并未因入蕺山门墙而有彻底改变,相反地,蕺山心学的薰陶,使他在“敛华就实”的表象下更自觉地形成起王阳明所谓“狂者胸次”。他曾说:
这使他成为师门中很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对此毫无惧色,仍保持鲜明个性并坚持自己的思想,尝叹言:“嗟呼!五六百年来,大道陆沉,言学之家,分崩离析,孰执其咎乎!语曰‘止沸者抽其薪’,此探本之论也。姚江之合知行,山阴之言一贯,皆有光复圣道之功,而于《大学》之解,终落落难合。仆痛此入骨髓,幸而天启愚衷,毅然辨《大学》之决非圣经,为孔、曾雪累世之冤,为后学开荡平之路。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而吾党无识,忧谗畏讥,苟倖一日之安,而不顾天下后世之计。此仆之所以抚噟摧胸,而又继之以痛哭者也。”这是他对自己思想个性特征的最好表白。
作为始终有着自身强烈个性特征的儒者,陈确最反对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说:“吾辈学问,只缘‘因循’二字,断送一生。”“学者先发个真切向上心,时时惟恐堕于禽兽,那敢因循,那得轻放过一事,那能不深求义之精微;此真切向上心,即孔子所谓志学也。”他治学无所依傍,无所瞻顾,其所论述绝无附和雷同,因而他的思想表现出一种处处标新立异的风格。他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但他认为“斯道之在吾身与在天下,岂有异耶?道明于吾身,即所以明于天下;道未明于天下,即是未明于吾身”,故其“不敢顾一人之身名,而忘千秋之道术也”,为求真理而不顾利害,乃至甘当万世骂名:“虽一家非之不顾,一国非之不顾,天下非之不顾,千秋万岁共非之不顾也。”在他看来,这才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君子之行止,论是非,不论利害;论是非之关于世教者孰大孰小,而不论利害之切于身计者谁浅谁深。”这体现出真正儒者的风范。
二
陈确所处的时代,中国历史正面临变革的关头,古老的中国文明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化。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唐甄、张岱等提出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命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早期启蒙思潮。他们对儒学的更新,揭开了儒学由传统而近代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序幕。作为启蒙儒者的陈确,其思想无疑体现了这时代的精神。
陈确儒学思想的启蒙性,处处有所体现。兹仅从下列三端予以论析:
第一,平等的真理观
陈确承继发扬阳明心学精神而力倡平等的真理观。阳明尝谓:“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陈确虽未直接称引阳明此说,但他屡言:
此道自开辟以来,便公之天下万世,且非孔、孟之所得私,况程、朱乎!今学者守一程、朱而废千古,诚非弟之愚所可解。
这显然是一种平等的真理观,而他之所以认同孔孟之学,并非是盲从圣贤的思想权威,而是基于这种平等的真理观,故其曰:“孔、孟之道,将以公之天下万世,决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夫道之所共,固无分于长幼贤不肖也。如其言是,虽幼不肖,不能不伸于长贤,其言非是,虽长且贤,不能不绌于幼不肖,惟理之归而已矣。”
在反对圣贤权威方面,陈确不如公开打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旗帜的李贽勇敢、彻底,犹坚信孔孟、《语》《孟》的权威,他所反对的只是程朱理学家推尊《大学》并将其驾乎于《语》《孟》之上的做法。他说:“嗟呼!学至于孔、孟,可以已矣;书至于《论》、《孟》,可谓有证矣。而犹以为未足,而无端举二千余年无证据之《大学》,而强以为圣经,而尊之《论》、《孟》之上,则喜新立异之讥,在程、朱固无以自解于昔日矣。”但陈确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无长幼贤不肖之分,人人都有平等追求真理的权利,人人都应“惟理之归而已矣”。这同卓吾一样,都具有反对文化专制而求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而从知识论角度看,陈确的思想不会产生李贽观点可能会导致的是非无定的虚无主义之弊。
陈确依据其平等的真理观,学无依傍,无所顾忌地进行理论探索,但其学又是立足实际的,而绝非玄虚空言。如他论儒经,以为“《学》、《庸》二书,纯言经济,而世不察,谓是言道之文,真可哑然一笑。”。陈确更说:“有依傍固是腐,无依傍者,亦何遽非腐?学固不容有依傍,然亦须著实。如置物然。必着实地,始无欹倾之患,要于置物之心可以无憾矣。……孔子不依傍逸民,孟子亦从不依傍孔子一字,是其学力之高,然于要紧著实处,亦未尝不同。岂惟孔、孟、夷、惠,虽千圣百王,皆可打合同印子。圣人之行不同,归洁其身而已。”这使其平等的真理观尤显可贵。
第二,力反理学“存理灭欲”说的理欲观禁欲主义的“存理灭欲”说是宋明理学的基本宗旨。陈确反对理、欲对置,以“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反对程朱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教条。
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在对待人欲的看法上有本质区别。先秦儒家认识到欲本是人生命活动的自然原动力,而生存又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故其坦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篇》)当然,他们更认识到道德理性高于自然的感性需求,故其或主“寡欲”(如孟子),或主“导欲”(如荀子),都主张为建立和维系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节欲。这种思想传之后世,成为汉唐儒学的主流,但至宋儒,受释老二氏深刻影响,理学家们的看法有了根本变化。周敦颐《通书》已明确把“无欲”作为学至圣人的纲领,二程更将“天理”、“人欲”对置,说:“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朱熹也说:“天理、人欲常相对。”(《朱子语类》卷十三)“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陆王心学虽与程朱理学相异趣,但也主张存理去欲,如谓:“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欲去,则心自存矣。”《(陆九渊集》卷三十二《养心莫善于寡欲)“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由此可见,禁欲乃是理学的宗旨,这是理学‘僧侣本性’之所在,也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支柱的根本原因”。
陈确坚决反对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宗旨。他本其师刘宗周“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纵,过也;甚焉,恶也。而其无过无不及者,理也”(《刘子全书》卷七)的主张,进一步发挥道:
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流而不反,若贫愚之之俗,过于欲者也。割情抑性,若老庄之徒,不及于欲者也。贤人君子,于忠孝廉节之事,一往而深,过于欲者也。顽懦之夫,鞭之不起,不及于欲者也。圣人只是一中,不绝欲,亦不纵欲,是以难耳。无欲作圣,以作西方圣人则可,岂可以诬中国之圣人哉!山阴先生曰:“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而其无过无不及者,理也。”斯百世不易之论也。
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如富贵福泽,人之所欲也;忠孝节义,独非人之所欲乎?虽富贵福泽之欲,庸人欲之,圣人独不欲之乎?学者只时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
周子无欲之教,不褝而褝,吾儒之言寡欲耳。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多为异端立帜乎?
陈确的这些思想,丰富而又平实,既有现实针对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理论战斗精神。他认为:(一)人欲作为“生机之自然不容已者”是普遍存在的人的生理与生存要求,是人类及其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生生不已的不竭源泉:“所欲所聚,推心不已,生生之机,全恃有此。”而饮食男女就是这“生机之自然不容已”的人欲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人个体保存和种族保存的本能,对之无法遏抑,也不可能灭绝,“真无欲者,除非死人”!(二)理学家把“无欲”作为学至圣人的纲领,但“无欲安可作圣?可作佛耳。要之,佛亦乌能无欲,能绝欲耳。二氏之学所以大繆于圣人者,专在乎此”。释、老倡“无欲”是对现世人生的精神超越,但在现实层面上并非“无欲”,而是“多欲之甚者,却累离尘,以求清静,无欲之欲,更狡于有欲”。所谓“能绝欲”,不过是超越现实人生的精神信仰之表现,而实际上,“绝欲者,必犹有欲于中,则是徒绝之以形,而未绝之以心。苟徒绝之以形而未绝之以心,则其不能绝也益甚”。故无须空言“无欲”,也不必强制“绝欲”,“强制之学,如盗贼革面,终防窃发。孟子不动心工夫,只是养气;养气工夫,只是集义。此外岂别有持志之法乎?……大约吾心吾身要使时留余地,使得舒展为佳,所谓生趣也。若过于桎梏,其弊正与放心等”。“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只要做到“无过无不及”就可以了,就可优入圣域。(三)人欲与天理本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另方面是“天理中亦有人欲”,所以,“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而身心受害最大的无过于处在现实社会生活底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肯定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并对之加以维系和巩固是程朱理学区分天理、人欲,进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实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其结果,在“顺乎理,‘乐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顺理安分,故无所忧”(《程氏经说》卷一)的美名下,下层人民尤其是妇女,“冻死则冻死,饿死则饿死”(魏校:《论学书》),其生存、生活乃至生命权利被无情剥夺。陈确有见于此,“每见世儒无识,喜扬节烈,于幽贞之德略而不宣”而“甚恨之”,说:“夫女子不天,遭履厄难,一时引义,千秋叹咏,其谁曰不宜?至若艰贞备德之妇,毕生犹苦,无烈女赫赫之声,而检其行事,有万非烈女之所能忍者,又曰此恒德,不足道。嗟呼!此吾夫子所以致叹于白刃之蹈,而中庸不可能者也。其亦不知轻重甚矣。”后来的戴震痛斥宋明理学家“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处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则是使“尊者以‘理’则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乾初、东原前后呼应,他们的儒学思想都具有启蒙性质。
在理、欲关系问题上,王夫之也认为“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卷二)。如同陈确认为“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王夫之亦“惧夫薄于欲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诗广传》卷二),他们都把“欲”当作“理”产生的源泉。就此看,船山实为乾初知己同调。而作为同门好友的黄宗羲却对陈确之说不能理解认同,他在《与陈乾初论学书》中质疑道:“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这虽然深化了对问题的思考,却也确实表明梨洲在这方面尚留有理学之余绪,并不如乾初反理学思想彻底。至于今人王瑞昌尽管也注意到上引陈确的那些思想资料,但他更从《陈确集》中搜寻到“宾婚丧祭,循礼而不循俗;日用饮食,从理而不从欲”、“所谓居易,只是循理;所谓行险,只是从欲”、“过天理一分,便是人欲”、“欲胜理为小人,理胜欲为君子。絀欲从理,儒者克己之学也”等话语,便作出乾初思想之“用意当是为了矫正宋明儒特别是程朱一派儒者当中出现的那种把‘圣学推向偏枯干瘪’这一倾向,是其‘琢磨程朱’诸言论中的一部分”的判断,甚至认为乾初所说“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与朱熹所谓“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朱子语类》卷十三),“其意实同”,而对陈确反理学的启蒙儒学思想性质丝毫无所抉发,更将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不妥切的。
第三,新型的公私观与“学者以治生为本”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同理欲观密切相关的是公私观。以程朱理学家而论,他们将理与欲截然对置的同时,又将公与私相对立,坚认“天理之不存,而与禽兽何异矣”(《程氏粹言》),故而力主“抑私”乃至“灭私”而达到“无我”、“无私”的“大公”境界。此虽富含理想主义,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理欲、公私之辨,“崇公抑私”,对个人意识、个人利益压制过甚,以至使人无法形成完全独立的人格。并且,“在向着‘大公无私’‘无我’‘无私’前进乃至奔跑的时候,除了臣民、子民们在道德上做‘兴公灭私’的努力外,专制的君主即当代圣人还要用政治手段督促甚至强制人们努力地崇公抑私,以便他们能够做到‘大公无私’,而成为人。在这里,公与私在道德上的对立和对峙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当然就得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而政治手段的采用又必然使公与私在道德上的对立和对峙呈现出更加强烈的不均衡状态,而公对私的遏制、扼杀和挤兑即崇公抑私的外表也必将变得更加酷烈而残忍。”。这不能不激起身处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社会时代的启蒙儒者们的反叛。而其时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及由此必然出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现实,更使其重新思考而提出新型的公私观,陈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确明确提出与其理欲观有着内在联系的公私观,撰有专文《私说》,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君子有私”的观念:“君子之心私而真,小人之心私而假;君子之心私而笃,小人之心私而浮。彼古之所谓仁圣贤人者,皆从自私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而可曰君子必无私乎哉!”内中又写道:
有私所以为君子。惟君子而后能有私,彼小人哉恶能有私乎哉!夫君子之于人,无不敬,然敬其兄与敬邻人必有间矣。君子之于人无弗爱也,然爱其兄之子与邻之赤子亦必有间矣。如是,则虽曰爱己之子又愈于兄之子,奚为不可?故君子之爱天下也,必不如其爱国也。爱国必不如其爱家与身也,可知也。惟君子知爱其身也,惟君子知爱其身而爱之无不至也。曰:焉有吾之身而不能齐家者乎!不能治国者乎!不能平天下者乎!君子欲以齐、治、平之道私诸其身,而必不能以不德之身而齐之治之平之也。则虽欲不正心以修身,得乎?故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非忘私之言,深于私之言也。
明代中后叶,著名的平民儒学宗师、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曾依据《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提出“安身立本”论,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答问补遗》)认为“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舍此,皆妾妇之道”,此说被黄宗羲称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心斋此论“是在古旧的语言形式下,蕴含了争取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他讲的‘安身’,首先是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安,即要求吃饱穿暖,能够活下去”。而上引陈确之说,乃是王艮“安身立本”论的最佳诠释。并且,陈确“自遭世乱,伤民生之日慼”而从“安身立本”的角度感受到孟子所谓“井田之法”的重要性,他说:
井田既废,民无恒产,谋生之事,亦全放下不得。此即是素位而行,所谓学也。学者先身家而后及国与天下,恶有一身不能自谋而须人代之谋者,而可谓之学乎?但吾所谓谋生,全与世人一种营营逐逐,自私自利之学相反。即不越《中庸》所谓“素位”者是。玩下文“正己不求人,居易俟命”等语,可见素位中自有极平常、极切实、极安稳工夫。此学不讲,便不自得,便要怨天尤人。贫可忘而不可忘,正己居易,正是不忘贫实学。到得不求人、不怨尤地位,则贫亦不期忘而自忘矣,斯真能忘贫矣。今学者漫言“吾能忘贫”,不知忘贫之久,终自不能忘贫处也。
又言:“天降民,而作之君以治民,而非待民自治也。人谋其家,与天子为谋其家,治乱相百。谋于上则一,谋于下则万不一。万不一,而乱何时已乎?有王者起,君臣一心,以隆尧、舜之治,舍井田恶先?孟子之言,百王不易之道也。”晚明清初、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启蒙儒者多热衷于讨论“复井田”的话题。如颜元把“均田”列在各项政事的第一位,认为“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三代第九》),而他所以要提出恢复三代的井田制,正是为了达到“均田”的目的。在他看来,现时推行井田制应“因时而措”,“可井则井,不可则均”,不必拘泥于古代井田制的“沟洫之制,经界之法”,只要能达到均田的目的就行。其弟子王源又依据着颜氏“天地间田进一步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原则,进一步提出“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惟农为有田”(《平书订》),主张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这种思想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均田思想的意义,而与章太炎、孙中山“露田无得佣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的平均地权思想相接近。陈确有关“井田”的看法虽然没有在土地所有制上提出要求,而只是与其公私论相关联,把“复井田”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途径,这与颜李学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但二者精神上又有相类之处。而在陈确看来,复行井田而使民有恒产,才能使民做到身安忘贫,其身安方能身尊,身尊亦即道尊,这也是他所谓“素位之学”的核心要义。由此可见,乾初与心斋思想深处息息相通,其启蒙儒学思想客观上是同情和左袒着普通劳动民众的。
从这种公私观出发,陈确不同于理学家动辄即言学圣人,而是明确提出“学者以治生为本”的主张:
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身,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治生洵是学人本事。而或者疑其言有弊,不知学者治生绝非世俗蝇营狗苟之谓,即草野一介不取予学术,无非道义也。……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治生以学为本。
元儒许衡尝谓:“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引自《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而王阳明对此颇致不满,说:“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但其弟子心斋王艮却认同许氏,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当然,王艮与许衡毕竟有所不同,“许衡仅为‘士君子’的利禄设想,王艮则对呻吟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民表示同情。要求摆脱贫困,争取人身生存权利的观点,是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和‘安身立本’思想的出发点”。而陈确所论虽是为学者而发,并无心斋那样强烈的平民意识,但他没有像许衡那样为“学者……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曲作辨护,而是强调“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结合其上述理欲、公私观以及他同情下层民众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说乾初的这思想同王艮是一致的,具有启蒙意义。并不赞同侯外庐先生“早期启蒙”说的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确思想具有“近代性格”,说:“陈确相对肯定了人的个体之‘私’,肯定了‘欲’,也肯定了学者的‘治生’,这多少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变化。从陈确、全祖望到戴震、钱大昕以至沈垚,儒家思想关于个人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似乎正在酝酿着一种具有近代性格的答案。一个儒家的人权观点已徘徊在突破传统的边缘上,大有呼之欲出之势了。”
三
尽管陈确辞世已340周年,但至今来看,他的启蒙儒学思想仍有现实意义,兹仅就其中洋溢着的崇真务实精神略予述论。
陈确认为:“学问之事,先论真假,次论是非。其真之至者,虽偏不失为圣,夷、惠是也。假之至者,虽中不失为奸,乡愿是也。古来王伯之辨,圣学曲学之分,可不察乎!”他指出:“学者通病,大率是一‘假’字。其驰鹜不知止者,三分是名,七分是利。进乎此者,则七分是名,三分是利。究之,名之与利,相去几何,总成十分,假人持此伪质,独安所之;幸而世方扰乱,名实淆溷,金之在罏,成色高低,终当自见。”他对“假道学”尤为痛恨:
今世所谓假道学有三种:一则外窃仁义之声,内鲜忠信之实者,谓之外假;一则内有好善之心,外无力善之事者,谓之内假;又有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内外虽符,名义亦正,而于道日隔,虽真亦假。破此三假,然后可以语学矣。
他所贬斥的这三种“假道学”,当今社会并未绝迹,至于名利是求者更不乏其人,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故而他所说的“学者通病,大率是一‘假’字”仍适用于今世。这就使其主张的“素位之学”在当下生活中具有纠正时弊的意义,如行道德之事,要根据自身的地位和处境“素位而行”,实事求是地本色做来,不装假,不务虚名。
尚真恶假的陈确,直率朴实地反映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劳动群众的苦况:
呜呼苍天,农民何罪!赤日中田,焦发裂骨。渴不得饮,饥不得食,閔其将死,不敢云瘁。天复不念,降此大戻。……呜呼苍天!吾农民之伤!而不知者,谓民已康。有丝满箱,而不得以为裳;有谷满仓,而不得以为粮。出,岂曰无获,为他人忙。呜呼苍天!吾农民之伤!
他不仅通过该诗直抒胸臆,揭示旱灾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他还本儒家仁爱情怀倡主仆平等之说,并谆谆告诫其子道:“家仆谓之义男,即有父子之义,于父仆即有兄弟之义矣。于义女义男妇亦然。君子当一体万物,而况家人乎!男耕女织,自其职分,而衣食之计,在我固宜有以周之,此劝忠之本也。”这是很可贵的。
陈确痛感“自《大学》之教行,而学者皆舍坐下工夫,争言格致,其卑者流为训詁支离之习,高者窜于佛老虚玄之学,道术分裂,圣教衰歇,五百余年于此矣。而通时达务之士,则又群相惊惧危恐,蓄缩而莫敢出一言”,“自程、朱揭出致知之义为《大学》始事,于是学者皆舍坐下工夫,争求了悟,今日言格致,明日言格致,谓学必先知后行”,因而明确提倡“事事求实理实益,不苟循虚名”。他主张研究生活实际中实实在在的理,认为“自然固指道体言,然舍却日用,亦无处更觅道体。一言一动,无非道也”。陈确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而其对于正谋求儒学当代发展的学人尤有重要启示。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并不在相应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而从纯理论层面上对儒学作出这样或那样现代性的诠释,而在于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第一,应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体认,调整、转换儒学的生长基点和思想内容。第二,将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投置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中,使儒学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第三,将儒学融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其多层面地满足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
[注 释]
责任编辑:郭美星
B249.9
A
1008-4479(2017)06-0052-10
2017-06-07
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