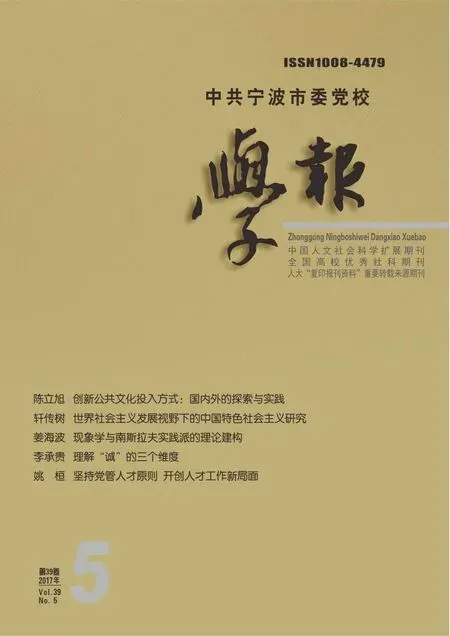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朱熹;仁爱;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孔子讲“仁”,主要讲“爱人”。孟子则既讲“亲亲”,讲“仁民”,又讲“爱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至于什么是“爱物”,如何“爱物”,孟子并没有做过明确的界定。朱熹把孟子的“爱物”注释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内涵着人对自然之物的合理开发利用的思想,或许可以成为当今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因而对于当今追求人与物的相互和谐、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仁民而爱物”
先秦儒家讲“仁爱”,讲亲疏有别、爱有差等,但既然讲“爱”,那么既要讲“爱人”也要讲“爱物”。据《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汉代郑玄将此理解为,孔子“重人贱畜”。与此不同,朱熹注曰:“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郑玄的“重人贱畜”,讲的是人与马的贵贱不同,似乎意味着,爱只能给予人,而不能给予马;朱熹则明确讲“非不爱马”,只是“未暇问”,所以,朱熹的“贵人贱畜”,意在爱有先后,先要给予人,但也要给予马,并非只爱人不爱马。
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朱熹《论语集注》引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在朱熹看来,孔子之钓鱼、射鸟,是“为养与祭,或不得已”;只是用鱼饵钓鱼而不用大渔网捕鱼,只以生丝系箭捕获飞鸟而不射宿鸟,表现了孔子“仁人之本心”。一方面,人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捕获鱼和鸟,另一方面,人又有“仁人之本心”而生发出爱鸟、爱鱼之心。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正是体现了既要爱人也要爱物,爱人在先、爱物在后的思想,并非只爱人不爱物。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对此,朱熹《孟子集注》曰:“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朱熹《孟子或问》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说:“禽兽之生,虽与人异,然原其禀气赋形之所自,而察其悦生恶死之大情,则亦未始不与人同也。故君子尝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尝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盖本心之发,自有不能已者。”人的生活需要宰杀禽兽,但是人对于宰杀同类生命又有不忍之本心,所以要“远庖厨”。
孟子讲“仁爱”,强调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又讲推人及物。《孟子·尽心上》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爱物”之“爱”,不同于“仁民”之“仁”,更不同于“亲亲”之“亲”。对此,东汉赵岐注曰:“先亲其亲戚,然后仁民,仁民然后爱物,用恩之次者也。”宋孙奭疏曰:“孟子言,君子于凡物也,但当爱育之,而弗当以仁加之也,若牺牲不得不杀也;于民也,当仁爱之,而弗当亲之也。以爱有差等也。是则先亲其亲,而后仁爱其民;先仁爱其民,然后爱育其物耳。是又见君子用恩有其伦序也。”认为孟子讲“仁民而爱物”,主要是讲爱有差等,对人以“仁”,对物以“爱”,并且为了人可以宰杀动物。朱熹《孟子集注》引程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在朱熹看来,孟子讲“仁民而爱物”,其中的“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对物与对人一样,都要给予爱;分而言之,对人之爱不同于对物之爱,有先后次序,这就是爱有差等。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多有讨论,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朱熹《孟子集注》不仅引程颐所言“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而且还引杨时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朱熹还说:
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这里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这里所谓“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讲的就是“理一分殊”。朱熹门人郑子上讨论“仁民而爱物”,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然谓之爱物,则爱之惟均。……窃谓理一而分殊,故圣人各自其分推之,曰亲,曰民,曰物,其分各异,故亲亲,仁民,爱物,亦异。”朱熹则以“此说得之”给予肯定。朱熹门人陈淳更是撰《亲亲、仁民、爱物只是理一而分殊》,指出:“亲亲、仁民、爱物,大意只是理一而分殊。然其所以为理一分殊者,亦有二义。以天言之,则乾父坤母,民、物皆为同胞,与吾亲同此一气体而生,是理一也;然亲也、民也、物也,其亲疏本末亦天然自有个差等处,是分殊也。……以人言之,则曰亲、曰仁、曰爱,皆一仁心之所流行贯彻,而所谓仁爱者,不过出于亲,是理一也;然亲者,隆于仁爱,仁者止于仁而弗亲,爱者止于爱而弗仁,其亲重亦有等,先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其缓急又有序,是分殊也。”在这里,《孟子》“仁民而爱物”被完全解读为“理一分殊”。
第二,朱熹强调孟子“仁民而爱物”中爱有差等的内涵。除了朱熹《孟子集注》对于“仁民而爱物”的注释,讲爱有差等,他还说:“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亲亲是第一件事。”他的《中庸辑略》载吕大临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虽无间,而有差等,则亲亲大矣。”朱熹也说:“自亲亲而仁民,自仁民而爱物,其爱有差等,其施有渐次,而为仁之道,生生而不穷矣。”在朱熹看来,亲亲、仁民、爱物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为仁之事”,但是各自又有差等,并且有次序的先后。
朱熹还说:
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本同一理,而禀气有异焉。禀其清明纯粹则为人,禀其昏浊偏驳则为物,故人之与人自为同类,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则仁之,虽其有罪,犹不得已,然后断以义而杀之。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尽于吾心矣。其爱之者仁也,其杀之者义也,人物异等,仁义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为正,非异端之比也。
显然,在朱熹看来,人与物本同一理,因所禀受气的不同而有别,爱人与爱物有差等,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爱人在于仁民,并依人与人之别而有差等;爱物则在于“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以尽人之仁爱之本心。所以,人与物虽有差异,但都要给予爱,这就是仁;爱人与爱物之不同而有差等,这就是义。也就是说,人与物虽有不同,但必须都以仁、义相待而不偏。
需要指出的是,在爱人与爱物上讲爱有差等,首先是讲对物与对人一样,都要给予爱,其次才是讲对物之爱不同于对人之爱,前者为仁,后者为义。实际上,爱人与爱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就爱人而言,对于亲人的爱也不同于对其他人的爱。所以,孟子对“亲亲”之“亲”,“仁民”之“仁”,“爱物”之“爱”作了区别。一般而言,人与人的爱,是相互的,而且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而人对物的爱,是单向的,而且往往是在对物的获取和利用中的爱。儒家讲亲疏有别、爱有差等,就爱物不同于爱人而言,只是强调由于人与物的不同,爱的方式、内涵和层次也不相同;而且,由于人与物的重要程度不同,在发生冲突时,爱的先后也有所不同,正如孔子先问人不问马,并非不爱马。对于人来说,无论是爱人或是爱物,虽然在朱熹看来,“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但真正的爱,人之本心所发,与贵贱没有直接关系,而往往与亲疏远近有关。
朱熹说:
天之生物,有血气者,本于父母,无血气者,本于根荄,皆出于一而无二者也。其性本出于一,故其爱亦主于一焉。盖一体分,血气连属,眷恋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则因其分之亲疏远近,而所以为爱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亲亲仁民,又至于爱物,而无不各得其所也。
在朱熹看来,无论对人还是对物,都要给予爱,但是,因亲疏远近之不同而爱有差等,有亲亲、仁民、爱物之别,对亲人的爱不同于对他人的爱,对人的爱不同于对物的爱。随着从“亲”到“民”再到“物”越来越疏远,爱的方式、内涵和层次愈来愈不同而有差等,而只有这样有差等的爱,才能使得人与物各得其所。
此外,朱熹还赞同门人郑子上对于“爱物”的阐述:“今观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兽之类是也;有无知之物,草木之类是也。如数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圣人于有知之物其爱之如此。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于市,圣人于无知之物亦爱之如此。……若吾儒于物,窃恐于有知无知亦不无小异,盖物虽与人异气,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气所生,与无知之物异,恐圣人于此须亦有差等。如齐王爱牛之事,施于草木恐又不同。”可见,不仅在爱人与爱物上须爱有差等,而且在爱物上也须爱有差等,对牛之爱不同于对草木之爱。所以,在朱熹那里,在爱人与爱物上讲爱有差等,并不是只爱人,不爱物,而是讲爱的方式和内涵之不同,爱的先后之不同
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先秦儒家对于自然物,不仅强调由“仁人之本心”而生发出来的爱物之心,而且从天道的角度,就人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物,提出各种见解。据《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载:孔子的门人高柴“开蛰不杀,方长不折”,对此,孔子指出:“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认为“开蛰不杀,方长不折”,既是儒家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恕道,合乎人之本心,又合乎天道,以便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
据《礼记·祭义》记载:孔子的门人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对此,孔子进一步指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这里讲断树、杀兽要以其时,为的是能够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在《孟子》那里有较多的阐释。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所谓“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二者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言,有相似之处;但是,前者的目的在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后者则出于人之仁爱之本心,二者并不不完全相同。
后来荀子对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作了发挥。据《荀子·王制》记载,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所以,荀子强调:“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显然,这里讲的是治国之道,讲如何发展农业,并不是为了“爱物”。
《礼记·月令》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月份的天象、物候作了描述,并据此对各种农事活动作了安排。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此外,《礼记·王制》说:“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这里涉及大量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而且确定为“礼”,但这并不是出于由亲亲而仁民而推展的“爱物”。
西汉初年的贾谊对“礼”多有论述。他说:“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睢而不逮,不出植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在这里,贾谊从“礼”的角度,把孟子出于不忍之本心的“远庖厨”,与为了“物蕃多”而对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并列起来。后来的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其中卷三十六《王朝礼》编入以上贾谊所言。
北宋胡安国把《礼记》所谓“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联系起来,而称之为“爱物”,说:“《易》称‘王用三驱’,在《礼》‘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夫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皆爱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鸟兽若草木裕,无淫猎之过矣。”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之类,更多的是体现人对于动物的爱心,但是,将这种爱心推向自然之物,则会得到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同样的结果。
朱熹中年时在与门人讨论《周易》时,曾就《文言》解“元亨利贞”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指出:
“嘉之会”,众美之会也,如万物之长,畅茂蕃鲜,不约而会也。君子能嘉其会,则可以合于礼矣。如“动容周旋,无不中礼”是也。利是义之和处。义有分别断割,疑于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谓利也。利物,谓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干”犹身之有骨,故板筑之栽谓之桢干。推此可以识贞之理矣。
在朱熹看来,君子不仅要“体仁”,而且要“利物”,“利是义之和处”,利物是“使物各得其所”。稍后,朱熹在所撰《仁说》中,既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其心之德为“仁”,又认为,“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而且,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
对于朱熹《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朱熹的好友张栻不赞同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指出:“《仁说》如‘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并且还说:“圣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是心之发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则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皆仁之至义之尽,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则王政行焉,鸟兽鱼鳖咸若矣。夫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则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则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在这里,张栻通过把人之本心与天地生物之心联系起来,把发自人之本心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对于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联系起来,并且还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相联系,认为这些“皆仁之至义之尽,而天理之公也”,而“禁杀茹蔬,殒身饲兽”则是违背“天理之公”。对此,朱熹《论语或问》作了引述,并给予赞赏。
朱熹《孟子集注》注“仁民而爱物”的“爱物”:“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在朱熹看来,《孟子》“仁民而爱物”之“物”,指的是禽兽和草木,即动物与植物;“爱物”之“爱”,即“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爱物”,指的是对动、植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朱熹还说:
爱物,……则是食之有时,用之有节;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牺牲无用牝,不麛,不卵,不杀胎,不覆巢之类,如此而已。
如前所述,朱熹还认为,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现了孔子“仁人之本心”。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既有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对自然之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在“取”、“用”过程中的爱,又有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爱,孟子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由不忍之本心所发出的对自然之物的爱,还有《礼记·月令》所谓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之类对于自然之物给予尊重的爱,当然,最重要的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讲“亲亲”、“仁民”、“爱物”,其重要之处并非只是指爱的对象的变化和推广,而是指随着爱的对象的变化,爱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不相同。从根本意义上说,儒家讲爱,无论爱人或是爱物,都由人之本心所发,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但是,亲人与他人不同,对于亲人的爱与对于他人的爱当然有相应的差异;人与物不同,对于人的爱与对于物的爱也有很大的差异。就“爱物”而言,其与“亲亲”、“仁民”的最大不同在于人对于物的爱,是在对物的获取和利用过程中的爱。
朱熹把《孟子》“仁民而爱物”中的“爱物”解读为对动、植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元之际,金履祥撰《论孟集注考证》,其中对“爱物”作了阐释:“《集注》草木禽兽皆举之,‘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先王爱物之政也。若释氏虽例以不杀为爱物,然知施于动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谓不知类。”陈栎对于朱熹把“爱物”解读“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说:“当取则取,当用则用,但有时、有节即爱也,若释氏以不取、不用为爱,则非矣。”“暴殄者,固非爱物矣。梁武之宗庙不用牺牲,亦非爱物之宜。”
陈天祥则对朱熹的解读提出反对,指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只是节其费用,不使致有匮乏而已。以此为爱,正与‘百姓皆以王为爱也’之爱相似,此本智者吝惜之爱,非仁爱之爱,与亲亲仁民之理差矣。……所谓‘爱物’者,如齐宣王悯其牛之觳觫,郑子产乐其鱼之得所,至于当春草木,不忍摧折;行视蝼蚁,不忍践伤,此皆爱物之道,是为仁爱之爱,与亲亲仁民之心,同是一本。”应当说,朱熹所谓“爱物”,不止有对自然之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也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对自然之物的不忍之爱;而且朱熹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意在于孟子讲“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
三、人对自然之物的合理开发利用
朱熹把《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注解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不只是停留于“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注解,对于以往儒家认为“仁民而爱物”主要是讲爱有差等,以及把“爱物”理解为“不食肉,不茹荤”之类来说,无疑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朱熹强调对于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也是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讲“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礼记·月令》所谓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之类,古代儒家处理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的智慧结晶。重要的是,朱熹把这一智慧结晶与《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联系起来,不仅丰富了孔孟仁学的内涵,而且把对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提升至新的高度。除此之外,朱熹强调对于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内涵着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除了以上孟子、荀子以及《礼记》所述之外,《管子》特别强调“以时禁发”,所谓“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管子·立政》)“天财”就是自然资源,“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开发利用,也就是说,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地结合起来。《管子》还提出春夏秋冬“四禁”:“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管子·七臣七主》)在这“四禁”中,有不少是涉及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措施。《管子》还说:“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暴火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蚊;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管子·七臣七主》)当然,这些论述都是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强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朱熹强调对于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中“取”,就是获取;“用”,就是利用。“取之有时”,就是获取自然之物必须根据其生长的时节;“用之有节”,就是利用自然之物必须有所节制。人在生存和生活中,其与自然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对于自然之物的“取”、“用”关系,人必须通过“取”、“用”自然之物,满足自己的合理需要;与此同时,人又出于仁爱本心之所发,给自然之物以爱。这样的爱,不只是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由不忍之本心所发出的对自然之物的爱,而且还有根据自然之物生长的时节获取自然之物,并在利用自然之物中作合理的节制,以保证自然之物在人的“取”、“用”过程中不受影响的爱。这种对于自然之物的合理获取和利用,就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对自然之物的爱,不仅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是如此,《礼记·月令》所谓“牺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也都是如此,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把《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界定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以与“亲亲”、“仁民”相区别。
就朱熹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包含对于自然之物的合理获取和利用而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实际上就是古代儒家对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表达,因而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供借鉴,成为基本的生态原则。
第一,朱熹“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实际上凸现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朱熹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意在于对自然之物的合理“取”、“用”,从广义上讲,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朱熹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并且讲“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把儒家仁爱与对自然之物的合理“取”、“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强调儒家仁爱包含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从而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抬高到儒家仁爱的高度。这就从道德层面上凸显了对自然之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第二,朱熹“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实际上为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了基本的解决方案。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本原于共同的理,同时又各有不同的理。就人而言,人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取”、“用”自然之物,但是,这种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就自然之物而言,自然之物各有不同理,取决于阴阳、五行及四时的变化,只有按照这样的理进行“取”、“用”,才为合理,否则就是不合理。朱熹说:“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作金用,便无此理。”相对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言,“取之有时”,就是开发须“有时”,实际上就是要按照自然规律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用之有节”,就是利用自然资源须“有节”,实际上就是要根据人的合理需要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重要的是,开发自然资源,不仅要按照自然规律,而且是为了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因此,要根据人的需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而不至于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同时,利用自然资源,不仅要根据人的需要作合理的节制,而且还要按照自然规律,做到物尽其用。
第三,朱熹“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实际上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出了基本步骤。在朱熹看来,要按照自然规律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首先必须“格物”。他说:
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
这里所谓“抚临万物”,对自然之物的“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即朱熹的“爱物”。在朱熹看来,爱物就是要“因其性而导之”,就是要根据它们不同的物性,合理地加以开发和利用,从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且,朱熹还认为,要能够“因其性而导之”,“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首先要“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认知自然之理,这就是要“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他还说:“古人爱物,而伐木亦有时,无一些子不到处,无一物不被其泽。盖缘是格物得尽,所以如此。”这里把“爱物”与“格物”联系起来,以为“爱物”首先在于“格物”。
与此同时,人对于自然之物的获取和利用,有天理人欲之分。他说:“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还说:
夫外物之诱人,莫甚于饮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则固亦莫非人之所当有而不能无者也。但于其间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厘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于吾之所行乎其间者,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是以无以致其克复之功,而物之诱于外者,得以夺乎天理之本然耳。
在朱熹看来,人为了生存和生活而需要外物,此为天理,但是外物对人又有诱惑,而有人欲,因此在对待外物上,自有天理人欲之辨,需要通过“即物而穷其理”,以辨明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正确区分天理与人欲,只有这样,才能在为了生存和生活而需要外物时,克服外物的诱惑。也就是说,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仅需要通过“格物”,认知自然之理,以便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而且还要通过“格物”,辨清天理人欲,并且通过克服人欲,回归天理,实现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由此可见,朱熹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中“取之”、“用之”是为了人,而“有时”、“有节”为的是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既体现人对于物的优越性,又体现物对于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而要求在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的同时,对于物的尊重,这就是“爱物”。与此同时,对于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既是为了人,也是为了物,追求的是人与物的相互和谐、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责任编辑:郭美星
B244.7;B248.2
A
1008-4479(2017)05-0060-08
2017-06-23
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