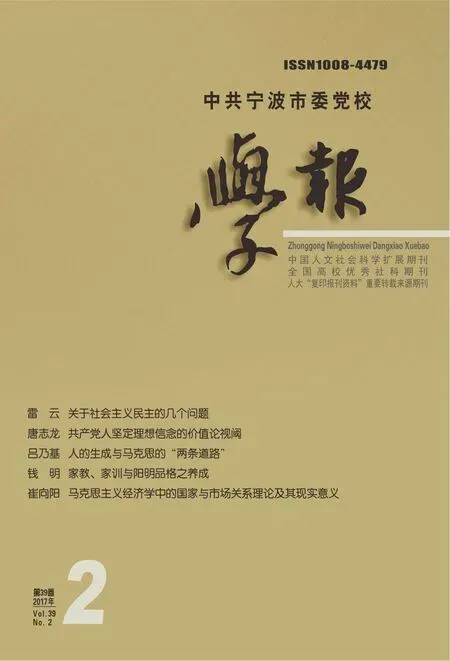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张品端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南平 354300)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张品端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南平 354300)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朱子;阳明;心学;发展
先秦儒学,孟子最先注重“心”的作用。他认为“心”具有先验的道德属性:“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还认为“性”根源于“心”,人性的仁、义、礼、智四端都蕴含于人心中:“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由于性根源于人心,因此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这类见解,确立了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此后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主流思想。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心本体”的思想。按照朱子理学,“理”是最高本体,可是他又提出了“惟心无对”(《朱子语类》卷五)。无对就是绝对,就是只有一个主宰。就理学家而言,朱熹是最强调心的,他对于心的作用,也是谈论得最多的,绝不亚于同时代的陆九渊。但由于他的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经过其门人和后学得到不断发展。如陈淳、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就着重发展了朱熹的心学思想。到了明代,陈白沙,以“自得”之功合“心”与“理”为一,克服了朱子“心与理为二”之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心学思想。而后,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完成了心学体系的建构。所以,清初张履祥说,在吴与弼、胡居仁讲学先后,“乃白沙、甘泉随于其时争鸣,则已为姚江先后奔走之资矣”(《备忘录》,《杨园先生全集》卷4)。
一
在心、理的关系上,朱熹认为:“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大学或问》卷下)这样,朱熹就提出了以心为核心的内外合一之学,广泛地涉及到主观同客观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朱熹那里,理是客观精神,心是主观精神,他即强调客观精神,又很强调主观精神,为了把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了“心与理一”(《朱子语类》卷五)的命题。上面讲的这一段话,从认识之差别统一关系立论,可以看作是朱熹对于心理关系的经典表达。它说明,心知与物理分为主宾双方。但双方又不能截然分割。心知的虚灵预备了主管天下之理的主体条件;理体作用的微妙,又只能在心知之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不能够按心内物外的对立视野,将双方分割开来。这也就是说,理的作用可以通过主体的概括发挥而表现出来,这是符合人们认识的一般规律的。但是,认识论之心理合一与本体论之心理合一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为前者可以有二有一,后者则只能一而不能二。
为了说明心理相对关系,朱熹又说:“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赅,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实用在心也。”“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朱子语类》卷18)可见,心与理不仅具有主客关系,而且具有体用关系。这种双重蕴含:一方面是心主而理客、客又统一于主的主客对应关系。在此关系中,理虽无所不赅,但却是“被管”;心体虽具备物理,但心都是“主管”。由于此主管和被管关系,心物、内外之理便归于统一,不可以内外精粗而分。另一方面,就体用关系看,理是体,心是用。理是遍在于天地间的客观本体,从体决定用的角度说,心用只是理体的表现;然而,心表现理又不是被动的,理之用在心,是通过心作为主体管摄概括万物之理而主动揭示出来的。因此在这里,主客关系要高于体用关系,也即朱熹所说的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正是通过这种以身为主的构架,理体的发动作用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这样也才能够说,在物之理体与在吾身之心体“只一般”。
由上述可知,朱熹所说的“心与理一”,实际上是由二而一的“心具理”(认识论意义上),而非本体意义上的“心即理”。朱子这种“心具理”的思想,其心学特色还没有完全突显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朱熹并没有完成“心与理一”的任务。
王阳明心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心理为一”。这是对朱子心学思想的发展。王学主张心与理为一,是出于对实践道德的论证。他把主观与客观合一,以说明仁、义、理、智不仅是客观的道德规范,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人心固有的天然本性。因此,他把具有伦理本性的个体之心当作宇宙本体,用它来同化道德内容,以形成修养论、认识论与本体论一体化的结构,达到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融合统一。在这里,王阳明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把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
王阳明同朱熹一样,认为心有体用,但他合体用为一,从而克服了朱熹体用为二的缺点。这是对朱熹心学思想的一个很大的发展。朱熹以性情、动静、未发已发、人心道心为体用,即以形而上形而下为体用,并将体用为二。而王阳明把体用统一起来,合而为一。如动静,他说:“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答薛侃》,《传习录》上)王阳明所谓“体用一源”,是说用在体,体在用,体用不可分离。“定者心之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答陆澄》,《传习录》上)心之本体即在动静上见,而动静之发不离本体。动静皆有定,定即是本体,静者体之静而不能无动,动者体之动而不能无静,因此不可以动静言体用。这就克服了朱熹把体用、动静分割开来的缺点。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王阳明说:“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传习录》上)这就是说,不能把二者分开,“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精神本体即在思虑作用之中。
王阳明认为“体用一源”,理气不可离,心外还有什么物?因此,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与王纯甫》,《阳明全集》卷四)的思想。从而对朱熹“心外有理、心外有物”的思想作了修正,克服了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矛盾。王阳明以人为世界的中心,把天地万物都从人的思维现象推出来。这样,其哲学的出发点已不再是概括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客观观念、抽象天理,而是具体的心性,人的道德性和主观精神。他剔除了朱熹哲学中与自然知识相关的内容,把“理”的内涵直接限制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这样就省去了从自然到社会的繁琐推证,把“理”直接放置到每个人心中,以便对人的行为发挥最大的效用。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的心本体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他的“内外合一”之学,虽然把客观世界消解于一心,建立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心本体,但他并不是认为,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万事万物都是虚无心体变现出来的幻妄。他把主观精神即“心”说成体,而把客观事物说成“用”,以心为本原,以物为心的派生物,不离心而存在。但他既然提出“内外合一”之说,就意味着没有完全否认外物的存在。
王阳明“体用一源”说的另一方面,就是以用为体。他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答黄省曾》,《传习录》下)所谓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以万物之声色臭味为体,心以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并不是说,客观物质是本体;而是说,心之体不离物而存在,因此以物为本。这就是他所说的“感应之机”。
王阳明曾有一段关于“岩中花树”的著名问答,就是“目以物之色为体”,说得就是心与物的感应关系。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答黄省曾》,《传习录》下)山岩上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是与心无关的,是客观存在的。当人出现时,花即成为反映对象,得到反映,一时明白起来;当人不在时,花未成为反映对象,没有得到反映,因此“同归于寂”。这里所谓“寂”,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殊状态。在王阳明看来,物不过是“意之所在”,或“意之用”。
二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除了继承程颐的知先行后说外,又总结了儒家一贯重视践履的思想,提出了重行说。同时还广泛地讨论了知行二者的相互关系,提出:“知行互发并进”说。朱熹的这些思想,其中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着矛盾。
关于知行先后的问题,朱熹认为,就一个具体的认识活动而言,先有知,后有行。“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故各有其序矣。”(《答吴晦叔》,《朱文公文集》卷42)“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朱子语类》卷九)但是,如果事事都是知了再行,那也不成。因此,他又作了修正。他说:“若曰,须待见得个道理,然后做去,则‘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功夫,皆为无用矣。”(《朱子语类》卷九)这就是说,不能什么都是知了再行,有所谓“学知利行”,“困知勉行”者,还是要在行中去知,或行而后知。因此,朱熹认为,知先行后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知行互相推进的。应该说,这是朱熹对程颐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说。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知行“相须”,就是二者不能截然分离,知靠行来实现,行靠知来指导。如目与足,目无足则不能行走,足无目则无法行走,知行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朱熹还进一步强调知行互发并进,提倡知行二者在并进中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好比人的两足,鸟的两翼,车的两轮,同时并进,“不可废一”。他说:“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朱子语类》卷117)如果只知不行,“如车两轮,便是一轮转,一轮不转”(《朱子语类》卷113)。这是强调知行不可偏了一边,更不可缺了一边,须是齐头并进,才能互相推动,互相促进。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作用,反映了认识实践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朱熹的知行互发说,虽然同是强调了二者并进,不可偏废,但他更重视行。因此,他又提出“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的思想。这是朱熹知行说的又一个特点。就朱熹的知行说来看,知行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合而为一。特别是朱熹把知解释成“格物致知”,而他所谓行,则是行吾心中之理。这就割裂了知和行的内在联系。这一点特别受到王阳明的批判,他认为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因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在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第一步,便以他的“知行合一说”为重要标志。他的知行合一说,也就是他的致良知说。良知属知,致良知属行。良知是意识本体,即主观精神;致良知是意识的发现流行,即主观精神的实现。二者是体用本末关系。知行关系同样如此。良知之外无知,致良知之外无行。因此,知行也是合一的。从理学的演变来看,他的知行说是在朱熹及其弟子陈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陈淳提出了“知行无先后”、“知行是一事”的思想,并主张“知行统一”。这个思想为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开了端绪。
王阳明和朱熹一样,非常重视行。他虽然提出心本体论、良知说等心学理论,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践行。他反对背诵词章、口耳谈说、空疏悬虚之学,主张要在身心上着实体验践履,把道德信念化为道德实践。他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他自认为他所讲的就是身心之学,是“圣门真传”。他为学生制定的《教约》中,第一条就是“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应该说,这是从朱熹的“重行”思想发展而来的。
王阳明批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但继承发展了朱熹的知行并进说。他认为持知先行后说,就不能贯彻知行并进说。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答徐爱》,《传习录》上)如果按照知先行后说,等先知得真了再去行,就是把知行分作两截。王阳明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个“知先行后”之说,才导致了现实性上的知、行分离,大家都先去做“知”的工夫了,结果是“终身不行”。王阳明认为朱熹之所以分知行为二,是由于他析心与理为二,“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可见他的知行合一说,是同他的“心外无理”的思想密切联系的。
王阳明进一步提出,知行是“一个功夫”,“不可分作两事”。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作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答徐爱》,《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原本就是一个工夫。知作为知识活动的过程或知识的形态,都必须通过行来实现。行的实际展开过程,同时即是知的表达与体现过程。就认识过程看,人的实践活动总是需要一定的认识为指导,而人的认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实现或完成,这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行二者是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
正因为知行是统一的,不可分离,因此,王阳明提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失知行本体。他所说的知行本体,除了良知说以外,还有知行统一的方面。他又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答友人问》,《阳明全书》卷六)这里,他用学与思说明知行关系,而把行包括在学之内。这说明,他并没有把知行二者都说成是意识活动,而是有区别的,也并不否定知行各有作用。
朱熹认为,学、问、思、辩都是知,只有笃行才是行。但王阳明认为,学不仅包括知,而且包括行。学、问、思、辩是学也是行,不只笃行才是行。这是对朱熹思想的又一个发展。作为认识过程,行贯穿于学、问、思、辩之中,不是等学、问、思、辩结束之后,才去实行。王阳明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就知行关系而言,这话是很有见地的。这已接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取得认识这样的光辉思想。
朱熹把“格物穷理”和实行分作两事,认为穷理属知,涵养属行。他所谓行主要指道德践履,而穷理则比较广泛,其中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他虽然提出,“格物致知”不能只知而不行,不能离开行,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格物穷理”应该包括行。这是他知行学说的一个不足。王阳明则前进了一步,他认为:穷理之学应当包括行。他说:“学问思辩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辩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这也是对朱熹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当然,王阳明所说的行,同样是道德践履;而他所谓穷理,则主要是“穷心中天理”。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还包含着以行为基础,知靠行来检验的思想萌芽,这也是对朱熹知行说的进一步发展。他所谓“未有知而不行者,不行只是未知”,“不行不可谓之知”,本是从程朱那里继承过来的,但内容有所发展。一方面,他认为知必须措之于行。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如果不行,知也就不成其为知,这是知以行为目的。另一方面,他还认为,知必须从行中取得。经过行来检验,其知才算“真知”。否则,便只是“悬空谈说”、“揣摸影响”而已,这就有行为基础以及行检验知的意义。
三
格物致知说,是朱子学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以及二者的关系。朱熹说:“致,推极也;知,犹知也。推极吾之知,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经一章)这是他对格物致知所作的解释。按照这个解释,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并穷至其极处。所谓理,当然指本体之理,但也有认识事物规律的意思。他所谓物,所指极广,“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朱子语类》卷57)。“吾闻之也,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大学或问》卷下)可见,朱熹所谓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朱熹所谓致知,是致吾心之知。这个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知觉,指心的认识作用;另一方面是知识,指心之所觉,即对心中之理的认识。他说的:“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这个知不是指知觉,而是指知识,即心中所具之理。推致吾心之知,是他的“致知说”的主要内容。致知是“就心上说”,格物是“就事上说”。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总之一句话,致知是由内向外,格物是由外向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内外合一”之学。
王阳明对于“格物致知”的讨论也是很多的。他一方面批判朱熹,一方面又继承朱熹的思想。他把朱熹的内外并用的方法发展为专求于内的一种方法。他否定朱熹的格物说,即否定朱熹向事事物物穷理的一面;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即接受了朱熹推致吾心之知的一方面。王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而朱熹所说的知,就其实质而言,也是指心中的天理。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是一致的。他不以朱熹格物之说为然,就在于承认“心外有物”,这是他同朱熹的一个主要区别。按照他的良知说,孝亲之理,在心中而不在所亲者身上,恻隐之理在吾心中而不在孺子身上。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他把朱熹的格物说看成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传习录》下)。
针对朱熹的这个思想,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格物致知说”。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他批判朱熹的“内外合一并进”的认识论,否定了朱熹由外到内的一面,而指出了一条由内到外,由心到物的认识路线。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格物思想的转折点,他否定了向物求理,认为外物本无可格,把格物穷理由外在事物引向主体自身,为此他发展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以打通把格物穷理理解为心上做工夫的道路。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从主体的“身心”上用功。即在人的意念发动处做“为善去恶”的工夫。
王阳明经过对朱熹“格物”说的批判和改造,使“天理”主观化,成为与人心合一的道德理性,人心的自性本原,以及主体自知自明的道德灵觉。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是“心”通过格致外物去体会,而是由心的“良知”来发放,使万事万物各得其理。这种“心之体用”说已超出了道德修养论,而涉及到本体问题。
《大学》提出:“致知”,王阳明认为致知的知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因而把致知发挥为“致良知”。良知不仅是先验的性质,而且具有普遍的品格,王阳明晚年明确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他以致知为致良知,什么是致良知?他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阳明全书》卷26)如果说朱熹格物的观念有三个要点,“即物”、“穷理”、“至极”的话,王阳明的致知的观念也有三个要点,即“扩充”、“至极”、“实行”。以“至”解释致,即扩充良知而至其极的同时,王阳明强调:“知如何而为温清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这都是指出“致知”包含着将所知诉诸实践的意义。表明“行”是致良知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所以,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去,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这是对朱熹致知说的发展。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说到底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点同朱熹并无本质区别,而比朱熹表现得更加明确,更加彻底。他虽然说,良知是人人所同具,“有不容于自昧者”,但又“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答陆原静书》,《传习录》中)格物就是去蔽,蔽之最大者就是人欲,只有消除人欲,才能扩充心中天理。学问的根本目的,“不过是去此心人欲之杂,存吾心之天理而已”。
以上从心与理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和格物致知三个方面,分析了王阳明对朱子心学思想的发展。从中可见,朱熹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达到了最高峰,完成了心学体系的建构,集宋明理学之心学之大成。
责任编辑:郭美星
B248.2
A
1008-4479(2017)02-0047-06
2016-11-29
张品端,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