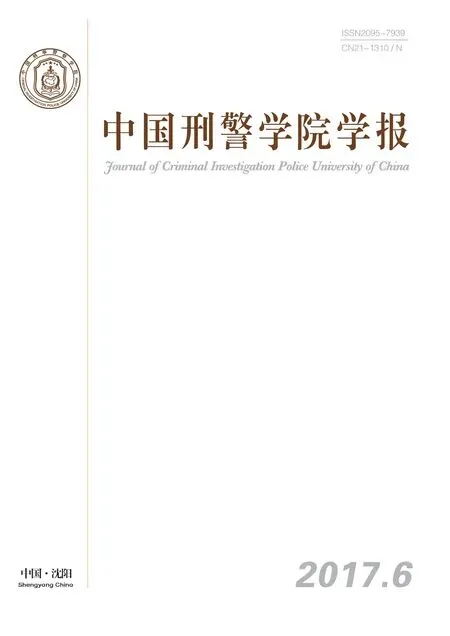反家暴案件中正当化事由的适用与限制
尹子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4)
1 问题的提出
2016年3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指出,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并通过30多个条文,全面详细地给出了受害人在家暴面前可以采取的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途径。但在二者未及时有效介入的场合,受害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家暴,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以暴制暴”,杀死施暴者。例如,1990年,刘某某与张某某结婚,育有3个孩子。婚后,丈夫张某某经常用铁棍、皮带、斧头、擀面杖等器械殴打刘某某。2001年后,暴力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甚至两三天一次。而且,每次张某某殴打她时都要关上门,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也不让孩子们出去;越是有人劝解,打得越狠。张某某的妹妹、父亲还曾因为劝阻其暴力行为而受到他的殴打。期间,刘某某想过报警,但是一想丈夫最多也就是被拘留几天,出来后一定不会饶了自己,只好作罢;其也想过离开,但被公公劝阻,也因自己舍不得三个孩子,而未能成行。村委会曾就此事进行过调解,但没有效果。刘某某也曾想过离婚,但被丈夫威胁到,“如果敢提离婚,杀了你全家!”2002年10月,张某某又对她实施暴力,用铁锹拍破了她的脑袋,血从头顶漫至眼睛,这让刘某某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2002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刘某某在赶集时看到了“毒鼠强”,找不到出路的她“突然下了狠心”,购买了14支,并心想,“只要他让我和家里人把这个年过好,我就不做过分的事”。不幸的是,2003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十三),张某某再次用斧头殴打了刘某某,这也让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1月17日下午,刘某某在给丈夫做咸食时,将“毒鼠强”掺入其中,张某某吃后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12年[1]160-161。
此案可谓大量反家暴案件中,“以暴制暴”的典型。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法院一般会在量刑阶段考虑被告人的防卫因素、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以及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等因素,酌情从宽处罚①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已在2015年3月2日所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该《意见》第20条指出,“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与此相对,部分学者则尝试从定罪层面入手,寻找被告人出罪的教义学资源,尤其是行为构成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避险等正当化事由的可能[2]13-26。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如果真如前述学者们那样得出肯定性的结论,那似乎就为问题的解决找到了更多的可能。
2 正当防卫的适用与限制
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以暴制暴”的场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正当防卫的适用:第一种情况是,受暴者在面临施暴者正在实施的暴力时,采取反击;第二种情况是,受暴者在施暴者尚未施暴前或者施暴后,趁其不备(比如吃饭或睡觉时),实施“反击”。
2.1 第一种情况下正当防卫的适用
适用正当防卫的首要前提是,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这里,“迫在眉睫的、正在进行的,或者说仍在继续进行的侵害可谓正在进行。”[3]而就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而言,不仅包括着手后的未遂状态,也包括接近未遂的使法益面临紧迫威胁的预备[4]433。在第一种“以暴制暴”的案件中,可以认定受暴者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满足实施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受暴者的防卫行为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1)防卫行为必须是必要的。防卫行为的必要性首先是指,防卫行为是适当的,能够起到防卫的作用;其次,防卫行为必须是必要的、最轻的,即在存在多种防卫手段的场合,应当选择损害较轻的手段。比如,如果一个警告或者一个拳头就可以制止侵害,就没有必要射杀攻击者。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要性的判断不是事后的,而应该是事前的判断;不能仅从防卫行为造成的结果来判断防卫行为的必要性,也即防卫行为造成的结果与所要保护的法益之间的比例或平衡关系不是考虑的重点,而应该从防止侵害的具体需要出发来认定防卫的必要性;尤其在防卫人对防卫手段的效果并不能准确把握时,其不必选择危险更小的防卫手段[4]43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5年3月2日所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也确认了这一点。该《意见》第19条第2款指出,“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所以,从防卫必要性的角度来讲,只要受暴者实施的反击行为足以制止正在进行的家暴行为即可。
(2)防卫行为的要求性。这里所要做的努力在于对符合必要性的防卫行为进行社会伦理上的限制。具体来说,对于发生在保证人范围内(尤其是配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暴力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保护的保证人对受其保护的人的攻击仅具有有限的正当防卫权。这样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到行为人之间存在着团结关系,保证人针对受保护人有特殊的团结义务和照料义务,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存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克制[4]453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刑法理论及实践中,这种基于保证人地位或者家庭关系而对防卫限度进行限制的观点存在淡化的趋势。此外,也有学者对这种限制提出了颇有道理的批评。参见:薛智仁.家暴事件的正当防卫难题——以赵岩冰杀夫案为中心[J].中研院法学期刊,2015(16):47-54;许恒达.从个人保护原则重构正当防卫[J].台大法学论丛,2016(1):372-374。。基于此,虽然《意见》确认,在防止家庭暴力的场合,“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行为是必要的;但是,毕竟实施暴力的不是别人,而是防卫者的家人,基于保证人义务或者团结义务的要求,在有多种手段可以避免暴力的情况下,行为人应尽量保持克制,选择防御性的温和的手段来避免暴力。也即,我们不仅要看到家庭暴力中“暴力”的一面,还应注意“家庭”的因素,动辄兵刀相向不是家庭生活的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正是“家庭”这一因素使得家暴的发生更为隐秘、频繁、长期、不容易被制止,而没有人是为了献出生命或者承受长期的虐待而踏入家庭生活,因此保证人义务或者团结义务对行为人正当防卫权的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尤其在保证人面临的是严重的身体、生命损害威胁,或者保证人承受着长期持续的虐待的场合[4]454。
具体到文章开头的案件,如果刘某某在被丈夫第一次殴打,而且殴打的程度并不严重时,在能躲避的场合,基于保证人义务的要求,其应该尽量躲避或者寻求其他救济手段,而不是一棍将丈夫打伤。而在长期的家暴与虐待之后,如果丈夫再次举着斧头向她奔来时,刘某某即便是可以躲避,也没有必要,更没有义务躲避。不过,本案的事实是,刘某某在丈夫实施暴力之前,就用“毒鼠强”毒死了丈夫,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情况:
2.2 第二种情况下正当防卫的适用与限制
如前所述,在直面家暴的场合,受暴者当然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不过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在一个存在长期持续严重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在施暴人尚未施暴前或者施暴后,受暴者趁其不备(比如吃饭或睡觉时)实施“反击”,甚至将施暴者杀害,刘某某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类案件中,一般认为不法侵害“尚未正在发生”,如果要适用正当防卫,便需要对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进行扩张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便是攻击尚未发生,但如果待攻击发生时便不能够实施防卫,或者只能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实施防卫,那么就可以认为攻击“正在进行”[4]432。这种观点其实是将防卫效果作为判断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的标准,从而使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判断从纯客观走向规范化,从存在论走向目的论。具体到家庭暴力的场合,如果可以说明,虽然暴力行为尚未开始,但待攻击真的来临时,受暴者往往不能或者难以实行防卫的话,就可以认定家庭暴力行为“正在进行”。
应该说,防卫效果对判断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是有影响的。倘若不考虑防卫效果,大可将不法侵害的着手等同于不法侵害的开始,但这样做会使大量的防卫行为变得没有意义。正是基于此,一般认为不法侵害的开始时点,不仅包括着手后的未遂状态,也包括接近未遂的使法益面临紧迫威胁的预备。但是,如果完全以防卫效果为导向来界定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似乎就走得太远了:这一方面会使一些离着手较远的不法侵害的预备行为被包括进来,另一方面也会将一些因为尚未着手还不能被认为是不法侵害的行为包括进来。对于前者,如果我们承认不法侵害的预备行为也是不法行为,那么容易将对预备行为的防卫与对实行行为的防卫混淆;对于后者,容易将对尚不能被认定为是不法侵害的危险的避免当成对不法侵害的防卫,混淆防御性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
此外,在现代社会,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基本为国家所垄断,公民仅被允许在紧急状态下,在公权力不能及时介入的场合,实施防卫或者避险。而从正当防卫的结构本身来说,(与紧急避险相比)其不要求防卫行为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实施的,同时对防卫限度的要求也较为宽松。如果在时间要素上也以防卫效果为导向,便容易使正当防卫失去其作为公民紧急防卫权的本来面目。所以总体来说,对于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判断基本上是客观的,防卫效果的考量仅仅是辅助性的,那种完全以防卫效果为导向的做法应予以拒绝。
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多数的家庭暴力具有连续性、紧迫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应该将这些连续性、经常性的不法侵害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从而得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结论,允许受害者在此期间实施正当防卫[5]。而陈璇博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正当防卫中之所以要求“不法侵害”,其目的不在于追究不法侵害人的法律责任,而在于为公民防卫权的生成确立先决条件;多个行为的连续性可能成为使其被评价为一罪的理由,但不足成为以使其融合为一个侵害行为的根据;上述观点混淆了罪的单一性与行为的单一性[2]15。其实,这类似于将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当成一个完全的精神病人,从而认为他对自己在所有时间段内(包括精神正常期间)实施的犯罪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从逻辑上讲,有偷换概念曲解小前提的嫌疑。此外,这种直接将多次家暴间隔期内的平静阶段评价进家暴行为本身或者根本就不予评价的做法,其实是用对侵害行为的重新解释来掩盖对侵害行为是否正在进行的认定,用规范评价来取代事实判断,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问题。
综上,在家暴的场合,既不能因为待家暴来临时不能或者难以防卫,而将尚未开始的家暴行为认定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也不能基于家暴行为的连续性、经常性,而将不同次的家暴行为视为一个整体,从而肯定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此,在施暴者尚未施暴前或者施暴后,受暴者趁其不备(比如吃饭或睡觉时)实施“反击”甚至将施暴者杀害的行为,因不满足时间性要件,不能被认为是正当防卫行为。具体到刘某某案,刘某某在其丈夫尚未实施暴力之前,就用“毒鼠强”毒死丈夫的行为不满足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要件,不是正当防卫。
3 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与限制
根据刑法第21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一般认为这里的紧急避险行为主要是指针对与危险源无关的第三者实施的避险行为,即攻击性紧急避险;但理论上认为,还存在针对危险源实施的避险行为,即防御性紧急避险[6]189。从第21条的表述来看,刑法并未否定防御性紧急避险存在的余地。那么,具体到家暴的场合,对于前述不符合正当防卫适用条件的第二种情况,似乎可以考虑适用防御性紧急避险。
3.1 危险的现实性
适用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前提是,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关于如何判断“危险正在发生”,理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判断应当与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判断一致[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有补充性要件(即避险行为必须是不得已的)的限制,较之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时间要件的认定更为缓和[8]。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因为危险这个概念更多地与将来相关,强调的是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高度的盖然性,而紧急避险正是在结果的发生虽有盖然性但尚不能完全确定时,赋予行为人的紧急权,其对现实性的要求不如正当防卫那样有约束[2]24;另外,因为有补充性要件的限制,时间要件上的放宽也不会破坏紧急避险作为公民紧急权的属性;如果对紧急避险时间要件的要求像正当防卫那么严格的话,在一些情况下容易导致正当防卫与防御性紧急避险的竞合,而因为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还有补充性要件的要求,这容易使其失去适用上的优势,丧失适用的意义。
在这样的理解下,理论上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肯定危险正在进行:第一,危险虽然不是直接面临的,但是如果等到危险来临,要么难以避免,要么要冒着巨大的危险来避免的话,就可以肯定此时危险就已正在进行。在这里,与正当防卫不同,紧急避险时间要件的判断其实是以避免效果的考量为导向的。第二,持续性的危险。这里主要是指,一种危险威胁的状态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随时都有转化为实害的可能[6]182。从判断标准来说,危险的认定应当从事前的、客观的、考虑行为人特别认知或者说案件具体细节的第三人的角度出发。具体到家庭暴力的场合,如果暴力虽未正在发生,但已经有发生的征兆,待到暴力发生时,受暴者难以避免的话,就可以认为暴力正在发生。或者说,虽然一次家庭暴力已经结束,但是基于暴力发生的频繁和持续,在短时间的将来可以合理地预见到下次暴力的发生,那么也可以认定暴力正在发生[9]。比如,如果丈夫经常在醉酒后关起门来暴打妻子和孩子,而当丈夫再一次在心情不好的情况下拿起酒瓶借酒浇愁的时刻,就可以认定危险正在发生,允许妻子实施避险措施。再如刘某某案所展示的,虽然在丈夫用斧头打了她之后,暴力行为已经结束,但是基于两三天就一次的施暴频率、动辄刀斧相见的施暴手段、必定关起门来殴打的施暴情景等,可以想见下次暴力的发生以及刘某某面对暴力时束手无策的困境,此时就可以认定暴力正在发生,刘某某的反击行为符合紧急避险时间要件的要求。至于她的避险方法(用“毒鼠强”毒死丈夫)是否必要以及适当,则是下面要考量的重点。
3.2 避险行为的补充性
避险行为的补充性主要是指,对于危险的避免而言,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避险行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的;当然,避险行为要有避免危险的可能,如果所有手段在事前看来都不可能避免危险,就没有必要也不能实施避险[10]208。那么在家暴的场合,比如刘某某案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除了杀害施暴人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避免家暴的办法?
按照现有法律社会制度的设置,应该说是有多种途径可助受暴者逃离被家暴的命运。但制度设计与现实之间总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契合,一些看似可行的手段在事实上却难以操作,所以紧急避险补充性要件的认定必须要结合具体案件来分别考量。更重要的是,在认定紧急避险补充性的场合,对一种避险手段是否可行的判断,是要看其能不能避免即将发生的具体的暴力,还是看他能不能助受暴者彻底摆脱家暴?应该说这两种目的有重合,但更有层次上的差别。一些手段对于避免即将发生的一次具体的暴力来说是可行的,但却不能使受暴者永远摆脱被家暴的命运,也即,从后一种目的出发,更容易得出“除了杀害施暴人之外,没有更好的避免暴力的办法”,从而肯定紧急避险行为的补充性。但是,对于紧急避险而言,前一种目的是具有刑法意义的,后一种目的虽更具有社会意义,但却不是作为公民紧急权的紧急避险所应承担的。因此,就补充性要件的判断而言,问题的核心应该被修正为:除了杀害施暴人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避免即将发生的具体的一次暴力的办法?
可以被纳入考量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救济途径:向妇联、居委会、村委会等投诉,向公安报案,选择协议离婚或者起诉离婚,提起关于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诉讼,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逃跑等。如前所述,如果从彻底避免家暴的目的出发,大抵可以得出所有这些手段都是杯水车薪,不能助施暴者彻底脱离苦海[2]20-22。比如,妇联、居委会顶多也就是劝解教育几句,作用有限;即便是施暴者被拘留几天,但放出来之后,施暴者仍然会继续施暴,甚至会更严重;选择离婚的话,且不说能不能离得开,即便是离婚成功,也阻止不了施暴者继续骚扰、施暴;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的话,时间一般较长,取证也比较困难,再加上执行上的困难,往往也难以彻底阻止家暴;而对于妇女而言,如果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再加上家庭成员的羁绊,逃跑基本上不可能,即便是逃走了,也会陷入困顿之中。
但是如果从避免一次具体的暴力出发,则可能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具体到刘某某案,显然村委会、亲友的劝解是不能阻止具体家暴的;因为丈夫的威胁,离婚这条路也走不通;就报警而言,刘某某未尝试,客观情况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持,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相当一部分警察并不愿介入这些“家务事”,有的仅是训诫几句,有的干脆不予处理。在本案中,如果当地警察大多也是这样的作风,应该可以肯定,报警这条路也走不通。而如果像刘某某所想象的那样,一旦报案,警察会将其丈夫拘留几天的话,则要进一步分析:在本案中,刘某某丈夫凶残成性,可以想见,即便是被公安拘留几天,也仅仅是延缓了刘某某被家暴的时间,一旦其丈夫被释放,这顿暴打仍然避免不了,甚至会即刻来临。在这里,也可以说,公安的介入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避免一次即将发生的具体暴力的效果,更不可能使刘某某彻底摆脱家暴。还有,假设刘某某虽然报过警但事后仍避免不了被打,或者说报过警但警察不管的话,也可以得出报警这条路走不通的结论。不过实践中,问题判断的难点在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出公安的介入行为(比如拘留几天)也不能成功阻止一次具体的家暴?在本案中似乎可以谨慎地得出否定的结论。但如果,施暴者被拘留几天后释放,隔了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又因为其他具体的原因实施了家暴行为,就很难说公安之前的拘留行为没有成功阻止了一次具体的家暴;就离家出走而言,如果说从人情的角度出发,大抵也可以承认,由于有孩子的牵绊,其在规范上可期,而事实上不能;但这一点似乎从责任的角度,肯定行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更为合理①需要指出,就刘某某案而言,陈敏(曾接受当地妇联的要求为刘某某做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鉴定)在“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一文中披露了更多的案件细节,比如刘某某曾经尝试独自外出打工,但丈夫发现她的行踪后,找到了她打工的地方,在那里又是砸电视、烧衣服,又是打她。而在赵凌的“杀夫:悲凉一幕”的新闻报道中并未提到这一细节,不能相互印证,本文在案情简介处并未收入这一情节。如果该情节属实,那么对于刘某某而言,可以肯定,离家出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参见:赵凌.杀夫:悲凉一幕[N].南方周末,2003-07-03(A12);陈敏.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J].诉讼法论丛,2004(9):134-172。。而就刘某某案之后才出现并为《反家暴法》所进一步规范的人身保护令制度而言,尚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调研认为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不能真正起到震慑施暴者的作用,而一些调研的结论则相反[2]21。但不管怎样,如果受暴人有虽然申请人身保护令但不起效果的经历的话,也可以肯定这条路走不通。
总的来说,在家暴的场合,对紧急避险补充性要件的认定而言,要结合具体案件分析。同时要注意,避险行为的目的不是帮受暴者彻底摆脱家暴,而是避免即将发生的具体的暴力。
3.3 利益均衡
紧急避险的成立除了需要满足危险正在发生,避险行为是在不得已条件下实施的这两个要件之外,还要求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通说认为,这里的必要限度是指,紧急避险所带来的损害要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另外有力的学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的前提下,足以排除危险所必需的限度”,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存在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但却超过了必要限度的情况;其次,即便是损害了同等法益,也不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充其量只能认为这样的避险没有意义[10]220。总结来看,也即,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首先应为避险所必需,其次不能大于所避免的损害。但是,这样的观点被批判为充满了社会功利主义的味道,忽视了无辜第三人所应享有的自主自觉的自由权利,有把无辜第三人工具化的嫌疑。更合理的理解角度在于,只有无辜第三人基于社会连带责任,有义务在特定范围内容忍损害自身利益的避险行为时,才能成立合法的紧急避险[11]。以此出发,即便是我们仍然坚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认定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问题,那么也应该注意到,与避险人所代表的利益相比,无辜第三人所代表的利益处于优势地位,应该是利益衡量所关注的重心;至少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所避免的损害只要等于或者稍稍大于避险所带来的损害时,就成立紧急避险。
但不管怎样,上述争论主要针对攻击性的紧急避险,在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场合,利益之间的衡量又会不一样。首先没有争议的有两点:第一,在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场合,利益均衡的要求比正当防卫严格,但比攻击性紧急避险宽松;第二,在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场合,与危险源所代表的利益相比,避险者所代表的利益占据优势地位。就第一点而言,正当防卫中,防卫人面临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场合,避险人侵害的是无辜的第三人的利益;而在防御性紧急避险这里,避险对象不是无辜的第三人,而是危险源,但同时危险并未表现为不法侵害或者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如果承认紧急权损害对象与危险源之间的关系影响利益衡量的判断的话,可以认为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利益均衡标准介于二者之间[2]22。就第二点而言,可以类比攻击性紧急避险中避险人所代表的利益与无辜第三人所代表的利益的比较,得出相似的结论[12]。
从这两点结论出发,有两种处理防御性紧急避险利益衡量的办法:一种认为,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攻击性紧急避险应适用相同的利益均衡标准,但在具体的利益衡量中,应该特别考虑防御性紧急避险中避险对象是危险源这一事实;另一种认为,防御性紧急避险应当适用独立的利益均衡标准,即所避免的损害与避险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相当,这里的相当是指,只要避险行为所保护的利益不明显低于所侵害的利益即可[4]489。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防御性紧急避险在利益衡量问题上的特殊之处,有争议的是,这样的特殊之处足不足以使得防御性紧急避险获得独立的利益衡量标准。如果我们认为,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除了法益比较之外,还有多种因素需要考量的话,那么第一种观点似乎更为稳妥和实际;但是如果看到二者质的不同的话,第二种观点则更为合理。也即,在攻击性紧急避险那里,无辜第三人所代表的利益处于优势地位,而在防御性紧急避险这里,避险者所代表的利益占据优势地位;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利益均衡标准虽然介于正当防卫与攻击性紧急避险之间,但却偏向于正当防卫。
从前述的第二种衡量标准出发,只要所避免的损害与避险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相当,就可以肯定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成立。具体到家暴的场合,比较棘手的是,受暴者常会为了避免家暴而将施暴者杀害。那么对于受暴者而言,所要避免的损害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说与避险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即造成施暴者死亡这一结果相当?陈璇博士从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出发,认为受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行为威胁的人身安全与生命法益即是相当的,也即,受暴者所要避免的损害达到上述重大人身安全的程度时,即可认为其与避险行为所带来的造成施暴者死亡的损害相当[2]23。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刑法第20条第3款所指出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威胁重大人身安全的行为是包含时间要素在内的。也即,只有这些行为处于正当防卫意义下的“正在进行”时,我们才可以说其与生命法益是相当的。当这些行为仅仅处于预备阶段或者更早以至于还不能被称为“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时,很难说这里存在一个与生命法益相当的所要避免的损害,而这种情景恰恰是防御性紧急避险所主要处理的。因此,如刘某某案所呈现的那样,在家暴的场合,在施暴者尚未施暴前或者施暴后,受暴者趁其不备(比如睡觉、吃饭时)将其杀害的行为,一般不符合防御性紧急避险利益均衡的要求,不能阻却违法。
3.4 认识错误问题
如前所述,不同于直面家暴的场合,在施暴者尚未施暴前或者施暴后,从客观角度来讲,受暴者应该有多种手段来避免家暴;但实践中的情况却是,相当一部分受暴妇女不相信这些手段能够有效地避免家暴,而最终选择将施暴者杀害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摆脱被家暴的命运;也即,受暴妇女常会对防御性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产生认识错误,认为除了杀害施暴人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家暴。“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受暴妇女会经常产生这样的认识错误。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由美国临床法医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提出,该理论由“家庭暴力的周期性”和“后天无助感”两组概念组成。前者旨在说明家庭暴力的发生是有周期性的,一般分为紧张情绪的积累阶段、家庭暴力爆发阶段、施暴人道歉和两人重归于好阶段,如此反复,家庭暴力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后天无助感”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如果受虐妇女不能在受家暴的早期采取反抗措施,那么她再想摆脱施暴人,便会异常困难,久而久之,便会感到无助,变得越来越被动和顺从,直到家暴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待家暴真的来临时,“后天无助感”已经使受虐妇女不相信、不敢、进而丧失了选择其他反抗方式的可能[1]136-138。
也就是说,对于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特征的妇女而言,对防御性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产生认识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①当然,“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以作为判断行为人认识错误是否可以避免的重要甚至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紧急避险所要求的补充性要件并未得到满足,家暴受害人对作为紧急避险基础的事实产生了错误认识,构成假想避险;但因为这样的认识错误不可避免,且是由于施暴人的施暴行为造成的,应该适用刑法第16条的规定,认定为意外事件。具体到在刘某某案的审理过程中,就有专家为其做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鉴定,认为刘某某在心理上有典型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症状[1]161-162。如果这样的专家鉴定能被采纳,似乎也可为刘某某的出罪(免除罪责)寻找到可能。不幸的是本案并未采纳,实践中其他案件也没有采纳的迹象。所以,即便是承认“受虐妇女综合症”所描述的症状,大多也只是在量刑阶段予以考虑。
4 结论
在家暴的场合,与实践中的做法不同,理论上更多地从定罪的角度来为被告人寻找出罪的教义学依据,尤其是行为构成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避险等正当化事由的可能。这种先考虑出罪的可能,在得出否定的结论后,再考虑量刑的思路本身是可取的,也是实践中缺乏的。从文章的分析来看,在直面家暴时,受暴者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在施暴者施暴前或者施暴后,受暴者趁其不备将其杀害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虽然符合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时间要件,但却很难符合补充性要件及利益均衡的要求,一般不能阻却违法;仅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借助“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来说明受暴者存在不可避免的关于紧急避险补充性要件的认识错误时可以阻却责任。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似乎只能在量刑层面考虑相关情节。
此外,就反家暴案件中正当化事由的适用而言,时间要素是其中的关键点:首先,时间要素决定了是适用正当防卫,还是防御性紧急避险;其次,虽然防御性紧急避险对时间要件的要求较为宽松,但时间要素却深刻影响着对补充性要件、利益均衡、甚至认识错误是否可以避免的判断,这是由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避险的紧急权属性所决定的;最后,就反家暴案件中正当化事由的适用而言,虽然文章得出了相对消极的结论,但这并不是否定受暴者的反家暴行为,更不是鼓励受暴者忍气吞声。只是说在反家暴的过程中,作为公民紧急权的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避险不能为此承担更多,也难以成为受暴者彻底摆脱家暴的主要途径。或许对于受暴者而言,在陷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窘境之前,更好的办法应该是选择不再沉默,在家暴初期就寻求社会或公力救济,这应该也是《反家暴法》的初衷所在。
[1]陈敏.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J].诉讼法论丛,2004(9):134-172.
[2]陈璇.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兼对正当防卫扩张论的否定[J].政治与法律,2015(9):13-26.
[3]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09.
[4]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33-489.
[5]钱泳宏.“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0-31.
[6]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9,182.
[7]大塚仁.刑罚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94.
[8]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7.
[9]Thomas Rotsch.Die Tü otung des Familientyrannen:heimtückischer Mord?- Eine Systematisierung aus aktuellem Anlass[J].Jus,2005:15-16.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8,220.
[11]王钢.紧急避险中无辜第三人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兼论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J].中外法学,2011(3):615-617.
[12]赵栩,谢雄伟.防御性紧急避险制度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792-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