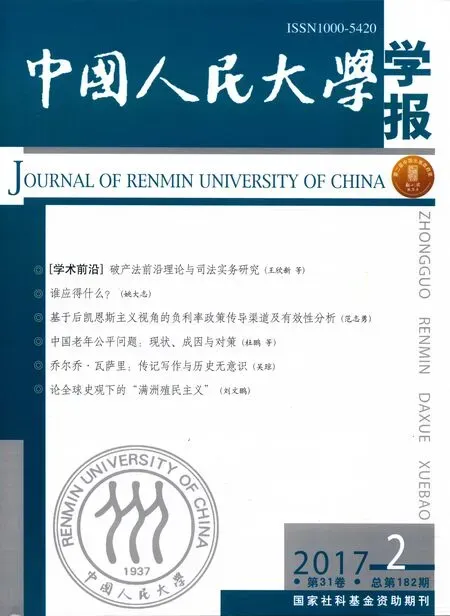破产法视野中的担保物权问题
徐阳光
破产法视野中的担保物权问题
徐阳光
破产法中的担保物权处理需关注担保法与破产法的交互影响,核心在于抵押权、质押权在破产程序中的限制和保护问题。担保物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破产法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我国破产法借鉴了国外的中止(暂停)理论,确立了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的抽象规则,但对破产清算程序如何处理存在争议,亟须立法明确,同时,担保物权人的救济措施问题重要性凸显。担保物权的保护主要体现为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确认,破产法在清偿顺位上应坚守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地位,尤其是在担保物权与劳动债权、税收债权的关系处理上,应当坚持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并严格遵循物权特定原则,对于一般优先权的处理,则遵循优先权的法定原则且不得违背破产法确立的基本清偿顺位规则。
担保物权;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自动中止;优先受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自2006年颁布至今已逾十载,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遇到了因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法本身的不完备和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带来的挑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改革背景下,总结和反思企业破产法实施的经验与问题,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制度,已是当下中国之重要改革任务。其中,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破产和解与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侧重抵押权和质押权)理当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物权与债权相比具有优先性,更是因为担保物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司法实践也反复揭示在别除权等理论基础上重塑担保物权保护和限制之规则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以破产法与担保法的交互影响为分析背景,侧重对担保物权的暂停行使、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问题进行解释论分析,并从立法论上提出制度改进的建议。
一、破产法与担保法的交互影响
破产与担保均是源于罗马法的古老法律制度,当今世界各国有关破产和担保的立法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彼此在看似各自独立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实则在有形或无形中发生着重要的交互影响,或是担保制度的变化带来破产立法的跟进,或是破产制度的突破倒逼担保立法的修正,此种交互影响或直接反映在立法文本中,或间接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因此,关注破产程序中的担保物权问题,势必应从破产法与担保法(侧重物权担保)发展的交互影响开始,并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维度进行分析。
(一)担保法的发展对破产法的挑战
担保制度的基本内容较为稳定,但在形式上变化多样,整体而言,担保制度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趋势:一是担保物权的范围日益广泛;二是非典型担保型态发展迅速;三是担保物权实现的程序渐趋简化。
首先,担保物权范围从权利形态到担保物的种类都呈现日益丰富的发展趋势。以中国法上的物权担保为例,其发展历程经历了《经济合同法》(1981年)、《民法通则》(1986年)、《担保法》(1995年)以及《物权法》(2007年)等多个立法阶段,最终确立了包括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在内的担保物权体系。[1]《物权法》一方面坚守物权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则放宽了抵押物和质押物的范围,在增加列举的可抵押物的同时,明确“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均可设定抵押,“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物权法》第180条)。不仅如此,我国以大陆法传统为特色的物权法还大胆引进了英国法上的动产浮动抵押权制度,同时允许动产抵押权和动产质押权并存。从立法发展趋势来看,担保物的范围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在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在防范风险、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基础上,赋予农村承包土地(指耕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功能,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其次,非典型担保型态发展迅速。学界一般将担保法、物权法规定的担保型态称为“典型担保”(即成文法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清楚、担保效力易于确定、担保权利义务稳定的担保型态),除此之外,具有担保性质的融资方式则被称之为“非典型担保”。非典型担保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物的担保内容的非典型担保,如按揭、所有权保留、附让与担保内容的证券回购等;二是无物的担保内容的合同型非典型担保,如附回购条款的保理等;三是混合型非典型担保,如融资担保。[2]这些新型的融资担保方式突破了传统典型担保的条框约束,程序简便、操作灵活且更具效率,在现实生活中大放异彩,但“在秉承概念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这些实践创生的担保方式与原有的典型担保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动摇了原有的概念体系……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下对各种新型非典型担保做出合理解释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3]在破产程序中,因各种债权清偿顺位的张力集中凸显,这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也就变得更为尖锐。
最后,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简易化。为提高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诉讼效率,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特别程序(第196条、第197条),由人民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担保物权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是,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担保物权人只能通过破产程序依法实现其优先受偿权,鉴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对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后担保权是否暂停行使存在争议,破产程序启动之前的担保物权实现程序也同样面临是否中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破产程序启动后担保权人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可以选择适用这种特别程序的问题。
担保制度的发展对破产法的挑战,除破产法原则上需要承认物权法、担保法确立的担保物权的范围及法律效力之外,同时还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第一,破产法关于担保物权的限制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担保物权和不同种类的标的物进行区分,概括的限制性规则可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担保权人的正当权益。第二,担保物的估值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这恰好是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保护的关键环节,这个问题既存在于破产撤销权的行使过程中,也体现在重整程序中对担保财产的估值和对担保权人的充分保护之中。第三,日益丰富的担保物权范围也将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分组表决规则产生影响。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将担保债权归为一组,可能难以满足现实的发展需要。第四,担保物权范围的扩充导致企业可供偿债的无担保财产锐减,重整融资中的“超级优先权”问题也因此更值得我们关注。第五,担保物的处置方式和表决规则也应当多元化发展,以因应日益丰富的担保物权范围。第六,对于基于金融创新所创设的新型担保权,破产法需考虑是否应该及何种条件下予以承认其破产隔离的效力,新型担保方式也对现有物债两分法也带来了挑战。
此外,更重要的挑战可能来自于间接层面却又是整体性的冲击,那就是担保制度的“与时俱进”带来的可能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无产可破”问题。担保物权范围的日益丰富、行权程序的渐趋简易,加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了贷款结构的变化,财产担保的贷款比重上升,造成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几乎没有未设定担保的财产,破产程序也因此沦为为担保权实现而进行的司法程序。如学者所言:“在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担保制度的完善和担保物范围的扩张,企业破产时,其绝大多数资产上通常都会附有各种各样的担保物权。在这一背景下,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和实现担保物权。”[4](P287)在此种情形下,管理人报酬的确定和支付、管理费用和其他优先债权的偿付都面临新的问题。
(二)破产法的发展对担保法的影响
担保物权为融资而产生,亦为防范破产风险而存在。从债务人视角考察,“鉴于担保物权的实现常会造成担保物价值之外的其他损失,如必要设备或厂房被拍卖会增加额外的停产与重置成本,因此,若仍具有清偿能力,债务人通常不会选择让债权人实现其担保权的请求……担保物权实现之时多是债务人陷入破产、无力腾挪之时”[5](P287)。正因为如此,破产法对于担保权而言,实则具有“试金石”之功效,若担保物权不能在企业破产时得到有效的维护,势必损害担保制度之本质。但是,现代破产法经历了理念变迁和规则重构之后,对担保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变迁。破产法最初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其立法宗旨与担保法类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平衡,再到社会利益本位的平衡协调。发展至今,当代世界各国破产法都十分重视大型公众企业的挽救问题,其典型制度变化就是国家通过司法权对私权利进行了必要的干预。[6]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对担保权暂停行使等限制性规则,以平衡担保权人与普通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次,破产重整制度的诞生打破了传统破产法的格局。传统的破产法就是破产清算制度,以收集财产和清偿债务为目标,而重整制度诞生之后,破产法的拯救功能日益突出,既包括直接启动重整程序挽救企业和事业,也包括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考虑是否有挽救价值以及时转入重整程序。“现代破产法,包括破产清算、和解和重整三套程序且可依法转换。破产法是警醒正常市场主体‘向死而生’之法,是帮助困境企业‘涅槃重生’之法,是促使失败企业、‘僵尸企业’规范退出之法。”[7](总序P1)现代破产法原则上尊重和承认担保物权的法律规定,但为实现挽救企业之立法目的,亦不同程度地确立了限制担保物权的规则,包括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包括担保财产)、担保权行权(自动)中止、重整期间暂停行使等诸多限制。
最后,破产法的“终极性”特征决定了优先权的冲突比非破产程序更为激烈,对担保物权造成了清偿顺位上的冲击。破产程序的启动,意味着与债务人相关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将彻底清理,最终结果是债务人的彻底消灭(破产清算)或涅槃重生(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此即破产程序终极性之关键。[8]因此,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6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此外,银行债权人也会在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时启动贷款加速到期条款,并采取“扣款抵债”等手段维护其利益。由此造成了担保物权与所有破产债权的竞争关系,再加上破产法本身和其他法律规定的优先顺位也交集在一起,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因此受到了挑战。
此外,破产法对担保法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面对破产程序启动后停止计算利息的规定,担保法应考虑是否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涵盖利息损失?第二,担保物权受限的规则是完全交给破产法来解决,还是借鉴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的规定在担保法中做出必要的规定?第三,担保法如何根据经济发展变化,对非典型担保(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以物抵债等交易型态)的效力及时做出立法回应,对于秘密担保权的效力,担保法如何在登记规则和对抗效力方面做出有效的规定,为破产程序中认定债权效力和确定清偿顺位提供实体法的支撑?
总之,破产法与担保法的交互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囿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其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与优先受偿问题,旨在为破产法中担保物权的限制与保护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二、破产法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问题
破产程序是一种概括性的执行程序,旨在公平清理全部债权债务关系,为此,程序启动前后为个别债权人利益所采取的诉讼和执行程序都要受到特别的处理。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立法指南》(以下简称《破产立法指南》)所言,有效破产法的关键目标是保护破产财产的价值不会因破产程序各方主体的行动而缩减,破产程序最需要防范的主体是债务人及其债权人。就债权人而言,现代破产法基本上都有一套用以保护破产财产价值的机制,不仅防止债权人在破产清算和重整程序中的部分阶段或全过程中通过法律救济手段启动强制行权程序,而且中止(暂停)已在进行中的针对债务人的诉讼和执行程序,其中,所谓“中止”是指“暂停所有的行动和延缓启动新的行动”[9](P83)。
上述中止(暂停)理论最主要的适用对象就是担保物权人,因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的差异,各国破产法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规则,我国企业破产法同样借鉴了中止(暂停)理论,在重整程序中明确规定担保权暂停行使,但在破产清算中则语焉不详,由此导致理论与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
(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1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但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该条款确立了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自动中止(冻结)制度,对物权法、担保法中确立的行权规则做出明确的限制。实践中,该条款的适用有效促进了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但也因条文规定过于抽象产生了理解上的分歧,出现了一些过度损害担保权人利益却无充分保护和有效救济措施的现象。为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破产重整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问题。
首先,立法目的的正确解读。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的规则,表现为阻止担保债权人行使权利,其所蕴涵的立法意旨在于:“为了给企业重整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避免因担保财产的执行而影响企业的挽救与生产经营。”[10]易言之,在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有助于企业的继续经营,使得债务人获得整顿业务的喘息空间,有时间制定和批准重整计划,并能采取其他措施”,“而且能为鼓励债务人发起重整程序提供重要的动力”。[11](P84)此外,虽然破产重整原则上并不会对全部或者主要财产进行清算变现,但在重整模式多样化的趋势下,也出现了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整体出售的“出售式重整”、“清算式重整”模式,担保物权的暂停行使客观上有助于提升这种整体资产处置的财产价值。*出售式重整又称事业让与型重整,是将债务人具有活力的营业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出售让与他人,使之在新的企业中得以继续经营存续,而以转让所得对价(即继续企业价值)以及企业未转让遗留财产(如有)的清算所得(即清算价值)清偿债权人。清算型重整,是指在重整程序中直接制定清算计划,清算计划以清偿债务为目的,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算、出售、分配的计划,与破产清算并无实质区别。参见王欣新:《重整制度理论与实务新论》,载《法律适用》,2012(11)。实践中,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重整、通用公司重整、雷曼兄弟重整都采取了出售式重整(363出售)模式,我国也出现了包括山东钜创公司重整在内的出售式重整案例。参见贺丹:《通用公司重整模式的破产法分析》,载李曙光、郑志斌主编:《公司重整法律评论》,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赵玉忠、张德忠:《关于企业重整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与应对——以淄博钜创纺织品有限公司重整案为视角》,载《山东审判》,2015(3)。尽管如此,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仍应坚守挽救企业和有助于企业继续经营的立法宗旨,但不宜过度伤害担保权人利益。因此,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的范围必须根据企业重整是否需要使用该项担保财产来确定,对非重整所必需的财产就不必暂停担保物权的行使,而应当及时清偿担保债权人。所谓“担保权暂停行使”,只是在程序权利(行权时间)上加以限制,而不影响担保权的实体权利(如担保物权效力和优先受偿属性)。实践中,有些重整的个案要求所有担保物权不加区分地一律暂停行使,甚至认为担保权的暂停行使也包括优先受偿权的暂停行使,这些做法是对担保物权暂停行使规则的误读,也严重损害了担保物权人的正当权益。
其次,担保权暂停行使范围的理解。依据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至少包括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其中“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留置权则以事先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为前提。*《物权法》第212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一旦将此类财产交还给债务人占有使用,则担保权及其优先受偿权便随之消灭。该法第240条规定:“留置权人对留置财产丧失占有或者留置权人接受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的,留置权消灭。”担保权暂停行使的规则如何适用于这两种担保物权型态?有学者认为,从担保权保护的角度看,凡是担保财产因占有转移回债务人而将失去担保权的担保方式,均不应暂停担保权的行使,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抵押担保和不转移质押权利凭证的质押担保这两种情况在担保中占大多数,其担保财产往往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通常也就可以解决原企业中重整需要财产的使用问题。[12]但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留置物可能恰恰是破产企业继续经营所需要的重要资产,而债务人尚无力完全清偿或提供令担保债权人单方满意的担保;管理人(或自行管理中的债务人)可能因为过于绝对的预判与过度刚性的规则而丧失对重整成功而言颇具价值的财产。[13]笔者认为,这种批评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取回质物、留置物”,考虑到了留置物可能为重整所需的问题,而且,取回质物和留置物的条件并不存在“过度刚性”的问题,后文即将述及的美国法上的“充分保护”也与之类似。如果放宽条件允许管理人在无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取回担保物,既是对物权制度的破坏,也违背了破产法自动中止的利益衡平原则,如《破产立法指南》所言:“(通过适用中止来保护破产财产)必须平衡兼顾通过实施广泛的中止以限制债权人的行动而使债务人得到的眼前利益和通过限制中止干扰债务人与债权人尤其是担保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程度而可能产生的长远利益。”[14]
最后,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的“充分保护”问题。我国《企业破产法》仅在第75条就担保物可能贬损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在第87条第2款第(1)项有重整期间担保权“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这种过于抽象的规定,与美国法上的周全的救济措施相比差距甚远。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却在担保物权制度方面有着超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即《统一商法典(UCC)》第9编*一些德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是美国私法领域中难得的在体系、逻辑上均超越德国法的法典之一。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的视角》,3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为美国破产法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提供了坚实的实体法基础。美国《破产法》中规定的“自动中止”针对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司法行为及行政行为等各种情形,涵盖面非常广,而就担保权而言,从财产范围来看,所有破产财产都要受到暂停行使制度变现的约束,包括所有权保留的情况。这一严格的“自动中止”制度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转,得益于自动中止的解除规则,其中缺乏“充分保护”是解除司法冻结的重要理由。充分保护是指无论担保物权人的债权是否进入破产程序都必须获得同样的保护。美国《破产法》第361条规定了三种非排他性的充分保护方式:一是现金支付,即债务人通过向担保物权人支付现金的方式补偿担保物价值损失,可定期或一次性支付;二是替代优先权,即提供额外或替代性担保;三是可使担保债权人在财产上的权益得到绝对同等实现的其他保护。[15]充分保护是重整案件中早期就需要进行判断的重要事项,其可能影响债务人重整及债权人求偿的最终结果。美国联邦第八巡回法庭在审理Martin一案中进一步揭示了判断某种利益是否受到充分保护的基本步骤:一是确立担保物权人利益的价值;二是确定上述价值的风险;三是判断债务人提议的对上述价值的充分保护是否可以近似地抵消这种风险。[16]不难看出,在充分保护的判断中,居于核心的往往是担保财产的估值问题,为此,美国法院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估值标准,包括清算价值标准、运营价值标准以及不同的市场标准。[17](P82)由此可见,破产重整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规则的设计,不是单纯的阻止担保物权人行权那样简单,需要在利益衡平原则之下设计精确的辅助规则。我国企业破产法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未来可以参考美国经验,在自动冻结的解除、充分保护的判断和财产估值方法等方面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
(二)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问题
从解释论视角分析,中国法上的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权是否暂停行使问题,法律规定不明确,由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9条(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第109条(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破产程序启动前的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属于执行程序应予中止,破产程序启动后担保物权行权冻结直至破产宣告为止,因为根据第107条的规定,只有宣告破产后,“债务人”方成为第109条所指的“破产人”,据此反推,在债务人未成为破产人之前,担保物权暂停行使。[18](P221)实践中,亦有法官撰文指出:“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担保物权人不能直接行使其担保权将担保财产变现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企业破产法》明确了重整期间担保物权暂停行使,未规定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由此反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因为法律没有做限制性的规定,所以原则上是不停止担保权行使。因此,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原则上不受第19条“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的限制。[20]台湾学者陈计男亦认为:“有别除权之债权人,不依破产程序而行使其权利……如有别除权之债权人于破产宣告前,业已实行别除权而经执行法院开始强制执行程序者,其执行程序不受影响,可继续进行,自不待言。”[21](P18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曾对此问题做了回应:“有担保的债权人即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原则上不受中止效力的约束,除非当事人申请的是重整程序。立法规定中止个别执行的目的,是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中止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并不能起到保障普通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作用,所以,中止执行的效力一般不及于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22](P152)虽是如此,争论依然存在,因为不少人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类似的担保物权限制,债权人会在债务人(濒临)破产时竭力抢夺和瓜分其现存财产而忽略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价值,产生所谓的“公共池塘”问题,使通过破产程序实现清理债务人财产的目的丧失了必要的基础。*关于这方面的表述,参见许德风:《论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3);程顺增:《论破产清算中担保物权实现的限制——以民法体系下实现之不同为视角》,载王欣新、郑志斌主编:《破产法论坛》(第10辑),217-21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疑问在于,《企业破产法》未对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担保物权限制做规定,却在第96条对破产和解程序中的担保物权行权问题做了规定*《企业破产法》第96条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权利。”,是否可以反推认为法院裁定破产清算之日起担保物权人不得行使权利?
从立法论审视,我国破产法确有必要反思如何系统全面地借鉴国外自动中止(暂停)制度,对破产清算中担保物权是否受限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必须与重整程序限制担保物权的理论基础区别开来,并在立法方式、限制期限、救济措施等方面加以规范。
首先,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受限的理论基础。破产清算程序侧重财产的全面清理和债务的公平清偿,破产重整则以挽救企业(事业)为己任,两者存在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对担保物权的限制也当有所区别。此外,破产清算程序还有可能转入破产重整程序,这种程序上的关联也当纳入考虑的范畴,但不能以此将重整程序中的限制规则简单套用到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立法指南》在指引“通过适用中止来保护破产财产”的制度设计时,也明确区分了两种程序。具体而言,重整程序中适用中止旨在实现企业的继续经营,破产清算程序中适用中止则在于“确保对程序进行公平和有序的管理,为破产管理人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免强行变卖导致无法实现清算资产的最大价值,同时又可在资产总体价值可能大于以零打碎敲的方式出售的价值时提供作为营运资产将其出售的机会”[23](P84)。
诚然,担保物权的设置使其可能会与债务人的其他财产有所关联,当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破产清算中对其他财产的维护、运用和处置。因此,即使是在清算程序中,为了保护债务人财产,保证它的价值以及升值,法律也会在权利行使方面对担保权人设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它受到财产上捆绑效应的影响。破产清算程序限制担保物权行权有两个目标:一是尽可能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二是为管理人进行财产状况调查和做出是否具有挽救价值的判断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目标的追求都应当避免过度伤害担保物权人的权益,需在立法方式和救济措施上做出考量。
其次,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受限的立法方式。从立法例考察,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担保物权受限,在立法方式上呈现出三种模式:一是中止措施自动适用的模式,典型者如美国。美国《破产法》第362条规定,破产申请一经提出,即可触发自动中止,违反自动中止的行为归于无效,行为人要赔偿债务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在特定情形下,还可能被判处惩罚性赔偿。[24]二是中止措施酌定适用模式,即根据具体案件的需要适用中止,避免不必要地适用中止和不必要地干涉担保物权人的权利,德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德国《破产法》第89条第1款规定,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债权人便不得再对破产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但该条规定并不能约束抵押权人,因为前述所指债权人并不包括别除权人。如果抵押物的变现干扰了破产程序的有序进行,破产管理人可以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的规定,主张对担保物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三是自动适用与酌定适用相结合的模式,即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误,协助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确保破产程序公平有序和具有透明度、可预测性而提出的替代做法,规定(在申请或程序启动时)中止措施可自动适用于具体指定的行为,经法院酌定可扩大该中止措施范围而适用于其他行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采取了这种做法。[25](P89)
具体到中国选择何种立法模式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前两种模式中考虑,但要充分认识两种模式各自的利弊。自动适用模式的优点在于覆盖面广、自动中止措施生效简捷,其弊端在于必须辅之以完善的救济措施,否则容易出现债务人滥用破产程序以阻却执行程序的现象。酌定适用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较好地维护担保物权人的利益,充分体现破产法对物权法、担保法的尊重,有助于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其弊端则是加重了管理人的举证责任,对法院的及时审查和判断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实践效果来看,管理人从职业规范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原则上只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尚未召开,一般都会提出暂时中止的申请,限制抵押权人的变现权,加之管理人的请求仅在会“严重影响”*“严重影响”是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30d条第1款的表述,实践中,法院关于“严重影响”的认定标准非常高,按照德国一位破产法学者的说法:“在信贷业务中,也许法院仅在中止抵押权实现导致债权人银行自身陷入困境时,才会根据该句规定做出拒绝中止的决定。”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的视角》,3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抵押权人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法院拒绝。鉴于中国目前管理人制度尚在培育发展中,加之前述担保物权范围日益丰富的发展趋势,债务人财产往往在破产之时均已设定了担保,如果选择酌定适用的模式,可能会给管理人带来大量的工作负担。因此,笔者建议选择中止措施自动适用的模式,但必须在中止期限和救济措施方面做出周全的设计。
再次,关于中止期限的规定。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美国和德国的中止措施均从破产申请时开始,但这种规定是建立在破产司法的市场化、法治化基础之上的,而且辅之以临时管理人来监督中止效力的实施情况。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破产申请和受理受制于诸多外在因素,加之临时管理人制度的缺失,不宜以破产申请作为中止的起点。此外,中止措施效力至何时为止?《破产立法指南》介绍了两种可能的模式:一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期限,从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立法来看,期限自30日至60日不等,在担保物对企业营运资产整体出售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可以延长适用期限;二是在整个破产清算期间对担保债权人适用中止,但如果有证据证明抵押资产的价值已受到侵蚀,无法予以维持,法院可下达解除令。[26](P85)笔者认为,第二种模式等同于重整程序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没有体现出重整与破产清算的程序差异,故建议在第一种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具体而言:规定一个中止适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担保物权原则上受限,解除受限的动议得到法院认可的除外,超过该期限的担保物权原则上不受限,管理人提出担保物对程序进行至关重要的动议并得到法院认可的除外。关于具体的期限,建议原则上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保持一致。如德国,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几乎会针对所有的抵押权提出暂时中止的申请,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后,则仅限于三种情形:一是债权人会议决定继续营业或整体出售资产,有关抵押物不可或缺;二是抵押物对于执行破产计划至关重要;三是不中止抵押物的变现会对破产财产的合理变现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27](P315-316)此种制度设计可倒逼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与担保物权密切相关的问题及时作出决议,亦有助于推动破产清算程序的有效进行。
最后,关于担保物权人的救济措施。自动中止模式下必须要对担保物权人的救济措施做出周全的规则设计。现行中国法上的条文无法得出公认的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自动中止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担保物权人救济措施的缺失。笔者建议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将以下情形列为破产清算和重整程序中担保物权人可提出自动中止解除动议的理由:一是债务人重整对此财产不存在权益,或者此财产对有效的重整来说并非必要;二是债务人或管理人无法为担保权人提供前述的“充分保护”,包括无法提供必要的利息补偿;三是债务人恶意申请破产的情形。美国《破产法》第362条规定,恶意提出破产申请属于获得救济的独立理由,即使存在充分保护,并且也不存在证明应予救济的其他理由,仅恶意申请本身就可以引发冻结的解除。虽然恶意申请存在判断的难度,但美国法院还是提出了一些可以认定“滥用司法程序和重整程序的意图”的因素,包括申请的时间、债务人是否正遭受“财务困难”、提出申请是否确实为规避正在审理的诉讼、申请的提出是否仅仅为逃避某个无利可图的合同。[28](P152)在此制度设计中,充分保护以及与之相关的财产估值等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三、破产法中的担保物权优先受偿问题
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与别除权理论相关。别除权(Exemption Right)是指债权人因其债权设有物权担保或享有法定特别优先权,而在破产程序中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从权利本源上讲,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创设,但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具有新的特点。别除权之名称,便是针对这一权利在破产程序中的特点而在破产法理论上命名的。参见王欣新:《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7(1)。别除权旨在保护担保物权,其主要体现在优先受偿权上,这种优先受偿权来自民法的规定。各国民法基本都承认,债务人特定财产上原已存在的担保物权或特别优先权具有优先受偿效力,约定担保物权是最为常见的情形。我国《物权法》第170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在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属性将面临来自劳动债权、税收债权等方面的挑战。
(一)担保物权与劳动债权的权衡
担保物权与劳动债权的冲突在企业破产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此,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债权只在无担保财产中具有优先受偿的第一顺位,而不应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劳动债权虽应优先保护,但是,将职工债权全部放在物权担保债权之前清偿则是不妥的,而仅靠采取这一种措施解决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债权问题更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29]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债权属于“法定优先权”,所以应将劳动债权置于担保物权之前,即赋予“超级优先的法律地位”,从而根本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劳动工资优先于抵押受偿的问题。[30]王利明教授曾指出,“所有的劳动债权都要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的观点旨在强化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应当通过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来解决,如果我们的破产法采用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符,而且也将会产生危害交易安全、破坏物权法原则、损害金融秩序等不良后果。[31]
面对上述争论,我国立法最终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案。《企业破产法》第132条做了折中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 易言之,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后所欠的劳动债权不能优先于担保物权。
笔者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带有人身依附性和情感纽带,所以在破产程序中赋予劳动债权第一顺位清偿权合乎情理,但当其与担保物权发生冲突时,由于担保物权所具有的公示公信力和对世权属性,一味地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牺牲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使有财产担保债权被隐形置换了受偿序位,显然有失偏颇。从德国、日本与韩国的立法实践可以看出,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通常会通过完善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等形式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不是采用赋予劳动债权“绝对优先权”的方式。[32]
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失业者”已经建构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弱化了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性。如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等国已经取消了工资优先受偿权,而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其清偿权益。[33](P135)可见,解决破产企业的劳动债权保障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赋予劳动债权以“超级优先权”,而是在于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工资保障基金。我国目前并未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债权保障基金,但已有地方试点探索经验。例如,深圳欠薪保障基金的实践经验,就是由政府主导设立劳动债权保障基金,企业一旦被宣告破产,立刻由劳动者劳动债权保障基金会作为代位权人参加清偿,劳动者不必等到企业财产变卖时才得到清偿,从而避免破产案件受理时间过长导致劳动债权迟迟难以受偿的问题。同时,应当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建立种类齐全、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的劳动债权保障保险制度,以使破产企业职工的劳动债权可以获得最终清偿,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诚信社会的建立。[34](P308)
(二)担保物权与税收债权的抉择
担保物权与税收债权的清偿顺序如何处理?在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债权优先受偿,因为税收债权属于公法之债,关系国家财政利益,理应优先于私法之债受偿;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物权优先受偿,因为担保物权具有对世性和绝对性,对维护交易安全与市场诚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两种观点各有其道理,关键看立法机关如何选择。
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税收优先权并非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学者所言:“由于税收的发生缺乏公示性和确定性,第三人无从知晓其存在及具体数额,税收优先权会对民事交易安全构成威胁,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理期待利益。另外,税收的公益性和风险性并不必然支持税收优先权。在世界范围内,税收优先权制度呈弱化趋势,有的国家甚至早已将其取消。”[35]实际上,澳大利亚早已废止了税收优先权规定,事实证明不仅没有给税收带来损害,反而促使征税机关积极运用税务保全、税收强制措施来保障税款及时征缴入库。不少国家和地区即便没有废止税收优先权,但在税收优先权的效力登记、适用范围、适用形式等方面也呈现弱化的趋势。[36]当然,立法论的分析只能供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参考,而现实问题的解决则必须依靠解释论。
从现行立法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与《企业破产法》第109条之间的冲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这是税收债权优先受偿(或曰税收优先权)的唯一的法律规定。《企业破产法》第109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09条和第113条的规定,破产程序中的债权清偿顺位应为:担保物权→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普通债权。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纳税人既欠缴税款同时又欠有其他债权人债务,没有能力同时清偿时,当其他债权属于担保债权时,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处于平等地位,按各自发生时间的先后决定执行的顺序,据此形成了完全违背《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债权清偿顺位:税收债权→担保债权→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普通债权。
从解释论分析,优先顺位被打乱并形成循环怪圈的法律事实已然发生,且两部法律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意欲解决这个困境,只有依据《立法法》关于同位阶法律冲突的处理原则来解决。对此,又存在三种解读的可能:第一,《企业破产法》的颁布时间晚于《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依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原则*《立法法》第92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优先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第二,《税收征收管理法》是面向纳税人正常状态进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所做的规定,属于“一般规定”;《企业破产法》是面向企业非正常状态(即陷入破产程序)所做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因此,应当依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立法法》第92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优先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第三,《企业破产法》是对全体债权进行公平清偿所做的规定,但其颁布时间在后,属于“新的一般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专门对税收债权优先顺位的规定,制定时间在前,属于“旧的特别规定”。根据《立法法》第94条的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对于上述三种解读如何取舍,取决于选择者对两部法律的特殊性的认识。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基本面向纳税人正常状态来拟定,很少考虑企业破产时的课税问题,而破产法是专为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设定的法律制度。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重在明确税收优先权,但实际上涉及税收优先权与担保物权、无担保债权、罚款等各类债权的处理,不能构成特殊规定;《企业破产法》则是制定在后的专门针对困境企业债权债务处理的特殊规定。税收优先权属于一般优先权,并非针对债务人特定财产设置的权利,不符合担保物权的一般特征,在破产程序中更不具有优先于担保物权的超级优先权。《企业破产法》规定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优先于别除权的超级优先债权,仅限于该法第132条规定的职工债权。加之,循目的论之解释方法,《企业破产法》未规定税收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是对其他立法上所设优先权的特殊调整措施,体现了对其他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考虑到在破产程序外,税收债权有强大的实现手段,而且已经有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受偿的权利,发生在物权担保设置前欠缴的税款甚至有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的权利,本可以优先实现,但其怠于行使其权利,实际上是消极地放弃权利,所以在破产程序中不应再给予其特殊保护。[37]基于此,笔者建议严格执行《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收债权清偿,《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依照时间先后处理的规定应仅限于非破产程序之中。征税机关意欲取得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优先于担保物权的效果,应当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采取纳税担保的方式并按担保权设定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实现,否则,纳税担保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即便是在诉讼、执行等非破产程序中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处理担保物权与税收债权清偿顺位问题,也需要完善以欠税公告为基础的税收优先权公示制度,将经过公示程序的税收债权赋予优先权,对未经公示的税收债权列为普通债权与其他无担保债权同序,以此平衡公私法益。
四、结论
破产法与担保法是互为影响的重要法律制度,破产法中的担保物权处理,重点在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根据破产法的特性,在债务人与债权人权益之间进行平衡,在担保物权人与普通债权人之间进行平衡。为了使破产程序有效进行,破产法中对担保物权做出必要的限制已成各国破产立法的普遍现象,但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限制应有所区别,而且限制应建立在保障(充分保护和救济措施)的基础之上。二是破产程序中的担保物权处理涉及物权与债权、普通债权与优先债权等多方关系,由于我国既有物权与债权严格区分的理论,又有法定一般优先权规则,导致传统民法制度中出现了物权有时候要让位于一般优先权的情形。我们应坚持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和严格遵循物权特定原则,坚守“物权优位于债权”的基本原理来处理担保物权与债权的关系;对于一般优先权的处理,则遵循优先权的法定原则且不得违背破产法确立的基本清偿顺位的规则,这既是对民商法原理的统一贯彻,也是对破产法清偿顺位规则的尊重。从立法论分析,“我国破产法对优先受偿的债权的列举也不是封闭的 ,更不是穷尽的, 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予以添加和调整……优先受偿的债权能否优先于有担保的债权的问题, 是一个立法考量的问题”[38]。
[1] 高圣平、张尧:《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非典型担保的命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
[2] 曹士兵:《对非典型担保的司法态度》,载《人民法院报》,2005-08-31(3)。
[3] 邸天利:《非典型担保共性解析》,载《政法论坛》,2011(1)。
[4][5][27] 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 王欣新:《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7] 王欣新、郑志斌主编:《破产法论坛》(第1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8] 徐阳光:《破产案件审判庭设置的正当性证成》,载《人民法院报》,2016-05-25(7)。
[9][11][14][23][25][26] UNCITRAL.LegislativeGuideonInsolvencyLaw.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05.
[10][12] 王欣新:《论重整中担保权的暂停行使》,载《人民法院报》,2015-07-01(7)。
[13] 王之洲:《论担保债权在重整程序中的保护与限制——兼与王欣新教授商榷》,载《人民法院报》,2015-09-30(7)。
[15] 11 U.S.C.§361(1)、(2)、(3).
[16] 761 F.2d 472(8thCir.1985).
[17] 美国破产法协会:《美国破产重整制度改革调研报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8] 赵雷主编:《新企业破产法讲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19] 蒋新华:《企业破产法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足与完善》,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2)。
[20][37] 王欣新:《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7(1)。
[21] 陈计男:《破产法论》(修订第三版),台北,三民书局,2015。
[2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
[24] 11 U.S.C.§362(k).
[28] 大卫·G·爱波斯坦等:《美国破产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9] 王欣新:《破产立法中永远的痛——谈债权人保护与对破产企业职工保护的关系》,载《证券时报》,2004-11-08。
[30] 申卫星:《论优先权同其他担保物权之区别与竞合》,载《法制和社会发展》,2001(3)。
[31] 王利明:《破产立法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载《法学》,2005(3)。
[32] 顾妍、钱菲:《劳动者权益保护在破产程序中的困局与应对》,载王欣新、郑志斌主编:《破产法论坛》(第10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33] 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4] 王欣新:《破产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5] 熊伟:《中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存废之辩》,载《法学评论》,2013(2)。
[36] 侯作前:《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前瞻》,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1)。
[38] 孙新强:《破除债权平等原则的两种立法例之辨析———兼论优先权的性质》,载《现代法学》,2009(6)。
(责任编辑 李 理)
A Study of Security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nkruptcy Law
XU Yang-guang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Whil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curity law and bankruptcy law in dealing with security interest in bankruptcy law, the key issue still lies in the restriction and protection of mortgages and pledges in the bankrupt proceedings.The restric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uspension of security rights during bankruptcy.The Chinese bankruptcy law borrowed suspension theory from abroad and it has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suspending security interest in restructuring.However, the law remains unclear in relation to bankrupt liquidation.Meanwhile, the issue of remedies of security interest holders becomes prominent.The protec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 is mainly resulted from its priority in repayment over other claims.The bankruptcy law therefore should reaffirm the priority of security interest in repayment, in particular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interest, employee claims and tax authority.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and creditor’s (contractual) rights shall be well preserved and the principle of numerous clause must be strictly complied with.As for the general prior rights, the relevant statutory ru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may not contravene the order of repayment established in the Bankruptcy law.
security interest; bankruptcy liquidation; reorganization; automatic stay; priority in repayment
司法部2015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破产重整制度研究”(15SFB2025)
徐阳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