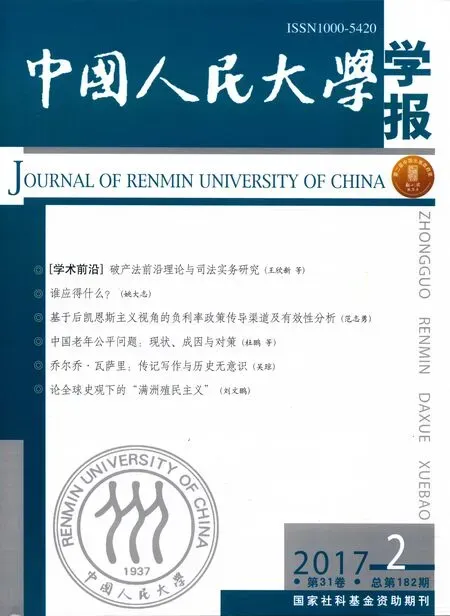女性主义对作者身份的建构
刁克利
女性主义对作者身份的建构
刁克利
女性主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发现和建构女性作者身份的历史。女性主义既可以看作是生理表征、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通过对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解读,可以发现女性主义与作者理论的密切联系。探讨作者身份对于女性的含义,借以阐明女性主义为建构作者身份而进行的抗争、局限和贡献。在文本中心和作者之死的理论潮流中,女性主义对作者身份的建构重申并凸显了作者的主体性和作者理论的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作者身份;性别研究;文学理论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和文化研究等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主潮。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被取代,作者的消解与死亡成为压倒性的理论观点。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著作,则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发现和建构女性作者身份的历史。早期的女性作者使用男性笔名代表了身份的藏匿和对男性作者权威的自然认同,雌雄同体的提出意在超越性别的羁绊,对“第二性”的揭示和对女性创造力的挖掘开启了对女性作者特质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则以揭示作品背后的女作者为目标,寻找发现和描写完整的女性作者。
因为要从强大的男性传统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女性主义为建构和确立作者身份而进行的论争就不仅涉及性别的意识形态、经典的界定和文学史的改写,而且也涉及人类对自身宽容意识的审视。在文本中心论和作者消亡的时代,女性主义重构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自身的特殊性重申并凸显了作者的主体性和作者构建对于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这既是对作者之死的有力反击,更是对作者的坚定辩护。女性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女性作者的困境,阐释和建构女性作者身份中所体现出来的性别之惑和性别之争,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学理论,乃至人类思想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启发。
一、自己的房间为什么重要
《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是女性主义的第一部重要文献。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强调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对于女性成为作家的必要性。物质条件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到,甚至认为物质条件是最不重要的。而这恰恰是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也是以往文学研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女性与小说创作为主题,开宗明义,直接点出女人写作与物质条件的关系。伍尔夫提出女人要写小说,必须有年入五百镑的收入,必须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然后她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以带听众漫步的方式,让大家随她体验女性的历史。
18世纪前女性默默无闻,女性作家不仅受男性的低看、社会舆论的影响,还难以避免受自己内心的禁锢。到了19世纪,人们仍不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艺术家的头脑必须是明净的,不能有窒碍,不能有未燃尽的杂质。”[1](P119)这样才能成就一流的、伟大的、像莎士比亚一样的艺术家,而女性很难达到这种精神状态。伍尔夫举出的几个例子:科勒·贝尔(Currer Bell)是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乔治·桑(George Sand)都曾用或用了男性笔名试图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结果却是徒劳。她们无一不是内心冲突的牺牲品。
19世纪几位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简·奥斯丁(Jane Austen)都没有子女,写的都是小说。原因可能是写小说“不需要格外聚精会神”,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书房,都是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写作,在操持家务的间隙写作。在这种写作环境中的女作家难免心怀激愤,心境难以达到明净的止境,即伟大的艺术创作的理想精神状态。伍尔夫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展开论述,道出了女性作者的写作由于积怨,总不能舒卷自如。女性写作之缺乏传统,则是根本的困难。“所谓困难,指的是她们身后缺乏一个传统,或者这个传统历时很短、又不完整,对她们帮助不大。因为我们作为女性,是通过母亲来回溯历史的。求助伟大的男性作家启示于事无补。”[2](P163)伍尔夫首次提出了关于女性文学的传统,这一点将得到后来女性主义者的积极响应。
伍尔夫在最后一章提出了雌雄同体的理念,这是伍尔夫留给女性主义的又一大精神遗产。
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中一起……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在此番交融完成后,头脑才能充分汲取营养,发挥它的所有功能。[3](P211)
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论及了女性写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后来女性主义关注的许多基本问题:女性写作的物质基础,独立意识,去掉自己心中的纠结和战胜父权社会从舆论和经济上的压迫,寻找自己的传统,坚持自己的特性,追求男性和女性意识的和谐相处,达到雌雄同体的理想等等。对于女性作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她寄希望于社会的改变和女性自身的改变,包括职业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对女性评价观念的更新等,时间为一百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够了,应该说伍尔夫梦想成真。这些问题很多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问题。对于探讨女性作家必须面对和克服的社会和舆论环境的感受,如何让女性达到自己理想的创作状态,成为更好的作家,甚至成为理想的作家,伍尔夫贡献良多。
二、第二性与创造力
较之于《一间自己的房间》作者的胸有块垒,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I,II)写得汪洋大气。较之于伍尔夫文笔的清澈流畅,波伏瓦写得厚实而嚣张。《第二性》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兼思想史、女性史、心理史和社会史于一体。
《第二性》分两部。第一部名为《事实与神话》。波伏瓦从生物学论据、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析女性的命运,提出为什么女人是他者?在历史的过程中,人类把女人变成了什么。她根据存在主义哲学,从人种志和人类史的证据追溯女人的历史,在对人类历史进行追溯的过程中,她提出:“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4](P87)。女人整体上处于附庸地位。她从人类发展史总结出了男人关于女人的神话。男人在她身上寻找整个自我,女人成为非本质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为了证实在普遍看法中存在的女性神话,她分析了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结论是:“每个作家在界定女人的时候,也界定了他的一般伦理观和他对自身的特殊看法:他往往也在她的身上记录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自恋的梦想之间存在的距离。”[5](P341-342)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神话是男性心理欲望的表征。有的作家鄙视女人,有的作家崇拜女人,比如劳伦斯就固守必须是男人引领女人。波伏瓦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评价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看出她们被扭曲被夸张被利用的形象,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重估文学史、重建女性传统、重新确立女性形象。
第二部为《实际体验》,讲述和分析女性的成长、处境、辩解和走向解放。波伏瓦在开篇即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6](P9)在最后一部分“走向解放”中,她重点讲述了独立的女人,提出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女性的具体自由。同时,她也说明,即使女人参加了工作,即使伍尔夫时代女性的大部分问题得以解决,她的独立仍然是在半路上。
《第二性》是从女人的整个处境研究女人。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卷尾,波伏瓦分别研究了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男性作家对女人的描写心理和实质)、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女演员和想成为作家的女人。像伍尔夫一样,波伏瓦同样看到了女性作家的局限,提出了理想的写作状态,指出了女性解放的途径和希冀。波伏瓦提出的创作的理想境界是:“艺术、文学、哲学是在人的自由,即创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尝试,首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一种自由,以便拥有这样的抱负。”[7](P575)对于女性作家,第一要务是生存,是存在。第二要务是自由,独立。第三才能谈得上创造,身心自由、完全放开自我的创造。这种无我之境的创造与伍尔夫所说的明净状态相类似。她的这种论述,不但对女性作家和创造性的劳动有启发,对于了解人类的存在状况和不同社会阶段的人的发展亦有启发。女人争取存在的斗争仍然艰巨。波伏瓦的希望是:
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问题、怀疑、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只要她仍然需要为成为人而斗争,她就不会成为一个创造者。[8](P578)
波伏瓦认为,女性之所以难以成为一流的作家,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而这自身的原因,究其根源,也来自人类文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长期以来对女性的定位,以及女性对这种定位的接受。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既是指她自身的发育生长,也说明这个社会舆论环境所助长和引导而刻意为之的结果。所以,一流作家的诞生是作家个人、社会环境、人类文明进程合力的结果,缺一不可。
波伏瓦在《女性与创造力》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女性与创造力的关系。这是她于1966年在日本的演讲,与《第二性》相隔近20年,基本观点不变。她首先强调了女性创造力受制于物质条件,如伍尔夫所强调的一间房子,物质条件与独立的空间、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等都会制约女性的创造力。其次是女性所获得的职业机会不均等。再次,艺术家的社会形象与传统的女性形象不符合,因而会给女性造成极大的心理和社会舆论压力。这种艺术家的形象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形成的。第四,传统女性形象的制约。第五,作家的品质和女性的经历局限。作家需要标新立异,需要自信和耐心。女作家缺乏这些,咎不在她,而是其经历所致。
除了剖析女性创造力受制的种种原因,波伏瓦还重点谈到了女性作家对世界的抗辩和责任意识不足。创作需要边缘处境与旁观角色,这是女性合适的。女性作家与社会同步,认同感高。另一方面这又成为她的局限,使其难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创作需要旁观和边缘,然而,更需要一种深切的责任,这是一种我是主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不会这么做的。她们会批评、驳斥某些细节,但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9](P156)
这和她在《第二性》中提到并强调的思想机会毫无二致。可以说,从《第二性》的发表到这次演讲的时间段内,波伏瓦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她没有看到女性作家有实质的改观。也可以说,20年间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在揭示女性写作的诸多困境的同时,女性主义论者总会提出自己对理想的文学与理想的作家的向往。伍尔夫和波伏瓦都探讨了理想的作家和理想的文学状态。伍尔夫的文学典范是莎士比亚,波伏瓦推崇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就所向往的理想的文学状态而言,对于伍尔夫,是消解了个体存在激愤和超越了个人恩怨的明净状态;对于波伏瓦,是超越性的自由和身为世界主人的解释世界、揭露世界、与世界抗辩的责任感。对于理想作家和理想文学的追求与定义,代表了女性作家的向往和自由写作的渴望,也是女性主义作者理论的重要特征。
每一代女性主义者都揭示了她们感到亲近的时代、阶层、种类的女性作家的困境,也都指出了努力和解放的新方向。她们对女性作家困境的揭示,对于理解作家状况和人类状况很有意义;她们对文学理想的设定和憧憬,对于理解作家大有启发。理解女作家,也是理解男作家;理解人类的另一半,理解同样处境的人类,理解人类性别意识形态的运行和作用机制,也是理解人自身、人的宽容和人的解放,以及人的前途是否可期,人的拯救是否有望。理解女性的文学理想,也是理解文学的特质,理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理解人类的智力和情感活动领域,理解文学的独特作用和魅力,理解人类智力和情感活动的边界和意义。
三、疯女人与性别之争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库巴(Sandra M.Gilbert & 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对19世纪重要女作家进行了视角独特的透彻研究。著作先检查了父权文化下作者的概念流变,提出了女性成为作者意味着什么,对女性创造力和男人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女性笔下女性形象的双面性。继而提出妇女作家的焦虑不是来自于文学传统的久远和文学前辈的压制,而是来自于对女性作者身份的焦虑。接着著作又以洞穴之喻为引子,寻找女性作者的完整性,“最后的这个寓言讲述的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10](P98)。著作理论构建与文学批评并进,她们以人物是作者的复本为核心观点和策略,以揭示作品背后的女作者为目标,建立女性主义创作理论。
这部著作对于作者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她们对作者观念的溯源大有裨益,其对女性作者身份焦虑的独特论断值得借鉴,有助于加深理解作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和文学创新。二是她们所分析的妇女作家多重面具的创作策略,及其所揭示的多重面具背后隐含的作者的愤怒和不平的实质,这有利于解释女作家的独特性和创作心理的复杂性。三是她们的女性主义诗学策略构建以所谓的男权文化下的作者为参照,在作者之死风行的年代,她们意图发现作品背后的作者,这是对作者中心论的认同、对作品是作者内心表现这一信念的坚守。
她们的著作以人物反映作者的观念,尤其疯女人为代表的人物作为作者的核心观点,坚持女性作家和她塑造的某类特殊女性形象的一致性。“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女作家才得以实现她自己那种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而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这位焦虑的作者才能为自己表达出以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怒火的毁灭,而那种怒火已郁积良久、再难遏制。”[11](P85)她们试图通过文本中的这种特殊的(发疯的)女性形象揭示藏匿在这形象背后的女作家的真实面目,描述女性写作的特色。在男性文化氛围中,女作家是性别的囚徒,亦必须是打破这囚笼的战士。
在她们对男权文化主导下的作者权威批判的前提下,最后恰恰是利用了作者权威界定建立自己的女性诗学。她们视作品中的某些特定的人物形象为作者的复本,甚至将作者等同于人物,乃至于把作者看作是文本唯一的意义源的观点,是传统作者中心论的再现。这和她们在著作开始宣称的作者是男性、上帝是男性的考据是一个循环。以此复兴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是否可行,值得商榷。这难道说明,女作家要回归男性传统,皈依男权文化吗?这无疑会给批评女性主义的批评家授之以柄,亦让后结构女性主义者难以认同。
后结构女性主义者认为,作者的概念本身就是男性的或父权的建构——作者的权威本身是父权制的固有方面。像她们俩这样的批评家面对的危险是在描写一个女性作者传统时,她们简单地重复和加强了父权方式,加强了坚持“把文学看作个人经验的简单、直接的表现,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把作者当作父权思维的一部分”[12](P286)。在《性别/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Politics)中,托丽尔·莫伊(Toril Moi)指出,把作者当作文本的来源、起源和意义,就是把父权制和作者身份联系在一起。“要解除这一权威的父权实践”,女性主义批评家需要“和罗兰·巴尔特一起宣告作者之死”[13](P62-63)。
的确,在作者之死的年代,她们对作者中心论的坚持虽然可贵,但亦饱受质疑。那么,如果换一种思路,这或许说明:作者是文本的创造者,是意义的权威的命题本身就是真理?如果相信后者,则一切矛盾都可化解,并不会引发性别的战争。作者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无论其是何种性别,但他/她一定是作为创造者现身的。
另一个启示:她们研究的是女性主义诗学,诚如她们自己所言。更确切地说,她们的研究是女作家创作理论。女作家的创造动力、作家身份、创作资源、创作特点,作家自我与人物形象之间的显性与隐性关系,作家创作动因与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的策略等。这一切的背后是假定在男权文化中,女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压抑性、边缘化,以及女作家对此的抗争的意图与应对的策略。这为作者理论和作家创作研究进行了理论探索,提供了例证。核心启示是:女性作者理论必以作者中心论为基础,创作理论必须是以作者中心论为依据。舍此,女性作者理论谁与归,创作理论何去何从,则都会成为疑问。
那么,假如把她们的研究称之为女作家创作理论研究,则这种研究对于所有的作家,不论男女,皆有益处。如果不把它局限于理论的建构,就不会引起那么激烈的批评。它研究的是创作理论,对于作者如何选择、利用、构建自己的素材、主题和情节,如何描写自己的核心意象和人物形象,都有启发。
女性像男人一样写作,还是以女人的身份写作?这是一个问题。女性批评家一方面拒斥女性身份或女性作者身份,同时却试图以之为特色,以一定模式的写作来表明它。虽然女性主义批评远不止被局限为以上简述的两端,从早期的“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70年代中期开始的“女性作家批评”(gynocritics)以及80年代末期兴起的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作者性别和作者身份始终是这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即使如西苏强调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进行女性写作,以性别界定文本特征也是因循了男性与女性之别的思路,更勿论作者性别这一不可更变的明显事实而必然与作者身份问题密不可分。
女性主义对性别之争似乎无以逃遁。女性写作对于身体的束缚难以摆脱。女性作家是以自己独特的生理经验、身体体验为素材为骄傲,还是以之为耻,掩饰逃避,这是伍尔夫意识到的问题,她从中看到了自身的或者说她所处时代的局限。这是以后的女性作家也必须要面对的。女性主义的写作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性别,还是为了超越性别?有没有一种可以强调性别又超越性别的方法准则?女性主义的性别之惑像极了民族的和世界的关系之争。如果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么,能说越是女性的就越是文学所需要的吗?如何成就女性,如何表达女性?这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问题。
四、反击与启示
作者问题是女性文学批评观念的中心。“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主义的斗争基本上就是为作者身份而进行的斗争。”[14](P145)与作者之死针锋相对,女性主义着力发掘女性文学传统,揭示女性作者的身份特征和身份焦虑。她们从整理女性文学传统出发,构建女性作者身份,既有自身的需要,说明了作者理论的生命力,又是对作者之死的有力反击。
女性主义反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揭示了作者之死的男性文化背景和历史特征。南希·米勒(Nancy K.Miller)认为,消除作者可以被看作是对女性主义话语基础和身份政治的攻击。作者之死的理论远不是导致关于作者的新思考,而是对任何写作身份的压抑和禁止,因此也是对女性作者的身份、身份认同、压抑和禁止抑制。因为妇女从来没有被认为拥有男性作家声称的那种作者地位,因而,作者之死并不适合她们。“作者的移除并没有为修正作者观念腾出多大空间。”[15](P104)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作者之死是传统的男性作者权威之死,对作者的解构可以被看作是男性作者的解构,对一定男性思维的解构和父权本身的解构。如果作者之死中的作者是男性,那么,作者之死与女性无关,女性作者需要的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和重生。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作者之死的理论,而是一个新的作者观念,这种新的作者观念不是天真地强调作家是原创性的天才,创造了历史之外的美学作品,而是在谈到妇女作家对历史构成的反应时不会抹杀其不同和重要性。[16](P148)
因此,女性主义之作者重建不是在需要解构时建构一个压抑性的权威,而是要被发现、被肯定,给予女性作者以身份认同。可以说,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之死不但对女性主义对作者理论不起作用,反而激发其走向相反的方向,即作者建构的方向,义无反顾地挺进。
女性主义对作者之死的反击沿用了传统作家研究的方法,继承并坚守了作者中心论。女性主义作者理论阐述了女性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或者妨碍其不能成为作家的各方面因素。这些方面恰恰都是作家中心论的要素。女性主义以为自己争取权利、表明自己的方式复兴了作者中心,复兴了作者与作品的密切联系。文本是有性别的,性别属于作者。相对于自古希腊文学以来漫长的西方文学史,女作家的历史的确不长。女性主义批评家重估文学传统,重新定义文学批评。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女性主义对作者重建具有异乎寻常的特殊意义。
女性主义是一场绵延不断的运动、行动、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批评视角和思维方法。女性主义发展先后受到了许多批评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者善于将新的理论运用于理论构建,广泛吸纳,产生了各种女性主义分支,论及亦惠及各种女性阶层。其多方面思考女性问题,讨论视角不断累加,从一种女性主义到另一种,从一个阶段的女性主义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增添新的概念。女性主义探讨过的问题有:对生育的态度,家庭和妇女角色,社会主体生产,种族和男性,女性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法律权利,教育机会,身体构成,心理构成,性别歧视,文化建构,压迫与压抑,帝国主义统治,帝国主义的文化身份,帝国主义的话语场,等等。女性主义始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扩展为对男女地位不均衡的原因探讨和背景揭示。女性主义不断调整批评的矛头,扩大批评的对象和范围,使得一切造成种种不平等或不均衡的原因和背景成为批评的对象和开火的靶子,直陈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潜流和表象下的真实和本质。女性主义几乎检查了一切批评理论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新的理论对女性主义都有启发,都能为之所用。女性主义的力量也在于此。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女性主义的性别之争和性别之惑,亦可以对女性主义做如下理解:女性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通过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作者希望达到的目的决不仅仅是性别的。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ok)所说:“我期望对帝国主义的深刻批判会引起第一世界读者的注意,这至少可以扩大阅读的政治疆界。”[17](P621)同理,女性主义的作者身份的建构也决不仅仅是对女性作者的思考,而是对文学理论,或者是对于世界的思考。因此,在思想层面上,女性主义对作者身份建构带给我们的更大启发是:每个作者都是女性。这样说的意思是,每一个作者都会经历和女性作者相似的历程:寻找传统,发现自己,拓展更新,融入并成为传统。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可能是女人。其意思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女性所经历过的各种情景和心路历程:被拒斥、被边缘化、抗拒力争、进入主流。这是女性主义作者建构对于文学理论的贡献,也是女性主义思维方式对于人类的贡献。
[1][2][3]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5]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I),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6][7][8]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II),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9] 西蒙娜·波伏瓦:《女性与创造力》,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0][11] Sandra M.Gilbert & Susan Gubar.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 Peggy Kamuf.“Writing Like a Woman”. In Sally Mc 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an(eds.).WomenandLanguageinLiteratureandSociety.New York: Praeger, 1980.
[13] Toril Moi.Sexual/TextualPolitics:FeministLiteraryTheory.London: Methuen, 1985.
[14] Seán Burke( 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Nancy K.Miller.“Changing the Subject: Authorship, Writing, and the Reader”. In Seán Burke (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Cheryl Walker.“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uthor”. In Seán Burke(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载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hor Identity of Feminism
DIAO Ke-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o a great extent, is a history of rediscove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author identity.The read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oretical classics of Feminism helps to interpret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being a female author, and shed light on the struggles, limits and contributions in forming and constructing female author identity.Against the trend of the text center 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Feminis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defines and highlights the author subjectiv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uthor theory.
Feminism; author identity; gender study; critical theory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作家理论与作家生态研究”(10XNJ026)
刁克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