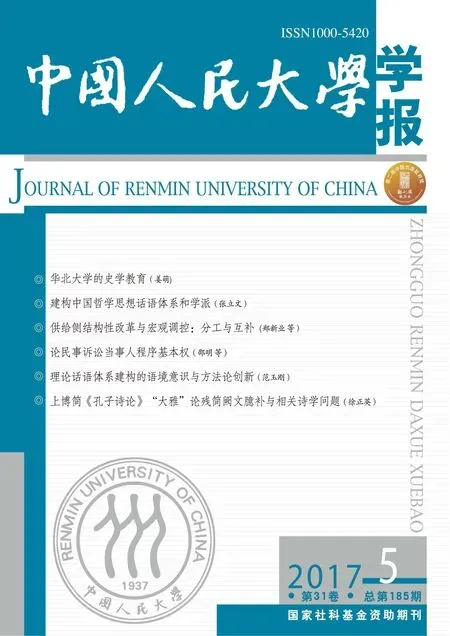物的凝视
——论审美静观的宗教性起源
高 薪
物的凝视
——论审美静观的宗教性起源
高 薪
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曾就艺术品的观看提出过一个令人难解的条件:距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使我们走向本雅明的“光晕”概念以及李格尔的“心境”概念。在这一问题谱系中,距离乃是开启审美静观的条件,这种审美静观包含了不同于一般观看的许多特质,它具有使物回看观者的能力、无功利性,以及观看的永不知足性等等。而且,静观是使艺术品产生效能的根本原则。本雅明和李格尔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特殊观看的培植追溯到其宗教性的起源,借助阿甘本有关宗教的论述,以及宗教与仪式的“隔离”和“禁忌”操作分析,来揭开审美静观的诸种谜题,并理解其在现代社会所遭受的种种批判;与此同时,这一揭示也预示了审美静观在新的个体伦理学视角下所孕育的解放性功能。
距离;光晕;心境;面纱;凝视
一、问题的提出:距离
1639年,画家尼古拉·普桑在给其赞助人保罗·福莱尔·德·向特罗的信中,曾提出一个怪异要求:“一旦你收到画作,若你喜欢这个主意,我希望你用画框装饰它。因为画框可让你从不同角度看画时做到目光专注,从而不致被其他相邻事物的印象分散注意力”[1](P146)。画家提出的要求使我们意识到,看一幅画,不同于单纯地感知一物,它不仅仅是看见。三年之后,普桑在另一封信中区分了两种观看方式:“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仅仅看到物,另一种是聚精会神地思量一物。”[2](P62-63)普桑将前一种称为“外观”,将后一种称为“内视”。外观意味着单纯去看,眼中自然地接收所见之物的形式与相似性;内视意味着在看的同时,还要仔细思量它,在对形式简单、自然地接收之外,还需煞费苦心地寻找一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对象的方式。路易·马兰敏锐地注意到,普桑对配框的要求所提出的正是从外观到内视,从一般观看到审美静观的可能性条件。[3](P324)
普桑进一步指出,审美静观的“内视”有三个条件:眼睛、视觉光线,以及眼睛与对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前两者是与一般观看共享的基本条件,那么决定性的就是这多少显得神秘而难解的第三个条件:距离。距离作为关键性因素,揭示了审美静观作为一种特殊观看的何种性质呢?
普桑留下的疑问将线索指向把本真艺术品的独特价值描述为“灵晕(aura)”的本雅明,因为在本雅明那里,“灵晕”不是别的,就是“一种距离的独特显现,不管这距离有多近”①本雅明对“灵晕”的定义出现在多处,最常见的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摄影小史》《拱廊街计划》以及更早期的大麻麻醉剂实验。参见Miriam Bratu Hansen.“Benjamin’s Aura”.Critical Inquiry, 2008, 34(2):336-375.。如果“灵晕”是本真艺术品的规定性特质,而距离又是使灵晕出现的条件,这就使普桑提出的有关距离的要求显得必要。本雅明又说,将灵晕的概念定义为“距离的独特显现”,是要阐明这一现象的仪式性特征,“距离的本质是不可接近性,而不可接近性事实上是仪式性图像的根本品质”[4](P207、239)。这一补充说明似乎指出了以距离为条件的观看在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性观看,或者说有关观看之距离的原则最初是在仪式中确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普桑对观看提出的更具体的要求:要为其装框,并挂在比视线稍高的位置。[5](P146)其中,画框所起的作用就是“距离”的作用——隔开观者与绘画;挂在稍高的位置则要求观者要向上仰望,这极度暗合了本雅明对仪式性观像的描述。普桑的作品已经完成,即将被送到观者手中,画家的眼睛即将被观者的凝视所取代,普桑在这里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即将处于展陈状态的艺术品如何才能最好地发挥其效能所做的考量。结合本雅明的论述,这似乎暗示了,作为本真艺术品之根本规定的“灵晕”乃是对处于被观看状态的艺术品所产生的效果的描述,而且,这种效果并非内在于“物”本身,而在于一种对物所持的特殊感知模式中。这种特殊的感知模式将由距离开启,并且最初是在一种仪式情境中培植起来的。
二、静观:物的回视
对这种特殊感知模式的强调不止为作为艺术家的普桑和作为批评家的本雅明所独有,也越来越得到艺术史研究的支持,尤其是当艺术与图像研究开始逐渐远离现代形式与风格分析的范式,转而探讨图像效能施展的时候。*艺术史研究的图像转向出现于1989—1990年左右,由汉斯·贝尔廷,大卫·弗里德伯格、路易·马兰、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胡伯特·达米施以及大卫·摩根等艺术史家所引导,尤其是贝尔廷出版于1990年的著作Bild und Kult: eine Geschichte des Bildes vor dem Zeitalter der kunst,以及弗里德伯格出版于1989年的著作The Power of Images,对后来艺术史注重图像及其效能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转向使艺术史研究离开由瓦萨里-潘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具有确定知识形态的艺术史,借助于人类学、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的帮助,进入人类更广阔的图像实践,充分挖掘图像及其效能的施展。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Confronting Images.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迪迪-于贝尔曼曾抱怨,“我们保留了几幅古画,但是我们已经不再知道那曾使其栩栩如生的目光”[6](P50),他所指向的就是对某种感知模式的遗忘。汉斯·贝尔廷在研究被归为新的“艺术”范畴之前的图像经验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如果图像在成为纯艺术之前曾具有强大的力量,人们面对图像祈祷,为之焚香点蜡,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图像能够与凡常世界区分开来,变得像完全超自然的符号或拯救的中介那样神圣?贝尔廷的答案几乎是对本雅明给出的“仪式”回答的现代改写:图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某种使“物”神圣化的机制,即依赖于一切神秘性的仪式操作。出于对这种机制的强调,贝尔廷甚至说,在图像的神圣性方面,神父不仅比画家更重要,而且是图像之神圣的真正作者。这里,贝尔廷用“神父”所指的就是培植这种感受力的仪式机制。
本雅明很早就注意到,在宗教仪式中培植起来的特殊注意力与其他形式的专注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1920年,在《论恐怖》一文中,本雅明将这种特殊注意力称为宗教式静观(Aufmerksamkeit)*本雅明对这种特殊注意力的描述,不只使用“Versunkenheit”或“Aufmerksamkeit”一词,而是常常从具有相近语义的领域中选取其他词汇,比如“Kontemplation”,“ Konzentration”, 以及“Geistesgegenwart”,参见Carolin Duttlinger.“Between Contemplation and Distraction: Configurations of Attention in Walter Benjamin”.German Studies Review, 2007, 30(1):33-54.,以对立于冥想、音乐以及睡眠中的专注:“在静观的状态中,人不是心不在焉的,而是有深沉冷静的心灵反应,唯一的、持续且无法被破坏的深沉冷静,是祈祷者神圣的静观”[7](P75),而后一类型的专注则有不断滑向其对立面的风险,神志不清以及不完满地沉浸于其中。在祈祷或其他类型的宗教静观中,意识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主体自身,因此,这种宗教式静观并不会模糊人与上帝之间的界限,而是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意识形式的基础,以保证心灵的在场,使主体抵御令人分心的干扰。在祈祷中,个体对神的静观并不会妨碍他对自我以及整个世界的意识,而不完满的沉浸状态则具有削弱心灵在场的威胁,并最终导致心不在焉。在这里,本雅明用“心不在焉”来描述失去自我意识的沉浸状态,宗教式的静观却将内向反思与持续的对外在的机敏结合起来。
这种在宗教仪式中培植起来的静观模式并不会随宗教的衰落而销声匿迹,而是仍然保存在人与艺术品的关系中,成为召唤艺术品之灵晕的必要条件。所以本雅明说“绘画呼唤观者的凝神静观”,“面对画面的个人欣赏,其专注与强烈程度堪与在密室中凝视神像的古代教士相比”。[8](P258-259)为了强调这种在宗教和艺术中特有的观审性质,本雅明提出一种颇具神秘色彩的描述:在静观中,“物具有回报以凝视”的能力,我们正在看的某人,或感到被人看着的某人,会同样地看向我们。静观我们所看的对象意味着赋予它回过来看我们的能力。[9](P188)本雅明进而强调,这种赋予“物以回视”的能力是一切艺术的源泉,这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静观这种感知模式在艺术发生机制上的重要性。
但本雅明的描述看起来仍旧神秘难解,使物呈现出灵晕的静观何以能够赋予物以回视的能力?事实上,将静观定义为“使物回看”观者的能力并非本雅明首创。16—17世纪,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在荷兰艺术的研究中发现,荷兰艺术具有某种不同的风格品质,他将其解释为一种人对物以及一般世界所保持的特殊关系,即静观,并以一种观看关系对其加以规定。根据李格尔,静观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总是蕴含着使对象回看的能力。在论及17世纪荷兰风景画家雅各布·范勒伊丝达尔的作品《林谷村》时,李格尔说,虽然画中的垂钓者没有看向观者,但是村庄的房屋,几乎毫无例外地朝向观者,“它们那带着窗户的山形墙,似乎静静地注视着观者”[10](P141);在另一幅画中,城市中的街道,而非街道上的行人,“凝视着观者……那房屋山形的立面聚精会神地整齐排列在后面”[11](P143)。似乎画中并非森林中休息或闲逛的人物,而是风景自身构成了一组群画像,在那里,人们目所及处,只剩下树,但是“每一棵树都涌现为一个个体,它们使人们无法抗拒地沉入到其阴影中”*“Wie soll ein Baum uns gleichfalls als ein beseeltes Individuum erscheinen ween wir davon nur die unregelmässigen Umrisse eines Farbenfleckens Wahrnehmen? ”,参见Margaret Olin.“Forms of Respect: Alois Riegl’s Concept of Attentiveness”.The Art Bulletin.1989,71(2):289.。换言之,静观使每一片风景或每一棵树都像一个灌注了生命的个体。观者在凝视的同时,也被其所凝视。
对李格尔静观理论的回溯使我们得以理解本雅明为何将静观中艺术品带有灵晕的存在规定为“物回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种回视的能力,不仅来自一般被认为具有主动观看能力的人——无论是人还是人像——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物。本雅明曾以夏日午后的远山及在观者身上投下阴影的树枝作为范例来描述灵晕之经验。*本雅明对灵晕的这一描述出现在多处,最著名的一处出现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参见Water Benjamin.Illumination: Essays and Reflections.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p.222-223.中文版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2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可见,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物”本身是否具有投来凝视的能力,而在于观者的静观,这与李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在论及作为现代艺术之内容的心境(Stimmung)时,李格尔指出,在这里构成心境之元素的不是母题(das Motiv)的问题,而是以距离为条件的“远观”以及由远观带来的宁静。*参见Alois Riegl.Die Stimmung als Inhalt der modernen Kunst.aus: Graphische Künste XXII, 1899, S.47 ff.[Gesammelte Aufsätze.Hrsg.Karl M.Swoboda.Wien 1928, S.28-39.-Gesammelte Aufsätze.Hrsg.Artur Rosenauer.Wien 1996, S.27-37]。其中,李格尔对“心境”之内容的阐释也是以对阿尔卑斯山山顶的风景描述开始的,这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灵晕”的描述如出一辙。在李格尔的谱系中,“距离”为李格尔勾勒不同知觉模式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其区分出近距离的“触觉”和远距离的“视觉”以构成一对描述风格运动的反题。这说明对李格尔而言,以距离为条件的“静观”会对观者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最关键的是,它能形塑一种对“物”的特殊心理倾向和态度,即无功利。李格尔将艺术中呈现出的人与对象以及世界之间的态度和倾向归纳为三种模式:静观、意志与情感。其中,静观是无功利的,而后两者都暗示了一种将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关系:意志寻求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克服,而情感要么在臣服于外部世界时感到愉快,要么就在与其抗争中感受到悲情。[12](P75)静观是积极的,但却允许外在客体对其产生影响,而不寻求对其征服。在主体对世界的心理模式中,意志和欲望着的自我想要改变世界或消费它,而静观的倾向则是无功利的。
李格尔将这种人对物所保持的特殊态度追溯到人类最初的拜物倾向中,“最初人类创造了一种肉眼可见的、敌对力量的载体,即拜物,并致以尊敬”,他同时指出,“拜物也意味着宗教和所有更高级艺术的开端”[13](P30-31)。在李格尔对荷兰绘画的研究中,他所用的“Aufmerksamkeit/attention”一词就是向对象致以尊敬的意思,但是这种致以尊敬并不会使主体自身的尊严降低,“他们清醒地接受世界所是的样子,对之致以尊敬并向其要求同样的尊敬作为回报”[14](P105)。值得指出的是,“尊敬”(respect)来源于拉丁语中“respicere”的过去分词,而“respicere”的意思正是“回头去看”[15](P94-95)。这解释了静观中的某物为何会变得似乎“具有生命”,并对观者投来凝视。基于荷兰艺术中存在的这种人与物以及世界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倾向,李格尔将其根源追溯到宗教绘画:在尼德兰艺术中,中世纪时期的态度存活下来,肖像人物被直接展现为承载着某种精神功能……其中,尽管没有奉献的对象,但是人物处于一种中世纪祈祷者的心态中,如同在一个崇高的祭坛前。我们因此可以自信地得出,这一群画像,即使我们认为它起源于更早的宗教改革之前的阶段,但其根源在于宗教绘画。*Alois Rigel.The Group Portraiture of Holland. Getty Research Instirute, 1999, p.67.对李格尔“静观”概念的宗教与伦理性诉求的研究,参见Margaret Olin.“Forms of Respect: Alois Riegl’s Concept of Attentiveness”.The Art Bulletin, 1989, 71(2):285-299.
三、物之处于面纱中的存在
通过李格尔和本雅明的论述,在由距离开启的静观中,“物”具有回报以注视的能力,而这构成了艺术品带有灵晕的存在。可见,美的艺术品起作用的根本原则与其说源于对象本身,不如说源于与对象保持的某种特殊关系,而两者又都将这种关系归于某种人类最初的拜物倾向或宗教性起源,这使我们得以追问,宗教母体何以能够培植出这种特殊的倾向?
根据阿甘本的词源学考证,Religio(宗教)这一术语,并非源自“联结”(religare,联结并统一属于人之物与属神之物的东西),相反,这个词源于“relegere”,它指的是在与众神的关系中必须采取的小心翼翼、殷勤专注的姿态,以及在为尊重神圣与神圣之外的分隔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前不安的踌躇。[16](P74-75)可见“宗教”一词最初所描述的不是某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是处于这种活动中的人对物保持的倾向和态度,而这种态度的生成则源于一种“隔离”操作。根据阿甘本所述,人类的一切宗教和神圣化操作,都以一种“隔离”或“区分”为前提,也就是将某物移出人的自由使用和商业的范畴:它们既不可被出售也不可被留置,既不能用来换取使用权,也不能承载劳役。任何侵犯或违反这种特别的不可使用性的行为,都将成为冒渎的。而实现这一分隔的正是仪式,通过一丝不苟的仪式,物从人的共同使用中移除,被转移到一个单独分隔出来的领域。“分隔”意味着彻底的不可接触性,以及由违反禁令所带来的恐惧*有关宗教与禁忌,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也就是由分隔操作的机制带来的在被分隔之物面前所必须保持的“小心翼翼与殷勤专注”的姿态。
物的绝对隔离意味着彻底的不可触及性,由不可接触的禁忌之法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即距离,也就是李格尔和本雅明所谓“远观”之要义。所以本雅明强调灵晕的出现以距离为条件,“无论这距离有多近”,因为这不仅是种空间距离,还是一种心理和精神距离,由在宗教仪式中被隔离之物的绝对不可触及性所产生。隔离也决定了被分隔出的物之绝对不可使用性,这生产出一种纯粹的无功利性,而这正是康德定义审美静观的主要特征[17](P106),也是李格尔将“Aufmerksamkeit”区别于意志与情感的主要原则。由仪式所确定的不可触性和不可使用性则确定了禁忌之法,培植出人对隔离之物“小心翼翼、殷勤专注”的倾向。在李格尔的语境里,“Aufmerksamkeit”一词实际上也是一个奇异地拥有双重语义的术语,它一方面意味着警醒的、警觉的或敏锐的;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谦恭或善意这一层面的含义。*相关论述参见Margaret Iversen.Alois Riegl: Art History and The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96;Margaret Olin.“Forms of Respect: Alois Riegl’s Concept of Attentiveness”.The Art Bulletin, 1989, 71(2):291.这种对物致以尊敬的态度,在李格尔那里不仅是对拜物的描述,而且是对一种客观性美学的描述,其中,物完全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因此能够作为客体与我们相遇,与观者相遇。这种相遇并不是传统所谓的移情,移情意味着使观者以自身体验去阅读作品,而不是与其面对面交流。李格尔所谓的客观性美学所要求的,是观者通过凝视与图像交流,而图像则回报以凝视,就像它是一个人,“它们是客观性的个体,其物理和心理状态是完全独立于观者的主观性感知的”[18]。
如果在起源于宗教仪式的静观倾向中,物已被升华为一个具有生命的个体。那么,其秘密就隐藏在仪式中。仪式具有一整套严密的操作系统,它的对象不仅包括即将被“隔离/神圣化”的“物”,还包括一整套配件。其中被分隔进神圣或禁忌领域的“物”,总是被放置到特殊的建筑结构或其他摆设中——包括庙宇、神龛、祭坛等一切服务于神圣化运作的装置——以确定其移出的边界。除此之外,人们面对“物”的心态、动作和实践也将被严格规定:人们将其置于光亮之中,为其覆盖织物,人们凝视、祈祷、舞蹈或下跪。也就是说,宗教生产出一套极其精确的机制,它规定着被观看之物的本质及地位,确立对图像的正确运用与控制模式,并决定着我们从中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中,“物”通过一种奇观化*在居伊·徳波对“景观”或“奇观”(spectacle)的讨论中,“隔离”(separation)起着关键作用,“景观”以一种隔离性为前提,从而与真实生活拉开距离,并成为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置疑和不可接近之物”,所以徳波才说,景观正是宗教迷雾对人类尘世生活的侵蚀,借助于现代技术装置的景观使人类的分离达到了顶点。参见居伊·徳波:《景观社会》,1-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的运作悬置了其原有的功能与意义,被分隔为绝对不可使用之物。这种“悬置”和“分隔”使物被转移到一个语义场域,成为空的能指,随时等待一个时代、阶层或主体的编码,为之赋予可欲之物,随时准备接受欲望的投射。换言之,仪式乃是封装意义的操作。从古至今,各个地区与时代的人们为被隔离出来的“物”封装进魔力、神圣、希望、爱、美、幸福、友谊,凡常生活之泥淖的避难所,以及已经失落的过去和一个更好的未来。在仪式中,所有这些可欲而又不可见之物通过可见的形式或形象得以在场,可见物与不可见之物合而为一,成为开启凝视的真正对象。为了描述这种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二而一的关系,拉康将恋物或拜物中充当恋物对象的“物”形容为一种面纱(veil)的功能,“面纱从那不在场但被投射和想象于其上的东西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存在和自身的连贯性”。*拉康有关“面纱”功能的讨论出现在其第四期研讨班,发表于1957年1月30日,此处转引自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3)。
根据弗洛伊德对人类早期图腾与禁忌仪式的研究,被隔离之物同时也总是被强烈欲望之物。“一件被强烈禁止的事情,必然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因为对一件没有任何人企图要做的事情加上禁忌是多余的”[19](P74),任何禁忌之下,一定隐藏着某些欲望。因此,在仪式中起作用的已然不是可见的“物”本身,而是由仪式封装于其中的、作为欲望之真正对象的不可见之物,是主体的视觉驱力在物之上的蔓延和物本身意义的放大与升华。*在人类学和宗教领域,这就是拜物的根源,参见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3)。真正引起欲望的乃是背后的不可见者,它因可见者的在场而触发欲望,但又总是根据一种欲望与视觉的辩证法而隐退[20](P273),这导致了观看永恒的不满足性*有关基督教圣像化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参见让-吕克·马里翁:《可见者的交错》,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这种观看之不满足性,既是宗教观像也是图像或物被归为“艺术”之名后的审美静观的根本特征。
在宗教观像领域,但丁曾把远道而来参拜圣物的朝圣者,比作某位虽然站在上帝真实的面容前却永远也不知足的人*《神曲·天堂篇》“第三十一歌”,参见但丁:《神曲》,4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马里翁将这种“不知足性”解释为神圣(不可见者)与其面容(可见者)之间绝对不可取消的距离所带来的分隔,分隔将二者联合起来,而又保持其各自的不可还原性,这最终构成了圣像的秘密与基础。*一旦取消了“距离”,圣像就沦落为“偶像”,后者与主体是“亲近的”,因为只有在这些属性是“我”与神圣共有的时候,才将这些属性赋予自身,“偶像”因此也沦为虚妄的。有关距离、偶像与圣像之间的关系,参见Jean-Luc Marion. The Idol and Distance: Five Studies.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8.因此,不可见者成为滋养视觉驱力的欲望之物,这导致了目光在可见物之上逗留、徘徊却总也不满足的特性。在艺术领域,保罗·瓦雷里将这种“不满足性”定义为我们识别一件艺术品的标准,“我们的感觉被其唤起,没有任何回忆、任何思想、任何行为模式能够抹除它的效果或将我们从它的掌握中解脱出来”。*相关论述参见保罗·瓦雷里:《当代社会的文学艺术》,一,巴黎,1935, 16.04-16.06以下,载《法兰西百科全书》,第16卷,转引自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2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本雅明根据瓦莱里的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何我们注视的一幅画反射回我们眼睛的东西永远不会是充分的,“它所包含的对一个原始欲望的满足正是不断滋养着这个欲望的东西”[21](P206),这便是视觉与欲望的辩证法,一种出现与隐退,现实与潜能的交织。欲望在此升腾,但却永远抵达不了其目标,这是一种抑制了目标的驱力的运动。本雅明曾以一种必要的遮盖状态来表述美的本质,美既不是遮盖物也不是被遮盖物,而是处于遮盖之中的物*本雅明对美的这一“物处于遮盖状态”下的定义,出现在多处,最典型地出现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与《评歌德的〈亲和力〉》,参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1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本雅明:《经验与贫乏》,225-22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而使艺术品处于遮盖状态的,就是起源于宗教时代的审美静观,“纪念碑和绘画只从敬仰的薄纱之下展现出自己,而这层薄纱是由那些仰慕者们几个世纪的热爱与敬仰为它们织成的”[22](P208)。本雅明将其称为古老的直观,只有在审美直观中,事物才在遮盖状态下保持“自身同一”,也就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统一;一旦面纱被揭开,本质美就已逃遁。这解释了审美静观中永恒的不满足性,以及世世代代的美的观者在物象面前的逗留与徘徊。
考虑到宗教仪式与审美静观中这种经验的相似性,本雅明强调,艺术品之带有灵晕的存在永远也无法与其仪式功能区分开。换言之,从充满力量的图像到艺术品,从崇拜、祈祷的态度到非功利的审美态度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的断裂[23](P1029-1056),如汉斯·贝尔廷所言,审美领域提供了一种和解,在我们已经失落的图像经验与保留的那一部分之间取得了一种和谐[24](P458)。
四、观看之欲的生产
审美静观中对象之永远处于遮盖中的存在使我们意识到,其中重要的是欲望或驱力,而非其对象。*弗洛伊德曾说,古代人赞美“驱力”本身,在驱力的作用下他们可以尊敬最次等的对象;而我们却贬低驱力本身的运动,并且只是因为对象的缘故才为其找到借口。Sigmund Freud:“Drei Abhandlungen”.In Gesammelte Werke Chronologish Geordnet, Vol.5, London: Imago Press, 1940—1952, p.46.如福柯所言,欲望的实质之所以会表现为隐晦难测的火,原因在于那些拒绝了它并一刻不停地试图扑灭它的东西。[25](P31-32)而那些试图扑灭它的东西,在人类文明中最早地呈现为仪式中的禁忌,后来,它在弗洛伊德那里表现为社会与文明所必然要求的压抑与禁忌,在拉康那里是象征之法对主体的删除与切割,在福柯那里则是现代性进程中必然的规训与惩罚,欲望的产生就在于法之禁忌生效的那一刻。它在主体身上留下一个永久的裂隙,由此,意识与无意识,可被经验之物与不可被经验之物分道扬镳。欲望并不会因压抑而熄灭,它只能被调节、被延宕,并且进入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或本雅明的“非意愿记忆”*本雅明有关“非意愿记忆”的描述与灵晕息息相关,参见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172-174页、204-2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中,并在主体的精神中留下一个永久的匮乏。这种意义的匮乏与不在场将使欲望的驱力更为固执,“当遗留的某桩小事永远也进入不了意识时,记忆的碎片通常是最有力、最持久的”[26](P173),它们会通过症状的方式屡次返回,因为它是尚未被清晰地经验过的东西,因此不能被定义为过去,而是以某种方式保持为当下。[27](P127)
如果驱力是禁忌与法的必然结果,而驱力寻求的是满足,那么,对象在驱力的循环中所处的位置只能由这一点来决定,即通过它,或者正是由于它,或如拉康所言——只有围绕着它——驱力才有可能开启寻找满足的旅程。这使我们得出,对象所呈现的不过是一个虚空、一个缺乏,而围绕着一个永恒缺席的对象打转的驱力,注定永远无法获得满足。这一对象在驱力中并不具有重要性,用拉康的语言来表述,即对象在其中完全无足轻重。审美情感提供了一个被抑制了其目标的驱力的典型案例,美总是与“缺乏”,以及“失去之物”保持着某种关系[28](P37),“那种使我们在美之中的欢悦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东西是过去的形象”[29](P206)。
当在艺术作品中意外地碰到它,我们的眼睛就从漫不经心的一瞥,立即转换为聚精会神的凝视。考虑一下罗格·德·派勒斯提出的问题:当你穿过一个挂满画的美术馆,你在其中闲庭信步,突然,在某个时刻,一幅画使你停下了脚步。是什么使你停住脚步?“这甚至不是一个我们被其询唤的例子,而是一个被观看的时刻”*Louis Marin: “The Concept of Figurability, or the Encounter Between Art History and Psychoanalysis”.On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7.“询唤”在法语原文中所用的是“interpellate”,英文译本译为“been spoken to”。,总有某种途径,使我们被艺术作品所召唤,去凝神沉思、被其引诱上钩,或被其捕获。这样的一个视觉时刻就是罗兰·巴特所谓的面对艺术品中“难处理之物”的时刻[30](P77),我们被来自于画中的某物刺穿,我们与一个陌生的自我相逢,并接受他的凝视。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们陷入无限的焦虑:那匮乏再次回返,让人难以承受,它们束缚了眼睛和感官,如同一个症候束缚并围困住人体,如同一片大火包围一座城市。这也是于贝尔曼所谓构成艺术品之“面”(pun)的东西,它构成了图像符号的灾难或切分,成为“补充性的线”,同时又是模仿布局中那“不在场的指南”[31](P270)。这还是最终能够使视觉从外观转向内视,从一瞥转向凝神静观的真正根源。在那里,它几乎包含着喷射的行为,又包含着把某种东西置于我们面前的行为,以及当我们看着它时它却正注视我们的行为。所以,人们绘画、写作,不是为了再现、复制已呈现的东西,而是为了展示不可见者,正是不可见者让在场的谜题或奇迹得以可能。[32](P280)
五、静观的现代批判及其效能
这一将物隔离的机制,即悬置其原有功能和意义,使其成为空的能指,进而通过一系列“仪式”使其升华为可欲的乃至具有崇高自主权的客体的操作,之所以被称为一套“机制”,乃是因为它可以脱离原初情境而获得独立运作。由于涉及对主体欲望的操作,而这一操作又如此成功,在现代社会,这一使物升华的秘密机制在宗教和审美领域之外,被成功运用到商业和政治领域。对这一秘密的揭示,成为马克思、徳波、鲍德里亚之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物”之商品化的秘密就存在于“物”首先被悬置了其真正的来源——劳动力的生产创造活动,然后通过一系列类仪式的操作(其中包括广告、橱窗、灯光、模特等等)——使商品本身获得了能指化和符号化,从而成为捕获消费者欲望的强力之网。[33](P88-99)之后,在徳波那里,随着现代各种技术装置的增殖以及资本主义商业的扩展,被升华为欲望之对象的商品逐渐增殖为将社会裹缚其中并无所不在的景观, 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则——社会以“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统治,在景观中得到绝对贯彻。到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观察,景观的无限增殖所形成的拟像乃至完全取代真实,成为超真实的存在,在这一批判理论的悲观视野里,主体被驯化为伪主动的乃至完全被动的,成为景观规则的不幸附属物,它们以主体浑然不知或理所当然的方式必然发生,而主体却以为那是偶然、随机或没有任何意图的:主体被其所捕获、调遣和俘虏,它们在一种欲望关系中迷惑主体,却能够保持自己的神秘。处于现代景观操纵中的主体的欲望不再是自己的,主体的过去、未来乃至希望都不曾、也将不会是自己的。
无论本雅明还是徳波,都看到了这种源自宗教和艺术的力量在现代商品社会的异化,所以连对这一传统如此迷恋的本雅明越到后期也越意识到其历史上的过时性乃至政治上的倒退性,“凝视和沉思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落落寡合的行为”[34](P259),“屈从于静观对象的观众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沉思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35](P10)。这尤其体现在本雅明的拱廊街批判中,拱廊街本身已经幻化为一个巨大的神殿,其中处于橱窗中被隔离的商品被覆上灯光与色彩,成为绝对不可使用的神圣之物,等待着被凝视与被膜拜,等待着欲望的投射。鉴于资本主义这种崇拜装置的无所不在以及强大魔力,一种使用之无能被推向极端,所以阿甘本才发出在当代“亵渎之绝不可能”的感叹。*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礼赞》,载《渎神》,123-16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阿甘本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宗教化运作,其秘密隐藏在使商品通过宗教式的隔离悬置一切使用权,通过绝对不可使用而升华为欲望之物的秘密,而“渎神”(profane)的含义正是祛除商品之绝对不可使用的神秘性使其回归人类的正常使用的政治行为:一旦遭到亵渎,那原本不可用的、被分隔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它的灵光,并被归还使用。
除此之外,本雅明还在法西斯的政治运作中看到了这种对宗教和审美力量的可怕运用。其中,不仅政治活动本身借用同样的升华机制模仿灵晕的运作模式,甚至战争和死亡也被升华为最高的审美快感来体验。宗教静观曾被看作心灵与自我意识在场的基础,孤独的祈祷在之前的世纪中曾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功能,使信仰者能够从教会的中介权威中解放出来。然而,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静观不仅失去了解放性的潜力,反而助长了社会分化和孤立的倾向。因此,宗教实践在资产阶级艺术接受中的遗留不仅不会导向更大程度的自我认知,反而极其类似本雅明在《论恐惧》中所批判的那种世俗化的自失状态。在这里,本雅明的批评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而是更加关注这种静观式接受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一状态内在的孤独本质,将个体与集体区分开来,阻止了交流、团结并最终妨碍政治行动。因此本雅明将具有宗教效果的静观模式拒斥为历史上过时的与政治上倒退的;作为一种对立模式,他转向分心(distraction)的立场,并将其重新抬高为一种解放的工具。
审美静观果真失去了一切潜能,沦为商业操作的附属?审美经验本身是否已经化身为一种牢笼般的体验,其中的主体丧失一切主动性并迷失在商业和政治操作的欲望之网中?事实上,这一悲观的理论视野和现代批判从未使艺术与审美的效果失效,它在历史中的绵延,其涵盖的范围之广,以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在场都不证自明地驳斥了时代对其“已不合时宜”的宣判。相反,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迫地需要这一审美静观的时刻。但这并非对作为商品/景观之蔓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而是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其中,这种审美领域特有的品质将撕下资产阶级的标签,进而在一种人类学乃至伦理学视域中,重获其解放性乃至救赎的潜力。
我们能在让-卢克·马里翁、路易·马兰、迪迪-于贝尔曼、达米施以及阿甘本的文本中看到这一新的理论视野的交织,而对瓦尔堡、李格尔、福柯、本雅明以及拉康和罗兰·巴特的重新挖掘将使之获得一种理论谱系的力量。如果欲望的缘起在于那个裂隙,那个导致了意识与无意识、可被经验与不可被经验者之分裂的原初事件,那么在画面中使视觉由漫不经心的扫视转为静观的正是这一不可能之物,这一罗兰·巴特的“难处理之物”,以及于贝尔曼在画面中发现的“面”。它那注视观者的目光由于触及了那原初失落的物,从而打开了一个记忆的空间:它或许是一次实际的经验,例如一次事故、一个幼年场景、一种驱力;抑或是由于其创伤的特点,以及处于某个对意识而言难以接受的原因,被压抑到无意识中[36](P124),成为一种潜能或潜在的形象。如果那个裂隙的时刻昭示了主体命运的开始,它在将某物或某事件压抑到无意识中的同时也为主体赋予了心理人格与历史上的连贯与一致,那么,审美静观的时刻就是这样一次偶然:其中迷住了主体、“刺穿主体”的那一“难处理之物”将成为返回原始事件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使观者能够通达一个未被充分经历的过去,返回一个对主体而言未被真正给出的事件。那是一个涌现的时刻,也是一次与陌生自我或过去自我的相逢,换言之,这是一次与不可能之物,与拉康的“对象a”,以及与萨特的“彼得”[37](P161)擦肩而过的时刻。只有抵达了这一时刻,现实的原初意义才可揭示。
如果这样的时刻只有在审美经验中方才可能,其未言明的解放性就在于,与其说这是对过去的某种激活,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有所宣示。只有在这种断裂之中,在这些让主体感到失败和偶然的事件当中,主体才能将本身去现实化,未曾预料之事才能突然来袭并中断既定的轨道,由此开启未来新的可能性。对福柯而言,这预示了解放性的那一刻,试图再一次与自己的开端取得联系,以此重新开始。在静观中,那正在看着我的“物”,“却使我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所以我能够从这种想象活动中破译出自己内心的法则,从那里读出自己的命运:这些情感,这一欲望”[38](P73-78)。
这样一个审美静观的时刻,将象征着顿悟。在那里,现在突然与最遥远的过去连接起来,或者反过来说,最古老的希望猛然间外化在当下一刻;久远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当下,最遥远的事情显现于最切近的空间。这就是一个灵晕体验的时刻,或是一个本雅明或阿甘本所谓的幸福状态,一个黄金时代:它摆脱了压抑,并完美地意识到自身,主宰了自身。*这也是本雅明所谓的救赎的时刻,“救赎”以过去为其对象,占有过去,并且有能力去引用它。福柯在同样的意义上指出,艺术或诗艺,也必须教会我们图和去摆脱对过去意象的迷恋,为想象重启它那通向梦的自由之路。有关本雅明的“救赎”理念,参见乔吉奥·阿甘本:《潜能》,237-23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福柯有关诗艺参见Michel Foucault.“Dream, Imagination and Existence”.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84-85,19(1):77-78.其中,那些被未言明之物,那些虽然发生却因心灵之压抑的日常法则而导致的未被充分经验之物,将在艺术品投来的目光的见证下,在他者的面容前,在记忆中登记注册,并作为诗的体验被封存起来,真正成为“我”的一部分。这种审美经验才最终幻化为一种澄明之境,或者李格尔所谓的“心境”。这样的时刻偶然而难得,但它仍旧存在,并成为对抗商业社会无所不在的欲望之网的有力武器,其中,不是欲望对主体的捕获,而是主体从零开始创造的意志以及绝不向欲望让步的决心。
[1][5] Nicolas Poussin.“Letter to Chantelou, Apr.28, 1639”.Elizabeth Gilmore Holt (ed.).ADocumentaryHistoryofArt.Garden City,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8 (2).
[2] Nicolas Poussin.Lettresetpropossurl’art.Paris: Hermann, 1964.
[3] Louis Marin.OnRepresenta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4][8][21][22][26][29][34] 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20]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在图像面前》,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
[7] Walter Benjamin.“Über das Grauen”. In Rolf Tiedemann,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eds.).GesammelteSchriften,Vol.VI.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1.
[9]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ssaysandReflections.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10][11] Alois Riegl.GesammelteAufsätze.Vienna:Augesburg, 1929.
[12][14] Alois Rigel.TheGroupPortraitureofHolland.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1999.
[13] Alois Riegl.“Die Stimmung als Inhalt der modernen Kunst”.GesammelteAufsätze.Wien: WUV-Universitätsverl., cop.1996.
[15] Margaret Iversen.AloisRiegl:ArtHistoryandTheory.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16] GiorgioAgamben.Profanations.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17] Immanuel Kant.CritiqueofthePowerofJudg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 Alois Riegl.“Objectivesthetik”.JournalofArtHistoriography,2014 (11).
[19]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3] Brigit Meyer.“Mediating Absence—Effecting Spiritual Presence: Pictures and the ChristianImagination”.SocialResearch, 2011, 78(4).
[24] Hans Belting.LikenessandPresence:AHistoryoftheImagesbeforetheEraofArt.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5][38] Michel Foucault.“Dream, Imagination and Existence”.ReviewofExistentialPsychologyandPsychiatry, 1984-85, 19(1).
[27][36] 吉奥乔·阿甘本:《万物的签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8] Hubert Damisch.TheJudgementofPari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30] Roland Barthes.CameraLucida:ReflectiononPhotography.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31] Georges Didi-Huberman.ConfrontingImages.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 Jean-François Lyotard.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 Galilée, 2000.
[33] 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3)。
[35] 居伊·徳波:《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7] J.P.Sartre.ThePsychologyofImagination.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1966.
Abstract: In 1639, the French artist Nicolas Poussin put forward an elusive requirement concerning how to look at a painting, which is “distance”.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eads us to the concepts of Walter Benjamin’s “Aura” and Alois Rigels’ “Stimmung”. In the genealogy of this problem, “distance” activates a different way of looking as defined by Poussin, and it defines the substantive properties of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Aufmerksamkeit). In this kind of looking, the beholder will receive the gaze from the object; feel disinterestedness and the insatiability of looking, etc,.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Aufmerksamkeit” has a deeply religious origin and only from this religious origin can we understand these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xplain why it is the dispensable principle for works of art to realize their potencies.
Keywords: distance; Aura; Stimmung; veil; gaze
(责任编辑张静)
TheGazefromObject:TheReligiousOriginof“Aufmerksamkeit”
GAO Xin
(Art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高薪: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9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 14ZDB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