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
——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王小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
——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王小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黄宗羲;私利关怀;自然权利;义利之辨
一、“自然权利”视角: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自近代海通以来,随着神州陆沉、西风东进,西方法政文明逐渐俘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芳心。在此背景下,国人展开了对自身传统的反思:为何现代法政秩序生于泰西而不出于我华夏?于是乎,作为古代后期法政思想之最高代表,黄宗羲自然地吸引了学界的广泛注意。然而,前辈学人出于“会通中西”的考虑,急切地希望从传统中找到“民主”因素,所以纷纷把黄氏思想比附于西方“民主”,以致招来了所谓“民主与民本之争”。此种争论一直延续到近年,归结起来,在此种框架下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定位大概共有四种意见:民主说、民本说、民主启蒙说、新民本说。①张宏敏:《当代黄宗羲思想与著作研究最新成果》,载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8期。又见张宏敏:《黄宗羲民本思想十年研究综述》(1996-2005),载于《从民本走上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研讨会(2006年·宁波)论文集》,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476页。
以今日眼光看来,不论是民主启蒙说还是民主说,都带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嫌疑。众所周知,主权在民、人权自由及代议制政府等观念为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之必要因素,而一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素不具备的——故单凭一句“天下为主君为客”,只能将黄氏思想归向“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能推向民主。②参见王小康:《黄宗羲式法政秩序原论——基于<明夷待访录>文本的分析》,载于《中西法律传统》第11期,陈景良、郑祝君主编,李栋执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21页。而民本说虽能把握黄氏思想的“民本”实质,但只停留于简单强调其与西方“民主”之不同,未能充分把握黄氏思想的真理性,不能体会其历史意义。至于新民本说,立意于调和折中,可谓用心良苦,但这种所谓的“新”却是含糊不清的:如果说,在缺少西方冲击的前提下,中国本土思想单凭内部动力并不能走向现代,那么这种“新民本”也就没什么新前途可言了。
(一)问题缘起:黄宗羲“私利”关怀是“自然权利”观念吗
对于以上研究格局,有学者提出,应以“自由”或“权利”范式来取代传统的“民主”范式,重新估量黄宗羲思想中的“自由”价值。③时亮:《从“民本”到“自由”——以洛克为参照的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201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论文,第14-26页。撇开其结论不谈,这种思考的切入方式令人赞赏。在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中,“自由权利”价值更具根本性,是“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石。以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授权来构建统治合法性关系,实现民主建国,恰恰是“自然权利”的逻辑推演产物。因而判别黄宗羲思想是否涵盖“自然权利”观念,也是回应所谓“民主与民本之争”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笔者赞同以“权利”观念为标准对黄氏思想进行重新考察。
“自然权利”思想是西方世界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兴盛中获得的基本信念:只有“权利”观念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积极性,才能为经济繁荣奠定文化基础。因此,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下,“合法性”之第一要义就在于承认个体之自由权利,并排除超然权威的专横干涉。④参见石元康:《现代社会中价值教育为什么会式微》,载于氏著《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6-164页。这种脱离专断而追求个体权利的理性倾向,正是西方话语中“现代性”的核心标志。⑤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正文第6-14页。
那么,黄宗羲法政思想是否体现了这种“权利”诉求呢?要回答此问题,我们只能将目光回向黄宗羲的相关言论。黄氏大著《明夷待访录》中有言: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笔者按:此言古之圣君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笔者按:此言后之暴君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⑥《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沈善洪、吴光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正文第2-3页。本文中对于黄宗羲言论的引用,一般遵循以下原则:短句、单句,于正文中加括号内注,只记篇名不出页码;长段、复句,加脚注并出示页码。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以上说辞是论者主张黄宗羲思想属于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基本依据。我们看到,这段话充满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自私自利”是人的自然天性,设君建政之目的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而其结果则起码是使天下人各全“私利”、各遂天性——这集中表述了黄宗羲法政思想中的“私利”关怀。
针对以上材料,学界观点截然分为两派:其一认为,黄宗羲思想表明了儒家士君子基于道德信仰而对专制秩序的批判抗争,蕴含了对个人“私利”的关怀,体现了中国“儒家式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然权利”观念。具体而言,他们认为,黄宗羲在人性看法上持“自然人性论”,黄氏所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即类似于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思想,具有启蒙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黄宗羲思想中的所谓“私利”关怀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他的学说实际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其终极目标还在于压抑私利而恢复“纯粹至善”之本性,因此这种“私利”关怀虽有与“权利”诉求相通之意蕴,但并未达到西方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高度。
那么,关于黄宗羲“私利”关怀究竟是不是“自然权利”观念,以上两种判断究竟哪种更合理一些呢?在笔者看来,上述二者各有所得,也都有所缺失:前者失之于比附,不能自觉黄氏固有之局限;后者失之于浅表,不能把握黄氏思想中真理性与局限性的并存,更不能解释黄氏局限性之根源。
(二)黄宗羲“私利”关怀的内涵:“圣贤治法”制度与“天下为公”精神
何谓“前者失之于比附”?现代语境下的“权利”一般是指人之为人所可以主张的正当的私利,而笔者认为黄宗羲“私利”关怀尚未达到此种高度。因为黄氏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统治者(圣君贤臣)的道德义务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社会成员积极主张——与此根本不同的是,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所谓“自然的、不可让渡的、神圣的人权”,恰恰是以理性的个人权利主张为本质特征的。①【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4页。而正是在其自身逻辑的局限下,黄宗羲“私利”关怀陷入了一种吊诡的进退两难境地。下面具体说明。
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遗臣,他以“反专制”思想而享誉近世。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不能不先谈一谈明朝的专制政治及其灭亡。著名史家钱穆先生以对传统文化之“温情与敬意”态度闻名于世,他向来不赞同以“两千年专制”将传统政治“一语抹杀”,不过他却认为明清两代实在可以“皇帝独裁”、“专制政治”名之。②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前言与引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这确实可见得有明一代对政治的败坏!
从宏观条理来看,元末革命虽有“恢复中华”之志,但明代并没有继承唐宋的开明风气,反倒是将元朝的蒙昧戾气“发扬光大”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坏唐宋君臣共治、制约平衡之局面,开有明猜忌士大夫之先河;罢孔子之通祀、删节《孟子》并罢孟子之配祀,是为从理论上伸张君主之“政统”而打压儒家之“道统”;创立“士夫不为君用”罪名、对士大夫滥用廷杖之刑,是为从现实中建立君主对官僚士大夫的绝对宰制——所有这些,全都表明了“明朝政制的劣质化”。③姚中秋:《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2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皇权失控而为所欲为,成了天下最大的祸根乱源,君主与“天下人私利”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皇权专制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才空前地凸显出来。
从微观角度来看,黄宗羲自己也经历了易代鼎革、天崩地解的祸乱,亲眼目睹了皇权专制对天下人之“私利”的危害: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晚明东林党中耿直的士大夫,却在与专擅皇权之阉党的斗争中死难;在后来参与南明朝廷的反清斗争时,黄氏自己也曾身受专制权力的迫害和排挤。当“蛮夷滑夏”、国破家亡而一切希望最终归于寂灭时,所有这些经历都促使他对皇权专制及其传统展开反思,并寻找安顿“天下人之私利”的良法。
黄宗羲的法政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简称“《待访录》”)一书中。此前笔者曾就《待访录》之结构、渊源及主旨辨析写过一篇文章《黄宗羲式法政秩序原论》,其中指出,“(《待访录》)正文21章内部是存在大致清晰之逻辑关系的:《原君》、《原臣》、《原法》三篇(以下称‘三《原》’)通过理论探‘原’,推求了君主权力、君臣关系及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和标准,并抽象出了其法政秩序之最高宗旨——‘天下为公’;《置相》以下18章则贯彻‘三《原》’之精神,对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作出了全面规划。”④王小康:《黄宗羲式法政秩序原论——基于<明夷待访录>文本的分析》,载于《中西法律传统》第11期,陈景良、郑祝君主编,李栋执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这样一种体系安排,当然是黄宗羲融摄传统而推陈出新的设计。顺承此意,这里笔者将其制度设计总结为四个字,“圣贤治法”(即圣君、贤臣、治法):《原君》者,欲使君主明“为君之职分”,所以成就“圣君”也;《原臣》者,欲使大臣明“出而仕也为天下”,所以造就“贤臣”也;《原法》者,欲使君臣共明“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所以恢复“藏天下于天下”之“治法”也。
所谓“圣君”、“为君之职分”者何也?黄宗羲认为,对于君主而言,只有抑制“天子之私”,而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才符合设君建政以成“天下为公”之“义”。也只有如此,君主才得成为“明乎为君之职分”的“圣君”。反之,若君主“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则“为天下之大害”,那么天下人就自然有选择“汤武革命”、“诛独抗暴”的正当性了。⑤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2-3页。
既然要有“圣君”,则也要“贤臣”;既然有“为君之职分”,自应有“为臣之职分”。黄宗羲以为,对大臣而言,“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只有践行“出而仕也为天下”之“义”,才能真正关怀“万民之忧乐”,才是合格的“贤臣”;以君主之好恶为行事准则的,是仆妾之奴臣,而不是师友之贤臣。①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4-5页。
“圣君”“贤臣”谈的都是对人的要求,《原法》篇所谓“治法”谈的则是对制度的要求,即以“天下为公”为正当性标准,因时损益,探究法制变革的方向。在黄氏看来,这个方向就是:恢复公天下、治天下的“三代之法”,废除私天下、乱天下的“后世之法”。何以故?首先,黄氏认为,“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价值取向存在天壤之别:“三代以上之法,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因此“三代之法”是充满了“天下为公”大义的良法;而“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故“后世之法”是无义之恶法。其次,黄氏认为,二者在治理效果上也是大相迥异:“三代之法”使天下人各得其私,故天下太平、争斗不起,这是治平之本;而“后世之法”惟识“敛福于上”,不知“遗利于下”,这正是天下大乱、斗争纷纭的根源,即“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虽然“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高下立判,但现实情形是:“三代之法”已亡,而“后世之法”肆虐。故在此背景下,所谓严守祖宗家法只不过是周旋于错误当中,实不可取。而恶法弊政业已病入膏肓,“小小更革”断不可行,“一一通变”才是正道。②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6-7页。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是《原法》篇中最紧要的一句话。③参见俞荣根:《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这体现了黄氏“复古更化”的变法要求,即宗本“三代公天下之治法”而进行制度变革。具体而言,就是要依照前三篇之后所条陈的种种“为治大法”来进行具体制度建设,如《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胥吏》、《阉宦(上下)》等。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莫不是要求以恢复“治法”来培养“治人”,而又以“治人”来践行“治法”——要之,其最高理想不出乎“天下为公”之外。④萧公权先生认为,“《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贵民’与《礼记》‘天下为公’。其政治哲学之大要在阐明立君为民与君臣乃人民公仆二义。”参见氏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82页。在黄宗羲看来,这种“天下为公”之“义”,其结果最起码是要使“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自利”。不过从“圣贤治法”的制度逻辑来讲,天下生民之“私利”只是映现于“圣君”、“贤臣”的道德义务及“治法”的道德精神当中,而非转成可以积极主张的“权利”。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置相》、《学校》两篇中。
在《置相》篇中,黄氏认为,君主和大臣同属于国家礼制序列,大臣不是君主的附属物,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分身之君”,而宰相则是君主最重要的协助者和制约者——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背景下,天子传子不传贤,“天下为公”之大义通过宰相传贤来保证,这是政治合法性得以延续的基础。在现实制度层面,黄宗羲批判了明代的内阁辅臣制度,认为其不足为训,而宰相制度之废除则正是明朝政治糜烂的根源。他主张应当仿照唐朝旧制、重建以政事堂为中心的宰相制度,以宰相制衡皇帝,规范中央权力格局。⑤政事堂体制见《新唐书·百官志》,参考《明夷待访录(译注)》,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页。《置相》篇此意,一方面体现了《原君》篇所谓君主“明乎为君之职分”的要求,一方面体现了《原臣》篇所谓大臣“出而仕也为天下”、“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的论说。⑥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8-10页。
在《学校》篇中,黄氏认为,学校的功能在于培养士人和评议政事,就像汉宋两代太学之作为那样。“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郡县“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这实际上是要求赋予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以参政议政的权力,包括决策引导和舆论监督。除了重视官学的参政职能外,黄宗羲还要求利用官学培养多元化人才,并大力推行儒家礼俗教化。《学校》篇此意,反映了《原君》篇“天下为主君为客”之大义,践行了《原臣》篇士大夫作帝王师的追求,体现了《原法》篇圣王“为之学校以兴教”的论说。⑦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12页。
由《置相》、《学校》的制度设计,我们看到:第一,虽然黄宗羲言必称三代,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但这主要是托古改制而寻求言说正当性,为了彰明“天下为公”之“义”;而对于“三代以下”的后世他并非完全否定,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失控性君主专制之类的“秦制”和元明,即所谓“夫古今之变,(天下之法)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第二,对于汉唐宋的开明专制,他虽然有所批评,如批判“汉建庶孽藩屏”、“宋解方镇之兵”属于“私心”而非“为天下之心”,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中,黄宗羲还是以汉唐宋君臣共治为范本而重建“圣贤治法”:以唐朝宰相政事堂制度为模范,重建君相制衡的中央权力秩序;以汉代和宋代中央太学积极参政议政为模范,重建“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的学校议政制度。
这样一种设计恰恰反映了黄宗羲虽有对后世专制君主制度的整体批判意向,但对于汉唐宋的开明专制仍然缺乏根本的批判性检视。假如宰相真的能够制约君主,那么何至于被废而使君主专制失控呢,何至于“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此外,学校议政是否真的能“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呢?如果君主一意孤行,丞相与学校是否具备程序化法度来制约君主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黄氏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只能依靠于君圣臣贤,而并未找到平衡君主之“私”与天下人之“私”的良法,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分权制衡”的效果。
在黄氏看来,既然天下人人有“私利”之心,那么君主之“私”肯定是敌不过天下人之“私”的,因为从绝对数量和势力上来看,君主一人之力实在不可能对抗泱泱天下。①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页。但黄氏并未就此走向对于生民“权利”的积极伸张,而是仍然回归陈旧的道德叙事,以重申“天下为公”的古老原则而等待未来圣明君主的采纳,即君主应当“明乎为君之职分”,使之自觉道德使命、克制“天子之私”,从而重建“圣贤治法”,而以“天子之公”成就“天下之私”。②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载于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黄氏法政思想的逻辑结构,决定了其“私利”关怀与“权利”观念的差别。
(三)区别于“自然权利”观念:黄宗羲“私利”关怀的进退两难
黄宗羲认为,依据其“圣贤治法”的设计,只要恢复丞相主政、学校议政、多元取士、建都金陵、方镇制衡等制度,并进行田制、兵制、财政、胥吏及阉宦等改革,那么就可以建立一种由士大夫主导的、君臣共治的政府秩序,而最高君主权力则进入一种受士大夫集团制衡的相对专制或开明专制之状态。但这终究不过是他的幻梦,汉唐宋的开明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元明清以降的君主专制则愈演愈烈。
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恰恰反映了黄氏思想的局限性:在他的潜意识里,想要达到天下大治,非但不能张扬人的“私利”之心,反倒是要予以压抑,因为从根本上他的天下大治只能依靠“治人”及其控制下的“治法”,亦即传统的贤人政治,而普通老百姓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参与的。正是在此局限下,黄氏只能想象一种君臣共治的相对专制政治格局,却无法跳出固有格局而想到启发生民之“权利”观念,这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不可能跳出专制窠臼——这一点我们从上述《置相》、《学校》两篇的制度设计中已看得十分清楚了。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黄宗羲“私利”关怀隐含着激烈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圣贤治法”制度设计有着强烈的“私利”关怀,意图安顿好“天下人之私利”;另一方面,在“圣贤治法”制度的实际运行当中,其并不能确保“天下人之私利”的实现,反倒往往是有强化专制、侵害“私利”的危险。
在《学校》篇中,黄氏主张将地方官学打造成郡县议政之所,并主管教化之事,其中就包括管理出版市场。他认为: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③《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1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黄宗羲对于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书籍,一概“不许传刻”、“追板烧之”,这分明显示了一种以道德干预政治,进行思想控制的想法。
在《财计(三)》篇中,黄氏主张要将端正礼俗、振作教化与富裕人民结合起来,其措施中就包括对市场交易行为进行道德规范。他认为:
“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何谓蛊惑?佛也,巫也……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4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治民行政,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次第,这本是儒家正宗,黄宗羲此论也不出乎此意。然而,对于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市场行为和宗教活动,黄宗羲不仅要“投巫驱佛”,而且要“一概痛绝之”,这分明显示了一种以道德干预政治,进行经济控制的想法。
黄氏自以为这种思想控制和经济控制充满了“救弊”的道德使命感,殊不知此做法与擅夺天下人私利的纯粹专制实际并无多少距离!在这里,道德直接替代法律而成为政策主张,那些具体“私利”不得不让位于黄氏信仰的儒家道义。其实,这正显示了黄氏思想中对于具体“私利”诉求的压抑,“天下人各得自私”只能由圣君贤臣以道德的方式予以安排,而不能由好利生民自主自专。但由于专制权力的体制性失控为黄氏所无力改变,这种所谓的“天下人各得自私”也就注定只有失败的命运了!
正是在此分析基础上,我们可将黄宗羲“私利”关怀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区分开来。一般认为,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是西方中世纪末期以来的一群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它以西方传统的“权利”观念为基础,以“自然法”思想为载体,以追求“自然正义”为最高目标,主张将人生而有之的“平等、自私、自主、自尊、自卫”的自然本性“宣布为权利”,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推翻与价值专断相结合的专制秩序,构建全新的“合乎自然、理性的制度”。②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5页。准此而言,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一是承认“私利”的天然正当性;二是以保护“私利”为其现实法政制度的出发点;三是维护“私利”的法政制度脱离于道德专断而具有独立性。
以此为对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黄氏思想并非“自然权利”学说。首先,从思想基础来看,黄氏思想并未论证“私利”的天然正当性,其“私利”关怀只是在“天下为公”的合道德性结果中得以落实,却不能以直接目的而存在;其次,从其法政理想的具体内容来看,他并不以“私利”为制度建构的直接出发点,因之也并未给出保护个人“私利”的良方;第三,在法政制度与道德观念之关系上,他有一些超越法律而以道德偏好压制“私利”的政策主张,如上述《学校》、《财计》篇之类。
事实上,这种将现实政治寄望于“圣贤治法”之道德精神的想法,本质上还是对私利的压抑,是黄宗羲重视“私利”而又不能积极伸张“私利”,“反专制”却不得不回归专制的根源——因为这种“私利”只能够映现于统治者的道德义务之中,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能容许社会成员积极主张。
由此可见,重视“私利”却又不能积极伸张“权利”,这就是黄宗羲“私利”关怀在其“圣贤治法”制度设计之下的“进退两难”处境。故而黄宗羲式的“私利”关怀只能视作传统民本思想内部的自我批判和推进,其与西方近现代“民主”、“自由”绝不相同,前人谓之“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启蒙思想”真乃是个天大的误解。
二、“义利之辨”视角: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局限性的探源
以上只是初步分析了黄氏具体制度设计中“私利”的尴尬地位,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其与“权利”思想之差距。事实上,黄宗羲虽没有道出“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的口号,但在他“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宣示下,我们分明看到了安顿好“天下人之私利”的努力,尽管其思想未必完善。因此,即使今人认为黄宗羲对于“私利”的看法尚未达到西方近代“自然权利”观念的高度,也不能抹杀黄氏关怀“私利”之铁的事实——换言之,黄宗羲“私利”关怀当中蕴含的真理性是不可忽视的。而否定黄氏思想为“自然权利”论者之浅表,正坐于不能把握黄氏思想中真理性与局限性的并存,当然也就不能解释黄氏局限性之根源。
故而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是,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固有的“私利”关怀,究竟因何未能转成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其真理性与局限性各何所在。对此,大而化之的答案或已有之,但专就黄宗羲思想来分析的尚付阙如。③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第71页。因此,这问题可说是研究者们有所觉知但并未深刻省察的,也是笔者所欲进一步探究的。而在笔者看来,要解答此问题,我们还须研究黄氏哲学思想中“私利”的地位,毕竟这里隐含了文化传统对他的滋养或者局限。而在笔者看来,传统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基础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将黄氏具体制度设计与其思想中的文化传统痕迹回环印证,我们才能理解其“私利”关怀的的全部内涵。
关于儒家伦理对中国现代转型之制约,马克斯·韦伯有个经典论断:正是由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对于“权利”诉求的抑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会滞后,在现代化进程上才会落后于西方。①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八章“儒教与清教”,第233-254页。黄宗羲法政思想中虽有“私利”诉求,却未能转成“权利”观念,不能给私利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这正是对韦伯论断的肯定性回应。然而,个中缘由何在,正有必要研究黄氏对“私利”之正当性的思考。
在中国传统中,探究正当性(“义”)与实利性(“利”)的伦理关系,属于儒学中“义利之辨”的范畴。“义利之辨”,也就是辨析分别“义”与“利”,探讨道德信仰与现实利益的平衡之道。因此,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私利”的“正当”性,当然就绕不开对“义利之辨”的讨论——因为对此关系的认知决定了文化结构中“私利”的地位,决定了“权利”观念是否能产生。申言之,要解答黄宗羲思想中的“私利”关怀因何未能转成“权利”观念,就必须研究“义利之辨”思想传统对他的影响,探明《待访录》中所谓“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与“天下之大公”的关系。②参见【韩】洪性敏:《黄宗羲哲学中公共理性的意义》,载于《从民本走向民主》论文集,第77-93页。
(一)思想传统之局限:“义利之辨”中“私利”的天然困境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由“义利之辨”入手来探求黄宗羲思想中“权利”话语缺失之原因是必要而且可行的。不过,在具体分析黄宗羲思想前,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古代“权利”话语缺失的一般原因有所说明,毕竟任何思想家都必须在具体社会环境和特定文化氛围中来思考言说——“无论他们怎样勇敢和具备反叛的性格,都无法跨越文化的界限”。③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换言之,也就是要分析“义利之辨”思想传统对于“私利”地位的一般影响。
有观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看似偏激的话无非为说明一点: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事件和行为无不是在某种思想观念之驱使下进行的,不论当事人对此是否自觉。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中,“义利之辨”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它指导着士君子的价值取舍,主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风向,正如朱子所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孟子所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再从西汉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宋明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凡有利心皆不可”,又从南宋事功学派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到清朝戴东原所谓“存公欲灭私欲”,虽然对于作为出发点的“义”与作为效果的“利”如何协调的问题上有所争议,但在有一点上却是共通的,即行动之出发点首先必须是合乎道德的“义”,单纯的“利”是不能成为行动之正当理由的。因此,尽管私利不可能被真正地消除,但在价值上却是被放在与“义”相对的否定性位置上。也是因此之故,在对“义利之辨”的持久探讨中,从来不发生“私利”是否正当的反思,而只会发生在伸张道义前提下私利应该被抑制到何种程度的问题。④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七章“义利之辨”,第168-198页。以同属泛道德化偏好之故,对“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理欲之辨”不多加区分,而径以“义利之辨”统之。由此可见,“尊义贬利”、“取公去私”的泛道德化倾向,造成了对“私利”诉求的贬抑,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中“权利”观念难以伸张的思想原因。⑤参考黄宇昕:《论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兼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又名《儒家政治哲学论纲》),载于《中华法系》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第82-83页。
那么,这种泛道德化的“尊义贬利”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种以道德压抑“私利”诉求的传统是如何造就的呢?笔者认为,以性善论为基础、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泛道德化传统正是“尊义贬利”思想倾向的根源。
根据前人研究,以区别善恶为特点的中国人性论大致包括以下几系:孟子—心学一系之一元论的性善论,荀子—理学一系之性二元论,韩非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性无善恶论、道家的性超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和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论。⑥参考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32页;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33~357页;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342页。不过,“各家虽同在论性,而其所说之性,意义实不相同”,其意旨大体可归为两个方面,一为人“生而自然”的性质,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及其在宇宙论上的究竟根据。⑦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50-253页。准此而言,孟子心学一系之一元论的性善论正是对第二问题的圆满回答,树立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正统。荀子与理学一系之性二元论则是兼顾两个问题,意图调和自然性恶与人性本善的矛盾,尽管在修养方法上跟孟子心学一系根本不同,但其实在第二问题之态度上与孟子性善论无区别。韩非子为荀子之“高足”,在第一问题上吸收老师“性恶”的观点,不过对第二问题置之不论,而专在利用人之自然性恶方面下工夫,为君主集权专制提供技术服务。此三者之外,其他各家观点要么不得其传或者对现实政治影响微弱,要么调和折中而不出于荀子—理学性二元论之上,故排除本文论述以外。此处要集中讨论的是孟子—心学、荀子—理学以及韩非子—帝王术这三种体系之人性论对于政治秩序的影响,尤其是对“尊义贬利”倾向之形成所起的作用。
学界认为,与西方早期国家“形成于氏族内部及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建立于旧的血缘氏族之炸毁”不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原始部族征战。①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在此背景下,“家国合一”就成为中国早期统治形式,即“在旧有的‘家’的组织里面灌注以新的政权的内容”。②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34页。于是乎,战胜部族中的旧有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制,其内容就是道德戒条与刑罚镇压的结合,而政治与道德遂处于混同状态。③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2页。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的道德自觉,这种“混同”逐渐从事实状态转成一种主动的价值取向而确定了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寻找统治合法性依据,代殷商而起的“小邑周”主张“天命靡常,惟德是辅”。④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9-30页。由此中国文化实现了统治者之“德”的自觉,并树立了政治与道德一体不分的“周文”传统,而其核心特征即为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这一原则在西周宗法封建制当中得到了良好实践,如果说礼法合治、德刑并用体现了其制度结构的话,那么《礼记·礼运》中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禹汤文武三代之英”等道德化政治之典范的歌颂则可视为此理念的经典宣言。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早熟之道德来压抑私利诉求遂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神圣传统。
作为“周文”之核心精神,“德”是周人将政治秩序建筑于道德秩序之上的基础,也是其最高政治目标“天下为公”之“义”的内在根据。由此我们看到,周人把维持政权先进性寄望于统治者的德性,这分明是“相信人的内心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发掘”,并“把这种信念引入政治,化政治为道德”。⑤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三章“治乱之道”,第98页。这种最早的对于人性之积极期待,我们在孔子之称“仁”、孟子道“性善”中都可以看到传承的痕迹。一般认为,儒家是“周文”的坚定维护者和宣教者,而这种人性论上的一脉相承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源自“周文”之“性善论”的文化正统性。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之“四端”乃是人“不学而能”的“良能”,是“不学而知”的“良知”。此种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既一定程度上维系了道德,也抑制了“私利”诉求,因为在此“良能”、“良知”鞭策下,永远只有人对自我的道德要求,而不可能有对外界的利益要求。在儒家圣训中,君子应该要恪守道义、轻视私利,而对于“小人”则无此要求。在此逻辑下,“小人”未必不能享有私利,但在价值上却总是弱势的——依据礼法和圣训,没有哪一条指示表明“小人”可以自己争取或者反抗,他们只能等待“君子”的安排——因此道义只属于“重义轻利”的君子,而汲汲于私利的“小人”是没有道义正当性可言的。所以,此种理论影响于政治,最多只可使生民之“私利”映现于统治者道德义务之中,并使“私利”诉求掩蔽于早熟道德之下,而“权利”思想则根本不可能产生——君王“以民为本”、士大夫“格君心之非”,这就是孟子心学的政治效用。⑥参见梁治平:《法辨》后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与孟子单就自然“本性”立论不同,荀子的思想是较为理智而客观的,他所关注的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因此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过正如前文所言,荀子之“自然性恶”与孟子所说之“人性本善”并无根本矛盾,因为这二者的指向不同,荀子之说正是对孟子理论的补充——尽管荀子对人之为人的“本性”之思索实不如孟子深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荀子的方案是“化性起伪”,即通过人为努力学习知识来改造人的天然恶性、回复本然之善;而与此种修养观相适应,荀子主张将儒家的道德理想建制化,即通过“隆礼重法”而将仁义礼智之道德精神灌注于国家礼法制度之中,从而实现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即所谓“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在荀子的方案中,泛道德化倾向是一贯的,正因如此,他对人自然欲望的论述并未导向理性自觉,而是积极主动地掩蔽“私利”诉求。因此,此种思维之根源终究还是应该归结到政治道德合一的“周文”传统:正因为中国文化中道德意识的过早自觉,荀子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熏陶,故其性恶之思只是服务于回复性善的手段;而正由于政治不过是道德之工具,那么运用礼法来矫正人民天然之恶也就理所当然了。进一步言之,既然人“自私自利”的天性是需要被礼法纠正的,那么“私利”诉求就是需要被天然抑制的,当然也就不发生“私利即为正当”的思考了。
韩非子为荀子之徒,二者思想间实有渊源可寻。一方面,韩非从乃师处继受了“人性恶”的观念,并予以发挥利用;另一方面,对于荀子所主张以“化性起伪”之方法而回复的“人性本善”,他是不甚关心且不予讨论的。韩非所欲达到的,乃是以“法术势”武装专制君主,用赏赐之恩、刑罚之威与思想钳制三种暴力驱使天下人,毁灭旧的封建制度,而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家主义秩序。在他而言,性恶论只是推行法术赏罚之有效性的一个理论支点,只有工具的意义,与信仰无关。①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第254页。表面上,周文所树立、儒家所发扬的“性善论”传统在这里已经被弃之不顾了;但事实上,韩非子并未真正从理论上驳倒儒家性善论信仰,这也就埋伏下了二者的某种兼容性。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韩非子的国家主义理论最终帮助中国完成了由血缘性宗法封建制国家向地缘性郡县国家的历史变革,它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架构,即君主专制的政治格局。在战国乱世的变法和兼并中,西陲秦国任刑重法,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最终囊括四海。在此背景下,旧的贵族政治被破坏无余,社会原子化被强力推行,而君主至高权威得以树立。此种君主专制制度自秦朝确立后,以迄于清,未发生本质意义上的变化,而中国政治遂落入了专制之深渊②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载于氏著《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55-107页。——正如黑格尔所批评的,整个国家除了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潜在的不自由人。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绪论第18页。作为秦制的最高理论家,韩非子主张“匹夫之私毁而人主之公利”,在他看来,“人生来自私自利”的天性只能够被利用和限制,因为他的目标只是实现君主专制集权。很明显,在此种思维中,个人“私利”真正是天然不正当而且随时可能遭遇侵犯的,因此也就绝难产生“权利”观念了。④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八讲法家的兴起及其事业、第九讲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之意义,第137-173页。这种思想的理路在于,“周文”中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早熟道德抑制了“私利”诉求之理性化,因而“私利”诉求转而以非理性样态出现,即以君主一人的私心控制整个国家——但由于君主自身德能的局限性,此种理论之实践结果最终只能是政治非理性和道德消亡。
本节之所以选取孟子、荀子以及韩非子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主要是因为三者的理论对后世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最为重大。我们看到,从孟子到荀子,这是一个由主观理想转入客观实践的过程,其底色仍然为“周文”的道德信仰,因此都属于儒家之列。而从荀子到韩非子,这种客观实践活动已经全然摆脱了传统道德信仰之束缚了。⑤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270-273页。这三者对“周文”的态度之区别,应该放在周秦之间时势变革的背景下理解:在西周的贵族封建制格局下,宗法等级制已将政治问题道德化,而社会中不存在绝对性权力,因此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秦以后的皇权时代,政治与道德的混同依然存在,但是君主专制政治格局业已形成,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扭转,即以政治支配道德、以道德执行政治。在这种局面下,政治权力才是实际的最高权威,道德信仰的制衡作用十分有限,更多地只能充当合法性外衣或者是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以早熟之道德掩蔽“私利”诉求而致使其无法理性化,正是此种扭转滑落的必然根源所在。
正是在此背景下,由“周文”所开启、孔孟所传承的“道统”遭到了“秦制”的翻覆:“重义轻利”的道德要求本来是作为统治合法性之维系而要求统治者的,结果却成为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荀子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正是他“隆礼重法”的儒学建制化将“尊义贬利”之价值取向与君主专制格局捏合到一起,为政治支配道德、道德服务政治奠定了基础。⑥谭嗣同曰:“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荀子与韩非子开启了君主专制格局和普遍的“尊义贬利”倾向,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心学一系是与此绝对无涉的。孟子心学一系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们继承孔子遗教,点出了道德价值的内在超越性,为中华文明立教垂范;但在政治与道德关系上,毋宁说他们对此也是缺乏足够审视的——在“私利”诉求未理性化之前提下,泛道德化的立场足以驱使他们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而现实的专制政治格局又悄无声息地将此逻辑扭转,意图支配政治的道德最终只能为政治所控制而失去其独立性!
从孟子到荀子,再到韩非子,这种泛道德化精神的推演最终导致了“私利”诉求的受蔽、政治的非理性及道德自身的消亡——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周文”传统与作为其反动的“秦制”传统的纠缠搅扰之中,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了二千余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逃脱的悲剧!总而言之,偏好性善论的人性认知局限与其所导致的专制政治格局结合,引发了“尊义贬利”的泛道德化倾向、对“私利”诉求的普遍压抑和泛政治化的实践,一方面是整个文化中对于“私利”堵截与扼杀,另一方面是暗地里人欲的放肆与泛滥。正是在此氛围中,意涵“正当私利”之“权利”观念不能生成。所有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法政传统,也构成了后世思想家进行思考的基本前提。
(二)“言仁义未尝不利”:黄宗羲调和“仁义”与“私利”的努力及其局限
为了说明传统思想中“权利”缺位的一般原因,上文对人性论思想根源及其导致的现实政治格局已作了详细阐述。从这浓墨重彩的渲染中,我们看到,在盛行“尊义贬利”之泛道德化倾向的传统文化中,“私利”诉求受到极大抑制,而“私利”的地位可谓十分尴尬:一方面对于社会运转来说“私利”是每时每处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社会话语中到处都充斥着对道义的歌颂和对“私利”的贬抑。尽管这种价值观并不是要从结果上消灭“私利”的存在,但是行为的正当目标中是没有“私利”位置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权利”思想了。自秦洎清两千年中,随着皇权专制的愈演愈烈,这种逻辑愈发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从泛道德走向反道德:既然“私利”诉求缺乏正当性,唯有皇权所代表的“公义”为正当,那么一旦皇权失控而为所欲为,则天下生民之“利”、士大夫官僚之“私”就通通无所保障,所谓“天下为公”之“义”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正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演化的实际情形,其中显现了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危机。而这正是黄宗羲所处时代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也是他展开相关思考的现实背景。
关于黄氏制度设计,上文以《明夷待访录》一书为依据已作论述;至于文化传统对其思想的影响,笔者以为《孟子师说》一书值得参考——此书是黄氏阐发乃师刘宗周思想的著作,叙述了黄氏自身的哲学观点,正是文化传统在其思想上的集中反映。
哲学界的一般意见认为,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的哲学见解,基本属于心学家数,而且是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殿军。①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6-337页。与其“理气合一”、“心性合一”的本体论相适应,在修养工夫论上,他强调“穷此心之万殊”以穷理、“功力所至即是本体”,即特别重视发挥道德省悟上的个体能动性,以恢复人性本然之“纯粹至善”——这一方面是对朱子知识修养论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对阳明“致良知教”的阐扬。②刘述先:《重访黄宗羲》,载于氏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新版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载于氏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第62-83页。在这里,我们无意于深究黄氏哲学的渊源和内涵,不过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初步感受到其性善论的基本倾向。性善论对于黄宗羲法政思想的影响,已有学者指出并作过分析。③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第110-136页。不过笔者以为,黄氏人性论思想虽可以性善论名之,但其内容却不光是孟子式的性善论,而是掺杂了荀子自然人性论的因素。
在《孟子师说》一书中,黄氏说:
“程子‘性即理也’之言,载得清楚,然极须理会,单为人性言之则可,欲以该万物之性则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据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于物也……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理者,纯粹至善者也。”④《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35页。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食色性也”章
“其实孟子之言,明白显易,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发,而名之为仁义礼智,离情无以见性,仁义礼智是后起之名,故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不待发而始有也。”⑤《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36-137页。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公都子问性”章
从论述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黄氏的道德理想精神,更可以联想到孟子名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这种对人性积极期待的性善论主张,既体现了孟子对于黄氏思想的影响,也印证了黄氏的心学立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待访录》中,黄氏又表现出对于人“自私自利”之自然天性的高度关怀: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笔者按:此言古之圣君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笔者按:此言后之暴君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正文第2-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认为,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自私自利”本就是人的自然天性;而设君建政之目的就在于为天下提供公共福利,这起码也应是使天下人各全“私利”、各遂天性,即“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但后世专制君主却“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丝毫不能实现此种目的,这显然是违背设君建政之原意的。黄氏此意虽不必是主张“自然权利”的,但无疑地对人之为人的自然天性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同情。从这里,我们又不免联想到荀子对于自然人性的论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尽管在具体方法取向上,黄氏与荀子不尽相同,但其思想中无疑存在荀子之痕迹。
那么,如何理解黄氏人性论思想中这两种因素的杂糅呢?关于孟子和荀子两种思想传统对于黄宗羲的影响,成中英先生曾经有所提及:在政治哲学上,黄氏继承发扬了孔孟“民本”之政道,由此宣示了政权正当性标准;在管理哲学上,他的“治法”思想则较多吸取了荀子直面现实公共行政的特点,另外《明夷待访录》各篇目与《荀子》各篇目的一些对应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②成中英:《论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政道与治法》,载于《从民本走向民主》论文集,第15-23页。这当然是很有创见的,但却未点出在人性论上的影响,更未具体解释为何会产生此种结合,不过这项研究至少使我们确信黄氏思想中容纳了孟荀二子之思想因子。
笔者以为,只有从黄氏著述用意入手,我们才能理解其思想中孟荀二子因素结合之原因,而这正是理解其人性论杂糅的前提。黄宗羲有言:
“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孟子》)七篇以此为头脑:‘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正言仁义功用,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遗亲后君,便非仁义,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笔者按:依据文义,疑黄氏此语有逻辑错误,”不是“与”未尝“必去一词,方符合此处对仁义与事功之统一性的强调)。自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全身远害,是乃遗亲后君者也。此宋襄、徐偃之仁义,而孟子为之乎?”③《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49页。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
在黄宗羲看来,儒学正统在于“内圣外王”,而仁义与事功原是一体。但“后世儒者”却将二者分离割裂,即所谓“事功与仁义分途”,则往往事功沦落而仁义亦寄之空言!因此若非重振事功,则仁义也无希望。这正是他眼见宋明沦亡、“蛮夷滑夏”而总结出的血泪教训。对于黄宗羲而言,如果说孟子所启发于他的是以仁义和“民本”作为统治正当性根据的话,那么荀子所启发于他的则是治国具体手段,即“为治大法”。④关于黄宗羲法政思想对孟子之内圣和荀子之外王两系思想的结合,学者时亮也曾指出,惜其并未深入到人性论的层次来探讨。参见时亮:《黄宗羲“治法”思想论析》,载于《中西法律传统》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248页。换言之,黄氏正是要将孟荀二子的优点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寓事功于仁义之中,而其中振作事功尤为迫切。黄宗羲说“言仁义未尝不利”,其意无非强调要用仁义之道而使天下人尽得其事功之利。
只有着眼于此结合之用意,我们才能理解黄氏人性论思想中两种因素的杂糅。在荀子的哲学体系中,“自私自利”的自然人性是其一切判断的基础。虽然他并不以此为天然正当,而是“恶其乱,制礼义以分之”。实际上,此种强调制度规则的思想与孟子强调统治者道德之功能的思想,只不过是方法的侧重不同,而在目的上并无根本冲突,都可以归结为:俾使天下人“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各顺其性。⑤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152页。如果说,修仁养义、恢复本善是人之为人、尤其是统治者的内在道德需要,那么使“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自利”则既是对统治者“以民为本”的要求,也是制度规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笔者认为,《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所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一方面是对《荀子》之自然人性理念的变通发挥,另一方面也是对《孟子》“保民而王”之价值取向的深刻阐扬,它们共同指向一点:统治者必须安顿好“天下人之私利”,否则就会丧失统治合法性。总之,在人性论上,黄宗羲基本是以性善论来融摄自然人性的:性善论指向的是人的本性,它指示了道德修养的应然归宿;而自然人性则是天下生民百姓的自然特性,是统治者所应当尽量满足的对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孟荀杂糅有一个内在矛盾:从结果来讲,“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是“天下为公”的应有之义;但从目的来看,在“义利之辨”哲学的指导下,任何“私利之心”都是缺乏正当性依据的,因此天下人只能等待圣君贤臣的安顿而不能自己争取。这是孟荀二子给中国政治奠定的基本传统,而黄宗羲实际上也未能超出此范围。在上叙引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崇仁义而建事功”,而不是西方所谓“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这是由于,尽管黄氏对于“私利”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在性善论的指导下,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是其必然选择,以自然欲望为基础的“私利”诉求受到抑制,他不可能提出以“私利”正当化为前提的“权利”思想,因而其“私利”关怀只能是“进退两难”:一方面“私利”不可退,因为一旦“天下人之私利”不存,则以政治执行道德之“天下公义”必成空话,统治合法性危机就会显现;另一方面“私利”不可进,因为一旦“私利”伸张而人欲泛滥,则以道德支配政治的圣贤权威就会受到挑战,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政治的文化基础。总之,按照泛道德化传统之话语逻辑,黄宗羲即使有对“私利”的极大重视,也根本不可能提出西方式的“权利”观念来。
事实上,就其“圣贤治法”制度设计来看,黄宗羲所批判的也只是失控之君主专制,而不是所有的君主专制。他所真正期盼的,即使不是回归所谓的“三代圣王之治”,也是回到汉唐宋的君臣共治局面。①总之,天下生民“私利”映现于“圣君”、“贤臣”的道德义务之中,而并非转化为其可以主动争取的“权利”。这种泛道德化传统对“私利”诉求的持久掩蔽和压抑,从根本上将黄宗羲思想排除在“权利”观念之外——他所主张的只是作为一种结果的“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自利”,而不是任由天下人发展其私利诉求。
正是基于此,我们发现,黄宗羲虽然致力于“反专制”,但他所提供制度方案之现实意义却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黄氏的所谓“反专制”,主要是反对元明两代“秦制”之类的失控性绝对君主专制,而不是汉唐宋的开明专制。在泛道德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他看不到由开明性专制滑落到失控性专制的内在必然性,看不到道德批判对于专制权力的无力。黄宗羲的这种无力,反映的恰恰是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的泛道德化传统之无力:正如由孟子到荀子再到韩非子的蜕变一样,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的泛道德主义,由于其对“私利”诉求的压抑,在其造就的专制格局面前只能不由自主地反转扭曲,变成以政治支配道德、以道德执行政治的专制帮凶,从而走向反道德。这种源自于先秦、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泛道德化传统,既是造成专制政治并致使“权利”观念不能产生的原因,同时在专制政治压抑“私利”过程中,又一次强化了自己。只有明了此种逻辑回环,我们才能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当中“权利”缺位的真相,才能在中西差异当中正视中国法政文明固有的缺陷和盲点。②
综上所述,黄宗羲把儒家传统的“天下为公”之义阐发成为“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自利”,虽然逻辑上并无根本创新,而事实上却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是由于其受性善论传统的影响,黄氏虽有对“私利”的极大重视,却也不能逃脱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的泛道德化倾向,因之只能压抑“私利”诉求而不能促进其正当化,故而也就不可能超越文化界限提出西方式“权利”思想来;反过来,又因为“权利”思想的缺乏,因此黄氏只能选择从失控性君主专制回归到开明性君主专制,但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君主专制权力失控的问题,而这又注定了其所谓“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自利”的理想只能落空。
三、走向“权利”时代:黄宗羲“私利”关怀的现代转化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固有的“私利”关怀,与“周文”觉醒之“德”、孔子创发之“仁”、孟子阐述之“义”,其理路实际都是一脉相承的,即天下生民之“私利”映现于统治者的道德义务之中,而这正是“天下为公”的应有之义。由此可知,黄宗羲乃是儒家“道统”的维护者,并无根本的创见。然而,真理之为真理,不在于新而在于真。在元明专制酷烈之际,黄宗羲将“天下为公”之“义”阐发为“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把这行将澌灭的“真理”再一次激活起来,顺应了反抗专制的时代潮流,延续了文化血脉,这正是他的贡献。
然而也必须承认,正由于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泛道德化传统之影响,黄宗羲只能在以道德掩蔽“私利”诉求、以道德支配政治的旧途上行进,因而他对“天下为公”之“义”的阐发也就只能止于“天下人各得自私”,而不可能提出西方式的“权利”思想来。在其泛道德化框架中,解放“自私自利”之人欲对于人间秩序是毁灭性的——“私利”公然泛滥就意味着道德的崩塌,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以道德为合法性基础的政治秩序的动摇。①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因而,黄宗羲的理论虽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专制政治的暴虐,却未能积极主动地伸张人的“正当私利”,因而无法从根本上逃脱专制政治的传统窠臼。由此我们发现,黄宗羲思想中的“私利”关怀,虽然确实表明了儒家试图突破传统局限的某种内部批判,但总的来说并未达到西方近代“自然权利”观念的高度,未能找到法政现代化的正确出路。
在今日看来,不能伸张个人的“正当私利”,这正是传统儒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之阻碍的根源——这是整个传统儒家在外王事功上的失败,也是黄宗羲的失败,尽管他曾努力突围。对于今人而言,探明黄宗羲“私利”关怀因何不能转成“权利”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以为,这种失败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以泛道德化倾向为特征的“义利之辨”思想传统对“私利”诉求的压抑。
(一)法政现代化转型: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
以现代哲学话语来讲“义利之辨”,则“义”即正当性,属于道德的范畴,解决内心信仰问题,“利”即实利性,属于理性的领域,解决现实政治和认知问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诡谲的,其所牵涉的道德与理性之关系,是哲学中最高位阶——精神哲学的核心主题。人之为人,既有精神生命,也有自然生命。从本质上讲,人是精神生命自觉的产物,精神生命将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理性推置于外,而以追求道德自觉为最高使命。对人而言,道德与理性是一体两面:道德的本体是精神生命,即内在于人的善良本性、“良知良能”;而理性则是道德本体在现象界的投影,它就是“根本恶”——理性以人自然生命为基础,它本身不是恶,却是现实中一切恶的根源。道德与理性之辩证关系在于,理性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理性主体与道德主体自我分裂,意味着二者的天然矛盾,但是理性主体的自觉又反过来促使人道德意识的觉醒,这是道德自我实现的前提;表面上,精神生命的应有主宰地位被其所投影的理性篡夺,但正因如此道德本体才会力求恢复主宰地位——事实上,只有当理性自觉和理性主体普遍建立而扫清现象界一切对于“形式之我”的束缚之后,精神生命才能获得普遍自觉和实现,道德主体才能真正得到安顿。②参考黄宇昕:《论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兼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第51-54页。基于普遍的人性,以上论述者乃是中西共通的。
事实上,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并非谬误。但直接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使政治成为道德的附庸,使“私利”之理性诉求受蔽而不明,这就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缺陷了。将道德作为政治之基础,是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保证,是评价现实政治的重要标准。中国自“周文”道德自觉以来,俾使统治者觉悟“天下为公”之道德义务,一直是国家文化命脉所系,是我们中华子孙、圣人之徒所应当万世传继的“道统”。然而,基于性善论的泛道德化倾向片面强调统治者之道德义务,对人之为人的自然欲望却缺乏客观面对,因而未能以理性自觉而为“私利”开出积极的道路;而在理性受蔽和不独立前提下,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的泛道德主义只会助长专制政治,而扭曲变态为以政治支配道德、以道德执行政治的专制帮凶,从而重复由孟子到荀子再到韩非子的蜕变。在此逻辑下,“天下人各得自私”并不能真正落实,“天下为公”之“义”也就只能沦为一句空话了。因此,这种泛道德化精神的推演最终只能导致理性的受蔽、政治的非理性和道德的消亡,这是包括黄宗羲在内的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教训。
关于泛道德化传统的内在矛盾,黄宗羲也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但他只能疾呼“向使无君也,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即从反面强调抑制“私利”诉求之道德化政治的非理性和反道德结果,但却没有跳出泛道德化倾向之窠臼,没有从正面伸张“私利”诉求之正当性,因而也就无法提出“权利”思想,不能真正破除专制政治之祸害。从根本上讲,这还是文化背景的局限所致,他不可能突破文化界限和思维盲点而提出以理性自觉和独立为前提的“权利”思想来,这也就决定了黄氏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在外王事功方面失败的必然性。①秦晖:《西儒融会,解构法道互补》,载于氏著《传统十论》,第199页。秦晖先生就曾指出,假如没有新思想资源的引入,仅凭黄宗羲式的醇儒是不可能克服专制政治的,更无法独自促进中国的法政现代化。
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政治虽然应当以道德为基础,却不能成为道德的附庸,不可直接以道德支配政治、以政治执行道德;政治应该相对独立于道德,而受到自觉之理性的支配,只有这样人的自然欲望与“私利”诉求才能得到合理安顿,道德之最终实现才有希望。在这方面,西方法政之学可以给我们较多启发。
坦然面对以人自然欲望为基础的理性,这是西方“权利”观念产生的前提。在西方,“自然权利”思想虽然是近现代的产物,但是其基本文化因子早在上古就已萌芽。在其传统中,西方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意味着,西方文化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其出发点是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理性,其内在结构是本能欲望和理性的抗衡。这种抗衡的结果,就是理性主体之自我意识觉醒:一方面承认自私自利为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个人“私利”的天然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外在制度进行协调约束。换言之,以“性恶论”来框定对人性之认知,以理性为基础,西方人建立了本能欲望理性化的“自然权利”、“自然法”体系,这是西方法政文化的逻辑基础。②参考黄宇昕:《论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兼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第78-84页。
以性恶论为基础而政治与道德相对分离,这是西方自上古以来就有的传统,而且随着时代推进这种分离愈来愈充分,直到近现代政治完全独立于道德和宗教。③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第88-96页。正是在此种理性自觉和独立的文化氛围当中,人的自然欲望才受到了客观面对和安排,这是“权利”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西方近代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的前提。以自觉之理性关注人的自然欲望,这恰恰是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所缺乏的——这种缺乏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泛道德化倾向所导致的,也是“权利”观念缺位和现代法政文明不能生成的直接原因。
由此看来,对今日正处于法政现代化转型之中国来讲,黄宗羲“私利”关怀之最重要启发在于,我们应将源自先秦的、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以泛道德化倾向为特征的“义利之辨”思想传统予以整体的批判性反思。而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以“权利”为基础建设民主法治制度,这正是中国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是当下中国顺应时代大势所应采取的态度。
(二)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义利曲通,西儒融会
那么,在此过程中,黄宗羲式的“私利”关怀将何以自处,这种中国式的“私利”关怀、事功志向是否能够与现代“权利”观念进行合理对接呢?中国文化还能否维持其自身主体性呢?
笔者以为,这种对接是既可能又必要的,而且与维持中国文化主体性恰恰是相辅相成。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有言:“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是‘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是‘实现’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讲使命。”④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新版序第3页。所谓“实现而不是适应”,就是说儒家不应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剪裁,而是应当主动地促成和改良现代化。就本文来看,传统儒学的“义利之辨”虽有其弱点,但亦自有其不可磨灭者在:性善论点出了人之为人的道德义务,将道德作为政治之基础,促进了统治阶层的人心驯化和社会风俗的良善提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魂要义,其意义是历千古而永在的。
因此,我们正是要将此“义利之辨”向前推进,开出“权利”观念、外王事功来,而不是根本否定此道德精神——正如牟先生所说,“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⑤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新版序第9-10页。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传统儒学的泛道德化模式,是根本无法推导出“权利”观念、外王事功的,这就提醒我们:内圣之学虽须坚持,但并非走传统儒学直接由内圣通向外王的老路。牟宗三先生认为,由内圣到外王,有“直通”,有“曲通”:“直通”是以前的讲法,事实上它只能导致外王的萎缩,这一点已为上文所印证;而“曲通”则是现在关联着民主科学的讲法,是间接相通。⑥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48-53页。具体言之,将道德信仰作为政治的终极基础,但反对直接以道德支配政治的传统做法,要使政治独立化、客观化,促使理性自觉和理性主体普遍建立,直面人的自然欲望和现实利益,以“权利”为基本点而建树民主法治的现代法政文明——这种“义”与“利”、道德与政治、内圣与外王的间接相通,笔者谓之为“义利曲通”——这也正是黄宗羲“私利”关怀对于中国法政现代化转型的启示。
显然地,在法政文明现代化方面,西方人早就走在了我们的前头,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法治对于他们而言早已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西方这方面的经验。当然这种学习必然是以反省我们自身传统为前提的,其中反思传统里面“权利”观念之不兴的原因尤为重要,这是今日改造传统以开出“权利”观念、外王事功的前提。如果说本文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主要就是以黄宗羲为标本对于“权利”不兴之原因有所回答。
至于如何改造传统以开出“权利”观念、外王事功,秦晖先生所谓“西儒融会”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启发,他认为:黄宗羲式的民本派儒家本身应当成为法政文明现代化可以凭借的本土资源,而这种资源的价值可以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符号价值,即为现代化价值观提供一种中国式表述;二是功能价值,即原初儒学民本精神与所谓西学在现代化转型中可能实现的功能互补;三是超越价值,即对于西方“现代性危机”提供一些中国式反思和意见。①秦晖:《西儒融会,解构法道互补》,载于氏著《传统十论》,第199-204页。以黄宗羲式民本思想对接西方现代民主法治,此说可谓至言!
据笔者看来,以黄氏所谓“天下人各得其私”来接引西方“权利”观念,使之本土化、丰富化,这是秦先生之前两层面的应有之义。当然,只有在“义利曲通”的逻辑框架下,这种“西儒融会”才能真正成功。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客观化态度认识“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促使以自然欲望为基础的理性走向自觉,从而启发民众的理性主体意识,催化“权利”观念之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泛道德化倾向是必须清算的: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精神生命之性本善,还要关注自然生命之根本恶;不仅需要启发道德主体的“德性之知”,还需要启发理性主体的客观物化之知;只有破除泛道德化倾向,我们才能使理性自觉和独立,才能解放出理性主体的客观物化之知来,这既是发展科学知识的前提,亦是开发以“权利”为基础之民主政治的前提。
那么,如何破除泛道德化倾向,促使理性自觉和独立,启发理性主体的客观物化之知呢?在这方面,牟宗三先生有过精辟论述,而其及门高弟李明辉先生则将其作了如下总结:
牟先生最早在《王阳明致良知教》当中提出了“良知之自我坎陷”说,原是为了说明良知与知识的关系,其后在《历史哲学》与《政道与治道》二书中他又重提此说,借以说明德性之知与科学、民主的关系。他把理性的表现区分为“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简单地说,理性之运用表现是一种“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一种概念式的思考,主体与对象表现为一种对待关系(coordination)。牟先生将传统儒家所着重的“德性之知”归诸理性之运用表现,而将民主制度与科学知识归诸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运用表现是道德主体的直接表现,而当它要转为架构表现时,道德主体表现经过一个“自我坎陷”(self-negation)的辩证的转折。这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间架进行一种现代转化,将“内圣”通往“外王”的过程由直通转为曲通。牟先生以此巧妙地响应了自由主义学者的质疑:他一方面承认德性之知与民主政治在本质上的不同,因而解释了儒家思想在过去未开展出民主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肯定德性之知与民主政治的内在联系,并为此提出理论说明。②李明辉:《阳明学与民主政治》,载于氏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由此可知,牟宗三先生所谓“良知之自我坎陷”,就是要从精神生命之中辩证地解放出自然生命来,也即从道德良知中开发出理性的“认识心”来,促进理性自觉和理性主体的普遍建立。而要达成以上目标,前提就是要改造儒家传统,使“内圣”与“外王”曲通,道德与政治曲通,也即上文所谓的“义利曲通”。只有使理性独立发展,我们才能促使民众真正自觉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由“天下人各得自私”转成“权利”观念。批判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泛道德化传统,以理性自觉而启发“权利”意识,建成相对独立于道德信仰的民主法治,这既是安顿天下人自然生命的前提,也是提撕精神生命的基础。③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9页。
至于秦氏所谓超越价值,笔者以为,那就涉及到对于中西文化的根本批判问题了。西方人之精神生命寄托于宗教道德,其信仰慑服于上帝的外在权威——这种以外在超越而安顿内在道德的做法,具有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进入了一个理性爆炸的时代,上帝被作为“祛魅”的对象而疏远了。正因如此,他们知识越多越远离“上帝”,道德无处栖身、精神生命无从安顿,以至于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机。这根源就在于西人道德信仰的外在性,在他们过于关注由理性出发来建构外在权威以规范自然欲望,而却没有意识到人“性本善”,更遑论进行良知自觉。在这方面,西方人恰恰需要向中国人学习,向儒家学习。在这方面,盲从西方而菲薄传统是不可取的,是违背理性与道德之辩证关系的。如果说,西方文化中以理性为基础的“权利”观念及民主法治制度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话,那么中国儒家文化中以人精神生命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同样是具备普遍性价值的。①参考黄宇昕:《论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兼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第114-118页。在政治上建设现代民主法治以安顿自然生命,而在道德上以儒家文化提撕精神生命,这种“义利曲通,西儒融会”既是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出路,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大同的应有贡献。
行文将尽,回归主题。本文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探究了黄宗羲“私利”关怀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观念的区别,深入分析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以泛道德化倾向为特征的“义利之辨”思想传统及其所导致的专制政治格局对“私利”诉求的重视与贬抑,展现了“私利”在传统文化氛围中复杂而吊诡的处境。事实上,黄宗羲“私利”关怀不仅是儒家传统的个案例证,其思考本身更包含了对传统的内在批判,而其批判的不彻底性又显示了传统之顽固,展现了中国法政现代化的复杂困境。当然,也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法政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辩证性: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走向“权利”,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以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今天我们提“义利曲通,西儒融会”,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相比黄梨洲而言,今人只不过多了一些西学视野,所以才有综合创新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国法政传统中的“天下为公”之“义”,今人理会应是不及黄梨洲之万一的!至于黄氏所阐发“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道理,当下恐怕更鲜为人知了吧,更遑论批评而推进之呢!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段志强.明夷待访录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张宏敏.当代黄宗羲思想与著作研究最新成果[J].哲学动态,2006 (8).
[4]冯天瑜.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5]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6).
[6]程志华.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J].哲学研究,2004(2).
[7]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师伟.崇公抑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主旨[A].刘泽华.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石元康.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0]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1][美]狄百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国的自由传统[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12][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姚中秋.国史纲目[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6]秦晖.传统十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1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8]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0]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1]黄宇昕.论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兼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结合[A].中华法系(第七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49-121.
[2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2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理与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5]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26]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
[27]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8]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9]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0]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责任编校:邹俊杰】
Reflections on Huang Zongxi's Concern about"Private Benefi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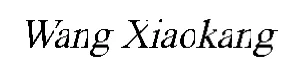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Thereareessentialdifferencesbetweenthetheoryof"privatebenefits"intraditionalConfucianpoliticalthoughtwhich isadvocatedby HuangZongxi,a Confucian scholarin theMing Dynasty,and thetheory of"natural rights"which is the basis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s,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semblances.Huang's concern about the public's"private benefits"can only be reflected in moral spirit that"the world is for all",because of his design of"perfect monarch,virtuous minister,and good system".In other words,the"private benefits"can only be arranged by the governor,rather than actively participated by ordinary people.As a result,Huang Zongxi puts forward"private benefits"to oppose autarchy,but cannot completely avoid it;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private benefits"but cannot propose and promote the concept of the"civil rights".In the final analysis,Huang's thought is influenced and limited by the tradition of"the debate over justice and benefit".Underthepan-moralizationpreference whichisbasedonthetheoryofgoodhumannatureandtheintegrationofpolitics and ethics,it is inevitable to glorify the justice of moral principle while censuring or belittling the pursuit of benefits.In the modernizationandtransformation of modernChinesepoliticalandlegalsystem,ontheone hand we should rethink Huang's concern about"private benefit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hought of"rights"and construct modern system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als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moral spirit of Huang's theory about"private benefits",and maintain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modern China.
Huang Zongxi;the Concern about"Private Benefits";Natural Rights;the Debate over Justice and Benefit
D997.9
A
1673―2391(2016)04―0012―16
2016-06-20
王小康(1993—),男,湖北黄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2015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