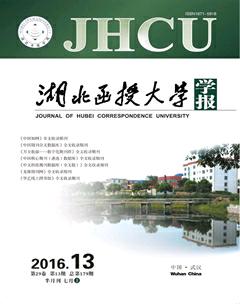“Economy”汉译名变迁的文化资本解读
吴央波
[摘要]从文化资本视角对经济学术语进行解读是非常重要但研究不够充分的领域。本文选取“economy”为个例,研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译名。经分析发现,其汉译过程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翻译场域,并成为一个以“economy”汉译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译者在“economy”汉译这一场域对文化资本的掠夺。该文对解读其他经济学术语的汉译可以提供一定借鉴,并且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诠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演进。
[关键词]“Economy”汉译;符号变迁;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3-0150-04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3.073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当今社会出现很多“经济”新名词,如“生态经济”、“国民经济”、“经济社会”等,殊不知百年前英文“economy”的对应汉译名不止“经济”一词,出现了“节俭”、“富国”、“生计”、“计学”、“资生”、“理财”、“兴利”、“养名”、“世务”,甚至“叶科诺密”等译名百花齐放的局面。为何百年前会出现这种术语万花筒的现象?当时的译者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各自采取了怎样的方式进行“economy”汉译实践的?当下流行的“经济”译名到底是对英文“economy”的汉译还是源于古代汉语“经邦济国”和“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译名的最终确立又经历了怎样的难产?
翻译以语言为媒介,却又超越语言本身。术语翻译“一方面受语言内在本质属性和术语翻译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外部因素的影响。”自19世纪下半叶起,“economy”术语的翻译实践经历了风风雨雨,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已构成了特定的翻译场域。整个翻译过程已然涉及如何调和各方张力的问题,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不仅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翻译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中“文化资本”的概念来分析“economy”汉译名变迁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而展开译名汉译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当中涉及的文化资本及其汉译权力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二、“Economy”汉译名词源考证
方维规教授指出,自马礼逊(R.Morrison)1822年以“节用”、“节俭”译“economy”以来,国人在理解和翻译“economy”和“economics”时常通用这两个概念。因此,笔者在论述各类汉语译名时,也基本上将“economy”和“economics”两个词“同等”对待。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术语都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产物,都会带有那个年代人们认识水平的痕迹,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术语的内涵会逐渐转变。因此,要了解那个时候各个译者为何会采用“节俭”、“富国”、“计学”、“养名”、“世务”等特殊概念,并挖掘当时多元系统内各种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张力关系,就必须从词源上进行考证,了解英文“economy”及“经济”诸汉译名在当时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内涵,这才是进行正确翻译和解读的前提。
(一)“Economy”一词的由来及其演变
英文“economy”一词其实是从古希腊文演变而来。最早使用该词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Xennophon),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该词意为“家庭管理”或“家庭生活”。这就是英文“economy”一词的始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概念主要还是局限于家庭这一块。再后来才逐渐通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或“安排”。而至近代,“economy”才慢慢具有经济和经济学双重含义。
(二)中国古典词:“经邦济国”、“经世济民”
由上节分析,我们得知西方的“经济”概念源自微观的“家庭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古汉语中宏观的“经邦济国”、“经世济民”不同。作为古典义的“经济”,是“经”和“济”的合成,而“经”和“济”在我国很多古籍中都有考证。“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据《晋书》记载,西晋“八王之乱”时期,长沙王司马义曾写信给他的弟弟司马颖,称他们是“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之后,又有陈亮的“志存经济,重许可。”这两处的“经济”均指经邦济国、经世济民之意,即治理国家和救助百姓。再如我们熟知的古时佳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里夸的就是司马迁、司马相如两位的文学才华,以及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所以古汉语的“经济”都是比较宏观的概念。
时至晚清,科举考试中开始设立“经济特科”,要求时人懂“经济”,也就是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一些来华传教士也开始使用“经济”一词,如1875年9月开始,林乐知(Young J.Allen)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中西关系略论》,便有“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一类的表达。这里也是指“经世济民”之意。
(三)日语借词:“经济”
根据刘正琰等人编撰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古汉语,即上文所述的“经邦济国”和“经世济民”之简称;二是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译法“keizai”。但事实上,周振鹤考证发现“keizai”起源于我国汉语典籍中的“经济”一词。此外,叶坦发现日本较为权威的辞典《广辞苑》对“经济”辞条的解释为:(1)《文中子·礼乐》治国救民、经国济民、政治;(2)economy,即经济;(3)俭约。可见,日本人在译该词时,选取了中文“经邦济国”义的“经济”,这点也可从以下的例证中看出。
日本江户时代,已经有了很多以“经济”命名的书,如海保青陵的《经济谈》、太宰春台的《经济录》等。1867年,神田孝平将英国义里士(W·Ellis)的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翻译成《经济小学》,这里就是用“经济”对译“economy”。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讲授西方经济学,所用的教材是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至此,日本人已普遍在理财、节俭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慢慢脱离了该词的中国古典义。但是,日本经济思想史专家山崎益吉指出:“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的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
不难看出,日本人最初在翻译西方经济学“economy”术语时,挪用了汉语中宏观意义的“经济”一词,而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一词实则在日本获得新义后回流汉语的日本借词。
(四)自创新词:“富国”、“生计”、“计学”等
事实上,对日本译文的“经济”一词,当时的国人还是持保留态度的,这可从常见的“日本谓之经济”之类的注释窥见国人的态度。那么时人又是如何自创来翻译英文“economy”的呢?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名出自清末京师同文馆的“富国策”。1876年,该馆总教习,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以英国经济学家福赛特(H.Fawecett)的《政治经济学提要》(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为教材,开设了经济学课程,并在四年后以《富国策》为名出版了此教材的中译本。1886年,另一位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S.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以《富国养民策》中译名出版。经清朝学部审定,“富国学”在这两部译作出版后成为经济学之译名。为此,“富国”也成为“economy”之汉译,符合当时国人希望“富国强民”的社会潮流。
除了由传教士倡导的“富国”经济译名外,时人中还出现了梁启超偏爱的“生计”、“平准”和“资生”,严复喜好的“计学”和其他“理财”等“economy”汉译名。跟“富国”译名的出现和流行一样,这些自创新词的出现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体分析见下章。
三、“Economy”汉译名变迁的文化资本解读
由上文梳理和分析,我们得知清末民初的“economy”译名,有传教士倡导的“富国”、来自日本的“经济”和国人自译的“生计”、“计学”、“资生”、“理财”、“平准”等,都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内涵。显然,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使得“economy”汉译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权力斗争场域,表现为译者在“economy”汉译这一场域中的博弈行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社会学,尤其是运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诠释其中的社会文化关系。
(一)翻译社会学与“文化资本”理论概述
布迪厄(Bourdieu)在其专著《区隔》中,曾经列出了简要的社会学分析模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其中,场域是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通俗点来讲,就是“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惯习是参与者个人表现的持久性性情倾向,与场域相辅相成。在特定的场域中,参与者因各自不同惯习所产生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资本。布迪厄借鉴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认为资本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三种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通俗来讲,经济资本类似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金钱、股票等;社会资本也就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人脉”;而文化资本是指教育方面的资源,如专著、译本、文凭等。这三类资本与社会权力紧密相连,且可相互转化。
本文将主要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分析“economy”汉译过程。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又有三类具体形式:具体的、客观的和制度的。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指的是“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它具体表现为一个人的文化、教育和修养等内化的东西,类似于上面所述的惯习概念。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指的是“一种客观化的状态,以书籍、绘画等物化产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指的是那种“被体制认可的、已经获得了合法性的文化资本。”
(二)“Economy”汉译名变迁背后的实质——文化资本掠夺
针对五花八门的汉译名,我们不禁会问各译者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在“economy”汉译实践这一场域斗争并获得文化资本的呢?为此,下文拟将每个汉译名在时空向度与具体的社会时间和场合结合起来,考察各译者对“economy”汉译这一文化资本的争夺,试图揭示出“economy”汉译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累积和投入方式,从而使其效用达致最大。以下将从具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Economy”汉译的具体化形式
从译者的角度来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相当一部分的具体化文化资本是经过译者后天努力获得的。很多译者在翻译之前,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花费大力气才积累和具备了一定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形式。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中国的文人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因此,洋务、自强等运动应运而生,使得“富强”二字频繁提及。在时人眼里,富强,即“富国”强兵,但也涉及到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或经济事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救国。来华传教士正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在选取译名上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倡导的“富国”经清朝学部审定成为当初“economy”之译名,这与明清时期传教士的“适应策略”有很大关系。此译名不仅满足当时特殊读者群体的需要,并推动和促进了“富国”经济译名在当时的传播。
从累积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一种信仰符号欲进入另外一种社会符号系统而无现成的对应词时,如果传教士们不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语言能力、知识结构,不审时度势地借用当时社会系统已具有的词汇而另创它词的话,这对当时很多读者的理解能力都是重大的考验。因此,在综合考虑当时语境的意识形态、读者的兴趣和接受度,为加快新概念在当时社会传播的速度和减轻自我创词的压力,积累最初的“economy”汉译文化资本,传教士们采用了时人熟悉的,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富国”一词。
当然,在“economy”汉译场域中,除传教士外,还有另外一个知识分子阶层,那就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是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阵营的代表,如严复、梁启超等。正因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具体化文化资本,使他们占有并享受由此而带来的诸多其他资本,如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等。而这些在权力场域中授予的种种特权,使得他们与那些提出新的符号形式或者赋予现有符号新的意义的提倡者们不断冲突斗争。正如傅敬民指出:“这个阶层在汉语世界的知识场域中处于权威地位,占据着汉语世界中符号解释的权力,他们试图在汉语世界中保持现有的汉语符号秩序与汉语符号再生产秩序。”
面对由日文回译过来的“经济”一词,梁启超和严复是持批评和保留态度的。1899年,梁启超在《时务报》指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偏爱“资生”、“理财”译名,前者谓“赖以生长,赖以生存”之意,后者谓“财产管理”之意。
那么梁氏为什么不使用现成的“经济”译名,而要另译它词呢?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书中,梁氏指出:“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虽日新学,抑亦古谊也。”由此可看出,他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西学此内容,所以沿用“富国学”一词,并另译“资生”和“理财”。译者具体的语言把握能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在译名初创之时,梁氏也很犹豫该用那个译名最合适。“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他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商量合适的译名,但请世人不要笑话他的“举棋不定”,因为都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对他连续使用好几个汉译名的解释。1902年,梁启超出版《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用于介绍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这里,他将经济学又译为“生计学”,他认为我国先秦以前,就有此学了。所以,译者根据自己具体的语言能力和社会局势选择合适译名。
同样,严复在翻译此术语时,也排斥日本的“经济”译名,并另译“计学”以代之,且在《原富》的“译事例言”中阐述如下: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伸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古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经济既嫌太廓,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译“经济”显得概念太宽泛,而译“理财”又太狭窄,所以发挥主体性,选择“计学”的译名。在严复眼里,传播新学,改造国人的世界观是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对汉语内部的各种语言包括古文、通俗文言、白话等作出了慎重选择。”所以,他的翻译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关注“民族生存”、“经世济民”等功用。
当然,当时社会还出现了诸如“世务”、“兴利”、“养名”等“经济”译词。“世务学”中的“世务”,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世情”和“时势”之意,而是汉语典籍里的“谋生治世之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因为它既含政治又有谋生之义。“理财”这个概念也是出自中国典籍,意为“掌握市场价格状况以兴利、生财”。也符合当时士大夫们想要富国强民,国家兴旺发达之意。与“理财”类似的是“兴利”说。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们高举“兴利”和“致富强”的旗帜,采取重商策略,发展国民经济。“养名”或“养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艾约瑟翻译杰文斯的《富国养民策》的影响。那时,“养名”成了西文“econo-my”的译文,不仅涉及生产管理方面,还包含交通贸易等方面。译者都希望通过这些不同“经济”译名的翻译来发展国家经济。
显然,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目的以及其与文化语境取得的互文性成为了翻译操作与文化资本操作的决定性因素。
2.“Economy”汉译的客观化形式
就“economy”汉译而言,其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就是“econo-my”各汉译名的语言符号及相关汉译文本得以保存并在汉语世界中流传开来。不管客观化文化资本以什么形式存在,它必然是物质性的,这点上跟上文的具体化文化资本是有明显不同的。
清末“富国”译名的流行,无不与当时出版的两作品《富国策》和《富国养民策》有关,而且前者还作为同文馆当时富国策课程的经济学教材在当时大量印刷,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正是以“富国”译名为书名作品的出版和流传,使得当时的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了解并且逐渐接受此译名。这就是“economy”汉译名“富国”客观化形式的存在。
上文提及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以及梁启超另一力作《生计学》的出版使得梁氏推崇的“生计”译名流行一时,而且当时《新民丛报》第7号提议使用“生计学”,来对译“econ-omy”,大力倡导“生计”译名。
对应的,严复在当时盛行的《群己权界论》和《原富》的“译事例言”中阐述的“计学”译名,也在某种程度上让这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帮助了“计学”的传播和流行。
再看“经济”译名,起初,很多人似乎不太愿意接受“经济”译名,或许原因在于国人认为它与该词的本义相差甚远吧。而后来,日本“经济”译名的流行,与当时晚清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清末民初,在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下,中国政府开始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并且国人大量翻译日译西书,出现了西—日—中三边的翻译浪潮。这种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强劲。比如,1903年,京师大学堂聘请日本的杉荣三郎为经济学教习,其编写的《经济学讲义》不断刊印,广泛普及了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之后,20世纪初的二十年间,逐渐出现了很多以“经济学”冠名的学术著译作:如李佐庭《经济学》(1907年)、熊元翰《经济学》(1911年)、刘秉麟《经济学》(1919年)。这些客观化文化资本形式的存在也正是导致由日文回译过来的“经济”译名逐渐流行普及的重要因素。
3.“Economy”汉译的制度化形式
“文化资本想要完全实现其价值,还必须使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得到制度的保障。”“Economy”汉译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形式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对“economy”汉译的政府或者官方许可或者默许,也就是通过清朝廷官方的部定或者认定,使得每一次的“economy”汉译取得官方认可获得合法性,并凭借官方本身的权力和权威实施控制。
当年,严复主张以“计学”对译“economy”。尽管梁启超对严复的“计学”译名持不同意见,但1909年清廷设立科学名词编译馆,学部尚书荣庆聘请严复为总纂,“这样译名统一工作就变成了政府行为。”从此,“计学”变成了当时部定的“economy”译名,使得该词成为20世纪起初十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所以客观化资本只有获得了集团一致认可的时候,才真正具备了客观性。这里,“计学”译名的流行正是因为获得了部定这样的制度保障才获得了一致认可。
译名之争不仅仅体现了文化资本的话语争夺,它也是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的诉求。文化资本只有得到社会体制化的保障并且转化为集体性资本才能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再看“经济“译名,此译名的最终确立,除当时诸多经济类文本印刷出版和流传这种客观化资本形式的保障外,更重要的也是得到了制度的保障,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提倡。1912年10月,他在《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中提及“economy”译名时说: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译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
作为民国总统,就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力,为“经济”译名得到政府保障并在中国的最终确立起了一言九鼎的作用。正是“经济”译名自身的妥帖与合适,加之名家倡导和政府部门保障,之后,“经济”成为英文“economy”的通用名。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economy”汉译权力斗争场域中,每个译者都存在着为了权威性、合法性、合理性而进行的对“economy”汉译读者施加控制的斗争,使得每个译名在每个社会阶段都有其存在和流传的原因。
当然,“经济”译名最后能够适者长存下来,方维规还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进行了概念、词源和接受度三方面的研究,认为这三个维度使“经济”这个既包含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含义,又符合19世纪晚期开始流行的简略原则的西方经济学术语译名在翻译界和经济学界屹立不倒。但本文从社会文化语境和资本权力操作的宏观角度进行多维度的剖析,倡导译名统一问题的翻译社会学的解决,能补充历史语义学光从词汇本身的语义、内涵进行单一研究的不足。
四、结语
翻译与文化资本是互动的,前者是后者的载体,也是后者运作的结果。在西学东渐之初,尽管大量西学作品的译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推动了汉语的现代化转型”,但苦于中西语言差异之大,及无相配之名词,需要译者适应社会环境自我创立译名,难怪“economy”一词经历了译名万花筒的过程。而选用什么词来对译“economy”,表面上看起来是译者个人的事情,实际上却是“economy”汉译场域内各方力量对抗、调和的结果,是争夺“economy”汉译这一文化资本拥有权的结果。“E-conomy”汉译就是一个代表着不同利益的译者运用其手握的各种资本进行相互比较、竞争的斗争场所,是译者相互间维持或者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并进行资本再分配的场所。这样的研究对于日后我们引进西方学术术语翻译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异质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冲突的矛盾,从文化资本角度进行深入的社会现象分析。
(责任编辑:章樊)